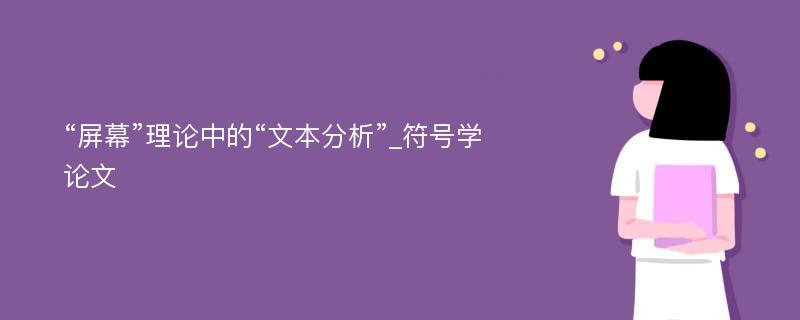
“《银幕》理论”中的“文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幕论文,文本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10)01-0082-08
一、《银幕》与《银幕》理论
《银幕》期刊(Screen)源于英国“电影教师协会”(Society of Film Teachers),1959年协会更名为“电影及电视教育协会”(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Film and Television(SEFT))并发行《银幕教育》期刊(Screen Education)。20世纪60年代,SEFT加入英国电影学院(BFI)教育系①。1969年,期刊整改后以《银幕》为名重新发行。
教育系计划发起一系列关于电影的严肃讨论,逐步发展电影研究的系统理论,使电影理论进入学术体制,成为一门“像音乐、绘画一样”的严肃学科。因此新发行的《银幕》关注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新兴的电影理论的发展,用其时《银幕》的新任编辑凯文·高-叶茨(Kevin Gough-Yates)和特里·博拉斯(Terry Bolas)的话来说,《银幕》将“提供一个研究和讨论电影、电视领域具有争议的问题的论坛”,当时最有“争议”的问题似乎是:电影研究的本质是什么?更直接地说,是否需要独立的电影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存在的依据是什么?这个新生的领域等待着定义,而《银幕》“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给电影研究领域定义”②。
然而这项将电影理论化、学术化的事业并不顺利;BFI学院的领导认为教育系的任务是将现有的电影资源应用到教学中去,以提高整体的电影“教育”水平,其将电影知识普及化、面向实践技术和“大众教育”的方针与教育系将电影理论化、学科化、面向“理论前沿”的方向产生冲突。在压力与妥协下,最初两年里《银幕》主要采取“务实”的方针,对英国本土电影进行“实践批评”,总体上趋于保守。
然而,随着冲突的发展,SEFT最终在行政上脱离BFI,1971年春,《银幕》再次改组,山姆·罗迪(Sam Rohdie)当上主编,杂志开始集中致力于“理论的发展和批评”,“为电影研究的发展建立理论基础”。③自此,《银幕》完全走上了“理论化”的道路。得益于结构主义、符号学、俄国形式主义等理论资源的日益丰富,尤其是列维·施特劳斯、巴特、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在英国的翻译和出版,《银幕》开始在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下自由发展,一方面介绍和讨论欧陆前沿理论和电影研究动态,一方面以批判和吸收的态度将新兴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电影研究。
20世纪70年代,《银幕》体现了三个鲜明的理论影响: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巴特的符号学、拉康的精神分析。《银幕》理论家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巴特、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经由对克里斯汀·麦茨(Christian Metz)的“电影符号学”的观照)、拉康和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判运用于电影理论研究,用《银幕》代表理论家之一史蒂芬·希思(Stephen Heath)的话来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在符号学领域的遭遇理论化”④,在电影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文本分析、精神分析电影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支理论流派被称为“《银幕》理论”,它创建了英国最重要的现代电影理论,深刻影响了现代世界电影理论史。
20世纪70年代,《银幕》理论与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成为英国的理论前沿,二者均脱胎于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不仅有共同的左派政治背景和阶级诉求,而且在理论层面表现出复杂的缠绕与交织关系,这对文化研究派别后来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法介入、“葛兰西转向”等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70年代末、80年代初后,《银幕》理论受到批评,而文化研究中发展的“语境分析”、民族志等更突出历史、社会具体考察的方法兴起,成为对《银幕》理论的一次反拨,昭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以具体替代抽象,以“语境(context)”替代“文本(text)”,以历史、社会考察替代心理考察,以“实际”的观众替代“文本派生”的观众。同时,《银幕》理论时代对文本的意识形态决定作用的过分强调、对主体创造的能动作用及主体对意识形态的抵制可能的相对忽略开始被文化研究更为乐观的抵制与反叛策略所替代,在阿尔都塞与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长久思考后,文化研究通过对葛兰西话语的重新整理,开始确立一套更具动态平衡的论述语言。今天我们对《银幕》理论进行回顾与梳理,意义在于增加对它的理解,同时更好地理解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中某些关键问题。
在电影研究领域,1968年后,“电影政治”、“政治电影”成为一股激流,政治性、理论性的电影研究潮流兴起,以电影为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改变社会的工具”和“催化剂”⑤,《银幕》与法国的《电影笔记》(Cahiers du Cinéma)、《电影评论》(Cinétique)⑥等同为这股潮流中的重要力量。1969年《电影笔记》主编让-路易斯·加莫利(Jean-Louis Comolli)和让·纳伯尼(Jean Narboni)的著名社论《电影/意识形态/批评》可视为这股电影政治潮流的政治和理论纲领,他们首次宣告一种新的激进电影研究的诞生,一方面与传统的主观、经验式的电影批评彻底决裂,倡导以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的现代电影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明确声明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归属,视电影产品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品”⑦,主张通过电影理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识的抵制和反抗。
“现实主义”成为这股政治电影潮流的第一号敌人。“客观再现式”电影忠实地再现了被意识形态渗透的“现实”,而对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置若罔闻,将被“污染”的现实表现为自然的、“本来的”现实,因而被视为主导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银幕》理论家保罗·魏里曼(Paul Willemen)指出,英国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无论是纪录片还是‘自由电影’”,都渗透了“植入的意识形态”⑧,必须摒弃那种将电影屏幕视为“现实之窗”的观念,才有可能打破这种模式。《银幕》理论家尼可拉斯·加汉(Nicholas Garnham)则通过对电视纪录片的“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作用解析,指出电影/纪录片不应伪装成“客观”现实,而应不断展示自己的“人工性”⑨。
20世纪70年代初,《银幕》参与《电影笔记》与《电影评论》对电影政治、电影政治手段等问题的讨论,研究电影政治、意识形态、电影技术等问题,同时研究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将其与六七十年代法、英等国的左派电影政治进行比照考察,对本土电影进行理论批评。20世纪70年代上期,《银幕》花了许多精力研究电影符号学,包括法国的麦茨,英国的彼得·沃伦(Peter Wollen),意大利的乌伯托·艾柯(Umberto Eco),皮埃尔·帕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等人的理论;希思认为,麦茨(等人)的电影符号学联系着以普遍的文化系统和逻辑为对象的普通符号学,其成果亦对后者产生影响⑩,因此,电影符号学为符号学中重要的一支,可与普通符号学一道服务于各种研究领域。如果说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尤其是其意识形态文本分析和“开放文本的创造”等理论对《银幕》理论等的现代主义创作取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巴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与麦茨等的电影符号学则为《银幕》理论增进了“技术分析”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维度。
因此,1971-1974年左右,《银幕》理论主要致力于进入政治电影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时代话语、梳理其时理论界的重要问题并用于本土电影研究等,自70年代中期开始,《银幕》理论则开始收获自己的原创理论成果,其中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以柯林·麦凯布(Colin MacCabe)和史蒂芬·希思为代表的“文本分析”方法。《银幕》理论涉及的内容很多,因为篇幅限制,本文重点讨论这一方法。
二、文本分析方法的运用
(一)“文本分析”概念
《银幕》理论中的“文本分析”概念是一个需要特别指明的狭义概念,它不是传统的文学或美学意义上对某个作品(文学的、电影的等)的“主题”、“内容”或“结构”、“技巧”等进行的(通常感觉经验式、主观的)“点评”、分析,或对作品中传达或隐含的意识形态信息进行提取和读解,而是在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精神分析概念体系中对文本意指实践中意识形态对主体进行定位的机制进行研究。
文本中渗透了意识形态,而文本传达意识形态的机制并非仅局限于——或者说根本不通过其表层结构或“内容”层面内发挥作用(如,一部电影是“反共题材的”或“社会主义改革题材的”,等等),相反,文本中的符号、代码的深层结构方式、文本能指的组织方式、文本建构的现实—想象关系等更深刻地决定文本的意识形态表征和对主体的作用机制:一个故事浮于文本表面,其表层的“虚假叙事”试图传达某种自称的或企图的意识形态,——《银幕》理论对此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故事的深层组织、文本模拟的现实—想象关系是如何将主体自然而然地“结构化”(structurize)、自然而然地“刻写”(inscribe)入一个结构位置——意识形态无意识作用于接受主体、对主体进行定位的方式和机制。左派政治的电影理论首先企图尝试的即是揭露这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将主体刻写入某个位置的隐秘的作用机制,这决定了这里所谓的“文本分析”是:
1.文本意指实践的符号学分析——将文本作为一种“特定的意指实践”来处理,不是内容或文学/美学的分析,而是对文本代码化过程(codification)中的结构特征、文本建构的现实—想象关系进行技术分析(这种分析,借用麦茨的话来说,对于一部爱情电影和一部海军科教短片来说都是一样的(11));
2.是意识形态机制分析——不是阐释或提取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信息”或意义,而是揭露意识形态通过文本的组织方式作用于主体、对主体进行定位的机制;
3.是精神分析式分析——借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对主体建构过程的描述,研究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其表征系统对主体的建构和形成施加影响,社会个体如何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被“召唤”(interpellate)/“刻写”(inscribe)/“缝合”(suture)入某个特定的“主体”位置。
精神分析在这里的作用是双重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理论与拉康的精神分析概念体系时有交叉,前者从后者借用了许多概念,其关于意识形态作用于主体的过程是经由拉康精神分析的“主体理论”机制描述的。
在电影理论(和文化研究)中,关涉阿尔都塞理论的主要部分为其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而其中主要关涉的是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描述为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体现,人们在意识形态中表达的不是他们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是“他们实践他们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方式”,是“人与其现实生存环境之间的现实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一种通过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的实践和生产活动再生产的物质实践,各种仪式、习惯、行为方式以及以实践方式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教育、宗教、家庭等,所有意识形态都具有(通过“召唤”机制)将社会个体塑造为“主体”的功能。阿尔都塞通过从精神分析借入“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结构因果律”(structural causality)、“召唤”、“认同”(identification)、“误认”(misrecognition)等概念,尝试经由拉康的主体理论阐释意识形态作用于主体、塑造主体的过程和方式,提供了一套借用精神分析进行意识形态机制分析的可能话语——《银幕》理论尝试的即是结合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的技术分析的方法,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理论运用于具体的电影实践和行为,研究“电影意识形态机器”对主体的具体作用机制,其目的在于揭露“电影意识形态机器”对主体的“刻写”作用,并寻求一种从根本上打破这一机制的新的激进电影,抵制意识形态通过电影对主体进行的刻写作用,由此创造积极的主体,改变现有的意识形态。
由于在文本能指层面运作,这种“文本分析”方法亦与叙事学、电影叙事学等的领域交叉,后者亦将其纳入叙事学领域的框架内,在这一框架内观察时,这种“文本分析”亦可视为一种“(电影)叙事分析”、“(电影)叙事研究”——但这种称谓(或者说过多的称谓)对于理解《银幕》理论有时会起到干扰作用,《银幕》理论发展的这种“文本分析”虽然涉及许多“叙事学”的项目,但其目的不是单纯为了研究“叙事学”或“电影叙事学”,而是通过对其叙事方式、现实塑造等技术分析,揭露意识形态作用的机制,因此有时那种将它称为“意识形态文本分析”的称谓比“叙事分析”更合适(虽然并不完整)。
本文中暂且概括性地将它称为左派意识形态—符号学—精神分析方法的文本分析,简称“文本分析”。这种“文本分析”为《银幕》理论中最具影响、最经典的原创方法之一,被广泛盗用,其兴起之后在电影理论和其他学术写作中造成了深刻、持久的影响,文化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吸取了这种“文本分析”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将这种意识形态—符号学—精神分析文本分析的方法视为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符号学浪潮的普遍冲击下形成的一种分析趋势,而《银幕》理论在其中则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将这种分析方法提纯、高度技术化,将其完善、使其达到成熟,并透过其高度的影响力将其进一步推广,从而形成这一支富有特色的流派。因此这些特征既构成《银幕》理论的本质特征,也赋予其独立存在的身份意义,使《银幕》理论得以成为一个名词,在理论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其后这种“文本分析”的方法受到颇多质疑、纠正与补充,现在其中的某些要素,如符号学的技术分析等,已成为普遍使用的资源,文本符号学分析、意识形态作用分析、精神分析等也已成为文化研究中多元化方法中的一员,仍然是在一定条件下使用的重要资源之一。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银幕》理论中这种“文本分析”方法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
(二)文本结构分析:《图腾与电影》
1969年初山姆·罗迪发表的文章《图腾与电影》可以说是电影文本分析的初次摸索,是较早将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电影文本分析的一次尝试,不过他的“结构主义”影响主要来自列维·施特劳斯。这篇文章分析了结构主义人类学中图腾神话中使用的代码和结构,讨论了将这种结构分析的方法引入电影研究的可能性,他对卡普拉的《狄兹先生进城》这部电影的“主题结构”—“城市”/“乡村”、“伪善”/“诚实”、“文化”/“自然”、“金钱”/“人情”等及电影的组织和技巧特色进行“结构”式分析,结果发现,这部电影的主题与技巧“平淡无奇”,但这却完全不影响影片本身的“宏伟和风趣”,因此他的结论是,这种结构分析无法回答“这部电影是否是一部好影片”、“其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等问题,所谓的“结构理论”只是把各种社会的、无意识的现象“归结为某种简单的关系”,“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说电影有一个结构”(12),因此他对将“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电影研究提出谨慎的警告,提醒这种方法“目前的不适当性”(13)。
山姆·罗迪将“结构分析”的方法(略显生硬地)套用于电影文本,得出了一个怀疑主义的、谨慎的结论,但是将结构主义方法用于电影文本分析的普遍趋势并未停止,在这些探索中,《电影笔记》编辑部集体创作的《约翰·福特的〈青年林肯〉》电影文本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银幕》理论的“文本分析”方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三)颠覆性读解:《约翰·福特的〈青年林肯〉》
1970年《电影笔记》编辑部集体创作的《约翰·福特的〈青年林肯〉》电影文本分析是一个巴特意义上的“颠覆性读解”的典范。这篇电影文本分析是《电影笔记》集体根据加莫利和纳伯尼提出的批评家的“任务”等“总体纲领”进行的批评实践,通过对福特的《青年林肯》电影的逐段的、颠覆性的解读,将解读本身参与影片意义的创造,揭露了影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作用:影片如何通过直线性、时序性的“现实主义”叙事将林肯的神话“自然化”(14),将林肯塑造为用作判断标准的“一个参照的形象,一个美国的象征”(15)(在福特的一系列影片中一直如此)。指出影片只是“匆匆记叙了几件先后发生的事情”,却“重新塑造了林肯在神话和永恒层次上的历史形象”(16),并且电影记叙的这些事件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事件,而是年轻时当律师的经历、案件、爱情等,不谈林肯介入的政治事件(共和党政治的复杂方面),而表现林肯的“道德品质”,通过道德的话语来传达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宣扬美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天赋人权”,将意识形态与普遍的“善”与“权利”结合。《电影笔记》通过对电影场景的逐段解读、对影片中“自然—法律—女人”的反复主题进行结构分析,揭露了影片中“自然—法律—女人”的主题如何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蔽作用相对应、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
这一文本分析的典范实践了加莫利和纳伯尼所列出的七种电影批评的一种,即在电影的“主题”意识形态与能指/形式层面的间隙之间进行意识形态解读,这种解读的有效性证明,“结构分析”并非如山姆·罗迪所担心的那样,“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说电影有一个结构”,而正是通过对文本的主题结构的“技术分析”,挖掘出潜藏于文本底下的意识形态作用。这种从文本能指出发、对文本进行颠覆性解读的方法给了《银幕》理论极大的启发(17)。
(四)麦凯布:“传统现实主义文本”研究
《银幕》理论原创的“文本分析”传统有两大代表,一为麦凯布的“传统现实主义文本”研究,一为希思的“叙事空间”、“缝合”理论。麦凯布延续巴特的现代主义取向和电影政治流派的反现实主义立场,对现实主义文本进行了意识形态、符号学的分析,研究现实主义文本如何通过隐藏叙事痕迹、使叙事“透明”(18),从而将主体“刻写”入某个意识形态的屈从位置。
麦凯布首先提出一个“传统现实主义文本”(Classic Realistic Text)的概念,这一概念既包括文学文本,也包括电影文本,他先从文学文本入手,解释说,构成文本的话语有若干层次,这种层次是从我们对“真相”的经验主义概念来界定的,简单的来看,可以通过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引号的用法来划分这种话语层次:小说的叙述语言为一个话语层次,小说中各个人物所说的话——小说中用引号围起的部分——为另外的话语层次,他借用巴特的概念,把小说的叙述语言称为“元语言”(Metalanguage),把引号中各个人物所说的话称为“对象语”(Object language),“元语言”判断“对象语”的真实,解释“对象语”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把“对象语”置入引号当中,将其真实性置于可榷商、可阐释的地位,而掩盖自身的“写作”状态,以试图建立叙述话语与现实的直接对等关系。
他以乔治·桑的小说《三月中旬》中的一段为例,布鲁克先生去拜访达格利的农庄,这时我们读到两种语言:一个是布鲁克先生有教养、彬彬有礼但不甚明智的话语,另一个是喝醉了的达格利无教养、粗鲁、几乎无法理解的话语,这两个话语层次均被置于“元语言”的语境当中,接受“元语言”的评价。小说接下来对这两个话语进行了阐释,将二者归入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叙述话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现实”,我们用这个“真正的现实”来对照和评判小说中人物所理解的“现实”。“任何(对象)话语都无法言说自身,其必须置于一个语境当中,该语境将其蜕化为一个简单、可阐释的内容。”(19)“元语言”——未说出、未写出的语言——通过其叙事过程成为主导话语,剥夺了“对象语”话语层次的最终言说权,使其沦为“二级话语”,接受“元语言”的阐释,“元语言”由此获得阐释“真相”的权力,直接代表终极现实。
这一概念模式是否适用于电影文本呢?麦凯布认为,在电影中,看起来似乎主导话语不明显,但是,由于在小说文本中,叙述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因为它处于“知情”的地位,即,只有叙述话语有能力给读者提供“真实的情况”、“真实的现实”,而在电影中,这种处于“知情”地位、执行“提供真相”的功能的,是电影中对发生的事件的叙述——电影对事件的组织和表现,因此,与小说文本的两个话语层次相对应,电影中的两个话语层次即为:电影中各角色的话语与电影的叙事话语。在电影中,充当叙事的是摄影机:摄影机向我们展示发生的事件,向我们提供“真相”,我们根据从摄影机话语所得到的信息来对各角色话语进行判断。譬如,他以帕库拉的电影《克鲁特》为例,影片中多次展示女主角布丽与心理医生谈话的片段,谈及她如何渴望独立生活,而后故事展现的“真正的现实”却是,独立生活的渴望只是心理幻觉,她内心“真正的”渴望是与男主角克鲁特结婚、过普通的家庭生活。尤其在影片结尾,二人收拾行李一同出发,声道中放出布丽与心理医生最后一次谈话,她说自己不会和克鲁特走,而摄影机则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一同出发,她将与他结婚。麦凯布用这个例子说明,在传统现实主义电影中,各角色的话语无法向我们提供真实的现实,摄影机的叙事话语掌握着提供真相的权力,与小说文本中的“元语言”对应。
在传统现实主义文本中,由于叙事话语将自己直接对应终极现实,其具有不容质疑的“真实性”,这种不容质疑性使观众处于一种布莱希特所说的“被动观看”(20)的位置:由于叙事话语已提供了一切“真实情况”,真相一目了然,读者/观众只要安心坐着观看即可,“阅读(观看)主体与现实的关系成为一种纯粹预知(pure specularity)的关系。”(21)由此麦凯布归纳出传统现实主义文本的两个根本特征:1.传统现实主义文本无法将现实表现为矛盾冲突的现实,2.传统现实主义文本的交互运动保证了主体处于一种主导预知(dominant specularity)的关系之中。(22)
即,传统现实主义文本将现实呈现为一种连贯一致、可理解、方便的状态,主体在这种有保证、连贯一致的现实表现中得以以简易、轻松的方式自然进入、并自然认可这一现实话语,这样,传统现实主义文本作为一种“完美的表征”,通过其叙事过程,为读者/观众提供了一个确定不移、没有冲突的现实,将阅读/观看主体纳入一个自然而然地被动接受“现实”(即文本提供的“现实”)、从属的位置,“一种主导预知的关系之中”。
这种消极的表征形式显然最容易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主要机制”,成为传递主导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自然化”的机制,将自己直接表现为无需证明、自然而然的“现实”要素,使主体无戒备地自然接受。麦凯布还讨论了另一种情况:传统现实主义形式的“革命电影”(如“左岸派”、“新浪潮”的一些工人阶级斗争题材的电影,等)。即,文本的主导话语与该时代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相冲突,即一种所谓“进步艺术”,其“主题”是进步的,但麦凯布认为,即使文本的“主题”是进步的,如果它采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形式,这种模式未揭示和打破意识形态作用的根本机制,它无法处理现实冲突,也无法通过更激进的方式来重塑主体与现实的关系,因而(用加莫利和纳伯尼的话来说)是“政治上无效的”。
那么,有效的进步文本是什么样的呢?传统现实主义文本作为一种高度封闭的文本,将自身话语直接表现为对象呈现,而隐藏自身话语的叙述痕迹,将自身话语等同于直接现实,使观众忽略文本话语与真正的现实之间的衔接,因而是服务于、或是无力颠覆主导意识形态的,而有效的进步文本则应该在文本之内,颠覆文本本身的主导话语,文本的主导话语不再是权威的、不容质疑的,而是被颠覆、被质疑的,这样,观众就无法再心安理得地坐着观看了,被打断、不再连贯一致的现实冲突迫使观众进入一个“疑难”位置,使他们陷入困境,现实不再是一目了然、有保证的,他们必须自己思考,自己理解、自己解决这个冲突的现实,从而以积极的主体方式来处理与文本话语及真正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进入布莱希特所说的“积极观看”(23)的状态。
麦凯布将有效的进步文本的颠覆作用分为两个等级:一个等级为对既有文本的颠覆性读解,为“文本中那些挣脱主导话语的因素”(24),即通过对文本的元话语进行解构,打破其意识形态的文本作用机制,从而对文本的意识形态作用进行抵制。他把《电影笔记》对约翰·福特的电影《青年林肯》的那篇著名的分析作为一个典范,这种颠覆“打破了观看主体与对象间永恒的病态的一致性,打开了新的天地—研究联系与差异—欲望的活动”(25)。他肯定罗兰·巴特及《泰凯尔》70年代初以来的研究对这种意识形态抵制策略所具有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个颠覆的等级为更高的等级,它“不是一个不断被打破的主导话语,而是系统地抵制任何这样的主导话语”,即通过直接的颠覆性创作,重新推出新的进步文本型式,从根本上改变“现实主义文本”的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不为观众提供一个文本主导话语,而迫使观众自己进入电影(26)。
麦凯布进而讨论了电影中“革命的文本”和“反动的文本”,他认为,布莱希特电影之所以为“革命的文本”,不是仅仅在于对主体的颠覆或对另种不同的(“正确的”)身份的表征,而包括在意识形态内将主体置换,以另种方式重新建构主体。通过迫使观众自己进入电影、自己生产电影的意义,重新建构观看主体与虚构材料及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意即,主体通过辨别“虚构的现实”与“真正的现实”之间的区别,重新建立自身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其有能力辨认和抵制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主体亦在此过程中重新建立自己的身份。他批评他所称的“反动的文本”——一种对布莱希特电影庸俗化的理解和拙劣模仿,如英国林赛·安德森等的电影,将布莱希特简单理解为嘲笑当代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讽刺主义,忽视其中“生产性的”(政治的)因素,纯粹搬弄“陌生化”技巧,通过表层的技巧模仿传达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27)。
(五)希思:文本“叙事空间”与“缝合”
希思作为《银幕》理论最重要、与《银幕》理论关系最为紧密的理论家之一,在《银幕》理论的各个阶段起着总结和统领的作用。希思著作丰富,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对电影“叙事空间”、“缝合”等问题的研究,代表著作包括1981年出版的《电影中的问题》等。他对电影文本叙事空间的建构过程和电影意识形态机器对主体的定位作用关系进行了心理层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成为《银幕》理论的“文本分析”传统中重要的代表成果之一。他的研究中显露出更多精神分析方法的影响,并更侧重文本结构的“过程”——而非将文本处理为一个封闭、静态的系统,因而具有更多后结构主义特征。
希思研究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空间的建构过程和特征,并由此揭露其中的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定位机制的运作。首先他将“动态的”的电影与15世纪“静态的”绘画进行比较,通过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指南”与好莱坞的“电影技巧指南”进行有趣的对比,比较考察了绘画与电影各自的形式特质。他采用符号学的方法,将古典电影(classical cinema)(28)作为一种“具体的表意实践”来研究,着重比较绘画中的静态画面与电影故事中的画面运动和动作表达,意图揭示电影通过一幅幅的画面来创造自身的叙事空间的奥秘。
希思认为,古典电影的表征代码采取的是一种15世纪的绘画空间模式,二者均依赖一种“中心透视系统”。如,在平面上描绘三维物体,使物体在画面上看起来与真实物体一样,使观者产生一种“真实”的幻觉,这要求观者满足两个条件:1.观看者只能用一只眼睛,2.眼睛必须放在透视的中点(29)。这一空间模式成为一直以来的主导模式,“五个世纪以来人们安于该空间,忠于中心透视图像”(30)。古典电影采取的也是这种“单向透视”,由于这种透视模式给人带来习以为常的真实感,使观看主体处于一个确定的视角,从而自然而然地对摄像机提供的内容进行认同。
而电影为“运动的图画”,运动——尤其是人体的运动——意味着动态的过程和变化,古典绘画传统中尝试的是通过画框内的构图来表现“运动”,而在运动的画面(电影)中,人物总是似乎要走出影框的画面范围,而其越运动,越需被保留在画面之内——因此电影必须通过“叙事化”(Narrativisation)手段来对运动进行处理,因为运动可能在视点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影响画面的清晰度。因此在电影叙事空间中:“受此影响的(画面)过渡尖锐地提出电影空间建构的问题,及如何取得空间的连贯、并将观者定位为一个既被其视图统一、又统一其视图的主体”(31)。也就是说,电影必须通过一系列手段进行叙事处理,控制画面的运动关系并对其进行合理分配,从而为观众营造一种“自然”、合理、可信的故事空间和叙事逻辑,以使观众可以保持在作为一个“连贯”、完整的“主体”的幻觉当中。
于是,电影采取了一系列“叙事化”手段来实现叙事空间的建构,这些手段包括如“电影指南”中的“建议方法”:主场景镜头(master shot)的使用,180度角规则(画面不超过180度角的视线范围,与人的视觉范围相符)、30度角规则(一般镜头的一次性移动不宜超过30度角,否则画面给人跳跃感),动作配合、视线对接、场/反场(一个镜头之后以逆镜的一个镜头相配合以使画面叙事完整可信),避免“不可能”的角度(即对于观众的视角来说不“现实”)、违反视觉常规和视觉心理惯势的角度,角度拍摄整合,声道跟进图像等。传统电影通过这些具体的拍摄、拼接规则和电影剪切、画面加工等编辑手段来对其叙事进行控制,并通过这些叙事控制,营造电影叙事中的虚拟空间——一种“真实的”幻觉——“自然剪切意味着将两个镜头拼接,而使其过渡不致造成明显的拉扯/错位,使观众可以保持在认为这是一系列连续动作的幻觉里”(32)。
希思认为,叙事空间通过“能指对所指的影响”起作用,传统电影并未抹去生产的符号(与麦凯布所称传统文本的叙事“透明”不同),而是通过“叙事化”手段来“抑制”它,叙事空间企图建立一个过程的概念,以对主体的位置进行处理和抑制。这就是说,传统电影中的一系列叙事手段(“自然剪切”、拍摄规则、剪辑处理等)都是为了使画面的运动看起来“自然而然”,使观者产生真实感和认同,从而能保持处于一个将电影认同为真实、连贯、完整的观看位置,并保持自己的想象性完整的主体身份。
根据拉康的主体理论,当婴儿进入语言体系、成为“儿童”,即共同遭遇一种永远的缺乏、失去、缺席的状态,这种缺席的初始不断重建主体、创造主体、成为主体,而主体必须主动否认和推卸缺乏与缺席,从而为自己营造一种稳定性、一种在场,并创造自我,由此使主体从中而出、在主体获得“我”的位置的象征秩序中获得一种想象身份——在此过程中,以稳定替代“运动”,以在场替代缺席,以想象替代象征,前者基于后者、从后者而来但高于后者、取代后者。拉康将这种合并称为“缝合”(Suture)(33)。希思用拉康的“缝合”概念来理解电影叙事空间如何为缺席的观者寻找一种连贯性/内在统一:“在电影的运动、画框、剪切、间歇中,电影不断地制造缺席、缺乏,又不断地填补这种缺席,这一过程通过电影空间的实现将观者绑定在一个主体的位置”(34)。这样,在这一过程中,这种“缝合”的运作不断“提供和提取缺席和在场,玩弄否定与撤销、流动与绑定”,将观者置于一个不断获得想象性完整的主体位置。传统电影通过给观众提供一种想象性完整,隐藏其生产过程,从而将主体定位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位置,而相反,先锋电影却通过展示、再创造其叙事空间代码,提供了一种激进电影的可能。
(六)“文本分析”方法
麦凯布与希思的这种研究为《银幕》理论中这种“文本分析”方法的代表版本,其共同特征在于通过对现实主义电影文本的话语和意指实践进行技术分析,指出其中意识形态通过“现实感”、“自然化”等机制使主体进入电影文本营造的“现实”话语,从而使主体对文本中渗透的意识形态进行无意识的认同。
在此分析下,意识形态必然是经过现实主义来作用的,因此要对这种意识形态机制进行抵制,就必须摒弃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在后来的多次辩论中,二人也不断修正过自己早期的某些观点,但在总体上,这种“文本分析”的方法呈现出鲜明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影响,并从精神分析的视点切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未能充分阐释、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试图论述的领域——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对电影文本的符号学分析和主体与现实的关系及主体自我建构的精神机制的阐述,研究意识形态如何将主体“刻写”/“缝合”入一个意识形态结构位置,从而揭露主流电影为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服务的作用机制。针对主流电影这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刻写”/“缝合”作用,《银幕》的理论家们倾向的解决方案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先锋艺术”和“现代主义”,但似乎他们不喜欢“先锋艺术”这个词,因为在特定的时期它曾用来指称之前某些特定流派,对《银幕》理论来说,真正有效的是延续布莱希特传统(35),从根本上破坏主导意识形态作用的机制,推出全新的、揭露和颠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进步艺术形式,从而使观众无法再处于一个放松、认同、被无意识地“刻写”/“缝合”的被动位置,而通过更“革命的”文本组织方式将观众置于一个“困难的”、被迫思考、寻求解决方法的积极位置。
“文本分析”方法既是《银幕》理论的最具影响力的部分之一,同时也受到众多质疑和争议,包括在《银幕》内部引起的争议和反思。这种“文本分析”方法在《银幕》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见"History",in Screen,http://www.screen.arts.gla.ac.uk/pages/history.html.
②"History",in Screen,http://www.screen.arts.gla.ac.uk/pages/history.html.
③Ellis,J.(1977)"Introduction",in SEFT.(1977)Screen Reader 1:Cinema/Ideology/Politics,SEFT,p.vi.
④Heath,S.(1981)Questions of Cinema,London:Macmillan,p.201.
⑤Garnham,N.(1971)"TV Documentary and Ideology",in SEFT.(1977)Screen Reader 1:Cinema/Ideology/Politics,SEFT,p.61.
⑥Cahiers du Cinéma Cinema,巴赞创办,致力于电影研究的理论化,为电影研究进入法国学术界奠定了基础。巴赞聚集了(养子)弗朗索瓦·特吕弗等一批“新浪潮”代表的年青电影人——多为“作者论”的倡导者,1958年巴赞死后,杂志更加政治化、理论化。Cinétique,与《电影笔记》同时的另一重要法国激进左派电影期刊。
⑦Comolli,J.and Narboni,J.(1969)"Cinema/Ideology/Criticism",in SEFT.(1977)Screen Reader 1:Cinema/Ideology/Politics,SEFT,p.3.
⑧Willemen,P.(1971)"On Realism in the Cinema",in SEFT.(1977)Screen Reader 1:Cinema/Ideology/Politics,SEFT,p.51.
⑨Garnham,N.(1971)"TV Documentary and Ideology",in SEFT.(1977)Screen Reader 1:Cinema/Ideology/Politics,SEFT,p.60.
⑩见 Heath,S.(1973)"The Work of Christian Metz",in SEFT.(1981)Screen Reader 2:Cinema & Semiotics,SEFT,pp.139—161.
(11)克里斯汀·麦茨,《电影语言》,引自Brewster,B.(1971)"Structuralism in Film Criticism",in SEFT.(1981 Screen Reader 2:Cinema & Semiotics,SEFF,p.8.
(12)山姆·罗迪:《图腾与电影》,引自《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李幼蒸,三联书店,p.125.
(13)同上,p.118.
(14)The Editors of Cahiers du Cinema(1970)"John Ford's Young Mr Lincoln",in SEFT.(1981)Screen Reader 2:Cinema & Semiotics,SEFT,p.123.
(15)同上,p.121.
(16)同上。
(17)《银幕》对这篇文章的讨论,见Wollen,P.(1970)"Afterword",Brewster,B.(1973)"Notes on the Text 'John Ford's Young Mr Lincoln' by the Editors of Cahiers du Cinéma",in SEFT.(1981)Screen Reader 2:Cinema & Semiotics,SEFT,pp.152—171.
(18)MacCabe,C.(1985)Theoretical Essay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35.
(19)MacCabe,C.(1974)"Realism and the Cinema:Notes on Some Brechtian Theses,初载《银幕》1974年15期2号刊,引自 Hollows,J.et al.(eds)(2000)The Film Studies Reader,Oxford Unversity Press,p.202.
(20)见Jameson,F.(1998)Brecht and Method,London,New York:Verso,p.107.
(21)MacCabe,C.(1974)"Realism and the Cinema:Notes on Some Brechtian Theses",引自 Hollows,J.et al.(eds)(2000)The Film Studies Reader,Oxford Unversity Press,p.203.
(22)MacCabe,C.(1974)"Realism and the Cinema:Notes on Some Brechtian Theses",引自Hollows,J.et al.(eds)(2000)The Film Studies Reader,Oxford Unversity Press,p.203.
(23)见Jameson,F.(1998)Brecht and Method,London,New York:Verso,p.107.
(24)MacCabe,C.(1974)'Realism and the Cinema:Notes on Some Brechtian Theses',引自Hollows,J.et al.(eds)(2000)The Film Studies Reader,Oxford Unversity Press,p.204.
(25)同上。
(26)麦凯布以罗伯特·罗西里尼的电影《德意志零年》为例,观众无法在一个确定的位置来观看这部影片,电影的叙事话语未偏向任何一个角色话语,叙事话语未统治对象语、使其服从一个主导话语,亦未以“知情者”的身份向观众提供“正确的”信息以便其对对象语作出判断,电影未提供观众进入电影的方式,观众必须自己进入电影。他认为罗西里尼的局限在于无法表现冲突的现实,摄影机只提供确定不疑的事物,未成为电影生产性环节的一部分。但罗西里尼仍代表尚未有人超越的高度(除戈达尔早期几部之外),要超越他必须寻求表达冲突的方式,如在小说中詹姆斯·乔依斯通过研究语言的不同形式来研究现实冲突,电影也可以通过进一步开发摄影机的作用,寻求一种比罗西里尼更激进的颠覆策略。
(27)MacCabe,C.(1974)"Realism and the Cinema:Notes on Some Brechtian Theses",引自Hollows,J.et al.(eds)(2000)The Film Studies Reader,Oxford Unversity Press,p.206.
(28)因麦凯布使用的“现实主义”一词引发各种争议,希思避开这一敏感用词,据一般习惯称(好莱坞)古典电影。
(29)Heath,S.(1976)"Narrative Space",初载《银幕》1976年17期,引自Heath,S.(1981)Questions of Cinema,London:Macmillan,p.28.
(30)同上,p.29.
(31)同上。
(32)Heath,S.(1976)"Narrative Space",引自Heath,S.(1981)Questions of Cinema,London:Macmillan,p.57.
(33)“缝合”概念来自拉康,为其最早在1965年一个研讨会中简要提出。后雅克-阿兰·米勒将其论述为一个概念,并以《缝合—能指逻辑要素》为题发表在《银幕》,将其定义为主体与能指链的关系。拉康反对这篇文章,在《科学与真理》中提到它,并采取一个完全相反的立场,不把缝合视为主体与能指链条的封闭关系,而强调其开放性,认为“科学无法缝合或生产主体完整的形式化”,拉康的主体是开放、模糊、模棱两可、无法驾驭的。60年代,让·皮埃尔·乌达尔在《电影手册》上讨论电影的缝合机制,认为电影屏幕首先为主体制造快乐,观者沉浸于画面的想象性误识中,与镜像阶段的经历类似,但当观者意识到画框的存在时,象征侵入想象,这种意识使观者焦虑,因其不确定描述的是谁的视角,其威胁打破电影幻觉,这一威胁本来被传统的镜头/逆镜拍摄机制阻止,通过下一个镜头使前一个镜头显示为某个角色的视角,这样就保持了完整性的幻觉,使观者得以保持在其窥淫的位置。后齐泽克也批评了封闭的“缝合”概念,认为“结构的鸿沟、开口被抹去,使结构将自身理解(误解)为一种自我封闭的整体主义表征”。
(34)Heath,S.(1976)"Narrative Space",引自Heath,S.(1981)Questions of Cinema,London:Macmillan,p.59.
(35)布莱希特与表现主义对英国现代主义起了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影响的更多描述,可参见Williams,R.(1989)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London:Ver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