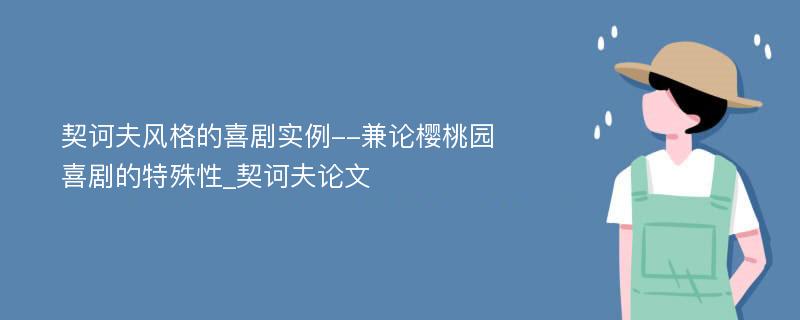
“契诃夫式”的喜剧范例——论《樱桃园》的喜剧特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喜剧论文,特殊性论文,范例论文,契诃夫论文,樱桃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樱桃园》是一部“契诃夫式”的新型现代喜剧。《樱桃园》用维持平衡状态这种特殊的推进方式,展示了无动作性的主人公与永恒变动着的时间之间的特殊的喜剧冲突;塑造了“与众不同”的喜剧人物;抛弃了巧合、误会、夸张等传统的喜剧手法,而采用气氛性布景、气氛性音乐舞蹈、气氛性人物等方法来营造笼罩全剧的喜剧气氛。《樱桃园》是契诃夫把喜剧改造成“高尚的体裁”的成功实践。
关键词 契诃夫 戏剧革新 喜剧冲突 喜剧角色 喜剧手法 喜剧的高级阶段
在人类文化史上,富于独创的天才不被理解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契诃夫富于独创性的戏剧作品同样遭遇过种种曲解。
《樱桃园》是喜剧,还是悲剧,抑或正剧?自它面世伊始,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契诃夫本人强调《樱桃园》是一部喜剧。1903年9月2日,他在致丹钦科的信中谈到:“我把这个剧本定为喜剧。[(1)]”13天后,他又写信给阿列克塞耶娃说:“我写出来的剧本不是正剧,而是喜剧,有些地方甚至是闹剧。[(2)]”与此相一致,契诃夫一再坚持《樱桃园》的男女主人公一定要由专业喜剧演员来扮演。可是,同年10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读完《樱桃园》的手稿后,欣喜之余,立刻写信告诉契诃夫:“不管你对最后一幕有什么样的解答,它决不是一个喜剧或是一个滑稽剧,如你所写的,而是一个悲剧。[(3)]”几个月以后,契诃夫溘逝,作为创造者,他来不及也没有责任从理论上阐述《樱桃园》的喜剧性。从此,对于《樱桃园》,学术界见仁见智,各执一端。说喜剧者有之,言悲剧者有之,谈正剧者亦有之。说喜剧者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叶尔米洛夫。叶氏用传统喜剧理论来印证《樱桃园》的喜剧性。然而,《樱桃园》不是一出传统意义的喜剧。它没有一波三折的喜剧性冲突,没有夸张怪癖的主要人物,没有巧合、误会等常见的喜剧手法,也没有好事终成的大团圆结局。因此,叶氏的研究成果仍有令人难以诚服之处。以至到了本世纪后期,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还态度暧昧地认为:“《樱桃园》这出戏,既可以作为喜剧,也可以作为悲剧来处理。[(4)]”可见,《樱桃园》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任何一个导演在排演这出经典名剧时必须面对的一个实践问题。
笔者认为,契诃夫是伟大的戏剧革新家。《樱桃园》是新型的现代喜剧。传统戏剧往往表现那些不属于日常生活的离奇事物,剧作家们常常让戏剧在生活之流冲决了日常堤坝的时候开始,也让戏剧在生活之流回归日常堤坝的时候结束。而契诃夫则认为人生伟大的戏剧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底层下面。他说:“人们要求说,应该有男男女女的英雄和舞台效果。可是话说回来,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说聪明话……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吃饭,谈天气,打牌……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作家需要这样写而是因为现实生活里本来就是这样。[(5)]”因此,契诃夫偏偏在传统喜剧还没有开始和已经结束的地方——日常生活的缓缓平流中开始了自己的喜剧。于是,在《樱桃园》里,喜剧性被赋予了“契诃夫式”的新的独特的内涵。
一
冲突是戏剧的基础。描写什么样的冲突,怎样展开冲突,直接决定着戏剧的艺术价值,也体现出剧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审美意念。《樱桃园》的主题是揭示封建贵族的衰亡。这样的主题,在西欧和俄国其他剧作家的笔下往往是通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封建贵族代表人物的正面交锋来表现的。《樱桃园》也设置了两个对立阶级的代表人物,这就是代表封建贵族阶级的柳鲍芙兄妹和代表资产阶级的罗巴辛。本来,契诃夫可以正面展开他们之间的冲突,写一出惊天动地、有声有色的戏剧。但他没有这样做。在《樱桃园》中,柳鲍芙兄妹同罗巴辛不但没有展开直接的正面的冲突,而且恰恰相反,从私人关系看,他们还是十分亲密的朋友。契诃夫不但没有描写罗巴辛如何处心积虑、阴险狠毒地去夺取柳鲍芙兄妹的财富,而且恰恰相反,还表现了罗巴辛如何知恩戴德地企图帮助柳鲍芙兄妹保住家产。那么,与柳鲍芙们构成正面冲突的是什么呢?是时间。在《樱桃园》中,时间是一个没有形体却处处可见的主角。剧作家通过剧中人物的口不厌其烦地反复谈到樱桃园的拍卖日期,强调了这个主角的存在:
“这片地产到八月就要拍卖了。”
“你的樱桃园就要被扣押,在八月二十二日拍卖了。”
“一到八月二十二日,这座樱桃园,连这一带的地产,可就全部都要拍卖出去了。赶快下个决心吧!”
“你非得最后下一次决心不可了,时间是什么都不等的呀。”
“让我再提醒你们一句,八月二十二,樱桃园可就要拍卖了,想想这个,好好地想想这个!”
通过这种以加强和凸现为目的的反复,剧作家给观众造成了时间正在向柳鲍芙们一步步逼过来的感觉,暗示出了时间和喜剧主人公的冲突。接下去,八月二十二日来了,时间一到,樱桃园立即被拍卖了。买下它的不是别人,而正是罗巴辛,正是把柳鲍芙当恩主,苦口婆心地提醒她,真心实意地为她出谋划策,企图救她于危难之中的罗巴辛。作家这样安排,就是为了强调与柳鲍芙们构成对立面的,决不是某个对他们不怀好意的个人,而是代表了当时历史前进方向的资产阶级。是时间,是历史,把封建贵族阶级推下了社会舞台。
特殊的冲突必有特殊的推进方式。在传统戏剧里,冲突由一系列平衡状态的变化来推进,从而达到戏剧的高潮——平衡状态被最大限度地扰乱;平衡状态的每一次变化就构成一个动作;一出戏就是一个动作体系。而《樱桃园》的冲突运动却恰恰是由一系列平衡状态的维持来推进并达到高潮的。在这里,动作有了与传统戏剧完全不同的内涵。我们看到,《樱桃园》喜剧主角的最强烈的动作恰恰就是不动不作。尽管他们把樱桃园说成是自己的生命,可面临它即将被拍卖的严重情势,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挽回这种局面的行动。在第一幕里,罗巴辛就认真地向柳鲍芙兄妹提出了一个和时间争夺樱桃园的有效行动方案,却立刻被加耶夫斥之为“废话”,柳鲍芙则宁肯去向老仆人费尔斯打听那个毫无用处的炮制干樱桃的秘方儿,也不愿去想想罗巴辛的建议。到了第二幕,当罗巴辛催促他们下决心行动,并恳求他们采纳自己的建议时,柳鲍芙的态度却是如此漠然:“‘是谁在这儿抽这种怪难闻的雪茄呀?’(坐下)”,加耶夫的反应更加冷淡:“(打哈欠)‘说谁?’”和他们在第一幕的态度一模一样,毫无变化,连“干还是不干”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强烈的内心冲突都没有过。正是主人公的不动不作,喜剧冲突才推进到了第三幕的高潮。在这个高潮里,尽管喜剧主人公所处的情势急转直下,而他们自己却仍然是没有行动和变化的,就连他们的内心痛苦也是虚假造作的。表面上,柳鲍芙象一个蹩脚的悲剧演员一样夸张地喊着:“要是丢了樱桃园,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当樱桃园被拍卖的消息传来,她虽然故作姿态地喊了一声,“真把我急死了,”可是在内心深处,在下意识里,她并没有把樱桃园的命运放在心上,就连老仆人费尔斯为此而痛苦得变色的感情都不能理解,她问费尔斯,“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你觉得不舒服?去躺下睡睡去。”是的,费尔斯该去睡睡了,而我们可爱的柳鲍芙并不需要去睡;她不但没有什么不舒服,还悠悠然地和皮希克跳起了华尔兹舞。而加耶夫呢,当他到城里参加拍卖回来,柳鲍芙向他问及樱桃园的命运时:
加耶夫:(没有回答)做了个厌倦的手势,哭着向费尔斯:“来,接过去……这是些糟白鱼,和凯尔契出产的青鱼。我这一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台球室门开着,从里边传出台球相撞声和雅沙的说话声:“七比十八”加耶夫的脸上的表情起变化,他不再哭了。)
尽管他看着樱桃园被拍卖了,却没有忘记买鱼;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不为丧失全部家产而流泪,却为没吃上一顿饭而痛苦;更意味深长的是,使他停止哭泣的是什么呢?台球的撞击声!他看重什么东西,青鱼、台球、还是樱桃园?他真为樱桃园的丧失而痛苦吗?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在第三幕里,柳鲍芙和加耶夫对樱桃园的态度和他们在第一、二幕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呢?仍然是那样等闲视之,戏谑为之,漠不关心,不动不作。以前也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樱桃园》喜剧主人公无动作性的特点(如劳逊等),但他们没有解释契诃夫怎么能用这些“无动作”的主人公组织戏剧冲突。抓住了时间是剧中的一个主角,是冲突的一个对立面这一特点,我们才能明白契诃夫赋予主人公无动作性特点的匠心:只有这些不变不动的人物才能和永恒变动着的时间构成矛盾,在这种变与不变、动与不动的矛盾中存在着最激烈的戏剧冲突。
那么,为什么说《樱桃园》展现的这种冲突是喜剧性的冲突呢?马克斯曾经深刻地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6)]”《樱桃园》展现的正是这种现实历史中的喜剧性冲突。《樱桃园》写于1904年,正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前夜。列宁曾经指出:“1862年到1904年这一时期,俄国正处于这样的变革时代,这时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则刚刚开始安排,而建立这种制度的社会力量,直到1905年才第一次在辽阔的全国范围内真正表现出来。[(7)]”这段时期的俄国历史是喜剧性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了,俄国的政治制度还是极其陈腐的封建君主制度,这种旧制度大大低于世界历史的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历史储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8)]”,在欧洲各国人民的眼中也已经过时,已经崩溃了。但因为“新的东西”还“刚刚开始安排”,还没有及时取代这些“旧的东西”,因此,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的旧制度仍然装模作样地继续充当俄国历史的主角,自然,它也只能是“早已过时”的历史喜剧中的滑稽主角了。在《樱桃园》里,契诃夫正是用封建贵族与时间的冲突,高度概括地反映了这段喜剧性的俄国现实历史。时间,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也是人的个性世界、社会心理世界和人类历史世界的对象。在时间定义背后,不仅隐藏着世界本身的种种抽象概念,而且隐藏着人的存在、人同世界的关系,以致某个社会集团、某种社会力量、某种社会形态同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样非抽象的概念。因此,通过直接描写封建贵族与时间的喜剧性冲突,《樱桃园》就反映了现实历史中的喜剧,并且通过这一冲突,嘲笑了早已过时的封建制度和早已过时的封建贵族,表现了封建制度和封建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重大主题,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不可遏制的正向运动。
二
传统的喜剧角色不外乎两大类:正面喜剧人物和反面喜剧人物。前者如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等等。他们是时代的先进,才智过人,充满活力,以幽默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后者则是最普遍最典型的喜剧形象。公元前三百多年,亚里斯多德就指出:“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9)]”在欧洲戏剧史上,从古希腊的阿里斯多芬到古罗马的普劳图斯,从法国的莫里哀、博马舍到俄国的果戈理,他们的传世之作都塑造了这类“坏的”喜剧角色。而契诃夫不满于走前人走过的老路,他说:“我要与众不同;不描写一个坏蛋,也不描写一个天使。[(10)]”《樱桃园》塑造的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喜剧角色。
《樱桃园》的喜剧主人公是柳鲍芙。这个女人显然不属于正面喜剧人物之类:她没有鲍西娅们的聪明机智,更缺乏薇奥拉们那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但也不能把柳鲍芙简单地归入坏人之列。与伪君子答尔丢夫比,我们说她坦率单纯;与吝啬鬼阿巴公比,我们看到她慷慨之极;与鱼肉百姓的安东·安东诺维奇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她相当善良。柳鲍芙是一个“契诃夫式”的喜剧人物。
柳鲍芙的喜剧性首先表现在她缺乏最起码的现实感和正常的时间感。作为末代贵族的代表,柳鲍芙不仅丧失了任何创造生活的能力,而且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现实的生存能力,她一生所干的除了“瞎糟蹋钱”,还是瞎糟蹋钱。喜剧开始时,她已经花光了祖宗的遗产,欠债累累,连利息都无力偿还了。可她仍然进豪华的餐馆,仍然点最昂贵菜肴,仍然雇请乐队来家里举办舞会,仍然随意地把金币施舍给路人。面临丧失家园的威胁,她只知道一味地沉溺于对过去、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之中。她完全不懂现在,完全不懂现实。这使她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樱桃园。樱桃园是人类过去时间在大自然的实体之中的沉淀和凝聚,它以物的方式,以人化了的大自然的方式,肯定了人类过去的实践,象征着过去时间的诗意。但是,当时间前进到了现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无产阶级已经崛起的“现在”,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为人类现在时间的实践所否定而成为滑稽的对象。在资产者罗巴辛眼里,它只能被砍倒,用这块地皮来建别墅;在面向未来的大学生特罗费莫夫看来,它不但没有旧日的诗意,而且已经是一个十足的丑角了。他说:“你想想看,安尼雅,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和所有你的前辈祖先,都是封建地主,都是农奴所有者,都占有过活的灵魂。那些不幸的人类灵魂,都从园子里的每一棵樱桃树,每一片叶子和每一个树干的背后向你望着……啊,这够多么可怕呀!”樱桃园的美是用千百万农奴的血浸润出来的假美,它用美的面纱掩饰自己的丑。而柳鲍芙看不见这种丑,她把这个丑物奉为全省之内“唯一值得注意,甚至是出色的东西”。在她眼里,樱桃园从过去到现在“一点也没有改样儿”,仍然是那么“年轻”,仍然是那样“充满幸福”,所以她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罗巴辛砍掉樱桃园,把地皮租给别人盖别墅的建议。她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固执地用过去的眼光认识和判断现在,充分相信过去,一心一意地追求过去的一切。在前进了的人类时间中,樱桃园明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明明已经堕落成了历史喜剧中的丑角,柳鲍芙却硬要把它奉为权威;樱桃园的那种带有血腥味的诗意,以及由这种诗意所代表的过去贵族生活的一切法则,明明已经脱离了现在生活的常态,她却硬要让它们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庄重,并据此来与无比强大、不可逆转的时间对抗。这种情形同著名的堂·吉诃德骑士硬要把自己奇丑无比的意中人当成天下第一美女,硬要不自量力地挥舞长矛同风车搏斗的喜剧又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啊!
柳鲍芙的喜剧性还表现在精神空虚堕落却又自诩高雅美好。精神空虚堕落,这便是本质的丑。但仅仅是丑还不能构成喜剧性格,“只有在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丑才变成了滑稽。[(11)]”因此,剧作家在塑造喜剧人物时,必须在其后面安上一面同舞台的第四面墙同样大小的镜子,一方面让其面对观众尽情地张开那一根根插在身上的孔雀羽毛,另一方面则让他们藏在孔雀羽毛后面的乌鸦尾巴在这面镜子里暴露无遗,使观众毫不费力地看清其乌鸦本质,而嘲笑其顾头不顾腚的笨拙表演。在《樱桃园》中,剧作家主要是用“巴黎”这个意象来充当这面镜子,从而照出柳鲍芙的真正的精神价值的。柳鲍芙在观众面前张开的孔雀羽毛是“祖国”,她登台不久,就充满激情地向人们表白:“上帝知道,我爱我的祖国,我真爱得厉害呀,我一路上只要往窗子外面一看,就得哭。”当瓦里雅把两封来自巴黎的电报交给她时,她没有读就把它撕碎了,声明“我跟巴黎的缘分已经断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俨然是一个爱国者。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言谈中,在她暂时忘记自己乔装的角色时,她灵魂深处的思想就常常脱口而出,祖国立刻让位于巴黎。第二幕,她出场不久就抱怨:“我为什么要跑到城里去吃这顿中饭呢?你们这儿的饭馆可真叫人讨厌死了,还有那种难听的音乐,那种一股胰子味儿的桌布。”这里边包含了多么丰富的潜台词啊!从“你们这儿”的后面,我们不难听见她思想深处的隐语:你们俄罗斯这儿的饭馆可真叫人讨厌死了,而我们巴黎那儿的饭馆可叫人喜欢死了;你们俄罗斯这儿的音乐难听极了,而我们巴黎那儿的音乐好听极了……一个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为“你们”的人,骨髓里能有几戈比爱国主义呢?接下去,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几段关于祖国和巴黎的台词: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我忽然怀念起俄国,怀念起自己的祖国,怀念起我的女儿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来)我今天接到这封从巴黎发来的电报……他求我饶恕他,请我回去……(把电报撕碎了)我听着好象远处有音乐吧?”(倾听)
加耶夫:“这就是我们这儿那个著名的犹太乐队……”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这个乐队还在呀?哪天咱们得请他们来一次,开个小小的晚会。”
罗巴辛:(倾听)“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哪。(低唱)为了一笔钱,德国人会把俄国人变成法国人。(笑)昨天晚上,我在戏园子里看了一出非常滑稽的戏,滑稽得要命!”
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柳鲍芙谈到的远处的音乐实际上有没有?导演是否应该在舞台空间安排“远处有音乐”这个音响效果?第二,罗巴辛的后两句台词与前面的对话有什么内在联系?这两句台词在剧情发展中有什么作用?这两个问题看起来细小,认真思考一下,便会觉得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只有把它弄明白了,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柳鲍芙的性格特征,更深刻地理解后一幕剧情发展。远处是否有音乐?对这个问题,剧中的三个人物有三种说法。柳鲍芙一开始提起时,只是“听着好象远处有音乐”,用了“好象”这个无定性的词。加耶夫倒是肯定了有音乐,但他的话明显地只是附和柳鲍芙,况且,他的性格特征是神不守舍,常胡言乱语,所以他的话是不能当真的。那么只有罗巴辛的话才是确实可信的了,而罗巴辛却明明白白地否定了音乐的存在。既然实际上外界并没有响起音乐,柳鲍芙怎么会突然从电报扯到音乐上呢?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联想。联系前言后语,便不难发现,巴黎在她的潜意识中占了多么重要的位置。柳鲍芙这一大段台词,主要是回忆巴黎,回忆她和“他”在法国所过的荒唐生活。在这里,她虽然第二次撕碎了电报,但这封电报已经把她带回了巴黎,她内心充满着巴黎的生活,巴黎的情夫,巴黎的音乐。她是那样如醉如痴,以致进入了一个幻想的境界,以为真的听见巴黎的音乐了。巴黎是她内心深处的音乐。正是这“音乐”使她萌发了请乐队来家开晚会的念头;正是这“音乐”使她忘记了俄罗斯,忘记了樱桃园,使她漫不经心地将舞会的日期选在八月二十二日。有了“这音乐”,剧情才能发展到第三幕的舞会。在樱桃园拍卖的日子里,在舞台上,柳鲍芙是踏着巴黎的音乐翩翩起舞的。她怀里揣着巴黎的电报,心里打定了回巴黎的主意,只等樱桃园的事情一结束就走。而到了第四幕,她果然离开祖国去了巴黎,回到她那个卑鄙的情夫怀抱里去了。难怪罗巴辛在她讲起那别人听不见的“远处”的音乐之后,会低声唱起“俄国人变成法国人”的歌子。面对柳鲍芙口里喊着祖国,心里想着巴黎的拙劣表演,他当然要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并说到“一出非常滑稽的戏,滑稽得要命!”在剧中,柳鲍芙的情夫始终没有出场,可是我们仍然认识了他。用特罗费莫夫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无赖”,“一个一文不值的”小人,柳鲍芙疯狂地爱着这样“一个一文不值”的小人,正好证明她的精神世界同样是一文不值的。此外,情夫这个角色是没有姓名的,他打来的电报,都被剧中人称之为巴黎发来的电报,这就强调和突出了巴黎,从中我们可以悟出剧作家所赋予的深意:巴黎——卑鄙的情夫;柳鲍芙,一个为情夫——巴黎而抛弃丈夫——祖国的堕落女人,一个精神和道德都已经完全堕落,却还要用“祖国”这类高尚字眼来装饰自己的喜剧人物。
三
传统喜剧大多数都是描写特殊的和偶然的生活,其喜剧冲突往往带有偶然性,因此,常常借用巧合、误会、夸张等手段来表现冲突、展开情节、刻划人物。《樱桃园》写的是朴素无华的日常生活,其冲突根本排除了偶然性,这就使作家必然要抛弃与偶然性冲突相适应的巧合、误会、夸张等传统喜剧表现手法而去寻求新的表现手段。这新的表现手段就是调动各种戏剧因素,造成一种总的笼罩全剧的和冲突相适应的喜剧性气氛。契诃夫用来造成这种喜剧性气氛的方法主要有那些呢?
一是气氛性的布景。《樱桃园》第一幕的布景是幼儿室。这一幕的主要内容是已在国外旅居五年的柳鲍芙回家。一贯重视客观、强调真实的契诃夫没有让久别归来的女主人和她的亲朋戚友象实际生活中那样相聚在客厅,抑或书房,抑或卧室,却让他们相聚在幼儿室。这决不是剧作家对生活真实的偶然疏忽,而是匠心独运之笔。请看柳鲍芙出场后的两段台词: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高兴得流出泪来)“哎呀!幼儿室呀!”
瓦里雅:“天够多么冷啊,我的手都给冻僵了(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你的那两间屋子,那间白的和那间浅紫的,还都是从前那个样子。”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幼儿室啊!我的亲爱的美丽的幼儿室啊!我顶小的时候就睡在这儿。(哭泣)我现在觉得自己又变成小孩子……”
只有在幼儿室里,柳鲍芙出场的第一句台词才可以是:“哎呀!幼儿室呀!”接下来,尽管瓦里雅提醒她去看看现在住的房间,她却不加理睬,继续对幼儿室大发感慨。这两段与幼儿室这一布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台词,对这个喜剧人物的塑造带有定调的作用,把她作为喜剧主人公的个性特征初步凸现出来了:一个躺在幼儿室里,用襁褓包裹着自己的老太婆。契诃夫曾经这样谈到过柳鲍芙:“这个剧本的中心角色——是那个老太婆,她的一切都在昔日之中,而在今天她什么也没有。”[(12)]剧中柳鲍芙的年龄虽然只有四十来岁,但她是和垂死的贵族阶级相连的,她的精神已经进入行将就木的老耄之年,而她的心理却停滞在她的幼儿时代。她这两段充满孩子气的台词,她对幼儿室的特殊眷恋,都说明她把自己当成小时候的自己,把世界当成她在幼儿室生活时的那个世界。正是这个矛盾现象构成了她喜剧性格的基础,而这一矛盾现象又是借助幼儿室这一布景才得以充分表现的。可见,幼儿室这一布景对于刻划喜剧人物,营造喜剧气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是气氛性的音乐舞蹈。《樱桃园》的第三幕几乎整幕都是在音乐舞蹈中进行的。这一幕表现了剧本的中心事件——樱桃园被拍卖。契诃夫没有正面展现这一事变,拍卖是在幕后进行的;也没有渲染柳鲍芙们的悲伤和眼泪,他别开生面亦别有深意地在舞台上展现了一场似乎不合时宜的舞会。在欢快、轻松的舞曲中,柳鲍芙和请来的客人们翩翩起舞,夏洛蒂则几乎拿出了她的全部看家本领来变弄各种戏法:猜扑克牌、腹语对话、用毛毯变女孩、戴高帽穿棋盘格子布裤扮小丑。这其间,柳鲍芙虽然也不无痛苦地谈到樱桃园的命运,但同时又可以由衷地为夏洛蒂的戏法大声喝采。其他人更是打闹嘻戏,不亦乐乎。唯一心情沉重、表情痛苦的瓦里雅则一出场就遭到特罗费莫夫的戏弄嘲笑。从这里,人们甚至不难发现闹剧的影子,这使第三幕成为了全剧喜剧气氛最浓的一幕。在第三幕,冲突达到高潮,这种浓浓的喜剧气氛与喜剧冲突的高潮状态正好相映衬。这一切,又与樱桃园被拍卖这一“不幸”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契诃夫就是要借此告诉人们:应该愉快地告别旧时代、旧生活。在这里,音乐舞蹈对于营造喜剧性气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音乐舞蹈,夏洛蒂就不可能兴致勃勃地大变戏法;没有音乐舞蹈,剧中人物的心情就不可能那样轻松,精神就不能那样无拘无束,言行就不可能那样忘乎所以。音乐舞蹈洗刷了樱桃园被拍卖可能带来的一切悲剧和正剧色彩,也洗刷了把舞会安排在樱桃园拍卖日的柳鲍芙身上可能有的一点点悲剧或正剧人物色彩。
三是气氛性的人物。气氛性的人物的特点在于:他们并不直接参加喜剧冲突,他们的出场常常只是为了表现出和冲突相适应的喜剧性气氛。在《樱桃园》中,喜欢变戏法的家庭教师夏洛蒂、几次抡起棍子打错人的瓦里雅、靠借债度日却依旧生活闲适奢华的皮希克、记不得身份把自己弄得象小姐的女仆杜尼亚莎、跟着主子去了一趟巴黎便不愿再见生身母亲的小厮雅沙等就属于这类人物。其中,叶比霍多夫又最为典型。他是“不幸”的拟人化。他穿着崭新铮亮但却吱吱作响的长统靴走上台,一会儿掉了花儿,一会儿撞了椅子……他的这些不幸都是由笨拙造成的,所以都是“可笑的不幸”,不但剧中的其他人物笑他,观众笑他,而且连他自己都在笑自己,在第一幕的开头:
叶比霍多夫:“我没有一天不碰上一点倒霉的事。可是我从来不抱怨,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什么都用笑脸受着。”
“我得走了。(一下子撞倒一把椅子,又把椅子撞倒)你看是不是!(得意的神气)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请特别注意“得意的神气”这个舞台提示。叶比霍多夫倒了霉,不但不痛苦,反而露出得意的神气。他得意什么?得意的是他的倒霉证明了他每天都倒霉的自我判断,何等滑稽!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个滑稽人物本身,而是他在全剧中所起的气氛性作用。一开场,剧作家就让观众很轻松地识别了他这种“可笑的不幸”的特征,使观众以后一见到他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想起“可笑的不幸”来。他在剧中的反复出现,便使“可笑的不幸”象诗歌的韵脚一样,造成一种回旋在全剧的调子和气氛。剧作家给他的头衔是管家,这使人很容易把他的性格特征与他的使命以及他所管的这个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剧作家给他的外号是“二十二个不幸”,而这正好又同樱桃园拍卖日期——八月二十二日相呼应,这就使叶比霍多夫的性格和他带来的“可笑的不幸”的气氛有了某种象征意义,给喜剧冲突起了定调的作用。是的,“可笑的不幸”正是《樱桃园》喜剧性的基本调子和基本气氛。如果说柳鲍芙们和时间的冲突以及这场冲突的后果也算是一种不幸的话,那么这种不幸只能是可笑的,就象叶比霍多夫的不幸是由他自己的笨拙造成的一样,柳鲍芙们的不幸也是由他们自己不识时务的笨拙造成的。其他气氛性人物对于表现冲突所起的作用,如夏洛蒂所代表的“可笑的荒谬”,皮希克所代表的“可笑的卑鄙”等等就不在此一一罗列了。总之,《樱桃园》中气氛性人物对造就全剧的总的喜剧性气氛,表现喜剧性冲突,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亚里斯多德就在《诗学》里系统地阐述了悲剧美学理论,而对于喜剧,不过聊聊数语。此后,西方戏剧美学界似乎一直存在一种重悲剧,轻喜剧的倾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喜剧被看成一种低等体裁,不过是供人逗乐解闷的工具,不可能象悲剧那样表现生活中严肃的内容。对于这种情况,不能以“偏见”二字简单地加以解释,因为美学史上的每一种认识多少都与一定的创作实践有关系,而一定的创作实践又与一定社会生活的发达水准相联系。卓别林曾说过:未开化的人很少有幽默感。在未开化的时代,人类对现实的胜利很少,可供嘲笑的丑也就很少。“只有社会生活愈发达,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面貌愈提高,美愈增多,丑愈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对丑的否定才愈能采取滑稽的形态。[(12)]”因此,与现代的喜剧相比,古代和近代的喜剧还只是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喜剧,还停留在嘲笑人的形体动作的丑和嘲笑个人精神世界的丑的上面。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发达,人们精神面貌的不断改变,喜剧也必然会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上升到嘲笑某种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中的丑的高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尚体裁。契诃夫是最先认识到现代喜剧这一使命的剧作家之一。他曾经劝告同时代的另一作家说:“不要丢掉通俗喜剧……相信我吧,亲爱的,这是一种极其高尚的体裁,而且不是人人写得了的。”《樱桃园》正是他把喜剧改造成“高尚的体裁”的成功实践。
The Cherry Orchard:A BriLLiant Example
of Chekhovian Comedies
Zhang Weijia[*]
Abstract The Cherry Orchard is a new type of Chekhovian modern comedy.Through the unusual advancing technique of keeping balance,the play has succeeded in revealing the special comedy conflicts between theheroes who seem to have not taken any particular action and the time which keeps changing,and has created unique comedy characters.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omedy techniques such as coincidence,misunderstanding and exaGGeration,the play appeals to atmospheric setting,atmospheric music and dance,and atmospheric characters so as to create a comedyatmosphere hanging over the whole play.The play is a successful case ofChekhov's practice in turning the comedy into a noble style.
Keywords Chekhov,drama reform,comedic conflict,comedic roles,comedy technique,the advauced stage of comedies
[*] Fos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528000 Foshan
注释:
本文未加注释的引文均出自焦菊隐先生译的《契诃夫戏剧集·樱桃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