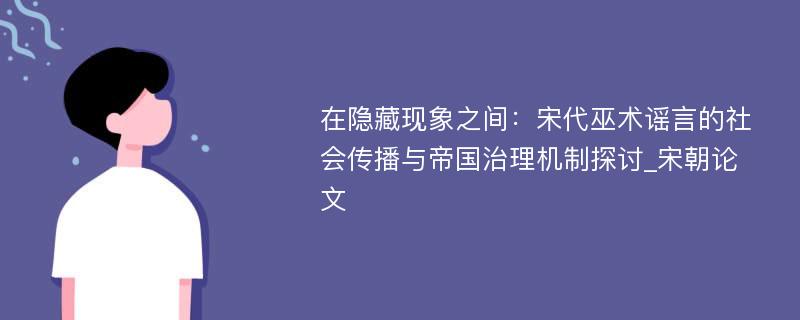
隐现之间:宋代妖术谣言的社会传播现象与帝国治理机制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妖术论文,帝国论文,宋代论文,谣言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在两宋时期,妖术谣言的社会传播往往左右政局变化,布成三百多年间政治舞台上丰富多彩的景象。这时期各种政治斗争频仍,传谣者往往带有预见性、隐秘性、蛊惑性的语言,以“谶谣”、“流言”、“讹言”、“浮言”、“飞语”等称谓,煽惑朝野舆论。当然,宋廷对于这些妖术谣言也采取相应举措,避免了王朝内部的重大变局。因此,本文拟以妖术谣言为载体,探讨宋代妖术谣言的社会传播现象、传播途径及其帝国治理方式,以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提供参照和镜鉴。 一、宋代妖术谣言的社会传播现象 自唐中叶以降,中原大地上演了一幕幕骄兵悍将叛乱、割据的悲剧,导致政权频繁更替。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利用社会上流传了一则“以‘点检作天子’为主要内容的、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1],做好了改朝换代的舆论准备。建国后,太祖、太宗等帝王对自身实力及面临的困境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在重建中央集权过程中,大体上采取“专务以矫失为得”[2]为原则的种种举措,如文武制衡、内外相维、上下相倾等政策,都分明体现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精神[3]。随着政策的矫枉过正,加上政治风云变幻翻覆,造成一些朝野人士造谣、传谣的活动逐渐升级,愈演愈烈。所以,宋代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事件中风云人物纵横捭阖均与妖术谣言传播有着密切关系。归纳其社会传播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特色。 其一,宫廷内幕往往成为妖术谣言传播的政治驱动力之一。历代王朝往往把谣言认定为威胁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毒瘤。凡是王朝更替、皇权递嬗之际,即使人人知道的虚假事情也可能被人为的造成一则谣言,对专制统治构成一定威胁。如若最高决策阶层巧妙利用谣言,又可能成为专制统治的自我调节器。南宋初期,高宗及小朝廷被金兵逼迫,逃到南方地区,产生了人们对皇权统治的信任危机。当时谣言四起,而让宋高宗担心的莫过于那条谶谣:“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却在继续蛊惑人心。当时宗室赵子崧想趁机篡位,借这则谣言来传檄天下,称:“艺祖造历,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4]。高宗得知后大怒,将赵子崧贬于岭外。此前,许多人把这则妖谣言解读成一种君命所授的政治依据,酝酿了多起谋反事件。太宗死后,内侍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及潘阆等人谋立太祖之孙赵惟吉。神宗朝,李昌龄之孙逢、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荧等人蛊惑太祖子孙赵世居谋反。这些事件说明皇权一旦遇到危机,谣言就被人利用。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上虞县丞娄寅亮公开支持这则谣言。在这种大气候下,宋高宗发现其不能生育后,便顺水摧舟,遴选太祖后人继承赵宋的江山。 其二,宋代政争、党争成为妖术谣言传播的重要场所。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宋代士大夫经常编造各种谣言,诋毁政敌。其实,谣言利用儒家的“察谣听政”传统与宋代“防弊”体制关系,达到排挤政治对手的目的。这也无形中造成了士大夫们陷入捕风捉影、歪曲附会及挟私打击报复的怪圈,使朝政陷入分裂斗争中而不可解。 北宋中后期以降,士大夫之间的党禁逐渐升级,最终演变成绵延不断的社会分裂。他们相互造谣生事,往往将对方扣上某党的帽子,给予“编管”、“安置”等惩罚。神宗时期的“乌台诗案”主角苏轼、哲宗元祐时期的“华盖亭诗案”主角蔡确、宁宗时期的“庆元党禁”主角赵汝愚、朱熹等,均因谣言诋毁而惨遭政治打击。因此,这些造谣风气不仅影响了士大夫们的政治心理,使他们疲于应付这些无根之语,而且加剧了政争、党争的惨烈程度。 其三,“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为妖术谣言在民众中间传播提供可行的土壤。对于妖术谣言,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在反复传播,可见不同的群体都有着“深刻的混乱、焦虑和不稳定”的感受。[5]有些官员趁机利用天灾人祸传播谣言,打造成一把政治利器。欧阳修、司马光、王陶等文臣纷纷把民间传播的妖术“讹言”当成利器来劝说仁宗早立储君。嘉祐七年(1062),右正言王陶上疏:“今春徐、陈、许、蔡迨京畿之民,讹言相传,掘土而食。近又龙斗于南京之葛驿。盛夏火王,金当在消伏,太白芒角盛大,凌犯荧惑。又太白经天与岁星昼见。天地人事,皆见变异,其占为兵凶,为人心不安,为甚可惧,太史必有以其术为陛下言之者”[6]。天禧三年(1019),亳州民众“讹言”兵祸来了,引起“老幼千余人夜奔陈州”的事件[7]。可见人们对于现实灾祸往往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与恐慌。熙宁元年(1068)七月,河北地区频繁地发生地震灾害,人们在惶恐中便“讹言大水且至,惊欲出走”[8]。这一谣言正好切中了人们对现实境况的恐慌,激起了他们参与传播谣言的欲望,经过一个接一个增减利已因素的传播,谣言越来越偏离本来的轨迹,最终造成人们携妻挈子、奔波逃难,破坏了社会稳定。 总之,宋代妖术谣言的滋生、传播过程中无不涉及到专制制度、利益诉求及观念差异等方面,归根到底谣言传播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上的。 二、妖术谣言传播的信息监控 在传播过程中,宋廷从制度层面入手,坚持预防为主,构筑起国家风险治理的信息平台,时刻监控着官民沟通的信息渠道。而这条渠道是一个预防系统,在上层和下层预防谣言传播方面之间,有着相互监视和防范的特点。尽管在不同层面中存在着等级差异,但这些阶层却拥有维护专制统治使命的特征,都成为不同阶层相互预防谣言传播的共同基础。 其一,台谏系统扮演了妖术谣言传播的监督角色。在构建防范与猜忌臣僚体系的同时,宋统治者纵有培养官员们的忠君意识,必然包含着排斥英才的事实。所以,在制度、利益及观念差异的影响下,患上人格分裂症的台谏官时常以风闻为借口,有恃无恐地抨击朝政,使得执政者有所顾忌,连帝王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宋仁宗谈到当时台谏官的行为:“台谏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将博问朝士大夫,以广听察。乃有险诐之人,因缘憎嫉,依倚形势,兴造飞语,以中伤善良,殆非忠厚之行”[9]。这并未改变台谏官继续造谣抨击朝政的行为。特别是他们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可以说达到完全丧失理智的状态。武将狄青因战功卓著升任枢密使。然而,欧阳修等文臣出于“恐武”的阴暗心理,造谣诋毁狄青。欧阳修说:“青之流言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为青计者,自宜退避事权,以止浮议。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近日以来,讹言益甚。或言其人身图谶,或言其宅有火光”[10]。不久,狄青在同僚的流言飞语中,被迫离职。无独有偶,枢密使、武将王德用也因台谏官谣传“宅枕乾纲”、“貌似太祖”等而遭到罢免。显然,宋代台谏系统长期“扇造浮语,诋毁危切”的行为[11],往往被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力量。 其二,皇城司扮演了最高决策阶层私下收集社情民意的重要角色。除正常渠道外,宋代统治者还设立了一个叫皇城司的特务机构。宋初,太祖命心腹史珪刺探朝野消息。随后,皇城司承担了这职责,成为统治者伺察民间奇闻轶事及危胁朝廷者的一条有力渠道。庆历五年(1045)五月七日,皇城司言:“访闻在京诸色军人百姓等,讹言云道:‘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脚攞沙’。恐是不祥之言,乞行禁止”[12]。可见,皇城司伺察能力很强,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并及时向统治者反馈谣言传播的信息。元丰七年(1084)秋,宋神宗在大宴群臣时,忽然得了疾病。随后,“京师方盛歌《侧金盏》,皇城司中官以为不详,有歌者辄收系之,由是遂绝”[13]。随着政治斗争的复杂化,皇城司时常与朝中大臣一起干预国事。熙丰变法时,宰相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其中,“村民有偶语者曰:‘农事方兴,而驱我阅武,非斩王相公辈不能休息。’逻者得之付狱”。“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14]。可见,最高决策阶层利用皇城司这个私家工具,清除异己言论,维护专制统治的稳定。 其三,地方官僚系统成为民间妖术谣言识别、排查、应对与围剿的重要链环。地方官僚在妖术谣言初期反应基本相同,他们并未第一时间通报皇帝,企图息事宁人,安抚民众恐慌,强烈打击谣言传播者。这因为地方官员需要足够的官场生存智慧,避免不利已的谣言流传到朝廷,成为政敌攻击的口舌。所以说,谣言也很难从民间流向朝廷,这归因于官员有能力控制传播渠道。另外,与普通民众不同,读书人出身的地方官僚从一开始就不轻信妖术。“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15]峨嵋有人“以讹言起祠庙,夜聚千余人”,被知嘉州犍为县吴中复“配首恶而毁其庙”[16]。宝元二年(1039)三月,有人“传张角之术,善以妖幻惑人”,致使人们受到“讹言”惊吓,“老幼东向奔走,道路三日乃止”。官员耿傅捕获这些传播妖术的人,并将“首恶伏诛,其支党黥若杖男女二十余人”[17]。当然人们之所以害怕妖术谣言,多因他们感到个人的生存被周围种种看不见的势力威胁,致使他们的生存安宁状态被无故打破。 在传播过程中,民间谣言所涉及议题的社会政治意义、利益越是重大,其影响力的最大公约数也越大,相关利益群体的规模也就扩大[18]。这就要求地方官员有防止谣言滋生、传播扩大化的政治智慧。宋初,四川地区出现一则“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的谣言,引起了人们恐慌。随后,知成都府张詠抓住“造讹者戮之,民遂帖息”。对此,张詠总结出一条经验:“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乎厌胜也”[19]。可见,地方官员具有一种认识、控制谣言的能力,对传播渠道的运转起着一定作用。 总之,无论处于前台风闻言事的庙堂、江湖,还是后台秘密的、特权的兼具私人耳目的皇城司,均对维持社会稳定起着预防的重要作用。 三、帝国治理妖术谣言的机制 对于谣言风险问题,宋廷主动地运用各种手段、各种力量构建了一套治理谣言传播的运行机制。而这套机制将治理方法运用到妖术谣言的控制中,并针对信息源头、民间媒介、官方信息及应变能力等可能存在问题,以全面、准确地识别风险点,来扼制妖术谣言传播的扩大化。 其一,制定法规治理妖术谣言滋生的素材。宋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君权神授”性,制定法规治理与造谣、传谣相关的书籍、人物,切断妖术谣言滋生的土壤。开宝八年九月,除名人宋惟忠弃市,“坐私习天文,妖言利害,为其弟所靠故也”[20]。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朝廷禁止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等妖术传播。景德元年(1004)正月,朝廷禁止人们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等书。大中祥符五年三月,朝廷发现“有人众目为先生。每夕身有光明。能于隙窍出入无碍。是必妖妄惑众。其令开封府速擒捕禁止之”[21]。当然,这并未完全阻止人们触及禁令。诚如吴育所言:“窃闻近岁以来,有造作纤忌之语,疑似之文,或不显姓名暗贴文字,恣行毁谤,以害雠嫌”[22]。可见这种“纤忌之语,疑似之文”触及统治集团紧张的神经,促使其防范措施日益严密。从图书甄别、鼓励检举及法令断罪等举措看,均显示出统治集团控制政治谣言传播的力度。 其二、宋廷灌输官员们的不传谣、不信谣理念,并时刻规范其政治传播行为。历来泄露宫廷内幕消息的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有官方背景的人士,他们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又不被人发现,往往选择谣言的方式传播消息。淳熙十四年(1187),临安市井歌曰:“汝亦不来我家,我亦不来汝家”[23]。可见,民间传播孝宗与光宗之间存在有矛盾的谣言,必然有官方背景的人士支持。宋代统治者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指出“险巧轻儇之徒,构造无根之语,鼓惑邪说,倾动中外。或播传迁责臣僚,或横议兴易政事,或妄意更革,或诈称差除,其说多端,朝更夕改,以致搢绅惶惑,不安厥位。立则聚谈,行则耦语。转相探刺,欲为身谋。各怀疑心,潜相睽异,为间谋之计。伸怨悱之私,浸淫成风,为害甚大”[24]。宋代统治者为此要求官员们有规则地传播,使其个人身份与统治集团目标统一起来,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协作式”的传播模式。如若士大夫脱离这种模式,不但失去统治集团给予的物质与精神利益,而且对政治稳定构成一定威胁。于是,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精神的感昭下,宋统治者连续颁布规范官员传播行为的诏令。一方面,官员必须不传谣、不信谣,保持名节,如《诫饬鼓惑之言御笔手诏》、《申谕公卿大夫砥砺名节诏》等。另一方面,严惩参与谣言传播的官员。政和三年(1113)十月,奉议郎、知河南府登封县赵冲因“讪上之慝”、“而措为无实之论”、“意在诋诬[25],被降授宣德郎、就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务等。 其三,针对专项风险,宋廷启动中央巡视专员处理突发政治谣言事件的应急预案。一般情况,在极具有画面感的妖术谣言描述下,人们易于信以为真的极力传播,很可能演变为一场政治危机。天禧二年(1018)五月,京师民众传播“帽妖”的谣言。官员张旻向朝廷汇报这“帽妖”谣言的状况:“近闻西京讹言,有物如帽盖,夜飞入人家,又变为大狼状,微能伤人。民颇惊恐,每夕皆重闭深处,以至持兵器捕逐。”[26]针对这则谣言的危害性,宋真宗鼓励人们检举造谣者,从而抓住了僧天赏、术士耿概、张岗等人。从事件处理机制看,统治者接到官员的谣言报告,马上派人调查真象,制定辟谣方针,安抚民众。 在突发事件中,朝廷派遣专员处理谣言传播的方式,形成了一套中央巡视运行机制。至和元年秋,人们都在谣传侬智高叛军到达四川地区,一时谣言四起,惊动了朝廷。宋仁宗马上派张方平前往抚慰。他抵达四川地区后,撤去戍守军队,并告诉人们:“寇来在吾,无尔劳苦”[27]。于是,谣言遂平息。所以,朝廷派遣得力官员对处理重大谣言事件的机制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谣言无处不在,如若官员处理不当,就会引发政治危机。所以,有官员认为要防范谣言,如奸人“缘饰语言”、“诬蔑善良”、“诋许朝臣,讥讪时政”等,必须保障信息渠道畅通,“严戒诸路按察官,不许采听暗昧不根匿名文书”[28]。从运行机制看,统治集团要防止奸人谣讪朝臣、动摇州县,必须做好秉公执法,化解民众矛盾等准备,才能保证从地方到朝廷信息渠道畅通,避免政权生存的威胁。 总之,宋代妖术谣言的风险治理与统治集团防微杜渐的意识密切有关。防微杜渐原则作为宋代谣言风险治理的精髓,它使统治集团始终对意外事件保持警惕心理,有效地杜绝了宋代内部重大变局,保证了政权的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