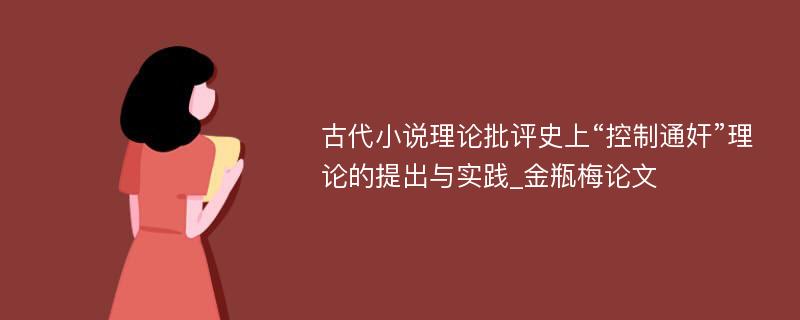
在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以淫制淫”说的提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批评论文,古代论文,理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以淫制淫”说是在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关于性事描写的各种主张中颇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观点之一。探讨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文学背景,分析其理论依据和矛盾缺陷,了解清中叶以后对此说的批判和反拨,肯定跨类型小说对此说的较为成功的实践,对古代小说中性描写发展演进轨迹的认识无疑会深入一步。
【关键词】明清小说 以淫制淫说 性描写 跨类型小说
一
有言曰:性,原本是“不把它当回事儿,也就不是事儿;把它当回事儿,还真是个事儿”的事儿。虽属戏言却深含哲理。唐以前,人们基本“不把它当回事儿”,性欲被视为如同吃饭穿衣一样的自然要求,文学作品也尚能真实地反映人的生物生理本能,情与欲大体处于和谐状态,因而也就“不是事儿”。时至宋明,随着存天理、去人欲和变化人的气质之性、恢复人的义理之性的理学的兴盛,人们越来越“把它当回事儿”,“万恶淫为首”的观点、“男女有别”的戒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使人们的性需要处于空前的压抑与禁锢之中,人的自然本性被严重扭曲,其结果只能是潜抑愈深反抗愈烈。明中叶以后以情反理的社会思潮,使得长期遭受压抑的人欲如久困的猛兽破笼而出,似久蓄之江水决堤奔流,以理学家们所始料未及的迅猛之势,冲击、破坏着旧礼教、旧秩序。反映在小说创作上,“猥亵”之风大炽,《如意君传》、《金瓶梅》等小说中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所掀起的张扬人欲的轩然大波,经久不衰,引起统治者和道学家的极度恐慌,因而使得性“还真是个事儿”。既然“真是个事儿”,就要解决这个事儿。于是朝廷明令禁毁者有之;卫道者冠之以“诲淫”,而要付之龙炬者有之;小说家中主张对这个事儿一概“勿视、勿听、勿写”者亦有之。然而,自然规律总是无法抗拒的。植物原始的生物性使之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炫耀自己的生殖器官——花,招蜂引蝶,生衍不息;野兽不失本色,坦然地、不遮不掩地进行天作之合;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虽然在性的问题上立下的规矩越来越多,以至由掩盖回避,发展到压制、禁绝,但任何时候也未能真正达到目的。统治阶层虽然立下种种清规戒律,但“法不加于尊”的特权,又使得这些规矩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纸空文。宫廷淫乱之事历来史不绝书;主张禁欲的理学创始人程朱自己也无法“六根清净”,朱熹勾引尼姑做妾、程颢与妓女共宴的事实本身正显示了自然人欲的不可抗拒;封建士大夫在人前不免道貌岸然一番,在人后却将“雪夜闭门读禁书”作为一件惬意之事;更不要说在民间,质朴自然的性观念、丰富活跃的性生活,从来就未因统治者禁止而灭绝。
人情解放思潮对灭绝人性的理学的清算,本是人类正确认识自身的一个进步,然而由于色情倡欲之书缺乏人本主义思想的光照,以极端反抗极端,“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疫”,所以在对礼教进行公然嘲弄的同时,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落入荒谬的泥潭。本来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组成部分的“贞节观”也被认为是“‘不自然的’或违反自然的行为,从而加以贬斥,并且认为它是陈腐的宗教信条以及衰弱政治的一个附带的条件,应该和这种信条和政治同其命运……许多人的性的活动便往往走上另一极端,不但把纵欲和乱交看作一个理想,并且真把这种理想见诸行事;他们不了解这样一个极端是一样的不自然,一样的要不得”(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
倡欲之书在问世之初,就是以“禁书”的面目出现的,最初的一批读者大都视之为“秽书”而主张焚毁。如沈德符对试图刊刻《金瓶梅》的马仲良说:“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谈及此书时说:“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之论者,也一再以诲淫的罪名对它进行攻击,力主禁毁,这就迫使喜爱它的人不得不一再为它辩护。辩护者的观点不外乎两大类:一类为“非淫书”说。如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云:此书“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其它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金瓶梅词话〉廿公跋》曰:“《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非淫书”说面对论敌的攻击,寸步不让,可书中过于显山露水的自然主义性描写,又使得他们陷入尴尬境地:“贼无赃,硬似钢”显然办不到;“背着牛头不认赃”的做法也并不灵验。于是有人退而求其次,以守为攻,提出了第二类说法“秽书戒世”说。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开头第一句直截了当地宣称:“《金瓶梅》,秽书也。”之后辩解道:“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詹詹外史(冯梦龙)在《情史序》中,大胆肯定了男女之情,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男女之情”及其教育意义:“私爱以畅其悦,仇憾以伸其气,豪侠以大其胸,灵感以神其事,痴幻以开其悟,秽累以窒其淫,通化以达其类”。其中“秽累以窒其淫”,恰是“以淫制淫”的意思。
较为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因势利导,以淫制淫”说的当推憨憨子,他在《绣榻野史序》中说:“余将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趋矣,人必不变。余以诲之者止之,因其势而利导焉,人不必不变也。”此观点从社会时尚及读者接受心理着眼,较之“非淫书”说,辩解有理有据,给后世以深远影响。西湖钓叟的《续金瓶梅集序》进一步发展了“因势利导”之说。本来,小说要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往往要接触到被一定社会、阶级、集团认为是“反面”的人物和内容。对于这些“反面”的东西,是排斥?是将以漫画化的简单勾勒?还是敢于描写,甚至作为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人们回答各异。西湖钓叟认为“盗”、“魔”、“色”,不仅都可以写,而且可以“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只要根本目的在于“以隐,以刺,以止”,“一归之劝世”,就怎么也不过分。他说:“今天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道,《金瓶梅》惩淫而煊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只不过“今人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非圣而畔道焉”。清代以评论苛刻著称的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亦赞同此说:“《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
明末至清初,“以淫制淫”论主要是小说理论界在总结创作经验的过程中,围绕如何写人欲而提出的理论观点,虽并未真正付诸创作实践,但对鼓励支持文学作品反映人的自然欲望起了较大作用。
二
“以淫制淫”说的理论根据是孔子删郑、卫之音。孔子所处的先秦时期,与初民生活境况相去未远,道德伦理秩序草创初建,故原始的朴素的性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从“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周易》)、“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老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礼运》)、“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荀子》)、“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吕氏春秋》)等经典中的观念,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作为一位道德至上论者,孔子认为淫是不道德的,应在排斥之列,然而,他也并非不知个中难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以对色和欲,他并未采取后来理学家那种绝对态度,而只是主张以德加以节制。经他删定的《诗经》,还是收进了不少他并不喜欢,并认为“淫”的郑卫之音。尤其是他将后世道学家斥为“淫奔者之辞”的《诗经》,毫不含糊地明确肯定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不仅为当时的情欲描写开了一个不算太小的后门,而且为后世的情欲描写提供了理论上的托辞。凡赞成“以淫制淫”说的人,无不拉此大旗以为虎皮。憨憨子在《绣榻野史序》中提出因势利导说后,紧接着摆出其理论依据:“孔子删诗,不必皆《关睢》、《雀巢》、《小星》、《谬木》也,虽‘鹑奔’、‘鹊疆’、‘郑风’、《株林》,靡不胪列,大抵亦百篇皆为‘思无邪’而作。”《〈金瓶梅词话〉廿公跋》云:《金瓶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云:“《诗》云‘以尔事(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此非金、梅等辈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等辈乎?乃先师手定,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托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事,兮子衿诸诗细为模仿耳。夫微言之,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
“以淫制淫”说在小说中的“内证”,主要是所谓“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的因果报应的结构。观海道人《〈金瓶梅〉原序》中的一段话较具代表性:“天道福善而祸淫,恶者横暴强梁,终必受其祸也;善者修身慎行,终必受其福也。子不观乎书中所纪之人乎?某人者邪淫昏妄,其受祸终必不免,甚至殃及妻孥子女焉。某人者温恭笃行,其获福终亦可期,甚且泽及亲邻族党焉。此报施之说,因果昭昭,固尝详举于书中也。至于前之所举其炽盛繁华者,正所以显其后之凄凉寥寂也。前之所以举其势焰熏天者,正所以证其后之衰败不堪也。一善一恶,一盛一衰,后事前因,历历不爽,此正所以警惕乎恶者也。奈之何子尚惧乎人尤而效之乎?”(引自陈昌恒整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第243页,华中师大出版社)
“以淫制淫”说的兴盛,说到底是礼教与情教调合的产物,以淫现身说法体现了情教对人欲的肯定与张扬,制淫却又企图将小说中的性描写纳入礼教之正途。对这一矛盾的认识,在明末清初只是限于理论之争,在实际创作中,大量的丑恶、阴暗、病态的人性,以及赤裸裸详尽直露的性描写,非但很难起到“制淫”的作用,相反只能成为宣淫导欲之工具。倒是崇祯刻本《鼓掌绝尘》赤城临海逸叟叙,对这一问题说得直截了当,不遮不掩:此书“倘谓淫邪贼正,视为污蠹之物,桑间濮上,宣尼父何不一笔削去之,其中盖有说焉。不惟淫欲炽而情态丑,足堤千秋之邪窦,即合卺野而白发贞,亦足愧万古之负心。嗣有穴隙钻而龙门跃,阳台为飞腾之基矣。逾墙从而六翮凌,超越成鹏博之遥矣。或一念幽情,开箕裘冠冕,片时佳会,结绝代芳声。舍此一途而不赏者谁”?这岂只是宣扬“以淫制淫”,简直是赞美“淫情”在人的婚姻家庭、功名利禄中起到的作用。
三
正因为“以淫制淫”说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陷,清中叶以后,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批驳此说的浪潮。曹雪芹、脂砚斋等人首先向“色而不淫”说发难。《红楼梦》第一回就对“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的“风月笔墨”进行了批判,第五回中说:“自古以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脂批道:“‘色而不淫’四字已滥熟于各小说中,今却特贬其说,批驳出矫饰之非,可谓至切至当,亦可唤醒众人,勿谓(为)前之矫词所感(惑)也。”与《红楼梦》几乎同时问世的《歧路灯》,针对以“惩欲”为名,行“导淫”之实的倾向,厉声质问道:“每怪稗官例,丑言曲拟之。既存惩欲意,何事导淫辞?”(第二回)其时,避俗向雅、抑欲扬情已成时尚。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北史演义》凡例云:“凡叙男女悦好,最易伤雅。此书叙魏武灵后逼幸清和,齐武成后私幸奸僧,高澄私通郑娥,永宝私通金婉,无不曲折详尽,而不涉一秽亵语,避俗笔也。”对“以淫制淫,因势利导”说进行全面清算的要数清项名达的《重刻劝毁淫书征信录》:“至恶莫如淫,难治亦莫如淫,逆制之忧惧不胜,顾可顺而导之乎?鞠淫之根由于迷,所以迷者由于认秽而为美……能顺以益迷者,淫书最烈”。
此时期的小说界,不仅在理论上注意对“欲”的清理,在创作实践上也力避“亵墨”。才子佳人小说中所写之“情”,已是对“欲”进行了净化处理之后升华而成的“纯情”,也是在“情”中又生硬地加入了“理”,用封建伦理道德严格约束的“情”。小说表现的不再是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那种情与理的冲突,而是让情服从于理,实现情与理的统一,因而绝无“淫风相煽”之嫌。尽管才子佳人之作以其创作主旨的千篇一律和人物形象的说教化、概念化,历来受到哂笑,但毕竟完成了世情小说由写欲到写情的过渡和转变,从而与《红楼梦》所写的“意淫”有了某种联系。“意淫”以其自始至终是灵魂的颤栗、精神的灌注,同以官能享乐为主要途径、以生理心理的快感为旨归的皮肉之淫有了质的区别。性目的、性方式、性解脱是性意识体系中的三个子系统。考察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性意识的美学嬗变之迹,可以明显看出,性目的由传嗣意识与享乐意识的分道扬镳,演变为“情痴”;性方式由禁欲与纵欲的既相悖相斥又互为因果,演变为“意淫”;性解脱则由性放纵导致的肉体毁灭,演变为超脱于肉体之上的精神的升华。《歧路灯》既是《金瓶梅》孕育的产物,又是对《金瓶梅》性描写纠正的结果。作者李绿园以其道学家思想,将淫词秽笔打扫得干干净净,绝不作自然主义的刻画和不堪入目的描述,表现出严肃的创作态度。
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对“以淫制淫”论的批判使得多数世情之作的性描写由俗转到雅,由肉转向灵。但是,“以淫制淫”说并未就此而偃旗息鼓。纵欲和禁欲作为两个动荡而各走极端的状态,正如钟摆一样,既摆到了东,便不能不摆到西。在多数才子佳人小说和世情之作性描写趋向雅化之时,仍有部分小说并非完全同步,相反,在作家的思想、情趣和作品格调、风格方面与淫亵之作保持同调。如署携李烟水散人的《灯月缘》、《赛花铃》、《桃花影》等,或写才子无与匹敌的淫事本领,或写众佳人与才子交股一床,大事淫污。这些小说作者或许有“以淫制淫”、警戒世人切勿效尤之意,但书中过多过露的淫事描写,实际上却起到恶劣的诲淫效果。
四
在创作上,真正将“以淫制淫”说付诸实践的,还是产生于清中叶的《野叟曝言》、《女仙外史》、《绿野仙踪》等一批有跨类型倾向的小说。此类小说与《红楼梦》相比,同它们附腐的妇女观、君臣观、等级观相适应,在情欲观方面力主“制欲”、“却色”,然而其又并非在描写中“去欲”、“却色”,而是承《金瓶梅》之遗续,对性的描写粗俗直露,企图“以欲制欲”、“以色却色”、“以淫制淫”。其性描写动机和指导思想源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道德理性思想方式:“读者深省之,可于淫欲世界,悟出圣贤学问。”(《金瓶梅》第二十五回回评)跨类型小说的性描写虽也写淫,但与此前小说中的淫秽描写有明显不同:
其一,写淫之目的,非为宣淫,而为戒淫。与猥亵书用果报轮回、“劝善戒淫”的道德外衣来掩盖淫秽内容不同,跨类小说作者多为正统文人,因而虽有一些性描写流露出低级趣味和变态心理,但总体看来,把握性描写的分寸是准确的。这是由于作者既承认情欲,又主张抑制情欲的观念在起作用。《野叟曝言》第二十回总评曰:“天地一情府也,生人一情种也,唯有礼以节之,故不至纵情灭性;有仁以导之,故不至纵情灭性。”《绿野仙踪》侯序云:“气热则嗔,财热则贪,色热则淫,至于嗔、贪、淫,则必荒乱迷惑,忘其所始,丧其所归。”于是在《绿野仙踪》里“冷”就成了作者理想人格必备要素之一。冷于冰之名,即缘起于此。第十五回回末诗云:“莫道于冰骨肉薄,由来仙子破情关。”第九十八回于冰曰:“修道人首戒一个‘淫’字”,都反映了对情欲的压抑。当然,在具体描写中,有时也能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情欲,如在被郑振铎先生赞扬为“是许多‘妓女文学’中写得最好的一段”(《文学大纲》)的温如玉与妓女金钟儿的情爱纠葛中,人物情欲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然而,写情写欲又是为了欲擒故纵,最终达到抑情制欲的目的。第六十七回至七十一回写冷于冰作法,让温如玉梦入华胥国,被招为附马,极尽淫乐,梦醒后,让温如玉幡然悔悟,表示自己“直觉心如死灰,便是天上许飞琼、董双成,我总以枯骨对待”,即使金钟儿重生,“我也视同无物”。第二十回写冷于冰设计试禅心,派一妇人勾引金不换,不换坚忍欲火,“每到情不能已处,便用手在自己脸上狠打,打后便觉淫心少歇”。制欲过程写得真实可信。
《野叟曝言》有多处以较长篇幅写及淫事,然而,写色是为“却色”。第十七回总评云:“却色至此回极矣……莺吹并未同床合被,其拥挽抱负皆本侠肠,无情丝牵绊;璇姑虽宛然在床,而为德不卒,谊士爱称,却之尚易;至于素娥则既感其恩,复许为妾,而当此赤体拥抱,哭泣求欢,犹且决意绝之,不几太上无情乎?……素臣定为天下无双正士,岂虚誉哉!”性心理学认为:“积欲与解欲是衔接得很紧的。积欲好比积薪,解欲好比积薪点着后火焰的上腾,这火焰不是寻常的火焰,而是生命的火焰,一经燃着,生命便可以世世代代地不断传递。这全部过程好像是两节的,而实际还是一贯的。”男女间性交合“也必得经历这两节而一贯的过程,才算正当,才算有效力,对双方才能满足”(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而在小说中,肯定积欲而否定解欲则成了理想人物文素臣“却色”的根据和法宝。第七、八两回写文素臣与璇姑同床共枕,耳鬓厮磨,独处三夜,却讲论三角圆周、天文历算,无涉淫邪。二人一番对话,可见出作者对理想化的两性关系的理解。素臣道:“男女之乐,原生于情,你怜我爱,自觉遍体俱春。若村夫俗子不中佳人之意,蠢妻呆妾不生夫主之怜,纵夜夜于飞,止不过一霎雨云,索然兴尽。我与你俱在少年,亦非玩钝,两相怜爱,眷恋多情,故不必赴阳台之梦,自然生寒谷之春。况且男女之乐,原只在未经交合以前,彼此情思俱浓,自有无穷兴趣;既经交合,便自阑残。”璇姑云:“窃以为乐根于心,以情为乐则欲念轻,以欲为乐则情念亦轻……据此时看来,相公已怡然自得,小奴亦窅然如迷,捱胸贴肉,几乎似片成团,交股并头,直欲如胶不解。床帏乐事,计亦无逾此者:恐雨云巫梦,真不过画蛇添足而已!”第八回总评曰:“论云雨为‘画蛇添足’,非深于情者,不能为此言。彼专以云雨为乐者,固属渔色之徒;既兼以云雨为乐者,亦非钟情之辈。盖情钟则爱,爱则怜,爱且怜则乐,虽衣冠钗饰,肃雍相对,其乐无涯;况捱胸贴肉,似片成团,交股并头,如胶不解乎!如演剧者,前数十出,极尽悲欢离合之致,令人欲歌欲泣;至团圆一出,则皆视为可有可无之事矣。夫优伶演剧,必至团圆后已;犹男女会合,必至云雨后已。其实云雨之可有可无,亦如团圆之可有可无。而非深于情者,不知也。彼《西厢记》等书,极摹云雨之乐,止可称欲鬼耳,岂情种哉!”
由上可见,与猥亵之书对欲的直露宣泄不同,跨类小说将性处理在压抑的态势之中,显示出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旨。
其二,小说主人公与猥亵作品中的“肉欲狂”迥异,均是抑情制欲的正人君子。且不说《绿野仙踪》的主人公冷于冰弃家室,抛妻子,求仙访道,终于位列仙班,就是手下徒弟也通过“以淫制淫”,一个个斩断情缘,修成正果。《野叟曝言》为表现主人公文素臣的制欲本领,多次设计了女子主动委身事之,而素臣都以“守经行权”之理打消对方欲念的情节。在书中“守经行权”四字犹如避水宝珠,保佑他在欲海淫浪中左右逢源,不至灭顶。最甚者莫过于第六十八回写素臣被景王叛党锦衣佥事李又全扣留,专食其精,以备采战。在被李又全众姬裸戏之前,他想道:“我有主意了。我想皇古之人俱是赤身,所以唤作裸虫。其实阴阳二道与耳口鼻一般,同为生人形体。明日只在这上头着想,便不怕满眼的赤身裸体之人了。至于诸般怪状便只以‘目中有妓,心中无妓’八个字应付之。”在淫窟中,素臣屡遭众姬狎戏猥亵,又时以“事有经权,拘沟渎之小节而误国家之大事又断不可乎”来寻求精神的解脱,取得心理的平衡,终未同流合污。
不仅跨类小说的男主人公能断欲却色,女主人公亦毫不逊色。《女仙外史》第六回写唐赛儿与林公子完婚后,林公子百般求欢,赛儿竭力“却色”。她对公子说:“我与公子,但居夫妇之名,竟做个闺门朋友如何?”芥舟批曰:“从来女子之有才者必多情,多情者必重于色欲而轻于伦理……赛儿刻刻学仙,扫尽情欲。”在此类小说中不仅求仙学道者了无情欲,他们的妻室也视欲为可有可无。冷于冰与妻子一别十六七年,首次回家探视,夫妻见面只叙家常,坐到定更后,于冰告辞,向妻子卜氏说要“在外面暂歇一宿”。卜氏答道:“我大儿大女,你就在,我也不要你。”《野叟曝言》第五十八回写素臣一家妻妾谦和,一妻二妾为陪素臣歇卧一事你推我让,谁也没去成,结果“为好成空三处衾绸皆冷落”。诗评曰:“家家妻妾为争夫,虎斗龙争定霸图,三美让夫成独宿,密淋漓换醋葫芦。”表现出作者理想化的家庭婚姻观。
其三,性的描写独出机抒,不落俗套。与猥亵之书专注于性交动作的自然主义描摹,喋喋不休地展览各式性交过程,描述性交时的肉欲快感不同,跨类小说注重在性描写中刻画人物自身的情与理、恩与爱、原欲与道德、压抑与追求等各种精神活动之间的复杂冲突与交融,从而揭示人物的内在精神和情感奥秘,并通过性关系辐射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内容。重视和强调情欲描写的正与邪、雅与俗之间的界限,努力驱邪扶正,避俗向雅,是跨类小说的一大特点。《女仙外史》第六回许旭庵批曰:“才子之文出笔便雅,即使题甚俗,而能愈俗愈雅。庸人之文落笔便俗,即使题极雅,而偏愈雅愈俗。读此回书,慧心者可以悟道,岂止雅云尔哉。”那么,同写淫事,究竟孰正孰邪,谁雅谁俗?跨类小说作者认为关键在于“笔意”。“笔在此意不在此”者为正为雅;“笔在此意亦在此”者为邪为俗(《野叟曝言》第二十八回总评)。如《野叟曝言》第二十八回叙连城与春红性事,陈采阴补阳之技法。该回回评认为,其描写虽“酷类《金瓶》诸男女秽亵世界”,又“非摹仿《金瓶》也”。这是因为《金瓶梅》笔在此意亦在此,故为淫邪;《野叟曝言》笔在此意不在此,“则勃溪唇中隐然有一非礼勿言之女道学,秽亵世界中隐然有一守身如玉女圣贤”。只要“辟邪崇正本旨自在言外”,就可“不比金瓶等书专描淫秽”(第六十七回总评)。《绿野仙踪》里温如玉嫖妓等描写与邪俗之书所差无几,然因最终使他浪子回头,修成正果,故“崇正本旨自在言外”,不可算作“专描淫秽”。《野叟曝言》第六十九回“南道学遍看花蕊,女状元独占鳌头”,可说是李又全的19个姬妾的性器在素臣面前的花样翻新的展览。评书人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此回淫亵已极矣”!另一方面又认为“以有素臣呈古裸虫一想,已将主意揭出,故不妨极情尽致以写之也……别家小说专以淫秽笔墨,使人读之心花怒放,诱少年子弟堕入畜生道中,不知造下几许罪孽。此书开卷揭出崇正辟邪之旨,若泛作道学话头,便如《感应篇》、《觉世经》板样。只就正面摹写,其意易竭,其书不奇,故处处用旁敲侧击之法;而淫秽之中各着一段正意,使作书大旨时时涌现,诚恐误人不知不觉之中,所以提醒之也……淫至《金瓶》,蔑以加矣。然种种花样不离交媾之时。此则变作把戏,专在牝户上设色,由用意迥别,文章现翻陈出新也”。在评书者看来,似乎只要不涉及解欲阶段,便如何放手详加描摹也不为过。
以毒攻毒、以淫制淫,是明清小说极写淫事而又心安理得的一种遁词。对猥亵小说而言,只是涂了一层淡淡的保护色而已,而作者张扬人欲的本意使得这层伪装全然失去效用。书中连篇累牍的说教在赤裸直露的性描写面前总是显得那样苍白无力。而在跨类小说中,情况有了改观,作者对性事描写的态度不再是浸淫其内,而是立身于外,欲抑先扬,最终纳之入正,所以说教与描写之间也不再是互不粘连的两张皮,而是有了一定的联系。总之,“以淫制淫”说在跨类小说中才得以全面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