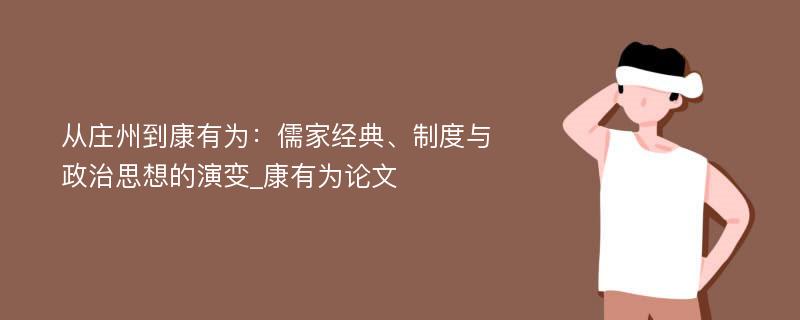
从庄存与到康有为:经学、制度与政治观念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康有为论文,观念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10-0052-06
随着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五经便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一直起着主心骨的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体现在它与统一思想、整饬人伦和建构制度这三者的密切关系上。经学在汉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其形态是基本稳定的,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清末,经学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乾嘉期间,政治相对稳定,士大夫们经世之心淡薄,热心于经学考据。但是到了道光、咸丰之际,由于外力相迫,风波渐起,士大夫逐渐不满于乾嘉考据之学细碎而不实用的做法,开始通过阐释和发挥经义来经世致用。随着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入,今文经学越古文经学而上,同时一些新思想借助今文经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使得传统的经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由此触动了中国制度与政治观念的变革。这种思想变革开始于对清代考据学的批评,庄存与、刘逢禄则拓展了今文经学经义发挥的空间,最后在康有为“以西解经”的经学思想中成型。
一 乾嘉考据学及其相关的批评
清代学术渊源于顾炎武。顾炎武认为,如果致力于考古之学,是可以通过文献考证等方法来逐渐恢复三代原貌并重新实现三代之治的。在评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时,顾炎武说:“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①在具体研究中,顾炎武也确以恢复三代古貌为根本目的,比如他在《音学五书》中指出:“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②
顾炎武对清代学术的贡献,邓实有这样一个评价:“亭林生当晚季,目睹不学之患,故首以读书哭告天下,力矫明儒之空疏无用,而以经世实用为宗,遂以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③清代乾嘉学术继承了顾炎武的复古主张,信古、征古、探古是乾嘉学术的基本追求。比如,《清史》对惠士奇如此评说:“於礼,疏通古音、古字,俱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④戴震在总结自己学术志趣的时候也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⑤从戴震的说法来看,乾嘉考据学者继承顾炎武的大致是实证主义的朴素做法,其理论核心在于以古为可稽,三代之治为可复,从而由唐宋上溯到两汉,再由两汉追溯到六经以至还原三代之治。
乾嘉之学这种实证主义的复古做法的问题在于,学者们呕心沥血以求复古,但三代制度依然模糊难辨,乾嘉考据学者自己却坠入琐碎的研究之中了。其实,关于古制古貌之不可复原,南宋朱熹在评价郑玄注《王制》的时候便明确地提到了此点。郑玄在注《王制》时,试图把《王制》展现为一套古代确实存在的完整的制度设计,朱熹对此评价说:“汉儒之说,只是立下一个算法,非惟施之当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日,亦有难晓。”⑥这就说明,汉儒的诠释未必与古人一致,因为朱熹很清楚,汉人未必说得清楚三代的制度设计,所以只能是“一个算法”。因此,乾嘉考据学者试图通过汉儒来确证字义、制度、名物,并通达古人制作的深意,其实是不可能的。
关于考据学的琐碎与粗疏,桐城派从汉宋之争的角度进行了批评。所谓汉宋之争,是指把清代考据学看成是汉学,从而与以理学为主的宋学形成对峙。在汉宋之争中,桐城派以宋明理学的继承者自居,并以理学的观点来批评乾嘉考据学者。桐城派的方东树说:“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菑畲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今之为汉学者,则取其遗秉滞穗而复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将以助农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饭,先生不得饱,弟子长饥。”⑦方东树以禾稼、舂米和“取其遗秉滞穗而复殖之”分别比喻汉儒、宋儒和清儒,指出乾嘉考据学派把精力放在考据时,遗弃了六经的义理,而仅得其粗糙、外在的东西。不过,方东树是以宋学作为六经之果实,以宋明理学来批评考据学,虽对考据学的琐碎有所批评,但还不曾在制度与政治观念上有所创新。
浙东史学派对于乾嘉考据学也有所分析和批评,这以章学诚为代表。章学诚从“六经皆史”的角度整体性地反思了乾嘉考据学。章学诚对当时的考据学风极为不满,他说:“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⑧在章学诚看来,虽然考据学者以为自己是在“求道”,但其实是坐井观天,他主张“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⑨章学诚意图使六经回归于作为先王治理之政典的本意上去,他发挥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⑩从这一角度来看,“六经皆史”的观点包含了把整个经学传统都掀翻在地的一种可能性,即抑六经为史。(11)章学诚按照自己的主张,致力于文史校雠,试图以此达到经国济世的目的,但这也是一条迂回之路,而且也是对考据学派的一种妥协,在制度与政治观念上也没有实质性的建树。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以考据为核心的乾嘉考据学以复古作为根本目的,但是复原古制的说法在理论上其实是不可能的,这导致了考据学落入了琐碎且无济于事的状态中,并且在制度与政治观念上难有建树,并遭受了其他各派学者的批评。同时,对考据学进行批评的两路批评者在政治与制度观念上也没有什么创新,乾嘉时期较为稳定的生活状况还不曾刺激起人们对制度与政治观念的反思。有清以来,因为经学处于绝对的主流地位,所以,哲学的、政治的观念曲折的革新与突破,依然要在经学中才能展开。但是,这种展开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与当时学术氛围的交叉离合中慢慢获得自身独立性,并且逐渐积累出一种思想革新的力量,这种曲折但意义重大的革新便寄托在今文经学之上。
二 庄、刘之学:从“至圣之法”到“三科九旨”的重构
随着清代考据学把考据作为学术核心而导致意义的流失,清代今文经学逐渐获得了独立于古文经学的存在意义:今文经学家认为乾嘉考据学局限于细枝末节的考证,忽略了孔子加于六经之中的微言大义,所以需要重新回到今文经学传统中去。但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也与清代考据学的文献观念有一定的关系,支持今文经学的学者认为,由于西汉今文经学与先秦有着未曾完全断裂的传承,所以从文献的角度来说,今文经学是值得信赖的,不过,今文经学没有停留在文献立论这一层面,今文经学更加重视挖掘今文经学的经世特性。由于时代的风波渐起,道光、咸丰以后的今文经学家,尽力发挥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并以此应对乱象丛生的时局,继而倡导变法、盛谈改制,从而在经学内部杀出一条制度与政治观念转变之路,使今文经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板块。
清代经文经学大行于世是在道光咸丰年间,但其开端却早在道光之前,并与庄存与有密切的关系。庄存与和戴震同时期,不过其仕途和经历以及学术取向都与戴震截然不同。庄存与久居京师,曾任上书房、南书房行走,并教授成亲王,因此,庄存与很多经学著作都与其教授王室子弟有关,这种经历自然也会对庄存与的学术风格有所影响。庄存与推崇春秋公羊学,在当时学界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人们都斤斤于文字训诂的时候,庄存与学术却重视《春秋》,讲求经学的义理,他说:“《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存法,示天下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12)这段话中的“辞”、“象”、“法”、“圣人之心”和“至圣之法”表达了庄存与对于圣人“微言大义”的关注以及对考据学纠结于细节的否定,这就为清代经学研究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庄存与对于春秋公羊学的推崇,也使人们把目光转向《春秋》所表达的王道思想的探索中去。
庄存与虽然肯定“圣人之心”和“至圣之法”是六经最重要的部分,但却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方式方法去探求“圣人之心”与“至圣之法”。继承庄存与开启的今文经学之路、更加系统地挖掘六经之“至圣之法”与“微言大义”的是刘逢禄。刘逢禄的做法是重构东汉何休的“三科九旨”,通过分析“三科九旨”来梳理和发掘春秋公羊学之义理。他十分推重春秋学,认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13)刘逢禄指出,《春秋》之学在于公羊学,而公羊学的核心在于“三科九旨”。他强调指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不仅如此,刘逢禄还认为五经中其他经典同样也体现了“三科九旨”的思想,他在解释《论语》的时候,便运用“三科九旨”的思想。今天看来,刘逢禄将“三科九旨”推衍到其他儒家经典的做法确实颇为牵强,但对于何休原来用来解释公羊学的“三科九旨”系统来说却是一种重构并赋予了哲学的意味,这为以后的人发挥公羊学提供了一个榜样。因此,刘逢禄公羊学研究的意义正是在于把已经快被遗忘的“微言大义”系统地整理出来,使“大一统”、“三世说”、“王鲁说”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今文经学观点作为哲学思想纳入思想者的视野,从而使人们的视线落到“三科九旨”这些今文经学条例的哲学阐发上,当这些今文经学条例与现实政治与制度状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从庄存与“至圣之法”到刘逢禄推重和重构“三科九旨”,是清代今文经学获得独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使得今文经学逐渐成为一种自足且颇具思想阐发能力的学术体系。
与刘逢禄有师弟之谊的龚自珍与魏源正是沿着刘逢禄给出的方向继续前进,进一步发挥出了公羊学在制度及政治哲学方面所具有的潜力。道光、咸丰以来,龚自珍与魏源并称。魏源留心夷务,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经学上则认为要“以经术为治术”。魏源专门对今古文之法做了细致的分辨,认为今文经学的兴起是学术发展的进步,也是复古的体现,他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于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一鲁变至道也。”(14)魏源的这一说法从学术演进与回溯的角度来论证今文经学的重要意义,虽然是以“复古为要”,但无疑也是一种要求变革的声音,因为他的目的在于“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其实质在于改变当时的典章制度。相较魏源的“以经术为制术”的研究,龚自珍则不拘泥于今古文之争,他把今文经学中的变革思想带入对现实的议论中去,并以瑰丽的文采来点评世事,从而对时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冲击。梁启超对龚自珍的评价颇为公允:“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15)龚自珍以今文经学的一些观点抨击现状,其实是对于清代僵化的制度与政治结构的一种深刻批评。
在魏源、龚自珍的时代,西力东渐已然成为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生存问题,在魏源、龚自珍的研究与诗文之中充满了“山雨欲来”之感。因此,从庄存与、刘逢禄发展到魏源与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思想,预示着在对传统生存方式的制度与政治观念上的思考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三 “以西解经”:康有为制度与政治观念的创新与比附
从庄存与的“至圣之法”到刘逢禄对“三科九旨”的重构再到魏源的“经世致用”,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其实就是清代思想面对现实状况、通过今文经学这一形式逐步寻求制度与政治哲学观念突破的过程。不过,虽然魏源在“经世致用”的思想引导下究心于西学,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也主张“以经术为治术”,但这种主张还没有触及到深层次的制度与政治观念的变革,特别是东西文化之间的深层差异还不在魏源的思考范围之中。
一直到康有为,今文经学中的思想革新才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爆发,并为现实的制度与政治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康有为借助当时的今文经学资源,通过《新学伪经考》否定了古文经学;而《孔子改制考》则把孔子树立成一个托古改制的圣人,从而鼓吹制度与政治观念的革新;不仅如此,在《大同书》中,康有为的“三世说”更是吸纳了一些西方的制度与政治观念,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代生存特征的大同世界,这就通过经学变革推动了中国的制度与政治哲学观念整体向近代转变。因此,康有为的“以西解经”的经学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革新了中国的制度与政治哲学观念;二是借用大量西方资源来比附中国传统思想或者以中国传统思想来比附西方思想。
首先,以“制度说经”的做法促使康有为将经学研究注目于制度与政治观念的思考上。在认识廖平之前,康有为早期的观点是侧重于古文经学的,正如梁启超所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应为《教学通议》)。”(16)但是据康有为自己说,他于光绪六年开始治公羊学:“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谬》,专攻何劬公者。既而悟其非,焚去。”(17)这似乎说明康有为在与廖平相见之前,已经对今文经学有所思考,但却未必有“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这种鲜明、清晰的立场。清代今古学之别,其实是通过廖平《今古学考》而显得泾渭分明的。在《今古学考》之后,廖平作《知圣篇》和《辟刘篇》主张“尊今抑古”,《知圣篇》是尊今,而《辟刘篇》则是抑古,更加彰显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差异。廖平“尊今抑古”的做法无疑对康有为有颇大的启发。对此,廖平曾说:“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巳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叔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18)康有为在给廖平的信中也曲折地提到了这件事:“惟执事信今攻古,足为证人,助我张目。”(19)
但是,虽然廖康二人同主张“信今攻古”,背后的思想关注点却完全是不一样的。廖平是“就经论经”,康有为却侧重于“制度说经”,对于二人的异同,从上面所引的廖平原话来看,廖平对此也是清楚的。由于侧重于“经例”的推演,廖平虽然明确区分今古文,但并不重视“微言大义”的阐发,因此他对于制度与政治观念的创新缺少关注,也没有思考如何打破现有的制度与政治观念,而这一点恰恰是康有为的长处。不过,虽然康有为如廖平所说“以制度说经”,但是康有为早期经学在制度与政治观念上并没有明显的革新,在康有为接触了西学之后,“以制度说经”才有了更大程度的发挥,并引发了今文经学革命性的变革。
其次,西学是康有为经学变革的另一个重大的思想资源。在进入今文经学领域之前,康有为已经开始接触西学并通过香港和上海租界了解西人的治理方式,这让康有为大开眼界,使他意识到西人不能等同于没有开化的蛮夷,而是有着高度文明的族群。康有为二十二岁(光绪五年)的时候,“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20)几年之后,康有为写作《人类实理公法全书》,借助现代性的自主、权利和平等观念对现代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做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描述。在《人类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通过人类公理与“比例”的演绎,初步构建了理想的大同世界,大同世界的基本特征便是人人有自主之权、平等以及极大的物质富裕。在这种理解之下,康有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的制度与政治观念,相对于构想出来的理想世界,中国传统的制度与政治设计在康有为看来是一种不够完美的“比例”,当这种思想与“三世说”、《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之说结合起来,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中的制度与政治观念革新便变得具体起来。
康有为通过理解现代的生存观念,制度与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使得康有为重新解读了传统的制度、政治思想。这种重新解读的突破口在于推崇《春秋》公羊学和分辨孟、荀。康有为说:“学者欲通孔子之大道,必于《春秋》求之;欲通《春秋》,必于《公羊》求之;欲通《公羊》,必于《孟子》求之。”(21)所谓“欲通《公羊》,必于《孟子》求之”,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判分,即在公羊学的框架下分辨孟、荀。随着对传统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于公羊学的接受与发挥,康有为倾向于把他所认为的传统“主防检”的生存制度造成个人得不到发展归因于荀子。康有为说:“荀卿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22)康有为的主张是,荀子开出来的“小康”之制应在摒弃之列,而这种小康之制在《新学伪经考》中又被挂在刘歆的名下。从制度与观念革新的角度来说,康有为认为,替代“小康”之制的应该是公羊学与《孟子》这一“微言大义”的思想。因此,在这种以《礼》与《春秋》的差异分辨孟荀的做法中,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主张革新传统制度,便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康有为把古文经学理解为“新学伪经”,并把刘歆解释成混淆了正统经学观念的人,曲折地把两千年来的制度与政治观念给否定了,因此包含了明显的制度与政治观的念革新诉求;进一步,康有为以今文经学的方式重回孔子,并在《孔子改制考》中以孔子为改制素王,认为孔子“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23)所谓“据乱而立三世之法”,其实正是意在打破传统的制度与政治观念,呼吁政治与制度结构的重构。但是公羊学“三世说”中并没有具体的制度与政治设计,康有为所推崇的《礼记·礼运》也仅仅做了小康与大同的区别。那么,未来应该建立一套怎样的政治与制度结构?
康有为的做法是“以西解经”,他以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来对应西方的政治观念,以此重新解释了三世观念。他说:“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此盖三统以明三世,因推三世而及百世也。……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至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24)因此,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具有现代政治观念特征的“君臣→立宪→共和”即对应着传统的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演变,这一说法使清末今文经学包含了一种鲜明的现代制度与政治观念。当然,在今天看来,康有为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比附,不过,却以经学的方式完成了一种中国制度与政治观念的转换,从而为今文经学的转变与中国的制度与政治观念向现代政治观念的迈进打开了大门,同时也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维新变法以后,今文经学本来是通过“微言大义”的阐发以应时变并促进中国的制度与政治观念的革新,但随着西学的越来越汹涌的进入之后,今文经学却走向了困局乃至式微。以梁启超为例,梁启超曾经是康有为所光大的今文学派的“猛烈的宣传运动者”,但随着他对于西学认同的程度逐渐加大,便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逐渐产生了分离,“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25)因此,总的来说,康有为的今文经学革新继承了庄存与通过今文经学寻求经国济世之“圣人之法”的做法并顺应了时代的变革,但随着对今文经学的过度发挥和“以西解经”的随意运用,今文经学本身也面临了极大的困境。因为容纳了太多的西方资源,今文经学自身性质遭到了冲淡,经学作为支持晚清中国人变革的思想主心骨,也在西学涌入的情况下成了需要淘汰之物。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中国学术逐渐接受西方的学科范式,经学作为一个类似于意识形态的意义体存在被“拦腰截断”,曾经风行一时的今文经学思潮由此销声匿迹。当然,清代今文经学已然完成了它的使命,即推动了中国制度与政治观念的演变,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打开了一条通向现代政治与制度的建构之路。
结语
从庄存与到康有为,今文经学经历了一个从复兴到极盛、从极盛到戛然而止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与制度观念转型的过程。经文经学由于自身的理论特征,在清代今文经学家(特别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新诠释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制度观念转型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新诠释对于今文经学和中国的制度与政治观念来说无异于一次大换血,今文经学的早期形态(特别是西汉)其实是侧重于强调尊王和大一统的,而在清代今文经学家们的手中却成了制度与政治观念创新的“利刃”。这就说明,真正活着的经学要与当下生活紧贴在一起,并对现实生活有所干预的。而今天中国的制度与政治哲学的创新遭遇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瓶颈,即现代制度与政治观念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呈现为“两张皮”的紧张局面,这种状态可以追溯到康有为那里,在康有为“以西解经”的做法中,其实已经包含了“两张皮”的因子。未来的经学研究似乎不可能再继续走清末今文经学与西方进行简单比附的老路,而是要从经学中更加基本的思想观念出发来寻求深入发展。但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经世思想、致力于从理论上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困境的努力,特别是在制度与政治观念层面努力探索的精神,依然值得今天的研究者们深入思考。
注释:
①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之《与黄太冲书》,中华书局,1959,第246页。
②顾炎武:《音学五书序》,中华书局,1982,第3页。
③顾炎武:《清代学问的门径》之《顾亭林先生学说》,汪学群编,中华书局,2009,第250页。
④《清史稿》之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六十八,中华书局,1977,第13179-13180页。
⑤《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455页。
⑥转引自《王制笺》,皮鹿门笺注,王锦民校笺,华夏出版社,2005,第30页。
⑦方东树:《汉学商兑》见《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411页。
⑧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答客问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第70页。
⑨章学诚:《文史通义》之《易教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第1页。
⑩章学诚:《文史通义》之《报孙渊如书》,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第153页。
(11)不过,这个巨大的效力在当时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到了民国以后才释放出它全部的威力来。
(12)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20页。
(13)《公羊春秋何氏释例序》,见《皇清经解》卷一千二百八十,上海书店影印,1988,第2页。
(14)魏源:《刘礼部遗书序》,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第242页。
(15)(16)(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63页;第65页;第72页。
(17)(20)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5集,《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63页;第63页。
(18)廖平:《经话甲编》卷一,见《廖平学术论著选集》,巴蜀书社,1989,第447页。
(19)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9页。
(2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2集,《孟子公羊同义证传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29页。
(2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5集,《孟子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411页。
(23)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孔子改制考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
(24)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6集,《论语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93页。
标签:康有为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新学伪经考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刘逢禄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