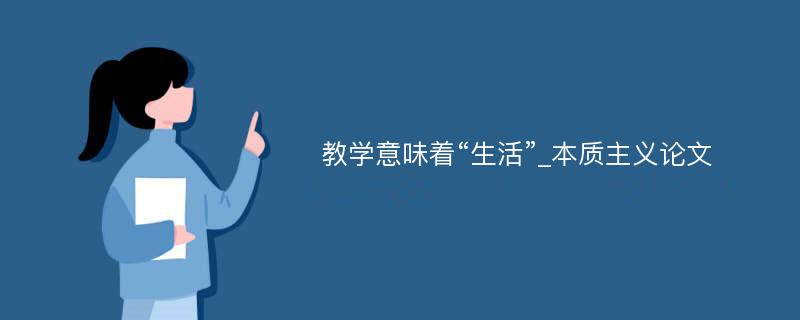
教学意味着“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的趋势之一,是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具体表现为形而上的追求和形而下的诉求两个方面。在形而下的研究中,强调教学内容与生活的联系,教学方式重视活动性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本文属于形而上的研究,仅从教育哲学的层面,提升教学过程本质讨论意义,主张赋予教学以生活的意义,以期为全面的教学价值提供前提,为我国教学的实践与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一
对教学过程的理解,是人们认识教学价值的前提和基点。在教学实践发展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都会产生对教学过程的重新理解。开始于20世纪末至今尚在进行的第二次关于教学过程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平台。(注:根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主要观点有:一是认为教学过程是具有生命的个体之间的合作交往以及与知识之间的对话过程(我们简称为“交往观”)。参见:《论教学与交往》(肖川,《教育研究》1999年第2期);《本体论中的教学与交往》(张广君,《教育研究》2000年第8期);《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叶澜,《教育研究》2002年第10期);《交往教学论的特征及理论价值》(田汉族,《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二是把教学活动的本质观定位于“教育性教学”。参见《重考教学活动的本质》(夏正江,《教育研究》,2000年第7期)。三是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师生创造生命意义的生活过程”。参见《教学本体论的转换》(迟艳杰,《教育研究》,2001年第5期)。四是坚持发展“认识说”。参见《教学认识论:被取代还是发展》(王本陆,《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在重新理解教学过程的讨论中,前三种观点的认识的角度有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研究者们都在自觉地反思和超越“教学过程的本质是特殊的认识过程”(简称为“认识说”),“要突破传统教学过程观主要是指凯洛夫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参见《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叶澜,《教育研究》2002年第10期)。)
教学过程的本质是学生的一种特殊认识过程,这种“认识说”为传授知识、发展智力的教学价值提供了前提,这是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人的态度、价值观、审美情感仍然是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的乃至首要的因素。康德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认为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因为实践理性是基础性的,它先行地为人的一切行为和认识澄明了价值前提。因此,教学的基本价值、先在性的价值追求应是实践理性、是人的伦理美德。具体来说,它包括合作、进取、坚强、责任、理想、价值观、人生观等,这些应是传授知识过程中高于知识传授的教学价值。
以往我们对教学工作的要求,都规定了教学在传授知识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但在“认识过程”的视域中,品德、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是没有理论前提和根基的,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理解教学过程。
二
“欧洲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有过一个非常相近的起因,即发现了表达式与被表达对象之间的‘意义’层。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可以被看做以各种方式对这个中间层的方法论和存在论含义的追究。”(注: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当我们使用“教学”这一概念表达式时,它与具体时空下的教学活动之间,也有一个不同于教学事实的“意义层”。在我们认识、理解教学时,我们的语言实际上都有赋予教学以意义的行为。维特根斯坦曾把“看见”(Seeing that)和“看作”(Seeins as)加以区分,(注: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210.)“看做”是看的格式塔意义,即对看到的同一事实却形成不同的意义。当我们认为教学过程本质是学生的特殊认识过程,我们实质上赋予教学以“知识论”的“意义”。
马克思说:“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这就是说,在与非生命物质相区别的意义上,人的存在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即“生存”;而在与其他生物相区别的意义上,人的存在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性存在即“生活”。“生存”与“生活”都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两者根本的区别在于“生活”是创造生存意义的生命活动。动物在它的生命活动中形成它的“生存世界”,人则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
教学是教师、学生以知识为中介的价值活动,也是教师与学生组成的人的世界。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教学过程中,人的存在先于人的认识。教与学是教师与学生的一种存在方式,教学世界也是教师和学生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创造着有意义的“生活世界”。所以,我们说在“意义”层面上,教学“意味”着“生活”。
教学“意味”着“生活”,是我们理解教学的一个认识维度,而不是要在“事实上”把教学变成一种日常生活或完全等同于社会生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谓教学是有一个把教师与学生联系起来的中介——知识(赫尔巴特语),是由受过教育的教师在一定的时空里传授知识的活动,这毕竟不同于在口耳相传的日常生活中学习。
而在“事实”层面上,教学与生活的关系,经历了融合、分化与加强联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古代,教学是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到了制度化教育的出现,尤其是在近代,分科课程基础上的班级教学的产生,知识这一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就愈来愈隔离了。夸美纽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想通过直观性原则来解决。而到杜威那里,则要把小学的低龄教学过程改变为“做中学”,教育过程体现民主的社会生活。
在“事实”层面,也就是在形而下的物器操作层面,我国也认识到了学校与生活、教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人们通过理解与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等,“加强‘书本世界’与学生‘生活世界’的沟通”。在课程改革中,加强课程与生活的联系,重视学生的实践经验,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我们现在的思考是,重新理解教学过程,赋予教学以新的“意义”,即把教学“看作”为教师与学生的“生活”。(注:赋予教学以何种“意义”,这不能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意向的作用,胡塞尔就强调“人的生存、世界的生存在最原本意义上靠自己的生存呈现、维持。”(张祥龙. 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56.)而且,只要人有分析、归纳的能力,就会概括事物的共同特征、追寻活动的意义。)
教学在“意义层面”意味着“生活”,这种“生活”是属于非实体性的范畴,它仅仅给出了我们理解教学的一个新维度。因此,我们需要把“事实层面”上加强教学与生活的联系和“意义层面”上的教学“意味”着“生活”区分开,不能混淆。进言之,我们提出“教学意味着生活”,并不是主张在“事实层面”上,完全要按进步主义教育中的激进做法去办学,也不是把教学过程变成日常生活。
三
以往教学论研究中,对生活意义的遗忘,有其思维方法上的原因,即人们持有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所谓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近代思维方式的统称,它是一种先在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注:高清海.哲学文4·传统哲学到现代哲学[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6.)人的本质、事物的本质都是现在设定的,事物过程的本质在事物过程之先、在事物过程之外被先在的设定了。教学过程的本质也是先在地、在活动之前就设定了。
这种思维方式已“被证明是与现实生活世界相敌对的”。(马克思语)因为,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寻求事物背后的“本质”,然后从中推演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因而必然忽视人此时此地的存在状况,教学过程中对知识的认识取代了对人当下存在的关怀;而教学过程中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也就不需要对当下的历史性予以询问和领悟,也不会从自己置身其中的教学世界出发,追问超越于知识的价值和理想。
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是马克思的实践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把现实的人的一切实践活动视为一切认识活动和知识的前提。他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过程思维或生成性思维是一致的。我们提出教学“意味”着“生活”,既有思维方式转换上的努力,还有如下的意义。
赋予教学以“生活”的“意义”,有助于使我们认识到,教学不仅仅是学生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或手段,也不仅仅是教师谋生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学生与教师的一种生活。教学“生活意义”的赋予,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敞开了广阔的空间,为学生和教师的自主发展提供了现实而坚实的基础,为全面的教学价值提供了前提和支点。
首先,教师和学生在传授和掌握知识过程的同时,赋予和追求“生活意义”中,才会产生伦理美德上的要求。教学的“生活意义”与其说是隐蔽的事物,不如说是我们赋予和追求的事物。教师可以在教学工作中,以自己的热情和责任感、渊博的学识和修养,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赋予教学积极的人生意义。这也就是说,对教师而言,谋生是一种生活的意义,但不是全部。对学生而言,追求分数是学习的一种意义,但也不是全部。教师和学生如果能进一步追寻“课堂生活意义”,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伦理学问题——“教与学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那些任务,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而且怎样做会做得更好?”当教师这样思考时,在他努力开启学生的心灵和智慧时,也就是在追求自己有意义的人生;当学生这样思考时,在学习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认真、负责、执着、勤奋、合作等态度和精神会应运而生。
这样,教学价值的追求就会以伦理学超越了认识论,知识的掌握与人的自主发展将得到统一,教学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既是为了人的未来、也是为了当下的积极“生活”。“倘若没有对某种崇高理想的信念为我们的一切活动注入热情与欢乐,我们便不可能获得生活的最大成功。”(注: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在教学生活这一意义世界里,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人“绽出地生存”着。(注: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92.)
其次,审美的情感也需要在生活中体验、感受和升华。赋予教学以生活意义,才会超越主客认识关系,达到主客相融的无功利的审美境界。
现代美学研究表明,“处于审美意识的物(艺术品)之所以能与人对话、交流,就在于人与物处于精神性的统一体之中,处于主客融合之中。”(注: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54.)教学中学生审美情感、体验的产生,只有在与知识的关系超越主客关系,在主—主关系中,双方才有相遇、交流、对话的可能,而这有赖于对当下生活的欣赏。进言之,在主一客认识过程阐释求知、求真的价值一维,有其理论的效准,然而一旦触及到“美的理想”、“教学之美”,其阐释功能就立即变得被动而不再有它应有的力度。这是因为“我与它”的主客认识关系不是超功利的、不是超知识性的。这也是认识论本身内蕴的不足。
而超功利的、超知识性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超越主客认识的关系,只有在当下的生活基础上才有可能。在生活中,教师和学生会以内在体验的方式参与教学,达到“我与你”的主客交融、相通。这是教师和学生体验、感受教学之美的前提。事实上,受过多年学校教育的学生或长期从事教师职业的人,都会对某一节课中自己乐而忘己、陶然自得的高峰体验状态记忆犹新,这正是一种审美体验。
赋予教学以生活的意义,教学生活既是功利的又是超功利的。师生以人的固有的尺度,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去创造、去体验教学生活的意义。这样,美怎样在认识过程中隐去,美也就怎样在生活过程中再现。
在教学过程中,道德、审美是对认识的超越,但对道德、审美的追求并不排斥对认识的追求。不论是学生的道德还是审美修养的养成,都是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展开的。
我们提出教学“意味”着“生活”,在知识价值的基础上,努力在理论上为教学追求伦理美德和审美感受提供前提和认识基础。这是时代发展对教育、对教学的要求,是20世纪以来人类生存危机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人的道德与理想的要求。其实,我国的学者已经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进行创新,新基础教育的实验就是对“教学过程是一种认识过程”的超越。因为,“新基础教育观的建构”原则之一就是“以焕发生命活力为基础的新课堂教学理论的形成”,从而突破传统的“教学认识说”。(注:叶澜.“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9.12-58.)
我们赋予教学以“生活”的“意义”,把教学“看做”为“生活”,并去体验和创造生活,实际上体现的是在对教师和学生作为完整人的关怀,是对教师与学生的生活意义的关怀,而非仅仅是对学生和对知识、智力的关注。只有这样,教师才会关注学生的存在状况,会采取人道的教育方式,会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追求人的道德、审美和自由精神,学生也会在领悟知识和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自主成长。师生在以知识为中介的教学过程中,会自觉地创造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从而实现“科学的人道主义的教学”。(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