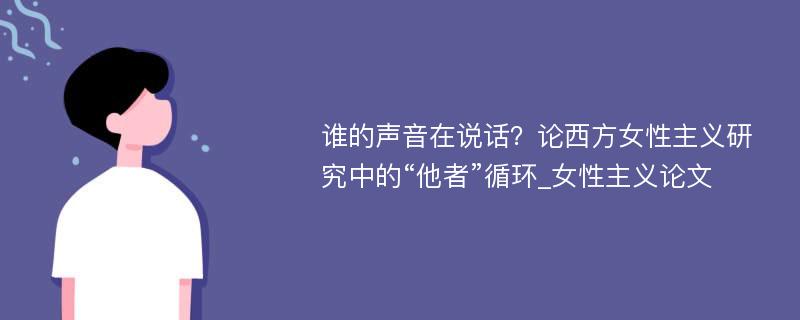
是谁的声音在言说?——论“她者”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流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谁的论文,声音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在西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如果以18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可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其作品《为 妇女权利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中为妇女的“自由、平等、博 爱”(注:Cornillon,Susan Koppelman,eds,Images of Women in Fiction,Feminist
Perspectives,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Ohio,1973,p.253.)等权利 大声疾呼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萌芽之始的话,那么,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已走过了两百多年 的风雨历程。在历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之后,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批评话语已从边缘走向了中心, 是当下西方社会内部自我剖析的一把利刃。
从历史渊源来看,毫无疑问,女性主义首先生发于个人主义高涨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的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这里的“西方”并不指与“东方”相对的一个地理概念,而 是指在世界事务中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发达地缘政治实体。从19世纪的玛丽· 沃斯通可拉夫特、夏洛蒂·勃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到20世纪的女性主义,如法国 派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海伦·西苏(Helen Cixious)、露茜· 伊利嘉丽(Luce Irigaray)和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英美派的安丽塔 ·克洛德尼(Annette Kolodny)、伊莲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walter)和迈拉·杰莲 (Myra Jehlen),无一不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精英。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通过文学与理 论文本批判着父权中心的西方社会,在文本中重构男女平等的理想。然而,就在西方女 性主义者以令人钦佩的勇气重新书写女性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却不能不引起我们 的警惕,并对其理论的合法性产生几分怀疑。这个问题是:在白人女性主义者的研究中 ,对她族裔的和来自异质文化、特别是第三世界女性作品的翻译文本的利用。以笔者20 02年秋季在美国纽约州州立大学所选的课“文学中的女性主义”(Literature Feminism )为例,在该学期的14本阅读材料中,除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三个凡尼》(The Three Guineas)外,其余分别是黑人女性文本和来自东方的文本。24名选课学生,除一名黑人 男生和两名亚洲学生外,其余均为白人女生。教师当然也是白人女性。这个个案也许不 足以说明全部问题,但从这门课所选择的材料,特别是对异质文化文本的选用却不能不 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西方文学作品和非西方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的 女性作品的翻译文本,回答这样几个问题:1.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为什么将目光投向“ 第三世界”妇女?2.对“第三世界”女性作品的翻译是否存在错误的表述?以及这种研究 背后存在的问题。
顺便提一下,“the other”在英语中指向两种性别,而“他者”在汉语中也存在着指 涉两性的模棱两可的内涵。因此,为突出文中探讨的女性问题,在本文中,特别使用“ 她者”。
西方文学传统中“她者”的建构
英国小说之父亨利·菲尔丁在其小说《汤姆·琼斯》(Tom Jones,1749)中塑造了女主 人公索菲亚,她美丽、贞洁,但毫无主见,对男人言听计从,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 是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索菲亚为早期英国小说塑造了一个西方男权社会中“劣等或差 异”(注:Williams,Merryn,Women in the English Novel,1800—1900,Macmillan
Press,London,1984,p.22.)的女性典范。这个形象在早期英国小说中十分普遍,如简· 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但随着小说的发展和女性主义思想的萌动,这个形象也在变化。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那个矮小、朴实无华、但坚强独立的女主角,可以说是 一个重大转折。随着世纪之交妇女运动思潮的蓬勃发展,文学文本中女性形象的转变在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迈出了更大的一步。这 些文学作品也成为后来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精神指导。
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被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垂青的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东方女性或 “第三世界”女性时,我们却发现这些来自异质文化的女性被凝固在历史的某个瞬间。 她们一经制造成品,就如潘多拉的盒子不得再打开,因为任何的改变将会危及制造者的 权力秩序。在其批判旨在制造“西方高贵/东方劣等”的惊世之作《东方学》
(Orientalism: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中,爱德华·萨义德将这种文本 中“她者”的建构称为“东方化”。于是,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和中国妇女的裹脚就如同 刺刻在女人脸上的“红字”一般,无法褪去。这种形象也成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妇女的条 件反射。萨义德进一步指出,东方主义不仅赋予西方表述东方的权力,而且给予它们改 变东方的合法权力,也就是给予了西方侵占东方的权力。为此,萨义德例举了法国小说 家福楼拜对东方穆斯林女性的表述:
福楼拜与埃及高级妓女的艳遇对东方女性模式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从不谈自己, 她从不表达自己的感情,谈及自己的存在和经历。是他替她言说,把她表述成这样。他 是个外国人,相对富有,又是个男性。正是这些占有的历史因素使他不仅可以在肉体上 占有库楚克·哈南姆(Kuchuk Hanem),还可以替她说话,告诉他(西方)的读者从她身上 可以看出什么是“典型的东方特征”。(注:Said,E.W.Orientalism: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Penguin,London,1978,p.10.)
在这段话中,库楚克·哈南姆所代表的不仅是西方话语中模式化的东方女性,她还是 西方霸权话语中被殖民的东方世界的隐喻——阴柔、驯服、沉默。这与具男子气质的西 方殖民者形成的反差,从理论上给予西方与东方的征服与臣服的关系以合法性。男性与 女性,西方与东方,这种根植于西方数千年的哲学思想与文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
(binary oppositions)在雅克·拉康的阳物中心主义(phallogacentrism)与雅克·德里 达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论说中得以解构。这种西方思想内部的自我解构,成为了当代女性 主义思想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而对西方文本中的东方女性形象的批判,则成为了 当代西方后殖民女性主义(postcolonial-feminism)的出发点。
福楼拜对东方女性的表述是从西方对贱民文化(subaltern cultures)的文化霸权和政 治占有的本位出发,建构“她者”知识体系的西方话语的一个典范。不幸的是,这些被 扭曲、凝固化的“她者”形象,却成了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偏执症。这些试图为西方女 性的权利摧毁男性话语的女性精英,却经常将自我的权利的获得建立在“她者”的牺牲 之上。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一直被女性主义研究者视为一篇女性的独立宣言。女主 角简·爱更是成为女权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具有女权意识的文本中的理想女性。然而,当 代后殖民女性主义先锋斯皮瓦克在其文章《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对这部女权经典进行了颠覆性的解 构。在其后殖民视角的阐释中,女主角简·爱被赋予了殖民者的文化身份。其坚强独立 、令人敬佩的形象,正是从殖民者本位出发的。而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伯莎·罗切斯特 ,男主角爱德华·罗切斯特的合法妻子诡异、贪婪、疯狂、野性的形象,代表的是被殖 民的“她者”形象。这个来自热带西印度群岛、被丑化、魔鬼化的女性,正是从欧洲中 心主义出发对“她者”的一个典型表述。简·爱的胜利是建立在伯莎的痛苦之上的。作 为“她者”,伯莎不仅被囚禁在牢笼中,她还应该坠入万劫不复之中。伯莎最后葬身火 海,象征着被殖民者在殖民战争的硝烟中的屈服。伯莎的死不仅使简·爱的身份合法化 ,而且预示着殖民者占领的合法化。
斯皮瓦克的另一篇文章《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性主义》(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了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女性的表述。在这 篇文章中,斯皮瓦克谈到了法国新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作品《 关于中国妇女》(About Chinese Women)存在的问题。这本书是以克里斯蒂娃1974年在 中国为期3周的访问为背景的。在这本书中克里斯蒂娃从一个西方女性的立场出发审视 中国妇女。其问题的症结在于克里斯蒂娃是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言人在言说。我们听不到 克里斯蒂娃所考察的对象——中国妇女自己的声音。斯皮瓦克认为克里斯蒂娃事实上是 借用这些材料和历史背景在阐释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因此《关于中国妇女》事实上成 了一本关于克里斯蒂娃自己的书,一个自恋的叙事。而用另一位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 丽拉·甘地(Leela Gandhi)的话来说,《关于中国妇女》“是一本再一次利用‘第三世 界妇女’的差异推动西方理论的文本”。(注:Gandhi,Leela,Postcolonial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87,p85.)这样看来,在 西方文学传统中,不论是男性作家笔下的东方女性,还是女性主义者自恋式的叙事,被 客体化的东方女性是失语的。她们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利,因为她们是“她者”。借用斯 皮瓦克的文章《贱民能说话么?》(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的隐喻,她们不能言 说,因为她们是“贱民”。鉴于文化本位主义的普遍性,西方文学传统中“她者”的失 语可以说是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无法指望别人对我们的表述完全公正,但是当我们 审视被移植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译本时,我们却发现同样 的问题。我们依然无法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她者”依然被片面化。翻译文本的问题 不仅是语言转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是文化权力差异造成的问题。
翻译文学中的“她者”
语言背后隐藏的经济、政治力量,决定了以该语言书写的文学的传播。从语言的权力 来看,除却正常的文化交流外,这种传播又反过来推动这一语言背后的文化对译入语文 化的征服。关于这一点,类似的例子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胜枚举。在当下全球语境中 ,英语的权力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如果说世界语曾经是人类试图重建巴比塔所做的一 种努力的话,那么英语在当前全球范围中的地位就是“自然天成”的世界语。英语的霸 权毫无疑问与老牌帝国英国的殖民史和新帝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无干系。在一篇关 于英语变体的文章中,布拉吉·B·卡克如(Braj B.Kachru)用“Englishes”一词指涉 “英语的思想、文化和精英权力。”(注:Kachru,Braj B.“World English:
Approaches,Issues,and Resources”,Reading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rown,D.H.& S.Gonzo,ed.Upper SR:Prentice,1995,p.245.)包括英语、法语、德语在 内的强势语言的文学,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翻译,从而走入其他文化,这都是因了权力的 差异,这些文化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语言文化的生产者。以英语为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当下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人们对英语的渴望。于是在“第三世界”,英语译 本,不论经典抑或消遣文字,都享受着《圣经》般的荣耀。而反观“第三世界”文学在 英语世界的处境,我们只能用“弃儿”或“流亡者”来形容了。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在其《翻译的困境》(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就谈到 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间翻译的“贸易逆差”。根据该书提供的数据,1987年全球翻译产 出中有近一半是从英语译入其他语言的。而在美国1994年出版的书中,翻译仅占2.74% 。在这些译本中,374本译自法语,362本译自德语,55本译自中文,17本译自阿拉伯语 。(注: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 of
Difference,Routledge,London & New York,1998,p.160.)这个数据首先说明的问题是 ,当下的美国是文化的制造者,而非消费者。其二,它反映了美国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 基本态度:对异质文化的怀疑。
然而,就在美国对异质文化的文本总体上持抗拒态度的同时,我们又不无惊讶地发现 有一类文本却倍受青睐,这就是“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来自阿拉伯、东亚、拉丁美洲 的女性文学,不断被译成英语,走进妇女研究的课堂,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材 料。当我们在为自己获得“她者”承认而感到欢欣鼓舞之际,却又为这一现象背后的目 的倍感悲哀。
在《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斯皮瓦克就指出西方(英 语与法语世界)在对第三世界文本的翻译中,“对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有一种近乎贪婪的 渴望。”(注: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St.Jerome Publicity,1997,p.84,p.85.)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渴 望是女性主义者传播“第三世界”女性文学的善良愿望。因为,为了摧毁或解构男权话 语,英美女性主义传统鼓励妇女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法国女性主义传统则鼓励女性“用 身体写作”。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西方女性主义者的一种企图,如路易斯·冯·弗罗 托(Luise von Flotow)所言,企图“消除西方女性主义的种族偏见。”(注:Flotow,
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St.
Jerome Publicity,1997,p.84,p.85.)
然而,甘努(Sne ja Gunew)指出,相当一部分西方女权主义者“将妇女遭受的压迫普 世化、超越种族和文化的疆界”(注:Gunew,Sneja,eds,Feminist Knowledge,Critique and Construct,Routledge,1990,p.280.)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在翻译中,这种无视地理文化差异的做法,也必然导致她们对所代言的异域妇女的误读。
勒菲费尔在其翻译理论专著《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摆布》(Translation,
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提出赞助人与翻译的关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西方女权主义者就是“第三世界”女性文学得以在西方文化 流通的赞助者,但是这种赞助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高尚行为。根据勒菲费尔的观点 ,翻译即改写,改写也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背叛。因此,如果对这些引入西方文化的 “第三世界”女性文学的译本作比较全面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两个突出的问题。首先 ,这些译本的主题鲜明,或者说单一。一个倍受青睐的主题就是父权压迫下女性的苦难 及其反抗。她们或在反抗中毁灭或偶尔胜出。这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重复着父权社 会中妇女的悲苦命运,并为西方女性主义者为何要颠覆男性话语的理论提供了非常有利 的理由:因为我们苦,所以要颠覆。在这方面,阿拉伯世界的女性文本十分符合条件, 因而大受欢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不共戴天的纷争由来已久,这一点从前 文韦努蒂提供的数据即可见一斑。因此伊斯兰妇女文本在西方世界的流通就不能不让人 思考。卡巴夫(Mobja Kabf)在其著作《穆斯林妇女的西方表述》(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uslim Woman)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她说:“绝 大部分的西方表述都围绕着穆斯林妇女遭受的伤害这样一个中心。”(注:Kabf,Mohja,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uslim Woman From Termagant to Odalisqu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9,p.10.)译入西方语言如英语的阿拉伯文本,如《打 开这扇门:20世纪阿拉伯女性主义文学——阿拉伯女性作家选集》(Opening the Gates :a Century of Arab Feminist writing),激进女作家莎达维(Nawal el Saadawi)的《 零点的女人》(Woman at Point Zero),都将女主角的身份定位为男性憎恶者或男性的 受害者。Haideh Moghissi认为,西方读者对这些译本的反映必然是“十分同情原教旨 主义统治下倍受摧残的妇女”。(注:Moghissi,Haideh,Feminism and Islamic
Fundamentalism,The limits of Postmodern Analysis,Zed Books,1999,p.vii.)比如 在《打开这扇门》中,数十篇文章历数了20世纪阿拉伯世界中不同社会阶级的女性遭受 的痛苦及她们对父权社会的刻骨仇恨。从某种程度上说,《打开这扇门》犹如让西方读 者打开通往阿拉伯世界的大门,目睹阿拉伯妇女的血泪史。因此就译本的主题来看,西 方女性主义者赞助着“第三世界”的女性文学在西方的译介,目的是促进自己的理论研 究。
勒菲费尔在《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中还提出:“赞助人通常更注重文学的 思想意识,而非文学的诗学”。(注: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Routledge,1992,p.15.)这也解释了为何流通于 西方的“第三世界”女性文学文本更像是一种纪实性的报告。出于其研究的意图,女性 主义译者往往缺少对译本文学性的考虑。译者翻译中考虑更多的是异质文化妇女信息的 传递。由于模糊了虚构和现实的界限,这些文学译本更像是他文化妇女的真实报告。事 实上,在选择文本时,对“第一人称”叙事的偏爱也是促成文学文本真实化的一个原因 。以《打开这扇门》为例,选集中大部分都是“第一人称”叙事。《零点的女人》讲述 的是美丽的乡村女孩费蒂尔斯如何沦落为一名妓女,最终因杀死一皮条客而被送上绞刑 架的悲惨的一生。小说“第一人称”的自述,将费蒂尔斯在男权社会遭受的层层压迫及 其内心对这个世界的仇恨,表达得淋漓尽致,仿佛是阿拉伯妇女的生活镜像。原作者萨 达维本人就是阿拉伯世界一个罕见的女权主义者。她曾因其激进的思想而流亡他国。她 的写作充满了政治性。在一次访谈中,萨达维在谈到《零点的女人》的创作时就说,“ 《零点的女人》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这个真实的女人是如此地打动我,以致我就当她 是真实的来写。想象仅占20%,可能仅10%。”(注:Badran,Margot and Miriam Cooke,ed.Opening the Gates:A Century of Arab Feminist Writing.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402.)这种将小说生活镜像化的创作方法在其被引入异质文 化中时,西方读者的反应很有可能是将之视为他文化的纪实性报告——人种学档案。被 操纵的译本更印证了西方读者原来从西方文学文本获得的模式化的她者。弗罗托对此批 评说,这样的文学译本“建构了符合西方品味的‘第三世界文学’及‘第三世界’”。 (注: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St.Jerome Publicity,1997,p.84,p.85.)
如果说上述的批评是针对译成强势语言的“第三世界”女性文学的,那么巴西学者艾 洛乔(Rosemary Arrojo)的《占有性的爱的阐释:海伦娜·西苏,克拉丽斯·李斯贝克 特与忠实的矛盾》(Interpretation as possessive love:Helen Cixous,Clarice
Lispector and the ambivalence of fidelity)就是针对“零翻译”的。西苏是法国新 女性主义的三剑客之一。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西苏就开始系统地研究巴西女作家李斯贝 克特,李斯贝克特的作品为西苏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为了做到绝对“忠 实”于李斯贝克特的作品,西苏杜绝其学生使用任何李斯贝克特已出版的法文译本,这 样她的学生对李斯贝克特的理解就只能完全依赖于西苏的法语阐释。但是,罗斯玛丽· 艾洛乔批评道,西苏对原作的“忠实”——
事实上是对原作的一种干预,一种改写。在这一改写中,省略和误引改变了作者的原 意,误导了读者。同时,这一改写常常无视李斯贝克特使用的葡萄牙语,或将葡语视为 法语的完美译文。(注:Arrojo,Rosemary,Interpretation as Possessive Love,Helen Cixous,Clarice Lispector and the Ambivalence of Fidelity,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ed,
Routledge,1999,p.151,p.160.)
在这个案例中,原作者李斯贝克特与译者西苏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置换。西苏对李 斯贝克特文本的阐释已大大超出“创造性叛逆”的范围。借用格弗荣斯基(Gavronsky) 关于翻译的隐喻,西苏的“忠实”,实际上是一种“食人”式翻译,即译者将原作囫囵 吞下,而后用自己的语言再生产出一个与原作者完全割裂的文本。这样“原作遭到俘虏 、强暴,从而发生乱伦”。(注:Garonsky,Serge,“The Translation:From Piety to Cannibalism,”Substance,16(1977):p.60.)事实上,纵观世界翻译历史,翻译中的“ 食人”行为不仅出现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过程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追溯至古罗 马时期对古希腊文本的任意宰割,也发生在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抗进程中,如巴西 后殖民翻译理论中的“吃人”论。其实,我国近代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对西 方文学所做的许多翻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行为呢?而西苏对李斯贝克特的阐释应该属 于前一种,即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操纵。艾洛乔犀利地批评道:
西苏对李斯贝克特的文本研究远非只是解构了男权压迫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它 将这种二元对立与父权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西苏的解读事实上反映了一种 对待“差异”时所持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态度”。(注:Arrojo,Rosemary,
Interpretation as Possessive Love,Helen Cixous,Clarice Lispector and the
Ambivalence of Fidelity,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ed,Routledge,1999,p.151,p.160.)
因此在西苏的阐释中,我们听到的并不是原作者李斯贝克特的声音,而是西苏“自恋 ”的声音。于是,这有幸走进女性研究的“第三世界”女性作家依然是“失语的流亡者 ”。斯皮瓦克在《贱民能够说话吗?》一文中有一句相当精彩的话:“贱民是不能够说 话的,也就是说,即使贱民冒肝脑涂地的危险发表自己的意见,她的言说也是不会被听 到的”。(注:Spivak,G.“Subaltern Talk:Interview With the Editors 1993-94”,in The Spivak Reader,D.Landry and G.Maclean,ed,Routledge,1996,p.292.)
越南裔学者特瑞恩·T·明和(Trinh T.Minh-ha)在其著作《女性、本土与她者》
(Woman,Native,Other)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她指出,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 运转使“第三世界”女性专题得以在西方流通,但是这种流通“只是在为将‘第三世界 ’女性视为更加不幸的姐妹的‘第一世界’女性的特殊性作广告而已。”(注:Gandhi,Leela,Postcolonial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87,p85.)另一著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者钱德拉·T·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在其影响深远的文章《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学术和殖民话语》(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中也谈到西方女性主 义话语中存在西方女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存在的等级分野。她说:
西方妇女是这样表述自己的:富有教养,摩登,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有自控能力,而她 们表述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则“无知,贫穷,传统,驯服,家庭型,受害者”。(注 :Talpade Mohanty,C.“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reprinted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 ,Patrick Williams & Laura Chrisman,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 4,p.200.)
这种话语逻辑的结果,必然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在对待“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时采取一 种高人一等的学术态度。她们在“第三世界”女性文本中试图解构西方男性中心主义话 语的时候,却又不由自主地在自己的理论中建构起“自我”与“她者”的二元对立—— 一种西方女性中心主义思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对“ 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研究存在着一种殖民主义者的态度。
结语
当我们将话题转到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上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对我们的了解 还太少,而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也不多。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国学界为了拉近与世 界、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的距离,大量译介西方的文学及文论。反观西方强势文化对中 国文学的译介,可以说寥寥无几。其原因除意识形态的影响外,早已模式化的中国观念 使中国文学进入西方世界的步履异常艰难。比如在美国,要想看到中国文学的译作是十 分不易的,即使有幸被译介过去,也常常存在着有失偏颇的阐释,特别是政治性的。而 中国女作家的作品更是少见。学者朱虹在谈到十几年前(1990)将我国女作家短篇小说译 介入美国时这样说道:“…美国很少能看到中国女作家的译作的”。(注:《读书》199 7年第4期,第130页。)时隔十几年,这种境况并未有大的改观。当一名美国大三学生拿 着一名华裔作家的有关上世纪一女子杀夫的中国小说兴冲冲地对我说他正在看一本著名 的中国小说时,我不知作何回答;当一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她的房东奇怪地问她为何没 有裹脚,我无言以对;而当我在“文学中的女性主义”课堂上阅读着一个旅居南非的中 国女作家的短篇小说《红色的杜鹃花》(Red Azalea)——一个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时 期的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日本女作家作品中透露出来的“灰色”的中国时,我的 心中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郁闷。
真正的翻译,沟通的不仅是两种语言,还应该是两颗心灵。但是在这个权力争锋的世 界里,译者不可能真正传达“上帝”的意旨,于是渴望沟通的心灵依然被蒙蔽。当人类 欢呼“全球化”的到来,以为可以用同一个声音言说的时候,却发现我们从未真正互相 了解。炮火取代翻译,世界依旧延续着人类历史绵绵不断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