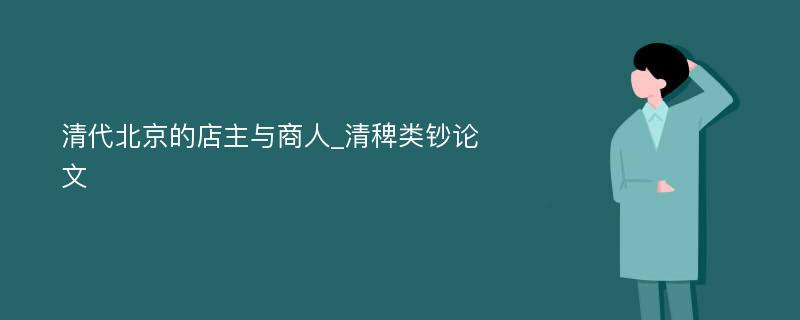
清代北京的铺户及其商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铺户论文,清代论文,北京论文,商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步入近代之前,中国的传统城市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阶层,但是,城市生活中的商业流通与货币需求,使得商人成为城市中的主要居民,并在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充当了主要的角色。但是,正如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城市的建立有为收取货币地租与各种赋税的目的[1],为的是满足官僚政治体制下的封建经济的需要。这就使得中国商人在社会角色上也难以摆脱地主经济附属地位的影响,处于两难当中。
通常,我们对历史上商人的考察,往往着重于资本规模、经营方式、资本流向等等,而本文则更关注商人在城市中的社会角色,试图通过对京城中有一定影响力度的商人与政府及其统治者关系的考察,能对上述问题有所回答。
一、铺户及百年老店
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在清代前期,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作为都城,不仅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也是贵族官僚、文人士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而且聚集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向被称作“商贾辐辏之区”。而京城消费型城市的特点,也使它形成了商业比手工业发展、官商优于私商等特点。在众多的商人中,他们通常都是以“铺户”作为个体从事商业活动的。
所谓“铺户”,是指开店铺的人户,是封建政府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对商人的称呼。由于店铺是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铺户的称谓也应当在封建社会后期才出现,而清代不仅官方文献《清实录》中有“铺户”的记载,即便是私家笔记中也有“铺户”的称谓出现。
铺户,非走街串巷的小贩,亦非在街肆摆设摊位的摊贩。通常,铺户都有一个带门面的店铺,只是经营规模大小不同,大多数的铺户都属于小家小户的买卖。而且除了杂货铺之外,铺户往往是经营着某一种单一的商品。在晚清人撰写的《燕市积弊》中,所列京城铺户有:钱铺、钟表铺、挂货铺、绒线铺、鞋铺、药铺、金店、翎子铺、首饰楼、当铺、香货店、嫁妆铺、红铜铺、纸铺、纸马铺、面铺、香蜡铺、米碓坊、蒸锅铺、裱画铺、漆铺、黄酒铺、南果铺、切面铺、刻字铺、喜轿铺、寿衣铺等,近三十余种。而每一行业的铺户又有数十家、数百家之多,如“以京都而论,大小药铺,足有三四百家”;“翎子这行买卖,向来是山西人所作,以北京而论,共四十余家”;当铺,“以北京计算,共有一百五十余家”;香货铺,“这行出在北京,并没有几处,就是这两三家”,等等。[2](P16)
在这些众多的铺户中,尤以来自山西和山东两省的外地人居多。清人夏仁虎有过评论:“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盖北京土著多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绸缎肆率为山东人所设,所称祥字号多属孟氏。初惟前门之泰昌为北京人,盖兼办内廷贡品者,各大绸肆必兼售洋货。”[3](P102)《燕市积弊》也对夏仁虎之说提供了佐证:切面买卖“在北京城里开铺子的分两路人:一是山东,一是直隶。”“蒸锅铺的买卖儿发明最早,凡在北京开设的,全是山东人多。”“北京的漆铺大半都是山西买卖。”[2](P82)
这些铺户主要分布在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以及菜市、花市等北京内外城的主要商业区[4](P16),而以外城的正阳门一带最为集中。
事实上,早在明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前后,北京的正阳门周围及两旁的大街便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区,聚集起众多的铺户。“明末市肆著名者,如勾栏胡同何关门家布、前门桥陈内官家首饰、双塔寺李家冠帽、东江米巷党家鞋、大栅栏宋家靴、双塔寺赵家慧苡酒、顺承门大街刘家冷淘面、本司院刘崔家香、帝王庙前刁家丸药……凡此皆名著一时,起家巨万。……富比王侯皆此辈也。”[5]进入清代,随着内城汉人的整体向外城迁移,正阳门形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品流通市场,而铺户之集聚居全国之首。如《都门纪略》云:“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6](P402)余蛟在《梦广杂著》中亦曰:正阳门外“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6](P417)其中不乏被誉为“老字号”、历经明清达百余年的铺户,如六必居、王麻子、王致和、烤肉宛、同仁堂、都一处、和顺居、天福号、内联升、便宜坊、全聚德、正明斋、瑞蚨祥、荣宝斋等。因而,晚清时夏仁虎在谈到这些铺户时,有“各不下数十家,互称老铺,争执可喙”[3](P99)的议论。
由于资料的限制,对于京城铺户的发展状况难以作深入的研究,但是,铺户及其商人对京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散见于时人的记载当中的。这些铺户在发展的过程中各自走出自己的道路,也形成独特的经营理念,但却摆脱不了传统社会的影响。其中,最知名的同仁堂也最为典型。
在药业行业中,虽清代京城中有大小药铺三四百家,但“四远驰名”,饶有诚信者当属“同仁堂之丸散膏丹,西鹤年之汤剂饮片”,而同仁堂尤其名气大作。
同仁堂坐落在正阳门外的大栅栏,为乐家所创,乐家原籍浙江宁波府慈永镇,明永乐年间移居北京,以串铃走方行医为业。清初,乐家四世祖乐尊育(1630-1688)敕授登仕郎,为太医院吏目,掌管出纳文书,后晋文林郎。五世祖梧冈字凤鸣 (1661-1742)因乡试落第,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创办同仁堂药店。所以有称同仁堂“明已开设”,似不准确。但同仁堂为“京师药铺之著名者”确是当之无愧的。其时,“外省人之入都者,无不购其硇砂膏、万应锭以为归里之赠品”。[7](P2297)雍正元年(1723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因此声誉日隆,以后同仁堂经历了盛衰的变化。乾隆十八年(1753年),乐家遭受火灾,第六代掌柜乐礼病故,同仁堂药铺难以维持,乐礼之妻申请主管衙门资助。由于皇家需要同仁堂药房,便出示招商,由乐家世交张世基认股合资经营。此后,同仁堂的股份越来越多,由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一张合股经营的废合同上可以看到,同仁堂的股东有21人,股银43800两。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同仁堂以价银60000两典给了朱某。[8]这期间,同仁堂屡经变迁,但不变的是挂在药铺前的“乐家老药铺同仁堂”的匾额。传至乐家十代的乐平泉,终于还清债务恢复祖业。乐平泉死后,同仁堂由其四子共同经营,形成四大方共管制度。
同仁堂的发展说明晚清时京城的某些铺户中已经出现了股份制经营,同时说明一些老店亦须得到封建政府的扶持,方能步入其老年的辉煌。其商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附着于传统社会关系之上。而且这种现象似并非特例。与同仁堂不分伯仲的“鹤年堂”,其大门里外所挂的匾额分别为明代权臣严嵩、严世藩父子所书。以酱羊肉闻名的月盛斋,“铺在户部街,左右皆官署”,“此斋独立于(官衙)中者数十年,竞不以公用征收之。”其原因除了“以酱羊肉出名,能装匣远赉,经数月而味不变”[3](P98)外,更在于月盛斋包揽承做清代用于祭祀的“全羊”。[9]
二、专做旗人生意的老米碓坊
作为大都市的北京,人口最为集中,粮食消费量也最大,且北京东郊的通州又是南方漕粮运至北方的终点。清前期,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漕粮经过运河运到北京城东的通州,每年约有五六十万石不等。因此,粮食业是京城的大行业之一,从事粮食业的商人形成不小的群体。他们当中有从事贩运粮食的行商,也有开店经营的铺户。
据文献记载,清代北京的粮食业最初掌握在山西人手中。但是,随着山东人的插足,山西人逐渐失去了对粮食业的垄断地位。咸丰年间开业的大顺粮店(崇文门外平乐园大街)是最早的山东铺户之一,随后由于同乡亲友互相援引,山东人经营粮业的铺户日渐增多,逐渐取代山西人掌控了粮食业。而在这些从事粮食业的铺户中最可论及者,当为最初由山西人创建的“老米碓坊”,它对京城的旗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米碓坊原本是从事米业加工兼及销售的铺户,但随着旗人口粮及禄米对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及利润影响的加大,老米碓坊开始专做旗人生意。而这一行业的出现与清政府对旗人的管理方式和旗人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时,凡属旗人,每月由朝廷发给钱粮,有官职和爵位者另发禄米。“这种口粮和禄米都是由南方漕运而来,存在仓内,陈陈相因,米色变红,故称‘老米’稻谷。米色好看的皆备宫中之用,这‘米色红朽’的老米除了供给旗人之外,还是六品以下官员的官俸。老米须经加工碾出米来才能食用。当时,由山东人开设的米碓坊备有碾碓承揽老米加工,其加工方法是将稻谷掺上白砂,用脚蹬石墩反复轧磨,磨去稻壳和糙皮,再经扇扬,即成净米。”[10]这种笨重的加工方法劳动强度很高,后虽改用槽碾,用牲口拉磨,却仍属于体力劳作,并非易于赚钱的行当。但是,随着老米碓坊在从事米业加工的同时,开始兼营高利贷,事情便发生了转变。
最初是旗人把老米加工的事委托给碓坊,并由碓坊代为办理领取口粮或禄米的手续,加工后直接得到净米,而碓坊则扣除一部分米作为加工费用,两相便利。但旗人大都不事生产,习惯于悠然自得,吃喝玩乐,每月领到的钱粮往往用不到月底。于是,就向碓坊预借,寅吃卯粮,碓坊便乘机加增工费,并对预借钱粮部分加收重息。而旗人为了救急,也只好任其盘剥。双方便逐渐形成了高利借贷关系。久之,许多碓坊竟然依靠对旗人的放贷致富,而旗人一旦进入高利贷的罟中,其家用生计越发依赖于此,也只能任由老米碓坊摆布。
虽然清政府严禁八旗官兵将领得的禄米或米票转让给铺户,却又不得不“听其自行售卖”。原因在于,旗人所支禄米,除供自己消费外,总有一部分剩余。大体上,“官兵俸粮留食者三四分,官局收买者二三分,余俱在外流通,奢济民食”。此外,对于八旗富户而言,禄米的转卖可以调剂粮食品种。据记载:“京师贵人家以紫色米为尚,无肯食白粳者”。百官、旗人等往往将领得禄米的多余部分“贱价售之米肆,而别籴肆米以给用”。[4](P68)这样一来,钱粮禄米就流向经营米的铺户,因京城人的生活习惯演变成市场行为,不易禁止。还有一部分“忽于生计,习为奢侈”的旗人,“饷银一经入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赀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予铺家,祗顾目前得钱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11]当时,内外城的老米碓房不下千余所,他们专门收购旗人的口粮和禄米,旗下兵丁也靠他们取得银钱使用,这些粮商铺户便逐渐控制了旗人的经济命脉。
据清光绪时人夏仁虎记载,其一旗籍友人曾议论说,清之盛衰皆因山东人。所谓“盛”,是指山东籍的三顺王降清,即“至皮岛之四将归(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而势力遂入关内”。[3]而其衰也亦由之,是指旗人在经济上受制于山东人经营的老米碓坊。由于旗人“世族俸银米悉抵押于老米碓房,侵渔逼勒久,遂握有全部之财权。因债权故,碓房掌柜之乡亲故旧稍识之无者,率荐入债家为教读,遂握有满族之教权。于是,旗籍人家无一不破产,并其子弟之知识亦无一不破产矣”。[33(P95)对此,夏仁虎认为,“语虽近激,亦非无因”[3](P96),并以身边的实例予以证之。
夏仁虎讲述曰:“昔居内城,邻人某满世爵也,起居阔绰如府第制。一日,余家人偶至街头老米铺,俄一少年至,视之,即邻家之所谓某大爷者。见铺掌执礼若子侄,而铺掌叱之俨然尊长,始以骂,继以诘,少年侧立谨受。俟威霁始嗫嚅言:‘今日又有不得已之酬应,仍乞老叔拯之。’铺掌骂曰:‘吾安有钱填若无底壑?’少年曰:‘秋俸不将至乎?’铺掌冷笑说:‘秋俸乎?汝家一侯二佐,领世职俸,养育孤寡,钱粮算尽尚不酬所贳也?’少年窘欲泣,铺掌徐捡松江票四两掷予之曰:‘姑持去,知汝需演探母也。’市井恶棍指逛窑也。少年感谢持去。家人归述之。……然则碓房握满人财权说诚可信。”[3](P96)《燕市积弊》中也说,老米碓坊“名为卖米,其实把旗人收拾的可怜,只要一使他的钱,一辈子也逃不出他的手”。[2](P81)
类似的故事,满族的后人也偶有讲述。现代作家老舍以自己在幼年时的亲身经历叙述说:“在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甲午海战等等风波之后,不但高鼻子的洋人越来越狂妄,看不起皇帝与旗兵,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而且威胁从此不再记账,连块冻豆腐都须现钱交易!”[12](P25)
可见,清代的八旗食俸制度在确保满人的经济特权的同时,也将入关后的八旗子弟培养成养尊处优、不农不贾、无所事事的社会庸人。而商人凭借其经济力量可以对王侯子弟大呼小叫,则表明封建社会的贵贱等级秩序在金钱面前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但需要指出的是,旗人与老米碓坊虽结成一种“依存”关系,京城的粮商铺户虽然成为部分旗人的债权人,但对于官僚体制却没有产生影响。实际上,粮商同所有的商人一样,其财富及资本的积累往往要受到政府相关政策的制约。
据记载,“乾隆年间通州商人在东关设有永茂、永成、福聚、涌源等四大堆房,专供粮商堆贮之用。每麦一石,无论停贮久暂,租价一分。等青黄不接之时,粮价昂贵之日,商人们再转卖给京城及通州本地铺户,以博数倍之利。仅乾隆四十二年,商人张雪如等二百二十余家粮店,自各处贩运麦五十三万九千余石,平均每户商人一年运来近四千五百石之多。”[13](P10)嘉庆、道光以后,运河因常年失修,遂至废弃,漕粮由运河改道海运,通州的重要地位丧失,建于乾隆年间的通州“四大堆房”有三家先后倒闭,只有永成一家在咸丰十年还在维持经营。[13](P41)这表明,附着于封建经济体制上的商人,其发展、衰落都与封建国家的政策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钱庄票号——京城铺户中最大的买卖
与粮食业一样,钱庄票号也是京城的主要行业。时人称曰:“钱当两行,为商业中最大的买卖。能够流通市面儿且与人有极近关系者,莫过于钱行。”[2](P85)其时,北京城众多的消费群体,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活跃,也直接促进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金融业”的发展。由于清代是银钱并用,且银钱比价不定,因此,在近代银行建立之前,银钱兑换的需要,吸引了商人们去经营银号和钱庄。
北京的银号铺户,最早由浙江绍兴人创建于康熙六年(1667年),名为“正乙祠”(因供奉正乙玄坛老祖,即赵公明),也称“银号会馆”。时“正乙祠”在正阳门左右列肆而居,“操奇赢,权子母,以搏博三倍之利”。[13](P11)此外,还有一些兼营钱庄生意的铺户。如“有柳泉居者,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资本厚而信誉坚,存款取息极微,都人以其殷实可靠,往往不责息。有存款多年,往取而银之原封曾未动者。”[3](P96)但是,京城“金融业”的迅速发展是在晚清。
在光绪庚子(1900年)以前,“京师钱市通行之物凡四种:一、生银(银锭、碎银);二、大个儿钱;三、银票;四、钱票。盖当时银钱虽通行于津、沪间,而京师则以国库出入俱用银两计算……银钱二票,为票号、钱店、香蜡铺(兼兑钱)所发行”。[7](P2292)所以,银号所经手的主要是大宗的银两,钱庄票号经营的主要是银钱兑换、发放“帖票”,并兼营存放款项等高利贷业务,其下还有所谓“香蜡铺”、“烟蜡铺”者,专作兑钱。
当时,虽有英法等外国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上侵入京城的各个领域,但大小银号、钱庄仍然生意兴隆,并形成了号称“四大恒”的“都中钱肆巨擘”。所谓“四大恒者,京师有名钱肆也,凡四家,其牌号皆有一恒字”。[7](P2292)即“恒和”、“恒利”、“恒源”、“恒裕”四大钱庄。《旧京琐记》曰:“银号首推恒和、恒肇等四家,谓之四大恒,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此外,钱庄票号的汇兑业也很发达。“汇兑庄亦曰票庄,皆山西人,交游仕宦,最为阔绰。有外放官吏,百计营图以放款,即京官之有外任资格者亦以奇货居之,不惜预为接济,然失败者亦往往而有。”钱庄“其下者为钱铺,外城则专与汉官往来。彼时朝官有定员,官之资格,铺人知之,且有外任之望,此辈钱铺随时接济,便利殊甚。”[3](P95)而汇兑业的发达不独士绅官僚的身家前程与之发生了关联,就连普通旗人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此行当。在老舍的笔下就曾提到,他的母亲在领回每月发放的俸银之后,就手儿在街上换了现钱。那时,“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钱号银庄一样,也兑换银两”。[12](P24)
但是,这些随处可见的钱铺、烟蜡铺却并非尽为诚信之家。“所谓烟蜡铺,亦兼兑换业,并出钱帖,往往出帖既多,随时关闭。”[3](P97)虽然清政府对经营钱铺的商人原则上要求“五家互出保结”,以防止奸商“关铺潜逃”,但欺诈谋财的案件还是时有发生。为此,朝廷官员多次提出予以制裁。《都门纪略》一书中,也对初来京城的人告诫曰:“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钱,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14]
在投机生意也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一些商人不择手段,纷纷承揽汇兑业务,甚至把获利的目标对准了以钱买官的“捐纳”。有记载曰:“金店者初亦作金珠贸易,至捐例大开,一变而为捐纳引见者之总汇。其上者兼能通内线,走要津,苞苴之入,皆由此辈,故金店之内部必分设捐柜焉。其掌铺者,交结官场,谙习仪节,起居服饰,同于贵人。在光绪季年,各种捐例并起,业此者莫不利市三倍,然皆非本业也。故讥之曰:‘金店之金在其招牌上所贴之金箔。’”[3](P97)这里,所记载的是官僚政治的腐败,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的京城,尚未成熟且不规范的“金融业”,其触角已经伸向了每个可以盈利之处。
可以说,钱庄票号的发展说明了中国封建经济自身的发展水平,即便没有西方的入侵与“冲击”,中国也将会以自己的方式在适当的时候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然,西方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毁了大栅栏一带繁华的商业区,“银号、钱庄、典铺一律停闭,市面萧条”。中国旧式的、但却在不断发展着的金融业先驱——钱庄票号,在这重重的一击下,变得一蹶不振。由于“京中银源顿竭”,清政府不得不拨出库银一百万两借给四大钱庄,“令其规复旧业”。[13](P11)
由此可见,金融业对于一个城市特别是对于都城的重要性。在这场变故中,从政府直接出面扶持并干预可以看出问题。
四、拥有诸多铺户的富商
有记载曰:“运盐者曰盐商,开质库者曰当商,售木材者曰木商,此三者之在闭关时代,皆为大商。”[7](P2292)但就京城的实力派商人而言,却并非盐商、当铺商和木商,而是与官僚、贵戚乃至朝廷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那些大商人或御用商人。这些商人也是由铺户起家的,但他们往往拥有诸多个铺户,兼营几个行业。
据生活在乾嘉时的礼亲王昭梿记载,京城殷富之家有祝氏、查氏、盛氏等。他说:“京师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15](P434)祝氏的居邸在崇文门外板井胡同,最盛时曾在外城建有园林,称“祝氏园”。“祝氏园向最有名,后改茶肆,今(清乾嘉时期)亦毁尽。”这位自明代就以巨富显名京城的米商,直到同治、光绪时仍然称富,被称作“米祝”。米祝“自明代巨商,至今(晚清)家犹殷实,京师素封之最久者,无出其右”。[4](P123)如前所述,清代的米商能在清末依然占据商界鳌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旗人的日渐贫困、大量出卖、赊欠禄米有直接的关系,而这种现象也正是清代衰亡、社会面临变革的征兆。然而,由于资料的匮乏,米祝的具体经营状况无从得知,这里也就难以得出相关的结论。
如果说米祝是靠经营起家的实力派商人的话,那么京师的盐商查友圻便可称之为与官府关系密切的商人,其为结交权贵不惜挥金如土。时人记载曰:一日,查氏赴内城官府燕宴,至日夕,“令仆告正阳门守役,迟一时下钥。次日为御史所纠,乃言因某事欲助帑数十万,是日不出城则不得资也”。[16]查氏以一商人竟敢传呼正阳门守役打破城门以时启闭的常规,足见其在京城的势力之大,而声言助帑十万于官府,不仅说明其家赀之巨,也证明了他与官府的“献纳”关系。对此,昭裢也有论及曰:“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与祝氏)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结士大夫以为干进之阶,故屡为言官弹劾,致兴狱讼,不及祝氏退藏于密也。”[15](P434)
在与朝廷、官府及贵族官僚关系密切的商人里面还有两位米商,声名、家世同样显赫,这就是山西亢氏和范氏。
亢氏,山西平阳府(今临汾)人,人称“亢百万”。亢氏以盐业起家,在两淮盐商中有“南安北亢”之说,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系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而北亢即为亢氏,这足以说明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此外,在业盐的同时,亢氏在其家乡山西平阳还开设了典当业,系诸多山西典当商人中资本最为雄厚者。据称,在康熙年间,《长生殿传奇》新版剧目刚刚发行,亢氏便“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17]
但最值得提出的是,亢氏还是一个大粮商,在京城的粮商中占有重要一席。如前所述,清代京城的粮食贸易规模很大,从事粮食贸易的商人众多,亢氏以其雄厚的资本既致力于长途贩运,也经营粮店,其铺面主要位于正阳门外。据说,因其名声在外,曾有人企图在运粮途中劫夺亢氏远道贩运的米粮,后被一位王爷获知,“拔刀相助”,才免遭此劫。可见,亢氏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大粮商,其与朝廷、官府乃至王公贵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凭借这些权势,他的资本才得以迅速积累。《清稗类钞》曰:“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钜”,其余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银两至百万银两的侯、曹、乔、渠、常、刘等数家富商。[7](P2288)
比起亢氏来,另一大商人范氏可称之为“御用商人”,而且是“皇商”。皇商是官商的一种,在清代以内务府的皇商资本最为雄厚,他们经营范围最广泛,与清政府的经济、政治联系最紧密。但他们多为满洲旗人出身,且多以公家资本行商;而从私商起家而成为皇商、并在皇商中占据一席重位者,则以山西介休范氏最为著名。
《清稗类钞》记载曰:“介休范氏有至刚者,明初,自城徙居张原村,七传而至肖山,家大起,贾于边城,以信义著。世祖(清顺治帝)闻之,召至京师,授以官,力辞,因命主贸易事,赐产张家口,即张北厅也,为世业,岁输皮币入内府。子德渊继之,中岁感疾归。孙毓髌代之,即德渊之子也。”[7](P2307)
张正明先生在研究中也指出,早在明初,范氏便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历经七代,传到范永斗时已成为张家口地区与满蒙进行贸易的汉人大富商,并与王登库、靳良玉、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王大宇一起被人称为山右八大商人。清王朝建立后,范永斗即承充内务府皇商;顺治初年,正式入了内务府籍。随着清王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范永斗在其子范三拔的襄助下,利用皇商特权,一面继续经营一些对边疆的贸易,一面扩大经营对象,增加了铜、盐运销,以及对外贸易和其他商业业务。大体说来,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经商鼎盛并在政治上取得相当地位的时期。范三拔的儿子范毓髌、范毓菏、范毓镡为清王朝运送军粮,建立了重大功勋。清王朝先后授范毓髌太仆寺卿、范毓韵布政司参政。范毓镡以武举而破例拔擢为正定总兵官,署广东提督等职。此外,范氏族人中还有充任太仆寺少卿、员外郎、郎中、道员、知府、同知、州同、县丞等职之人。范氏的祖辈,如范永斗、范三拔被封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等,他们的妻子被封赠为夫人、宜人等。当时的范氏,已经不仅仅是大富商,而且变成了豪门权贵。[18](P151-152)
有关范氏特别是范毓髌为清军用兵西北筹措运送粮饷所建立的功绩,在《清稗类钞》中也有生动的记载:“毓髌,字芝岩,卓荦环伟,忠实能任事。承祖父遗业,谙悉边地险易,蒙古诸部长往往知其名,谓为魁杰才。”“康熙丙子、丁丑间,盛祖又亲征噶尔丹。官军馈饷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后期,苦不继。辛丑西征,官运视前值为准,芝岩熟筹之而曰:三之一,足矣。遂以家财运饷万石……费一如所计,克期至,无后者。”雍正晚年,清军再征准噶尔之噶尔丹策凌,以筹饷孔亟,范芝岩以怡亲王所荐再度受命筹运米石。他“悉力自任,计谷多寡,差道路远近,以次受值……擘画精详,悉中机要。”“车轮驼负,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资装、刍粮、鞅靽率先期集办,临时咄嗟应手”,终致“军得宿饱”。以是功,授予范毓髌太仆寺少卿衔,再加二级,章服同二品,“前所未有也”。[7](P2302)范氏此番成为道地的官商、皇商。
至乾隆年间,范氏又进入铜业的贩运。当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货币流通量大幅度增加,作为当时主要货币的铜钱出现严重不足,于是清政府允许各地大量铸造铜制钱。但由于铜源有限,遂照明朝例允准商人赴日本等地购买铜,当时称办理这种业务的人为“洋铜商”。而范毓髌经由内务府奏请,承担了一部分贩运洋铜的业务,即“奉命采办洋铜”。由于清王朝为保证运铜事务的顺利进行,对运铜船只带往日本的丝绸、瓷器、药材等中国货均予以各种优惠,进口铜又免税,故贩运洋铜一度成为当时获利很大的商业。而范氏在这一业务中占有相当比重,经常拥有洋船六七只,成为洋铜商人中的大户,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
不仅如此,范氏由于其对朝廷的忠诚,除了掌控粮业、铜业等行业的经营之外,还得以涉足盐业。有人估计,范氏在长芦盐区的资本不止百余万银两,实际上的资本要比这个数字多许多。而范氏在河东盐区的资本,估计亦不在少数。此外,范氏还经营木材、人参、茶、马等商业。有资料表明,乾隆二十一年(1756),范氏第四代还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买卖玻璃的合同。可见,不论畿辅腹地,还是省外边疆,不论内贸,还是外贸,到处都有范氏的商业足迹。
范氏虽然资本雄厚,但是这种依赖于朝廷、官府发展起来的官商,其资本的积累与封建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受其影响也最深。
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范氏的经营即开始出现衰败迹象,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拖欠官银的罪名查封了范氏的全部资产,并将其家长逮捕问罪。兴盛于康雍时期的范氏家族,于乾隆中期衰落下去,这期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盐商向朝廷的“报效”,范氏同所有的实力派大商人一样,承担了巨额的“报效”。其时,范氏身系长芦、河东盐区的主要盐商,又是最大的铜商,向以“忠于”朝廷为己任,乾隆朝接二连三的“报效”,无疑是范氏家赀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此外,满足官僚的索取也是范氏的重要支出。张正明先生指出,先是于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范芝岩一次向内务府总管大臣董殿邦行贿白银四万余两,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范芝岩又向内务府郎中都图一次行贿白银五万六千余两。[18](P152)
但是,作为御用商人,范氏最后走到债台高筑的地步却不仅仅是因为封建政府及其官僚的婪索,还因为清政府政策的变化,即对其多方的限制。诸如,采办洋铜最初获利甚大,但是,清廷不但规定了采铜的最高限量,而且规定了官办与民办的比例与价格,从而束缚了采铜商人的手脚。范氏曾要求清政府调整官办铜价,但清廷不准。范氏办铜,终致由盈而亏,最后破产。范氏可谓近代之前御用商人在资本积累方面的一个典型,而其衰落的原因却与清朝对商人的掠夺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通过考察,可以认为,清代的京城聚集着人数众多的铺户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说明中国正在一种传统的政治经济运行模式下按照常规秩序化地运行着。他们当中虽然出现了资本雄厚的大商人,但由于他们过于依赖朝廷,其资本的积累与封建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难以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他们的衰败也几乎与政治的衰落同步,甚至更早。
标签:清稗类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