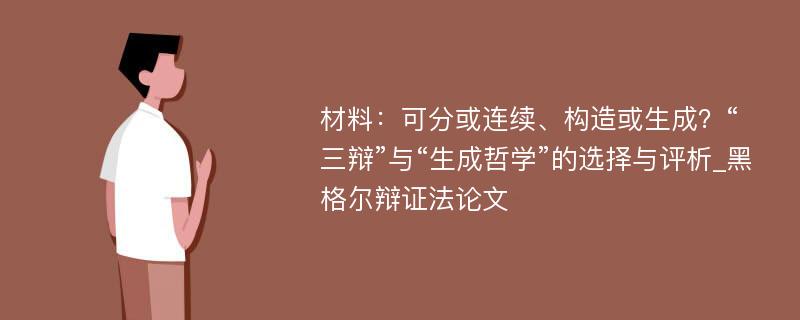
物质:可分的或连续的、构成的或生成的?——选评《3大论战》与《生成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质论文,哲学论文,大论战论文,选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65(2002)01-0001-04
甲:最近读到了何祚庥教授的新著:《3大论战——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①这本著作使人感觉到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浓厚兴趣。作者的科学实在论(即科学唯物主义)倾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乙:我也读过了这本书,特别细读了《何谓“可分”?粒子或场是否“无限可分”?》部分,我对何先生肯定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适性的基本立场非常赞同。然而,他对“无限可分”的论证方式却使人想起黑格尔所批评的“恶的无限性”,所引出的某些极端结论则使人容易联想起机械唯物论的思考方式。随后我又读了据说是持对立主张的金吾伦教授的《生成哲学》②一书,读完后感到金先生的生成辩证法观点十分精彩,很有说服力。依我看,它或许可以看作探索现代辩证法的一个新的型式。按理说,何先生本应把金先生当作可靠的辩证法盟友,谁知前者却把后者当作论敌,并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我真有点茫然了,很想听一听你的看法。
甲:实际上,他们之间关于“物质可分性”问题的学术争论早已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基本观点学术界都已了解。你提到的《生成哲学》一书,是金先生的最新著作,是他的《物质可分性新论》一书的基本观点的继续和发挥。金先生的这些见解不是一时兴发,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而是长期学术探讨的结果,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提出这些见解是一种学术创新,也需要有理论勇气。我主张应当心平气和地对他们各自的观点作具体分析,充分肯定各自论点的合理性,同时指出其不恰当之处,我主张以一种多元化的宽容心态对待不同观点的争论。(乙插话:我对多元主义方法论向来情有独钟。)千万不要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那不利于学术争论,不利于学术繁荣,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一
乙:能不能先讨论一下物质“可分性”问题。何先生在《毛泽东和粒子物理研究》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强调了“分”就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矛盾的统一”,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处不在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观念,这就是辩证法”。(见①,第145页)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吧?
甲:当然“分”的最基本涵义、最基本形式是“物质实体作为整体分解成不同的要素,与不同的层次”。何先生、金先生虽然都表态要拒斥构成论,何先生强调“一分为二”,金先生则强调“生成哲学”,但都是在上述意义上把握“分”的基本涵义,因此当何先生坚持物质“无限可分性”观点时,就必然会遭到金先生那样强有力的反驳。的确,当代物理学深入到基本粒子世界之后,有一系列事实在直观上是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相违背的。比如,金先生提到的“夸克被禁闭”而在事实上是分离不出来,电子之类的轻子的可分性仍缺乏实验根据,光子的个体性、整体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玻尔所提出的能态的跃迁也是一种一次完成而且是不可再分的突发性事件,作用量子h是一个非无限可分的有限作用量,其个体性与整体性是量子理论的最基本的前提等等。
乙:这里你所提到的量子论整体观,使我想起一本名为《新整体论》的书,我认为它对“无限可分”的说法是个有力的冲击。《新整体论》(1996)是孙慕天与采赫米斯特罗教授合著的一本书,这本书对D.玻姆在《量子理论》中的整体观作了进一步发挥。在这里,我可以作三点概括:1)新整体论最核心的观念是终极不可分的整体性。它根本否认了存在轮廓清晰的宇宙基本砖块的可能性,“摒弃了实在可以绝对地彻底地分解为其组成要素的观念,……始终注意到世界在物理上的终极不可分性的这一事实”(见③,第51页)。2)关于普朗克常数的哲学意义。h不仅是对能量“无限可分性”的自然限制,而且更一般地说,普朗克所发现的作用量子,它使牛顿的经典本体论的基本理想——把物理系统的状态完全无止境地分割成界线分明的要素集合——成为泡影(参看③,第41页)。3)与此相关的是相空间格胞的存在。也就是说,相空间是量子化的,其物理含义为物理状态并不是无限可分割,它存在一个最低界限。想引进某种物理操作去确证格胞内个别要素及其集合的模型终究是行不通的。相空间格胞的存在正是上述终极不可分的整体性的又一直接体现,如此等等。
甲:诚然,当我们讨论物质层次的可分性、物质实体的实际分割时,千万不能忘记量子世界的“终极不可分的整体性”的限制。看来只有强调可分性与不可分性两者的“对立统一”才有全面的真理,才是辩证法,单纯强调“可分”并不是辩证法。
乙:除了上述“分”的基本形式外,还有什么其他形式呢?
甲:此外,还有对物质实体的性质与关系的分析。罗嘉昌教授提出的关系实在论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在《关系实在论:纲要和研究纲领》一文中指出:“所谓关系的实在性,是指它的内在性,不可还原性和在先性。关系内在于系统整体而成为基本结构要素;它们不是附加于与它们相关联的东西,而是构成了其总体实在。(见④,第82页)罗先生认为,“现象和性质总是在特定的关系中显现的”。(见④,第78页)他对关系性实在作了极其细致的分析,我基本同意罗先生的论证。特别是像中子、质子、电子、μ子这样的理论实体,它们并不像宏观世界的经验对象那样的明显摆在我们面前,它们作为潜在的实体只有与我们的观测条件以及其它对象发生关系,其性质才能显现出来,才表现为现象而成为现实。我们只有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才能够把握理论实体本身。依我看,列宁所说“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坂田昌一所说的“中微子也是不可穷尽的”,都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乙:说得好,我也是从电子、中微子的关系性质的无限复杂多样性的角度去理解“不可穷尽性”的,而不相信什么电子、中微子真的还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
甲:关于“分”的意义变化,金先生在《对“物质无限可分论”的再认识》一文中明确指出:“粒子物理学研究还表明,基本粒子尽管在非常高的能量下能够被分裂成碎片,但这些碎片不是组成基本粒子的更小成分,而是其他基本粒子。这些粒子的空间尺度或质量有的甚至可以等于或大于被分割的母粒子。”(见②,第17页)。甚至何先生在《对“物质无限可分论”的再探讨》一文中也承认:“由于质量亏损效应,部分的总和往往大于它的整体。例如,原子核由中子和质子所组成,但自由中子和质子的质量的总和往往重于所构成的原子核。在一些工作中,甚至可能发生单个部分重于它的整体这种特殊情况。”(见①,第140页)这些论述也都涉及“分”的意义的变化。这里,分出来的部分之和大于整体,这是就质量等物理量而言的。分出来的部分之和也可以小于整体,如分出来的中子、质子就不具有原子的功能,这是就系统整体功能的丧失而言的。
乙;你喜欢强调“分”的概念的“意义变化”,而“意义变化”则是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的说法。我更喜欢从辩证逻辑概念论的视角看待“可分性”问题,看待“分”的概念的辩证演变。你还记得当年(1994)武大哲学系的专家茶座么?“辩证逻辑之本质”的主讲人就说到,辩证法的核心是自否定,自否定的矛盾不是外在矛盾,而是同一个东西的自我分裂(真正的“一分为二”!)自否定有自反性,它成为二律背反的源泉,辩证逻辑本质上是自否定的逻辑(见⑤,第62页)我们可以把这些观念用到“可分性”问题上。人们历来以为“分”意味着使大变小,使重变轻,可是现在你看,对于基本粒子,小“分”出大、轻“分”出重来了。“分”的概念按其自否定的内在逻辑,转向自己的反面,变为与原先完全不同的“他者”。这里到处是生成和相互转化,到处需要流动范畴。日本物理学家武谷三男说得好:“作为终极要素的实体——基本粒子本身也是相互流动地相互转化的。这件事变革了以前的物质观,显示了辩证逻辑的正确性”。(见⑥,第28页)确实,这里有本来意义的辩证法与辩证逻辑,但决不是在机械的“可以无限分割下去”的意义上去理解的。
甲:总的说来,我认为可分与“不可分”是互补的,是辩证统一的。单纯地坚持“分”或“不可分”都不是辩证法。孤立的固执其中任何一方都会走向形而上学。
二
乙:金先生在《对“物质无限可分”的再认识》中,指出何先生的物质无限可分论是建筑在机械的“构成主义”的基础上的。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甲:我认为金先生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的。“整体分离出部分”这种物质可分论确与这种“构成主义”相对应。如果认为“物质无限可分”,必须要假设物质结构具有无穷的层次,不仅在宏观上而且在微观上都有无穷的层次,于是微观层次的束缚态必然会趋于无穷小,这显然与“粒子”(作为最小实体)及“分”的本义相矛盾,因为这里谈到的不是数学上无穷小分析,而是在物理上对实体粒子的“分”。何先生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尴尬局面,于是他采取了三种变通的策略。第一是把可分性的意义扩大了,宣称无限可分论不仅仅是以构成主义为基础,而是以更一般的对立统一规律为基础。他说:“无限可分的观点是以对立的统一为基础的,‘构成’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可能形式,而不是它的唯一形式。”(见①,第140页)这无非是说,物质层次不一定有那种可分离出部分的结构,但一定是对立统一体。这就把“可分性”及“构成”的意义扩大成了“对立统一性”。不过,虽然“分”的意义可以扩大,但“分”与“对立统一”并不是同义的,黑格尔关于“杂多”与“矛盾”的讨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我们现在所讨论是科学上的可分性问题,要考虑“一分为二”在物质形式上的具体表现,要考虑前面谈到的关系实在论的分析,系统学的分析等等。
第二是宣称“可分性”及“构成”涵义上的可变性。何先生说:“通常理解的构成主义,确实以部分能由整体分离出来做为条件之一。但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夸克禁闭并不会妨碍人们认为介子是由夸克和反夸克所构成。所以,应该看到现代构成主义在内涵上的变化。而且,现代构成主义还应抛弃一种陈旧的观念,即整体等同于部分的总和。”(见①,第140页)。这里所谈到的关于“构成”与“可分性”的意义的变化,是有道理的。实际上,随着实验自然科学对物质结构的认识的深入,从道尔顿原子论到量子力学的原子模型,又到基本粒子世界,我们所谈的“结构”、“构成”、“可分性”的意义确实是在不断地改变。这完全是符合辩证法的。
第三,是从实物粒子的“可分性”与“构成”概念转移到更为基本的场的“可分性”与“构成”概念。何先生在该文中重复了金先生的反驳无限可分论的例子,即电子偶与光子的相互转换,原子核的β衰变中电子的生成,还有π介子簇的生成等,却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从现代的粒子理论来说,上述这些现象所以出现是和场的效应相联系的。在现代粒子理论研究中,场是更为基本的概念,粒子只是场的某种特殊的量子状态,或者说,粒子仅是处于平面波中的场。……从场的观念出发,π介子场既能激发出单个π介子,也能激发出任意多个π介子。关于原子核的β衰变,关于正负电子和光子相互转化的现象,……都是场的激发效应的结果。”(见①,第141页)。这是量子场论的基本解释,在这里场比粒子更为根本。实物粒子的“结构”与“可分性”被归结为场的“结构”与“可分性”。何先生又说:“更为深入的一种理解是认为所谓π介子场量仅是夸克和反夸克构成的复合场量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夸克和反夸克场形成的复合场除了可以激发出任意个数的π介子外,还能激发出……许多种介子。正是这种夸克场与反夸克场的对立统一,解释了全部介子的产生、湮灭,……种种变化。”(见①,第141页)这大概是何先生的得意之笔。π介子场的“可分性”被归结为夸克场的“可分性”,并且是“夸克场和反夸克场的对立统一。”
乙:依我之见,何先生的得意之笔,即关于场通过激发效应生成粒子、场与粒子的辩证相互作用的分析,不仅不与金先生的生成哲学的理念相冲突,而且还需要生成论的理念来补偿。我真希望将两派意见辩证地综合起来。哦,看来对何先生的上述见解,你都是同意的了。
甲: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何先生所指的是与粒子层次相应的场的层次的“无限可分性”。这就需要预设粒子与场的无限多层次的存在,需要承认粒子与场在上层与底层两个方向上都要有无穷多的层次,这在科学上是与量子理论关于个体性、整体性、不连续性和终极不可分性的基本观念相予盾的。而且该预设还要承认极限意义上的无穷小束缚态、无穷小层次的间隙,以及形成这种束缚态的无穷大能量,这是与“粒子”与“分”的概念的本义相矛盾的,也是与层次概念相矛盾的。从哲学上来说,这里所预设的粒子与场的层次的无限性是黑格尔所批评的那种“坏的或否定的无限”。
乙:是不是因为何先生预设了粒子与场有无限层次,金先生才批评物质无限可分论是不可证实的呢?
甲:正是这样。与金先生的观点相呼应,薛晓舟和张会先生还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观念,永远是不可证实的”,“物质是有限可分的论点,永远是不能证伪的。”
甲:何先生显然不甘心承认“物质无限可分”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并认定这是一个真理。断言关于物质无限可分和物质有限可分问题的争议,只能由实践最终作出判断。他指出:“如果他们承认时间发展的无限性,那末无异承认实践发展的无限性。既然实践是无限地发展着,为什么由此还不能判断‘无限可分’的真伪?而尤为可怪的是,无限发展的实践竟然永远不能‘证伪’物质是有限可分?(见①,第163页)”。且不说,何先生这里所讨论的无限,仍然是黑格尔所批评过的那种从来没有离开有限事物范围的“坏的、否定的无限”,且不说人类的存在是否必定为无限,仅仅考虑到实践检验(证实或证伪)的复杂性,其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就明显地感到何先生的这些话太虚妄了!
三
乙:谈到无限可分论,金先生在《再论物质可分性问题》一文中有一段话:“近代科学就是沿着构成论的思想思考一切的。它主张一切变化都是不变要素的结合与分离。一切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它的变化是由基本粒子的分离和结合造成的。而基本粒子的变化是由更基本的粒子分离和结合造成的,如此继进以至无穷。‘物质无限’可分论就是这种‘构成论’思想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见②,第227页)如何看待这一界定?
甲;这段论述的确阐明了传统构成论的基本思想,道出了在近代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还原论的实质,道出了物质层次无限可分论的实质。然而这种机械的物质结构观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它常常被人误以为一种不可动摇的辩证法思想。尽管何先生抽象地否定了这种“构成论”思想,然而每当他转入具体问题的讨论时,他所贯彻的却仍然是这种“构成论”,认为任何所谓基本的粒子或场都是更为基本的粒子或场的“复合”,前者由后者所“组成”。他的逻辑是,不承认物质层次的无限可分性就等于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就要承认物质层次的无限可分性。我认为,正是这种简单等同的逻辑妨碍了何先生的视线,使他看不到“分”的广泛性、可变性、多样性的辩证涵义,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辩证关系,也使他看不到结构主义与生成主义的辩证关系。
乙:请把最后一句再解释一下。
甲:你刚才提到的金先生的那句话是对机械的“构成主义”的概括。它是从西方古代流传下来的在近代学术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贯彻。在现代科学中,甚至在近代科学发展中,这种旧的构成论早巳被新的构成论所超越了。“由构成主义的旧结构观转变为新的结构观。”(参看②,第227页)。因为人们不再简单地把物质实体的变化说成是“由基本粒子的分离和结合造成的”,甚至也不仅仅认为基本的物质形式是由更基本的“物质形式”所组成,而且还认为这些物质形式是从其它的物质形式转化而来的。“机械论”构成主义是与生成主义相对立的,在这里,即使说到“生成”也是基本元素的“结合”,也可归结为“构成”。而有机论的构成主义则是与生成主义相统一的;在那里,“生成”就是新形式的产生、结构变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构成”;“生成”与“形式结构”是互斥又互补的。
乙:看来你完全赞同金先生而且还更进了一步,似乎整个粒子世界和原子世界乃至全宇宙都为“生成过程”所统治了。
甲:不过,我对金先生也有保留意见,我认为,他所赞同的“构成论将必然被抛弃,而代之以整体论”(见②,第47页)的结论太绝对了。在我看来,我们在否定构成主义的机械性质的同时不能抛弃“形式”、“结构”、“组织”等概念,因为这些概念与“整体”、“生成”、“发生”等概念实质上是相反相成、辩证统一的。
〔收稿日期〕2001-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