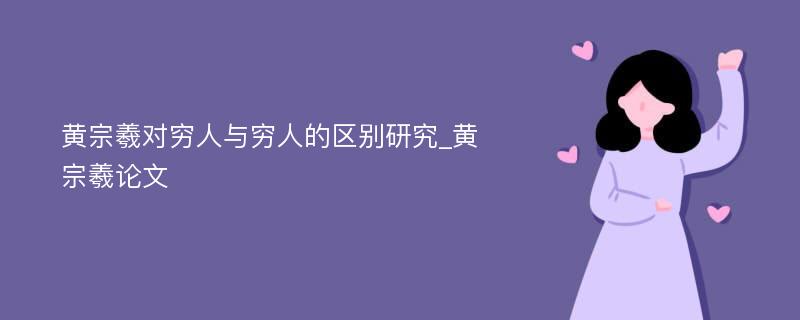
黄宗羲穷心的万殊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学论文,黄宗羲穷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3)05-0001-10
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学术史家,黄宗羲的哲学思想继承其师刘宗周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和合心性情、道心与人心、理气、未发已发等范畴,试图在刘宗周哲学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要实现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不仅要回到中国哲学元创期,寻找创新的精神动力,而且要融会贯通中国哲学思想史。自先秦以来,历代具有标志性、代表性的哲学思想创新者,无不符合这两条规则。黄宗羲之所以花大气力撰著《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梳理研究学术思想史,就是从中吸收营养,以便度越前人理论思维,从而建构新的理论思维体系。然而,由于《宋元学案》未及完成他就与世长辞,因此他对传统学术、思想的梳理和研究并没有完成,因而也就来不及在此基础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进行哲学理论思维的逻辑演绎或感悟归纳,没有开出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之新来。当然,这并不是说黄氏的哲学思想没有创见,而是说,其创见不在于其理论思辨哲学,而在于其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即《留书》《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一 盈天地皆心
黄宗羲继承了刘宗周《人谱》“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的思想。《人谱》是刘氏的绝笔之作,而黄氏“盈天地皆心也”[1](P.3)的命题亦是他逝世前两年在病中口授其子黄百家所写成的《明儒学案·自序》中的第一句话,都是深思熟虑之后铸炼而成的。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穷心则物莫能遁,穷物则心滞一隅。”[2]心的思议想象,神妙莫测,上可穷碧绿天穹,下可穷幽暗黄泉。心无本体即其本体,他提升工夫的价值作用,工夫所至处,即本体即工夫。“心无本体”,乃是“无极而太极”、“无善而至善”的表述方式。黄氏一反朱熹的“格物穷理”、“即物穷理”,而沿袭陆王的“心即理”思维,以穷理即穷心,不是穷物的万殊或穷理的万殊,而是穷心的万殊,与程朱异,与陆王亦异。他认为,穷心即能彻上彻下,天地万物的万殊无不观照,而穷物便滞于方隅。
穷心之万殊思想在《明儒学案序》的“改本”中有所阐发,为《自序》所无。“盈天地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夫苟工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即如圣门师、商之论交,游、夏之论教,何曾归一?终不可谓此是而彼非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茅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3]天地万物与人一体,为什么一体,如何一体?黄氏沿用王守仁“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4]之说。王守仁认为,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心),便一无所有。“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5]所以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黄宗羲亦以一气充周来诠释:“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凉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心失其养,则狂澜横溢,流行而失其序矣。养气即是养心。”[6](卷2,P.60)天地间一气充周,即“盈天地间皆气”的命题,那么,此与“盈天地皆心”是否冲突?否。人物虽禀气以生,但心是气的灵明处,心体流行而有条理为性,流行而不失序为理。从一气生人物,转气的灵处为心体流行,理气、心性融合不二,心与气亦不二,心即气,养气即养心。就此而言,“盈天地间皆气”即“盈天地间皆心”,心与气一体,天地万物与人一体。
心体至善。“既云至善是心之本体,又云知是心之本体。盖知只是知善知恶,知善知恶,正是心之至善处。”[7](P.223)知善知恶之知即良知,良知正是心的至善处,至善即良知,同为心的本体。这作为一种价值本体,是先验的、自然的,譬如见父自然知孝,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不假外求。“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又立个心去恶,此是先生洞见心体处”。[7](P.222)好好色与恶恶臭的爱好与厌恶的心意,是与看到美好的颜色、闻到恶臭的气味同步的,都是原有的那个心体,不是又立一个心去好去恶。作为“至善本在吾心”[7](P.221)的心体,自然知善知恶,好好色恶恶臭,这是心体本具的价值德性和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心体没有不善的,不善是过与不及产生的。“《通书》云: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刚柔皆善,有过不及,则流而为恶,是则人心无所为恶,止有过不及而已。此过不及亦从性来。故程子言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仍不碍性之为善。”[6](卷2,P.68)性的未发为中,刚柔都善;发而中节,无过不及,便为善;发而不中节,有过不及,就流于恶。作为心体的性体本身是善而无不善的。由于有过不及是从性的发动而来,所以程颐讲恶不可不讲是性。黄宗羲认为,这并不妨碍性体是善的。
心体为二。“仁,人心也。常人心在身中,所居血肉之内,如何得安?仁者身在心中,藏身于密,祸患不至,故为安宅。”[6](卷4,P.93)常人心在血肉之躯的身中,不得安宅,仁者的身在心中,退藏于密,祸患损害不了它,所以得安。
“人心无不仁,一念之差,惟欲独乐……战国之君,杀人盈城盈野,只是欲独乐耳。”[6](卷1,P.52)譬如白起发一疑心,长平一战坑四十万人,李斯发一饕心,横尸四海,杨国忠发一疾心,激祸百年。尽管心是仁的,但一念之差,为图自己的快心而杀人盈野,祸国殃民。仁为四德之首,发为四端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满腔子皆恻隐之心,以人身八万四千毫窍,在在灵通知痛痒心,便是恻隐之心。凡乍见孺子感动之心,皆从知痛痒心一体分出来。”[6](卷2,P68)满心都是恻隐之心,它流通全身的细胞,这就是知痛痒的心,即恻隐之心。推己及人及物,推己恻隐之心于天地间,盈天地便都是恻隐之心的流动。“满腔子皆恻隐之心,无有条理可见,感之而为四端,方可言理……盈天地间皆恻隐之流动也。”[8]恻隐之心,即是不忍人之心,这是人人普遍具有的价值本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是一种仁爱的心,大爱无疆,推而仁民爱物。
“仁”,宋明理学家曾训其有生生之意,黄宗羲承之说:“仁之于心,如谷种之生意流动,充满于中,然必加艺植灌溉之功,而后始成熟。《易》言一阴一阳之道,道不离阴阳,故智不能离仁,仁不能离智,中焉而已。‘继之’即戒惧慎独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继之’者,继此一阴一阳之道,则刚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6](卷6,P.143)谷种的生长成熟,必须加以种植灌溉培养,这犹如《周易·系辞传》所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不离阴阳,由阴阳而成道,人的恻隐的仁心不离种植灌溉之功。“继”是继此一阴一阳的道;“成”是中和大本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纯粹至善的心体。
心体为理义。理义之悦吾心,“此理义,即天所降之才也,故为心之所同然”[6](卷6,P.137)。理义之心,具有伦理道德理性。“其所谓义,方是天地万物之理。告子以心之所有不过知觉,而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不以吾之存亡为有无,故必求之于外。孟子以为有我而后有天地万物,以我之心区别天地万物而为理,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更不必沿门乞火也。”[6](卷6,P.134)告子以义理不在心内,天地万物与我心的存亡无关,而不得不求理义于外。孟子认为有我而后有天地万物,我心就蕴涵理义,我心存,理义自明,不必沿门托钵乞火,即不必外求。“夫所谓理者,仁义礼智是也”[6](卷6,P.135),就是传统伦理道德理性。这是人与禽兽之所以区别的所在。释氏讲“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即无情有性,便是将人与禽兽混同,把父母之亲,入禽兽轮回。“(虽然)人而丧其良心入于禽兽者有矣,未有禽兽而复为人者也”[6](卷6,P.135),没有禽兽变为人而行人的伦理道德的。
理义之心,即仁义之心。所谓仁心与义心,即“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其流行次序万变而不紊者,义也。仁是乾元,义是坤元,乾坤毁则无以为天地矣。故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舍仁义更无他道”[6](卷1,P.49)。仁心为天地生物之心,义心是流行次序和万变不紊之心,天地万物的资始资生和治国平天下,都有赖此仁义之心。从历史演变的进程来看,三代以下,春秋时虽有乱臣贼子,但整体而观,行事论说,还是以仁义为骨干;及至战国,人心机智横生,人主所讲求的,谋士所揣摩的,只在利害二字上,仁义被边缘化了。
然而,仁义的功用价值,是“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是自然天地与社会人纪的根据和支撑。尽管“后世人心,汩没于利欲,故利之所在,视为极重之事”[6](卷7,P.157),但“乾坤之所以不毁,人类之所以不灭,全在亲戚、君臣、上下太和保合,人皆可以为尧舜矣”[6](卷7,P.157)。天地不毁、人类不灭的所以然之故,就在于社会人际之间的伦理道德的“保合太和”,即和合、和谐。这样人人都可实现成圣的人格理想。
心体为太虚。“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先师谓先生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是谓无生死,非佛氏之无生死也。”①[9]太虚的心体,无生无死。所谓无生死,是指尽其道而生死。既尽其道,而心与道,一而不二,这就是太虚的心无生死。心为太虚,便可包容一切事物,也可开出无限事物。
太虚心体,无所归宿,由其无所归宿,便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所以“心与事融,外不见人,内不见己,浑然至善之中,万物一太极也,盖无处非大德之敦化矣”[6](卷4,PP.109-110)。外不见人,而无人执;内不见己,而无我执;无人执我执,才能不固执己见,而吸纳人见。太虚心体若有归宿,便是住。无归宿,即是无住,无住才不会停滞、滞留,而能为道屡迁,唯变所适。心体有了归宿,便会有所执著,只有“一物不着,正是湛然。若空守此心,求见本体,便是禅学矣”[6](卷2,P.70)。心体不着一物,便是清澈澄明的。
心体至善,心体为仁,心体为理义,心体为太虚,这是黄宗羲在继承刘宗周心体说的基础上,对心体的界定。这一界定蕴涵着他对明亡的“天崩地解”和其抗清失败的思议:一方面从心体中追求生命生存的智慧;另一方面,从心体中探赜挺立主体精神的精神动力;再一方面则从心体中获得国难家仇的精神慰藉和终极关切,即生死出处的精神家园。
二 心性一体万殊
穷心的万殊,先儒竭其心的万殊而后成体,“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1](P.3),心的万殊是我心体变化的印证。心体本身是一,由其变动不居而有万殊,天地万物千差万别的万殊其根据和源头是心体。“全将自己心源,印证群迹。吾心止有一,常人自去分门立户。”[6](卷2,P.66)以证心源、心体一与万的关系,一统摄万。然由其万殊,而构成心体与各相关概念范畴的内在逻辑联系,譬如构成对心性的体认。
心性是体现宋元明清理学哲学思潮的核心话题之一。心的万殊,是心体的大化流行。“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6](卷2,P.60)心体流行,心体在变化万殊的过程中,有条理而为性。性作为心体的流行条理,而不能离心。“即心言性,非离心言善也”[10],犹善不能离心。黄宗羲引其师刘宗周的话:“古人言性,皆主后天,毕竟离气质无所谓性者。生而浊则浊,生而清则清。非水本清,而受制于质,故浊也。水与受水者,终属两事,性与心可分两事乎?予谓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时而浊,未离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终锢于浊,则习之罪也。”[6](卷3,PP.77-78)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此处以水喻心,以水之清浊喻性。若以清为性,浊也不能不为性,这是讲性相近的意思;若终固于浊,便是习相远。无论水的清性混性,终不离心水。心有万殊,性也万殊,继善成性,“及到成之而为性,则万有不齐,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草木有草木之性,金石有金石之性,一本而万殊,如野葛鸩鸟之毒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孟子性善,单就人分上说。生而禀于清,生而禀于浊,不可言清者是性,浊者非性。然虽至浊之中,一点真心埋没不得,故人为万物之灵也”[6](卷3,P.77)。尽管天下人物,各有其性,千差万别,但都是性,性体为一,分而万殊,这便是“一本而万殊”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是道学家“理一分殊”思维方法的继承和运用。
黄宗羲阐释了性的特质:性体与万物一源,而非与万物二本。这是其“一本而万殊”思维原则的贯彻。“只为性体原是万物一源,故如人参温,能补人,便是遇父子而知亲;大黄苦,能泻人,便是遇君臣而知义。如何无良知?又如人参能退邪火,便是遇君臣而知义。大黄能顺阴气,便是遇父子而知亲。如何说此良知又是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者?”[7](P.238)这是对王守仁“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的诠释。为何“原是一体”?是由于性体原是与万物一源的。黄氏以中药人参和大黄为喻:人参性温能补人,遇父子而亲爱温暖;又能退邪火,遇君臣而知正义。大黄味苦能泻人,遇君臣而知义;又能顺阴气,遇父子而知亲。从药物的性味——父子君臣关系——知亲知义伦理道德,以论证性体与万物一源,这种论证把人性与物性、人的社会性与物的自然性、人的道德性与物的非道德性完全等同浑一起来,显然是一种主体单向的想象和臆测,其间并非有实际的关联。人参与大黄并无知,如何能达知亲知义,也构不成父子君臣的社会伦理道德关系。
黄宗羲以为,“夫性固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而言性者必以善言性,决不以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言性,一体可以见善,而善之非一体明矣。且如以恻隐言一体可也,以辞让言一体亦可也,使羞恶是非历然,吾独知之中,未交人物,与浑然一体何与?则性于四端,有所概有所不概矣。”[11](PP.144-145)由“一体而万殊”而演绎的性固浑然天地万物一体、又非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言性前后矛盾;既讲善恶皆性,又讲仁义礼智四德发为四端的恻隐、辞让可见善而为一体,则羞恶义之端、是非智之端如何为独知而未交人物,如何与浑然一体无与?以性于四端有所概括有所没有概括,这种将四德四端分离的陈述与孟子不符。
性体空虚无可想象。“孟子所谓扩充,动心忍性,强恕而行,皆是所以尽心。性是空虚无可想象,心之在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可以认取。将此可以认取者推致其极,则空虚之中,脉络分明,见性而不见心矣。如孺子入井而有恻隐之心,不尽则石火电光,尽之则满腔恻隐,无非性体也。”[6](卷7,P.148)尽心是实行的,不仅可动心忍性,强恕而行,而且有恻隐等四端可认取。尽心知性,性是空虚的,不可想象的,但在这空虚的性中,脉络清晰分明,便可见性知性,譬如见孺子入井,人满腔都是恻隐之心,而去救孺子,这满腔恻隐,就是性体。又譬如“父子兄弟之间,纯是一团天性,不容直情径行”[6](卷4,P.106),天性即是性体。
性体好善恶恶。“好必于善,恶必于恶。性本如是,感物而动,则有欲有不欲,能不失其性体,而可欲在善,是知及之也。善无形质,不可把捉,我即可欲之而落于想象,终非己有,如颜子之拳拳服膺,是仁守之也。”[6](卷7,P.162)性本身是好善恶恶的,但性感物而动,便有习于欲望与没有习于欲望,欲望在善是知善。尽管善无形质,但不失性体。“孟子说‘性善’,即习有不善,不害其为性善。后人既宗‘性善’,又将理义气质并衡,是明堕‘有性善,有性不善’与‘可以为善,可以不善’之说了。且告子说无分,虽不明指性体,而性尚在。后人将性参和作两件,即宗性善而性亡。”[12]性本善,习有不善。道学家虽宗性善,但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并衡,以义理之性(天命之善)为善,气质之性有善也有不善,这样便堕入《孟子·告子上篇》孟子所批评的几种性有善有不善和可以为善为不善的观点。道学家参和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虽讲宗性善而实性亡。
尽管性是心体流行的条理,但黄宗羲在论述性体与万物一源、性体空虚无可想象、体性好善恶恶时,将性体空虚化、本体化,从而与心体具有等价的性质和功能。
黄宗羲在其心性体悟的基础上,对王守仁“四句教”宗旨的种种解释、论争,试图作一终结。他说:
天泉问答:“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体无善无恶是性,由是而发之为有善有恶之意,由是而有分别其善恶之知,由是而有为善去恶之格物。”层层自内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机,则良知已落后着,非不虑之本然,故邓定宇以为权论也。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恶念耳。两句只完得动静二字。他日语薛侃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即此两句也。所谓知善知恶者,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知亦只是诚意中之好恶,好必于善,恶必于恶,孰是孰非而不容己者,虚灵不昧之性体也。为善去恶,只是率性而行,自然无善无恶之夹杂。先生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无病,学者错会文致。彼以无善无恶言性者,谓无善无恶斯为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无善之善,无乃断灭性种乎
王守仁“四句教”既是教人定本,亦是其晚年定论。自其亲炙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四有”与“四无”论争以来,莫衷一是。其“四有”与“四无”之争的出发点都是对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不同诠释。
许孚远作《九谛》,周汝登作《九解》,相互辩论。许孚远认为,周汝登的“无善无恶不可为宗”,“‘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盖指其未发廓然寂然者而言之,则形容得一静字。合下三言始为无病。今以心、意、知、物俱无善恶可言者,非文成之正传也”[13]。以此,王守仁“四句教”宗旨不违圣门之旨,性无不善,便知无不良,良知为未发之中。认为心、意、知、物都无善恶的“四无”说,不是王守仁正传。对于许孚远的诘难,周汝登作《九解》伸其说,“以为善且无,恶更从何容?无病不须疑病。恶既无,善不必再立,头上难以安头。本体着不得纤毫,有着便凝滞而不化”。[14](PP.112-113)大致主“四无”说。
黄宗羲对此评说,《九解》“只解得人为一边,善源于性,是有根者也,故虽戕贼之久,而忽然发露。恶生于染,是无根者也,故虽动胜之时,而忽然销陨。若果无善,是尧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释之判,端在于此。先生(指周汝登)之无善无恶,即释氏之所谓空也。”[14](P.113)他不同意周汝登的“四无”说,以此与佛教所说的空无别。黄宗羲别开路径,以无善念恶念解“无善无恶心之体”,意念解善恶,善恶是内心的一种未发动的意识潜能或心理动机,因此是一种无善无恶的意念,意念本无善恶,这便谓“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董吴仲作《刘子质疑》寄予黄宗羲。宗羲说《质疑》的“大意主阳明教法四句,以先师破意已发之说,与阳明‘有善有恶意之动’不能相合。余谓先师之意,即阳明之良知;先师之诚意,即阳明之致良知。阳明不曰良知是未发之中乎?又何疑于先师之言意非已发乎”董吴仲认为刘宗周以意为已发,黄宗羲认为刘宗周的意指王守仁的良知,诚意为致良知。“使蚤知意属未发,则操功只有一意,前后内外,浑然一体也。”[15](P.467)《中庸》讲喜怒哀乐未发为中,发而中节为和,致中和,为天下大本达道。王畿从日用伦物之应感以致其明,欧阳德是以感应变化为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聂豹和罗洪先以归寂守静,致中不致和,都不能中和兼致,这就把意分动静、未发已发为两截,而不知意的前后内外浑然一体之旨。
“知善知恶是良知”。“其所谓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有善有恶之意,以念为意也。知善知恶,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好善恶恶,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即性也。阳明于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16]喜好善、憎恶恶,是天命自然明亮而不昧的良知,不是意动而为善恶。良知知善知恶,就是讲性善。“为善去恶是格物”,论争不多,黄宗羲的理解与王守仁相符。
黄宗羲心性之学的特点在“一本而万殊”,以穷心的万殊与性的万殊而归宗心体与性体,心体与性体不二。其对王守仁“四句教”的解释有综前人说的价值,然其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释为无善念、无恶念,是黄氏之体认,不一定是王守仁的本意。由于时空的差距,后人对文本的诠释,无疑都有“前见”和“前识”的遗留,因此不同时代、不同人对同一文本的体认就有不同,各释其释,各需其需,各是其是,这亦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人们只是在各种不同体认中,选择一种较为现实、公允的意见而已,而不需要非要辨明谁是谁非,各种不同的诠释都可作为参考。
三 气理心性会通合一
黄宗羲哲学理论思维的要旨是试图把宋明理学的理气心性等核心话题融通和合起来,不仅以心性一本,而且以性即理、心即理。他说:“人与天虽有形色之隔,而气未尝不相通。知性知天,同一理也。《易》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理者尽其心也,心既理也,故知性知天随之矣,穷理则性与命随之矣……但先儒以性即理也,是公共的道理,而心是知觉,知得公共的道理,而后可以尽心。”[6](卷7,P.148)气通天人,故尽心知性知天,穷理即是尽心,因为“天下之理,皆非心外之物,所谓存久自明而心尽矣”[6](卷7,P.149)。所以心即理、性即理,是一个公共的道理,知道公共的道理,而后可尽心,尽心知性知天即穷理尽性至于命,是同一道理。
黄宗羲在评魏校时,批评其将理气心分为三:“理也,气也,心也,歧而为三,不知天地间只有一气,其升降往来即理也。人得之以为心,亦气也。气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荣枯,寒暑之运行,地理之刚柔,象纬之顺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气之自为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间气之有过不及,亦是理之当然,无过不及,便不成气矣。气既能主宰而灵,则理亦有灵矣。”[17]气作为一种质料,它的变化运动的升降往来就是理,人获得气为心。气的运动有其规则性,这种规则性是由气主宰的,自然界、气象界、社会界等的变化,都是由气主宰的,气之所以能主宰,是由于理。气理心非歧而三,而是会通合一。
从分合的视域以观理与心。“自其分者而观之,天地万物各一理也,何其博也。自其合者而观之,天地万物一理也,理亦无理也,何其约也。泛穷天地万物之理,则反之约也甚难、散殊者无非一本,吾心是也,仰观俯察,无非使吾心体之流行,所谓反说约也。”[6](卷4,P.110)分合说即博约说,一本而万殊,一本是吾心,散殊是心体一本的流行,天地万物的理虽各分殊,但合为一理。
虽理气有分,但理气亦合。“形色,气也。天性,理也。有耳便自能聪,有目便自能明,口与鼻莫不皆然,理气合一也。心是形色之大者,而耳目口鼻其支也。”[6](卷7,P.157)形色与天性的关系,犹理与气之关系,耳目口鼻是有形色的气,其聪明是其天性理。心是形色的根,耳目口鼻是支外。“耳目口鼻,是气之流行者。离气无所为理,故曰性也。然即谓是性,则理气浑矣,乃就气中指出其主宰之命,这方是性。故于耳目口鼻之流行者,不竟谓之为性也。纲常伦物之则,世人以此为天地万物公共之理,用之范围世教,故曰命也。所以后之儒者穷理之学,必从公共处穷之。”[6](卷7,P.161)[18]耳目口鼻的流行不是性,是形色。理气浑然,理不离气,离气无理。气中主宰的命,是性。社会的纲常伦理的规则,是天地万物公共的理,以此来范围、规范人世的教化,这是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尽天地万物内在的道理、条理,体认天地万物错综复杂的性质、特性,以把握天地万物的必然性趋势或指向,揭示了气理性命的逻辑演化次序,及其各自的性质、功能。
理不离气,“无气外之理,‘生之谓性’,未尝不是。然气自流行变化,而变化之中,有贞一而不变者,是则所谓理也、性也”[6](卷6,P.133)。气是不断流行变化的,形色之气在变化中必呈现万殊现象,气在变化流行中贞一不变的是理是性。换言之,变中不变的理与性是比较稳定的,因它是所以区别事物与事物之间不同的理则和性质,也即万殊之所以是万殊的识别和标志。
理气心性圆融无碍。“圣人即从升降之不失其序者,名之为理。其在人而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气之流行也。圣人亦即从此秩然而不变者,名之为性。故理是有形(见之于事)之性,性是无形之理,先儒‘性即理也’之言,真千圣之血脉也。”[11](P.146)圣人以气的升降流行按一定规则秩序而不混乱,称为理。在人而言,四端的心都是一气流行而合理。圣人又以气流行有秩序而不变的,叫做性。
理作为气变化流行而有形显现于事物的性,性是无形的理。由此而观,先儒讲“性即理也”的话,真是千圣的血脉。千圣的血脉必然流向千古而不绝。
四 《明夷待访录》的政治哲学
黄宗羲哲学理论思维最有创见和最能凸显其时代精神的是其政治哲学。黄氏在其师绝食殉明和自己抗清失败的外在自我主体激烈震撼下,在内在自我主体不断反思中,于顺治十年(1653)撰写了《留书》,直接批判社会政治。十年后的康熙二年(1663)修改补充《留书》,撰写《明夷待访录》,晚年又撰著了《破邪论》。在其人生智慧致思历程的40余年中,他没有间断地思议政治哲学话题。
政治哲学是对于社会政治理念或政治理想的思议、反思的学说,是对于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制度、权利义务、集体个人利益、教育宗教等规则的融通和合。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首先是求制度与权利的协调。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制度是统治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是维护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和维护统治者特殊权利的合法支撑。黄宗羲说:“古之有天下者,日用其精神于礼乐刑政,故能致治隆平。”[19]礼乐刑政作为政治、法律、文化的制度性建设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在秦废封建、立郡县以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得以实施,并推行两千余年。黄宗羲批判与鞭挞的矛头所向,就是这种制度。这种制度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作为权力中心的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20](《原君》,P.2)。把天下一切权利都归于君主自己一人,君主的权利和行为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和制约,不仅把天下之害归于别人,而且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自利,于是君主把自己大私转说成天下大公,为其把千千万万人的天下变成其一人的天下作合法性的解说。
天下成为君主一人的天下,国家成为君主一人的国家,在这种君主专制的体制下,天下就成为君主自家的产业,天下就成为其一姓的产业。“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20](《原君》,P.2)既以天下为自家产业,为维护其产业,便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20](《原君》,PP.2-3)。在这里,黄宗羲严正地揭露和控诉了君主专制制度敲剥的不合理性和压迫人民的残酷本质,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0](《原君》,P.3)。只有废除这种君主专制制度,人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20](《原君》,P.3)人人为了各自生命的延续存在,各得自私、自利,是自然合理、合法的。
黄宗羲为了人各得其私其利的合理、合法性,便从人类的元初状态说起。“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20](《原君》,P.2)黄氏所诉求的社会制度与君主的关系是:人人各自的自私、自利与天下的公利、公害,社会制度与君主权利等要达到平衡、协调。这种平衡和协调的取得,就在于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要使天下人受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为天下人除害。心怀天下人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而无一己的私利,这是君主的正当权利。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制度与权利的和谐,国家才能致治隆平。
其次是求职分权力与义务的统一。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君主权力过分膨胀,丧失了其千万倍于天下人的勤劳而不享其利的崇高道德品格,迷恋于一人的淫乐,而不尽其职分的义务,使权力与职分义务产生严重冲突。“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不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20](《原君》,P.3)许由和务光为尧、虞时高士,尧虞让以天下而不受,召以官职而不欲闻,这是尧虞明白自己职分的权力与义务的表现,使天下人人相让。若不明白君主职分的权力与义务,民间人人都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私利而争斗,许由、务光这样的高士就不闻于世了。由于君主职分不明,便由淫乐而换来无穷的悲哀。
君主职分的权力与义务,是为天下人谋利益,而不为一己谋利益;为天下人除害,而不为一己除害,所以君主比民众勤劳千万倍。然当下君主职分的权力与义务变了。“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20](《原君》,P.2)古今君主职分的权力与义务的转变:一是转天下民众为主而为客;二是转君客为君主;三是转君为天下人经营谋利除害为一己谋利而搞乱天下。
这种转变,凸显了“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亲,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20](《原君》,P.3)。天下人对君主态度的变化,既反映了君主职分的权力与义务的变化,亦反映了民心的变化,在这里,君主的权力与义务是统一的。为天下人谋利除害,人民就爱戴君主如父如天也不为过;如果荼毒敲剥天下人,那么就视其君主为仇寇、为独夫民贼。所以君主要认清自己职分的权力与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汤武讨伐桀纣的下场。
由君的职分而推致为臣职分。黄宗羲认为,为臣职分的权力与义务,不是忠于君主一人,而是因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20](《原臣》,P.4)天下国家广大,君主一个人治理不过来,需要臣来分治,以管理国家事务。所以为臣的权力与义务就在于为天下、为万民谋利益,服务于天下万民,而不是为君主一人一姓,这是为臣职分的宗旨。为天下万民利益考虑,是为臣的权力与义务,不符合天下万民利益的事,即使受君主的强迫,也不去做,杀身也不从。如果为君主的一人一姓的嗜欲私利,做臣的听之任之,那么,为“臣不臣”,即没有尽到为臣职分的权力与义务。朝廷之所以设宰相之位,是因为“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20](《置相》,P.8)。宰相的职分是以其贤能补救君主的不贤不能,这就是说宰相要守住自己职分的权力与义务,为天下为万民,使国家长治久安。
黄宗羲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20](《原臣》,P.5)。万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万民的忧乐,是决定天下治乱的力量。黄氏依其对历史的考察,认为治乱循环,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又会出现暴政而大乱。“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20](《原臣》,P.5)骄奢淫逸的君主,不是选贤能之士来辅佐补救自己的不贤不能,而是选择那些为其奔走服役的草野之人,无异于君主的奴仆。
黄宗羲通过古今君主职分与为臣职分的比较,以及揭露批判今世君臣职分权力与义务的严重失衡与冲突,以求君臣职分权力与义务的平衡和谐。
再次是求道德与法律的和谐。德治与法治的话题自古以来常谈常新。人们往往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则看成是对等的,而忽视其和谐性。道德是内在自我主体的自觉,法律是外在客体加于主体的一种强制。黄宗羲将古今之法作了比较:“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20](《原法》,P.6)。二帝三王关爱天下百姓的衣食教以及婚姻,凸显德治之法,德治之法一切为天下百姓,而不为一己之私。这是三代德治之法的本质,体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性、和谐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20](《原法》,P.6)。德治之法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藏天下于天下百姓的民本政治规则与和谐社会秩序,而不在于刑赏之权和贵贱地位。
后来的君主,破坏了三代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的统一性、和谐性。“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20](《原法》,P.6)君主为了巩固自己一人一姓的长治,因而制订法律,以保证其子子孙孙永远拥有天下,这种法律规则本质是一家的私法,而非天下的公法。“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20](《原法》,P.10)把法律藏于自己的筐子里,专为自己所用,即变公法为私法。这种私法只能制乱于天下,是为“非法之法”。这种“非法之法”的私法,是保护一人一姓利益和统治的法,造成了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的严重冲突与紧张。
第四是求教育与宗教的辅成。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机构,“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20](《学校》,P.10)学校不仅为培养士子,而且是天下致治的场所、议政的平台。“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20](《学校》,P.10)学校营造了一种宽松的、自由的学术气氛,以及宽容的议政的风气,可以议论天子的是与非。天子受到学校这种议政舆论的监督和左右,亦不敢自以为是与非,体现了一种天子不敢自专的民主政治的气象。
不仅天子为政治国的决策要采纳学校议政的意见,而且天子的权力也受一定的制约。譬如“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20](《学校》,P.11)显示了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学校议政的力量与反映民意的作用,使社会奸邪之气得以收敛,正气得以发扬。
然而,“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20](《学校》,P.10)三代以下,在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压下,国家的是非一出于朝廷,决定于君主,便没有了真正的是非,学校不仅失去自由议政的功能,而且失去制约、监督政治是非的职能。学校成了为竞争科举考试、富贵利禄熏心的场所,也就失去了培养人才的意义和价值。
黄宗羲主张:“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20](《学校》,P.11)郡县学官不要朝廷选派,由郡县民主公议,不拘泥于当过官和未当过官的,都可以担任。学校设《五经》教师,以及兵、法、历、算、医、射的教师。在学宫以外,乡间的寺观庵堂改造为书院小学,由经师、蒙师任教。寺院产业归学校,以供给贫穷学生。郡县在朔望日,大会一邑的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祭酒,推选当世大儒或退职的宰相担任。每到朔日,天子率宰相、六卿、谏议大夫到太学听讲,天子官员就弟子列。国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天子的儿子,年十五,与大臣的儿子就学于太学,使其了解民情,习于劳苦,不要闲置宫中,整天所见所闻不出宦官宫妾,而养成妄自尊大的坏习。
学校不仅是议政、学习、培养人才的机构,而且是教化道德礼仪,敬祖尊老、祭祀乡贤的场所。在乡饮酒礼时,合郡县的缙绅士子,士人庶民中七八十岁年长者,请面南上座,郡县、学宫的官员都面北叩请乞言。乡贤名词,以功业、气节、文章、言行为标准,不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先贤陵墓祠宇的修饰和表彰,都由学官负责管理。这种修饰和表彰乡贤祠宇的活动,不仅是一种纪念活动,更在于树立敬畏,学习先贤言行,使人的心灵得以澄明,精神得以慰藉,而获得精神家园的温馨。这从一个层面培育和提升了人的宗教情操。
先贤之立祠宇或从祀,其标准与孔子之道相一致。“余以为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世治,则巷吏门儿莫不知仁义之为美,无一物之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乱,则学士大夫风节凛然,必不肯以刀锯鼎镬损立身之清格。”[21](《从祀》,P.193)孔子之道的内涵,是仁义道德,它是天地人纪赖以生存的生命力和常运接续不息不坠的动力。由此,国家治乱时百姓都知道仁义道德为美,士大夫能保持道德情操风节,即使刀锯鼎镬加于身也立身清格。具有这样崇高道德品格的人,才能从祀。百姓从这些从祀的人格精神中获得教益和道德升华。
黄宗羲认为,对天应有敬畏之心。“今夫儒者之言天,以为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诗》言‘天降丧乱’,盖冥冥之中,实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时将颠倒错乱,人民禽兽草木,亦浑淆而不可分擘矣。”[21](《上帝》,P.195)尽管黄宗羲破佛教的诸天说、纬书的五帝说和天主教抑佛崇天说,而以理释天,但他仍然承诺在冥冥之中实有主宰者,否则,四时就会颠倒错乱,人民禽兽草木就分辨不清了。最终黄氏以此冥冥中的主宰者是天。对天的敬畏和信仰,在中国百姓心灵中根深蒂固,是百姓万民遭遇灾难变故、人生不幸等困难时的心灵缓解机制、心理安慰力量以及精神的避难所,百姓万民从天那里获得心灵的安宁,这就是中国式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操。这种宗教意识与宗教情操又和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操相和合,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与宗教的和谐,教育与宗教的相辅相成。
黄宗羲是一个有政治头脑和眼光的思想家、学术史家和政治家,他的《明夷待访录》批判的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鞭挞君主是独夫民贼、荼毒人民的屠夫,他立足于天下万民,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而具有鲜明的民本思想,并推致由天下万民公推选择君主的民主思想,而具有近代化意识。然而由于清入主中原,这种具有巨大生命力的近代化意识连同其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运动,统统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特别是清代实行文化恐怖主义的“文字狱”,学术自由创造的环境被彻底埋葬了,明清之际所呈现的各种创新思想也被残酷地窒息了。
收稿日期:2013-08-23
注释:
①先师指刘宗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