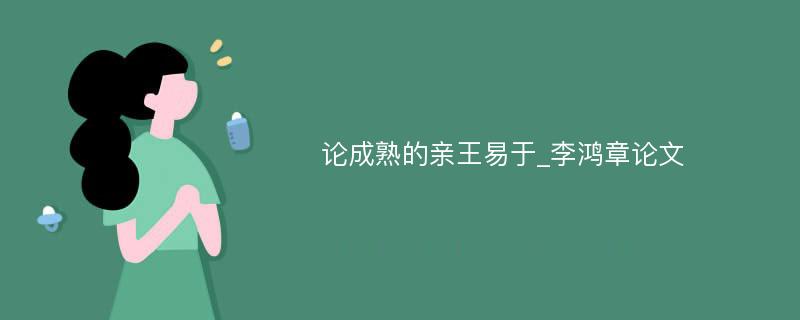
论醇亲王奕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6)—02—0097—10
醇亲王奕譞是晚清皇室一著名人物,曾在光绪十至十六年(1884—1890)实际主持清朝中央政府之大政方针近七年时间。作为清代最后两朝皇帝的本生父祖,其历史地位之显赫早已引人注目,但他在晚清史上的重要性却主要不在这里,而在其主持或参与的一些重大决策对当时的国内外政局及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有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这一人物,以往的研究还很薄弱,相关涉及之论,字里行间多有贬斥之意,特别是其协助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一事,尤为人所诟病。笔者以为,这样的观点并非实事求是,至少是十分片面的,在颐和园问题与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认识上更存在某种误区。本文拟对此进行考察,以期使奕譞其人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并使人们对光绪年间其主政时期的一段历史能有正确而详实的了解。
一、醇王的政绩与品行
奕譞,号朴庵,道光帝第七子,生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40年10月16日),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登基后封为醇郡王。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政变”时,与恭亲王奕訢一起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出力,事后奕訢封为议政王,主管枢垣、总署,奕譞则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主管神机营练兵事务。同治十一年(1872)晋封亲王,十三年末因次子载湉入承大统为光绪帝,疏请开去一切差使,懿旨允之,命以亲王世袭罔替。光绪六年(1880),中俄伊犁交涉事起,时局紧张,受命复出,参与议政,再管神机营。十年(1884)三月,中法越南事急,北宁、太原失守,主持全局的恭王不能有效应对危机,慈禧太后与醇王定议,免去恭王本兼各职,军机处全班易人;醇王以皇帝生父关系,不便公开主持大政,懿旨命中枢、总署遇有大事与之商议,迄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月1日)因病去世,实际柄执朝政近七年时间。
自咸丰十一年末创立垂帘听政之制,至光绪十六年醇王去世,在此三十年间,清廷的内外大政实由恭、醇二王先后主持。尽管亲王入主中枢不合清朝祖制,但垂帘听政既已打破祖制,中枢领以亲王亦属名正言顺。其间,慈禧太后以女主当国,虽为人精明,性格果断,却因学识、经验等条件的限制,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不能如前此历朝男性皇帝一样“乾纲独断”,操纵枢垣,而不得不依靠恭、醇二位“最近支”的亲王作为“首辅”——实为主政。时人有谓:“两宫垂帘听政,则军机必以亲王领班,下以数大臣辅之,所谓军机王大臣是也。凡事由亲王作主,商之大臣而定。每日上班(按:即“见起”——引者),必由领班之亲王开口请旨。所请何旨?即未上班时所商定者。虽偶有更动,亦罕矣”①。因此,这三十年间清朝政治的一切成败得失均与二王密切相关,谓三十年政治先后是恭、醇二王的政治,也不为过。如果没有二王先后主政,这三十年的政局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虽然不好想像,但只要看一下二王故去后,光绪己亥、庚子年间慈禧依靠端王载漪等人主政期间的政治状况,便不难找到答案。所以,不能不说恭、醇二王实为同光时期三十年中国政局的中流砥柱。
而这三十年在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中,是所谓“同光新政”时期。它上承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二十年社会动荡阶段,下接甲午和庚子两次对外战争失败及由此引起亡国灭种危险的二十年灾难深重时期,是整个晚清史上时局相对稳定,因而得以进行洋务运动的时期,客观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其中,恭王主政的二十三年间(1861—1884),洋务事业主要是由一些地方督抚如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其各自管辖范围内和力所能及条件下分别进行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洋务事业具有地方性和零散性,缺乏由中央政府统一主持和推进的力度。而这种情形在醇王主政期间(1884—1890)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中央政府主导和推进自强事业的力度较以前明显增强,这是恭醇二王在个人性格和见识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主政者个人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也是人所公认的事实。
醇王主政时期,清中央政府先后完成如下重大政治举措:其一,比较稳妥地处理了中法越南交涉的和战问题,当战则战,当和则和,从而创造了晚清对外战争史上仅有的一次以签订不含割地赔款等内容的条约而结束战争之特例,并带来战后十年晚清历史上国内外局势最为平静的一段时期,为自强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②。其二,新疆、台湾建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三,确立大治水师的战略方针,在此方针之下,创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建成第一支近代海上力量即北洋海军,在中国军事近代化历史上留下深刻足迹。其四,支持直督李鸿章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并把兴修铁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最终排除守旧势力对铁路事业的阻挠(详见下文)。其五,支持鄂督张之洞创办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为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建立打下基础。其六,将开始于中法战前的电报事业继续推广延伸,数年之间北起黑龙江黑河,南抵广东海南岛,西至新疆喀什噶尔,无不架设电线。凡此一切,均为醇王主政时所完成的业绩,其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以往人们对醇王的以上政绩多视而不见,在对比恭、醇二王先后主政的这段历史时,总是褒恭而贬醇,譬如论甲申易枢,有所谓“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之讥评③,甚至有“逐恭王出军机,以瞽瞍继任”之恶谥④。此类说法不过是时人根据一己好恶,随便乱发的感慨。今人受此影响,也有所谓醇王“才具平庸”,“学识才能与聪明才智样样都及不上恭王”的说法⑤,甚至有说醇王是晚清时的“大贪官”,是当时京城中“生活最豪华、最糜烂”者⑥。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有谓:奕譞“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任事,聪颖弗逮其兄訢,而劲爽过之”⑦。不知这里所谓“聪颖弗逮”一语(大概这就是所谓“学识才能与聪明才智样样都不及恭王”之说的根据所在)所指事实为何,但说醇王性格直爽,敢于任事,则确属事实。由于这一性格,醇王在其主政期间对于认为正确之事敢于果断而坚定地加以实施,在这一点上恭王不免相形见绌,这在兴建铁路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详下)。至于醇王的聪明才智,且不论上述其主政期间所创政绩决非才具平庸者所能做到,仅以其密友翁同龢的下述一段话便足以说明问题,他说:醇王才思敏捷,平生著述诗文甚夥,“雄文丽句,浩若江海。初未尝构思,而下笔遂与古人相抗,所著《朴庵文集》、《诗集》、《竹窗随笔》、《滦阳日记》、《航海吟草》、《退潜别墅存稿》、《窗课存稿》为世所宝”⑧。这恐怕不尽是翁某的吹捧之言,因为这些诗文至今尚在,人们尽可找来一阅。
关于醇王的操守问题,上述费氏之书又云:奕譞“势虽赫奕,而励廉隅,包苴不入……操行为诸王冠”⑨。对此,时任吏部主事的何刚德在民国间的回忆可作为旁证:“醇王薨,以其邸改为醇贤王庙……余时派往查估工程,见其房屋两廊,自晒煤丸,铺满于地,俭德殊不可及”⑩。如所周知,煤球是寻常百姓人家为节省开支,以煤粉掺水自制的廉价燃料,作为烧饭、取暖之用,醇王以皇帝生父且为实际执掌中枢和总署的最高当权者之尊,家中不用上等煤块,而自晒煤球,仅此一事,便足以窥见其生活俭朴、居官廉洁的品行。溥杰先生近年的回忆也说过,其祖父奕譞曾以“不爱财”作为治家格言,写成条幅张挂于堂屋,用以教育子孙后代(11)。醇王既能如此要求其后代,便意味着其自身便是以此作为行事准则的。据奕譞自述,自幼其母便不准其索要他人些微财物,以防微杜渐:“尚忆十岁时,索取太监张进喜一珊瑚豆为佩,吾母见之,严加询问,因以实对。于是怒甚,索杖欲责。余跪求数刻,母怒稍解,泣曰:‘汝尚孩提,即索取他人之物,将来当差,必一贪婪败类也,吾尚何望乎?’言讫大哭。余虽幼,亦知此语甚重,当即自誓必改,方邀免责,慈颜不怡者竟日。及余任事后,母犹尝举此事为戒。”(12) 可见,醇王的“操行为诸王冠”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家庭和自律方面的深刻原因的。在这一点上,其六兄奕譞显然不能与之相比。恭王曾被人指为“贪墨”,如王闿运《祺祥故事》中曾谈到同治初年恭王以议政王领枢垣时,家中收受门包,以至贿赂公行,流言颇闻云云(13),但在时人笔记中却找不到醇王的这类事情。
此外,醇王为人正直,在官场同僚间能够主持正义,疾恶如仇,也显示了其人格的一个方面。左宗棠收复新疆,为国家民族立有大功,醇王对其十分敬重,曾邀请他到自己家中畅谈,并合影留念。光绪十年七月,礼部尚书延煦参劾左氏以大学士而未在万寿节之日随班叩拜,要求交部议处,参折中诋毁左氏“不由进士出身”,并将左以年迈疾病缘故未随班叩拜诬为“蔑礼不臣”等。醇王为之愤慨,出面仗义执言,指斥延煦饰词倾轧,藉端訾毁,肆口妄陈,实属荒谬,请将该尚书亦交部议处,慈禧因将延煦革职(14)。此事也显示出醇王丝毫没有满汉族群之见,不因延煦是旗人而站在他一边,而只讲是非原则。又,李鸿章举办洋务,屡遭守旧势力攻击,而醇王主政则全力支持李氏兴建铁路,创办海军,举办漠河金矿等事业,李氏将其引为知己,以至醇王去世后,痛感在朝中失去倚靠,时常提及醇王的知遇之恩,其意盖以为这不仅是他(李)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一大损失。
甲申易枢是晚清政坛大事之一,历来为论者所乐道。一般以为,这是慈禧借机赶走恭王,使醇王取而代之,以遂其假公济私之目的。但这不过是主观推想,没有任何证据的。实际上,此次易枢的原因就在恭王主政后期办事因循敷衍,对中法越南交涉的和战大计徘徊不定,一筹莫展,引起慈禧严重不满的缘故。光绪十年三月,面对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的险恶形势,恭王在见起时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而慈禧并不领情,“谓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恭王“犹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几不能起”,以致一同见起的末班军机大臣翁同龢忍不住“越次”发言,劝其“宜遵圣谕,勿再琐屑”,并在事后的日记中喟叹:“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15)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易枢之事。要知道,中法越南交涉,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容不得含糊敷衍的,恭王既然无能为力,慈禧决定以醇王取代之,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不可能有什么假公济私的用意在其中。
以往论者还有说醇王是顽固守旧派之领袖的。这种观点十分片面,因为它只看到醇王早年的思想守旧,而未注意到其后来——特别是主政时期——思想的根本转变。醇王自幼生长宫中,耳濡目染及所受教育均属传统范畴,其早年思想之趋于守旧,固属情理中事,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从前对西方事物“尝持偏论”(16)。这集中体现在同治八年(1869)讨论修约问题时的一个奏折中,称:“请皇上自今以往,将大内西洋物件尽行颁赏,明为贱货贵德,暗示永远弃绝,则天下臣民闻风向义,效法乐从,无不以佩带洋货为贱为耻,渐至无人售买,则惟利是图之夷人将不待驱逐而自遁矣。”(17) 足见此时其思想的保守与简单,竟至以为只要大内不好洋货,便无人再用西洋之物,于是洋人即可“不待驱逐而自遁”。如所周知,这种思想在晚清时期是有其普遍性的,不见醇王说此番话三十年后的光绪庚子年间仍有载漪、刚毅等人要尽毁洋货吗?可知同治年间醇王有此想法也是不足为奇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醇王并没有像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思想长期守旧不变,而是不久以后即改变了原来的思想,以下所述他在铁路问题上的态度便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二、醇王与中国早期铁路事业
奕譞在其主政的近七年时间内以清廷主政者的权威,在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配合下,先后举办了一系列新政事业,已如上述。其中,排除守旧势力的阻挠,支持直隶地方首先开修铁路并把兴建铁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对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的影响十分显著。
铁路是随着十八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发明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于西方各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铁路里程的长短,是其近代化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中国人之知道铁路,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同治年间。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此一事物只可用于西方,而不适于中国;对西方事物向持敌视态度的顽固守旧派自不待论,即使少数以思想开明著称的所谓洋务派也同样未曾认识到修建铁路的必要性。同治六年(1867),清廷就与英国修约之事命各督抚奏陈意见,涉及的问题包括铁路、电线等事,江督曾国藩复奏有谓“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是以“皆不可行”,建议“就小民生计与之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18)。鄂督李鸿章亦称,电线、铁路“此两事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而铁路比铜钱尤甚”(19)。当时连曾、李都对铁路持如此看法,他人更可想而知。然而数年之后,时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首先对铁路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同治十三年(1874)底,李在其著名的《应诏筹议海防折》内从国防需要的角度谈到兴建铁路之必要:“军情瞬息万变,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里,则统帅不至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20) 这里, 李鸿章虽然改变了其以往认为“铁路有大害于我”的意见,但仍说是中国“急切办不到”之事,何以如此?主要因为时人的保守观念实在顽强,朝野上下的反对力量过大的缘故。尽管这样,但他还是认为只要朝廷主政者能够与自己认识一致,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加以强制推行,仍是可以办到的。因此,翌年(1875)李便利用进京叩谒同治帝“梓宫”之机,面见恭王奕,请后者主持兴造铁路,得到的答复却是“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也遭拒绝,据称“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于是,李鸿章“从此绝口不谈”铁路之事有五年之久。(21)
光绪六年(1880),中俄伊犁交涉事紧,原直隶提督刘铭传奉旨入京,首次正式奏请修造铁路。奏折中,铭传历数铁路关系国防及民用的种种利益,建议急造数条铁路干线,最后说:“事关军国安危大计,如蒙俞允,请旨饬下总理衙门迅速议复。若辗转迁延,视为缓图,将来俄局定后,筑室道谋,诚恐卧薪尝胆徒托空言,则永无自强之日矣。”(22) 旨交李鸿章议复。 鸿章遂乘机在沉默了五年之后再提铁路之事,极力赞同铭传意见。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内阁学士张家骧、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等众人纷纷上折反对,极言铁路之诸多“弊端”。恭王即顺水推舟,决定对刘铭传的建议不予理睬,遂有翌年(1881)正月所谓“叠据廷臣陈奏,佥以为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的谕旨(23)。由此足见恭王在铁路问题上的因循保守态度。此种态度不能不极大影响中国近代化之进程。要知道,同时期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大力修造铁路,时至甲午战争前夕,其通车里程远在中国当时仅有的二百余公里铁路之上,而这一点正是导致甲午之役结局的原因之一,可见恭王不能不对其主政时期中国近代化速度的迟缓负有责任。而且需要注意,甲午前夕中国所造全长二百余公里的津榆铁路,还是在醇王主持下才得以建成的。更主要的是,醇王不仅使直隶境内建成了一段铁路,而且经过艰难努力,排除守旧势力的干扰,最终使慈禧太后认可兴修铁路的必要,从而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
光绪七年(1881)初,正当朝廷决定拒绝刘铭传请修铁路奏请之时,醇王私下致信李鸿章,对兴建铁路一事表示出兴趣,流露了赞同意向,谓不妨“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24)。由于有了奕譞这一暗中支持和提示,李鸿章才敢于批准在其管辖的直隶境内矿区试造铁路,这便是开平矿务局以运煤需要为名,于同年五月建成的唐山至胥各庄全长二十华里的一段铁路,成为中国自造铁路之嚆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此事标志着奕譞对西方事物认识的转变,而且一经认识即力图付诸实施。尽管他当时尚未主政,但也可利用其地位和影响力设法推进自强事业。在这一点上,与恭王的畏难因循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当他取代恭王而实际主持朝政后,便以手中权力正式开始兴建铁路。
十二年(1886)四月,醇王亲历风涛,巡阅北洋海防,其间就大力兴办铁路一事与李鸿章进行了深入面谈,回京后又往返函商,认为铁路之修,势在必行,不容拖延,决定先将此前所造唐山至胥各庄十八华里铁路延长六十五里至阎庄,再从两端分别接造,西至天津,东至山海关,以使京畿附近沿海防务贯通一气,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轻重缓急,逐步筹划全国铁路事业。因于十三年(1887)二月以海军衙门名义正式奏请修造津榆铁路,谓此路若成,则驻扎津南小站的盛军万余游击之师“在此数百里间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云云(25)。奏入,经慈禧太后照准,直隶方面便开始筹集商股,并借洋债一百万两,着手兴修。足见醇王在早期铁路事业上所起关键作用。李鸿章为此致函醇王感谢说:“幸得殿下亲历北洋,决疑定计,奏准兴修津沽铁路,鸿章额手称庆。以为铁路乃举世所疑,而殿下雄心毅力,一闻鄙言,如石投水,诚千载一时,为中国自强之基。”(26)
十四年(1888)八月,阎庄经塘沽至天津东门的一百七十五里铁路告成,李鸿章乘车沿途察看之后,以“铁路洵为今日自强急务”,又致函醇王,请“大力主持”,将铁路从天津接修至通州,使京津通车,以为各省兴造铁路表率(27)。对此,醇王自极表赞同,立即又以海署名义上奏,请续修津通铁路,慈禧太后也照例允准(28)。不料,此项懿旨发布后却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先是,津沽铁路建造之时京中士大夫们已在议论纷纷,只是碍于醇王面子,且阻拦的理由也不充分(不好再说铁路不适于中国),暂时忍隐未发。至此总算抓住一个他们自认为是充足的理由,即京津若通铁路,则险要尽失,适予来自海上之外敌提供一个入侵京师的方便工具。于是也就不顾醇王意见,群起上折大加反对,其中不乏盛昱、余联沅、屠仁守、洪良品、翁同龢等诸多名流。面对如此浩大的反对声势,醇王不为所动,即以海署名义上奏,作针锋相对的反驳,并坚定表示“铁路为军国要务……不敢为众咻牵制”(29)。旋又以个人名义奏称:“方今时局为自古所未有,欲弭非常之患,必有非常之法……议者动云祖宗时所无,独不思方今天下局势,岂开辟以来所有哉!”(30) 此语鲜明的表现出醇王此时决心排除守旧势力的阻挠,引进西方先进事物,以实现自强目标的思想。须知,当时能有这种进步思想的中国人还只是极少数。
同时,醇王还对一般顽固守旧者阻挠新事物的言行表示了愤慨,说这班人,当中外有事之时“空言盈廷,杳无实策”,“及军事甫定,局内(指当政办事之人——引者)创一事则群相阻挠,制一械则群讥糜费,但阻本国以新法备敌,而不能遏敌以新法图我”(31)。这是很令读史者掩卷叹息之事。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清时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之所以屡遭挫折,以至在与日本进行学习西方的竞赛中输给对方,这些思想守旧的士大夫们的阻挠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日本的伊藤博文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曾在该国高层的一个秘密会议上针对某些日人以为中国会迅速富强的担忧,说是大可不必,理由是清朝当局向来因循保守,“稍为变更,则言官肆口参之”,“现在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32)。然而,伊藤这里所说清朝当局惯于因循苟安,一、二年后必又“睡觉”的预言却并未言中,因为他作此预言的时间是在光绪十一年十一月末(1886年1月),而此后奕譞主政期间, 清廷一直在奋力排除因循守旧势力的阻挠,力图深度创新以求自强。兴建铁路政策的确立,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光绪十四年因修建津通路而引发的铁路问题大讨论,虽有奕譞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主张,但由于京中反对者过众,使慈禧不得不暂时收回已经作出的允建津通铁路的懿旨,改令各省督抚就应否广泛兴建铁路问题各抒己见。在各督抚的复奏中,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署江苏巡抚黄彭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力主大修铁路的意见颇受慈禧和醇王重视,尤以张之洞关于修建芦汉铁路的意见最受重视,盖较之津通一路,芦汉一路纵贯南北三省,里程更长,规模更大,且可避开守旧者所谓邻近海口易于资敌的反对理由。于是,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慈禧再发懿旨称,铁路一事,“为自强要策……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举办,毋庸筑室道谋!”(33) 这标志着清廷自此以后已将修建铁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一切顽固守旧者对于铁路之事不容再予置喙。继而,清廷指令户部每年拨款二百万两作为修建铁路的常年经费,并将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起从南北两端分头筹办芦汉铁路。旋又支持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以炼铁轨,复决定兴修关东铁路,以加强东三省防务。
津榆铁路在甲午战前已经通车,关东铁路也已修到山海关外,这主要是李鸿章秉承醇王的遗志,在坚决修建铁路的国策保障下,竭其所能完成的事业。甲午战后直至清末,清廷更是注重铁路事业的发展,芦汉铁路、京张铁路等相继建成。只是由于赔款所造成的经费困难等原因,全国范围铁路事业的进展仍举步维艰,但至少在朝廷内部再也无人敢于公然阻挠修铁路了。奕譞的这一历史性贡献,是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做不到的。
三、醇王与颐和园问题考辨
所谓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一事,历来是人们评价奕譞时的一个焦点问题,此事给他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论者以此蔑视其人品,贬低其作为晚清一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甚至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归咎于他。笔者认为,这里既有对关键史料理解上的问题,也有对慈禧修园一事的来龙去脉了解不够的缘故,因而此类观点并非客观公正。由于此事不仅涉及醇王作为一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也关系到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探讨,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非同一般,有必要进行一点考辨,以了解事情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有关醇王与颐和园问题的最早一条史料,见于《翁同龢日记》中光绪十二年十月的一个记载,即:“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34) 这是一条人们熟知且引用频率极高的史料,用以说明奕譞明知颐和园工程将要祸及北洋海军,仍违心附和慈禧太后,以不惜毁掉北洋海军的代价重修颐和园云云,成为论者对奕譞进行否定性评价的一条主要证据。窃以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这里似存在一个史料理解上的错误。
上述史料中的关键一语是“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对于其中的“勃海”一词,论者一般释作“渤海”,认为代指北洋海军,进而认为以“昆明”取代“渤海”,就是用北洋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的意思。然而试问,有何理由断言“勃海”即为“渤海”?显然,“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实为一对偶句,即“昆明(湖)”与“万寿山”相对,“勃海”与“滦阳”相对。既然昆明湖和万寿山都是颐和园(清漪园)的一部分,则“勃海”与“滦阳”亦应是同在某地的两处山水园林才说得通。若把“勃海”释作“渤海”,便与“滦阳”(避暑山庄)风马牛不相及,是说不通的。如所知道,汉语对偶句的上下两词,不仅词性上要相同或相似,含意上也要有相当的共性或关联性,即所谓“沿对革,异对同,白叟对黄童,江风对海雾,牧子对渔翁……梁帝讲经同泰寺,汉皇置酒未央宫”,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试思“渤海”与“滦阳”有何含意上的共性或关联性可言?这两个名词之不可相提并论,是不言而喻的,一为我国内海海域之名,一为避暑山庄之别名,二者实在毫无瓜葛。且恕孤陋寡闻,笔者也从未见过时人有把北洋海军(或与北洋海军相关的事物如北洋水师学堂等)以“渤海”一词来代指的,甚至也未见过时人有像今人一样以“渤海”、“黄海”等名称指称我国近海海域者,而都是以“北洋”、“南洋”等名称呼之。因之,不能设想“勃海”一词会与北洋海军有什么关系。所以,把这条史料与北洋海军联系在一起,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笔者注意到以往也有对这条史料作出不同解释的学者,如吴相湘先生说:“《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有云:‘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由是可知:颐和园修建计划定计由来,慈禧初意且欲修其热河行宫(滦阳),经醇王、庆王斡旋,始弃远就近,作此决定”(35)。这里把“滦阳”、“勃海”仅理解为热河行宫,未与北洋海军挂钩,可避免牵强附会之嫌,是颇有见地的。但解释仅限于此,仍有所缺憾,盖未进一步说明何以如此解释,特别是未就“勃海”与“滦阳”问题作出说明,尚难彻底服人。
笔者以为,翁同龢所说的“勃海”应为“白海”之误,而“白海”则是元朝时地处塞北的一处皇家行宫所在地,与清朝时也是地处塞北且同为避暑行宫所在地的“滦阳别墅”有着很强的相似性,是醇王用的一个典故。
元朝也是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同样定都北京的朝代,其皇室也有每年夏季赴塞北避暑的习惯,位于滦河上游的上都(即清代的开平城)是其北行的终点。上都,因为地处滦河北岸,元时有“滦阳”之别称,时人谓“滦阳,即上都”,且有诗云:“李陵台畔野云低,月白风清狼夜啼……举杯一吸滦阳酒,消尽南来百感情。”(36) 另在距上都不远处,且位于大都(燕京)通往上都途中, 当时有一片面积广大、烟波浩淼的湖泊,蒙语名“察罕淖尔”,汉译“白海”(按:蒙语“察罕”,白色之意;“淖尔”,海子),元帝室在湖畔建有行宫,名察罕淖尔行宫或白海行宫,作为往来时停留休憩之用。时人诗云“行宫临白海,金碧出微茫”或“凉亭临白海,行内壮黄图(原注:右,察罕脑尔,犹汉言白海也)”等(37),就是描绘白海行宫情景。因之,元朝时地处塞北的“滦阳”和“白海”都是皇家避暑行宫所在地。换言之,“滦阳”和“白海”是元代塞上避暑行宫的代名词。醇王是借用了元朝的这一典故,代指清朝皇家同样位于塞上的热河避暑山庄(滦阳)及其附近的另一座行宫——“滦阳别墅”。
清朝前期,康熙、乾隆、嘉庆诸帝每年夏季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居住。避暑山庄,地处滦河中游,位于北岸,因此也有“滦阳”之别名。而且,在离避暑山庄不远处,并在北京前往避暑山庄途中,当时另有一座被称为“滦阳别墅”的喀拉河屯行宫(滦平县治所在地),作为从北京到避暑山庄来往休息的场所。该行宫由多尔衮始建于顺治七年(1650),是清朝皇室在塞北修建的第一座用于躲避京城酷暑的行宫,康熙年间热河避暑山庄建成以后,仍作为前往山庄途中停留休息之用(38),其位置和作用与元朝的白海行宫十分相似。所以,醇王用“白海”与“滦阳”相对,不过是借用了元朝皇家避暑行宫的故事,代指清朝皇家位于塞上的两处行宫罢了,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我国内海渤海没有任何关系。至于《翁同龢日记》中之所以把“白海”写作“勃海”,大概是因为发音相近,一时笔误,或由于翁氏不知此典故,且非直接听醇王所说,遂不免发生这一小错。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一小错竟使人们误以为醇王有意自毁北洋海军,岂不厚诬古人!
醇王自光绪十二年巡阅北洋海防后,对海军一往情深。十四年(1888)二月,醇王患病甚重,以至生命濒危,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前往王府探视。父子相见,“行拉手礼”,谈话之后,醇王解下带在身上的一块如意交与光绪帝(该如意乃十二年其巡阅北洋海防之后慈禧所赐),深情嘱咐说:“无忘海军”(39)。仅此一事足见醇王对北洋海军的高度重视和深厚情感,怎能想象他会自毁海军?
或问,上述史料中的“当谅其苦衷”一语又当作何解释?答曰,是因为大兴土木以修园林宫殿之事,向来不得人心,而慈禧太后既已开修三海,复欲再修清漪园,同治间众臣群起阻其母子修复圆明园之事,人们记忆犹新,醇王担心此番或仍有效法者,事先请求谅解其主持工程的难处,不要像上次同治帝出面倡修时那样再加阻止,此即“当谅其苦衷”之谓。
总而言之,奕譞所谓“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不过是说慈禧太后要修复清漪园,作为京城郊外的夏日避暑场所,如同康乾诸帝去塞北的先例一样,请诸位同仁予以谅解。仅此而已,与北洋海军毫无关系。试思,奕譞作为光绪帝本生父,且为实际主持清廷大政方针的最高当权者之一,即使从维护爱新觉罗家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也断不会自毁海军,而且也不会允许其他任何人用任何方式这样做的。
那么,有关奕譞挪用海军经费以助慈禧修园之说究竟缘何而来,北洋海军建设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否因此而然?
慈禧太后对山水园林的喜好,如同康熙、乾隆诸帝一样,确是追求个人享乐的本性使然。但她知道自己所处时代非康乾盛世可比,也知道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大兴土木为帝王劳民伤财之劣行,凡动用国库之款以供一人游玩享乐的行为,总要受到舆论和后世的指责,至少要受到言官谏阻的。同治十三年(1874)其母子欲修复圆明园而引起包括恭王、醇王为首的王大臣群起反对,以至激起风波之事,对她也是一深刻教训,因此自光绪元年再次垂帘以来,有十年时间未重提修园之事。但中法战争结束后,国内外局势空前平静,出现道光末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加之光绪帝渐至成人,归政在即,紫禁城内又非情愿久居之地,遂重萌开修园囿离宫之念,于是首先下令修葺紫禁城旁边的三海,意犹未足,又要修复京城西北郊外的清漪园。
既要修园,又不想受舆论指责,在这种矛盾心理主使下,慈禧在修园经费问题上想出了一个所谓“不动司农正款”,即不准动用部库存款及其他正式收入,而只许使用“闲杂各款”来修园的主意。然而,内务府等处每岁收入有限,何来闲杂款项可供使用?这一想法实属强人所难,但主持工程者又不得不遵旨照办,于是生出种种麻烦,这些麻烦最后都落在醇王一人头上,因为他作为朝廷内外的主政者,一切均须负责操持之故。
光绪年间户部大库和各省的存银数量,虽然不及雍正、乾隆时那般充裕,但由于海关洋税和厘金两项新增收入,加上传统地丁赋税及杂课之类,在甲午以前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存储。据在光绪十年以后长期任职吏部司员的何刚德说:“户部之库,余在京时奉派随同查过四次,出入互有盈绌,盈时不过千一百万以外,缩时亦不过九百万以内。”(40) 由此可知,奕譞主政时期仅只户部大库的常年存银就在一千万两左右,这在晚清是很大一笔数目。这笔存银尽管不能轻易动用,但当国家有事之时,可由廷旨指令拨付,比如光绪十四年郑州黄河决口工程及赈灾用款,十五年光绪帝大婚典礼用款,同年决定的每年二百万两兴办铁路经费(其中一百二十万直接出自库银,另八十万由各省分摊)等,都是动用的部库存银,亦即所谓“司农正款”。倘若慈禧太后敢于以国家工程的名义修其园林,堂堂正正地指令户部拨用库银,虽一时可能有御史等上疏谏阻,却直接痛快,可为醇王省去许多烦恼。无如慈禧不作此想,而一心要个好名声,害得醇王只好百般设法,东挪西借,又不便明说修园,陷于一种尴尬境地,正如他在为三海工程筹措经费时对李鸿章所说:“既不敢琐渎天听,又无法商诸同事,惟与立山(按:总管内务府大臣)蹙额相对,是可愁亦可笑也。”(41)
海军衙门既为奕譞直接主管,为了应急,正式放款之外如有剩余,或难免有所挪用,但其数额不会很大,更不会因此影响北洋海军建设。因为当时海署所管经费,收支皆有定数,几无余款可言,且自光绪十一年海署成立后,北洋海军应得放款均如数供给,保证需要,从无短缺。北洋海军经费包括修筑炮台、船坞等所需海防经费和“三铁舰”、“四快船”的薪粮煤油等费,前者由海署指令各省关直接解送北洋,后者由北洋派员来京领取,两项合计,其数为每年一百二三十万两(42)。海署所管经费主要来源于光绪元年所定南北洋海防经费,海署成立前这项海防经费名义上岁额四百万两,“实收不及原额十分之二”几乎有名无实(43);海署成立后以中央政府权威的催收力度增强,但“岁入不过二百九十余万两”,而岁出放款则有北洋海军一百二、三十万两和东北练饷一百万两,另有南洋水师五、六十万两,三项合计已超出岁入之上,颇有“入不敷出”之感(44),不存在大量闲款被挪用于园工的可能。
奕譞在罗掘俱穷仍难以满足园工需要的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李鸿章,请后者出面,要求张之洞、曾国荃等各省督抚筹集一笔款项作为颐和园工程专款(45)。由于张之洞等踊跃认筹,竟筹集到二百六十万两一笔巨款,出于照顾慈禧太后畏忌舆论的考虑,以海军衙门名义存天津洋行生息,名曰“海军巨款”,以息银按年解京,供园工应用,修园才算是在理论上有了固定的经费来源(46)。然而,由于这笔筹款用的是海署名义,且涉及各省督抚,消息传出,所谓以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之说便不胫而走,愈传愈广,愈传愈离奇,后来竟有挪用数千万两,甚而至于上亿两的说法,实在不可思议。
要之,海军经费作为“正款”之一,其收支数额基本固定,是不能挪用的;换言之,海署的闲款极其有限,没有多少可供挪用的余地。各督抚筹集的“海军巨款”,实际就是修园专款,只不过为迎合慈禧害怕舆论指责的心理而用了海军的名义而已。然而却事与愿违,弄巧成拙,竟造成更多的流言及身后骂名,这应是慈禧和醇王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北洋海军成军后之所以停止发展,其原因根本不在经费问题上,而在战前国防战略的失误。当日本军国主义以中国北洋舰队为假想敌,千方百计逐年添置新舰之际,清朝当局却视若无睹,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对策,及至当对方把战争强加在头上的时候,才恍然醒悟,试图亡羊补牢,却为时已迟。换言之,能否添购新舰,取决于朝廷在思想上对外来威胁有无正确认识,是否存在危机感和紧迫感,而与海军常年经费无关,因为后者主要是一种养船费,而非购舰费。不管这一经费是否被挪用过,都与购舰问题无涉。所以,那种从修园与海军经费关系上去探讨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观点,实际上是陷入一种认识误区之中,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我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与借鉴。(47)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修园之说,最初是由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为丑化政敌而使用的一种宣传手法,不具客观真实性,吴相湘、王道成诸先生早已考证其说不确(48),今后实不该继续沿用这种说法,否则将误导我们对甲午战败真实原因的认识,也使醇亲王奕譞这位在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收稿日期]2005—11—5
注释:
①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1,上海古籍书店影印,第1页。
② 关于醇王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决策活动及战争结局的评价问题,拟另作专文,这里不展开讨论。
③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十七日。
④ 《清宫遗闻》卷上,“慈禧之侈纵”。
⑤ 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⑥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16页。
⑦⑨ 费行简(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亲贵·奕譞”。
⑧ 翁同龢:《致祭醇贤亲王读祝文》,载《瓶庐丛稿》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⑩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第10页。
(11) 见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12) 奕譞:《朴庵丛稿·竹窗笔记》,第8页。
(13) 王闓运:《录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14卷。
(14) 《光绪朝东华录》,十年七月戊申,总1772、1774页。
(1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光绪十年三月初四、初五日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
(16)(29)(30)(31)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186页;第231页;第231—232页;第232页。
(17)(18)(19)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4,第5、6页;卷54,第2、3页;卷55,第13页。
(2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应诏筹议海防折》。
(21) 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复郭筠仙星使》。
(22) 《刘壮肃公奏议》卷2,《请筹造铁路折》。
(23) 《清德宗实录》卷126,光绪七年正月己卯。
(24) 见《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2,《复醇亲王论铁路函》。
(25) 《光绪朝东华录》,十三年二月庚辰。
(26) 《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3,《详陈创修铁路本末》。
(27) 同上书,卷3,《海军照章定议并筹建津通铁路》。
(28) 《清德宗实录》卷261,光绪十四年十月乙巳。
(32)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0,第2、3页。
(33) 《清德宗实录》卷269,光绪十五年四月癸未。
(34) 《翁同龢日记》第4册,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条。
(35) 吴相湘:《清季园苑修筑与海军经费》,《近代史事论丛》第1集,1970,台北。
(36)(37) 金志节编:《口北三厅志》卷15,“艺文四”,乾隆刊本;卷14,“艺文三”。
(38) 文萍:《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载《围场文史资料》第六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4年编印。
(39) 《翁同龢日记》,第4册,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条。
(40)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3,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
(41) 《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2,《醇邸来函》。
(42)(44)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海署请添拨洋药税厘折,《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637—638页。
(4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6,《请饬拨海防经费折》。
(45)(46) 《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7页。
(47) 参见拙作《论甲午战前十年间清朝的国防战略失误》,载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48) 见王道成:《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吴相湘:《清季园苑修筑与海军经费》,《近代史事论丛》第1集,1970,台北。
标签:李鸿章论文; 光绪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和硕醇亲王论文; 慈禧论文; 铁路论文; 北洋水师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