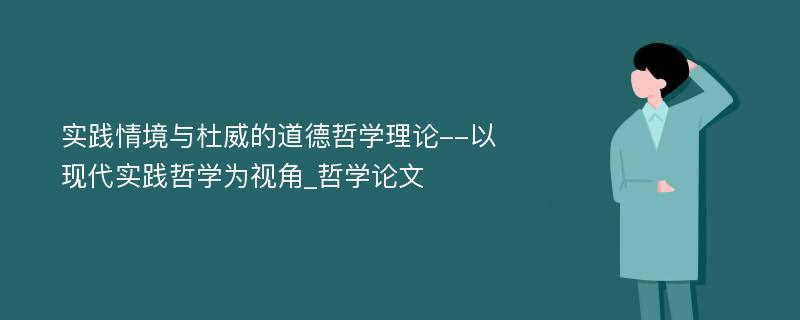
实践境遇与杜威的道德哲学理论——从现代实践哲学的视角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境遇论文,视角论文,道德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的西方实践哲学转向问题是当下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课题。而在这个“转向”中,我们认为有一个人物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视,这就是被誉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之父”的杜威。作为唯一的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在经历了短暂的“没落”之后,又重新被很多当代哲学家所推崇,例如罗蒂、普特南、哈贝马斯等等,而其中人们谈论较多的则是杜威的实践哲学。因为杜威的实践哲学在当代哲学界,尤其是美国哲学界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许多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都从他那里寻找理论资源,以至于普特南把杜威称为自己的“哲学英雄”。国内学界对此关注相对较少,而且多限定在教育理论的视域内。故此,在很大程度上,国内学术界对杜威哲学理论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及其对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影响并没有给予有效的阐释。而我们认为要想真正理解杜威哲学的重要意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当代实践哲学的视域下来理解杜威哲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开创性。这两个特点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体现在他所奉行的那种实践性的逻辑原则,即把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理论生活世界化,把传统理性中的理性逻辑转化为原经验中的实践逻辑,把对“至善”的追求转化为对现实行为之善的探究,并以此来重新审视道德哲学问题。可以说,杜威的道德哲学是一种与康德道德哲学传统不同的另一种道德哲学取向。所以杜威在考察道德问题时,他的着眼点不是传统哲学无法绕过的形而上学根基,或者是康德的绝对理性,而是现实的具有实践性意味的实践情境:一种有问题的、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选择的“道德情境”。因此,杜威的道德哲学理论不仅为批判二元论的传统形而上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以现实生活世界为基础,以探究发展为旨向,重新建立了道德哲学理论的实践性内涵,从而为传统哲学的实践性转向以及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参照。
一、实践境遇:道德行为无法逾越的根基
谈到道德,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以及在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道德观念。然而与此相对,杜威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康德的道德传统进行了批判,并对道德判断的经验世界基础进行了新的追问和阐释。在杜威看来,道德的特点不在于绝对理性的指导,而在于现实世界中具体的实践情境,即由历史沉积下来的人的生存境遇所决定。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总会感到周围世界充满各种矛盾、冲突和危险,总是会运用自己的各种能力来抵御这些妨碍自己美好生活的障碍。“这个经验事物的世界,包括着不安定的、不可预料的、无法控制的和有危险性的东西。”①所以作为一种“被抛”的存在者、一个首先是生物性存在的存在者,人的首要的任务就是维持自己生命的持续性。这就要求人类必须与来自外界的各种危险进行抗争,主动地与周围世界进行作用,从而不断充实自己的生存经验,恢复自身与外界的相互平衡。当然,这种相互作用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还包括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处理,所以这种恢复也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起点,而是在达到平衡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充盈和发展。而这种充盈并不只是动物性的那种生存需要的满足,它同时也是经验的圆满化,与周围世界的和谐化,以及生命的价值化的过程。因此,在这种前提下,人就不能仅仅作为纯粹理性或绝对精神的载体,而必须以一种整体性的眼界来看待,即以生活世界中实践性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进而,人的各种实践行为也必须在生活世界这一大背景下来重新进行审视。这样,实践境遇就作为探究道德问题所无法逾越的前提基础而进入到道德哲学的视域内。在这种视域中,道德哲学就不可能从某种固有、最终的至善概念开始,而必须从探究生命体的实际经验开始,必须关注生存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关系。因此“实践情境”在杜威的道德哲学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背景。
在道德哲学中,杜威坚持着自己的经验性的实践原则,把道德作为一种经验性的以人的全面成长为宗旨的行为探究方式。所以他的实践探究情境实际上也就是人在生活世界中所遇到的需要解决的包含着某种关系和问题的“境遇”,或者就是人的现实实践情境。“‘情境’一词所指示的不是单一的对象或事件,亦不是一组对象或事件。因为对于孤立的对象和事件,我们绝不可能经验,亦不能形成判断,除非联系整个语境。后者就是所谓的‘情境’。”②所以,实践情境首先就是道德行为进行选择的一个必须考虑的大背景。而它的存在作用首先就是防止我们脱离具体的现实问题而以一种超验的不符合人性的观点来进行行为指引或进行不合理的行为选择。它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防止当下的实践行为主体仅仅限于当下的视界和感受来进行行为选择,进而进行一种孤立的不合理的非道德行为。所以杜威的实践情境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之前的思虑背景,一个必须通过它的过滤器,借此找到我们行为价值和意义的方向。正如杜威所言,“具体情境的独一的和道德的终极性质的首要意义,是将道德的重量和负荷转移于智慧上去,这是令人惊奇的事。这并不是毁弃责任,只是勘定它的位置。道德的情境是在公然行动以前需要判断和选择的一个情境。”③在这种情况下,康德意义上的那个先天的绝对道德律令就不再作为一种绝对标准来赋予这种境遇以道德内涵,进而提供一种必然的行为方向,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实践理智对整个生活世界背景下的多种可能性,以及蕴含其中的属人的那种特有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究,进而根据我们的实践智慧在这经验性的、含有多种可能性和多种选择,因而也更为复杂多变的境遇中来寻求并实现这种意义和价值。这就让道德行为不再成为一种单一的孤立的没有责任的个体,而是成为这个环境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与现存的环境相关联,并非与孤立的对象相关联,即便单一事物,亦可在决定如何对整个环境做出反应时发挥重要作用”④。所以,道德主体再不能够把某种行为看作是想当然的,而必须对其进行各方面的实际探究,从而选择一种最有意义的能够促进人的完满成长的行为。
二、道德情境中的变项因素
既然实践境遇是人的实践行为所无法逾越的根基,那么实践行为主体在当下所遇到的各种不确定性就成为其进行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道德实践问题,杜威首先从人的生活世界性的角度出发,把善、恶问题具体化。他认为,“实际上我们是在具体的条件下来正视善的,而这些条件是与现有的需求相关联的,而且获得的每一种具体的善都会毫无意识地融入到一种与它的新的需求和重新建构的成就不相协调的新环境中去”⑤。所以当我们谈论道德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像传统的道德哲学家一样只是孤立地、简单地讨论善和恶的问题,而必须把与道德主体相关的各种现实的独立变项考虑在内。这样,人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进行判断并做出行动的时候,就具有了一种现实的具有实效性的特征。所以人们进行实践行为时,主要面对的是生活世界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动荡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可进行绝对预测的后果。由此杜威认为,现实的实践艺术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及其结果并不都具有一种绝对的必然性。⑥这就决定了行为选择的偶然性和矛盾性,更进一步来说就是绝对道德律令在道德行为中的失效性。“从这种观点来看,不确定性和冲突是道德所固有的;任何被正当地称为道德的情境的特征是:人们不知道终局和善果,不知道正确的和公正的做法,不知道美德行为的方向,人们必须去寻找它们。道德情境的本质是一种内部的、内在的冲突,判断和选择的必要性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必须处理一些没有公分母的力量。”⑦因此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人不再是纯粹理性的附属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限”存在者。这里的“有限”不仅仅是指时间上的“终有一死”,还指生活世界中人的多重规定性。情感、冲动、愿望、爱好等等都会作为建构“完整的人”的一方面因素而出现。因此一个健全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把这些因素从自己的存在状态中剔除掉的,而且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人们才会面临道德情境的各种问题,而道德评判也才有价值和意义。我们知道,在一个完全由理性支配的世界里,或者一个完全由本能支配的世界里,道德问题都不会出现。因为,在一个纯粹的理性世界中,所有的行为都在必然性的掌控之下,不会有任何僭越和逆反的可能性,这个时候的道德充其量是一种装饰品而已。相反,在动物世界里我们是无法谈论道德的,因为它们不会给你任何这方面的希望。而人们所生存的生活世界恰恰处于二者之间。我们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判断的智慧和思维能力,但是我们又无法把我们的冲动、偏好和欲望完全排除掉。正是在这种冲突和争执中,在面对着无法预知的后果而又无法逃避必须选择时,道德才会作为一个“显性”的存在跳跃出来进而得到发展。所以杜威认为,在道德问题中,冲动、爱好和愿望是我们在道德情境中必须考虑的一个独立变项。
而人除了自己的非理性部分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外,还有来自外在的独立变项:“对别人的行为提出要求这种做法就其来源和自然表现而言,对于关于理性的、目的论的目的和善这个总的原则来说是一个独立的变项。”⑧作为一种群居性的或者说社会性的存在者来说,我们总是会相互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人为了自己的某种要求而采取行动。但是这种要求并不一定得到认可,除非这种要求和被要求的人的某种目的或计划达成了一致。所以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这种关系最终要形成一种互惠的要求体系,并被普遍接受下来。但是当某个人提出某种要求时,其实是在实行自己的一种未被认可的权利,用杜威的话来说就是提出要求这一事实还没有赋予要求以权威,而这种权威是需要通过社会在情感上和理智上表示赞同来产生的。而这就涉及到了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个人认为有利的选择可能会被社会认为是有害的,而社会认为是有益的要求可能会损害到个人的利益,而二者的相互认同则是通过逐渐的习惯而达到的。所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个体所提出的要求及其由此引发的行为与普遍的善的目的并不一定统一。因此,道德要求的起源和操作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后果就成为道德情境中无法预测的又一个变项。
而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现世的道德问题,则还要涉及到“个人对别人的行为进行赞扬和谴责、认可和不认可、鼓励和责备、奖赏和惩罚”的问题。这也就是杜威所说的道德中的第三个独立变项。这种因素以个人评价为基础,包含着个人对他人行为出现之后或预期别人要做出的行为的道德判断。“被普遍认可的行为和意向构成原初的美德;被普遍谴责的行为和意向构成原初的邪恶。”⑨所以,这种本身就带有社会性的行为评判意向影响着他人的行为标准和方向。在杜威看来它们是人性在面对别人的行为时的一种自发的表现,只是对美德和邪恶的一种折射性的反应。但是,它们却反映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共识,所以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们必须作为要仔细思考的因素而予以重视。由此可知,现世的道德情境是充满着各种真实地而且尖锐的矛盾冲突的,所以在实践行为选择过程中,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相互对立的要素得到和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说:“道德的问题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使某些来自不同来源的要素相适应。”⑩这里,我们如果和康德所提出的道德存在的形而上学基础——绝对的道德律令——相对照的话,杜威的观点就更加明显。对于道德问题,康德强调的是内在的决定性,因为“理性把作为普遍立法者的意志的每一准则都与每一个别的意志联系起来,而且也与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联系起来,而且这并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实践动因或者未来的利益,而是出自一个理性存在者的尊严的理念”(11)。所以道德选择行为的进行在于内在的先验规定,而不依赖于情感、冲动和偏好的影响。进而康德为道德设定了一个普遍、统一的基础性前提——纯粹理性。但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道德问题时,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或者我们被给予的那个指引却是偶然的,尽管有传统文化在提供参照和范例,但是生活世界的整合性和偶发性却是无法控制的。换个角度来说,当道德问题出现时,道德主体或者说行为后果和责任的承担者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超验的理性,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人的“美好生活”或“完满成长”,而不是那个抽象的绝对的理性原则,更不是“这是不是善本身?”的超验性思考。当我们说到某个普遍法则的时候,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实施这一原则的人和与此相关的“他者”的生活前景及其和谐幸福的美满程度,而不是这个原则本身的实施满意程度。也就是说,这个原则是为人而存在的,而不是人为这个原则而生存的。某个原则可以使某种目的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目的就是这种原则。如果人们对这样一种关系理不清楚的话,那些集权的、恐怖的法西斯行为就会以一种合理的形式出现。
三、语言、文化传统与实践选择
然而人的实践活动除了具有当下时代性的特征之外,还具有一种历史性的维度,亦即实践主体做出行为选择时实践情境所蕴含的隐性的话语背景和思维背景。
语言在生活世界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借用卡西尔的说法,语言就是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和桥梁。同样杜威也极为重视对语言的研究和探讨,而且他更注重语言和现实情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杜威认为,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现实情境、语言和意义都与我们的实践行为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关联。用他的话说,“我们之所以能把握住我们自己语言中的话语的意义,不是因为不需要对语境有所意识,而是因为语境如此不可避免地就在这里。各种话语习惯,包括句法和词汇以及解释方式在内,都是在话语的那些有关的、规定性的情景中形成的”(12)。因此当我们在生活世界中遭遇到一个道德事件时,我们的思维必须从物的世界中跳出来,进入到可思维的语言世界中去;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对事件和语言符号进行了一次无意识的关联和转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思考到事物,而不是通过事物来思考”,“思想对事物的关注在于事物把心灵引至事物自己之外;事物是一些运载手段,而不是终点站”。(13)但是它们之间又是不可分离的,并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在实践境遇中,我们看似简单的善恶行为的选择实际上隐含着复杂的“物—语”转换,即由现实的存在物或事件转化为思维意识中的抽象的语言符号,并进而把我们所要确定的价值和意义以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主体与选择行为之间便产生了一种间距,而这种间距一方面使道德主体的行为受到理智的指引,另一方面也使将要发生的行为选择具有历史性,关涉到主体的传统文化背景、长期的思维习惯以及由此形成的话语模式。
因此当人们面对着那些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表述为善的目的,以及都有某种理由使他必须承担的责任的时候,超验的理性必然性就失去了人们所给予它的那种权威。而这个由生活世界中各种力量所汇集起来的道德困境,就只能以道德主体的实践境遇以及道德命题形成的历史语境为基础,从影响具体的善的形成的各种关系和条件的探究中寻找出路。由此,“实践理智”(practical intelligence)便成为道德行为选择的一种依靠。
这里的“实践理智”是杜威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极为关键的术语。谈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亚里士多德的“明智”概念。尽管杜威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他的“实践理智”与“明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从这两个词的含义上仍然能够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对杜威哲学的影响。“明智”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是指“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14)。其重要的特点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拥有一切有用的经验”(15)。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明智的人的特点上就是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而这里的“善和有益”“是指对于一种好的生活总体上有益”。(16)从这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通过充分确定“明智”对于善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确立了善的实践性特质。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善与经验、技艺、社会环境或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便成为道德哲学所关注的课题。这就打破了传统习俗对人们的生活进程所造成的束缚。但是,对于这一观念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贯彻始终,而是在此之上又设立了“至善”,并且在更高的层次上用“最终的像那些不可改变的习俗一样的规则”的“理性”替代了明智来指导人们的生活,“进而道德被放置在了近2500年都不敢离开的轨道上:寻求终极的善,以及唯一的道德力量”(17)。在这个问题上,杜威虽然深受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影响,但是就“实践理智”概念而言,他无疑要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
之所以如此,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杜威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同时又发展性地融入了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即认为哲学必须为现实的生活世界服务;尤其是对詹姆士关于真正的伦理关系只能存在于纯粹的人类世界的观点的合理继承。在此基础上,杜威认为,在道德实践中人们需要扎根于经验世界的“实践理智”而不是超验的理性。因为“实践理智”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对当下的各种各样的善的辨别,和对能够使它们实现的各式各样的直接方法的考察”(18)。它具有反思、探究、批判、试验的特质。因此它也是一种以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基础的沉思性的思维:“对知识的任何信念或者假定的形式以及进一步所要得出的结论从支撑它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持续的和细致的思考。”(19)进而,杜威继续贯彻了实用主义的传统,认为“实际上,理智是通过行为而达到对未来经验的确证的工具”(20)。因而它总是“保持着怀疑和系统而具伸展性的探究”(21)。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实践理智指引下的伦理学就不再是那种通达终极至善的途径,而成为“帮助人们生活更富足、帮助人们对生活更敏感、进而在情感上使生活更加充实的艺术”(22)。
此外,也正是由于实践理智的指引,传统文化与习俗作为善形成进程中的重要因素而从过去来到当下,影响着实践行为主体的选择。因为“每个文化群体都具有一套意义,深深地镶嵌在它的习惯、职业、传统以及解释物质环境和群体生活的方式中,以至于形成语言系统的基本范畴,凭借此解释其细节……它们是具体信念和判断的规则和‘规范’”(23)。所以杜威认为,思维的这种背景既是空间性的又是时间性的。它的空间性,意味着它可以被事件中的主体所注视、观察,从而看出它与当下情境的差异之处和相似之处。而它的时间性则意味着思想的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由过去到现在的超越性。“传统是一种环绕在思想周围的空气,思想必须呼吸它;任何人除非吸入其中某些空气,就不可能有任何观念。”(24)所以思想的文化传统背景就像一块漫无边际的画布,覆盖了思维过程出现于其中的整个环境。我们的任何一种思维都会把自己反映到传统背景之上,而传统也始终与解释、观察、评价并明确地加以思考的事物相关。“选择并不存在于一种外在于习俗的道德权威和内在于其中的道德权威之间。而是存在于采用的或多或少的理智和具有重要意义的习俗之间。”(25)从抽象思维角度来说,当我们身处道德情境的时候,对我们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中,我们的行为和思维的载体——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较为重要的,而作为一种隐性因素的文化生活背景和语言习惯及语言结构又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习惯。所以当我们对道德问题进行哲学性探究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问题涉及到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时候,现实的文化、语言和习俗传统又作为一项重要的选择结构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选择,进而必须予以思考。如此一来,与此相对的传统哲学里的具有霸权性的绝对理性就显得有点单薄而独断了。
四、当代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杜威道德哲学
杜威作为当代极为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其道德理论在现代哲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现代性视域下的很多实践问题都不会绕过他。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希拉里·普特南,还是理查德·罗蒂,甚或是哈贝马斯,都会从中获取自己的理论资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杜威的哲学看作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转向的一个典型,进而我们认为其道德哲学理论也只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更加凸显出应有的合理性价值。
在康德式的实践哲学传统中,我们可以发现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超验理性为核心线索来统一理念世界和世俗世界,并希望以此为人的实践行为寻找一个永恒的指引标准。然而问题在于,人的存在并不完全是超验性的,绝对的理性并不能完全代表人的存在本身。换个角度说,人在实践境遇中并不是完美的存在,而是一个不完满的具有各种实践“偏向”的“活的生物”。因此,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为其设定的各种完美的构架就成为一种无效的装饰品。
与此相对,杜威的实践道德理论则是以经验世界为基础,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于道德实践问题的关注,即对我们所遭遇到的、具体的、处于情境之中的道德问题进行探究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他的着眼点不是终极之善本身,而是现实的经验世界中实践行为的可行性问题,以及在现实的境遇中人之选择的合理性问题。而这些又都是以关于实践境遇的重新理解和阐释为基础。从以上各部分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实践境遇问题在杜威的道德实践理论中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它直接决定了杜威的道德哲学的发展基调。而他的这种问题视角也为当代实践哲学的发展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第一个是,杜威为哲学思维从传统的理性逻辑向生活世界化的实践逻辑的转变提供了一种参照。传统形而上学所遵循的理论逻辑表现的是以对传统理性的信赖为基础的由事实到事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僵化的推理方式,例如传统的三段论、因果论。传统形而上学大都推崇这种自足性的逻辑思维方式。而且这种逻辑思维方式一直主导着传统哲学对于各种属人问题的思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哲学在思考道德实践的时候总是以这个世界的二分为前提预设,即生活世界中的混乱背后肯定蕴藏有一个与之相对的统一的能够通过理性这个绝对的中介而获得的终极原因,只要人们把握这个终极的因素,就可以找到厘清各种现象的钥匙。所以康德实践哲学的目标就是要找到现实背后的那个“绝对的道德律令”。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只要人继续是一个人,情感、欲望、意向和选择就总是有的;所以只要人继续是一个人,就总是要有关于价值的观念、判断和信仰”(26)。人总是会受到各种外在的、偶然的因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实践行为的逻辑规则就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化的。因此传统的以理性自足为根本保障的单向度逻辑思维模式必然失效,以至于最终陷入各种困境无法自拔。
与此相对,生活世界化的实践逻辑是一种多元的、多向度的、发散性思维模式。它更注重理论与实践活动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因而包含有探究性的意义内涵,所以表现为一种由事实到意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以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的。或者说,生活世界化的实践逻辑是以人的实践理智为基础的,因而人的实践行为就不会局限于传统的理论规则,更不会受“绝对知识”的迷惑而故步自封,取而代之的是包含有人文价值维度的实践探究。所以,在这种关系中,人的自由行为的多重价值及其意义就清晰地体现出来。(27)而杜威对于生活世界的重新认可和阐释无疑为现代哲学的这种转化提供了一个理论参照。他对道德情境的实践性阐释也无疑是对这种实践逻辑的一种经典性的运用和注释。这就为我们在现代性的视阈下,推动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个就是杜威在道德情境中对于“整体的人”的认可。杜威道德哲学中的道德主体不再是传统理性主义视野中的理性的载体,也不是功利主义视野下感官享乐的承受者,而是生活世界中具有理智的“活生生的”人。他有情感、冲动和欲望,也有进行思虑的实践智慧;他既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或者就是二者冲突的调和者。在这种意义上,人不是一个天生就被构造完整的理智之人或道德之人;相反,人是一个处于过程中的、不断趋向完满的“被抛者”。现实的偶然性、特殊性以及矛盾和冲突虽然给人的存在和发展设置了障碍,但同时也促进了人的成长和进步。更重要的是,人的自由以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也由此而产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杜威对道德情境的阐释的意义不再仅仅局限于伦理学的发展,而是关涉到人类的整体性发展和完整人的实现问题。这也就和马克思关于“完整的人”的阐释产生了某种共鸣。所以从这些方面看,杜威的实践哲学以及他对道德实践问题的论述,对于当代实践哲学的发展来说,无疑表现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参照和意义。
注释:
①[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6页。
②④(23)[美]苏珊·哈克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445、440页。
③[美]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88页。
⑤(25)John Dewey,Human Nature and Conduct: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Modern Library,1922,p.278,p.81.
⑥(26)[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上海人民出版2004年版第6、301页。
⑦⑧⑨⑩(12)(13)(24)[美]杜威:《杜威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353、354、355、202、203、211页。
(11)李秋零主编:《康德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14)(1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3、173页。
(15)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页。
(17)John Dewey,Ethics,New York: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09,p.6.
(18)John Dewey,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0,p.68.
(19)(21)John Dewey,How We Think,Lexington,Mass:D.C.Heath,1910,p.6,p.13.
(20)John Dewey,Creative Intelligence,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64.
(22)Steven Fesmire,John Dewey and Moral Imagination:Pragmatism in Eth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p.92.
(27)对于这个问题,可参阅丁立群:《哲学·实践与终极关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标签:哲学论文; 杜威论文; 道德哲学论文; 道德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思维障碍论文; 哲学家论文; 康德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