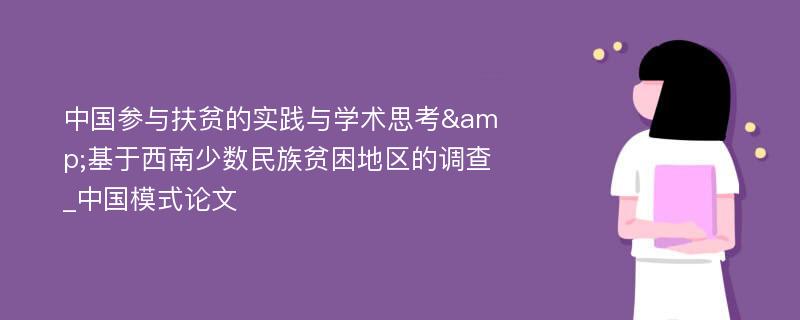
参与式扶贫的中国实践和学术反思——基于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参与式扶贫作为目前承载国际主流化发展理念、模式和制度的扶贫方式,比以技术和经济为中心的传统扶贫模式有了巨大改进,其终极目的是促进贫困人口有效摆脱贫困,特别是缓解久扶不脱贫的局面。
依笔者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贫困研究的经验来看,少数民族的久扶不脱贫问题是一个包含自然、经济、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一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在市场经济中的边缘地位;二是地方性文化与主流发展话语的不相容。基于这些经验,并结合宏观材料,本文尝试探讨参与式扶贫是否能够有效缓解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久扶不脱贫问题。
一、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式
被视为扶贫创新策略的参与式扶贫的关键词是“赋权”,这是一个赋权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过程,以实现项目各利益相关群体(尤其是穷人和弱势群体)能够影响和控制涉及他们的发展介入、发展决策以及相应资源。① 这一反贫困模式是对于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直接经济援助过程中所采取的传统发展模式的创新。传统的发展模式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继承了古典进化论思想,将发展视为进化,也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二是技术进步被视为发展的关键部分和动力;三是市场经济的扩张和理性经济人的培养;四是传统文化被视为发展的障碍和对象。② 这种发展模式在实践当中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文化冲突、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调、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
参与式扶贫就是对这一传统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式发展理念和实践逐渐主流化,被学者们总结为民本主义的参与式,它宣称“地方”是发展介入的核心,发展代理者应由指令性的外来专家向擅长于地方知识的专家和能人转变,同时通过赋权于发展对象参与发展项目的每个阶段来实现“上”、“下”之间权力关系的平衡。③
参与式发展项目与传统发展项目相比,其“赋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1.尝试在项目周期内发动主要利益相关群体参与项目的决策,尤其注重在项目设计准备阶段中主要利益相关的参与。
2.注重能力的培养。作为参与主体的项目目标群体,需要具备一定的参与能力和参与组织才有可能达到在项目周期中表达自己声音的目的,由此参与式发展项目往往在开展传统的物资传递援助外,还关注“人”的问题,尝试通过一些能力培养项目,提高参与主体的组织能力和发展意识。
3.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和穷人等等。参与式发展项目不但注意评价项目的实施对这些弱势人群的负面影响,强调保证弱势群体的平等受益,还常常在项目中单独设计专门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项目援助。
参与式实现“赋权”的主要途径是围绕参与式乡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PRA)工具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PRA的工具包主要由一系列可视化的图表、排序工具,以及开放式的座谈和访谈组成。这是一套基于发展项目的,极具灵活性、适应性的方法,其宗旨就是创造机会,激发村民说话。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掌握社区概况和所需特定领域的资料。PRA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通过PRA激发出一系列的权力“倒置”(reversal),④ 使发展专家成为当地人的“学生”,当地人被鼓励坚持不同的观点,对他们自己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调动乡村社区的力量为实现他们所设想的未来而采取行动。
“参与”的引入使发展援助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改变,国际学术界和发展实践者就“参与”能否实现有效的“赋权”问题一直进行着反思和争论。
有的学者尝试通过改进以PRA为核心的工具来提高赋权效果。如一些学者认为,需要在实践中适当调整“参与”的程度和目标。以实现绝对赋权和权力倒置为目标的参与式发展,只能作为一种范式,也即一种包括了参与想法、价值观、方法的模式。⑤ 有学者提醒注意参与对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避免社区内部因在年龄、性别、阶级、种姓、族群、宗教和性别基础上的权力关系而导致的利益和需求偏见。⑥ 有的学者则指出需要回顾参与的历史及其能够为民本主义参与式提供的借鉴,在整个发展理论中审视和定位“参与”所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等等。⑦
有的学者却对“参与”则不以为然,这批学者是发展话语的解构者,他们尖锐地指出发展话语中西方霸权的局面从来没有因为“参与”的引入而发生改变,“参与”所宣称的“赋权”实际上是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渗透模式。“参与”从一开始就是与“第三世界发展”或所谓“援助工业”的联系在一起的,它并没有改变自上而下的“援助工业”主流。相反的是人类学家的传统方法被援助工业以简化了的方式或者说歪曲的方式(PRA)使用,甚至成为“自上而下”计划谋取合法性的帮手。这样的“参与”是以伪装起来的现代化线性发展观和工具理性价值及相应的干预措施为内容,其结果说到底仍然是对被援助对象的生活世界采取无视态度的。⑧
从上述批评或改进“参与”的争论来看,不论是赞是弹,“权力”问题都是理解“参与”争论的关键线索。参与式发展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发展过程中发展者与发展对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暴露和修正,尤其是“赋权”被明确界定为参与的核心内容以后,权力问题成为理解参与式发展的关键线索,发生权力关系的双方主要是西方援助者和受援对象,争论的焦点是本土文化与发展话语之间的权力倒置是否能实现?如果可以,那可行的“参与”究竟是什么?虽然参与式发展鼓励无标准和灵活化的参与实践,但是指导实践的参与理念、根据具体情况设计的参与实践中均充分体现和延续了西方政治学基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有关权力和民主的理解。
二、久扶不脱贫与参与式发展的实践
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在实践中,面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能否有效缓解我国这些扶持多年、仍需长期扶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在缓解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中的边缘地位方面,不论是我国政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导的指令性政策性扶贫,还是国内外主流化的参与式社区扶贫,无一例外的是一个将贫困人口纳入市场化的过程——通过为贫困人口建构参与市场化的基础,市场化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农副产品,以实现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在西方参与发展中,清晰可见解释权力的“power to”线索。在这一模式中,权力被视为如个人能力和财产一样,具有生产能力,经过努力经营,即可实现增长;而且权力还可以出让,可以通过有权者出让权力,改变无权者的弱势地位。这样,赋权或者参与首先应着手理解不同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培养无权者经营、争取权力的能力,迫使有权者放弃、转让权力的实现。
从这一角度出发,参与发展模式往往基于项目援助,在社区层面上推行这种赋权,比如发展项目往往在了解社区权力结构和社区决策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将项目资源直接落实到穷人、扩大穷人参与决策和管理项目的代表人数和机会、培养穷人的自我组织能力等手段,实现改变穷人在社区中无权无势的边缘地位。针对农民在市场中的不适应和弱势地位,参与式项目着力培养贫困人口的市场观念和应对市场的能力。如许多参与式项目采取组织农民,帮助农民建立合作组织,以提高农户应对市场风险能力的扶贫开发思路。比如,在我国,与一系列推动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短、平、快的种养扶贫项目的推进一致,出现了五种农民合作协会:1.自办型。即农民自己组织兴办的合作经济组织。2.改造型。即由原来的企业改造而来。具体又有四种情况:一是将乡村企业改造成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将供销社与农民重新联合,组建成合作经济组织;三是将个体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四是由几个经营主体联合并改造成合作经济组织。3.领办型。即由农技、畜牧等涉农部门领办的合作经济组织。4.依托型。即以农产品加工、运销等龙头企业为依托,兴办合作经济组织,实现龙头企业、农户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有机结合。5.虚假型。出于各种目的由各种机构组织虚构的协会。⑨
这种围绕培养赋权能力的项目思路忽略了权力的另外一面。Bachrach和Baratz认为权力不仅仅在决策过程的参与者中实践,还在存在于决定参与人群资格和参与主题方面。假如参与主题被禁止提出,那么行动者也就相应被禁止有所行动。权力最重要的一面不是在斗争中获胜,而是在决定哪些问题可以进入斗争的领域。⑩ 对于处于发展大背景中的贫困人口来说,他们根本无法选择是否服从发展的逻辑来延续今后的生活,是否以参与市场化提高收入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权力除了通过强制,迫使从属者去从事他所不愿意之事外,同时它还通过影响、改变、决定从属者的价值观念来施加权力,让从属者主动地、不知不觉地接受强权,这种通过改变思想来实施的权力往往是不可见和最为重要的。(11) 因此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他们能否通过某个种养项目来致富,而是当市场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后,他们的日常生活该如何延续。
市场化是一个政治经济化复杂的过程,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不断制造着“中心”与“边缘”的差异。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往往是贫困人口的生存成本和期望提高,而现有扶贫活动所设计的项目利润主要汇集方向却并不是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的位置仍然是边缘化的,甚至会更加边缘化。正是这一结构性原因的存在,使得反贫困事业存在着潜在的危机。
因此,今天的参与发展在实践上,不仅是让穷人获得在社区层面获得参与决策机会,更要意识到权力运作的复杂过程,对涉及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内部,东方和西方社会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有所考虑,这个层面对参与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少数民族地方性文化与主流发展话语不相容方面,参与式浪潮的核心是正是尝试通过谋求被发展者的地方性知识与发展者所属知识地位的平等,来实现发展过程中西方/东方、发展/被发展者的权力倒置。不过在参与式的实践中,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和运用存在着斯科特所说的“简单化”(12) 特征——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只表达了发展者所感兴趣的片段。
在援助实践的过程中,缺乏一种整体性理解发展对象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发展观,就如何将社会文化因素切实引入扶贫开发实践的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主要表现在:
1.以经济、技术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影响深远。技术和物资的援助仍是发展援助的核心,扶贫项目仍然以治贫、治愚、治病为主要内容,缺少从社会文化因素方面着手的有效反贫困措施。
2.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带有明显功利性和工具性,对影响贫困和脱贫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外部发展力量对贫困的影响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且考察手段也十分有限。项目之前开展社会经济文化调查的时间很短,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帮助项目援助能够顺利的推行。这就导致人们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研究,而仅仅关注了与项目有关的文化事项,如经常被提及的地方性技术知识、生物学知识、医疗知识等,但忽视了对当地人价值观层面的地方性文化逻辑的探询。
3.以当地人是否赞同项目作为项目是否适合于地方性知识的标准。这个标准在参与式发展项目中得到特别推崇,但这并不一定能保证项目适合于地方性知识体系的逻辑。但很多时候,生活在自己文化中的人们,往往很难总结出自己文化的逻辑,并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并不赞同外来的发展援助。
4.缺乏在发展项目中自始至终关注地方性知识的机制。即便是在参与式发展援助中,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关注也主要是在项目的设计阶段。一旦项目设计完成了,这套项目方案就被认为是符合当地地方性知识体系而被加以实施。如果项目失败了,人们容易以当地基础太差、穷人素质低等原因解释,而地方性知识体系对于项目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则很少有人会关注到。
此外,提倡关注“本土文化”的参与式扶贫项目还常常会表现出对少数民族本土文化的过度假设。如笔者在凉山地区的调查就发现,一些外资参与式扶贫项目为发掘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对保护生态、提高收入的作用,在彝族村庄规划建立了各类旨在复兴或运用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小组如毕摩文化小组、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小组、资源保护与利用小组、民间纠纷调解小组等等。实际上,这些本土知识在彝族村庄中久已存在,并且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必不可少。村民们对这些文化十分熟悉,而且有固定的人群从事相关知识的实践和传承。项目却将这些本来存在的东西规划为项目的内容和目标,那么这样的项目不管落不落实,其效果也一样存在。
可见,当前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式模式,仅从话语的角度出发,注重形式上的权力倒置,却没有从扶贫实践的角度出发,关注扶贫开发的成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久扶不脱贫的两大主要因素,而这是导致参与式扶贫实践过程中理想和现实差距的根本原因。正是参与式这种在扶贫效率上的有限性,使参与式正面临着形式化的批评。(13)
三、思考和启示
对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式扶贫模式的倡导,在其学术脉络上,是人类学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参与”展开的发展研究,实际上是人类学者化解“发展”被话语解构尴尬局面的一种策略。
通过“参与式”实践,关注和研究那些被视为不可见的、沉默的、边缘的发展对象及其文化来展现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问题,以批判或是改进西方的发展主义,并保卫多样性的本土文化。基于拉美、非洲、东南亚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开展西方发展援助的研究经验,学者们所号称的复杂的发展权力网络,实际上仅仅是以“本土”和“西方”二者为主角建构和展现的。(14) 笔者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经验中体会到,围绕“参与”开展的发展研究,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需要完善:
1.关注多种利益相关群体对发展话语的实践。仅讨论“本土”和“西方”之间的权力倒置,并不足以解释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在贫困地区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在各自的语境中,实践着多面性的发展话语,共同建构了贫困人口所处的市场环境及其本土文化。比如在中国的语境中,中国政府的影响不可忽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扶贫政策、制度建设等主导了少数民族的发展进程。由此,研究需要关注多面性的发展话语,分析不同的发展话语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它们各自在多样化的发展话语中居于何种地位,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如何。
2.为展现多种利益相关群体的发展话语实践,需要对“本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人类学者已经意识到,今天纯粹的“本土文化”已经不存在了,所谓的“本土文化”实际上是与多种来源的知识体系文化杂合的产物。(15)“本土文化”由此成为多种发展话语相互作用的关键领域。仅以提升“本土”的地位,实现权力倒置为目标的“参与式”对本土文化的复杂性显然认识不够。比如各少数民族对发展的历史记忆各不相同,这常常是导致发展对象以不同策略应对“发展话语”的重要因素,历史的视野需要被引入人类学的发展研究中。还有,关于“参与式”如何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参与式学者们试图仅对“参与”进行框架性的界定来保证它的开放性,这样做实际上是回避了“参与”与“本土文化”互适性的问题,导致了“参与”处理地方性文化的手段极为有限,人们只能在理念上达成参与的共识,而无法提出衡量参与和赋权的统一标准、落实参与和赋权的严格步骤和方法、明确参与和赋权应该落实到何种程度、如何界定并处理各个项目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规定每个利益相关群体在参与和赋权中的明确地位和职责等等问题。理论的反思需要对实践有所启示,基于中国的实际,笔者认为今后参与式扶贫的研究和实践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1.从强调“权力倒置”到强调“内源发展”。实际上,参与式的目的就是实现内源发展,但为标榜与其他发展模式的区别,有关参与式的研究和实践过于强调“权力的倒置”,以至于在实践中,人们对“参与”过程中形式上“赋权”的关注大大高过了对“以人为本”的内源发展的追求。笔者看来,对内源发展的强调才是参与式发展与其他发展范式的根本区别。强调内源发展,需要援助者在意识和援助制度上打破“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也需要从受援对象的层面着手帮助他们解除禁锢自己发展的“贫困文化”。因此,今后有关参与式扶贫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从提升发展对象自我能力、激发发展对象主动性、创造性等方面出发,展开更深层次的探讨,拓展更多的技术和途径。
2.用“参与”的方法开展援助者也即扶贫体系内部的反思。多年的扶贫开发经历在为下一步工作积累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使得整个扶贫开发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路径依赖”的危险,我们很必要对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扶贫开发日常术语进行“变熟为生”反思。如对于“市场化”,我们常常是哪个产品市场前景好就规划种养哪个产品,哪里好卖就想卖到哪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贫困人口弱势的市场地位及他们地方性知识的惯性,对市场化的范围、内容、途径等方面做出因地制宜的安排。此外,还有对于扶贫开发目标的定位上,除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水平之外,对于贫困和弱势人口来说,更重要的也许不是加入市场竞争提高收入,而是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实现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而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协商咨询手段,正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运用于扶贫体系内部不同层级展开反思。
3.参与式扶贫需要在发展关注地方性知识的机制方面有所进展。在目前参与式扶贫援助中,由于过于强调参与式的“赋权”效果,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往往被形式化为“权力倒置”的证据。PRA虽然有助于援助者了解本土文化,促使援助与文化相适应,但绝不是一套有助于整体了解贫困文化体系的好方法。而且以PRA为核心开展各种“赋权”活动,人们往往会在项目的设计阶段为提高项目效果会考虑文化因素,一旦项目设计完成了,这套项目方案就被作为符合当地文化体系的加以实施。而如果项目失败了,人们则很容易以当地基础太差、穷人素质低等原因解释,放弃深究地方性知识与项目成败深层关系的机会。笔者初步的设想是,这套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机制是建构全方位贫困观的基础,可在参与式扶贫已有的一系列理念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在实践中,需要在参与式培训体系中加入基层项目实施机构(尤其是县级机构)人员的少数民族语言培训,习得语言是保证整体性掌握地方性知识的前提条件。此外,还有完善扶贫体系效益的评价机制、扶贫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价机制、基于社会文化经济特点开展的区域性扶贫规划机制、本土文化与扶贫目标适应程度的评价机制等。
注释:
① World Bank,The World Bank and Participation,Forth Draft,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4.
② Crewe,E.& E.Harrison,Whose Development? An Ethnography of Aid,London & New York:Zed Book,1989,pp.25~48.
③ Samuel Hickey and Giles Mohan,Participation:From Tyranny to Trans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04,p.11.
④ 参见Chambers,Rural Development:Putting the Last First,London:Longman,1983.这些“倒置”包括:空间的倒置,转变技术、财富、权力由中心向边缘、都市向农村扩散的状况;知识偏好的倒置,转变由于中心—边缘、都市—农村、工业—农业之间的层级关系所导致的各领域知识发展的不平衡;转变发展中相关学科越来越专业化、排他化的发展趋势;转变技术必能带来发展的观念,思考发展过程中相关群体的利益得失情况;实践方法上的“倒置”,向农民学习本土知识,采取从下至上的管理方法。
⑤ Robert Chambers,"Paradigm Shifts and the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 Nici Nelson and Susan Wright,eds,Power an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1995,pp.30~42.
⑥ Irene Guijt and Shah Meera Kaul,The Myth of Community:Gender Issues in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London: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1998.
⑦ Samuel Hickey and Giles Mohan,Participation:From Tyranny to Trans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04.
⑧ 朱晓阳:《反贫困·人类学田野快餐·援助工业》,《自立》2002第4期。
⑨ 周大鸣,秦红增:《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8~459页。
⑩ Bachrach,Peter and Morton S.Baratz,Power and Poverty: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11) Lukes,Steven,Power:A Radical View,London:Macmillan,1974.
(12) 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13) 参见以下文献:Raft Carmen,Autonomous Development:An Excursion into Rad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1996; Frances Cleaver,"Paradoxes of Participation:Questioning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1,1999,pp.597~612 ; M.D.A.Rahman,"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Towards Liberation and Co-optation?" In Gary Graig,eds,Community Empowerment:A Reader in 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1995,pp.24~32 ; Francis,Paul,‘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t the World Bank :The Primacy of Process’,in Bill Cooke and Uma Kothari,Eds,Participation :The New Tyranny? 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01,pp.72~87;朱晓阳:《在语言“膨胀”的时代再谈“参与式”的内在困境及“补药”》,《自立》2003第3期。
(14) 杨小柳:《发展研究:人类学的历程》,《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15) Sillitoe,P.2002b,"Globalizing Indigenous Knowledge",In P.Sillitoe,Alan Bicker & J.Pottier (eds.) ,Participating in Developmen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项目组织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文化扶贫论文; 贫困地区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贫困人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