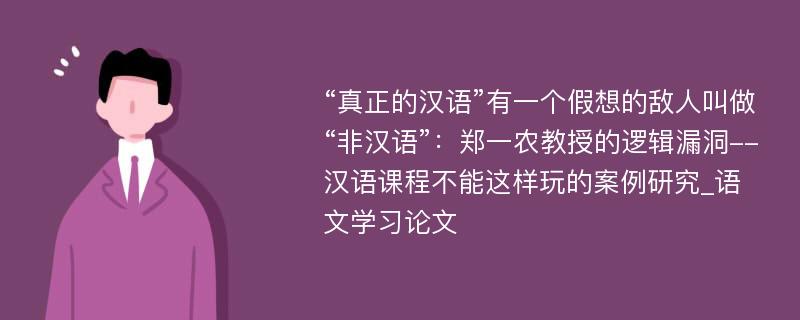
“真语文”有个假想敌叫“非语文”——以郑逸农教授《语文课不可以这样玩》的逻辑漏洞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论文,假想敌论文,有个论文,不可以论文,语文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建设》2014年第4期刊发了浙江师范大学郑逸农教授的《莫为泛语文课推波助澜》,郑教授在文中重提两年前的一个争论——《中国青年报》2012年2月8日曾以“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为题,报道了苏州史金霞老师的“不拘一格教语文”,郑教授忧心于史老师的“非语文”而作一尖锐的批评——《语文课不可以这样玩》,发表于《语文学习》2012年第6期。(编者注:本刊2012年第11期同时转载了这两篇文章)笔者对其中的“主义式”批评方式很有点感触。前段时间听了一节课,更触动了我警惕“主义式行为”的神经。 那是一次市级评优课活动。有位教师执教电影剧本《辛德勒的名单》,整体设计很好,重点的功课是几个精彩的人物对话情景,通过对场景及人物对话和神态描写文字的赏析,来领会“人性复苏”这一主旨,总用时约40分钟。评委们在交流中都觉得这课上得非常好,其第一名的位置几乎已经在评委们心中确定。然而,这位教师的最后5分钟却让她功亏一篑。她以“战争导致人性扭曲,呼唤和平”为由头展开,一下子补充了好几部此类题材的影视或文学经典,出示了一些画面或作品评价,用近5分钟的时间播放,自己不多言,也不要学生互动,一口气看完。从学生观看时屏气凝神的气氛来看,这些补充内容引发了学生内心的强烈震撼和深刻反省。但就是这样一个设计,让这位教师失去了第一名,理由是“这5分钟是非语文”。作为评委之一的笔者虽不同意,但1比4,无法扭转乾坤。“多数们”的理由很有靠山,那就是“真语文”的流行追求与价值观——这位教师被认作是做了画蛇添足或是狗尾续貂的事,走到“非语文”的一面去了。这与郑教授对史金霞老师的评价如出一辙。 两事联在一起,再思考“真语文”对“非语文”的批判,就发现其中的逻辑颇多有待商榷之处。 一、“非语文”是“真语文”假想出来的“不法身份者” “直语文”对“非语文”(也有称“泛语文”)的批判,实质是出于语文课程内容的考量而产生的。语文“性质之争”的背后,就是“内容之争”,却一直争不出结果;现在的争论往往不再就性质纠缠,而是换了名号,比如以“真语文”向“非语文”出击——背后其实还是从“内容”上否定对方的合法性。 人文性张扬在尺度把握上产生的过妄,引起有识者对语文被所谓“非语文”入侵的担忧,于是,“语文味”、“真语文”、“让语文安静”、“让语文回归本位”等主张以升旗的方式展开了对“非语文”、“泛语文”的围剿,其主要出发点是,语文学习是基于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运用,脱离这个本位的教学便是“人文泛滥”,“走出了语文”。从基于“问题”来看,这是有价值的警示,但把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升到“非语文”、“泛语文”层次并加以讨伐,其实是逼出并树立了一个“出身不合法的篡位者”。与很多国家的纯粹的语言学习与运用学科不同,我们的语文很特殊,课程标准对课程内容的界定一直无法完成,只知道它包含了古代、现代甚至是外国的语言文字、文章、经学、文学、文化等多种附着物、寄生物,姑且名为“语文”——甚至不是一个明确的学科。语文课程内容极宽泛,边界模糊,特定教学时空更有不同的变化,如:揣摩一个文本的语言文字是语文学习;了解一部文学作品是语文学习;教师出于某种需要,在学了某篇课文之后,专门用一节课就某问题作了个哲学拓展是语文学习;请莫言做一个讲座,也是语文学习。假想敌“非语文”的树立,一方面会窄化语文课程内容,一方面又会把很多尺度问题、效率高低问题、具体文本的价值取向和特定教学内容的选择问题等统统变成了严格的“身份”问题,还会因“线划”和“站队”错杀了语文学习中的有效方式,这对语文教学来说并非幸事。 有个很直观的现象:“人文性”登场发声时,语文批评的话语方式更多的是“语文是××,语文也是××,语文还是××”(××包括但不仅限于文化、人文、精神、美、生命、生活等);然而近10年,不知不觉中,也许是出于对“人文性”过滥的反思和警惕,从防止语文泛化出发,“语言本位”渐成主流话语,话语方式主要是“语文不是××,语文也不是××,语文更不是××”。这诸多“不是”的目的,是剔除那些泛滥的“非语文本位”的东西,去“伪”求“真”。那么,“语文本位”或者那个“真”是什么呢?现在较一致认同的是“基于言语形式或语言文字理解和运用的学习”,以此定性为“真语文”,非如此则被评为“假语文”、“非语文”、“泛语文”。 从前面的“语文是什么”,到后面的“语文不是什么”,在价值追求上,就防止语文泛化和纠偏来说,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笔者也赞成千万不能把语文课大面积、成规模地上成脱离语言文字体悟与咀嚼的思想内容课、视听课、美术课、哲学课……但适当为之、适可而止是可以的,这里面有个主次关系,而当“真语文”用“语文不是××”去“求真”、“归本”并批判假想的“非语文”时,往往连带着否定了“语文学习中的多感官、多渠道、多外延”,其实是举着语文的内涵去否定语文的外延,用“基本”去否定内容的繁杂性、模糊性。事实上,在实际教学中,根本无法“纯真化”。 二、“可以这样玩”不是“全都这样玩” 首先,我们来看郑教授在《语文课不可以这样玩》一文中所作的关于语文课应该是怎样的表述: 什么样的课才是语文课?集中于语言表达的形式,品味其中的语言之美,培养学生语言的感受力和表达力,提升学生的语言素养;在完成语言学习任务的基础上,再自然地从语言形式中感受作者的情感之美、思想之美,提升学生的精神素养:这样的课才是语文课。 理由很简单,“语文这一门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叶圣陶先生的,后一句是2011年刚修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新加入的。 笔者想问郑教授的是:课堂里可不可以有歌声、有戏曲,出现不是课本中的东西?如果有,就是“非语文”?我想,任何一位语文教师包括郑教授,都不会如此武断吧。那郑教授为何就要疾言厉色地告诉史老师“语文课不可以这样玩”?原来,郑教授在激动之中忽略了《中国青年报》原报道中的标题是“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中的“可以”。什么是“可以”呢?逻辑上是说一种可能性或部分属性,而不是非得如此或全部如此。而郑教授的文章标题是“语文课不可以这样玩”。什么是“不可以”?就是坚决不行或全部不行,它与“可以”并非对等的相反关系。但郑教授又似乎不甘心失了准星,于是就硬把史老师的“可以这样玩”,偷换成了“全部这样玩”。这从郑教授自己的文章里体现得非常清楚。试看郑教授的话语方式: 如:教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才看了一遍课文,就由作者对母亲的愧疚自责引发开去,列数历史上孝敬父母的典型故事,讨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待母亲,如何珍惜母爱,如何做一个孝顺的子女,于是教室里会响起《世上只有妈妈好》之类的歌声;教学鲁迅的《祝福》,初识文本,就由祥林嫂的不幸引发开去,讨论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畅谈今天社会男女平等的幸福,教育学生要珍惜今天的幸福,并讨论如何做一个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女人,教室里可能还会响起《女人花》之类的歌声;教学沈从文的《边城》,还没疏通文本,就从翠翠的朦胧爱情和傩送的出走引发开去,讨论如何看待他们的爱情,再讨论我们今天应该有怎样的爱情观,教室里甚至还会响起《那时我们还不懂爱》之类的搞笑的歌声:“我问你,爱我还是不爱?你问我,留下或是离开?” 上面的情景,与《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开头描述的情景,是不是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郑教授为了达成“史老师的课非语文”的表达目的,在上面这段他的“引伸与设想”中,一直在自设前提“才看了一遍课文”、“初识文本”、“还没疏通文本”。看来,郑教授是知道“可以”与“不可以”的不对等性的,所以他要加上这些前提。于是,成了“欲加之辞”。 以上对于郑教授文章的逻辑分析的核心是,语文课堂上是不是不能有一点与文本的语言形式无关的内容?我想,绝大多数人会认为可以有,虽然它们不是主阵地的构成,但也可以有,甚至是不可少。比如,一位教师教学《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除了让学生把握文章的思路结构和一些语言表达的效用以呈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之外,课的后半段引导学生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些现实的思考和历史的评价,又有哪些听者认为这是政治课、哲学课、社会课,而不是语文课?哪天郑教授请来了莫言给他的学生作一个讲座(我想郑教授肯定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语文学习活动),那郑教授是不是会要求莫言一定要给学生上一堂紧扣语言形式的语文课呢?其实,郑教授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并不反对有些课上可以“玩一玩”,他反对的是“才看了一遍课文”、“初识文本”、“还没疏通文本”就“玩”。问题是,他为了表达自己对“非语文”的厌恶,就把史老师“捉”来作一回“靶子”,明明史老师说的是“可以玩”,郑教授却先作了一个“全部玩”的偷换推定。想问郑教授:你怎么知道,史老师的课是“才看了一遍课文”、“初识文本”、“还没疏通文本”?假想敌,其实是一种逻辑构陷。我想,这是语文批评的一个态度问题。 三、“语文教材文本精读教学”只是整个语文学习的阵地之一 郑教授以及现在很流行并成为正统的“把语文课上成语文课”的观点,我赞同,大多数教师也赞同;史老师的“语文课原来可以这样玩”我也赞同,不少教师也赞同甚至也一样在做着。我这样说,不是和稀泥,也不是矫情地打着个“兼容并包”的旗号说事,实在是因为它们不是同一概念。郑教授说的是语文课而且主要是针对语文教材篇目的精读指导课,而史老师的做法也“活”在语文教学中,是一种语文学习活动,它不是阅读课,即使是就某篇教材文章进行的阅读教学,当她完成阅读任务(郑教授所说的紧扣语言形式的课堂教学)之后,“玩一玩”,它是一种拓展和延伸——郑教授可以从规范的文本阅读课研讨的角度请她打住,以免“失分”,但作为一种日常教学,史老师那样做,会有害?或者会有益?我想,郑教授的答案不会是前者。 语文教学的探讨从关注“怎么教”发展到研究“教什么”是个很大的进步,“教学内容确定性”以及“本色语文”、“真语文”、“语文味”等话题表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实质是相通的,这样的潮流之形成应该是语文正本清源、朝向正路而去的幸事。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话题的探讨、阐发和实践,大多是针对课堂上教材文本的阅读教学,对“教材文本精读教学”以外的事情则表述不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材文本精读教学”是当务之急,是主阵地,或者说过去一直有问题而现在特别急迫地需要指正。这就是“真语文”的出台背景。其追求和价值观,还是用郑教授的话来表达: 教师在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学习语言表达的内容,知道它表达了什么含义、表现了什么情感;但更要由此深入下去,学习语言表达的形式,探究该含义和情感是用怎样的形式和技巧表达出来的。在探究表达形式的过程中,体会作者用语的巧妙和用意的精妙,从而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语文教师的职责,就是要引导学生集中于语言表达的形式,欣赏语言的音、形、义,品味语言的色、香、味,掂量语言的轻与重,估摸语言的刚与柔。语文……虽然在品味形式的同时也在理解内容,但它的目的主要不在把握内容,而是学习特定的形式如何表达特定的内容。” 先不说“语文……目的主要不在把握内容,而是学习特定的形式如何表达特定的内容”是否超越了“语文课程内容难以界定”的现实或需不需要考虑文本特殊性,仅就所涉范围看,很明显,郑教授的“真语文”是针对具体的教材篇目的阅读教学而言的。笔者也基本认同。然而,以郑教授之疾言厉色批评史金霞老师来看,俨然是个“非我族类”的心理方式加上典型的“用黑马否定白马”的话语方式。他的推理过程是,“真语文”的追求,就是学生通过语文学习所获得的一切都要从语言形式中来;反之,一切不从语言形式中来的,就是把语文课上成了历史课、政治课、电影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靠谱的结论?郑教授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教材文本精读教学”与整个语文学习混为一谈。 这些年,语文本位的审视有着特定背景和现实意义—侧重于课堂上的文本阅读教学阵地。但整个语文学习的阵地又不仅仅是文本阅读教学这一个阵地,再加上课程内容的模糊性、宽容度,所以,语文教学研究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既需要研究课堂怎么教文本,也需要研究语文学习手段、途径的丰富性。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现状来选择是着重呼吁着眼于教材文本精读教学的“真语文”,还是着重呼吁着眼于整个语文学习系统的“大语文”,但不可以用其中的一个否定另一个,它们本身都是合理的、客观的存在。郑教授用“真语文”来否定史老师的“语文学习”,其实是用微观否定宏观。 语文学习的外延又怎样?过去流行过“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样的说法,大家都很赞同,据说,现在不大这样提了,要反思了,理由就是现在要强调“真语文”和怕走到“非语文”里去,这实在是“过敏”了。分属两个维度的具体文本精读教学和语文学习的生活质地、多样途径,奈何成了一真一非?郑教授拿史老师的“玩”猛批,其实是为了呼吁“真语文”而混淆了“语文学习”和“语文教材文本精读教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颇有些“主义式”划线的意味。 四、要提倡“大语文观” “什么是‘泛语文课’?顾名思义,‘泛语文课’是对语文课的泛化。面对教材中的文本,教师不是集中于语言表达的形式展开教学,而是集中于语言表达的内容。”“什么是‘非语文课’?顾名思义,‘非语文课’已经不是语文课,是在‘泛语文课’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走,走出了语文,走向了‘广阔的天地’。语文教材中的文本只是一个由头而已。”从郑老师的这个定义来看,“泛语文课”泛在目标集中于语言表达的内容而非形式;“非语文课”非在走出了语文文本而指向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生、社会、伦理和政治思想领域。对这个问题,笔者想提醒几点: 其一,语文课的主体可以是语言表达形式的学习,但是不是除此以外就不算语文课?内容已经无所谓? 其二,重心集中于内容还是形式,有时跟文本特点有关。如果我们跟学生讲的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怎么办?非要从中抠出“语言表达形式”而且不能多讲“孔子的思想和春秋时社会特点”?如果文本在形式特征上并不是很突出而思想是其精华,那么重心理应集中于内容层面。 其三,有时候,语言形式和内容水乳交融,以至于很难明确地判断关注重心应是语言形式还是内容——其实完全可以两者并重,或根据学情作尺度把握,而不一定要非此即彼,更不可以见到后者登台,立即大声呵斥犯规。至于所谓“走出语文的问题”,如果总是脱离语文文本而探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和政治问题,自然是走出了语文课,但在语文文本学习的基础上,由此引发学生思考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未尝不可,可以算是一种自然的引申和发挥,根本就不存在走出的问题。 其四,郑教授的定义中特地加了“集中”作为修饰,以求严密,郑教授定义中的“集中”的含义应该是“全部(或接近全部)”的意思,而事实上,有谁上课会“全部是围绕语言形式展开教学”而不越出一步,或“全部围绕语言形式的内容”而根本不管语言形式?那郑教授所描述的“非语文”岂不是一个假想的伪命题? 着重于语言形式的“真语文”的提出本来是为了纠偏,纠正一些架空的课堂文本教学,但如果忽略了这个背景,而以为它是语文的全部本质,显然是走到另一个偏颇上去了。况且,我们的语文课的内容标准几十年来并未得到课程专家的结论——文学、语言、言语、文化、思维、自学能力,甚至心灵品质、人文素养等既相异又交叉的概念,似乎都在语文的范畴之内,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以哪个为侧重,也可以认可现在的“真语文”观(即以语言形式为主),但只是一个侧重或为主,而不可能排除掉其他方面。既然如此,语文语言性的体现就不是那么机械的,“真语文”和“非语文”的边界有个大致区分就可以了,应该模糊化而不是绝对清楚明确,否则我们将人为地把语文局限死了。最关键的是,语言形式之外的情感、思想德性等,究竟是服务于语言形式的凭借还是它们本身就是语文学习的内容?就阅读教学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以具有形式典范性和精神思想含量的语文文本为基础,囊括语言修辞和结构分析等文学技巧形式层面和整个人生、人性、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内容层面在内的“大语文观”,而不是狭隘的“纯语文观”。从这样的“大语文观”角度来看,史金霞老师把爱情、社会和政治常识等问题纳入,是在内容层面上突破了传统语文观的牢笼;把音乐戏剧等元素引入语文课堂,是在教学形式层面的有益探索。至于讨论奥巴马的执政理念等,似乎明显属于公民课范畴的问题,则是在当下公民教育缺席的背景下,已经觉醒的语文教师不得不担负起来的沉重责任。这是责无旁贷的。因为语文教师首先是教师,然后才是语文教师,除了培养学生母语运用能力的职责,语文教师更有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迪和人格熏陶的义务。如果我们承认“培养公民”这个情感思想内容也是我们教学的担当,那为何一定要冬烘地基于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才算合乎规矩? 何况,完全限于文本语言形式教学的负面走向,我们也领教过了,那就是钻牛角尖般的生抠死挖、拆零销售——精深赏析很可取,但如果处处深挖狠掘,不得不说这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应试的影响。我们有多少精力?一年中学生又能读多少文本?你能说,把一文拼命嚼烂,就比粗粗一读,只把握内容精髓从而省下时间去读更多的文本(哪怕是粗读),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有效?我们常说某某人语文素养高,更多的是指他有思想、有文学素养,还是指他会分析语言形式? 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担忧的不是所谓“非语文”入侵了语文,而是让学生没有时间阅读或者只要学生玩命地揣摩品味教材选文,是用腐朽老套的所谓人生哲理命题,来助长学生说空话、套话却不说真性情话的“本领”这样的整个教育乃至社会问题。又在此意义上说,“真语文”可以作为具体的教研活动(如评课时的话题)来探讨和具体例析,若是当做一个攸关“语文命运”并“主义化”的东西来怀忧,则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