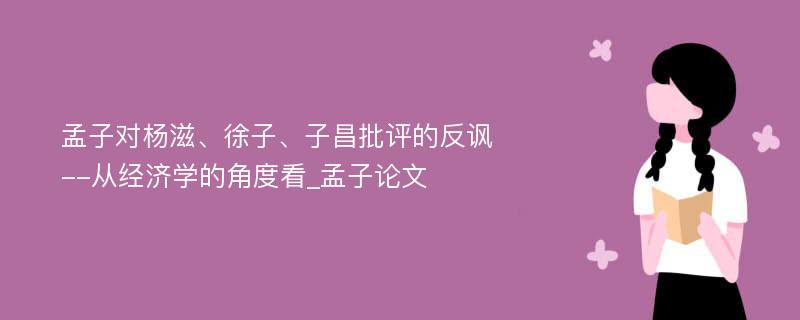
孟子对杨子、许子和子产批评的再批评——从经济学的角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批评论文,经济学论文,角度论文,杨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4)05-051-03
《孟子》对许多人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些批评,在时隔二千多年的今天读来,也很有意思,甚至可以说,很有时代感,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观点,都会有支持者。
本文选择了孟子对杨子、许子和子产三人的批评,先简单介绍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观点,然后从经济学的角度,作一点粗浅的再批评。
孟子对杨子的批评
本来是想写孟子和杨子的争论,但因为资料的不完整(信息不对称),只有孟子对杨子的批评,没有杨子(或其学生)的反批评,所以只能是介绍孟子对杨子的批评,并据此谈一点感想。
《孟子》一书,三万五千多字。其中,有三处提到杨子,分别是:
《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现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尽心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尽心下》,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篱,又从而招之。
由这些引文看,可以知道杨子的学说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百家争鸣”的景况之盛和水平之高,为此而惊讶,而折服;另一方面,象杨子这样一个学者,竟没有一部著作传下来,也令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随后二千年的“万马齐喑”的专政之威和扼杀之厉,为此而悲哀、而叹息。
孟子对杨子的批评,是这样的“三段式”:鼓吹“一毛不拔”,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只有自己,只为自己,就没有君王、不为君王了;为我无君,就是禽兽,就至乱世。
现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杨子讲述“一毛不拔”观点的比较完整的记载,就是《列子·杨朱》。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闲。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
从这一段文字看,杨子的“一毛不拔”,并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由孟子解释)的那个意思。第一,“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只是论述中为了强调论点,而使用的一种极端化语气。因为杨子知道,一毛是不能济一世的。对于禽子的假定,杨子感到难以继续对话下去。第二,杨子所强调的,是对于一体的最小要素“一毫”,也即一国的最小要素“一人”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尊重。第三,杨子并没有鼓吹“损人利己”(这才是真正应该反对的极端的自私自利),他所反对的只是“损己利人”(这是他和儒家的本质区别,因为儒家的主张就是“损己利人”)。最有现代意义的是,杨子主张的是“利己利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就有了这样的思想。中断了两千多年后,我们又需要重新树立这个观念。让我们说什么?!
孟子批评杨子的三段式,第一段,误会(歪曲)了杨子的本意;第二段,无限上纲,在政治上将杨子学说推上了断头台(哪一个皇帝会客忍“无君”);第三段,臆想事实,因为世界发展的历史证明,杨子学说不是乱世之源。
孟子对许子的批评
笔者以为,孟子的许多观念,如果不说二千多年前一开始就是错的话,起码在现在是不合时宜的(比如对杨子的批评)。但笔者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孟子,在笔者的心目中,孟子仍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孟子的学说,也有许多在今天读来也很有光彩的论述,《孟子》中对许子的批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孟子对许子的批评,集中在《滕文公上》的一节,有1100多字(占《孟子》全书篇幅的3.15%。对杨子的批评,是和对墨子的批评联在一起的,有三处,共700字)。原文太长,就不全引了,用白话简述如下:
被孟子所批评的许子的主张,在于这样两点,其一,圣明的君王,应该和民众一样,自耕自食,再治理国家。要民众缴纳粮食财物,是损害民众来奉养自己。其二,童叟无欺的市场,应该是一物一价,布的长短一样,价格就一样,丝的轻重一样,价格就一样,米的多少一样,价格就一样,鞋的大小一样,价格就一样。
先谈第二点,因为这一点短,《孟子》中只有123个字。孟子认为,一物一价是行不通的,因为同一类型的物品,也存在差别,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要这些物品卖同样的价钱,没有人愿意,如果强迫大家这样做,大家就都会做假了,天下就会大乱。
很清楚,许子的想法太天真了。中国在经济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有点象是在实践许子的主张,对价格管制很严厉,同类产品,不管质量好坏,价格差别很小(实际上是靠特权大小来调节供求关系),但也远没有做到“一物一价”。现代经济学解释价格决定,当然不只是孟子所说的这么简单,但孟子的思路是正确的。
孟子批评许子的重点在第一点,有900多字。这900多字,如果要我概括,就是两个字:“分工”。别小看“分工”这两个字,这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其实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思想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通常认为是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分工理论”。
说斯密照抄了孟子,太牵强附会,太“阿Q”。但说孟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了“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虽然孟子只是利用了经济活动中分工提高效率的事实,而引出自己的政治结论。因为孟子和许子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经济上的“分工”还是“不分工”,而是在于政治上的“王治民,民治于王”和“王与民并耕而食”。
许子是自耕自食,但穿戴的衣帽、烧饭的锅盆、犁田的铁器,却是用自己种出的粮食和各种工匠们交换来的。对此,孟子指出两点,第一,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出来才能享用,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疲于奔命(这一点讲了分工的必要性和交换的必要性);第二,交换的双方,都不是对对方的损害,农夫没有损害工匠,工匠也没有损害农夫(这一点讲了交换的正当性。孟子在这里讲的,是市场的正常状态。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好的交换中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是人为地背离了市场的正常状态)。
孟子的结论是,许子(或者其他真正的农夫)既然不可能做到自耕自食又制造各种用品,那末,君王更不可能做到自耕自食又治理国家。“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接着发挥议论,讲尧、舜、禹“忧民如此,而暇耕乎?”“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现在,我们应该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孟子的分析和结论。孟子的分工理论和斯密的分工理论,单在经济学上,也有差别。可以说,斯密的分工理论主要是在微观水平(制针工场里各种工序之间的分工。当然斯密也论述了宏观水平的分工),孟子的分工理论则是在宏观水平(国家中君王和民众的分工,各行各业的分工)。
在经济学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个角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都是成立的。因为事实上如此(实证分析),谁也改变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反其道而行之”,推行“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让工人王洪文当副主席,农民陈永贵当副总理,将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赶到农村种地,那样做,并没有改变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做大官的王和陈,变成了劳心者,种地的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变成了劳力者。再因为道理上也应该如此(规范分析),大家都必须遵循。只是对于“劳心”的内涵,要有不同的界定(比如现在肯定不能只将“劳心”理解为“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
孟子对子产的批评
“先思后行“和“宽猛相济”,是出自子产的治国之道:“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春秋左传·襄公》)“子产…曰,…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春秋左传·昭公》)
著名的成语“道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是出自子产的治国之政绩:“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衅。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史记·子产传》)“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史记·郑世家》)
孔子和子产是同时代人,两人有交往,是“称兄道弟”的关系,“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史记·郑世家》)孔子对子产的评价很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但孟子却对子产持强烈的否定态度,而且就是非常明确地针对孔子所肯定的“惠民”这一“君子之道”(孔子赞赏子产“惠民”,在《论语》中提到两次。除见于《公冶长》一篇外,还见于《宪问》一篇)。孟子认为,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对民众施小恩小惠,不是大政治家的作为。
《孟子》中提到子产,有两处地方。一是《万章上》,讲到子产的“得其所哉”典故,因为不涉及治国之道,这里就省略了。再—是《离娄下》,译成白话:子产主政郑国时,用自己的专车帮老百姓渡河。孟子说,这只是施舍小恩小惠,他不懂得治国之道。如果政府建造好行人和行车的桥,老百姓就不会为渡河的事犯愁和痛苦了。主政者只要把大政搞好,出外时前呼后拥、鸣锣开道都可以,哪里用得着帮老百姓一个个渡河?主政者要一个—个地讨老百姓欢心,时间就太不够用了。
撇开孟子对子产的总体评价是否准确,甚至还可以撇开子产用自己专车帮老百姓渡河这件事是否真发生过,孟子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对于统治者、领导者,大政重于小惠。主政者自己应该明白这一点、做到这一点,老百姓对主政者的判别,也应该按照这个标准。
孟子在多处反复地阐明了这个观点。比如对梁惠王说,同样是有高台深池、珍禽异兽,圣明的周文王得到人民的祝福和欢呼,而暴虐的夏桀则被老百姓诅咒和痛恨(见《孟子·梁惠王上》)。再比如齐宣王检讨自己,“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则开导他,如果将国家治理好了,好战、好财、好美女、好宫乐、好田猎,都不是坏事,老百姓会喜欢这样的君王(见《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在现在能不能够成立?
在某种条件下,回答是肯定的。
假设—个最简单的模型,将主政者的行为分成大小两类(大指治国,小指个人),行为的效果分成好坏两类。这样可以得到四种组合,A.大好小好;B.大好小坏;C.大坏小好;D.大坏小坏(复杂的话,行为和效果的分类、以及两者的组合都可以无限的多)。说A最好,B次好,C次坏,D最坏,大家应该没有意见。
孟子对子产的批评,实际上只是涉及到B和C的比较,B优C劣,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C和D相比,则是C优D劣;如果A和B相比,则是A优B劣。
“新儒家”将孔孟之道概括为“内圣外王”,相当于上面所说的A型。而且是“外王”必先“内圣”,这太苛刻,也太理想化了(脱离实际)。起码从《孟子》看,孟子讲得最多的,还是B型。他觉得,B型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外王”不必“内圣”。可惜的是,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个次一点的标准,达标的政治家好像也不太多。
[收稿日期]2004-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