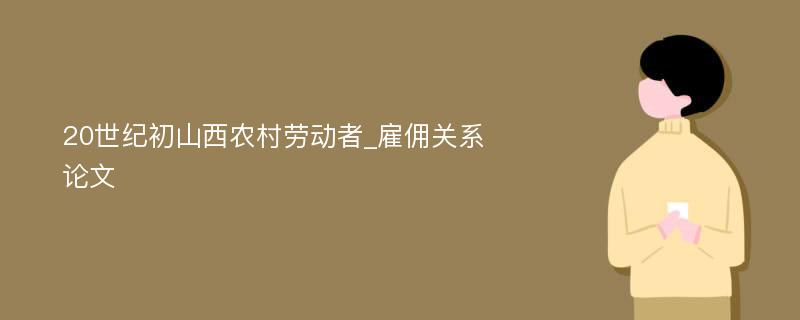
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乡村雇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雇工论文,山西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对于近代中国乡村雇工的研究,多将其作为具有资本主义趋向的农业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而论及,雇工被视为农村土地集中和出现两极分化后产生的固化的阶层。近年来有论者指出,雇佣关系与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似乎没有必然的关联,①“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雇佣关系的兴起不等于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的兴起也不等于向资本主义过渡。在劳动力被牢固附着在土地上的西欧,自由劳动力的出现肯定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一。但在农村劳动人口过剩、基层结构较松散的中国,则不缺乏具有相对人身自由的劳力”。② 既然如此,近代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雇工群体到底应如何认识?雇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关系是怎样的?这些方面,尚有较大拓展和挖掘的余地,尤需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世纪前期山西乡村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是因为笔者获取了相对比较集中的山西地方文献资料;另一方面也因为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即使以“华北”为范围)甚少涉及山西,③ 从社会史角度对于山西雇工的研究仍付阙如。当然, 本文视野所及乃至资料的运用并不完全局限于山西地区。至少,将某些省区与山西的相关资料或数据进行比对,可能提示出区域差异(即使基于习俗、文化传承乃至经济水平形成的区域差异)背后的同质性结构和共趋性意义。
一
在既往的研究中,乡村雇工认定的标准并不一致,或按户主职业而定,户主为长工者即为雇工;或以全无土地的雇农为雇工,或把自己不经营土地而出卖劳动力的农户(包括无地户和有地而出租与人的农户)都算作雇工。也有以农具之有无来定雇工者:“佃农自身未拥有尺寸耕地,雇农则并农具亦无之。”④ 本文所论及的雇工包括“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雇农和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自耕农”。⑤ 由于出卖劳动力不一定用于耕种,故本文研究范围特指旧文献中所述“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的农村雇工;⑥ 也即毛泽东所言的“农业雇工”:“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⑦ 至于众多在农村或小城镇被雇从事喂养牲畜、账房伙计、油坊、纸坊等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长期或短期做工者则不在考察之列。
已有研究说明,在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剧烈变动进程中,与“农村破产”趋势相伴随的现象之一即是雇佣关系的普遍化和雇工群体的活跃。所谓“自作农日渐减少……地主也渐渐的增大……雇农也与之俱增”。⑧ 在华北,“有田五百亩以下的人家多数自己经营耕种,不将农田出租。他们往往雇用了通常的年工和短工,来进行规模较大的经营。这样,一方面雇工经营成分在华北就占较大的比重,同时农村各阶级中农业劳动者的成分也较中南部为多”。⑨ 近年以河北清苑为个案的研究表明,雇佣关系是农村“最基本的剥削关系,远比租佃关系普遍得多。在各调查村,地主可以不出租土地,但很少有不雇工的,富农当然更是依靠雇工剥削。农民各阶层中,一部分中农和贫农在农忙时也雇佣人工”。⑩ 显见增长的雇佣关系成为农村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
那么,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中的雇工究竟有多少呢?据许涤新估算,雇农约有3000万。(11) 更多的统计则是对雇工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关注。新近出版的《吕梁地区志》对1928年山西11个县的雇工(雇农)调查统计情况十分详细(参见表1)。
表1 1928年山西各县自耕、半自耕、佃农、雇农比例(%)
县份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雇农
交城 49.2531.109.81
9.80
文水 64.1922.458.73
4.52
岚县 43.3627.8914.87 13.78
兴县 49.4824.1 13.8
12.58
汾阳 30.1121.6932.53 18.67
孝义 62.6 14.7715.9
6.73
临县 38.8420.3320.5
10.78
石楼 62.4617.5317.04 3.17
离石 57.3830.625.00
7.00
方山 80.015.98 6.99
7.01
中阳 28.8532.6917.31 21.15
平均 51.5 21.1515.22 10.48
资料来源:据吕梁地区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吕梁地区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表改制。
表1中显示,1928年山西雇工占农户平均比例是10.48%。这一数据与1930年代的调查统计大致相当。据当时的估算,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雇工占农村人口的百分比分别为11.4%、9.3%、8.1%。(12) 具体到山西,1933年南京中山文化馆调查山西43个县雇工占农户总数则为10.29%。(13) 而据《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记载,“1935年山西省1829836户,其中,出卖劳动力的雇农为170803户,占总户数的9.33%”。(14)
当然,因为统计范围之不同,所见雇工平均比例数也略有出入。据学者研究,山西阳高在辛亥革命之前自耕农确占最高优势,“至于富有的地主以及赤贫的雇农与佃农,简直微乎其微”,而到了1930年代初,“佃农、雇农已占农户总数的41.9%,其中雇农占到总数的15%”。(15) 晋北三县(天镇、大同、阳高)“无地的佃农及雇农等竟占户口总数底百分之三十一”。(16) 1930年代后期山西雇工有11个县占20%以上,这些县大部分是棉麦区或垦荒区,如棉麦产区的永济县雇农占总户数的34.24%,垦荒较多的静乐县雇农占总户数的23.72%。(17) 这说明,由于情况的特殊和复杂性,雇工所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存在区域差异,有时差别还很大。
需要说明的是,不管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是由何种原因引起,有一点可能是共同的,那就是雇工中的短工群体,可能没有完全列入统计之内(大多将其列入自耕农或佃农之中),而事实上日渐增长的短工群成为构成农村雇佣关系中的主要成分。
在晋西北兴县黑峪口村,“这里富农常常雇佣些短工,没有统计在内”。(18) 保德一些乡村的佃农、贫农也“常佣出一部分劳动”。(19) 一项以晋北和晋东南乡村的比较调查说明:“半自耕农,自己所有之土地,多不足以自给,因其余力兼种他人之土地,藉以补助,则雇佣长工者必少,工农住户自然亦少矣。”(20) 这里的“工农住户”即专指“长工”而不及短工。河南的一项调查资料也表明,贫农中出外为短工的“几乎比纯粹雇农要多两倍。辉县贫农兼雇农的更多……以纯粹的雇农十二家来比,差不多是四与一之比”。(21) 社会的动荡和生活的无助,造成贫农、佃农与雇农间的流动,“贫农则时时有变为佃农或雇农的可能,佃农又时时有变为雇农的可能”,(22) 如保德县段家沟村,1936年佣短工者有7户,1938年为9户,1942年为10户。打短工者多是贫农或自耕农,“这里给人雇工的,多半是贫农,他们除给自己工作外,剩余劳动力很多(土地少不够做),抽空便给人家打短工(走口外的除外)”。(23) 该村“小商”大都是口外回来的雇工,“他们对于土地都非常羡慕,所以在可能条件下,还要种些土地,因为农业生产比经商作工可靠”。(24) 而这些“雇工”只是列入贫农和商户统计之中。此外,有些乡村并“不宣布雇佣关系。雇工(无论长短),多是雇主亲戚,名义上作客或帮忙,实际乃是雇佣关系”。(25) 这类情况也很难统计在内。
此外,除了一般的长工(也叫年工)、短工(俗称打短儿),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雇工。如“季工”,又称“月工”,俗称包月子:“营生够一个月时,就要雇一个包月子”,“每阶段的佣工期限是一两个月以至三个月……总计多不过五六个月而已”,其性质和长工相似,不过时间较短,断断续续。一般来说,月工是“当耕种、中耕及收获等农业劳动紧张底各时期,临时雇佣的”。(26)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即“半月以上为月工,半月以下为日工”;(27) 如“长做短算”,即长久的短工,是短工的性质,和短工做一样的工作,做一日算一日,不过连做的期间比短工要长,只适用本村人,如果雇主想随时雇人,双方可约定时间随时来做活,其待遇与短工相同或稍高。时局不稳雇工难求时,雇主多采取短工之特殊形式。又如“冬工”,长工在冬季三个月做工即是冬工,多事育牲口(育牛较多)、驮炭、家中什役、支差、背破柴、打围等,一般为大户人家使用,其工资当是平常工资的一半;此外还有“半工”(即半个长工的工作期限,也叫一份份工)、“份工”(双份份工)等。(28)
以上这些类型的雇工大体多活跃于1930年代前后,从总体上展示出乡村雇工群体的扩展趋势。无疑,拘泥于户口统计意义上的雇工(雇农)比例,远不足以反映乡村社会生活的实况。“然无工农住户,不能即断定其无工农。”“农家人力多而土地不足者,须有数人在自己家中务农,数人分往别人家佣工,但此种现象,仅其家中人有一部分为农工者,非纯粹工农住户也。”(29) 照这种情况看,乡村雇工的数量其实远多于雇工的户口统计。
此外,衡量雇佣关系在农村社会中地位的另一指标是雇工在农业劳动中的比重。1920年代以后山西发展垦殖,雇佣劳动的需求增大,但由于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和经济能力脆弱,雇佣人数一般不会太多,“使用雇工的人数一般是二个至三个,此外还用些短工”。(30) 左权县大岩村雇工,“最强的劳动力能种十五亩地,平均每人种十亩地,最低的劳动力种六亩地,平均种五亩,有牲畜的能种十七亩,无牲畜能种九亩”。(31) 根据山西农村“七紧、八慢、九逍遥”的俗语(意即每亩地要用七个到九个工),“按每人全年在地里劳动8个月计算,每人平均种30亩地(畜工除外)就够照护了”。(32) “神池县每壮农可耕作一百垧。其永和县每壮农可耕一百二十亩”。(33) 另外,农户雇佣劳动比重,既因地区而异,更随农户经济状况而定,由于大多数农户是按家庭成员的耕作能力和生活需要确定经营规模的,农业中因为小经营的广泛存在,再加上人多地少、资金短缺等原因,一般农户所使用的雇工数量也十分有限。按照学界的研究估计,1930年代“北方地区完全或主要靠雇工经营的土地约占20%—30%”。(34) 而根据1929—1933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山西雇工劳动占农业劳动总数的15%—20%,与其他省区相比,在被调查省份中属中等水平。(35) “根据武乡、五台等县的统计,农业经营中雇佣劳动的比重分别为27%和26.5%,略高于全国平均比例的25%”。(36)
二
雇工、雇主及雇佣市场的存在共同构成乡村雇佣关系的要件,这是理论上最简要的概括。在实际生活中,山西乡村雇佣关系几乎涉及村社各个阶层,具体情况较为复杂。
农村雇佣关系基本上通过雇工市场来完成,1930年代山西乡村雇工市场十分活跃。劳动力市场在北方称“人市”、“工市”、“工夫市”,交易对象通常为日工和月工。短工雇佣具有较强的时效性。1934年对山西65个县的调查表明,35个县有相对稳定的雇工市场,(37) 占总数的53.84%,30个县无市场,占总数的46.15%。(38) 大多数短工是同时耕种自家田地的小农,不可能离家很远。因市场时间和空间范围都受约束,所以人市是季节性、地方性市场。入市一般是在较大村庄定期举行,即“一定时间集合于一定场所”,通常清晨开市,最迟到中午便散去,“每天早晨五点左右,雇主就到短工集中地点,双方商定”。(39) 有较大集镇的市场有时持续一整天,因需要连续雇佣,直到本季农事结束,所以在中午、下午与农工定约,第二天再上工。
一个短工市场可供给周围十个左右村庄的短工需求。人市规模视周边村庄大小、季节及收成情况等而定,有时多至几百名农工待雇,但有时可能只有二三十人。从西烟镇人市看,“在锄苗、秋收季节,上市的短工每天竟达两千余人,各处来此者络绎不绝。人数除西烟镇及属村的贫困农民外,大部分来自临县,南面寿阳、阳曲,北面五台、定襄,东面阳泉、平定,西面忻县、崞县”。(40) 即使小规模人市也有附近村庄的短工及雇主参与,据刘大鹏所记,“里中豫让桥为佣工之市,凡佣工皆在其上。”“稻秫成熟,业已开镰刈之,今朝见有多人,荷担持镰寻觅刈稻之家,询系外县之人。”人市雇佣时多时少:“今朝有二百余人被西镇、花塔、硬底等村农家雇去,未留一人。”但有时人市没有雇工:“今朝市上无一雇工之人,雇人者皆苦无人,不得在田作……乃到别处雇下三人。”(41) 刘大鹏日记的零星记载,为研究乡村雇工市场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人市上的劳动力价格,一般是日出前工价高,日出后工价则低,工资由雇主与雇工双方协定。根据陈正谟的调查,山西65个县,全无中人说价,有雇主喊出农事种类、工价以求雇工者,倘无人应征则增加工资,同样也有雇工喊价求雇主的。劳动力价格受供需关系的影响,也受粮价及气候的影响。“山西孝义、左云各县日工工资亦随粮价涨落。”(42) 有些雇工市场禁止雇工与雇主商议雇佣价格,市场中每日都标有日工资的价格表,此表多由雇工市场所在村村长,或寺庙僧侣决定。当雇工与雇主认为价格不合理,他们就与村长或僧侣商议,最终由其决定。这样在人市上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但也有雇主把持行市,使雇工没法搞价,如民谣所唱“打短工,不说价,人家干啥咱干啥;商量好,不会差,家家工钱一般大”。(43)
雇佣劳动力市场在山西的分布相当普遍,但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必须上市交易。在距离市场较远或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地方,往往是成群结伙的上门求雇或预定。如山西隰县,“有扎工组织,农工每十人一组,内有领工一人”,(44) 由领工帮助揽工。汾西有数十人组成的“农工团”,内有工头一人,与雇主接洽工作与工资。这其实是一种“准雇工市场”的状况。短工的雇佣已经很少受到限制,虽然某些地方短工交易中存在中间人,但既不普遍,更没有形成制度,只是一种习俗而已,其约束力也只发生在雇主与雇工达不成一致时。
至于长工,则一般不通过人市受雇。其雇佣或由雇主与雇工直接商洽,或通过中人介绍,其中还有较多的私人关系。没有中间人的介绍与牵线,长工一般不可能找到工作,经他人介绍后,在雇主家作为雇佣地点而议定雇佣价格及其他条件,并达成口头协议,由雇工找保人担保。
从雇佣倾向来看,长工和短工的取向主要取决于双方经济或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明显地受制于“制度”或“身份”的强制性作用。193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意向选择长、短工的雇工分别占52.46%和19.67%,另有27.87%的雇工选择“因环境而异”。(45)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雇工的受雇倾向,但并不能完全说明愿当长工者一定比愿当短工者多,它只是在某时内的表现。究竟是做长工还是短工,依具体情况而定。据当时的抽样调查统计可知,愿当长工者的主要原因是无家室(2例),无田地(11例),生活安定(31例),共44例;选择愿当短工的主要原因为是有家室(2例),有田地(28例),多挣钱(7例),共37例。(46) 显然,决定其选择长工与短工的主要因素是田地与生活安定两项,而有稳定做工机会的“生活安定”因素显然又是最主导的原因。
雇工的生活境况和经济估价也是制约因素:“当长工能积蓄总数钱,不易零星挥霍。当短工挣的零星小宗钱,容易挥霍;当长工虽按全年日数平均起来比短工的工钱少,但不论闲忙都有工钱,短工在忙时虽挣的钱多,一至闲月,即无雇主,是以不愿当短工。”(47) 另外,“因出外营工,农人以为是望风扑雨,能否赚钱发财,还是问题。若专靠附近村里做些短工,但机会很少,所以多愿当长工。既可靠准赚钱,复可代做家务及耕种自己之田地”,表明愿当长工是因为“天灾人祸,农村破产,做工的人供过于求,工资常有更变……以其工资确定,而堪保险也”。(48) 另一部分人是由于地少劳力多,劳动力的过度闲置而当长工。而选择短工是因短工较自由,雇主往往对长工有不平等待遇,且长时雇佣,田地不能耕种,所以做工不敢约定日期长,愿意打短,做一天算一天,(49) 长工多是负债太多而不能谋生,但短工利于谋生。(50)
从雇主方来看,选择雇长工的原因是,“短工没有长工受苦大,长工天不亮就起床了,短工上工迟,下工早,短工只在地里受苦,家里苦不做”。(51) 其次“短工没把握,今天有人做工,明天也许没有人。”“长工负责任,短工和短算不负责。”“家里没有贴苦人,一切营生都由长工计划安排,长工是常年受苦,一切事务,全凭长工。”(52) 因此,雇主才能省心。刘大鹏曾记述说:“王老四为吾家做长工于今第四年矣,田中一切农务均能了解,予一为指挥,即能应声而往办,予得多日不赴田也。”(53) 当然,雇短工也有益处:只在工作太忙时才雇人,这样可节约工资和伙食,且可使工作效能提高,即“一个短工能做出一天半的工作(一个人锄五天,雇短工三天就锄完了)”。(54) 然而,由于雇主资产有限及其他原因,雇短工的农户远多于雇长工者。1930年代费肼石对山西61个县的调查统计表明:多雇长工之县为26个县,占42.62%;多雇短工之县为35个县,占57.38%。(55)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劳动力在一部分时间内急需,一部分时间内闲置,这引起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矛盾。在最佳农时,“佣工之人到处皆缺,工资虽大,而觅工不易”。刘大鹏记曰:“雇工甚缺,工资甚大,欲雇一长工不能。”“雇工无人,予欲麦中勾谷,昨晚寻佣,奈无一人,受苦者抑何若是之缺耶?”尤其在“春秋正忙”季节,“人工甚缺,由于戒烟紧急,一切佣工受苦之人逃之他处者半,拘留者半,农家受此之害,而为政之人并不虑及于斯也”。(56) 据30年代的一项调查,山西各县农工劳动力供需状况大体是:过剩者为20个县(占36%);适中者11个县(占20%),缺乏者24个县(占44%),(57) 劳动力仍是山西乡村劳务市场的主导方。因此,在雇佣关系上雇工的选择似更为主动,“解雇与退工,只要有正当的理由,解雇与退工都是随便的。一般的雇工退工的时候多,雇主解雇的时候少。饭食不好,雇工就退了,俏皮的雇工在作工三个月后夏天到了,为挣大钱也辞退了。雇主则以长工退了仍得雇,但工资既大,人也难雇,所以多不愿意解雇”。(58)
那么,在乡村社会发生着的雇佣关系,亦即主雇之间是否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分层明确的、边界清晰的标示其不同地位、身份和角色的社会关系呢?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前提之一。
首先是雇主。一般而言,富农与雇农是雇佣关系中基本对立的两极,“然而在农村经济劳动紧张的时节,往往不仅是大部分自耕农,甚至连一部分佃农及贫农,也临时以雇主的资格而出现……同时,在雇主方面,要绝对除外地主,也是事实上不允许的”。(59) 所以几乎所有寻找工作的人,都有可能受雇,几乎任何出得起工钱的雇主都可雇工。富农、地主是当然的雇主阶层。中农雇人主要是短期内人力有限,“雇长工的均因劳动力不足,有的经营商业,但多数是一些劳动力或出外参军或出外工作的缘故,因之常喊苦小不够”。(60) 贫农雇佣是因为自己劳动不足,再加上自己负担的工价的原因才雇工,这一阶层的雇佣主要是由于农事紧急引起的。佃农“有的是由于家庭劳动力不足,或是遇到疾病变故……也有的是因为他们所营农业的规模超过了家庭劳动力可能耕作的限度,求之于雇工”。(61) 然而佃农雇人的情况少之又少。
雇长工者多集中于富农和地主阶层。据有关调查材料,武乡县大有镇有大地主1户,雇有长工9人;经营地主1户,雇长工5人;富农20人,雇长工24人;商人17户,雇长工2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者等78户,没有一户雇佣长工。(62) “山西寿阳、应县、左云、平定、武乡等,是富户雇长工,非富户不能雇长工,其安邑、晋城、灵石等县则是中等以上之农户雇长工。”(63) 长工的多少基本由经营土地的多少决定。受经济状况的制约,山西各村地主户雇佣长工人数一般2—3人,富农户为1—2人,少数中农雇佣长工的多只1人,个别的还不到1人(与人合雇)。兴县(抗战前)每农户(富农)平均雇佣不到一个半雇工。据神府县、兴县八村雇佣关系调查,雇主在各阶层(共26户)中的分布情况为:富农1户,富裕中农12户,中农10户,贫农2户,小商人1户。(64) 可见,乡村短工雇主构成更为广泛,只是穷人没有富人雇的多,也没有其雇的时间长(富裕中农与中农雇得最多,时间最长)。据1941年晋西北杨家坡雇工调查资料,雇短工的10户中,地主与中贫农各占5户。(65) 当然,一般地区地主雇佣天数最多,富农、中农、贫农依次递减,“全年各类雇主雇佣短零工合计总户均天数为59—68天,即相当于两个月或稍多一些。”(66) “短工通常平均每年受雇约40—50天。”(67)
其次是雇工。失去土地的农户是农村中天然的被雇对象,但雇佣劳动却并不限于“农村无产者”,贫农也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有关不同阶层做雇工的原因,可参见表2。
表2 各阶层做雇工原因分析表
雇农贫农 中农贫民
做长工没财产;久做工有些地不够种,有余力余劳力;为挣钱;
买地、买牛
做短工*
没找上长工;懒汉 没找上长工;为自由;没吃余劳力;无耕牛; 木匠、石匠等
的;没耕牛;有少量余力 买布、帽等
做包月子 由长工退工找不上长工;没耕牛;不够余劳力;无耕牛;
吃;有余劳力买布、帽等
做半工捎种地(租的);缺吃、捎种自己地,不够种;缺吃、
没吃的;找不上长工; 没吃;找不到长工;自由;余劳力;自由
伴租地;伴种地伴种地;租地
做冬工勤劳;没办法 勤劳;没吃没穿 勤劳
长做短算 找不上长工;自由 找不上长工;自由
两份份工 捎种地;伴种地;找不 捎种自己地;捎种地;伴种
上长工;缺吃 地;缺吃;找不上长工
资料来源:据山西省档案馆藏《雇工零碎材料》改制(山西省档案馆,A88—3—34—6)。*此外,短工中还多为地痞、流氓,为挣钱,不好受苦。
表2显示,虽然原因各不相同,长工、短工的主体则为雇农,但也有中农、 贫农、贫民。需要说明的是,贫农占有土地要比中农少得多,如果不另求生计就无以维生,打短工对他们来说十分普遍。他们一方面喊“地不够种”或“没有地种”,一方面则要另寻营生,“在农村中打短的,弹花的,干(擀)毡甚至一份份或两份份长工的,也正是这些人”。(68) 因他们有小块耕地,既不能远离家门谋生,又不足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卖劳力来补充家庭收入。因此,实际上贫农兼雇工的远比纯粹的雇农要多,“贫农是劳动力买卖的主要供给者”。(69) 因土地缺乏,劳动力差不多普遍的剩余,而土地养活不了自己,便只有苦力佣工。“有许多家父亲在家种地,儿子当长工,或哥哥种地,弟弟当长工。”(70)
在雇工群体的构成上,长工基本都是雇农阶层;贫农更多的是当短工。短工的“构成分子非常复杂,可以包括了劳动农民群众中各成分底全体”,(71) 尤其是佃农和雇农之分别并不十分明确。佃农“他们完全没有土地,他们之所得,一部分是由于相当于工资的租种田地的报酬,一部分是藉帮工或从事手工业得之收入”,(72) “中国佃农的收入,不够支持他们一家生活的,他们除了耕作土地以外,不得不兼营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或者兼营手工业及小贩等生涯,补救生活上的不足。”(73) 按1946年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规定, 雇工“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他们没有土地,“他们的生活主要靠揽工打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人家地里受苦”。但事实上,在其文献所举三例雇工中也都分别有不同形式的土地经营(如租种、伙种,自有,全佣等)。(74) 所以,事实上“雇农也常是有家庭及私产的,假如一无所有,恐怕早已不再滞留于农村而漂泊到通都大邑去了”。(75)
在打短工的人群中,贫农最多,其次是中农、贫民和雇农。中农、贫农常常既属雇主又属雇工的双重角色,然其出雇日远多于雇入日。可以看出,雇佣关系的社会构成涉及乡村社会各主要阶层,雇主和雇工双方角色并不完全固化。中农、贫农、少数佃农和雇农可同时兼有雇工和雇主角色,只是雇工和雇主不断相互易位,形成一种循环式交互雇佣。
在以家庭为主的农业经营中,以完全雇佣劳动为主的经营还异常的稀少,普通雇佣者只是当作家庭劳动的补充。“小农户具有的按亩计算的劳动力几乎要比大农户多两倍”,(76) 多数贫农因耕地缺乏,劳力多有剩余,往往于农忙时临时受雇于人,把出卖劳力作为家庭重要副业之一,而形成兼业的雇佣劳动者。这使农村中缺乏真正的纯粹雇工,而存在大量季节性兼业雇工。可见,乡村社会雇佣关系的普遍化是通过雇工身份的非固化或雇佣角色的互换性得以实现的。
三
有研究者指出,“雇农是乡村中社会地位最低、生活最悲惨的一个群体。从经济收入看,常常自顾不暇,难以娶妻成家,事实上许多雇农都是终生过着鳏居孤独的生活”。(77) “困苦终日,不得温饱”是雇工家庭物质生活的常态。对于乡村大量雇工的出现及其日渐恶化的生活状况,以往人们多以“两极分化论”加以解释,认为是土地高度集中、两极分化的结果。因为“有小商品生产者,就会有分化,就会从小商品生产者中产生富人和穷人,雇主和雇工。”(78) 而近代以来,“军阀割据加剧了土地的兼并与集中。……迫使不堪重负的佃农沦为雇农”。(79) 然而,这种“灰色”的理论预设,面对鲜活的历史事实时不得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有学者通过对康熙年间起直到民国时止的一批地籍档册的分析,发现在关中,“二三百年间土地分配状况虽然是因时因地而有各异,但地权分散这一特征是较明显的”。(80) 即使在江南地区,“由康熙初年(5—15年)至1949年,二百七、八十年间,地主同自耕农占地的比率几乎稳定在65∶35。看来人们设想的地主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的必然性,在这里没有得到证实”。(81) 郭德宏依据大量不同统计资料对1925年至1949年的土地占有情况作过精详分析,确认“无论按哪种方法计算,土地占有在旧中国几十年间总的来说是趋于分散,而不是趋于集中了”。(82) 与全国土地占有趋势相比,“山西土地固不如他省之集中,地主势力尚小”。(83) 如抗战时期的一项统计表明,(84) 在各区县中,晋西北地主富农土地占有比例最高,为60.8%,达到或略高于上述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余地区地主富农占地平均比例最高者为31.5%(平定、盂县),最低者为15.5%(太谷、祁县等地),远远低于上述全国土地集中水平。因而,事实上在土地改革之前,即使在土地相对集中的晋西北兴县等地,“土地的占有关系已在发生变动”,变动的“确定和必然的趋势”恰恰是“地主土地总数的减少与中农、贫农土地数量的增加”。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断定,“地权的转移,在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是通过表面自由买卖实现的”。(85) 正如当年张闻天调查所见:“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动,也是朝着地权细分、自耕农群体和质量都增大这个方向发展的。”(86) 这一事实显然与“土地集中”所致的“两极分化论”相去甚远。
从物质生活层面的比较而言,“两极分化论”诠释的基点是社会阶层贫富之间的强烈反差及其扩展趋势。但档案资料显示乡村各阶层的物质生活差异的“两极分化”趋势并不显著,如在粮油盐肉等必需消费总量上,临县雇工家庭与贫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完全一致,与中农家庭略有区别,与地主富农家庭的消费有较大差别,但也是程度之差。就其消费质量(即主食种类)而言,乡村社会阶层之间的物质生活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如1937年晋西区之保德林遂、晋东南之武乡),不过,各阶层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为粗、细粮或有无肉食(且地主之家也仅年节时偶有肉食)和食盐之别。地主家庭的日常生活无疑优越一些,但从调查资料看其特别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平日里地主本人吃白面(但媳妇吃谷窝窝);过年节有白面饺子吃。(87) 山西乡村大多数家庭的物质生活都“极其简朴,极其节约,达到了非常苍白的程度”。(88) 中共晋西区党委在兴县赵村调查资料显示,乡村各阶层之间的日常生活并无太大悬殊,“群众平日不吃菜,吃起菜时就做一大锅,尽够吃(不论贫富都如此——原注)”。(89) 就衣物层面而言,农家衣被材料的支出不大, 从各阶层全年消费布料对比情况看,雇农与中农家庭的年用布量差别微小,人均相差仅2尺;与富农家庭相差7尺。(90) 武乡县东沟村在抗战前各阶层衣物消费在地主、富农、中农与贫、雇农间的差别也并不十分突出。(91)
雇工家庭与中农家庭的衣用情况相差无几;地主富农较为富足,也不过年均衣物各季两套罢了。对于大多数乡民,“通年仅换两次衣,最多不过三次而已。”(92)
作为人类维持最基本生存条件的衣食状况,构成社会成员分享社会地位的基本前提。衣食消费上量与质的差异及其殊分趋向,是判定社会分化与否以及分化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但差异并不等于分化。资料表明,乡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并不特别悬殊,即使在地主、富农与贫雇农之间,尽管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却也并未形成“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它所呈现的是一种“普遍贫困化”的乡村生活情景。1936年《中国农村》描述山西中路农村的境况说,“一片片的废墟荒丘,便会呈现在你的视野中”,“太谷县北堡村在六十年前村中有一千三百户人家,三十六家大小商号,房屋有一小部分是瓦房,其余多是楼房。街道上两边密密地排着人家,……而今呢!只有从废墟中找人家。共计只有六十户”。作者调查的另一个村落,“现存三百余家。当嘉庆时代,户数本来是五千以上的”。(93) 这与刘大鹏日记中所载太谷县里满庄败落情形几乎完全相同:“昔年……该庄富户甚多,通共二千户,高楼大厦金碧辉煌。……迄今里满庄大败,现在仅有对开百来户,率多贫困,拆卖楼阁亭台而度日者十之八九,无一富户。”(94) 显然,这种整体败落的“触目皆凄怆之象”,更集中地发生在富贵的“大户”人家。“近数年来……农民逃村数不断的增加,荒芜土地每年有扩大的倾向,……引起了全省经济生活一般的停滞,更弄得贫乏化的农民越发无法以对付。”(95) 阎锡山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1935年)中也描述说,“年来山西农村经济整个破产,……以至十村九困,十家九穷”。(96) 适在此年,刘大鹏日记记述本地乡村衰败的惨景:“‘农家破产’四字是现在之新名词,谓农家颓败不得保守其产也。当此之时,民穷财尽达于极点,农业不振,生路将绝。”特别值得体味的是,刘氏叹息道:“即欲破产而无人购产,农困可谓甚矣。”(97) “无人购产”现象充分揭示出,这不是“两极分化”所展现的“财富转移”的集中,而是整体意义上的败落。整体败落的“普遍贫困化”(98) 与“两极分化”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演进趋势,虽然都可以造成乡村弱势群体——雇工生活状态的日趋恶化。
20世纪前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分化并不充分,这直接导致乡村雇工群体的“非纯粹化”。“这里给人雇工的,多半是贫农。他们除给自己工作外,剩余劳动力很多,抽空便给人家打短工。”“所以佣短工的户数……还是发展的。”所以“兼雇工”的总人数远比纯粹雇农的数量要多。(99) 而本文前述“乡村社会雇佣关系的普遍化是通过雇工身份的非固化或雇佣角色的互换性得以实现”,也是“普遍贫困化”趋势演变的历史结果。这自然也关涉到乡村雇工群体的社会分层问题。
首先,乡村社会分化不充分,使乡村雇工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当时一些农村社会调查资料就指出,中国乡村没有剧烈的阶级分化,大地主并不多,其现状是“大地主虽少,而中小地主的人数却很多。”(100) 同样,“雇农可以说同‘大粮户一样的稀少,其中大都是由佃农中分化而来的”。因此,不仅常常把“‘日工雇农’……归纳在上列佃农的百分比中了”。(101) 而且在很多地方,雇农与佃农、自耕农之间的界限既不分明,也是随时而变动的,“雇农可以变为佃农,佃农可以变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可以变为纯粹自作农,同时自作农也可往下变去。土谚说:‘千年田八百主’,可以想象这个变化的迅速了”。(102) 所以,“雇农有时可以作佃农,佃农有时也可以变为雇农,不是永久不变的,他们的分界也极细微的”。(103) 尤其是短工群体,“这个日工底构成分子非常复杂,可以包括了劳动农民群众中各成分底全体”。(104) 甚至有些乡村出现多重身份的农户,“中农变为雇工,而同时又兼为富农。把他家的人抽出一人去作年工,而自己雇上一个半年工,对别人亦能应付,而自家收入又能增多”。(105)
毗邻山西的河北省井陉,“本县农民,绝对没有产业的,居最少数。那有产业不够一家人耕种的,便给人家做长工,将自己田地租与了,或带地做长工,便成了工人。也有因为自己地少,租典人家些的,便又成了佃户。或者也不做长工,也不成佃户,只等着农事忙迫时候,急速把自己的工作完毕,去给人家做‘找工’,也算一种投机做法了”。(106) 长工、佃农找工不同角色和身份的转换,既昭示出村民身份的“自由”特征,也揭示着雇工角色与其他角色“胶合”难分的特征。这其实也是当时“农村社会调查者”无法确认“雇工”身份及其数量的主要原因了。(107)
还有所谓“半佃农和佃农——实际是指‘在东家土地上干活的雇农’,他们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归自己,其余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五归地主——东家。最能说明雇农状况的是他们的工钱:东家管伙食,每年挣二十到五十元”。(108) 因而,从1930年代末平北迥源头村雇工身份的转换中也可以观察到这种情况:贫农将地租出,自己去当雇工;中农变为雇工,而同时又兼为富农,即把他家的人抽出一人去做年工,而自己雇上一个半年工。(109) 同样,雇工转化为贫农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其经济地位的上升。(110) 所以,仅仅依凭“雇佣关系”恐不足以对乡村社会关系的性质作出有效的解释。因为,我们常常发现,本来是典型的自耕农(中农),只是由于劳动力短缺成为“其使用雇佣劳动的主要原因”,从而使得这些“中农向富农的发展,也只是在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经营方式的某种改变,而在经济上并没有新的扩大”。(111) 20世纪初期,乡村雇工是一个正处于急剧演变之中的、尚未形成相对独立阶层的一个社会群体。
其次,雇工与雇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构型复杂,“地富—雇农”的“两极化”阶级关系模式并不足以反映当时乡村社会关系的实况。事实上,雇佣关系并不仅局限于地主富农之间,雇农常常“被雇用于自作农与佃农”。(112) 作为乡村社会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雇农全部“分寄附于地主及自作农两方面”。虽然,大地主雇工自种比较普遍,但“自作农家田产稍多的尽有常年男妇雇一两个或两三个不等,有许多雇农都从佃农中招雇来的”,也正由于这层关系,要精确制定乡村农户分配的比例,“事实上也很不容易”。(113) 自作农的雇工经营既是乡村雇佣关系普遍化,也是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的符合逻辑演化的历史进程:“自作农所有之田,不能悉数耕种,势非用雇工不可,故大半雇农,为自作农所雇。”所以“自作农与雇农有密切之关系,……此种自作农,未有不用雇农者。”(114)
在山西中部一些地区,所谓雇工经营的“地主”,其实是缺少男性劳力的小户人家,甚或是大的佃户:“做地主的差不多是男人出外营商或是只有女人小孩子的小户农家,而承佃者的,反而是当地的大地户。”(115) 而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江苏松江地区。(116) 因此,由雇工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两极分化”的阶级对立情势,“一般地看出来,租佃关系——地主与佃农的对立形势,在当地是非常模糊的”。(117) 因为,不仅“雇主待遇雇农,极为平等,与奴仆绝异”,而且在“自作农与地主,无严格之分别”。(118) 雇主与雇工之间阶级的判别既不分明,虽然不免有当时乡村调查者主观认识的迷失,但其阶级鸿沟尚未出现明晰分野,恐怕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故自作农有或为地主,有或为雇农。雇农有或为自作农,有或为佃农。佃农的或为自作农,有或为雇农。”(119) 因而,由雇工而发生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多重复杂的网状构造,而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结构。诚如时人所析:“农民这不过是笼统的名词,他们正可以分为地主,自作农,佃农,雇农四个区别。在地主方面,多属于殷富的人们和大资本的商人。雇农,则属于自作农和佃农的范围下工作”,并与地主、自作农、佃农以及地主兼自作农、佃农兼自作农直接发生关系,成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交结点。(120)
因而,“雇农对于他们的雇主”虽“也有一种苦处”,却“没有阶级的裂痕”。(121) 甚至,传统社会里雇工家庭的子弟也曾有“受地主的栽培读书”而成为举人的。(122) 至少,“在这里底雇佣关系中,现象底复杂混乱,确是难以把握,易入迷途”。(123) 主雇之间阶级的分层和对立冲突并不十分明晰。如此,作为地方士绅的刘大鹏对于曾离开自家已十余年的雇工的“出葬”也颇在心,谓“适遇出葬,即行送丧”。(124) 有些长期受雇的老长工,“曾换得了主人家的微薄优待,吃饭和家人一样,不另外做”,以至于“老长工的心意曾和主人的心意一样无二致”。(125) 乡村社会发生的雇佣关系,其实是一种多重身份、地位和角色交叉的网型构造,呈现了利益与情感原则并重的运行特征:“雇工有戚谊者,论戚谊,无戚谊者,家长对雇工称名,雇工对家长或叔或伯或兄之,视年岁为定,衡无贫富阶级,亦无主仆名分,故相交以诚。”(126) 主雇之间“有理由或双方感情不和时,可以随时解退”。(127) 在这里,“互惠准则和生存权利”同样“坚实地蕴涵于农民生活的社会模式”中,“而这些社会模式将其力量和延续性归之于农民能够施加的道德认可的力量”。(128)
20世纪前期之山西乡村社会,被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导向的社会变迁牵引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乡村雇工群体生活状况的劣化只是整个乡村社会变动过程中的一个面相而已。但这个面相事实上又与乡村社会诸多关系相交融、相胶合,其复杂多重的社会关联昭示出这个时代演变的基本特征。对于雇工群体的时代性认识,有必要置于当时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事实中进行研究。而“社会分化不充分”既是雇佣关系普遍化和雇工身份非固化的导因,也是雇工群体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阶层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刘克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雇佣劳动数量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钞晓鸿:《本世纪前期陕西农业雇佣、租佃关系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61页。
③ 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内山雅生:《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李恩民、邢丽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 祁之晋:《“土地村有”下之晋北农村》,《国闻周报》第13卷第11期,1934年3月,第24页。
⑤ 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4页。
⑥ 祁寯藻:《马首农言注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⑦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
⑧ 汪适夫:《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江苏靖江》,《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第119页。
⑨ 《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第200页。
⑩ 史志宏:《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50页。
(11) 许涤新:《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第45页。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327页。
(13)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58页,转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63页。
(14)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省档案馆,1983年印行,第7页。
(15) 范彧文:《现阶段阳高农村经济的鸟瞰》,《新农村》第20期,1935年1月,第9页。
(16) 范彧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1935年5月,第8页。
(17) 《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第7页。
(18) 《黑峪口土地使用》,1942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A141—1—99—2。
(19) 《抗战以来阶级关系的变化》,《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942年7月,山西省档案馆,A137—1—3—1。
(20) 刘容亭:《山西高平、陵川、神池三县十六个乡村概况调查之比较》,《新农村》第9期,1934年2月,第9页。
(21) 西超:《河南农村中底雇佣劳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第68页。
(22) 周谷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0页。
(23) 《借货与押地》,《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942年7月,山西省档案馆,A137—1—3—1。
(24) 《土地占有与使用的分配和发展》, 《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942年7月,山西省档案馆,A137—1—3—1。
(25) 《统一战线政策材料汇集》,《晋西北的阶级》,1941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A21—3—37。
(26) 范彧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第13页。
(27) 吕梁地区方志编纂委员会:《吕梁地区志》第二编,经济(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
(28) 《为适当改善雇工生活促进雇工生产我们提议实行一五分红》,《晋西北区档案资料》,1942年,山西省档案馆,A88—3—23—3。
(29) 刘容亭:《山西高平、陵川、神池三县十六个乡村概况调查之比较》,《新农村》第9期,第9页。
(30)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9页。
(31) 《左权县工农青妇救国联合会大岩村雇工调查》,1943年4月,山西省档案馆,A7—1—12—9。
(32) 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史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442页。
(33)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8月,第365页。按,山地以垧计,读音如“赏”,农民书写时,或从“土”(垧),或从“日”(晌),按从“土”之意,以其为土地之名,而从“日”之意,说者以为含有每日需一个人工之意,即每人每日所工作之土地面积为一垧也。每垧亩数在各地不同,或即因各地每个人工每日所工作之亩数不同也。山西西北部土地贫瘠,若一律以亩计算,则相差甚远,盖西北部农田一垧之产量,仅能抵他县一亩之产量。人工亦省,他处一亩所需之人工在西北一带即足以经营一垧。神池县农田面积,普通以五亩为一垧计算。
(34)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21页。
(35) 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李锡周编译,北平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第123、170、120页。
(36) 徐松荣主编:《近代山西农业经济》,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272页。
(37)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第333页。
(38)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771页。
(3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盂县委员会:《盂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第89页。
(40) 《盂县文史资料》第1辑,第89页。
(4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18年7月15日、1933年9月11日、1932年10月1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3、477、458页。
(42)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第332页。
(43)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
(44)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第334页。
(45) 费肼石:《雇农工资统计及其分析》,《内政统计季刊》第1期,1936年,第111—112页。
(46)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第362页。
(47) 《杨家坡雇工调查会记录》,山西省档案馆,A88—3—32—1。
(48)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第359、360页。
(49) 《雇工零碎材料》,山西省档案馆,A88—3—34—6。
(50)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第360页。
(51) 《雇工调查会记录》,山西省档案馆,A88—3—23—1。
(52) 《杨家坡雇工问题》,山西省档案馆,A88—3—32—2。
(5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6年3月29日,第322页。
(54) 《雇工零碎材料》,山西省档案馆,A88—3—34—6。
(55) 费肼石:《雇农工资统计及其分析》,《内政统计季刊》第1期,第110—111页。
(5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3年6月30日,第308页。
(57) 费肼石:《雇农工资统计及其分析》,《内政统计季刊》第1期,第108—109页。
(58) 《杨家坡村雇工问题》,山西省档案馆,A88—3—32—2。
(59) 范彧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第12页。
(60) 《任家湾底人口、劳动力、雇佣劳动》(四),山西省档案馆,A141—1—118—1。
(6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62) 《武乡县大有镇土地调查材料总结》,1942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A181—1—44—1。
(63)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第363页。
(64)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65) 《晋西北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材料汇集》,山西省档案馆,A88—3—32—3。
(66) 史志宏:《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55页。
(67)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80页。
(68) 《任家湾底人口、劳动力、雇佣劳动》(四),山西省档案馆,A141—1—118—1。
(69)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1页。
(70) 西超:《河南农村中底雇佣劳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第68页。
(71) 范彧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第14页。
(72) 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广州:国立中山大学,1933年, 第91页。
(73) 长野朗:《中国土地制度研究》,陆璞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第395页。
(74)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7页。弗里曼对河北饶阳五公村的研究表明,1936年时“有33个村民被雇作长工”,“95人被雇为短工,几乎全是自己有地的农户”。见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75) 李树青:《中国农民的贫穷程度》,《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1935年10月,第73页。
(76) 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伍丹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
(77) 侯建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中人口流动与雇工》,《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第60页。
(78)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页。
(7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331页。
(80) 秦晖、 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81) 章有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文中强调:“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以至二三十年代,200年间, 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地权分配比率,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见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90页。
(82) 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83) 杨木若:《山西农村社会之一斑》,《新农村》第2期,1933年8月,第5页。
(84) 据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所载各县部分村庄调查数据,平定、盂县部分村庄地主富农占地31.5%;灵丘、广灵等101个村地富占地为27.85%,晋西北兴县等9个县20个村为60.8%;太行区黎城、潞城等县123个村为20.24%;晋中祁县、太谷等5个县部分村庄为15.5%;晋南万泉、曲沃等4个县20个村为24.36%。详见该书第8卷第555—556页。
(85) 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第42、43页。
(86) 张闻天:《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87) 《各阶层每户生活变化举例》,《晋西区党委统一战线政策材料汇集(二)人民生活负担》,1941年,山西省档案馆,A22—4—2—1。
(88) 范彧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第21页。
(89) 《中共晋西区党委兴县实验支部赵村的了解》,1942年1月,山西省档案馆,A22—1—4—1。
(90) 《晋西区党委统一战线政策材料汇集(二)人民生活负担》,山西省档案馆,A22—4—2—1。
(91) 《武乡县东沟群众生活概况对敌斗争》,1941年,山西省档案馆,A181—1—36—1。
(92) 凉农:《山西寿阳县燕竹村的枯竭景象》,《新中华》第2卷第9期,1934年,第78页。
(93) 荫萱:《山西中路农村经济底现阶段》,《中国农村》第2卷第11期,1936年,第74页。
(9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35年12月25日,第491页。
(95) 马松玲:《敬告十年建设计划诸君》,《新农村》第6期,1933年,第1页。
(96)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第7卷,第238页。
(9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35年9月18日,第477页。
(98) 关于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普遍贫困化”的致因,笔者将撰文另作研究。
(99) 《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942年,山西省档案馆,A137—1—3。并参见西超:《河南农村中底雇佣劳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第68页。
(100) 《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第2页。
(101) 董孝先:《海门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24页。
(102) 严促达:《湖北西北的农村》,《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45页。
(103) 孤芬:《浙江衢州的农民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56页。
(104) 范彧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第14页。
(105) 《一九四一年平北县合理负担总结》,山西省档案馆,A—191—1—39—1。
(106) 赵德华:《井陉农民生活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96页。
(107) 南方也有类似情况者,如江苏武进县:“七十万农民中,有自作农,自作农而兼佃农所谓半佃农,佃农及雇农等,界限既然不很清楚,即调查数目亦难于准确。”见《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江苏武进》,《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105页。
(108) 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109) 《一九四一年平北县合理负担总结》,山西省档案馆,A191—1—39—1。
(110) 如唐家吉村雇工原为4户,有两户因敌人扫荡无人雇用,转化为贫农,其生活反而受到影响。见《唐家吉阶级关系及其变化》,山西省档案馆,A141—1—118—2。
(111) 如1936年时唐家吉村两户中农因各有一子参军,劳动力紧张,前曾常雇短工,自去年起开始雇佣长工,就上升为富农了。见《唐家吉阶级关系及其变化》,山西省档案馆,A141—1—118—2。
(112) 《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安徽当涂》,《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143页。
(113) 董孝先:《海门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25页。
(114) 《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江苏武进》,《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106页。
(115) 张稼夫:《山西中部一般的农家生活》,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2编,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380页。
(116) 《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江苏松江叶榭乡》,《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该调查说:“需要这种雇农的,除非他们——自作农和佃农——田亩太多,自家不能照料照顾,或他们自家没有男人。”(第127页)
(117) 张稼夫:《山西中部一般的农家生活》,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2编,第380页。
(118) 《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安徽当涂》,《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143页。
(119) 巫宝山:《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江苏句容》,《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116页。
(120)(121) 《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安徽合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132—133、147页。
(122)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卷1,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123) 范彧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第12页。
(12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36年12月25日,第501页。
(125) 《杨家坡村雇主调查》,山西省档案馆,A88—3—32—3。
(126) 刘清如主纂:《馆陶县志》卷六《礼俗志·风俗》,1936年铅印本,转引自张佩国:《近代山东农村的土地经营方式:惯行描述与制度分析》,《东方论坛》2000年第2期,第85页。
(127) 《晋西北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材料汇集》,山西省档案馆,A—88—3—32—3。
(128)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德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