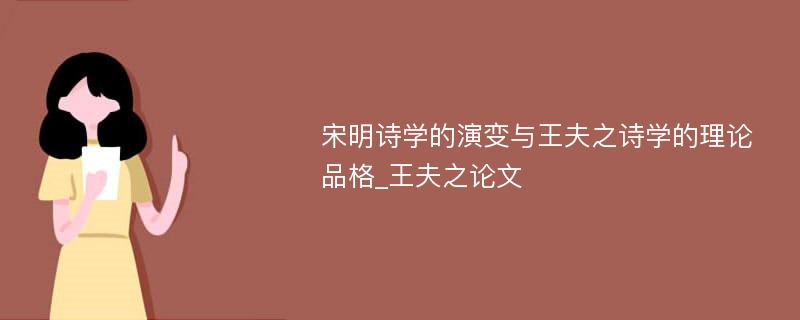
宋明诗学的流变与王夫之诗学的理论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品格论文,理论论文,王夫之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1-081-06
一、宋代主流诗学以理性为基点
宋代主流诗学是以理性为基点建立起来的,逻辑、知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的长足进展为前提,宋人保持和发展了对“理”的持续不已的兴趣。所谓“理”,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思想,具体化为“诗以意为主”的命题;第二个层面指日常情理,即以常识去解读诗中的描写;第三个层面指与思想相关的表达方式,如以议论为诗,将文法推广到诗法等。
“诗以意为主”代表了宋代主流诗人的基本诗学理念。刘攽《中山诗话》云:“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云:“陈无己先生语余曰:‘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余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谒玄元皇帝庙》诗,叙述功德,反复外意,事核而理长;《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赠蔡希鲁》诗云:‘身轻一鸟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诗云:‘蕊粉上蜂须’,功在一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像之乎?’”(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诗以意为主”,由此出发,对“识”的强调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范温《潜溪诗眼·渊明出处》从见地超迈过人的角度“发明”苏轼《和贫士诗》的内涵,并认为这是该诗美感魅力的基本来源,体现了宋人评诗的特色。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李白识度甚浅》之评李白诗,亦着眼于识见之高下。
理性精神不仅与“识见”相对应,还与实证精神相对应。重“识见”,乃着眼于思想的深刻、命意的超拔;重实证,则是以社会人生的具体经验去衡量诗中的情境是否合理。《王直方诗话·论杜诗者之误》云:
范蜀公云:“武侯庙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参天二千尺’,古之诗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围,乃是七尺,而长二千尺,无乃太细长乎?”余以为论诗正不当尔,二公之言皆非也。[1](P86-87)
尽管王直方批评了范、沈二公,但范、沈二公的解读方法却正是典型的宋人家数。《艺苑雌黄·欧阳修词山色有无中》:
欧阳永叔《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为永叔短视,故云“山色有无中”。东坡笑之,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盖山色有无中,非烟雨不能然也。[1](P569)
欧阳修在平山堂望江左诸山而有“山色有无中”之感,究竟是因为作者“短视”,还是因为自然界的“烟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体现出的正是对实证的兴趣。宋人试图用实证知识来照亮感觉和鉴赏力。
重视命意,重视“识见”,重视可以实证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之相应,在表达上便形成了以议论为诗和借鉴文法等特点。如范温《潜溪诗眼·山谷言诗法》:
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此概考古人法度,如杜子美《赠韦见素》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皆儒冠事业也;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言误身如此也,则意举而文备,故已有是诗矣。然必言其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谓传诵其诗也。然宰相职在荐贤,不当徒爱人而已,士故不能无望,故曰:“窃笑贡公喜,难甘原宪贫”;果不能荐贤而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祗是走踆踆”,又将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迟迟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所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于江湖之外,虽见素亦不得而见矣,故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终焉。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1](P323-325)
范温曾从山谷学诗,他从那儿得到“文章必谨布置”的教诲,便用以分析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诗,可见山谷所说的“文章”是包含诗在内的。在黄庭坚那儿,“诗法”服务于诗的“立意”,显然是在诗的写作中借鉴了唐宋古文的章法。而就诗的传统本身而论,杜甫诗亦以有法则可循著称。如《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也说:“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
综合上面的考察,我们的结论是:宋代主流诗学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推理精神和实证精神共同体现了理智的力量。在相当一部分宋人的理念中,理智力量被视为诗的真正驾驭者,而不仅仅是哲学和科学的驾驭者。理智与诗密切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有时以感受作为中介,有时不以感受为中介。一部分宋人如邵雍甚至认为,理智可以直接转化为诗。理智在诗的领域中大行其道,成功地培育出了宋诗的品格:以思理筋骨见长,而不以丰神情韵取胜。诗人的精神活动被尽可能地限制在理解的范围内。至于“以文为诗”,则是理性精神在艺术表达上的体现。
二、明代主流诗学推崇经验规则
与宋人推崇理性有别,明代主流诗学关注的则是有关诗歌创作的经验。经验规则取代理性规则,其表征是对前人艺术实践的信任,就七子派而论,他们信任的是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的艺术实践。前七子盟主李梦阳相信,汉魏和盛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遵循了某种艺术法则,尽管其作者也许未能明确地意识到;后人如果想揭示或制订规则,就必须具体地考察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从中发现秩序并遵循这种秩序,企图任意行事或另起炉灶是不成的。他在《答周子书》中指出:“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李空同全集》卷六十一)他的意思是:法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内在规律,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其不可违背的“法”即规律;这种规律完美地体现在“第一义”的典范作品中,因此,在创作中必须严格地仿效前人的经典之作。以对创作经验的尊崇为出发点,李梦阳热心于从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中归纳技巧,以这种技巧来指导创作。其《再与何氏书》云:
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沈约亦云:“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即如人身,以魄载魂,生有此体,即有此法也。《诗》云“有物有则”,故曹、刘、阮、陆、李、杜能用之而不能异,能异之而不能不同。(《李空同全集》卷六十一)
所谓“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这实际上是一些经验标准,尽管李梦阳认定这是“物之自则”——事物内部所固有的规律。所以,如果说宋人以推理和实证来实行其理性原则,李梦阳等则是以经验标准取代理性标准:他们首先选定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为诗的模特儿,然后从模特儿身上发现规则。他们用经验规则取代了理性原则,习惯和传统构成这些规则的基础。
在对经验规则的考察中,明代主流诗学提出了两大重要命题。其一,诗“贵情思而轻事实”。李东阳《麓堂诗话》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里应该郑重指出,“情思”包含了“情感”,但其含义又非“情感”二字所能取代,因为,它同时还强调了感觉和音乐效果。“比兴”与“情思”的联系指向对诗人感觉的关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与“情思”的联系则表明情感、情绪与音乐相通,一旦进入诗的情感和情绪氛围,同样有聆听音乐时那种迥肠荡气的感受。李东阳的这一创获,李梦阳显然也是认可的。李梦阳在《缶音序》中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这里,李梦阳不是以“情”作为“理”的对立面,而是以“调”作为其对立面,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用法。“情”是多层面的,理学家也有理学家的情。但“调”却强调“感触突发”,由此导向对感觉和意象的捕捉;强调“流动情思”,“其声悠扬”,由此导向对诗的音调节奏的关注。“情思”同时关涉文学语言和音乐语言,“情思”与议论事理和铺叙事实是格格不入的。并且,从诗与作者的关系看,所抒之“情”是可作伪的,即所谓“心画心声总失真”。但所表达的“情思”,却是不可作伪的,因为,诗人的创作个性、创作风格无法矫饰。对此,李梦阳所见甚为真切。他在《林公诗序》中说:“夫诗者,人之鉴者也。夫人动之至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律,律和而应,声永而节。言弗睽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故诗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气,平言者未必平调,冲言者未必冲思,隐言者未必隐情。谛情、探调、研思、察气,以是观心无廋人矣。故曰诗者,人之鉴也。”“言”不由衷是可能的,如热衷功名的人故作清高之论,性情怯懦的人故作豪勇之语;而“调”、“气”等则属于个性和风格范畴,是不能作假的,这些才真的是“人之鉴”。李东阳、李梦阳等人用“情思”而不用“情”来作为建立诗学的基础,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沟通诗、乐,另一方面又将诗与史区别开来,“史”强调的是“事实”,诗关注的则是“情思”。[2](P334)
其二,作诗“不可太切”。中国古典诗学中有“辞不尽意,意在言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说法,这里的“意”,不是与逻辑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意义”,而是富于情绪色彩的“意绪”。诗人的意绪,尤其是那些源于自由感觉的“意绪”,如弥漫的烟雾,如“梅子黄时雨”,要加以清晰的界定和阐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完整地传达这种意绪,就应尽量避免涉于理路,就应尽量向读者提供含蕴丰富的意境,“排除思想分析而直入世界内部的特征”。由此出发,明代主流诗学反复强调:诗的表达不必“太切”,因为“太切”就意味着作家有明晰的“意图”。谢榛《四溟诗话》说:
诗不可太切,太切则流于宋矣。(卷二)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说:
杜题柏:“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说者谓太细长,诚细长也,如句格之壮何!题竹:“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说者谓竹无香,诚无香也,如风调之美何!宋人《咏蟹》:“满腹红膏肥似髓,贮盘青壳大于杯。”《荔枝》:“甘露落来鸡子大,晓风吹作水晶团”,非不酷肖,毕竟妍丑何如?诗固有以切工者,不伤格,不贬调,乃可。
“诗言志”是中国诗学中的一个经典说法,在宋人的主流阐释中被理解为诗以作品所包含的作者意图为主。在这种言志观念笼罩下,文学批评强调的是“文以载道”的“道”、“有德者必有言”的“德”、“内容决定形式”的“内容”,强调的是作品背后的“意义”、“主题”、“中心思想”。宋人视野中的“诗言志”原则强调:诗歌是诗人思想感情的流露、表达或形象的写照。或者换一个说法,艺术作品实质上是把内在的变成外在的,它同时体现了诗人的知觉、思想和感情。所以诗的渊源和题材,是诗人自己的精神素质和内心活动;如果外部世界的某些方面,在诗人的感情和内心活动作用下,从事物转化成诗,那么它们也能成为诗的源泉和题材。由这一理论产生的评价诗歌成败的标准是:它与诗人在写作时的意图、感情和真实的思想状态相符吗?这种理性原则在“不切”论中被明确地放弃了。[2](P267-286)
作诗“不可太切”,就与外在景物的关系而言,旨在否定宋人的实证精神。在诗的写作中,为了获致某种韵味,诗应该或可以摆脱事实的束缚。中国的文人画努力达到忽略外在细节描写而捕捉事物气象、神韵的境界,明代主流诗学也追求和认可这样的境界。
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着眼于确定诗的体裁规范,作诗“不可太切”着眼于确定诗与志、诗与景之间的关系。这两大命题是从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的经验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明代主流诗学具有“常识”诗学的特性。它立足于写作经验,与立足于理性精神的宋代主流诗学形成对比分明的两极。明代主流诗学所确定的统系,旨在恢复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的传统而摒弃宋代主流诗学,其统系选择不是为了深化学术,而是为了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的创获为后人研究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提供了值得珍视的学术资源。
三、超越理性和经验:王夫之诗学的理论品格
讨论王夫之诗学的理论品格,必须明了一个前提,即他的思考常常是针对宋代主流诗学和明代主流诗学的弊端,并致力于扭转这种弊端。王夫之在宋、明之后建立他的诗学体系,其理论思维首先着眼于宋、明主流诗学的失误。在他看来,理性诗学对逻辑和思想的兴趣有悖于诗的本性,诗不是以逻辑、思想作为基本立足点的。经验诗学热衷于从经验事实中总结法则,如一情一景、起承转合之类,王夫之也认为过于拘泥,乃是作茧自缚。王夫之对明代主流诗学的失误,感受尤其强烈,因为他本人就在一定范围内参与了明末诗坛的活动。他意识到,经验诗学所认定的种种技法、规则都只是前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果,一旦我们从经验形式回溯到其形成力量,一旦我们的注意力从事物是什么转移到事物何以如此,技法和规则的神圣性便烟消云散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虽然反对理性诗学和经验诗学,但理性原则和经验规则所注重的“意”、“议论”、“情”、“景”、“音律”等在王夫之的诗学理念中依然是构成诗的要素。王夫之的诗学理念是超越理性原则和经验规则,以直觉来支配诗中的各种要素。王夫之推崇审美直觉,不承认我们非得在理性原则和经验规则中二者择一不可;他致力于克服理性原则和经验规则的冲突,并把审美直觉置于超越这种冲突的优越地位。对美的直觉可以驾驭理性和经验。王夫之郑重地将佛学的“现量”概念引进诗学领域: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第五则)[3](P52)
佛家法相宗认为心与境的关系,有现量、比量、非量三种差别,王夫之《相宗络索》“三量”条云:“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量”指知识。“比量”是经由逻辑思维所获得的知识,“现量”是“不假思量”直觉到的知识。王夫之将“现量”概念引进诗学领域,表明他对感受的直接性异常重视:所谓“寓目吟成”(《古诗评选》卷一斛律金《敕勒歌》评语),所谓“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唐诗评选》卷三张子容《泛永嘉江日暮回舟》评语),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第七则),均旨在强调直觉的作用。
直觉与感受的直接性是相互对应的。而感受的直接性需要两方面因素的凑泊,一方面是当事者的“情”,另一方面是当事者所面对的“景”。“情”是“心中”所有,“景”是“目中”所见,“心中”之情与“目中”之景,二者相“触”而产生诗,这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初非想得”,“不在刻意”。由于直觉同时关涉作者与外在世界,情、景二者在诗人的直接感受中总是密不可分、丰富多彩、不能用经验法则来加以限定的:
“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日暮天无云,春风散微和”,想见陶令当时胸次,岂夹杂铅汞人能作此语?程子谓见濂溪一月坐春风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薑斋诗话笺注》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第四则)[3](P50)
“所怀来”即“心中”所有的“情”,每个人的“胸次”有高低之别,故即使面对同样的“景”,其感受也不相同。美不是事物的属性,而仅仅是事物与感受它们的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关系有别,则同是一景,亦意味不同。故写诗时只能遵循直觉,而不能拘于“一情一景”之类的经验法则。直觉世界的情景比经验法则中的情景更富魅力。审美并不源于纯粹和无色彩的思维,也不源于经验法则,它需要对比,需要明暗的分布,一句话,需要感受。任何理性原则和经验法则都取代不了直接的印象。
王夫之反对以逻辑思维介入诗的创作,并非摒弃思想和知识,而是说,直觉可以涵容思想和知识(“理”):
不许文人,不许理人,文人无此心宇,理人无此心旌也。只“水光流素寒”五字,令黄山谷、陈无己无处挂羚羊之角。(《明诗评选》卷四许继《拟远游篇》评语)[4](P1287)
“文人”指拘守经验法则的明代主流诗人,“理人”指拘守理性原则的宋代主流诗人;他点名批评黄庭坚、陈师道,锋芒所向,主要是“理人”;否定“理人”,又旨在否定拘于“名言之理”的人,并非否定“理”本身,因为诗人凭直觉也可以把握到“理”。“桃之夭夭,其叶蓁蓁”所体现的“物理”(《诗绎》第八则),谢灵运诗中的“思理”(《诗绎》第一四则),“钟声扣白云”所隐含的“名理”(《唐诗评选》卷三綦毋潜《题灵隐寺山顶禅院》评语),都不是以逻辑方式演绎出的“名言之理”,而是在诗的境界中呈现出的理。所以王夫之强调:一方面,诗不能说理,另一方面,诗人不能没有“名理”的涵濡,否则,“非理抑将何悟”?王夫之在一种比较朴素的意义上看待理性。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的体现事物绝对本质的东西,它只是一种后天获得物而不是遗产。理性不再被视为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被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
王夫之对“意”的态度与他对“理”的态度是相互照应的。他明确反对“以意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法为诗。但是,他并不否定“意”,并且再三指出“意”在诗中的统帅地位。王夫之笔下的“意”字,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含义。《明诗评选》卷八高启《凉州词》评语批评“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4](P1576)这里的“意”指的是思想、意图、议论;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第三则“以意为主”之“意”,则指作者凭直觉把握到的“思想”,一种富于诗意的感受。这种感受,与作者的“名理”涵养密不可分,但又不能混为一谈。其差别在于,“名言之理”是逻辑思维所把握到的“理”,部分宋人致力于阐释这种理,所以是失败的;“以意为主”之“意”则是直觉所把握到的“理”,它只能呈现出来,而不能演绎出来。诗以呈现为其基本生存方式,而呈现须以作者的直接感受为主,即以直觉所把握到的意为主。“意”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经验,它包括感觉、反省等多种形式。故王夫之论谢灵运,既说他善于“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又说“情景相入,涯际不分,振往古,尽来今,惟康乐能之”(《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评语)[4](P1730)二者其实是同一命题。“尽其意”即“尽”其心理经验,心理经验是“情景相入”的产物,“意”与“情景”遂贯通起来了。王夫之称“情景相入”所产生的心理经验为“意”,旨在强调“名理”涵濡的重要性。他反对以“名言之理”为诗,但又重视诗人的人格陶冶。当王夫之宣称“意犹帅也”之时,他并非用“意”来指理论知识,或指能被还原为确定的逻辑规则和具体概念的命题、判断。以他之见,“意”与世界的内在理智结构对应,对这种结构,无法单凭概念去认识,也不能经由对个别经验的归纳加以把握,而只能直接经验,用直觉去把握。在这里,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消失了,理性原则和经验法则的对垒消失了,一切秩序和规律性,都统一在审美直觉中。如果说理性原则和经验法则还有变化,人类的审美直觉能力却始终大体保持不变。它比理性原则与经验法则更为可靠。
感觉现象是王夫之关注的焦点。他不想超越感觉现象去讨论诗,去讨论诗的依据。他不满于理性原则,因为理性原则是轻视感受、压抑感受的;他也不满于经验规则,经验把诗人的活动局限于为诗的创作定出技术规则,局限于就艺术作品对观赏者产生的影响作心理学的考察,同样是忽视感受的。在王夫之看来,诗人能够直觉到理性,而其感受的自然表达即是不可更易的规则。他并未背离理性和经验,他只是超越理性和经验而已。凡存在于理智中的,无不先存在于感觉之中。
收稿日期:2003-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