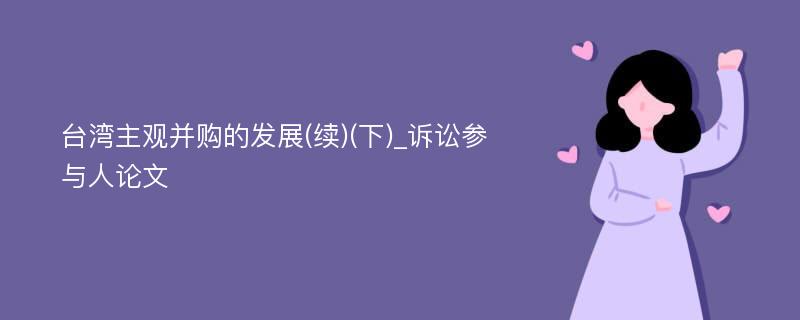
主观合并之诉在台湾地区的发展(续)(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主观论文,地区论文,在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肆、检讨
一、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应否准许?依本文资料显示,在实务上显仍有纷歧。虽“最高法院”迄今只有采肯定见解的案例而无采否定见解之案例,但一、二审则呈现肯定说及否定说案例杂陈的情况,此不但会一再出现法院裁判歧异之现象,且颇为不公平。盖在一、二审如原告幸而遇采肯定说之法官,则可利用此一形态之诉讼制度并获“最高法院”之支持,如遇采否定说之法官,于一审遭裁定驳回后,抗告二审再遭驳回即告确定,而无再抗告至“最高法院”之机会,致使原告无法利用此一形态之诉讼制度,此观案例八及案例九即明。尤有甚者,以案例七为例,原告洛克公司于1988年对先位之民航局及后位之中信局提起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第一审即认先位之诉无理由而就后位之诉为审理并裁判,历经第二审、第三审均不否定后位之诉之合法性,在当事人就实体缠讼近5年后,二审法院忽于1993年为更(一)审判决时, 宣称“应认就现行法规定,难以承认此种诉讼形态,法院应以后位之诉请求为不合法,而驳回之。”将第一审就后位之实体判决废弃,改判后位之诉驳回,使两造即洛克公司及中信局近5年诉讼,归于徒劳,其情何以堪? 人民对司法之观感又将如何?因此,关于肯定说、否定说在实务上之争论,实应尽速解决而求其统一,不可再任其争论不休。否则,被牺牲的是人民的权益及司法的公平及信誉。此所以笔者于本文“前言”,对于司法院民诉法研修会第429次会,就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所做成“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仍留待实务上运作,暂不增订条文”之决议,提出质疑之原因,亦为笔者撰写本文之主要动机及目的所在。
二、至于究竟应否准许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正反两说各有所据,论者已多,本文不拟就两说论点再事论述。兹欲检讨者,有如下几点:
(一)依主张肯定说者所见,承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有诸多利益,诸如防止裁判冲突、有利于统一解决纷争、符合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原告陷于自相矛盾窘境、保护原告实体法上之权利(包括免罹于消灭时效)、防止被告推诿责任、有益于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功能等,此等利益,一般言之,采否定说者亦多不否认。而否定说所指谪者,主要为:1.被告地位不安定;2.因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之适用,先后位诉讼时有难始终维持合并审理情形,致裁判亦无法达到统一。(注:以上参阅本文所介绍各学者论文。)惟吾人似应思考:
1.如案例四、五、八为多数原告之主观预备合并,乃由先位及后位原告协同定其顺序而主动提起,其有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利益无庸置疑,至后位原告地位之可能不安定,乃其预先了解评估后自愿选择者,吾人何以反其意愿,谓顾虑其地位不安定而不准提起?或谓此时所考虑者非后位原告,乃后位之诉之被告,就后位之诉之地位不安定,故不准提起。惟后位之诉之被告,因其亦为先位之诉之被告,势必始终参与诉讼,纵就后位之诉言,非全无地位不安定之问题,然其情形,应与客观预备合并中后位之诉之被告相同,既许提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主观预备合并又何不可?
2.如案例七为多数被告之主观预备合并,原告本于契约有所请求,先后位被告均一致主张后位被告始为契约当事人,认先位被告非适格当事人,后位被告始为适格当事人,应就后位之诉裁判。故后位被告对原告提起预备诉之合并,始终无异议。如此情形,被告地位安定之考虑,是否仍应优于承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利益考虑?显可置疑。此所以“最高法院”1993年度台上字第2961号判决认:“须待当事人提出抗辩,法院始得加以斟酌,如当事人不提出抗辩,……为求诉讼经济,法院似无依职权加以斟酌,并驳回当事人后位之诉之必要。”之道理。
3.纵如案例六,后位被告抗辩主观预备诉之合并不合法,后位被告地位不安定之考虑,是否即可压倒承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利益,而构成否定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存在价值之足够理由,亦非无疑问。盖:
(1)防止裁判冲突、统一解决纷争、求取诉讼经济、 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功能之利益,不但属于原告及被告,且此亦属公益,(注:参见前揭邱教授文。)此等利益考量,应超过被告地位不安之利益考量,何况,被告地位不安之不利益,如后所述,并非毫无减轻甚至完全消除之可能。事实上,为求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相牵连之数纠纷,以符诉讼经济原则并避免裁判结果之不一致,“使法院对当事人之同一法律关系得为相同之裁判,而树立司法威信。”司法院民诉法研修会已决定就民事诉讼法增订第259条之一采行强制反诉制度, 规定被告在一定情形下应提起反诉,否则,除被告陈明保留另行起诉之权利或有第260 条第一项不得提起之情形外,不得更行提起独立之诉。(注:参见1992年12月司法院印“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初稿条文暨说明”第241页至243页。)依此立法趋势,益可说明不可因后位被告地位不安定之理由,否定承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上述利益。
(2 )在客观预备合并之情形,原被告虽为同一,但就后位之诉言,被告之地位,因后位之诉是否受裁判尚不安定而亦不安定,其情形与主观预备合并之后位之诉相类,只是程度容有不同而已,今既可接受客观预备合并之不安定,何不可接受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4.至于先后位诉讼时有难始终维持合并审理情形,固属问题,惟先后位诉讼维持合并审理之情形,仍属甚多,如案例四、案例七即属之,似不应因噎废食,以零和之论断方式,谓因未能完全确保先后位诉讼之始终合并审理,而否定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存在价值。何况,非不可能从解释上甚或立法上限制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之适用,尽量增加先后位之诉合并审理之机会。
(二)如上分析,主观预备合并有如客观预备合并之诉,毕竟为利较多弊较少之制度,且此制度非只存在于学说,在实务上,它确已存在且在运作发挥机能之中,何可轻言“禁止”?吾人似应努力于如何设法从解释上甚或借助立法,使此一制度发挥其积极功能而减少其消极弊害。至于是否应以后位被告同意为限?基上说明,笔者采否定见解。
三、由于现今实务上肯定及否定之判决杂陈,似应早日统一而采肯定见解,使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得以在我国继续发展。此实有赖实务界及立法之努力也。
伍、建议
一、关于是否准许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争论,最直接之解决方式为立法。惟主观预备合并之诉问题甚多,立法贵在简明,自不宜亦无法以简明条文解决诸多繁杂问题,故在立法技术上,应选择最基本及最重要之原则事项,加以规定。基此,笔者建议先就下列事项加以规定,其他事项及问题,则不妨留待实务运作:
(一)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是否准许之问题,宜于法条中首先宣示予以肯定。
(二)主观预备诉之合并,是否限于其先后位之请求,于性质上互相排斥而不能并存者,始得为之?鉴于主观预备合并确有被告地位不安定等弊病,基于此制度边际效益之考量参以客观预备合并通说及实务亦以先后位请求须性质上互相排斥不能并存为必要,(注:参见“最高法院”1966年度上字第2090号判决(载于法令月刊16卷11期)及1976年度台上字第82号判例(载于司法院公报19卷1期。 ))笔者赞成将此条件列入。(注:参见前引陈教授文第149页。)
(三)认许主观预备合并之利益之一为裁判冲突之防止,有利统一解决纷争,除应明定就先后位之诉,法院不得为歧异之判决外,并应明定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准用之”。既规定为“准用”,而非一体“适用”,尚容留性质不合时可不予准用之空间。
(四)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最被指谪者,为陷后位被告于不安定之不利益地位,日本西村宏一之理论及陈荣宗教授之主张,认先后位之请求,不过为原告受胜诉判决之顺位而已,故法院必须同时就先位请求及后位请求为裁判。(注:参见前引陈教授文第147页至150页。)果如此,不但所谓被告地位不安定之顾虑,可以消除,且更可确保前述(三)之利益。(注:学者对西村宏一之理论亦有批评,认其说已不合向来预备合并之法律构成,且亦尚有诸多瑕疵。(详请见前引骆教授文第27页、第28页,吕先生文第35页、第36页)惟权衡利弊,笔者仍认其说有价值。)故可考虑明定法院应就先后位诉讼合并辩论合并裁判。
(五)认许主观预备合并之利益既在裁判冲突之防止,以利统一解决纷争,应明定就先后位诉讼之裁判,不得歧异。且如此规定,有助说明何以有“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准用之。”规定之必要。
兹试草拟条文如下: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须以先后位之请求互相排斥者为限,始得提起。
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于前项诉讼准用之。
第一项先后位诉讼应合并辩论及裁判之。
前项先后位诉讼之裁判,不得歧异。”
二、在实务界方面,尽早把“最高法院”1978年度台上字第1722号判决之前段要旨正式编为判例,以止息实务上肯定说、否定说杂陈之乱象,其内容为:“按在诉之合并之形态中,有所谓预备之合并,而预备之合并复有客观的预备之合并与主观的预备之合并之分。所谓客观的预备之合并,即同一原告预虑其对于同一被告提起之某诉(先位之诉)无理由,同时提起不能并存之他诉(预备之诉),以备先位之诉无理由时,请求法院就预备之诉审判。所谓主观的预备之合并,即在共同诉讼,或由共同原告对于同一被告为预备之合并,或由同一原告对于共同被告为预备之合并,前者原告甲预虑其对于被告之诉(先位之诉)无理由时,请求法院就原告乙对于被告之诉(预备之诉)审判,后者原告预虑其对于被告甲之诉(先位之诉)无理由时,请求法院就其对于被告乙之诉(预备之诉)审判。关于主观的预备之合并,实系法院依原告所为先位声明及预备声明定审判之顺序,本于民事诉讼法系采辩论主义之立法精神,尚非法所不许。”
陆、问题探讨
一、在现行法之规定下,是否可承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一)对此一问题,采否定见解者,(注:见前引王甲乙、杨建华文;案例七之台湾高等法院1991年度上更(一)字第311号判决、 案例八及案例九之一、二审裁定。)其所持理由约略为:1.后位当事人地位不安定;2.先位当事人与对造间之裁判,对后位当事人无法律上之拘束力,徒使后位当事人浪费无益之诉讼程序;3.因先后位之诉以互相排斥为必要,难认有合一确定之情形,无从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而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如此,亦无从达到先后位诉讼始终于同一诉讼程序合并审理,防止裁判冲突达到裁判一致之目的;4.况若有于第一审准许先位声明,而第二审改驳回先位声明,准许后位声明之情形,则实质上损及后位当事人之审级利益。
(二)惟吾人试以主观与客观预备合并做比较,就上述:1.之所谓地位不安之问题,于本文肆、二、(一)中已有所论列,说明不应构成否定说之理由,兹不复赘,以2.、4.两点论,就后位之诉而言,无论主观或客观之诉之预备合并,均同有此问题,何于客观合并即可忍受而主观合并即为不可?殊难有令人信服之理由!实则,主观、客观预备合并之最大差异点,在于3.之问题,亦即在主观合并之诉,有是否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5条之问题,而在客观合并则不生此问题。姑不论如后所述,在现行法规定之解释论言,非无可能类推适用同法(以下未说明为其他法律者,即为“同法”)第56条,以限制第55条之适用。即退步以言,不类推适用56条而只适用55条之规定,其不利后果亦不过先后位诉讼无从保证始终合并审理而已。但是:1.无从保证始终合并审理并非必然全皆不可能始终或虽非始终,但仍能维持相当程度之合并审理关系。易言之,先后位诉讼除在第一审必然可合并审理外,尚有可能到达二审甚或三审仍维持合并审理之关系,例如第一审认先位之诉无理由而就后位之诉为裁判,如判原告胜诉,原告对先位判决不服,而后位被告对后位判决不服均上诉第二审;或如判原告败诉,原告对先位及后位判决均不服,提起第二审上诉之情形是,此观案例七第一审判决先位之诉无理由而就后位之诉判原告部分有理由,部分无理由,而两造均就自己败诉部分,提起第二审上诉之情形,即足明之。既然如此,岂可以零和方式论断,只因无法百分之百确保始终合并而轻易否定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固有功能?2.就客观预备合并之诉言,亦不能确保先后位诉讼百分之百始终合并审理,例如:(1 )第一审判决原告先位声明胜诉而未就后位之诉裁判,被告不服上诉第二审,则后位之诉是否亦一并移审而可并受第二审之裁判?至今,无论学者或实务,似仍未有定见。学者中趋向采肯定说者有杨建华、吴明轩、姚瑞光、陈石狮(注:参见民事诉讼法研究会“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一)”杨建华教授报告“预备诉之合并在实务上值得研讨的几个问题”中关于第五问题之发言,见第183页、190至191 页、第199页、第203页杨建华教授部分,另参见氏著“民事诉讼法问题研析(一)”第232页至第234页。)。骆永家(注:见骆永家著《诉之客观的预备合并》一文(原刊于中兴法学第18期,收载于骆永家著《民事法研究Ⅱ》第89页起)。),采否定说者有陈荣宗(注:见陈荣宗著:《预备合并之诉》,法学丛刊第88期第62、63页。),实务上采肯定说者有“最高法院”1976年台上字第2274号判决(注:“最高法院”1976年台上字第2274号判决:“上诉人为原告,在第一审所为应受判决事项之声明,除先位声明,请求被上诉人交还系争机器外,并以预备声明,请求被上诉人给付价金347691元及其法定利息。第一审认上诉人之先位声明为有理由,而为被上诉人败诉之判决,固无就预备声明,再为审判必要,惟经被上诉人对于第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原审如认上诉人之先位声明为无理由,仍应就其预备声明进行审判,始为合法。乃原审认上诉人之先位声明为无理由,并未就其预备声明进行审判,迳将第一审判决废弃,改判驳回上诉人之诉,于法显有违背。”见司法院公报20卷1 期。)、同院1977年台上字第947号判决(注:“最高法院”1977 年台上字第947号判决:“民事诉讼法上所谓诉讼预备之合并, 系于先位声明有理由时,则即准许其请求之判决,如先位声明无理由,始就备位声明加以审判。故第一审法院就先位声明行为之判决,为全部终局判决,经合法上诉后,该诉讼事件,即全部生移审之效果。如第二审法院以第一审之判决为不当时,非就其备位声明予以审理判决不可。本件原审基于被上诉人之上诉,既认上诉人先位声明请求为无理由,而将第一审就此为其胜诉之判决予以废弃改判,乃又未就上诉人之备位声明加以审判,难谓非就已受请求之事项未予审判之违法。”见司法院公报19卷7期。)、同院1984年台上字第3981号判决(注:“最高法院”1984年台上字第3981号判决:“查本件第一审就上诉人之本位声明为上诉人胜诉之判决,而未就预备声明为裁判。但经被上诉人提起上诉,该预备声明应生移审之效力。原审如认上诉人先位声明为无理由时,仍应就其预备声明部分,加以裁判。”见裁判选辑四卷四期第88 页。 )及“最高法院”1984年8月16日第八次民事庭会议(注:“最高法院”1984年8月16日第八次民事庭会议决议:“关于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后位诉移审力之问题?采第二说:诉之客观预备合并,原告先位诉胜诉,后位诉未受裁判,经被告合法上诉时,后位诉生移审力,上诉审认先位诉无理由时,应就后位诉加以裁判;若后位诉同时经原审判决驳回,原告未提起上诉或附带上诉时,因后位诉既经判决而未由原告声明不服,上诉审自不得就后位诉予以裁判。本院1977年5月4日民事庭会议决议(二)应予补充。”见戴森雄编《民事法裁判要旨广编》第七册第1225页。);采否定说者有“最高法院”1978年台上字第2296号判决(注:“最高法院”1978年台上字第2296号判决:“所谓上诉移审力者,指上诉除有不合法之情形,应由原审以裁定驳回外,该诉讼事件于当事人不服声明之范围内,脱离下级法院移转盘属于上级法院,当事人就此所为之声明,不生诉之追加或变更而言,并非谓当事人未予声明,即自动移审于上级法院而应加以裁判。卷查上诉人既未就其在第一审所为之预备声明,在原第二审为任何声明,原第二审未予裁判,自不生违法问题。”见司法院公报二十卷十期。)、“最高法院”1982年台上字第3247号判决(注:“最高法院”1982年台上字第3247号判决:“上诉人在第一审系受先位声明之胜诉判决,被上诉人提起第二审之上诉,其效力自仅及于上诉人该先位声明部分。且上诉人在原审所具之答辩状,及到庭辩论,亦未附此预备之声明。原审未就其在第一审之预备声明为判断,于法尚无违背。”见前揭戴森雄编《民事法裁判要旨广编》第三册第2880页。);(2 )如第一审认先位声明无理由后位声明有理由,被告不上诉原告上诉,第二审法院得否就先位声明为实体上判决?又如得为实体上判决而认先位有理由时,未上诉之后位之诉是否亦移审而并受第二审法院之判决?此不但学者尚见解不一,(注:参见民事诉讼法研究会“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一)”杨建华教授报告“预备诉之合并在实务上值得研讨的几个问题”中关于第五问题之发言,见第183页、190至191页、第199页、第203 页杨建华教授部分,另参见氏著“民事诉讼法问题研析(一)”第232 页至第234 页。所示《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一)》杨建华教授报告关于第六问题之各位发言,另参见陈荣宗著:《预备合并之诉》,法学丛刊第88期第60页至第61页。)实务上亦尚无判决例可循。则何以在客观预备之诉,不因此成为否定其制度存在价值之理由,而在主观预备之诉,则成为否定之理由?似无使人信服之理由。基上说明,笔者认为在现行法之规定下,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如同客观预备合并之诉,虽非无待克服之困难问题,但既接受并承认客观预备合并之诉讼形态,自无拒绝承认主观预备合并诉讼形态之理由。
二、就现行法言,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是否可类推适用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一)预备合并之诉,其主要利益之一为防止裁判冲突,以利统一解决纷争,为达此一目的,有必要尽量使先后位之诉,始终维持先后位关系而并受审理。故在客观预备合并之情形,学者多主张先后位之诉讼,应避免将其分离,而应使其始终结合,并受审理,且不得为一部终局判决,(注:见参见民事诉讼法研究会“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一)”杨建华教授报告“预备诉之合并在实务上值得研讨的几个问题”中关于第五问题之发言,见第183页、190至191页、第199页、第203 页杨建华教授部分,另参见氏著“民事诉讼法问题研析(一)”第232页至第234页。所示研讨会中杨建华、吴明轩、姚瑞光、陈石狮等之发言;另参见骆永家著《诉之客观的预备合并》一文(原刊于中兴法学第18期,收载于骆永家著《民事法研究Ⅱ》第89页起)。)否则,就难以发挥预备合并之诉防止裁判冲突之功能。惟在主观预备合并因涉及共同诉讼,先后位当事人间如无从适用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势必依第55条之规定,适用共同诉讼独立之原则。果然如此,先后位诉讼除在第一审以外,随时可分离,不但导致后位当事人地位不安定之不利益,且因此而使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功能,受到限制,也因此,否定说乃有其立论之基础。而主肯定说者,亦体认此困难,而主张应适用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注:参前揭陈荣宗、吕太郎先生文。)
(二)在主观预备合并之情形,论者每谓先后位之诉既须相互排斥,无从视为一体,依其性质,不但难认为有合一确定之情形,且先后位当事人利害关系不一致,且属相反,有利不利,难予认定,因此,认为不应适用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注:参见《法学丛刊》第113期第113页,注1)骆文之注37。)惟:
1.先后位之诉因须相互排斥,在形式上利害相反,而难认有“合一确定”之情形,但以案例四、案例五、案例六、案例七、案例八为例,无论是原告多数亦或被告多数,先后位原告或被告,不但所主张之事实及理由均相同,且均委任相同之律师为诉讼代理人,为形式上利害相反之先后位当事人,统一为诉讼行为(即主张事实及理由)。可见先后位原告或被告,在“实质”上不但不相冲突对立,且显立于利害一致之协同地位。何况,如前所述,在案例四、案例五、案例八原告为多数之主观预备合并情形,必先后位原告事先协同定其顺序后,始能提起,何得谓其利害相反而无从视为一体?因此,所谓先后位之诉因须互相排斥,无从视为一体之说,似与此类型诉讼之“实证”情形不相符合。
2.关于共同诉讼人间之关系,系以第55条为原则,第56条为例外。虽第56条以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之各人,必须合一确定,为其适用之条件,而依“最高法院”1943年上字第2723号判例所示:“非在法律上对于各共同诉讼人应为一致判决者,不得解为该条之必须合一确定。”但是,何以有第56条之规定,以限制第55条关于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之适用?究其原由,实因在必要共同诉讼,诉讼标的对于各共同诉讼人必须合一确定,裁判亦必须合一,求其一致而不得有所歧异使然。就此而言,主观预备合并之先后位诉讼,既以“互相排斥”为必要,虽难谓系“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之各人,必须合一确定”,但正因“互相排斥”,法院就先后位诉讼之裁判,自亦不得冲突而有所歧异。易言之,就法院对先后位各共同诉讼人之裁判,不得有所“歧异”之点而言,实与必要共同诉讼相同。从而,纵谓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并不合乎“合一确定”之要件,不得谓系必要共同诉讼,但基于“不得歧异”之要求,仍应解为有类推适用第56条之必要。
基上说明,笔者赞同吕太郎先生前揭文中所做“应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6条之规定”之结论。
三、主张在立法上规定“先后位诉讼应合并辩论及裁判之”,其立论依据为何?
(一)预备合并之诉,应就先后位诉讼同时辩论,学者似无争论;(注:参见第114页注①所示研讨会杨建华、吴明轩、陈珊、姚瑞光、 李学灯等发言。另参第114页注③陈文第59页。)惟是否得合并裁判? 则无论学者亦或实务,均采否定见解,认先位之诉无理由为后诉裁判之停止条件,唯于法院认先位之诉无理由时,因停止条件成就,始得就后位之诉为判决,故如认先位之诉为有理由时,不得就后位之诉为裁判。(注:参见“最高法院”1959年台上字第187号、同院1960 年台上字第1535号判例。另参见前揭“最高法院”1978年台上字第1722号判决。)如前所述,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最被指谪者,为陷后位被告于不安定之不利益地位,且先位当事人与对造间之裁判,对后位当事人无法律上之拘束力,徒使后位当事人浪费无益之诉讼程序,以及第一审认先位之诉有理由而未就后位之诉判决,上诉第二审认先位之诉无理由而就后位之诉判决,有损后位当事人之审级利益等。然而,先后位之诉既以互相排斥,不能并存为必要,则在对先位之诉做判断之同时,亦已对后位之诉实质上做出判断,此观本文所举之前开案例,即足证之。从诉讼经济言,何不同时为裁判?如此可一举两得,发挥预备合并之诉防止裁判冲突以利统一解决纷争功能之事,何不为之?何况,如此亦可解决上述否定说所持之质疑。
(二)质疑者可能会认为在先位之诉有理由之情形下,如对后位之诉同时为裁判,无异就当事人未声明之事项为判决,参诸第388 条之规定,应非法所许。惟:
1.正如前述西村宏一之主张,先后位之诉之预备合并,自原告立场观之,仅得解为其所要求受胜诉判决之顺位而已,事实上,先后位之诉,乃系并列存在,既互相排斥,则为先位有理由判决时,势必驳回不能并存之后位之诉,此实符合原告提起预备合并之诉之本意,亦为其请求之真意所在。先以本文案例四、五、八原告为多数之主观预备合并为例,依先、后位原告之共同主张,均认后位原告并非契约当事人,先位原告始为当事人,有权依据契约对被告主张权利,因此求为先位原告胜诉之判决,只有在先位之诉无理由时,始退而求其次,求就后位之诉为后位原告胜诉之判决。故先位之诉无理由,乃为判决后位原告胜诉之停止条件,并非为后位之诉之判决条件。如法院审理结果,认先位之诉有理由,而同时把相排斥之后位之诉驳回,正符合先后位原告请求之本意,何必强解为系就未受请求之事项为判决?再以案例七、九被告为多数之主观预备合并为例,原告系主张后位被告并非契约当事人,先位被告始为当事人而应依契约负责,故请求先就先位之诉判决原告胜诉,只在先位之诉败诉时,始请求就后位之诉判决其胜诉。因此,就后位之诉而言,原告请求之本意,系以先位之诉败诉,做为其受后位之诉胜诉判决之停止条件,并非以先位之诉败诉,做为后位之诉之判决条件。故如法院认先位之诉为有理由时,同时就相排斥不能并存之后位之诉为原告败诉判决,正符合原告以预备合并方式起诉请求判决之本意,又何必强解为系就未受请求之事项为判决?实则,就上开案例之具体事例观察,原告之声明及陈述,并无任何所谓“以先位之诉无理由,为后位之诉判决之停止条件,以先位之诉之有理由判决确定,为后位之诉诉讼盘属之解除条件”之表示,则学者通说及实务,凭何而做此解释,并以此解释强加于诉讼当事人?如此,是否符合辩论主义及处分主义之精神?殊可质疑!因此,笔者不但赞同陈荣宗教授在其前述论文中所为“对于主观之预备合并之法律构造,必须放弃通说所谓附解除条件之说明”之见解,且主张应放弃通说所谓“以先位之诉无理由为后位之诉判决之停止条件”之说法,而建议改为:“以先位之诉无理由为后位之诉有理由判决之停止条件”。(注:在有立法明确规定之前,如依原告起诉之主张,其就先后位两诉之关系不明确时,审判长应行使阐明权予以阐明,如原告之意思确系以先位之诉之无理由,为后诉判决之停止条件,则可依传统通说及现行实务之方式处理,如其真意系以先位之诉之无理由,为其后诉胜诉判决之停止条件,则应不再依传统“解除条件及停止条件说”之方式处理,而应就先后位之诉,合并辩论合并裁判之方式处理。)
2.传统通说及实务见解,把预备之诉之先后位关系,解释为“以先位之诉无理由,为后位之诉判决之停止条件,以先位之诉之有理由判决确定,为后位之诉诉讼盘属之解除条件”,其不符合案例实证之检验,有如前述,且此种解释,亦不合乎诉讼之理论。盖原告有其诉权,被告亦有其诉权,此所以第255条第一项规定诉状送达后,非得被告同意, 原告不得将原诉变更;第262条规定,被告已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者, 非得其同意,原告不得撤回诉之全部或一部。如依传统通说及实务之停止条件及解除条件说之见解,就后位之诉而言,其既与先位之诉同时受审理,被告已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而终又不获实体判决,不但其地位不安定,且又置被告诉权于何地?就此而言,案例七中台湾高等法院1990年度上字第1062号判决,于认先位之诉有理由之同时,并就后位之诉为实体驳回之判决(详见该案例之说明(2)), 虽该判决其后为第三审所废弃,仍应予以肯定。
3.论者或谓如先后位诉讼均予裁判,实质上又与先后位之诉以单纯诉之合并方式提起,而由审判长定其审理顺序者(第198 条第一项)何异?实则,预备合并既有先位后位诉讼之别,且以先位之诉之无理由为后位之诉有理由判决之停止条件,准用第56条第一项之结果,使法院就先后位诉讼同时裁判而又不生歧异,不但尊重当事人之本意,符合处分主义,且足可防止裁判之矛盾冲突。反观单纯之合并,既无先后位之别,又不准用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较之预备合并之诉,自不符合当事人之本意,且无法发挥防止裁判矛盾冲突及统一解决纠纷之功能。
(三)诉讼行为,原则上不得附条件,各诉讼行为之间,互有密切关系,诉讼行为如附加停止条件或解除条件,其效力将陷于不安定状态,从而影响诉讼程序之顺进行及安定,导致诉讼程序之混乱及浪费。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依传统通说及实务见解,乃是例外容许附条件之诉讼行为,之所以予以承认,乃因其有防止裁判矛盾及统一解决纠纷等利益,但是,仍不免于因附条件而生之弊端。至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所以引起应否准许之争论,亦因把后位之诉解为系附条件之起诉,产生陷后位被告地位不安定之弊所致。如立法上规定“先后位诉讼应合并辩论及裁判之”,把先后位之诉的关系,解为“以先位之诉之无理由为判决后位之诉原告胜诉之停止条件”,而非“以先位之诉之无理由为判决后位之诉判决之停止条件”,并扬弃“以先位之诉之有理由判决确定,为后位之诉诉讼盘属之解除条件”之解释,自可解除预备合并之诉附条件之缺点及弊害,而回归诉讼行为不得附条件之原则。(注:“以先位之诉之无理由为判决后位之诉原告胜诉之停止条件”,乃是对法院判决其胜诉所附加之条件,并非就后位之诉之起诉行为本身附加条件,故于诉讼盘属之安定性及应受裁判之确定性,均无所影响,不但符合处分主义之精神,且亦符合诉讼行为不得附加条件之原则。)
四、如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做如本文建议之立法,将与现行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之学者通说及实务判例不相符合,应如何处理?
(一)无论是主观抑为客观之预备合并,皆为预备合并之诉,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尚涉及共同诉讼之问题,有如前述外,其余两者之性质及所遭遇之问题,基本上相同,因此,笔者认为两者之处理方式,基本上应使之相同。故如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以立法方式加以原则性之规定,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亦宜一并加以规定,使趋一致而无所扞格。果如是,笔者建议条文如下:
“预备合并之诉,须以先后位之请求互相排斥者为限,始得提起。
前项先后位诉讼应合并辩论及裁判之。
前项先后位诉讼之裁判,不得歧异。
第56条第一项之规定,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讼准用之。”(注:预备合并之诉,既然规定先后位之诉应合并辩论及裁判,仍称“预备合并”之诉,是否适当?称谓是否须修改?实则,后位之诉虽不再以先位之诉无理由,为其裁判之停止条件,但就原告立场而言,仍以先位之诉无理由,为其后位之一诉判决之停止条件,易言之,就原告获胜诉判决之立场言,后位之诉仍具“备位”之性质,故名称仍可继续沿用。)
(二)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在实务上案例甚多,处理之经验亦有相当之累积。故如认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继续留待实务运作发展,而仅先就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加以立法规定,继两者有所扞格,亦非不可。盖:
1.两者主要扞格之处,厥在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有“第一项先后位诉讼应合并辩论及裁判之。”之规定,此与通说及实务判例认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系以先位之诉无理由为后位之诉判决之停止条件,如认先位之诉为有理由,则无庸亦不得就后位之诉为判决者不同。则就客观预备合并之诉言,上开关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规定,乃系就主观预备合并之特别规定,并不当然适用于客观预备合并之诉。详言之,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仍不受上开规定之影响,而可依目前通说及判例之方式,继续运作发展。
2.如嗣后认为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运作,效果良好,则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仍可随时以变更判例或修法之方式,改依主观预备合并之方式处理。此于我国预备合并诉讼制度之发展,或有其助益亦未可知也。
五、先后位诉讼之请求不互相排斥者,是否亦得提起主观的预备合并之诉?从处分主义的精神来看,似应容许先后位诉讼之请求不相排斥之预备合并之诉,但是,处分主义原则与诉讼程序安定追求原则的冲突问题,在此应加以考量。
(一)依处分主义原则,当事人可自由决定其是否为诉讼行为,亦可自由决定其诉讼行为之内容。本此,原告提起后位之诉并附加其裁判之停止条件及诉讼盘属之解除条件,自无不可。然而,如此只强调处分主义原则,势将破坏诉讼行为不得附加条件之原则,进而破坏诉讼程序之顺畅进行及其安定,自非适当。预备合并之诉,依传统“条件说”,违背诉讼行为不得附条件及诉讼程序安定追求之原则,之所以仍例外予以承认,实因其有防止裁判矛盾及统一解决纠纷之“利”之故,此乃利害相权之结果,并非只强调贯彻处分主义原则之结果。因此,讨论预备合并之诉是否应予准许,以及应于如何限度内(是否以先后位请求“互相排斥”为限?)予以准许,不可仅以处分主义原则之贯彻为考量,尚应考量诉讼程序安定追求原则之维持等因素,权衡利害而求取平衡。
(二)从利害权衡观点考量,依边际效益原理,先后位请求在性质上互相排斥而不能并存者,最有提起预备之诉之实益,且此一实益之追求,应强于“附条件”之弊害,故在“互相排斥”之情形,应予承认预备合并之诉,已如前述,但是,在非“互相排斥”之情形,因其在裁判矛盾防止及统一解决纷争之实益,显然不如“互相排斥”之情形,其提起预备合并之诉之必要性,自亦显不如“互相排斥”者之殷切。“实益”如此淡化后,是否仍足以超越程序安定之需求,非无可置疑。
(三)在互相排斥之情形,依本文所见,先后位之诉应合并辩论及裁判,而且法院就先后位诉讼之裁判,不得歧异。如此,不但保存了传统预备合并之诉之“利”,且避免违反诉讼行为不得附加条件及诉讼程序安定追求之原则,而去除预备合并之诉之弊害。以观非互相排斥之情形,因先后位诉讼不互相排斥,似无要求合并辩论、裁判,以及裁判不得歧异之坚强理由。在“互相排斥”之预备合并之诉已获解决途径之前提下,是否仍应为实益已淡化而弊害依旧之“非互相排斥”类型之预备合并之诉,保留存活空间,显然是个疑问。
基上说明,先后位诉讼之请求不相排斥者,应解为不得提起主观预备合并之诉,较为妥当。
柒、结语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讼形态,有其特殊之功能及存在价值,虽其与客观预备合并之诉讼形态,同有其困难及弊病,有待克服,但吾人仍应肯定其存在,使其发挥固有功能,不可因噎废食,率尔加以否定。笔者希望,借由本文之检讨及建议,能早日透过立法及编入判例,解决实务肯定说及否定说杂陈纷乱之局,不但促使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在我国之稳定发展,且亦可藉此进一步检讨并改进目前关于客观预备合并诉讼形态之运作,使预备合并诉讼制度,得以在我国健全而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