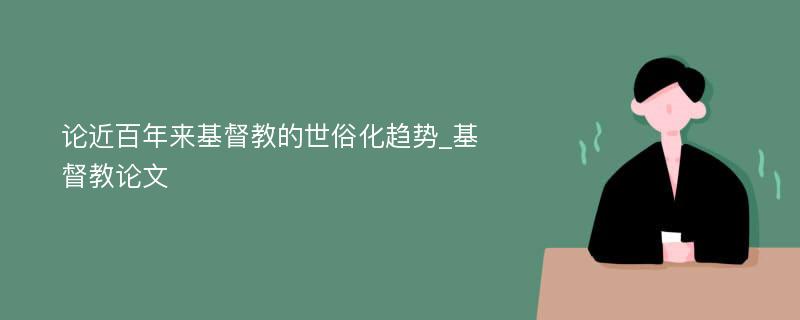
论近百年来基督教的世俗化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近百论文,世俗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纷争频起、流派众多的20世纪哲学思想领域,稍加分辨即可发现有这么一种值得探索的现象,人们试图对世纪之交遭到摧毁的基督教神学及信仰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亦即面对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的现实,希图从重新论证与确立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入手,找到人们的信仰依托和应遵循道德准则的根据。事实上,呈现这种基督神学体系人学化趋势,既可以视为思想家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神学的反思,在新形势下促进人——神关系和谐所作的努力探索,亦可以认为是西方布道士们为维护摇摇欲坠的西方文化,维护别具精神特质的西方精神世界所作的努力。
当然,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总是以双重属性而双重存在的。一方面,它具有自己相对的封闭性与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又总是根植于现实时代,受制于各种历史因素,并反过来对现实社会施加能动影响。这既是任何意识形态的自身存在特征,亦是组成社会系统各子系统的运作功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的运行历程,也大体上是遵循这一规则的。基督教神学所树立的超验上帝之神,以及该神的各种启示,它们都不能绝对超脱具体的社会现实而存在,而必须有限度地顺应时代,与人世相关联才能上,从19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就跨入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嬗变之中,这种变动趋势到了本世纪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更为加剧。现代基督教及其神学理论也被置于一个既充满挑战与危机,又充满生气和希望的时代。它不仅受到来自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冲击,而且还受到其它文化的撞击。因此,在基督教神学体系内部也面临着一种独特的两难处境。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教众,影响遍布全球并有严格组织制度和社会职能分工的存在。一方面,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断世俗化,以缓解这种世态对基督教神学体系所构成的威胁,必须对各种外部力量作出更多的让步,走向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宗教道德与世俗道德的趋同。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基督教神学应具备的特殊精神面貌,维护其教律所规定的信仰标准和价值规范,以使其保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应有的体系的完整。于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摆在西方神学家们面前。由于传统的势力,基督教被公认为人们道德准则的源泉,并铸造了西方人的特有精神气质。传统观念中具有绝对超验的神——上帝已日趋内在于尘世,并由人类理性所不能企及的神圣中心,变成自然神论中的存在实体,由维系人类生存信仰的价值依靠变成了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枷锁。因而道德的真空危险正日渐暴露,并且社会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的理性秩序有可能被价值虚无的非涝行为所吞噬。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个既可以唤起人们觉醒,又可以是稳固且为人们信服与自觉依赖的价值系统,以抵销虚无主义盛行所带来的负面作用。由于传统的定势,这场艰巨的努力过程中,仍然是见仁见智,但就其主流而言还是主张神不能绝对超脱人世,神——人须由对立走向和谐。
一、社会生活、思想领域中的价值虚无与宗教内部矛盾
人们习惯于将宗教与世俗、人——神关系与人——人关系作必要的区分和界定,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意义卓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具任何世俗内容的东西。事实表明其情况恰恰相反。神是人塑造的,神性是人性的异化。各种宗教体系在教义上如何规定神的权力与道德属性,要求善男信女服从神的什么性质的诫命和审判,是按照社会的要求和人——人关系的性质来决定的。当人——人关系发生了变化时,它迟早会在人——神关系上表现出来,并对宗教规定之神性及其教义教规的具体含义作新的解释以适应尘世的演变。基督教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也同样体现出上述原则。
首先,在20世纪发生了触目惊心、创伤巨深的两次世界大战。它们给人类思想带来巨大冲击,有如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后的残酷现实将启蒙思想家鼓吹的“天赋人权”、“理性天国”一类幻想击得粉碎一样。两次大战显示出了人类相残的一面,科学的创造成了杀人的工具,把理性与科学万能之类的理想化为乌有。西方世界由此面临着空前的精神危机。
在对社会现实的不断探讨与反省中,西方思想界有这么一种倾向,认为导致人类社会进步受挫的原因是黑格尔思想体系对人们实践的误导,而最大的祸首又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理由是“绝对理念”的实践造成人类(尤其日尔曼民族)的理智失控,社会现实与人类理性相悖,特别是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专制独裁。“绝对理念”误把人间帝王当作人类终极价值的代理人,他们不仅有绝对真理与价值准则的裁定权,自以为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而且还认为只需要他们的功业,即可为人类在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建立起理性化的道德原则和实践规范。因此,大众完全丧失参与国政的资格,并且在此方面民众既没有必备的能力,也没有这方面的愿望。从而,启蒙运动所称道的个体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所高扬的自由主义,被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服从意志所替代,无数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和进一步完善被单一的自命为体现大众利益之代表的至上主体利益所取代。但是,西方思想界的这种反思,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黑格尔哲学在欧洲思想界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单凭“绝对理念”而奠定的,它有一个系统而完备的内在体系,过分夸大“绝对理念”的现实作用是不恰当的。同时对黑格尔思想体系作如此武断的判断与评说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黑格尔作为最后一位古典理性主义大师,在他那里作为辩证理性的“绝对理念”及其自我展开,乃是18世纪启蒙思想鼓吹的“永恒理性”的脱胎与发展,并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一面,赋予了变动不拘的特性。如果我们探究理性主义在启蒙时代得以弘扬的内在动因,亦可以看到,在理性作为信仰婢女的中世纪漫漫长夜之后,被摧残殆尽的人类理性思维从笛卡尔那里得到光大。带有一定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黑格尔哲学中的国家中心主义与其“绝对理念”一脉相承。同时也正是这种国家中心主义理论的实践,破坏了欧洲正常的社会格局,且导致许多恶梦般的后果。诸如集权政治、民族狂热、经济生活中的弱肉强食、社会财富中严重分配不均等等。理性化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导致社会职责和社会重心过分集中,失调的国家机器为了摆脱社会秩序失控的恶性循环,最终把人类拖入疯狂的战车之上。
同时,作为富于传统文化修养的欧洲思想家,黑格尔又的确受到基督教神学的深刻影响,他始终是一名有神论者。然而,中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一旦把逻辑思维作为通向世界彼岸的桥梁,那么理性就被迫放弃它的现实的创造力,理性主体的人也只会被异化为论证上帝的工具。黑格尔力图克服这一点并努力证明有一个人神关系和谐的上帝,它不仅具有理性的特质,而且就是理性的化身。当然人神是不能并列的,作为个体的人只具备有限的理性,且只局部地、在某些狭隘的时空中表现为理性的存在物,而上帝才是无限的,它的理性在一切场合都有完整的体现。但是,人类的理性本质整合出上帝,上帝可以内在于某一具体的个人,人也就因此拥有了一种新的超越一己之狭隘时空的辩证理性。如此,某一具体之人的需要须符合全体的利益,个体的价值取向就是民众的价值选择。因此,人们不必为寻求或实现各自不同利益需要而频繁争斗,应为共同的信仰而真诚合作。从这些方面看来,黑格尔似乎还是一个基督改革论者,而历史的事实表明,历史的进程并没有顺从黑格尔的一厢情愿。
本世纪西方思想界,关于道德、价值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探索,也同时深刻地印记着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以神本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痕迹。它们对黑格尔神学理论作了有力的修正,但又矫枉过正。过分强调个体的存在与发展,必然导致除了个人的意志自由,其它一切都可以外在于个人的行为,不提倡社会责任、公共道德,反而鼓吹没有条件、无节制的个人纵欲主义。人只要凭其良心、良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道德规则即可约束人们的妄动行为。但事实上,对个人的行动而言,外在的说教往往是缺乏力量的。很显然,单凭个体的生命意志来废黜传统的理性上帝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适时的道德谱系。“道德翻转”的结果必然导致新的价值虚无。为此,现代基督教神学的使命感增强了。既然基督教信仰和古典理性主义共同塑造了完整的西方精神,那么基督教神学的紧迫任务就是重新论证人——神关系,重新发掘终极信仰的真谛,以此为人类建立起顺应时代的超验的价值原则。
其次,与世俗生活中的虚无主义泛滥相伴而来的是宗教的世俗化。一则“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组织见识发展得更进步,他们的道德的与宗教的节调就起变化,没有什么比这种世俗的变化更使人注目”(注: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之种种》,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52页。)。进而“日常生活的神圣被凡俗所取代,创造物和世界都被看成是世俗的,对世界进行宗教性改造的意愿,变成了自治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技术学”。(注: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钧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从宗教学的观点看,宗教的世俗化运动,也可以被视为宗教内部的一种自我反省,是对曾有过的漠视人的命运,忽视人的生存价值传统的反省与批判。宗教应积极介入尘世,既要维护上帝的严肃性、神圣性,但同时亦应该尊重现实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并且神的一切作为都应充满对人的爱。人神关系要和谐有序,必须尽力改变现实中各种不合理的人类生存状况。
而传统观念上的上帝被认为是人们一切生存准则的制定者,一切行为合理与否的裁决者,并在理性之外规定人类的终极目的。除理性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类,又只能藉这唯一媒介达到彼岸。因此,人类通过理性即使能对自然界有整体把握,也不会找到道德价值的源泉。自中世纪开始,对于道德依据的寻求途径从根本上被调整了,上帝被生硬地理解为宇宙万物的设计者,既是理性的化身,亦是可被认知的对象。它身兼二任,既要超验地确保人的终极价值,又要先验地维护宇宙的理性和谐。善恶的存在体现出上帝的全能,而人类主动选择善、恶则体现了上帝的宽容。但中世纪封建主义结束后,沐浴了资本主义清风洗礼的人们,随着生活观念的改变,价值取向开始了由教堂向尘世的转变。马克斯·韦伯以其异常敏锐的目光洞察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同时又十分无奈地分析了转折后随之而来的现实矛盾。因为在积极的“入世禁欲主义”倡导下,金钱和权力变#在的东西,对上帝难有虔诚的青睐,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再是出于精神的需要,被经济机器异化而毫不自觉,从前对神的赞美变成对物质的津津乐道。因此,理性一旦单纯作为工具而被非理性的目的所操纵,其结果必然使作为目的的终极价值蜕变为一具空壳。对这一关键性转折的认识,韦伯的后继者也是很明白的。从康德揭露出的四组“二律背反”,同样可以窥见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水火不容。当然,这两位思想大师,他们的见解是精辟的,但对前途的认识又是悲观的。在他们看来,要唤醒人们的良知,有效的办法是呼唤已逝去的宗教时代。
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则完全走向另一道路。他把目光投向更为彻底的层次,认为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性背驰,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特点——“商品拜物教”。进而指出要克服这种人性分裂的途径是,在不断的人类劳动中,理性才能找到合理的天地,也只有在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中,才会寻找到人类的价值根据。同时,也只有基于现实的合理改造并对自我不断超越,才会使人性真正地不断完善。在这里,尼采则完全走向另一极端,他力图站在抽象思维的空中楼阁为人类的和谐设计一套一劳永逸的方案,顽固地坚持人类主体的绝对,拒绝上帝对人类理性有任何把握的可能,他呼传统的上帝已经死了。但仅凭逻辑推理对现实社会难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他至死不明白,抽象的主观性如果不同具体的现实力量进行适当的联姻,是永远不可能为人类提供生存意义的理由。因而,尽管他以超人的胆识道出“上帝死了”,但他的努力对血淋淋的社会现实中的人们并没有给予精神慰藉。
当然,西方神学界也清楚地认识到,宗教世俗化趋势对宗教自身的发展是有利的,它有助于促进宗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因为,西方世界出现的信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在于传统的神学规范与现实的脱节。要改变这一现状,途径之一就是要在保持基督教神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之下,对于基督教神学进行更进一步的人世化。在此,也就为人——神关系展示出一座新的航标。那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神学不能远离现实,人世与尘世应该合拍,人神应相互承担苦乐。上帝之子耶稣能为人类忍受“十字架”的灾难,那么人还有什么理由为生存的烦恼而痛苦呢?于是,尽管人生是要经受折磨的,生存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是否定的,但对上帝对整个人类来讲具体的个人有责任顽强地生存下去。个体人的生存不仅为人类承担责任而且也在为上帝分担苦难,上帝与你同在。况且人类的终极信仰与价值的完善,也正是在人神的永恒交往中得以完成。
二、人学意义上的现代基督教神学
本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的人学化大体上也遵循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道路,即以反传统理性主义对一切领域的独断开始自己的重构。具体表现在,一是对人类已有的知识进行结构性反思,探索其发展的动力及法则,并规定其范围;二是对人的本质重新界定,进而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予以特别关注,力求为人们的现实生命及行为寻找一个终极的超越具体生活活动的精神依靠,并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既是生命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亦是现代西方神学,特别是影响巨大的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责任。基督教神学对人神关系的调整表现为,趋向于力图解救人类生存观念的根本困境,对现实的人给予空前的注意。
首先,神学家们极力展示上帝的神圣与对人的无限超越,维护基督教神学应有的严肃性。认为仅靠抽象的思辨是无法对上帝有所把握的,“上帝之道”的主题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既不能与一般的人类哲学相混同,也应保持与自由主义神学的严格分野。主张人所具有的有罪性与局限性,决定了他不能对上帝有主动的认识,但上帝可以洞察人世,遣子耶稣到人间传达启示并代人赎罪,才使人类知晓上帝的存在。卡尔·巴特、朋霍斐尔等“新正统主义”思想家坚持这样的立场,其特征是对人与天国间的关联呈现羞羞答答的回答,较少地注意人类的现实处境,更多地论证上帝对人的超越。但是大战造成的灾难,尤其法西斯政权的伪上帝对人类的践踏,使宗教意义上的上帝形象并不那么伟岸,以致传统的严肃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处境尴尬。他们所称道的高尚纯洁的价值观念,也由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没有什么用处。因而,现代基督教神学家们十分需要对人神关系作新的论证与调整。
其次,神学家们又进一步论证人类生存的有限,尽管传统的神学观无法解救人们的现实苦难,但人类在尘世中还是不能找到处理世俗矛盾的良方,人间规则及价值依据的确立还得依赖于人们所信仰的上帝。朋霍斐尔在其晚期著作《狱中书简》中改变了过去新正统派的立场,认为上帝并非远离尘世,而是已经进入到人们具体的生活空间,内在于个体的人生之中并把握了人的存在,因此不是上帝高高在上地作为人们的信仰依靠,而是进入到个体的生命之中并使人具有主动追求高尚道德信仰的意向。保罗·蒂里希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较为完备的作为生存价值论的神学体系,认为现实中作为个体的人在与上帝沟通的同时,人自身也对原有自我进行调整,即既肯定作为具体个性的自我,又必须肯定作为大众一员的自我。照此逻辑,在神学思想体系中,“绝对信仰”是永恒的,上帝是超越主体而存在的(蒂里希称之曰:“超越上帝的上帝”)。因而人类就不会在尘世中迷失方向,“超越上帝的上帝”也不是外在于人的某个实体,它既有对人世无限超越的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内在于人并为人的生存意义寻求价值保证。那么,人类的理性价值观念也就不会因尘世的苍凉而黯然失色,上帝之神无时不在给予人类普遍的关怀。
实际上,在较晚近的神学界,由于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破产及现实的灾难,人们一直在反思:人是否可以归结为一种“理性动物”,道德准则是否可以导源于个体的理性。当然,这种深省的某种意义上会对理性本身进行否定。因为,作为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其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永远不可自满。数学界“哥德尔定理”(注:“哥德尔定理”认为,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不可能同时具备无矛盾性与完备性。)的发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纯粹理性”是不会完备的,理性的新发展有可能使过去的认识成果土崩瓦解。同时,人类的发展史也证明,如果把人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理性,最终只会是理性把具体的人异化为客体,非人的主体便对人类这个真实的主体进行无情的嘲弄。但是,人是具有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存在之物,抛弃理性的后果同样也是可怕的。如此,社会体系将成为一具空壳,变成魔鬼的道具,而具体的个体之人也只剩下虚无情绪体验之物。这种体验要么导致人以绝对的“空”为根,要么导致人以其生命的本能为根。两种极端都对人类社会体系有害无益。这就使新近的神学家意识到,仅仅觉察到传统理性的空洞还是不够的,还应更深层次看到理性的空虚必将导致人性的虚无。因此,现代基督教神学家深刻认识到,对人的本质的追问不仅必须超出理性,而且还应超越人的生命本身。对现实的人有无限超越的上帝之神才是人的价值的本源,人的本质就在于有朝向上帝的内在意向。#予启示,而对人本身来讲,得到启示的场合是他在对理性彻底绝望之后,不顾一切生存法则所跨入的那个虚空。克尔郭尔的“悖论”概念在此成了很好的注脚。它与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认识不一样,并可以视之为一种“启示的神学认识论”。其根本之处正如巴特所述“如果说我们确实知道上帝是创造者,这种了解既非完全地,亦非部分地由于我们认识了某种类似于创世的东西。仅仅是由于上帝给予我们的启示,我们才认识了它,而且从前以为自己对于事物的起源及原因所知的一切,也就开始受到怀疑,开始转换方向,开始得到改造了。”(注:卡尔·巴特《教会信条》,转引自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何光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
因此,在新近基督教神学思想中,上帝被认为从内部把握了人的生命本质。既然恢复上帝的真实性无非是为了给人确立信仰依托,使人的生存本质不受侵蚀,而人类的生存又总是现实地和具体地体现在他们的主客观行为与生命的延续过程中。那么,超验的价值依托也就要求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并贯穿于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中。蒂里希主张,在舍现实中贯彻“阿加披”(圣爱)原则,就是要把基督教神学的终极道德原则具体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因而,上帝就内在于每一个人,并是人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应互相尊重对方的合理意志和选择自由。由此可见,在现代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中,“圣爱”已不是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要内化为人们处世的价值取向。正如蒂里希所说:“阿加披根据处境的具体要求,它的条件,可能后果,牵涉到的人们的内在状况,他们的隐微动机,他们的局限性心理状态和他们的不自觉的愿望和烦恼而行动。……爱把人们从绝对伦理传统的奴役下,从习俗的道德下,从自称不必先了解独特时刻的要求就知道什么是正确决定的那些权威下解放出来……”(注:保罗·蒂里希《道德与非道德》,转引自宾克莱《思想的冲突》,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9页。)。另一方面,现代西方神学思想倾向于,上帝作为一位绝对的彼岸存在,但同时又具有神圣的人格特征。这样在现代高度物质文明冲击下的西方精神领域,人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应有合理的位置。人们在现实的矛盾中不必无所依靠,人可以通过对自身的反省与对神的祈祷来获得精神的安慰。并且,神之道德亦即人之终极价值,对神之道德的维护亦即对人类道德的保证,反之亦然。
综上可见,20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由于时代的变迁,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与重新解释传统教规。在人神关系上,既要努力维护基督教本身的严肃性与神圣性,又必须承认,人是神不得不关注的根本所在。正是无数个体的人的延续与永恒存在,以及人类的一切现实行为,才证实和维护了上帝的神圣与存在。这一现象表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神学,其自身也有一个适应时代与完善的过程。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任何宗教所信仰和崇拜的神都是人的创造物,神的神性本质上是人的人性的异化。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必然使传统权威(传统的宗教权威、政治权威、道德权威)衰落,使人格独立和主观能动精神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