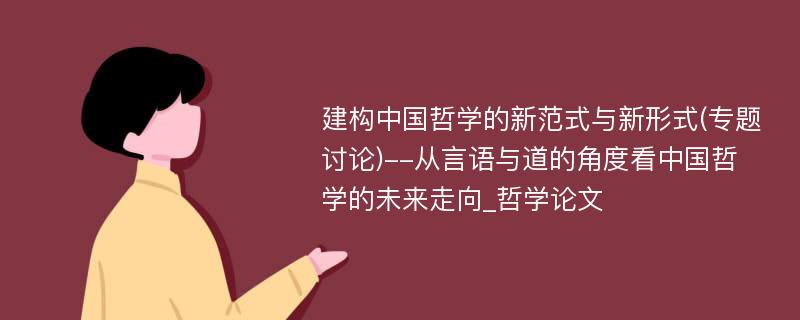
创建中国哲学学科新范式与新形态(专题讨论)——从言道方式看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3-0046-15
一
我们先从著名的“濠上之辩”谈起:“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施的上述辩论,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物方式:惠施是一位彻底的知性主义者,重视逻辑推理,从主客二分的立场出发,认为庄子是庄子,鱼是鱼,所以庄子无法知道鱼之乐;而在庄子心目中,鱼与己两者皆为“道”中之一物,故从“己乐”即可推知“鱼乐”。
这一“濠上之辩”不仅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物方式,而且可视为两种不同的哲学运思方式。这里,我将惠施式的以主客二分为根据的哲学运思方式称为“对本体”的思考方式,而将庄子式的非主客二分的哲学运思方式称为“自本体”的思考方式①。前者强调认知的“客观性”,从重视“客观性”的立场出发,发展出一种重视与强调认识论的态度;而后者采取非主客二分的态度,认为对于中国哲学而言,形上本体与形下经验世界是合一的,也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道即器,器即道”。
我认为,把握中国哲学“自本体”思维这一本质属性,不仅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的特质,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何以会采取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的言道方式。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哲学“对本体”思维方式的支配,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西方哲学的范畴、观念来对比中国哲学的范畴、观念,结果发现,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审查与衡量中国哲学文本,中国的这些哲学文本很多是“不合格”的。然而,从“自本体”思维来看,中国哲学的文本之所以采取这种言说方式却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因为,任何看待世界的方式都表现为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有不同的观物方式与思考哲学的方式,就自然会有不同的哲学语言与体现这种语言风格特点的文本呈现方式。
二
语言如何把握形上之道?这是中西哲学普遍遇到的问题。西方哲学采取“对本体”的思维方式,试图用概念语言或者“名言”去把握与言说形上之道,事实证明,这是难以言说宇宙之“大道”的。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形上之道必得自己呈现出来,是“道自道”,因此,中国哲学的言道语言首先是一种“道言”,人言只是对道言的应答。海德格尔曾指出,传统的西方哲学语言是无法把握形而上学的,传达形上之道必须凭借“思”与“诗”。这一点与中国哲学有相似的地方,因为中国哲学的文本中的确有采用诗来言道的,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哲学的语言并不完全是“诗性”的。我认为,中国哲学的语言其实是一种意象语言,是用意象语言来把握道的。这种意象语言在中国哲学文本有不同的呈现样式:
1.本然陈述。在《势至原则》中,金岳霖谈到“本然陈述”,认为可以用它来言道。他认为,本然陈述表达形而上学的“元理”,《论道》中“能有出入”这样的陈述就是本然陈述。他指出,从本然陈述的结构上看,文法上有主宾词,而实际上没有主宾词,有点像“甲是甲”那样的逻辑命题,不过主宾词却不是概念而已。这样看来,本然陈述的主宾词是相互包含的。举例来说,像“能是纯活动”这样的话,是说“能”与“纯活动”是一而非二,以“能”为主词的本然陈述,无论宾词如何,都只陈述“能”本身。②如此说来,中国哲学中表达形上之道(“元理”)的不少句子,其实就是“本然陈述”。如《老子》中的“道可道”以及《中庸》、《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等等,无不是以“本然陈述”的方式对道的言说。
2.经验陈述。除了本然陈述之外,中国哲学还大量使用经验陈述来表达形上之道。经验陈述指称的是现象界。按照中国哲学“道亦器,器亦道”的传统,形上之道也必体现为形下之器,况且“理一而万殊”,故任何经验现象也是整个道体或宇宙大全之组成部分,因此,指称与描述形下世界的经验陈述也成为言道的一种方式,是用“人言”来言说“道言”。这类经验陈述在中国哲学的文本中比比皆是,如《论语》所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不忧”等等。从文法上看,经验陈述与一般的经验命题并无差别,但由于它通过对经验世界的表达另有所寄托,故为了将它与一般的经验命题相区分,我才将它们称为经验陈述。
3.比喻、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也是中国哲学通常的表达道的方式。例如,《老子》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论语》中“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等等,皆运用了这类修辞学的方式来诠释道。这种言道方式,颇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
4.中国哲学还使用“负”的方法对道加以言说。本然陈述、经验陈述以及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使用,皆是以“正”的方法对道的言说,而所谓“负”的方法,是对道的消极言说,即指出道不是什么。《庄子》的“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等等,禅宗中大量的公案,均是典型地使用了这种方法。中国哲学之所以使用“负”的方法是出于这样一种事实:任何运用语言对道的言说(包括本然陈述、经验陈述、比喻、象征等),对道来说都既是一种“敞开”,同时又是一种“遮蔽”,需要运用负的方法来对这种遮蔽作用加以揭示。负的方法不能取代正的方法,而是对正的方法的一种补充。
三
以上是从语言形式入手,对中国哲学言道方式所作的说明。但中国哲学文本的语言现象却有着自身的复杂性。
首先,没有仅仅采取一种言道方式的“纯文本”。在任何一个中国哲学中,以上这些言道方式经常是交互使用、互为补充的,它们不仅共存于同一个文本中,甚至同时存在于同一个文本的某一个段落乃至于同一个文句中。
其次,在中国哲学文本中,除言道之言外,还有对于这些言道之言的解说。它们采取的就不一定是意象语言,而可以是概念语言与概念命题。故中国哲学文本中的语言其实由两大类组成:一类是言道的意象语言,另外还有解说这些意象语言的概念语言。意象语言与概念语言都采取语言符号,只不过具有功能上的不同,对它们很难从语言形式上加以区分,而须从含义上加以判别。
再次,中国哲学除了有形上学,还包括对哲学其他分支如伦理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乃至语言哲学的言说。这些哲学分支学科内容的表达却不是采取意象语言,而是采用通常的概念语言。换言之,就某一个具体的中国哲学文本来说,其中既有对形上之道的言说,也有对形而下的世界的“事理”的言说,而对后者的言说采取的是概念语言。
最后,中国哲学具有重人伦与重践行的特点,中国哲学文本中可以见到大量的教诲人如何去践道、行道的“教化语言”。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教化之学与形上学有密切联系(讲体认功夫、修养等等),但它们本身并非形而上学,故谈论教化之学的语言也并非是意象语言,而是概念语言。
四
通过对中国哲学文本的语言表达方式尤其是其中的言道方式所作的说明,可以看到,由于运用了意象语言以言道,中国哲学对语言可以达道这个问题的看法总体上是乐观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发展了悠久的哲学诠释学传统。所谓中国式的哲学诠释学传统,也就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诠释以见道。由言达道与由言见道,构成中国哲学思维逻辑的两个环节。如果说,在中国哲学中,对道的言说以经典文本的形式呈现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如何对经典加以诠释与理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表现为中国哲学一直讲究“文以载道”和对经典文本加以注释与诠释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人们惯于以西方哲学的思想观念来理解与诠释中国哲学,因而中国哲学的诠释学传统发生了断裂。其实,哲学在中国古称“道学”或“道术”,是一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问,它追寻的是宇宙万物包括自然、社会人事与个体生命现象在内的宇宙终极原理。因此,在言与道的有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人虽然一方面重视如何用语言来明道,认为可以观象以见意(道)、观言以见象,另一方面又强调“得意忘言”、“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一句话,语言仅仅是道的载体,而不是道本身。这也就是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这样看来,在言与道问题上,中国哲学表现出一种恒常的张力:一方面,语言可以载道、明道;另一方面,对道的理解又要超越语言。由此,中国哲学诠释学固然重视对经典文本的研究与理解,同时又认为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研习者自身的主体素质及境界相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所谓的经典诠释常常涉及主体的人格修养问题。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歧甚大,表面上看,程朱理学教人通过读书(“格物”之一种)见道,陆王心学则认为道是主体良知之呈现。实际上,这只是他们论述问题时的重点所在,程朱之学并不否认人格修养的重要,犹如陆王心学并非教人不读书一样。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以何种方式来体认圣人(经典)之道。
由此观之,中国的哲学诠释学可以以“境界诠释学”名之。这里所谓境界,既包括经典研习者本人的境界,也指经典文本中存在的境界。而所谓通过研读经典以见道,其实就是作为研读者的主体的境界与经典文本的境界发生融合的问题。此点与伽达默尔提倡的哲学诠释学中的“视域交融”相似(但不一样,此将另文详说)。也就是说,在研习者研读经典的过程中,研习者的境界与文本的境界发生了交融。由此我们发现,经典文本的意义(道)并不存在于经典之中,而是处于经典文本与研习者的一种关系之中。
因此,中国经典诠释学(或者说哲学诠释学)其实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对经典的解释,重视文本原有意义的传统;另一种是强调主体修养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其实相辅相成:对圣人之道的理解必须以经典本身为据;对经典的理解则必须跳出经典本身,取决于主体的人格与修养。
五
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一种“自本体”思维,无论在观念以及方法上,都与西方哲学有着根本上的差别。完全照搬照抄西方哲学的观念与方法来理解中国哲学,是不得要领的。今天,我们要发展中国哲学学科建设,应当是重新面对中国传统学术,将中国哲学“自本体”的言道方法发掘整理出来。
应当强调,西学对于我们来说并非完全是多余了。其实,任何对“自我”的认识都是通过“他者”来了解的。正是由于有西方哲学的存在,我们才可以通过对照,发现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与特质。从这种意义上说,将西方哲学作为一种参照系来比照,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而这与将西方哲学的观念与方法来套用于中国哲学研究是迥然相异的。
其次要看到,西方哲学在言道方面固然有其限制或所短,却也因此有其所长,这就是它精于逻辑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哲学对于任何思想观念的探讨都非常重视“方法”。它可以将表面上简单的东西加以分解,以见其内部的复杂,这其实就是一种精巧的逻辑分析技术。正是凭借这种精巧的语言与逻辑分析,西方哲学能使含混的东西变得不含混,使之能够传达。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其实是一种“哲学知识”。反过来,中国哲学重在哲学智慧,但是对于如何言说这种智慧,主要借助于意象语言。因此,取西方哲学语言与逻辑分析之长,补中国哲学之短,应当是未来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哲学智慧与哲学知识必得相互补充,它们合则双美,分则两伤。一种完善的哲学应当以哲学智慧为体,以哲学知识为用;用必须有体,体必须转化为用。因此,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一方面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两者相互交融,以成就一种既有哲学之体又有哲学之用的哲学。讲到这里,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濠上之辩”的问题:假如不是经过惠施层层的问难与推理,庄子一下子就把最后的结论“我知之濠上也”和盘托出,其结论反倒是索然无味甚至是难以理解的。正是经过庄、惠之间层层的逻辑推证与相互驳难,我们最终才发现最高的道是超越名言与主客二分原则的,也才会对于庄子所言的“知之濠上”有豁然开朗之悟。这也正是冯友兰所说过的:人必须说过许多话,然后才能沉默。中国哲学的“自本体”思维,也必须经过西方哲学的“对本体”思维的洗礼,方才得以重生。
注释:
①参见胡伟希:《自本体与对本体:中西哲学的诠释学基础》,载《孔子研究》,2005(3)。
②《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3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