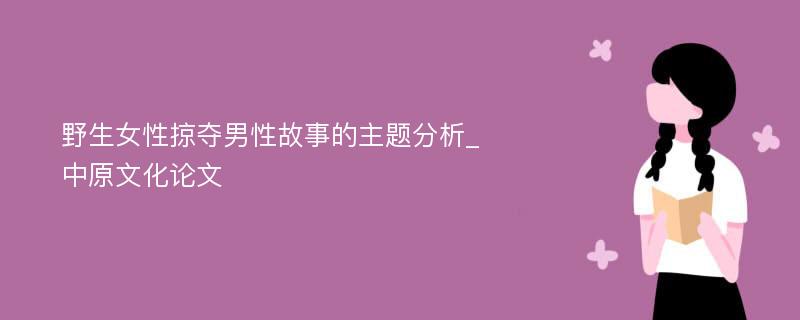
野女掠男故事的主题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事论文,主题论文,野女掠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野人传说是从古到今一个说不完的恒久母题,其中野女掠男的分支,是带有较多文化意蕴的,一直罕见有人探讨。对于所谓野人,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野人》曾试图加以总结:“野人有二种,有一等通往来话言之野人,乃卖与城间为奴之类是也;有一等不属教化、不同言语之野人,此辈皆无家可居,但领其家属巡行于山,头戴一瓦盆而走,遇有野兽,以弧矢标枪射之而得,乃击火于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药甚毒,同党中常自相杀戮。近地亦有种豆蔻、木棉花、织布为业者,布甚粗厚,花纹甚别。”而我们所说的与此有别,是在中国古人视野中被视作一种特殊动物的野人,体现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和观照异域的眼光。
一 野女掠男故事的佛经文学根源及误读
东亚流行的野女掠男母题,当起自佛经中的海外异类结亲母题,乃是人与异类通婚故事的一个变种。
唐初传译佛经中的海外异类结亲母题,讲述同母之异类弟代为复王位故事。说是婆罗痆斯城有一商主,娶妻不久妻子怀孕,他入海求宝,妻子非要同去,遇摩羯渔船破,众及商主死,妇孤身一人浮板漂至海洲,为金翅鸟王娶为妻室,不久生一子颜貌端正;然而后来则生一鸟子,形如金翅鸟,王死,此子立为王。母告鸟子,汝兄当立为婆罗痆斯王,答应了。于是金翅鸟王以双足爪将城中现国王弃于大海,将其兄置于师(狮)子座上,威胁诸臣不许违令。这王便称为梵授王。……[1]可见这一故事,实际上是人与异类通婚故事的一个变种,只不过其角色关系及性质是具有规定性的,即男野人抢掠女人强行为妻。
巴利文佛本生故事描述梵授王王后因做越轨之事,转生为马面母夜叉,住在山洞里,专门捕食从东到西路上的行人。但一次她抓住了一个漂亮的婆罗门驮回山洞,却禁不住激发了情欲,爱上了这男人,留作丈夫。他们和睦相处亲密同居,每次她出洞觅食,总是用大石头堵住洞口。但母夜叉生下了儿子(菩萨托生),儿子渐渐长大,问知父母脸面长得不一样的原由是人妖之别,就劝慰父亲回归人间,出逃一次未成功,就缠住母亲了解到她能力管辖范围,于是再次带着父亲逃走。走到界河中央追来的母夜叉央求儿子和丈夫回来,父子俩不同意,出于爱子之心,母夜叉说人世生活是艰难的,不懂得技艺无法谋生:“我懂得一种名叫‘思宝’的咒语,靠它能辨出十二年任何行人走过的脚印。如果你不回来的话,你能靠它维持生计。孩子,拿去这个无价的咒语吧!”待孩子学会后,母夜叉就悲伤心碎而死。后来,儿子靠着咒语揭露、处死了假扮窃贼的国王,自己当上了国王[2]。
但是,故事到了中国,却在误读过程中进行了新的“性别置换”。也许是受到了六朝以降“刘晨阮肇”一类仙乡洞穴遇女仙母题的影响,相关故事多表现为男性主人公因祸得福——实为一次带有男性“艳遇”性质的行为,仙话的理想色彩变得十分鲜明。人与仙女之恋,实为作为外乡来客的中原男人为偏远外域的土著妇女(即相对于载录者的外族)所扣留。所谓“夜叉”(药叉、野叉),则往往就是对于偏远地区土著妇女的一个蔑称。药叉所生之子都具有奇异的力量和才能,即使药叉与人所生之子也往往具有不同于凡人的异能,能帮助那位人类父亲成功逃离其异类之母,而母野人的人情味儿和逃离男人的冷血果决,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例如佛经中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较有深刻复杂意味的:“时婆罗痆斯有婆罗门子,因取樵木须往山林,见紧那罗神女,遂将婆罗门子入石龛中,便与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花果时,自既出已便将大石掩蔽其门,人不能动。后经多时诞生一子,其子行时身形速疾,遂与立字名为‘速疾’。”父于儿子跟前总是说自己故乡好,还乡不得的原因是不能移动大石,儿子说“我当为开”,“子便数数取石试之。乃至力能排大石。报其父曰:‘户既得开,共父逃走。’父曰:‘汝母暂为花果须出,急即还来无由得去。若其于路逢见我者,必定相害。’答曰:‘我作方便,令彼迟来。’父言:‘好事。’母持果至,子便取噉,嚼而吐出,母曰:‘何意如是?岂不美耶?’答曰:‘母懒远去,近觅苦果。谁复能飡(餐)?故须弃却。’母曰:‘若尔,我当远去,觅好果来。’答曰:‘善哉,为觅好者。’母至明日,即便远去。子报父曰:‘今是走时,无宜更晚。’遂去其石,父子俱逃。至婆罗痆斯父生之处,其母来至,见石室空虚,棰胸大哭。”邻人得悉来劝。母曰恨未教一技,邻人说本来也想到婆罗痆斯,母就以一箜篌授之,说姊妹见到我儿,以此授之,只是其第一弦不能触,若触者必有损害。当时婆罗门已将儿子付师就学,儿路遇邻人,得到箜篌,到学堂见同侣弹了一阵,禁不住同侣说无妨,就弹奏了初弦,诸同学都起舞跳跃不能自止;到师处亦然,先生及妇都起舞而不能自持,屋舍都崩倒了,先生把他斥逐村外”[3]。
故事虽旨在强调箜篌初弦不可触的禁忌,实际上乃是述说了一个航海飘落到外洋岛屿上的人,是如何幸运地在异邦土地上生活,并且如何克服艰难险阻,携子(与外洋土著妇女所生)回归故国的远游历险故事。
大约成书在公元1000年左右,作者为阿拉伯人伊卜拉希姆·本·瓦西夫王这样记载,说是在东方的海边,有一种似人实兽的女性种族:“她们像女人,其味道更为宜人,能给人带来美妙之快感。该地区芳香扑鼻,胜过樟脑。该种族没有男性”;“另一神奇的种族是海女种族,被称为水中之女。她们具有女性之外表,发长而飘动,有着发达的生殖器,乳房突起,讲一种无法听懂的语言,伴有笑声。一些海员说,他们被大风飘到一个岛上,岛上有森林和淡水河川。在岛上,他们听到叫喊声和笑声,便偷偷靠近她们,没有被发现,他们当场捉住两个,并把她们捆绑起来,和她们生活在一起。海员们去看望她们,并从她们身上享受快感。其中一个人相信了自己的女伴,为其解开捆绳,她便立即逃到海中,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她。被捆的另一个则一直呆在其主人身旁,她怀了孕,并为其主人生下一男孩。海员把她和孩子一起带到海上,看到她和孩子在船上无法逃跑,便有点怜悯之情,于是给她松了绑,但她却立刻离开孩子,逃进大海。第二天,她出现在海员面前,扔给他一个贝壳,贝壳里有一颗贵重的珍珠。”[4]
这一故事的载录者相信传闻中的这类女性“似人实兽”,实际上恰恰相反,是游泳技术极高的滨海部族。传闻发生的地域大致可以推断,就在东南亚到南中国海沿岸及岛屿。而且,其故事的形成,至少从地缘接近和叙事情节单元结构上,与上面流传在中国内地上的类似,可以猜测出其与印度次大陆的民间故事母题亦不为无关。
二 野女掠男母题的异质文化交流折映
野女掠男母题的系列性和稳定性内蕴的结合,说明其体现了较为稳定的文化观念。尤其是体现了华夏中原人与南太平洋和西印度洋沿岸和岛屿土著以及大陆西南边疆等边缘偏远居民交往的心态。在这种歧视偏见为主的非正常心态支配下,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故事往往突出了一种发生地区的边缘性。
早在六朝中原人的记载里,就突出了野女掠男的故事的地缘性。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二早有这样的“异人”描绘:“日南有野女,群行见丈夫,状皛(皎洁明亮)目,裸袒无衣禣。”[5] 这一传闻在后世每多被提起,例如,北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可是曾经有了向南远至海南岛经历为官的苏轼,仍在《雷州八首》之一中咏叹:“旧时日南郡,野女出成群。此去尚应远,东风已如云。痴氓托丝布,相就通殷勤。可怜秋胡子,不遇卓文君。”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七也称:“邕宜以西,南丹诸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名曰埜婆,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媪也。……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如此漫长时段中这一野女求合故事居然传颂不息,而相对于中原腹地的是故事发生地在空间上的遥远,似乎在暗示,此类异俗和传闻来自于那毗邻的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
按,此启发了关于人与海外异乡妇女和人兽通婚的叙事模式。当然,不能排除现实生活事件触发的可能,可是,先前的载录倾向性引导,也是不应忽视的。洪迈《夷坚志》的载录昭示了福建泉州一带航海南洋带回的传闻:
泉州僧本偁说,其表兄为海贾,欲往三佛齐。法当南行三日而东,否则值焦土,船必糜碎。此人行时,偶风迅,船驶既二日半,意其当转而东,即回柁,然已无及,遂落焦(礁)上,一舟尽溺。此人独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岛畔。度其必死,舍木登岸。行数十步,得小径,路甚光洁,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妇人至,举体无片缕,言语啁哳不可晓,见外人甚喜,携手归石室中,至夜与共寝。天明,举大石窒其外,妇人独出。至日晡时归,必赍异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无者。留稍久,始听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纵步至海际,适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风误至者,乃旧相识,急登之。妇人奔走号呼恋恋,度不可回,即归取三子,对此人裂杀之。其岛甚大,然但有此一妇人耳。时妇人继来,度不可及,极口悲啼,扑地,气几绝。其人从蓬底举手谢之,亦为掩涕。此舟已张帆,乃得归。[6]
这当是宋代福建沿海海运发展后,中国内地居民远涉南洋贸易经商频繁起来,这就是其中较早一段冒险经历的叙述。
而在此前,唐人戴孚《广异记》则载录了这样一个相关文本:“杜万员外,其兄为岭南县尉。将至任,妻遇毒瘴,数日卒。时盛夏,无殡敛,权以苇席裹束,瘗于绝岩之侧。某到官,拘于吏事,不复重敛。及北归,方至岩所,欲收妻骸骨。及观坎穴,但苇尚存。某叹其至深而为所取,悲感久之。会上岩有一径,某试寻,行百余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狰狞,不可复识。怀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状类罗刹。极呼方寤。妇人口不能言,以手画地,书云:‘我顷重生,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书之悲泣。顷之,亦能言,谓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当杀君。’某问:‘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儿,随某至船所,便发。夜叉寻抱大儿至岸,望船呼叫,以儿相示。船行既远,乃擘(分开)其儿作数十片,方去。妇人手中之子,状如罗刹,解人语。大历中,母子并存。”[7] 这是一个中原女性被南方某土著民族救助成婚,又回归中原地区的故事。其中的蛮族男子,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男性“美狄亚杀子复仇”式的人物了。而在这里,来自于中古汉译佛经多所讲述的“夜叉”、“罗刹”,已经没有分别,指的都是为中原人感到陌生和恐惧的魔鬼般的岭南土著人。而其实六朝志怪《神异经·中荒经》早就有:“北方深山有兽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体大如驴,善缘高木,皆雌无雄,名曰绸。顺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强牵男人,将上绝冢之上。取果并窃五谷食。更合三,毕而定,十月乃生。”当然这故事还不能排除受到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影响的可能。
洪迈《夷坚志》支甲卷十《海王三》故事,也当属于这一母题。尽管该故事明确描写:“女容状颇秀美,发长委地,不梳掠,语言可通晓,举体无丝缕朴樕蔽形”,然而飘流到这一“珍禽怪兽,多中土所未识”之岛的海王三,仍旧在疑虑中心存异志:“不能测其为人耶,为异物耶?默念业已堕他境,一身无归,亦将毙命豺虎,死可立待,不若姑听之,乃从而下山。”即使他已经与这个“容状颇秀美”的土著女子在山洞生下一子,仍要义无反顾地抛弃之,抱儿返乡。
宋元之际的周密还记载:“邕邑以西,南丹诸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名野婆,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飞猱,自腰以下,有皮纍垂盖膝,若犊鼻,力敌数壮夫,喜盗人子女。然性多疑,畏骂,已盗,必复至失子家窥伺之,其家知为所窃,则积邻里大骂不绝口,往往不胜骂者之众,则挟以还之。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常为健夫设计挤之大壑中,辗转哮吼,胫绝不可起。瑶人集众刺杀之,至死,以手护腰间不置。剖之,得印方寸,莹若苍玉,字类符篆不可识,非镌非镂,盖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宝为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间使大理,取道于此,亲见其所谓印者。此事前所未闻,是知穷荒绝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见闻所未及,遂以为诞也。后汉《郡国志》引《博物记》曰:‘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见夫,其状皛(明亮)且白,裸袒无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记》当是秦汉间古籍,张茂先盖取其名而为志也。”[8]
元代周致中《异域志》卷上,则以中国内地东北方区域传说的叙述,传扬了类似母题的深蕴。说是东北女真国的东北有大野人:“国有大山林,男子奶长如瓠。曾鞑靼追赶至,将奶搭在手上奔走。会人言,食叶,即野人同。”此外还有一种小野人:“在女真国之北,性狠戾,不畏生死,以杀死为吉祥,病终为不利。父子相杀以为常焉。种类以黥面为号。”故事体现了从中原中心叙事视点上的一种博物传统趣味和叙事视野,此其一;体现了对于周边民族奇异习俗歧视的观念,此其二;突现边缘区域野人的习俗、类似野兽的体貌和生活方式,带有中原强势文化的优越感和话语权力欲,此其三。可以说,有关边缘地区“野人”与中原“人”交往的传闻,虽然庞杂众多,其中还真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几乎全部是中原人的“强势话语”,一律把周边的相对落后的民族视为“野人”,强调中原人落在野人手里,虽然没有被故意虐待,却仍然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必要以千方百计逃脱为幸运。
与此女野人传闻叙事相对应的,是关于男野人——“人熊”的传闻载录。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禽兽门·人熊》则如是描绘那最为多发的西南边陲的野人:
广西有兽名“人熊”,乃一长大人也。被发裸体,手爪长锐,常以爪划橄榄木,取其脂液涂身,厚数寸,用以御寒暑,敌搏噬。是兽也,力能搏虎,每踸踔(行走不正常状)而行,道遇一木根,必拔去而后行,登木而食橡栗,必折尽而后已。余夜宿昭州滩下,闻山中拔木声,州师急移舟宿远岸,问之曰:“人熊在山,能即船害人。”又云:“往年融州有人熊渡水,人以为兽也,拏(拿)舟刺之以枪,熊就水接枪折之,遂破人舟。在山中,遇人则执人手,以舌掩面而笑,少焉以爪抉人目睛而去。尝有人熊,日坐于瑶人之门,瑶人每投以饭,因起机心,以大木两片紧合之,中椓一杙,令两木中开,次日,人熊至,见杙而怒,跨坐,拔去杙而两木合,正害其势,乃死。瑶人急去木,以米泔洗地,继而雌至求雄,莫辨所杀之处,遂不为害。不然,虽瑶人亦不可得而安居也。”[9]
如果我们在先前文献中追溯,就不难看出,这种“男野人”在徐铉《稽神录》中也曾加以注意,该书就有正常人在流落异乡过了较长时间非人生活之后成为野人的描写:
卢延贵者,为宣州安仁场官,赴职中途阻风,泊大江次数日。因登岸闲步,不觉行远,遥望大树下若有屋室。稍近,见室中一物,若人若兽。见人即行起而来,延贵惧而却走。此物连呼:“无惧,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状貌奇伟,裸袒而通身有毛,长数寸。自言商贾也,顷岁泛舟,至此遇风,举家没溺。而身独得就岸,数日食草根,饮涧水,因得不死。岁余,身乃生毛。自尔乃不饮不食,自伤孤独,无复世念。结庐于此,已十余年矣。因问独居于此,得无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腾空上下,虎豹无奈何也。”延贵留久之,又问有所须乎?对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下不速干,得数尺布为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药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贵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与刀而去。罢任,复寻之,遂迷失路。后无有遇之者。[10]
此外,实际上,许多传说中的野人,是中原人在自我中心视点上所看到的边缘、落后地区的土著居民而已。早在东汉时期,处于中国内地西南边陲的日南郡,就是造反动乱的多发地区。《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可是在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日南、象林蛮夷二千馀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馀众乃降”;“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建康元年,日南蛮夷千馀人复攻烧县邑,遂扇动九真,与相联结”;“光和元年,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刺史朱儁击破之”。可以说,自东汉以来,相对于中原中心地区,日南、交趾就是一个边缘化的、时时具有离心倾向的代名词。
三 明清小说中该母题的多重扩展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写罗刹化作美女诱惑过往商人,僧伽罗被诱入铁城,与罗刹女王生有一子,后脱逃,“时罗刹女王持所生子飞至僧伽罗前,纵极媚惑,诱请令还,僧伽罗口诵神咒,手挥利剑,叱而告曰:……罗刹女知诱惑之不遂也,凌空而去。”似乎是遥承前作,千载之下,蒲松龄《聊斋志异·夜叉国》写商人徐某泛海途中误入卧眉岛,被夜叉掳去,以雌夜叉妻之,偷渡回国后,其夜叉夫人和子女跟随而来,其女夜儿“开百石弓,百馀步射小鸟,无虚落”。丈夫每次出征都与这位女夜叉一道比翼齐飞,于是竟真的“奇勋半出于闺门”。
如果说,唐宋时代人们谈论南方野女袭击中原男子,非要“负去求合”,是中国文化南移,北方文化南渐过程中,中原人们对于南方地域风情不甚了解,很不适应的心态支配下一种惯常叙事话语的文学表征,那么,到了南北文化渐趋交融的明清时代,这一话语的深层价值观念则发生了巨大的、本质性的变化。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借此母题的叙述,讲述化为兽民的人心和归依中原文化的向心力。
明清时代小说及野史相关叙事中的女野人形象,主要表现为这三种深层文化意蕴:1.南方野女变得友好了;2.她们往往还会莫名其妙地具有中原人一样的敬孝、忠君等伦理观念;3.甚至,在通俗小说中,“野女”一类的亦兽亦人的形象,还往往带有人类所难以企及的超凡能量,与早已存在的“猿公”形象类似,成为佐助边疆平叛英雄立下战功的女将领。
至若明人邝露《赤雅·印娘》也注意到类似的传闻:“邕宜以西,有埜(野)女焉。处于石洞,含灵抱一,白皙姣好,百岁后,容发差黄,乃下山采药补益之,椎结裸跣,皮若犊鼻,垂腰盖膝。群雌无雄,遇男子辄负去,倾洞求合。惊死者掩之,生者复还故处,泄其真气,寿至百岁。若盗小儿,必至其家瞯之,群骂咒诅,则夹而还之,缘崖走屋,其行如风,误堕网罟,以手护膝而死,腹有玉印文类符玺。唐蒙《博物志》:日南有埜女,群行不见夫。其状晶且白,裸袒无衣襦。”[11] 事实上,这与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七的载录大体上还十分类似,然而,“白皙姣好”大异于南宋周密所描绘的丑陋的“黄婆”,有了较多的亲近感,倒是与《夷坚志》载录的海岛野女“容状颇秀美”相似,都状写出男性眼光中对于异邦女性外貌的欣赏。
到了清代,草亭老人小说集《娱目醒心编》卷一第二回也写,孝子曹士元入川寻夫,“又尝于深山僻处见一妇人,通体精赤,发长数尺,散披肩上,向士元看了一回,走入深林中去了。问之居人,居人道:‘此是山魅,见孤身客人,便要驮去求合,能致人死。想你是个孝子,故不来相犯。’”小说把中原人才可能有的伦理意识赋予女野人,作为男性孝子的一个烘衬,这一形象显然是一个“意识形态形象”。有理由认为,在清代,满族作为统治者,面对汉族这一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被统治者,更加忌讳自己是边缘化的族类,于是在提倡“满汉一家”时更看重北方作为中心的地位,于是以这种注视“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西川”的兽类,也希望或曰宁可将其看作是蒙受大清天朝德化的。
当然清人载录中,也有的只是把女野人仍作为外夷诸多怪异的一种。如陆次云《洞溪纤志》则称:“风者,出黔中,无形无影,能以旋风摄人。夜叉,产蜀之黎州,穴生,长七尺,亦名曰玃,路见妇人,盗之入穴,生子以杨为姓。木客,产粤洞中,衣服举止与人不异,在怳忽有无间。野婆,亦产粤西,状如妪,陟险如飞,遇男子,负去求合。尝有人刺其腰间,得一玉印,篆文莫能识。”[12]
何以在野人求偶故事中,其角色身份的关系总是叙述“男人被女野人劫掠”?例外的,倒也不是没有,但基本叙事结构及其倾向性却是相当稳定的。可以说,这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民族观与男性中心文化观念的融合,其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维的影响下,总是习惯于将周边的外族看成是野兽,而“男尊”的惯常思维又总是把外族女性视为“妖女”,类似的思维积习再同相关传闻互动,很自然地在叙述之中形成了“女野人抢男人”的叙事模式。
与此极为接近的母猿形象,在明清通俗小说中,也往往作为人兽混合的带有鲜明性别文化色彩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形象的描绘,每多突现为其由异端(异类)向正统的转化过程。像小说《锋剑春秋》第四十一回第十七回写西万山中雁愁涧,“那洞中有个母猿,名唤马铃,采天地之精气,受日月之光华,修炼多年,神通广大,能未卜先知,所生一子名唤白猿,就是盗仙桃盗天书与孙膑的,战国时曾下山到魏营中抢过草人,救过孙膑,后来回山告修,已成了正果。”
明末小说《七曜平妖传》,记述了天启年间(1621~1627)官军镇压山东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的实事。不应忽视,小说一再写到下层文人的介入,而以素质较高的官军将领娶了母仙猿——异类被改造来有意无意地加以抵消。小说第四十八回写胡参将介绍女将裴月娥的出身,竟不顾中国人传统的婚俗,毫不隐讳她与自己的辈分之差:“乃水帘洞盗桃孝母之猿也。吾师(孙膑)尝为吾谈之,曰:‘异日沙场相会,必须救援,毋效俺孙庞故事,为万世之讥也。’吾师之书,乃孝猿之授,吾之诀,又吾师之授也。授受相传,必载其祖,乃饮水思源之义。……此女必有高见,不迷本性,破妖者此人乎?”由猿精转世的裴月娥,果然投了官军,阵上求偶,嫁给了许参将,平叛时立下大功。古代小说中写猿公甚多,而写母猿的不多,这是少有的一个例子,似乎,与明代民间秘密宗教崇拜女大师,亦不为无关。是的,能够在灵兽之中找到一个人类“第二性”的代表,也是很有审美煽惑力的。
人类学家曾经揭示,许多描述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报告,所描写的不是印第安部族,而是猿猴的样子,猩猩作为半人半兽,常常出现在大众的信仰之中,对于这些看似无意义的神话传说,应该以更深刻的眼光,“去查找居住在统治居民附近或其中的某种受轻视的土著民族,某些被压迫者或异教徒,被统治居民看作动物一样,并按照动物的样子给他们加上了尾巴。”[14]我们看待古代中原传说与通俗小说中的女野人,实际上也应该注意到这一明显的种族中心话语的局限和偏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