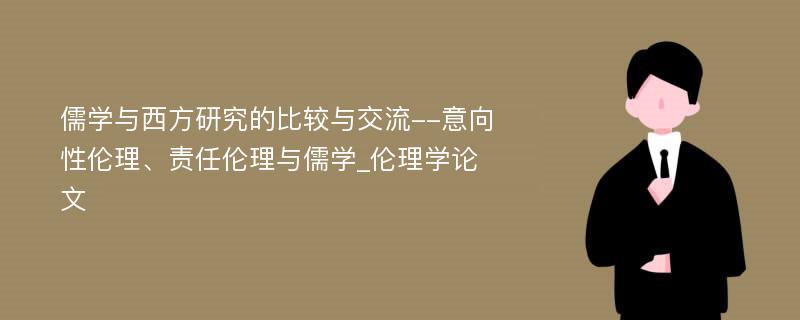
儒学与西学的比较与沟通——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西学论文,儒学论文,儒家思想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存心伦理学”(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学”(Verantwortungsethik)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使用的一组重要概念。
本文之作,主要由黄进兴教授的两篇论文所引起。这两篇论文分别为《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均收入其新书《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
我们可以将黄教授的主要论点归纳为以下两个命题:
一、韦伯的“责任伦理学”与康德的“自律伦理学”(连同其“存心伦理学”)在逻辑上不兼容。
二、基于以上这点,我们无法同时藉康德的“道德自律”及“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来诠释儒家思想。
但是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也可以用以下两个命题来表达:
一、康德的“自律伦理学”(连同其“存心伦理学”)在逻辑上不但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不相抵牾,甚至涵蕴后者。
二、基于以上这点,我们可以同时藉康德的“道德自律”及“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来诠释儒家思想,而不致形成逻辑上的矛盾。
接着,我们可进一步讨论这两个主要论点,并且在讨论的过程中一并处理次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存心伦理学”与“功效伦理学”视为伦理学的两个基本型态,亦即将它们视为依严格二分法而划分的两种“既穷尽又排斥”的伦理学,则以当代英、美伦理学家的术语来说,存心伦理学当是一种“义务论伦理学”(deontological ethics),功效伦理学当是一种“目的论伦理学”(teleological ethics)。简言之,目的论伦理学坚持:道德义务或道德价值之最后判准在于相关行为所产生的非道德价值(非道德意义的“善”);反之,义务论伦理学则坚持:我们判定一个行为或行为规则之道德意义对所根据的最后判准,并非其所产生的非道德价值,而是其自身的特性。这两种伦理学观点是互不兼容的,并无可能协调。但此处要注意的是:义务论伦理学不一定排斥非道德意义的“善”;它只是反对以它作为道德价值之唯一的或最后的判准。因此,这种伦理学仍可能接受譬如功利原则作为衍生的道德原则。根据这种界定方式,康德伦理学的确属于“存心伦理学”。但笔者将下文指出:如果我们也可以将康德伦理学视为一种“形式伦理学”,则“存心伦理学”仅构成其部分内涵;换言之,“形式伦理学”必然是“存心伦理学”,但“存心伦理学”未必是“形式伦理学”。因此,舍勒的理解未必合乎康德的原意。
但无论如何,从舍勒自己的观点来看,其“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也是一种“存心伦理学”,而且比康德的“存心伦理学”更地道。依他的看法,康德伦理学由于其理论的片面性,有流于“虚假的存心伦理学”之嫌疑。
因此,根据舍勒的用法,“存心伦理学”有两种:一种是他自己所代表的“真正的存心伦理学”,一种是对于康德伦理学多少适用的“虚假的存心伦理学”。依舍勒在叙述康德伦理学的第三项预设时所说,康德伦理学“将存心或是具有存心的意欲视为‘善’、‘恶’价值的原初承载者”。在舍勒看来,这正是其片面性之所在。
“责任伦理学”与“存心伦理学”这两个概念主要出现在韦伯于1919年所发表的演讲〈政治作为志业〉中。
康德伦理学之所以被称为“存心伦理学”,是因为它坚持:一个行为之道德意义只能凭其所依据的原则(即存心),而不能凭其后果去判定。但康德并未止于此,他进一步主张:一个真正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只能以“形式原则”,而不能以“实质原则”为依据。所谓“形式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在目的方面无所预设的原则。如果一个原则预设了任何特定的目的,它就是“实质原则”。实质原则不能作为道德法则,因为它不具有道德法则所要求的普遍性。反过来说,真正的道德法则必然是形式原则。所以,康德伦理学也被称为“形式伦理学”。就理论上说,一个信奉存心伦理学的人也有可能不依形式原则、而依实质原则来行事。在此情况下,其“存心伦理学”不即是“形式伦理学”。从康德的观点来看,韦伯所批评的耶教伦理学当属此类。反之,一个信奉“形式伦理学”的人却一定接受“存心伦理学”的原则。总而言之,“存心伦理学”仅构成“形式伦理学”的一个面向。康德进而指出:唯有形式原则才能是道德主体(意志)为自己所定的法则,才合乎“自律”——意志之自我立法——的理念。因此,康德伦理学也被称为“自律伦理学”44(Ethikder Autonomie)。在此意义之下,我们可以将“形式伦理学”与“自律伦理学”视为同义词。
康德的“存心伦理学”并非仅考虑存心之纯粹性,全然不顾及行为之后果。康德在决定行为的道德意义时固然坚持以存心之纯粹与否作为唯一的判准,但是这无碍于他同时肯定:一个出于纯粹存心的意志必然会要求自己对其行为的某些可能的后果(这些后果可概括于“幸福”概念之下)负责。一般学者将康德伦理学视为“存心伦理学”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因此,笔者同意德国学者考尔巴赫(Friedrich Kaulbach)对康德伦理学的如下诠释:
在康德看来,行动之“意义”必须被理解为由两项要素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一项要素是意志的道德境界——这个意志是一个善的意志,它选择其目的,并且借着这项选择使其目的成为善的目的。行为意义的整体包括行动者的存心、以及另一项要素:负责任地实现所选择的目的。对于“善的意志将在最高善的世界中终的于成”的这种出于理性的信仰系指向未来:它是一种“期望”。在康德看来,我们无权在责任伦理学与存心伦理学之间作非此即彼的区别,因为行为意义是由责任和存心构成的整体。在这两者之中即使只少了一项,我们也无法将“意义”归诸行为。
换言之,如果我们要将康德伦理学称为“存心伦理学”,则这种“存心伦理学”与韦伯所谓的“责任伦理学”不但不形成对立,甚至可以涵蕴它。
依笔者之见,康德的伦理学的确涵蕴“责任伦理学”的概念,但是这种“涵蕴”关系在层面上须稍作分疏。韦伯的“责任伦理学”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套独立的伦理学系统,因为它是一套特殊伦理学(在此是政治伦理学),在一般伦理学的层面上必须有所预设。在这个层面上,若根据存心伦理学与功效伦理学之严格二分法,韦伯的“责任伦理学”无疑预设了“存心伦理学”。换言之,韦伯的“责任伦理学”若要取得完整的系统意义,就不能不在一般伦理学的层面上预设康德式的“存心伦理学”。但是韦伯的“责任伦理学”概念可以在政治伦理学的层面上凸显出康德的“存心伦理学”中隐而未发的一个重要面向,这是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贡献。
确定了康德的“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二者之关系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儒家思想本身。笔者曾撰写一系列的论文来说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流思想基本上包含一套“自律伦理学”,因而也包含“存心伦理学”的面向。这些论文均收入拙著《儒家与康德》中,读者可以参看。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最足以表现存心伦理学的特征的,莫过于孟子的义利之辨。简言之,孟子的义利之辨包涵两项基本意涵:(1)“善”之异质性,或者说,道德意义的“善”与非道德意义的“善”之原则性区分;(2)非道德意义的“善”从属于道德意义的“善”。因此,孟子反对以非道德价值(功效价值)来决定行为的道德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在孔、孟的思想中发现责任伦理学的面向。黄教授所举孔子称赞管仲的两段话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两段话分别载于《论语·宪问》第十七及十八章,其文如下: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如果将这两段文字从其原有脉络中抽离出来,我们似乎也可以将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理解成一种功效伦理学的道德评价方式,亦即从行为的后果来评判其道德价值。但是这样的理解方式势必会与孔子的上述言论所表现出的存心伦理学面向相抵牾。因此,在笔者看来,依“责任伦理学”的原则来诠释这两段文字,实在是最顺适不过了。黄教授对这种诠释的可能性有所保留,恐怕也是由于他不了解“责任伦理学”与“道德自律”、因而与“存心伦理学”在概念上的兼容性。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亦不难了解:何以主张义利之辨的孟子会一再呼吁当时各国的国君改善人民的生活?这类为民请命的言论在《孟子》书中俯拾皆是。譬如,《梁惠王上》第三章载其言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如他盛赞禹、稷、伊尹,《离娄下》第廿九章载其言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在《万章上》第七章中,他说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这些话都只能从责任伦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因为唯有如此,它们才能与孟子思想中所涵的存心伦理学面向融合无间。
总而言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流思想基本上包含两个伦理学面向,这两个面向分别对应于康德的“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依笔者在上文所作的分析,这两种伦理学不但在逻辑上彼此兼容,前者甚至在概念上涵蕴后者。在这个意义之下,笔者同意德国学者罗哲海(Heiner Roetz)的看法:“古典儒学的真正理想”是“道德存心与伦理责任之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