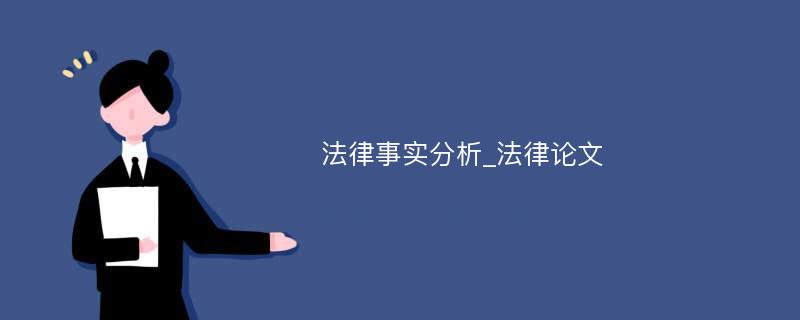
法律事实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实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81(2007)06-0040-8
是什么促使我们来研究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呢?庞德曾感言:事实问题“是司法上由来已久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法令承认提供的事实并根据事实来宣布指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提供给我们的。确定事实是一个充满着可能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困难过程。[1](P29)季卫东先生也说过:“程序开始之际,事实已经发生,但决定胜负的结局是未定的。这给国家留下了政策考虑的余地,也给个人留下了获得新的过去的机会。”[2](P19)对于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来说,一切都是既定的,但一切也都是未定的,确定事实的道路充满了荆棘、诱惑与陷阱。本文试图在对于法律事实的辨析中,体悟出事实的复杂、主体的限度。
一、事实界说
要理解法律事实,首先应从考察事实的规定性开始。“事实”一词在德文中译为“Tatsache”或“Sachverhalte”,在英语中为“fact”。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事实”的解释是:“事情的真实情况”。什么是事实,许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这一概念在日常生活和现代文献中的运用来看,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它通常被在多种意义上来使用,有时甚至会出现矛盾和混乱的情况。比如罗素在1922年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所写的“导论”中就明确指出:“严格地说,事实是不能定义的”。[3](P7)但后来,他在《我们关于外界世界的知识》一书中又指出,他所谓的“事实”乃是指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等等有关事物的情况,而不是仅仅指的事物自身。[4](P39)而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他又提出:“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我都把它叫做一件‘事实’。太阳是一件事实;凯撒渡过鲁比康河是一件事实……”[5](P176)从而在他的概念中,“事实”与“事物”没有了区分。在法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证据法学研究领域,“事实”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基本概念,但是,对于“事实”这一概念的误用和滥用的情况也比较严重。为此,有必要对“事实”的基本含义进行梳理,区分“事实”的不同含义,以避免因概念使用的不统一而产生的误解。关于事实的含义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种说法:
1.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如罗素曾经对事实下过如下的结论:“事实是不论我们对之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而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东西”。[6](P219)在这里强调了事实先于人或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性,甚至可以说是与人无关的。
2.事实是世界的总体。维特根斯坦主张:“世界是事实的总体”。[3](P25)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事实就是发生的事情,世界是由原子事实构成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对原子事实的认识,而且,这里的原子事实不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事实,而只是一种被描绘处于原子状态的经验。他对事实与事物作了区分,强调了应该从命题与事实的相互关系上把握事实的含义。
3.事实是指“事实存在”与“事实判断”的结合。“事实存在是指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的真实情况’。其中所说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形态和状态:物质的、制度的或观念的;历史的或现实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等等。事实存在处于认识之外,是一种‘自在’。当这种‘自在’进入人们的认识,就有了事实判断,即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陈述或认定。例如,桌子上有一只杯子,这是一种事实存在,而张三对李四说‘这张桌子上有一只杯子’,则是在作事实陈述。”[7](P4)
4.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种观点是在区分事与物、事实与事情的基础上来界定事实的。从物与事的区分看,事实总是一件事,不是一个物。而“事情”既可以从它的发生、经过、结束来看,也可以从它实际发生过已经摆在那里来看,“事实”则单从一件事情已经发生摆在那里来看一件事情,因此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却不能说“发生了一件事实”。从广义上来讲,凡已然发生的事情、凡摆在那里的事情都是事实。但这只说出“事实”这一概念的一半,那另一半是:事实是为论证服务的,我们之所以需要事实,是因为我们要从发生过的事情里选取一些因素作为证据进行论证。事实是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上截取下来的,截取可以有不同的长度,不同的层次等等。[8](P1)
5.事实是客观发生的过程或状态。这种观点认为“事实”是一个实实在在发生的过程或状态,在时间上是连绵不断、生生不息的,在空间上是浑然一体的。“事实”是客观世界的现象、过程、事件,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是自在自为的,事实就是所发生或存在的一切,没有肯定与否定之分,本身也谈不上真假。[9] 事实的根本特征是它的客观存在性,这是区别事实和非事实的本质特征。针对实践和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状况,可以进一步对事实的形态作出分析,这就是事实既包括了客体性事实,即一切对象的客观存在及其现实状况,也包括了人本身的主体性事实,即“通过主体本身的存在和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事实”。“是因主体不同而不同的客观事实”。[10](P269-270)
6.事实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或情形。事实的英文表述是“fact”,而“fact”一词原指行为、行动、特别是犯罪行为,后来泛指实际发生了的事情或实际所是的情形,与猜测和虚构相对,可用作真实可靠的证词和证据。[8](P1)
7.事实是指与行为相对的变故或事件。这是《牛津法律大词典》对事实(fact)的一种解释:事实与行为不同,是指非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之变故或事件。[11](P411)
8.事实是接受了的或安排了的所与[12](P738)。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认为:“事实是为主体用概念所接受了(或安排了)的感性呈现。稍具体一点说,呈现于人们感官之前的现象,只有当其为概念所接受(或者说为概念所摹写,所规范……),由主体作出了判断,这才是知觉到了一个事实,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嗅而不觉,那就表明,虽有呈现于感官之前的现象,但未为概念所接受,未为主体所察觉,这就不能说是有了知觉,更不能说是有了事实。”[13](P123)
通过归纳和比较可以发现,人们对于事实这一概念基本上是在两种意义上来使用的:
第一,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事实是指外在于人的事物、事件及其过程。这是一种作为存在的事实,在这种意义上,“事实”这个概念本身就和“客观存在”、“世界”、“客观事实”同义或近义。先在于人的自然界以及打上了人的烙印的一切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存在本身都是事实。这实际上是把事实等同于一种纯粹的“自在之物”。[14](P75-76)事实就是存在,包括自然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静态的事物与动态的行为、生活状态等,而且,这种事实不依靠我们的意愿。
第二,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事实是主体关于客观事物、事件及其过程的反映或把握。这是一种作为命题表述的事实,在这种意义上,事实不仅与主体相关,而且是主体的实践与认识活动的结果,实际上是把事实等同于对事实的认知。[14](P76)如张志铭先生在界定事实时就分析了事实的主观性,把事实判断作为事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此种意义上,事实如果不进入人的意识,只是作为“自在自为”的客观存在,对于人类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为人所知并具有一定意义的存在才能构成事实。事实作为陈述或判断结论的命题,既可以是对日常生活状态的描述,也可以是对事物抽象的概括,是认识主体——人的一种主观相信的状态,这种相信即可能是来自主观的感受,也可能是出于理性的判断。[15](P7)
两种意义上的事实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作为命题表述的事实是经由对作为存在的事实的承诺才进入人们的视野的。但由于作为存在的事实与作为命题表述的事实在内涵上的不同导致二者在外延上有很大差异。具体来说,作为存在的事实指称的是事件的原貌和自然状态,包含事件的所有细节和所有信息。而作为命题表述的事实指称的则是进入人的实践认识活动进而能被主体以一定形式反映出来的事实,由于主体的限度和其他限制性因素的存在,在范围上它可能只包含存在的事实所涉及的部分细节和部分信息,即从内容上看,二者之间可能会表现为一种相互的交叉、重合或是某种程度上的背离。本文认为,区分两种意义上的事实对于我们分析司法活动过程中事实问题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作为存在的案件事实的承诺是本文的一个前提,这是司法活动赖以启动的力量之源。然而,在具体的司法语境下,从程序的视角出发,作为存在的事实只是一种诉讼外的事实,在诉讼之内,它并不存在,或者说称它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对它无从把握。由此,司法活动应以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为基点,进而,司法活动的目的应从发现事实真相转向确保事实形成过程(即描述“客观事实”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总之,承认并区分两种事实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法律事实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二、对法律事实的重新界定
(一)关于法律事实含义的诸种学说及评析
一般来说,法律事实经常在以下几种意义上被使用:
1.构成要件说。该说把法律事实等同于完全的法律规定(或完全法条)中的构成要件。如梅仲协先生所讲的:“某种特定事实,发生某种特定效果者,我们称之为法律内容;当事人所完成的法律关系及其它事故,谓之法律事实。所完成之法律有直接紧连于法律之命令或禁令者,或依据权利授与之方式者,其因而获之结果谓之法律效果。”[16](P193)这种观点把法律事实的一种分类当成是法律事实的全部。用大陆法系的法律技术来衡量,它属于法律中的法律事实模型,是判断生活事实是否是法律事实的标准。
2.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法律事实者,发生法律现象之原因也。法律事实与法律现象既处于因果关系,则凡法律事实有使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法律现象亦必随之而有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状态”。[16](P194)也即法律事实就是“由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17](P140-141)也就是说,正如法律规范并不调整人类的所有活动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会与法律规范发生联系,导致相应的法律后果出现,只有具有法律意义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定事实才是法律事实,那些与人类生活无直接关系的纯粹的客观现象就不是法律事实。
3.法律规范之事实说。该说认为,道德、宗教规范所支配者就是道德或宗教事实,而为法律规范所支配之事物即为法律之适用对象,人们称其为法律事实。这种法律事实实际上是把法律看成是社会关系的调控器,认为只要能纳入法律调整和控制范围的事实都可称之为法律事实。它是把法律事实与宗教、道德等规范控制的事实进行比较后而得出的结论。[18](P284-285)
4.实证法之规范说。该说认为,“所谓法律事实当指实证法所规范之生活事实,从而法律事实之主要特征应有:(A)具体性,(B)事实性,亦即法律事实所指称者,本来或一直是发生于或继续存在于具体案件中之事实或状态”。[16](P199)
5.法律适用的前提说。该说认为,“法律事实是由法律所规定的,被法律职业者证明,由法官依据法律程序认定的‘客观’事实。”[19](P23)即法律事实就是指经法官认定的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这种观点结合法律适用过程中所运用的三段论推理,认为在三段论中,法律规范是大前提,法律事实是小前提,判决就是法官运用法律规范对法律事实进行推理所得出的结论。
6.综合说。该说认为,以上五种关于法律事实的观点反映了研究法律事实这一概念的两个角度,这五种观点都含有对法律事实认识的真理性成分。具体来说,“第一,关于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说、实证法之规范说和法律规范的事实说,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概括生活事实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角度强调了法律事实中法律规范或规定中所含有的立法意旨,认为事实只要能与法律所设定的模型重合就可称为法律事实。”……“从这一角度审视法律事实,我们会发现,法律与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分不开的。因为事实是法律中的事实,法律要对社会进行调整就不能在其所创立的规范中舍弃事实。从这一角度所分析的法律事实都是规范或典型的法律事实,都是关于法律事实的共性的认识,人们分析这样的事实看不到其中的个性,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是由立法者在法律中设计的法律事实模型。”“第二,法律事实的司法前提说和法律关系的因果关系说,是站在司法的立场上对法律事实所作的定义。在这两种定义中,法律与事实是分开的,法律在这里主要是指规则,而事实则是法官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排除了大量个性(当然它们看到了事实中的个性)的事实。这种事实既引起了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又是由法官等在法律程序中反复质认、最后由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18](P285-286)综合说主张,对法律事实的研究应把上述第一、第二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即“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所框定的,而又经由法律职业群体(法官起着最终决定作用)证明的‘客观’事实。这其中的法律规范反映了立法者对什么是法律事实的框架性认识,而法律职业群体证明的则是客观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意义。”[18](P287)
以上观点确实反映了人们对于法律事实的不同角度的认识。本文认为,不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角度界定的法律事实都是属于作为命题表述的事实,即它们都不属于作为存在意义上的事实一类:从立法角度界定的法律事实是立法者基于对生活事实的抽象与概括而形成的,是立法者主观意识介入下的产物;从司法角度界定的法律事实则是进入诉讼的相关主体主观活动下的产物。所以,在考察作为命题表述的法律事实时总体上要考虑这种事实形成的诸多限定性条件及其正当性问题。但是,本文对于将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去界定法律事实的作法不能赞同。因为,两种观点所反映的法律事实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其背后的理论意义也完全不同。
从立法角度概括的法律事实严格来说是一种“制度事实”,它是指法律规范中存在的行为模式或假设条件,是立法者对认为需要由法律调整的生活经验事实所作的归纳与描述乃至预测,所以当具体事实发生时,法官才能够依据法律规定对纠纷中的两造作出权利义务的裁决。“制度的存在必然比它的任何实例的存在提前一段时间”,“制度作为一个概念而言在逻辑上早于它的任何实例的存在”,[20](P68)我们在一种法律的语境下谈论事实问题,必须要引入并澄清制度性事实的概念。制度事实包括法律规则中所概括的事实,也应当包括法律原则中所概括的事实,还应当包括政策、正义、理性、道德、习惯法等非正式法律渊源所应概括的事实。一方面,制度事实通过分配和矫正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发挥着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预测、指引、教育、制裁、威慑等的作用;另一方面,制度事实作为一个规则体系具有“既使自己保持同一性又使自己结晶化”的特点,即制度事实作为一种先在的规范事实发挥着对于司法裁判过程中形成的事实进行剪裁的作用。所以,本文认为,从理论上区分法律事实与制度事实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助于我们廓清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界域,并深化对于问题的讨论。本文就是从司法的角度界定法律事实的。
(二)法律事实的含义及特点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法律事实是与制度事实极为不同的概念。这里的法律事实是指在法定的程序空间内,由多方诉讼主体依据既定的规则建构起来的一幅案件事实图景,它是某种法律裁决据以作出的事实依据。就像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中所说的:“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一如人类学家所言,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的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务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21](P80)法律事实是存在于整个诉讼过程中的,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存在法律事实,也都具有相应的意义。以刑事诉讼为例,自诉讼程序开启之后,就伴随着法律事实的形成,比如侦查终结,不起诉等等都是依据一定的法律事实作出的,无罪的法律事实可能在审判前就被加以认定,有罪的法律事实和部分无罪的法律事实一般是在法庭审判阶段认定。由于法律事实的内容及其所具有的意义的不同,其可能是侦查人员据以作出侦查终结结论的依据,也可能是检察官据以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依据,当然,它更是法官据以作出司法裁判的依据。需要说明的是,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背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法律事实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的。因而,这里的法律事实又可以进一步界定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据实体法规则、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等建构起来的一幅刑事案件事实图景,它是法官据以作出刑事裁决的依据。
上文界定的法律事实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法律事实形成的时空条件来看,法律事实形成于一定的程序空间内。一个刑事案件发生之后,作为一种存在的事实就自在于世界之上,但是,这个自在的事实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律事实在意义上是不同的,这个“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无法直接以某种方式转化为法律事实,它们之间隔了诉讼程序这一屏障,然而,也恰恰是诉讼程序为法律事实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为当事人重塑事实提供了一个机会。法律事实的形成直接源于诉讼程序的启动,法律事实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依凭诉讼程序来赋予的。所以,在探讨法律事实的相关问题时,与其说我们的目标是努力使法律事实保持与自在的案件事实相符合,而毋宁说是如何规范在程序空间内重塑案件事实的过程,保持法律事实形成过程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法律事实是经过程序法规范过滤了的事实。
第二,从制约法律事实形成的规则上来看,法律事实的形成离不开规则的规制。如前所述,制度规范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准则和指针,是人们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评价的尺度,在通过诉讼程序规范法律事实的过程中,事实审理者、案件当事人或相关证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依据规范中的要件事实来搜集、整理、判断证据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法律事实。所以,司法程序是将客体事实的意义抽象为符合实体法规范要求的制度性事实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法律事实是实体法规范制约下的产物。同理,法律事实也是在证据规则作用下的产物。由于证据规则的作用,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可能导致许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证据材料被排除,使得一些证据信息不能进入诉讼之中发挥证明作用。但由于形式理性在司法程序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一般说来,只要符合证据规则的形式要求,法律事实的认定就是有效的;而且也只有在符合证据规则的形式要求的情况下,认定的法律事实才是有效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事实是依据证据规则而剪裁出来的事实。
第三,从影响法律事实形成的主体因素来看,所有的诉讼参与人都是法律事实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都参与了法律事实的重塑过程,只不过每个主体所发挥的作用不同罢了。法官是整个审判程序控制者,在主导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法律事实的形成,同时,作为认定法律事实的主体,法官要依据法律事实作出最终的裁判。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在起诉书中,检察官一般要提供一个关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基本事实轮廓,进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通过法庭上的调查、辩论活动逐步地将其所描绘的事实图景清晰地呈现出来,以赢得法官的确信。作为辩护一方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相反,其在整个刑事庭审过程中都试图着力改写或部分改变控方所描绘的事实图景,使其呈现出另外一种样态,以达到对其有利的目的。至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证人、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则作为控辩双方中某一方的辅助者参与对事实的描绘活动,进而从具体细节上影响事实的形成。
第四,从法律事实的内容上看,它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在法定的程序空间内,依据实体规则、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建构出来的法律事实并不会变幻莫测、难以把握,其内容具有相对的确定性。美国法学家弗兰克在《初审法院》一书中曾分析了案件的实际事实和“认定的”事实之间的差异及其可能对判决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裁判事实猜测说的理论。以对证据的可靠性加以质疑为基础,他认为所谓的“真相大白理论”(“Truth-Will-Out axiom”)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的情况是,证人的作证只是对过去事件的回忆,由于认识论上的原因,这些回忆与案件的实际事实不可能完全一致,多少会带有猜测的成分,而事实审理者正是在证人的这些具有猜测成分的回忆基础上来推测认定裁判事实的,因此裁判事实只能是对客观的案件事实的一种猜测,而且是在证人猜测基础上的猜测,完全是一种主观性的事实。[22](P23)本文认为,弗兰克因裁判事实具有主观性就将裁判事实看成完全是一种主观性的猜测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作为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虽然法律事实与作为存在的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可能交叉、重合、甚至背离,但是,这种主观建构出来的事实的内容并非是完全不确定的。因为主观建构不是随意进行的,它是依据一定的规则而展开的,而这些规则本身都具有保证建构出来的事实具有相对确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无须担心建构出来的事实是否会走得太远?在主观性与既定规则之间,在必要的张力背后是法律事实内容的相对确定性。
第五,从法律事实的形成过程上看,它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由于法律事实的形成不是依赖于一个事先的模型去还原或模拟的过程——这是一个制约主体的能动性和内在激励因素的封闭过程,而是一个面对无限可能的去满怀希望去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建构者的智识努力的影子,有包含建构者个性特征的价值诉求,结果如何是待定的,一切都看程序的运行,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实结论自然就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而且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为法律事实结论的非既定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了围绕一个给定的对象加以恢复的封闭性束缚,所以建构法律事实的过程也是开放的——主要体现为程序的开放性,诉讼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事实建构过程的正当与合法性。当然,在这里,还存在一个饶有意味的悖论,法律事实的建构本身是在程序的空间内来进行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在封闭的程序空间内展开的建构活动,但是同时,当主体在程序空间内从事建构活动时,这种建构活动本身却是开放的,没有既定目标的限制。其实这并不矛盾,相反,它可以激发主体去建构事实的冲动,面孔还不清晰的未来事实向创造力敞开了大门。
三、法律事实建构理论的提出及其意义
由前文对于法律事实的界定可知,本文所主张的法律事实不是对历史性案件事实进行探知、回复活动下的结果,而是在法定的程序空间内,由多方诉讼主体基于自己的个性化认识,依据既定的规则建构起来的一幅新的案件事实图景。在这里建构与发现是两种相反方向的活动,其背后所承载的理论模型是截然不同的,从而两种观点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也就有了重大差别。
事实发现理论坚持的是一种反映论的观点,其以对于“真”或“真理”的追求为理论原点,强调发现真实的结果对于诉讼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理论的基本理论结构是这样的:其一,预设一个独立于人(心灵)的客观事实的存在。这是一个并不以我们是否认知或是否有能力认知为条件的客观存在,即这是一种不受人的认识能力限制的、独立于人(心灵)的存客观实在(reality)。[23](P55)其二,主张对于客观事实的认识过程是一个排除了价值干扰的过程。也就是说,这里的认识主体基本上是价值无涉的。第三,坚信能够获得一个客观的与先在的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认识结论。这种理论始终确信主体在正确的方法论的指导下是能够按照其本来面目反映真实的,或者说主观认识可以与客观真实相符。以上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这种理论的内涵。真与善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事实发现理论对于真的执着追求本身似乎不应该遭到否定性的评价。但是,理想化的求真理论在诉讼的语境下却是先天不足的,其具有不可克服的弊端:其一,为事实发现活动预设一个客观事实的目标的同时就为主体的活动施加了潜在的限定,这种限定反过来又导致事实发现活动变成一种封闭性的活动,这种封闭性的事实发现活动不但排斥多元价值的介入,而且限制了主体的积极能动性的发挥,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表现;其二,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导致人们在面对案件事实的客观性时只是片面强调抽象的客观性,而忽视作为具体的经验性认识的限度或者对具体的认识条件的限制视而不见,促使诉讼活动走向发现真实的极端,法律事实的意义——进一步讲是人类自身生活价值与意义却被抛弃了。
本文主张法律事实是建构的,这是一种与将整个司法过程全都诉诸于真实发现的反映论截然不同的理论主张。法律事实建构理论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在诉讼程序的空间内,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事实;第二,诉讼活动并不是追求过去发生之事实的最终真相的探索过程,而是建立一种关于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的版本,即这是一种主体诠释的过程。第三,通过诉讼活动所建构起来的描述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只能描述事实的局部,而非全像的反映,其合法性与正当性无法依赖于其自身的存在而具有,而是由法律规范赋予的。
法律事实建构论的提出对于前述真实发现理论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很显然,在事实发现的理论之下,法律事实必须以其所获得的客观真实性向人们彰显其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在法律事实建构论之下,法律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契合已经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对真实的诉求已经在规范事实建构规则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关照,真实的底限也由此得以保障。因此,诉讼活动应从作为命题表述的事实的特点出发,以规范法律事实形成过程为中心任务,对法律事实的判断标准也应该由真实性的判断标准转为合理性、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即在封闭的程序空间内,由主体建构出来的法律事实的正当性是法律规范所赋予的。明确这一问题即完成了一种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实际上,司法程序就是一种关系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在某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具体的司法框架的样态如何?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如何体现法律的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理应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毕竟从根本上说,法律所关注的并不是过去的事情,而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或会发生的事情。本文努力辨析法律事实的含义也是意在引导人们由研究制度的解构或建构到研究具体的司法过程,由关注静态的法律到关注法律的动态运作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