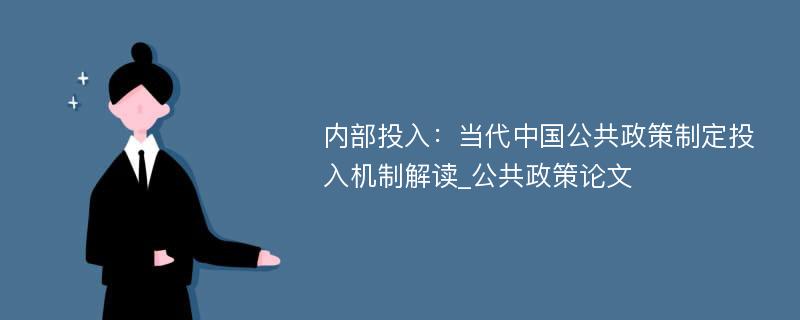
内部输入:解读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输入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51年拉纳和拉斯韦尔的那本标志着政策科学诞生的著作——《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问世以来,政策科学获得了长足进展。“政策科学运动”(Policy sciences movement)旷日持久,并形成了所谓的拉斯韦尔—德洛尔政策科学传统的主导范式。那么,何谓公共政策呢?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
所谓公共政策,就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注: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第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笔者之所以采用此种界定,基于两点原因:其一,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公共政策无非是政府调整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工具,公共政策本质上反映、调节的是一种社会利益关系。从利益的视角观之,整个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一个公共利益分配的过程。而那些在中国普遍存在的所谓“争政策”现象,无非争的是利益,所谓的“政策资源”的说法,也无非是从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一定的利益这个意义上说的,而绝不是指政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其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代中国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西方的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的话,那么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则完全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实际政治下,这里的政府概念的内涵应有所扩大,包括党组织和政府组织,而且党组织是政府机构的核心,更是制定公共政策的核心主体即政策中枢,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更不用说试图解读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了。
对于公共政策制定,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注:陈振明:《政策科学》第212页(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丛书,MPA Serie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琼斯、安德森把它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构建、目标确定到方案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而德洛尔则从广义上把它理解为整个公共政策的生命过程,包括政策制定阶段和后政策制定阶段。本文采用广义的理解,并结合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运用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所提出的作为比较政策过程和方法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将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即政策过程粗略地划分为三大阶段:政策输入、政策输出、政策反馈。
政策输入即向政策制定系统提出的要求和支持,这种输入来源于政策制定系统的外部环境和政策制定系统内部本身。来源于系统内部的政策输入有时叫“内部输入”。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政策输入的过程也就是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过程。利益表达是社会中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政策要求的过程,它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利益综合则是指决策者将各种利益要求转变成可供选择的重大备择方案的过程。利用表达以及进一步的利益综合的过程共同构成了政策输入过程。如果这种被表达并综合的利益要求获得了大量政治资源的支持,那么它们就会成功地“进入”或“接近”政策制定系统,成为重大的政策选择。这也就意味着政策议程得以建立,政策问题有可能得以解决。依据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此时政策问题进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在政策制定系统内部会经历一个转换过程,然后成为权威性的政策输出即具有约束力的公共政策。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黑箱”特征,无法对内部转换过程作具体分析,只能从较宏观的层面上对决策过程作一简要分析。鉴于此,笔者这里所指称的政策输出是一种大输出,包括决策和执行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决策的过程就是把有效的利益要求转换为权威性的公共政策的过程,这是政策过程的核心。公共政策出台以后并不能立即对目标群体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这里还有一个将政策意图转换为政策行为或政策结果的过程即政策执行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在整个政策输出过程中,通过政治文化的桥梁作用,政策输出所产生的政策结果会进一步反馈到政策制定系统即形成政策反馈回路,并对政策制定系统的未来政策行为产生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整个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不仅仅是一项决议,而且包括目的、计划、规划以及实现它们的程序”(注:[美]E.R.克鲁斯克等主编:《公共政策辞典》第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在政策过程诸阶段中,政策输入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一项利益要求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那么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就此而言,研究政策输入过程中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特征以及方式、途径就显得十分重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番简要分析。
二、分析的框架: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
从逻辑分析概念上说,公共政策过程是以公共政策问题为逻辑起点的。所谓公共政策问题,指称的是那些由作为社会公共权威的政府加以体察和认定并列入政策议程的社会公共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公共问题只有经过政策议程才会成为政策问题。关于政策议程,科布和爱尔德在《美国政治中的参与》一书中曾经区分了两种基本的议程,即系统议程(或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或正式议程)(注:[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第6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公众议程本质上属于讨论议程,由那些已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关注且又属于政府权限范围内需要政府加以解决的问题组成。而政府议程即政策议程则由那些已为政府决策者所察觉和注意并将之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可能对之采取具体行动的一些事项构成。政策议程本质上是一种行动议程,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共问题进入公众议程加以讨论,然后引起决策者的关注从而进入政策议程,最后才形成政策问题并由政府决策者加以确认。然而事实上,很多问题可能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由政府主动列入议事日程并直接进入政策议程。这一点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十分突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党组织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代表者,以及它们在政策制定的权力结构中所处政策中枢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们拥有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权力,对于社会公共问题能否进入政策议程具有决定性影响。在中国,常常是党组织和政府主动寻求和发现问题,并把它直接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从而使这些问题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形成政策问题。可以说,党组织和政府是我国各种重大政策问题的主要提出者,在政策问题的提出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从政策输入的角度上看,所谓政策问题就是反映不同利益的问题,政策问题被发现和提出的过程就是人民群众或社会利益群体反映和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促成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予以满足的过程,也是党组织和政府集中与综合这些利益要求并通过政策制定予以体现确认的过程。简言之,政策问题提出的过程就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过程。只不过,在西方,由于其社会利益结构分化明显,压力集团作为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比较发达,其社会性利益表达现象也比较普遍、有力,所以,西方的政策输入过程更多地表现为各种政治力量的社会互动过程。而在中国,由于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分化并不那么明显,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较为明显的多元利益结构,也没有分化出相应的利益集团以及其他社会性的政策输入结构,所以,基于党组织和政府群众路线的决策规范,以及党的领导和政府官员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和决策方法,当代中国的社会性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并不主要由社会性结构来承担,而主要是由党组织和政府内部的各级官员们来体察和认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利益表达与综合的社会互动过程,相反,近年来这一互动过程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趋势(注:胡伟:《政府过程》第17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笔者在这里只是想说明,在当代中国,党组织和政府在对社会利益表达的认定和利益综合方面显得更为重要。在政策输入过程中,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制定系统外部的社会利益群体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政策中枢)中去,而主要是由党组织和政府官员们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认定和利益综合的输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输入过程呈现出“内部输入”的一般特征。当然,这里的“内部输入”的一般特征只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说的。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输入都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性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政策制定者对社会利益的主动认定和综合总是必不可少的。西方的政策输入功能并不完全由社会利益集团来承担,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认定和综合作用也很重要;而中国的政策输入功能也并非完全是由党组织和政府官员们来完成的,社会性利益群体在基础性的利益表达和初步的利益综合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只不过中国的社会性利益群体更多的不是作为利益集团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而是较多地发挥了在党组织和政府与人民群体之间沟通信息、反映情况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性利益群体更多地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政府整合特征,这可以看作是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它们在政策输入过程中所承担的基础性利益表达和初步利益综合功能也可以看作是党组织和政府“内部输入”功能的一种合理的非政府延伸。与此相适应,它们在政策输入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并不具有多少社会互动的色彩,而是与党组织和政府“内部输入”功能交织在一起。“它们既代表一部分群众向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表达意见,又常常反过来协助党和政府做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群众的工作,而不是简简单单地施加‘压力’”(注: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8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从而使当代中国的政策输入过程表现出高度的政府整合性和组织化一体性。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政策输入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内部输入”特征。当然,如果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认为这种内部输入过程中也有互动的话,那也只是公众与党组织和政府、党组织和政府内部的上级与下级之间信息沟通性质的互动过程,而绝不是西方那种政策输入性质的社会互动过程。
如前所述,在政策输入过程中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过程也就是政策问题的提出和政策议程确立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同质的,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基于群众路线的决策规范,党组织和政府在政策问题提出和政策议程确立过程中的权威地位和主导作用,使得很多问题常常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进入政策议程,这只是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中国政策输入过程中“内部输入”的一般特征。这一特征使中国政策问题的提出更多地使用内在提出模型和动员模型(注:[美]罗杰·W·科布:《比较政治过程的议程制定》一书中把政策议程的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内在提出模型、动员模型、外在提出模型。载《政治学评论》第70卷第126~138页,1976年。),而较少使用外在提出模型;亦使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更多地呈现出“单方案决策”的特征(注:孙光:《现代政策科学》第13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不是多方案的择优。正因为如此,政策输入成功与否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决策和政策合法化反而显得没有多少实质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立意的要旨之所在。
三、内部输入机制:途径分析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当代中国的政策输入过程主要地表现为一种“内部输入”。这只是从一种较宏观的、总括性的层面上加以分析的。具体而言,在这种“内部输入”大框架的观照下,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各种利益要求究竟是如何被输入到政策中枢中去的呢?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进行的呢?笔者认为,中国“内部输入”机制的途径也即政策议程建立的途径主要有以下诸项:
第一,结构内的组织体制和工作程序。这是内部输入机制下最主要的也是制度化、程序化的输入途径。党和政府都从上而下地建立了层层控制的严密的组织机构体系,上至中央和国务院,下至党的基层政权,甚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都承担着大量的经常性的利益表达与综合的功能。这些组织机构通过一定的工作程序,基于群众路线的决策规范,主动地考察和认定各种社会利益要求,然后自下而上层层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直至党和政府的政策中枢系统,从而完成整个政策输入过程。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政策输入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与综合的组织结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各级人大和政协组织也是群众性利益表达和初步综合的重要途径,承担着一定的政策输入功能。作为社会各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通过提案、建议、批评等形式直接进行利益表达和一定的利益综合。另外,笔者认为,“内部输入”机制下,中国政策输入的结构内组织体制途径还应包括各民主党派和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它们也承担着一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功能。
第二,内部沟通通道和非正式关系。所谓内部沟通通道是指党组织和政府等政策中枢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具体而言,中国政策中枢系统内部沟通通道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会议、讨论、通报、批示、文件传递以及体制内的政策研究机构提供的内部政策建议或咨询报告等。一般而言,内部沟通通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它在政策输入过程中亦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利益表达和综合最终都必须通过内部沟通通道才能到达政策中枢系统。可以说,内部沟通通道是政策输入过程的必经途径,与内部沟通通道紧密相联系的是非正式关系。如果说内部沟通通道是内部信息传输的一种正式渠道的话,那么非正式关系则是一种非正式渠道。所谓非正式关系,是指未经规划并超越于法定组织制度和工作程序以外的某种关系(注:桑玉成、刘百鸣:《公共政策导论》第12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它具体表现为亲属关系、老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老乡关系、师生关系、亲朋好友关系等人际关系。通过这些非正式关系可以传输一定的政策信息,甚至进行一定的利益表达和综合,履行一定的政策输入功能。由于采用非正式关系途径的政策输入者较容易或直接接近政策制定者,同时政策制定者对此种途径所体察和认识到的利益要求和政策信息亦相当信任,所以非正式关系途径在政策输入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正常的结构内组织体制政策输入途径不那么畅通时,这种非正式关系的政策输入功能就会日益凸显。
第三,大众传播媒介。“公共舆论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注:[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第95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最主要的公共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而且它在政策输入过程中亦履行着一定的利益综合功能。各种利益表达一旦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支持,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就会对政策中枢系统形成一定的压力,使其主动体察和认定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从而使政策输入过程变得比较顺畅。更重要的是,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联结人民群众与政策中枢系统的桥梁,为很多无法直接与政策中枢接触的基层群众的利益表达开辟了通道,从而扩大了政策输入的来源。而且,作为一种政策输入途径,大众传播媒介可以直接向政策中枢反映利益、愿望和要求,从而大大缩短了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建立的时间,有利于政策问题的解决。
第四,调查研究。基于群众路线的决策规范,党组织和政府等政策中枢系统的政策制定者有时直接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主动发现问题,了解情况,从而对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要求主动进行体察和认定,并直接建立政策议程(并不经过公众议程)制定政策予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策制定者在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和综合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和绝对主导作用,政策输入过程异常地顺利、直接、迅速,政策问题很快获得解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调查研究成为政策输入的一种重要途径,而且是“内部输入”机制下最富有特色的独创性的输入途径。
第五,体制外压力。相对于那些在现行制度框架内的合法化的政策输入途径来说,体制外压力是一种与现行制度不相容的强制性的利益表达方式。它主要是指某些个人或群体采取激烈的方式,向政府中枢系统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提出他们的政策问题,以期获得解决。当然,这种体制外压力方式所表达的利益要求能否最终获得满足,则完全取决于政策中枢系统对它的体察和认定,这是内部输入机制下所导致的必然结论。然而,应当看到的是,采用体制外压力方式进行利益表达的普遍化无疑会对正常的政策输入过程产生巨大的副作用。所以,应疏通和扩充政党的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策输入途径,尽量避免采用这种体制外压力的利益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