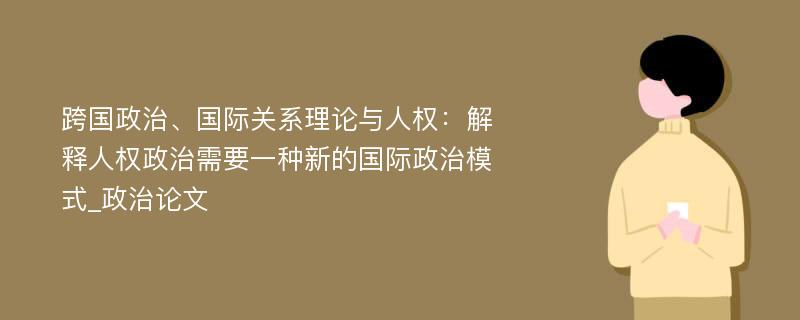
跨国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及人权——解释人权政治需要一种新型的国际政治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人权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下半叶,人权问题作为一种国际政治问题的兴起,使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们感到迷惘。我们许多主导政治理论——现实主义、理性选择和经济利益集团理论——在解释人权政治出现的原理时都不能自圆其说,它们都反对排除一个边缘的、不重要的或意识形态的幌子,即经济利益集团和霸权国家追求着自身的利益。但是其他论文和新闻报刊十分清晰地表明,人权问题并非是边缘性的。日益详细的政策和制度机制的存在能保证国际人权标准的完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政策对人权实践会产生直接影响,有助于减少政治压制和政权更迭。
福塞斯(D.Forsythe)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论点无可辩驳,即政治学家应该对国际范围的人权问题作出充分理解和把握,然而,这一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均遭到了忽视,使人权成为一种研究课题。原因之一是,主导政治理论没有为我们提供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的研究方法。人权观念和政策也未能影响国家运作,人权政治的出现促使我们去对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政策,以及为什么这些政策有时会导致国内的重大变化作出解释。实际上,任何一个解释人权兴起的理论都必须将标准和观念的政治力量和那些人权观点超国界的传播和扩散方式等因素考虑进去。另外,为了理解人权政策如何使国内产生变化,我们要知道这些观点是如何为国内反对派开辟空间和时常重新民主化起作用的。
理解这些变化十分重要,因为人权正是当今政治科学诸多研究领域之一,因为国际人权标准问题的地位影响着社会和国家主权,特别是,人权问题时常给主权国家体制的中心逻辑提出有力的挑战,正如布尔(H.Bull)在其名著《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所言:
将这种逻辑发展到极端,国际法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是对人类应被组织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社会这一原则的破坏,因为如果在政治舞台上,每个人的权利维护都超出并反对其国家的要求,而每个人的义务表达则完全不考虑他是奴仆还是公民的地位,那么,国家作为统治其公民的主体的权威地位,并赋予其命令公民服从的权力,将受到这种挑战的抵制,主权国家的社会结构就会在摇摇欲坠中更替。这为用另一种世界主义组织原则来颠覆主权国家开辟了道路。
我认为,从一个有限的和不完善的意义上讲,这一“方案”将在20世纪末被取而代之。新的模式与布尔所言的“新中世纪主义”很相似,非国家作用力开始削弱国家主权的地位,一种新型的“重迭的权威和多元忠诚”的体制出现了。布尔激励研究者们实证这些变化的本质和外延,并详细说明哪一种国际政治视角可以修改和取代主权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心地位,国际关系学者和法学专家们已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并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为了理解这些挑战在国际政治学人权领域中的地位,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我们关于国际政治学的规范和观念的理论。对这些规范和观念的关注总能活跃国际政治的研究。然而,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模式总是片面地转移对这种规范和观念的关注,直到80年代早期的政权学说为更广泛地研究关于观点和规范以及80年代末和90年代国际关系学说为社会架构的研究开辟新的道路为止。然而,这些研究都未能融合成国际关系中一种更加统一的规范和观念理论,因此,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建构关于规范的起源和效力的更一般的理论是必要的。
为探索和拓展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规范理论,人权问题显然是一个特别有希望的事例;人权问题的研究为寻求上述问题的解答开辟一些视角,政治科学家将就既定行为者的适当行为规范的定义达成一致,规范如何影响行为,是一个包含两个阶段的过程:“规范出现”阶段和普遍接受规范阶段,即法律理论家萨因斯坦(C.Sunstein)称之为“规范串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有一个分水岭,即接受规范的有关国家的临界数,我认为,共同宣言中许多国际人权规范所取得的进展标志着我们已经超越了规范出现阶段,并自70年代后期以来进入了国际人权的规范串联阶段,这一主张的支撑点不仅仅在于批准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数量,而且在于国家将国际人权纳入其外交政策和国内法律的程度。
大多数人将注意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人权规范日益重要,但同时全球范围内人权日益遭践踏的时期,然而,人权破坏事件的出现,不应该使我们忽视在其他地方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东欧出现的重大的人权改善。的确,对人权破坏意识和政府对此破坏反应不足的批评程度,部分地成为人权规范对期望的外交政策影响的指示器。
这些规范最初是怎样形成的呢?一些理论家认为,当这些国际规范受到霸权的拥护和支持时,它们就出现了。例如, 克拉斯纳(Krasner)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权问题最能反映那些拥有经济和军事优势的国家所关注的问题。但这些理论家没有就为什么霸权国家开始关心人权政策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现实主义不能给出一个解释来说明人权方面的霸权行径的社会目的。为什么英国决定用他们的海军力量去结束奴隶贸易并最终废除奴隶制?为什么美国采纳人权政策?在60、70年代,一般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它支持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共产党集权统治,但是为什么在70年代中期,也就是冷战结束前,美国改变了它的利益认识而开始率先制定一种人权政策呢?
有关这些规范的研究表明,许多国际规范的起源并不在于业已存在的国家利益,而在于强制性的原则观(是非观)以及使其他不同的观念同化的意图。纳德曼(Nadelmann)把这种意图叫做“道德改宗”, 并把执行这种意图者叫做“跨国道德的倡导者”这样的道德改宗时常包含改善国家对待个人的规范或个人之间怎样相互对待的规范。国际人权规范的研究揭示了个人在这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反种族灭绝会议把“一个非凡的贡献归于波兰法学家莱姆金(R.Lemkin),他在1994年创造出种族灭绝一词, 并帮助推广这个词的使用,由此促成了反种族灭绝条约的起草和顺利通过。 三位司法专家在制定国际人权保护规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智利的奥万瑞依(A.Alvarez)、俄罗斯的曼德斯坦姆(A.Mandelstam)和希腊的弗兰高利斯(A.Frangulis)首先在两次大战期间起草和公布国际人类权利宣言。这种人权思想被独立地纳入到战时英国作家威尔斯(H.G.Wells )发起的关于战争目的争论中。虽然非政府组织在人权规范的起源方面发挥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但时常是,政府内部或国际组织内部的规范倡导者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结果导致人权规范的出现。在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语言是与政府有联系的个人(像埃莉诺和罗斯福)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大赦国际在1973年反践踏人权运动中所创造的、有关践踏人权的全球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是政府官员与大赦国际协商安排了反践踏人权会议。
对个人来说,人权规划的发展是不够的,他们必须通过紧张激烈的运动来提高全球范围的人权规范标准,在许多已经出现的国际人权规范中,跨国联合或者非政府组织中个人联络有助于引导重大跨国运动,并说服他人认识新规范的重要性和价值。反种族隔离运动、反对奴隶制运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国际人权运动和消除对妇女暴力以及最近的反使用地雷运动都是这样的事例。考威特(Kowert )和莱各罗(Legro)把这个过程称作“社会扩散”,对通过网络为倡导规范而进行的积极工作来说,那是一个太被动的类型。规范不会自由地传播,也不要期望新的集体在理解规范时像墨迹一样深深渗透到网络中去,网络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是所有的国际运动都会导致规范被采纳,有许多大规模运动不成功的例子。
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最终需要得到强有力的国务活动家的支持,他们批准这些规范,并把它们的社会化作为他们议事日程的一部分。这些早期规范倡导者把对规范的关注变为强国政策制定者所关注问题的过程,几乎是一种纯粹的劝说。这些团体和个人一般具有传统意义上强大力量,但也不能就规范强制达成一致,他们只能靠有关规范的论据力量和事实去支持他们论点并使之受到注意,网络和道德倡导者常常通过他们的语言、信息和象征性活动来重新界定一项活动的是与非,人权政策的出现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对利益的胜利,而是显示了重新理解国家利益的思想威力。人权政策的采纳并不是忽视国家利益的表现,而是表示对长远国家利益认识上的根本转变,人权政策的出现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开始对一个国家人权状况不是合法对外政策的主题的基本观点和支持侵犯公民人权的压迫式统治来促进国家利益的随意假设提出质疑。为了理解利益认识变化的来源,我们需要看看国内外的规范倡导者为改变国家的政策而开始进行的努力。
一旦规范出现,我们还要解释为什么一些规范特别有影响力,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规范都是同等重要的,但我们没能形成清晰的理论去解释为什么有些规范是“串联式的”,而有些则不是。在人权案例中,我们怎样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它们会变成当代极富吸引力的政治思想,正如福塞斯引用布热津斯基所说的。
在关于规范作用条件的文献中,有一系列的假说。霸权社会化说认为,要解释哪些规范将有影响力,就得考察哪些规范得到霸权主义者的最有力的拥护。然而,这种解释不能说明在霸权内部规范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主要的人权胜利不是霸权压力的结果,在人权变化的一些基本事件中,如妇女选举权,全球反种族隔离运动,霸权主义只是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
规范传播的另一种解释是,那些在国内确立的规范(不只是在霸权国家而是在更广范围的国家)变得国际化。拉姆斯登(Lumsdaine )提供的广泛文献证明,外援的规范根植于国内反贫困的规范中,在许多方面就是福利国家的国际反映。说国际人权规范显然是国内人权规范国际化的结果时,这种解释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规范的国际化会一直跟随国内规范的进程(从1948年的人权共同宣言到1789年法国人类和公民宣言赋予法国公民的国际权力),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中,国际化跟随得更为直接。然而,有证据表明,国内和国际的规范进程日趋同步进行。例如,国内和全球反对家庭内部殴打妇女和对妇女使用暴力,在很多情况下是一同演变的。国际规范应用刺激国内变化,反之亦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哪些国内规范能够成功地国际化。许多国内规范难以国际化,而其他一些则易于取得国际响应。
福塞斯把国际合法性作为解释国际人权规范日益需要的一部分,然而他认识到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是多样的,为什么国家要关心国际合法性?为什么和怎样使人权逐渐变成一个合法性的尺度呢?
我相信,人权规范包含着某些内在特性,给它们力量和感召力。人权规范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它界定了适当的行为规则,它有助于确定自由国家的特征。然后,人权变成了衡量进入和退出自由国家俱乐部尺度的一部分,社会学的制度主义研究表明,融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于一体的西方文化规范将会特别强大。然而,尽管许多西方规范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相和谐的,但只是其中一个子集才有强大的跨国影响,包利(Boli)和托马斯(Thomas)已经对这进行了某种提炼,并归纳出世界文化的五大原则:普遍主义原则、个人主义原则、自愿主义的权威,理性进步和世界公民。凯克和我已经提出了更为专门的主张。我们认为,有两个广泛的规范范畴在国际上和跨文化上特别有效:一是那些脆弱的或“无知”的集团,它们需要保护身体的完整性和防止体伤,特别是当它们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时;二是法律上的机会平等规范。规范倡导者必须对超越特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信念系统和生命世界方面作出解释,尽管身体伤害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上已经有解释,但它们与大多数文化共有的人的尊严产生共鸣。如果拥护规范的一个基本动机是移情作用,那么,我们将期望跨文化规范基于一个起移情作用的人类共同特征之上。但包括身体伤害在内的问题,并不会发展成为“串联”的国际规范。要使这些问题受人注意,就要求国际规范倡导者努力使它们得到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注意。例如,跨国规范倡导者在网络上组织起来,已经成功地用传递身体伤害的图像的方式在特定国家发动反践踏人权的跨国运动。关于问题内在性的争论表明,不是所有的人权规范是同等重要的,并且,我们希望一些人权规范比其他规范更快、更广地被接受。
总之,希望理解人权政策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们需要有一种不同的国际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种国际社会,不仅由国家组成,而且还包括具有跨国身份和为多方负责的非政府组织。当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继续是一个中坚力量时,它们的行为不能被理解成是无政府主义的自我救助,而是应该被理解为由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社会的成员的行动。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行为可能变化,这不仅因为制裁经济的成本,而且还因为国家领导人关心其他国家领导人怎样看待他们。正如费隆所说,人们有时遵循规范,因为他们要其他人看好他们,也因为他们看好他们自己,人们看好自己的能力受相应团体固有的规范的影响。国际法学者通过把国际法视为“文明国家”社会内相应的法律,早已认识到这个关系到许多人的规范的本质。今天,文明化国家的思想已经失去风格,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依然是陈述社会规范和赋予集体合法性的基本工具。一些法律学者正在讨论一种“自由国家”社会,将其视为和平、民主、人权的一个范畴,并以此来区分“自由国家”与非自由国家之间的关系。人权规范有根本的影响,是因为好的人权表现是他国把它确认为自由国家社会的一员的一个必要标志。政治科学家需要特别注意人权政治,不仅因为它具有提升人类尊严的潜力,而且因为人权问题对于开拓国际政策可选模型来说是特别有用的事例。
摘自《美国政治科学与政治》杂志199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