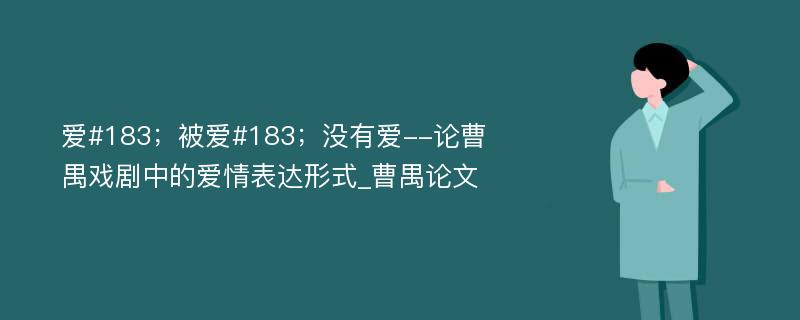
爱#183;被爱#183;无爱——曹禺剧作爱情表现形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论文,形态论文,爱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曹禺为数众多的优秀剧作中,有相当部分以爱情为题材,其在剧作中的情爱表现具有独立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曹禺以构建错综变幻的情爱冲突著称于世,他的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其爱情表现的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型:爱,被爱,无爱。
一、爱——精神历险的甘苦悲欢
在曹禺剧作中,爱情被赋予它所特有的诗意和美感。既洋溢着追求生存幸福的活力与热情,又透露出人类向真善美的崇高境界迈进的憧憬与追求。曹禺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写了爱情,更在于他深刻地揭示了爱情对于人生的超验意义。
在《雷雨》大量的情爱纠葛中,人们自然不会忽略青春期的周冲对四凤至纯至真的爱。他那颗涌动着情感的激流的心在兴奋、幸福中摇漾,他向四凤吐露的心声是一首明净、感人的诗:“我象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朗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象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象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尽管人们可以有一百种理由否认周冲这种感情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却无法否认这种感情的真实性,无视它所具有的灵魂震撼力。周冲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眼光,来看待那个他几乎一无所知的女性世界的,并由此形成了他的心理期待和情感倾向。善良、单纯、平和的周冲视四凤为他心中的偶像、精神的引导者。他迈出了人生中心理和情感历程的重要一步,兴奋激动又羞涩心怯,燃烧的爱情之火激发了他追求善和美的热望,以向所爱的人奉献一切为幸福,他无限憧憬、跃跃欲试,尽管目睹了父母失和的变故,仍未动摇和摧毁他的痴迷情怀。然而,年幼的周冲显然缺乏对爱情成长过程中所要承受的磨难的足够的心理准备,并付出了超乎寻常的代价。
如果说周冲对于四凤的爱由于特定年龄和身份而具有浪漫诗意的话;那么,繁漪对于周萍的爱却是那样地沉重滞闷。在繁漪最需要情爱的年龄,却被无情地幽闭在冰窟一样的周公馆,在她心中燃烧、奔涌着的是一个成熟女性对自己生命的热烈的情欲,她对周萍的爱,使她真正地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她置名声和道德律条于不顾,爱得那样地决绝、热烈、刻骨铭心。她为挽救和延续与周萍的爱费尽了心血,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自尊和他人的利益。对于她近乎疯狂的情感,我们似很难用资产阶级的生活准则之类的话来准确说明其内涵。事实上,繁漪的爱的权利是一个女性的本能和自觉,只不过由于特定的境遇她表露得更加大胆和离经叛道,也因而赢得了剧作家的偏爱。她是曹禺剧作中一个率真、勇毅的精神女神。我们无法指责繁漪为爱所做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应当谴责和诅咒的是给予繁漪种种不幸和灾难的罪恶社会和封建礼教。繁漪的悲剧还在于,她忽略了为她所爱的人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情感是无法由她绝对控制和管束的;她毕竟不是他,他们有各自独立的情感流向,一旦他厌弃和背叛了那一切,挽回的可能只是虚幻的。也许,在繁漪,这是一种命运;对于将爱情视为生命第一要义的繁漪,这种命运又是怎样的的凄苦!
我们曾经一度否认周朴园对侍萍的爱,因为他是那样的粗暴、恶劣、充满铜臭气地面对侍萍。然而,试品味剧本的序幕和尾声部分,我们会分明感受到人生暮年的周朴园在四面楚歌的凄惶处境中,并未泯灭他对侍萍的爱恋与疼惜,即使他曾有过将侍萍母子赶出家门的举措,即使他曾对从天而降的侍萍满怀敌视的警觉,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在青年时代的浪漫情怀中对侍萍曾有的痴心爱恋。人们往往说周朴园是出于维护其家长的权威形象的动机才做出纪念侍萍生日、保存原有家具、保持侍萍的起居习惯等等行为的;然而,难道在周朴园的行为准则中,他的家长权威真的要靠这些生活琐事来建立和维持吗?在他和侍萍分别的三十年中,依然极其珍视那件侍萍曾亲手缝补过的衬衣,其中所包含的睹物怀人的情感意向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周朴园固然有其政治上反动、思想上没落的特征;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人,在家室之乱之累的可悲境遇中,他对侍萍的那份情思亦自感伤哀切。
在曹禺的许多剧作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诸如此类的现象。愫方对于曾文清的爱,无怨无悔,曾霆对袁圆的爱诗意葱笼;方达生对陈白露的爱痴情万种……值得深思的是《原野》中焦大星和仇虎对金子的爱。大星作为金子的丈夫,为金子的容貌倾倒,为金子的女性魅力沉迷。但他对金子的爱是怯怯弱弱的。这一种精神萎缩的病态人格所导致的自卑情结下的可怜可悲的情感状态。在他身上,爱是粘乎乎的,没有激越慷慨,没有灵魂碰撞搏斗的火花,也没有血气的浇灌,所有的只是哀求,受伤的弱者的乞怜,缺乏舍身赴难的义勇。以一种仰视和巴结的姿态来吃力地维系本不坚牢的婚姻基础。这种爱的不平等正是导致他们的婚姻走向死亡的内在原因。
与焦大星相反,仇虎浑身洋溢着男子汉的刚勇威猛之气,他顶天立地,敢作敢为,具有狂风暴雨一样的激情冲动。他爱金子,但在他对金子的爱的内在心理构成中却渗透着强烈的复仇意识。他以占有金子——焦阎王的儿媳妇(这是中国传统伦理规范中的奇耻大辱)为快意,以谋求自己的心理平衡。同时,如果说焦大星心理中不乏自虐倾向的话,仇虎则具有明显的他虐倾向,他对金子的情感既单纯又复杂。金子既是他当年的恋人和未婚妻,又是他仇人的家庭成员。为了他自己和家族的利益,他把对金子的占有视为雪耻的一种方式。在他抛戒指、扔花的等等细节中,透露出他的他虐倾向。他要到金子的房里、焦阎王的家里去做一件在传统礼仪观念中最恶毒的事。在这种意义上,金子不仅仅是他的恋人情人;而且,在潜意识中,也是他发泄心中仇冤的惩罚对象,只不过这种惩罚采用了独特的方式而已。人们或许认为,仇虎最后的失去理智,神智不清显得荒诞不经,其实,证之以前此的言行,可发现仇虎不仅有他虐倾向,而且也有自虐倾向。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这两种倾向往往是伴生共存的,仇虎对自己容貌(丑)、形体(折了一条腿)的自我感受、由自虐心理生出的对于环境的恐怖、忧惧、与金子偷情而产生的愧怍的心理重负,都导向了他最后的精神失常。的确,家人惨绝的下场,本人在狱中多年的非人生活,都极大地影响了仇虎的心理,扭曲了他的人格,使他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曹禺从呼唤人性解放的崇高追求出发,高扬人道主义旗帜,对人们的爱情追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烈的颂扬,极其深入地发掘了有着二千多年专制历史的中华民族人性解放历史进程的沉重艰难。曹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能够深切地逼近剧中人微妙的内心世界,充分揭示主人公在追求爱情过程中情与理、灵与肉的矛盾,深潜的内心冲突中所包蕴的多重意义;向罪恶的社会发出了猛烈的攻击征战之声,向封建礼教的最后防线发起了挑战,具有强烈的思想意义;站到了近代进步思想的最潮头。
二、被爱——聚散难得两依依
爱与被爱本应是对等的、均衡的;付出与得到亦应是同步的。然而,由于被爱者的个性、心理、人格等原因,特别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被爱者并不一定能够践行自己的心志,大胆去爱爱自己并为自己所爱的人。这其中,在曹禺剧作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文清和高觉新。
曾文清,这个没落世家的长子,以他的清婉、柔纤的个性赢得了愫方的倾心。他对婉丽、柔美的愫方也极称赏,情有所钟。尽管愫方一再以特有的方式寄寓和表达自己的爱,然而她从曾文清那里所得到的回应只是一无所有的虚空。曾文清切实地感受到了来自愫方的爱的呼唤,他尚未最后死寂的心在颤动,甚或会把愫方的一片痴情当作自己战胜污浊环境和自身婚姻灾害的精神支柱。然而他是那样地怯弱、懦怩;他不敢跨越传统礼教雷池的一步,甚至失去了在妻子面前堂堂正正做人的颜面、勇气和资格,只能一天天地浑浑噩噩地苟存性命。他的内心充满了自私、卑怯的因子;人们可以发现他对愫方的牵系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斟酌。面对暴戾、蛮横、粗野的妻子对愫方的羞辱,对于他和愫方之间情感的践踏和玷污,曾文清是那样地无力和无能。他既无力保护爱自己的人,亦不能给予爱自己的人以切实的情感补偿和心灵慰藉。所能做的,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愫方,用他特有的充满怨艾、委屈、乞求的目光牢牢地牵缠着愫方。难道这不是一种残酷的占有!愫方曾怀着殷殷的期待之心,祝祷他能飞出曾家这个精神牢笼,振翅翱翔,砥励自己,成为生活的强者,自己命运的主宰。为此,愫方在曾家忍辱含垢,代行孝道,连他素所喜爱的字画、鸽子都悉心呵护。然而,这位曾经向爱自己的女性发誓“除非天塌了就不再回来”的曾文清,在仅仅离家出走的二个月之后,就灰溜溜地踅进幽暗破旧的庭院,高卧烟榻,重新开始了他梦魇一般鬼蜮一样的生存。他再也不会飞了!他对爱情的不认真和虚浮之气,伴随着人生境遇的凄冷衰微,使他跌入了黑暗的深渊。失去愫方的爱,也最终失去了灵魂的依托,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振作和重新开始的可能。他的软弱、缺乏勇气和力量导致了自身生命的全面失败。《北京人》在社会、文化的层面固然对传统礼教规范进行了凌厉的声讨和攻难;而在民族的情感层面,由“北京人”所传达的“大胆地爱”的精神追求,正代表了作家的心声。面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的萎靡、衰微,作家以情感问题作为了寻求振奋民族精神的途径的艺术切入点。
与文清相近,觉新的情感构成亦极复杂。梅表姐在他心目中无疑占有弥足轻重的地位,是他青春生命最可珍惜的财富,觉新迫于环境的压力,未能与梅缔结婚姻,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把梅推入了苦难的生活与情感的地狱;而且,也使自己堕入了无尽的负罪心理的折磨。觉新的情感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背叛了和梅之间的默契。冷静剖析觉新对梅的情感取向,梅身上特别浓郁的东方女性的诗意、温雅,的确牢牢地攫住了觉新的心。即使在出嫁守寡之后,梅依然在奉献着自己的情思,觉新试图和梅维持精神之爱的关系,既有要对梅给以扶助的意愿,更有为自己寻求慰藉,寻求精神支撑的考虑。尽管善良、敦厚、善解人意的瑞珏对觉新一往情深,用一种混合着崇拜心理的牺牲精神待他;但,在觉新先天性干渴的心田,瑞珏的充满母性的爱的滋润还是不够的。觉新的痛苦来自于对梅的深深歉疚、对自己人生失误的懊悔,这使他无比地痛恨自己、进而折磨自己,一遍一遍地审判自己,最后却又几乎一无所得,觉新陷入了“情感怪圈”,始终无力自拔,灵与肉分离之苦的煎熬、感情天平的没有定律的摇摆,使觉新为自己的软弱付出了惨重酷烈的精神代价。
同是被爱的角色,陈白露之于方达生更能引发人们探究的兴趣。陈白露自从脱离了原来的群体,沦入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情妇不是情妇的境地,心中郁结着许多的愁怨和不甘。她缅怀曾有的朝气和血气,极其珍惜一个痴心男子为她奉献的真挚恋情。当方达生在几年别离之后,再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并初衷未改仍倾心于她时,她的内心掀动着情感的狂涛巨澜。方达生用率真的心弹奏出的爱的乐意,摇撼着她的全身心。由方达生的爱,她复苏了对美好纯洁生活的热烈向往,一声充满怜惜与忧伤的“竹均”的轻唤,竟使她那样地欢喜兴奋。和纯真、朴实、爱意无限的方达生在一起,她解去了日常穿惯的铠甲,轻松自如。然而,陈白露毕竟不再是过去时代的竹均。她的性情、心理、价值取向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异。她的机敏、聪颖中掺进了世故的圆滑和取巧。她所追求的不再仅仅是空灵的情与诗。她要活得有身份、有地位、值得。面对这个“乡下人”一样的痴心男子,陈白露极其清醒地意识到了他们之间在人格、情感、阅历各方面的距离。方达生不可能再度成为她的恋人,她不需要他这样的丈夫。所以,她是以一种朋友式的心理情态来面对方达生的。也许,他们可以共患难;但他们绝不可能同享乐。他们可以齐心协力面对共同的敌人,却无法真正坦白地面对他们自身。陈白露对方达生,有柔密,有女性的温情,甚至有撒娇,但同时也溶入了不屑、奚落的冷淡。方达生身上的土气乡气使她觉得格格不入,她更倾向于浮华、狂躁,在方达生的正直、纯洁面前,她感到一种精神的压力。
面对方达生热烈的求婚,陈白露的一番话“我要人养活我……”向来被视为她堕落腐朽的“自供状”。然而,我们却忘了,陈白露、方达生、或任何一位善良的人,都有资格享受那一切,都有权利拥有那一切,这也是人生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谁来说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只在于通过什么方式获取这一切。陈白露是一个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虽然她不得已而生活在附依他人的境地,但在她性格中充满了极强烈的维护自尊和个性独立的成份。从某一方面讲,方达生所说的二十四小时给予回答的要求,是对她自尊心的伤害,她容不得这样的轻慢。所以,她所宣布的自己的生活标准,只不过是吓退方达生的武器。更深一层的心理内涵,我觉得,却是在方达生的纯朴、真拙面前,陈白露有一种由于别后的“不洁”而来的自卑感。她善良、厚道的一面使她不愿以自己的“不洁”辱没了方达生的纯情。尽管,她极度厌倦现在的生活,急欲摆脱,重新开始,但她不愿使自己成为方达生的累赘和债主,她拒绝了方达生,也就是给了方达生以自由投注其感情的权利。她以仅有的余力,为方达生的幸福做出了点滴的却是极可贵的大奉献。因而,陈白露的形象主要的是善的形象,她的悲剧,也是善被毁灭的悲剧。
周萍对于繁漪的爱的别弃,在道义的角度看来,无疑是极端自私和残酷的。在中国传统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审美模式中,他扮演了一个可鄙和丑恶的角色,自应受到唾弃和指斥。然而,周萍作为一个人,他和其他人一样有选择或重新选择其情感投注对象的权利和自由。如果面对繁漪的情感攻势,他屈服于良心和道义,不仅自己无幸福可言,给予繁漪的也只能是新的枷锁和牢笼。因而,他对繁漪的抛弃有着合理性。固然,繁漪在这场情爱角逐中所受到的心灵创痛令人叹息;但是,周萍被裹挟在二个同样爱自己的女人中间内心所受的荡涤和挤压也是沉重、痛苦的。我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剧作家才希望扮演这一角色的演员能为周萍找到同情。这一情感态度乃是剧作家理性思维的归宿。在周萍的情感灾难中,隐含着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难题。尤其是崇高德政的中国民众,要跨越“周萍式灾难”,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的生存谋取更多的自由,使每个人都全身心地获得解放就会更加艰难。尽管周萍有着令人难以容忍的自私、怯懦等劣点,但这并不排除他灾难中孕含的启示意义。
爱情是一把利剑,能在强大的生命体上砍斫出耀眼的火花;能使精神孱弱者受伤或致死。无爱是痛苦的,无力面对爱同样也是痛苦的,而在犹疑彷徨之中失去所爱的人则是更大的痛苦。
三、无爱——没有胜利者的婚姻悲剧
婚姻与爱情的背离,在旧中国的婚姻模式中乃是一大通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缔结方式,剥夺了人们在婚姻成为事实前建立感情的可能性;而“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观念又构成了婚姻生活中培养或增进感情的障碍。传统礼都对人的情感的岐视和禁锢,由此导致的一般人对情和欲充满罪恶感和耻辱感的心理积淀,都使传统社会的婚姻构成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生存的“合理”形式而已,婚姻是不独立的、是为他的。近代思潮的冲击,腐朽道统的瓦解,人们开始了大胆尝试新的追求的努力。然而,人们自强、奋斗的进程是那样艰难,婚姻只是作为一种躯壳,一种纯然外在的形式,一种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背负的枷锁仍屡见不鲜。曹禺多次写下了婚姻中根本无爱者的痛苦和血泪,以透彻地分析这些主人公们的复杂心理和尴尬处境,呼唤民主自由之光彻底照亮我们民族的天空。
在周朴园和繁漪的婚姻中,繁漪完全是被动的。无论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走进周家,成为周朴园的妻子和周公馆的女主人,她在过去和其后的生活中,都未曾燃起对周朴园的爱的热望和情的欲念。她不爱周朴园。在她眼里,他只是一个暴君,一个自由与幸福的剥夺者和毁灭者。她冷眼斜睨着周家的崩溃,以及周朴园所标榜和崇尚的体面、权威的瓦解。恶意地、充满报复情绪地对抗着周朴园,以增加周朴园的不快为乐事。她蔑视周朴园的权威,憎恨和诅咒在周公馆这座精神的囚牢里所过的暗无天日的囚徒一样的生活。最终,她勇敢无畏地撕下了周朴园的假面具,摧毁了周朴园苦心孤诣营造的体面家庭。繁漪本是受过近代文化洗礼的知识女性,她有过人的聪慧、天生丽质,内心有着对美好情感的渴望;然而,上帝却安排她生活在冰窟里,她性格中怪戾、阴鸷的因素和最后的疯狂,同她在周朴园面前所承受的精神压抑、性压抑等有着极重要的联系。她为这场婚姻悲剧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于自身缺乏更高的追求和更有效的反抗而可悲地成为周朴园的牺牲品。也正是由于这种无爱的现实,逼使她失去了最可贵的对于孩子的责任感,成了一无所有的精神与情感的赤贫者。
毫无疑问,周朴园也不爱繁漪。在这场婚姻悲剧中,他也是一个牺牲者。他所希冀于妻子的恭顺、乖觉,绝对地服从,繁漪并不具备。他感情地闸门自始至终未曾向繁漪切实打开过。他的理智驱策他只是把繁漪看作自己的统驭对象和惩治对象。在他对繁漪的颐指气使、暴烈狂躁中,不仅有封建家长的专制精神和权威意识,而且潜意识中还具有虐待和惩罚的因子。如果说他常年在外即使偶尔回家也忙于应酬的生活方式是出于他社会角色的需要;那么,到晚间一个人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就不仅仅是为了安逸,更多的是回避繁漪,冷遇她——虐待她。如果说,周朴园的内心深处仍埋着对侍萍的思念根子过于牵强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在和繁漪缺乏爱情的婚姻中,聊以慰藉他干涸心田的也只有他对和侍萍度过的日子的怀念和咀嚼;而这,又反过来使他更坚执地推拒繁漪。周朴园既强大又渺小,既充实自信又空虚无奈,和他在事业上的春风得意,事事遂愿相反,生活的、情感的重负才是使他最终颓然废然的根本原因。
随着时代的巨大变迁,人们也许不再特别注目于侍萍和鲁贵的婚姻,只是觉得乏味、平淡而已。侍萍清醒而痛楚地和鲁贵这样一个吃喝嫖赌之徒缔结了婚姻,是她被赶出周家后最切实的生存需要使然。一个女人,一个带着不明不白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的女人,在那个时代还会有更美满的结局和更顺遂的遭际吗?纵使倔强的侍萍不甘委屈自己的心,但是抚养大海的母亲的责任感也使她只能在忍气吞声中和那个她十分厌恶的男性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仿佛一枝被酷风凄雨打落飘零委泥于地的残梅。她和鲁贵之间的分歧,不是一般的柴米油盐的争执,而是两个高卑悬殊的灵魂永难和谐、融通的悲剧。
曾霆和瑞贞,这对尚未长大成人的小夫妻,被别人象两只羊一样牵到一起,开始了他们毫无心理准备的情感积累的婚姻,最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婚姻模式的畸型和病态。就象是满身疮痍的老树上一枚病果。瑞贞由于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更厌倦了曾家阴森古板的生活,决心离开这个从未将自己的妻子放在心上,加以保护、关爱的小丈夫。她对曾家赋予她的传宗接代的责任尤其不能接受和担承。即使面对丈夫和另一个少女的嬉戏追逐,她也无动于衷,因为丈夫毕竟没有在她心中占具应有的位置,她坚定地逃离了曾家,不仅摆脱了不幸的婚姻,也拥有了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之路的权利。曾霆完全是在情感的朦胧期开始了婚姻生活的。爷娘们把瑞贞推到了他身边,瑞贞只是他的媳妇而不是爱人。他经济上既未自立,精神上亦未长成,只是一味地顺从着爷娘的训斥,做着小大人的样子,对于瑞贞既无热烈深挚的爱,也不愿听从母亲的盅惑去规范和约束她,甚至连瑞贞的来踪去影也漠不关心,更勿论瑞贞内心情感的细波微澜。他于爱的荒漠中萌生了对于袁圆的恋情,固然是他情感成熟的表现之一,而其中亦不乏对于和瑞贞婚姻的厌弃和绝望。他们最终在平静中中止了这场婚姻“闹剧”,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能不说乃是一种大胆的叛逆之举,在旧中国尤其难能可贵。
在曾文清和思懿的婚姻实际中,曾文清可谓心如止水。面对刁顽、阴险、无赖的思懿,曾文清除了默默地忍受她烈日一样的威严和寒风一样的冷彻之外,只有懦怯的规避和屈服。他忍气吞声,他作践自己,他无志无求,这一切似乎是他面对自己的灾难性婚姻所做出的一种必然抉择,是他企图在麻木中淡化对于苦重的现实的凄惨感受的最无奈的选择。然而,婚姻的失败对于曾文清来讲并不仅仅是情感的失落和精神的荒漠,这一灾难还更深潜地影响和左右了他整个的人生。他的萎靡、困顿、消沉、倦怠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灾难使他切实地感觉到自己的黯淡前途使然。曾文清悲剧的沉重性也许还在于:作为男性,传统观众中处于主动、支配地位的角色,他的权利和资格被剥夺和诋毁了。剩下的、留给他的只是微弱的叹息。思懿又何尝不是失败者!尽管她精明干练,有着一般女人所没有的智谋和手腕;然而,在这场婚姻悲剧中,她所渴望得到的权利、地位、金钱最终一分一毫也未得到。她对曾文清的轻蔑、不屑和憎厌并未使丈夫具有勇猛威武的大丈夫气概;她的威压,只是使他的人格精神更其困顿;她的特别之处也许还在于对文清统驭权的迷恋。她要占有文清,容不得他和愫方恋情的存在和增长,并不是因为她心中爱文清,只是因为她要牢牢地抓住文清,使走向瓦解和崩溃的婚姻得到巩固,使自己长子媳的女主人地位不生动摇。她完全是从实用的、功利的动机出发来面对和处理与丈夫之间的关系的。思懿的不幸也许在于:将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的砝码置于对权利和物质的追逐之上,这种利欲熏心的畸型生活,几乎消溶了她对人格缺损的丈夫的不满和对这一婚姻不幸的痛心疾首,至终却又脱不出两手空空,一切都徒然枉然的结局。
金子对于焦大星,鄙弃、厌倦多于关切和痛惜。她不能容忍丈夫受婆母的怂恿而施压于她,她要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报复大星母子。她象一只强硕的母猫,把老鼠似的大星玩弄于股掌之上。她的良知,她的性情都使她本能地嫌厌和憎恶大星,与大星的婚姻生活对她纯然是一种屈辱、被奴役的生活。她最终的投入仇虎的怀抱,憧憬遍地都是金子的理想之国的追求在她当是大胆、倔强的个性发展演进的极致。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在无爱情的婚姻悲剧中没有胜利者。曹禺以自己的深刻观察、敏锐思考,艺术地剖示了旧中国悲剧婚姻中可哀可怜的生灵,他们是如何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做了那婚姻的祭品,失却了正常合理情感生活和人生权利,辗转呻呤在这种婚姻“坟墓”的一派萧杀冷寂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导致自身和他人的生命悲剧,无一例外地付出了沉重之极的血泪代价。这一幕幕人生惨剧向人们诉说着作家美丽感人的意愿:告别黑暗中的恶梦,到光明的天地去享受生命的大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