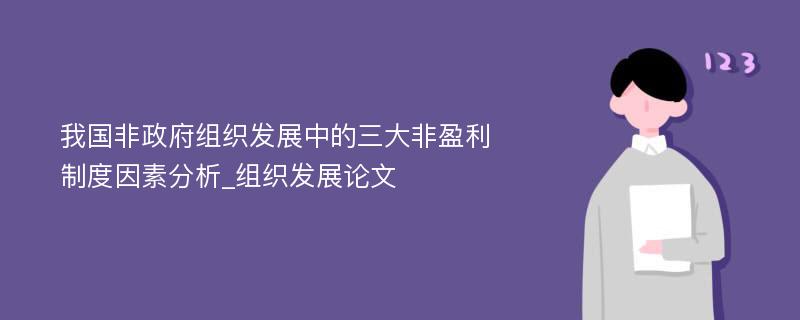
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三大不利性制度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中国论文,不利论文,民间组织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状况与动力机制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组织形成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1911-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中国至少存在四种类型的社团组织:一种是传统手工艺者;一种是学术协会;第三种类型是学生会、工会、妇女联合会等;第四种类型是宗教和慈善组织。第二阶段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有效管理已经存在的社团组织,国家于1950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社会团体”随后成为中国此方面的主要用语。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一度使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陷于停滞状态,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各类社团组织的数量寥寥无几,50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的社团也只有大约6000个(注:毕监武:《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85页。),这与当时有着几亿人口的中国相比,相形见绌。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民间组织蓬勃发展提供了契机。1988年和1989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10月又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根据王颖等人的研究,浙江的社团组织在1978年至1990年间增长了24倍(注: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社会中间层》,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截止到1989年底,全国性社团已发展到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注:毕监武:《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85页。)。1998年10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另外,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单位体制改革的深入,部分事业单位原先由国家兴办转为由私人或社会出资兴办,在政府与市场机制之外开始出现了一种有别于“社会团体”的“民办事业单位”(注: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将这一组织类型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与“社会团体”相并列。1998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与此同时,民政部原社会团体管理司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于是成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截止2004年,民政部登记的各类社会团体数量达到近15万个(注:陈剩勇、马斌:《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温州服装商会的典型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12期。http://203.93.24.66/shxw/zzysq/P020050221286930930902.pdf。),重新登记确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约13万家”(注:民政部:《我国民间组织发展与管理情况解读》,http://www.mca.gov.cn/redian/mjzuzhih2.html 2005-07-01。)。截止到2004年,中国大陆地区每5265人左右有一个民间组织(注:毕监武:《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中国民间组织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背后必须解决它的动力机制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将陷入僵局。康晓光认为,社会发展、制度框架和社团的内在发展逻辑等3种力量推动着中国民间组织的形成发展,其中,一套有效的制度框架将为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注: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王名等人在分析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动力机制时也指出,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面临着制度约束,如果制度约束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将受到抑制(注:王名、刘国翰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66页。)。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前景,与制度建设是分不开的,及早地为民间组织预备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理性的制度框架,需要学术界、政府部门和相关民间组织共同努力(注:苏力、葛云松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194页。)。制度因素对于民间组织发展之所以至关重要,原因在于这类组织也存在部分失灵:(1)业余化的服务供给:民间组织往往受到资金的限制,因此较难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从而缺乏一定的组织运作经验及能力。(2)资金供给不足:民间组织之所以受到资金的限制,原因在于其提供的是公益物品,加上这类组织不象政府部门那样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另外,由于民间组织往往依赖非制度化的社会捐款,因此,这类组织很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这类捐款数目往往骤减。(3)也易偏离社会需求、公益目标:为民间组织提供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该部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如何分配收入等,因此,一方面这些组织往往容易忽略其理应满足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也容易偏离公益目标而成为满足私益的工具(注:田凯:《机会与约束: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shzc/t20040729-2316.htm。)。民间组织这些不足正好是政府的优势,政府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这类组织接受统一的管理并获得必要的运作知识与管理经验、使这类组织获得足够的资源开展活动、使这类组织得到有效的监督,从而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然而,现实情况是:目前中国存在着一些制度上的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成为了民间组织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制度“瓶颈”,这些不利因素至少包括:控制型登记管理制度的阻碍、资助型税收制度的缺失、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二、控制型登记管理制度的阻碍
根据邓国胜对中国第三部门组织的问卷调查初步分析,中国的民间组织按其法律地位,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注册;二是以企业法人身份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三是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单位内部开展活动;四是其他类型,包括工、青、妇等不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和无法人地位的次级团体。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1508个团体中,68.2%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6.3%是在事业单位内部登记备案;14%的团体属于其他类型。另外,还有6.4%的团体没有回答该问题(注:邓国胜:《中国NGO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http://www.usc.cuhk.edu.hk/wk-wzdetails.asp?id=1676 2005-03-19。)。事实上,在第四类团体中还包括大量“非法”独立开展活动的团体,它们没有在任何部门登记,也没有挂靠在任何单位或合法登记团体之下。谢海定于2002-2003年上半年在深圳、安徽部分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经过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数量只占民间组织实际数量的8-13%(注: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选自《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http://www.iolaw.org.cn/paper/paper280.asp。)。另外,“保守估计,全国已经登记和未经登记的乡村两级的民间组织至少有300余万个,占全国民间组织总数的2/3以上。”(注: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2002年版,第200页。)另据民政部官员于1998年11月公布的初步摸底统计,当时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就已经有约70万个,而截止2003年,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数只有11.1万个。
中国民间组织的现实法律地位以及大量非法运作的事实是与中国控制型登记管理制度密切相关的。控制型管理建立在对管理对象的不信任基础上,而理由在于管理对象的“幼稚无知”。目前,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采取“一体制三原则”的做法,即:双重管理体制、分级管理原则、非竞争性原则和限制分支原则。
所谓双重管理体制指的是,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实行双重管理的体制。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具有审查、指导活动、年检初审、协同监督等5项管理职责。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具有登记、年检、监督等3项管理职责。要想登记注册的组织不得不首先有一个监管自己的部门实体,或者形象地说是需要一个“婆家”,只有得到“婆家”的同意,该组织才能到民政部办理申请登记手续。就这个意义而言,业务主管单位相当于是政府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控制的一种延伸。而且,对于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所要寻找的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非常严格:例如根据等级管理的原则,一个具有全国规模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不在最高政府级别寻找业务主管单位,这一困难可想而知。寻找一个“婆家”,对于几乎每一个潜在的民间组织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即使一个组织能够找到一个“婆家”,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这个“婆家”有权力单方面任意终止与该组织的关系。每年许多组织因为这个原因而丧失了合法登记的身份,从而不得不继续寻找新的“婆家”。另外,办理申请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需要有10万元最低启动资金,地方性社会团体需要有3万元最低启动资金,社会团体需要有50名以上个人会员或30个以上单位会员(注:Cough Kristina,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China: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Conditions and Possibilities Available to Civil Society and Its Organisations to Act in China,published by Sida,2004.)。在中国,业务主管单位对民间组织的成立所进行的实质审查仅仅是“初审”而已,登记管理部门仍然要独立进行实质性审查。任何一方不同意,民间组织都不能合法成立。所以,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又可以被称为“双重许可主义”(注:苏力、葛云松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双重管理既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也给社团组织增加了负担。例如,每当年检的时候,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既要向业务主管单位(社会科学联合会)提交年度报告、缴费,还要向登记注册管理部门提交年度报告、缴费(注:毕监武:《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也正由于这些原因,许多民间组织经常会选择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因为这种方式注册的好处是没有太多的监管部门,没有太多依附性的关系,而且整个注册过程很快,申请一般在两到三周后就开始处理了(注:Gough Kristina,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China:An Overall Assessmento of Conditions and Possibilities Available to Civil Society and Its Organisations to Act in China,published by Sida,2004.)。所谓分级管理原则指的是,对民间组织按照其开展活动的范围和级别,实行分级登记、分级管理的原则。这其实不利于民间组织开展活动的连续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组织的创新性。所谓非竞争性原则指,为了避免民间组织之间开展竞争,禁止在同一行政区域内设立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民间组织的原则。这实际上人为造成了垄断,不利于同类组织通过竞争得到发展,而且也使处于垄断地位的民间组织由于这种垄断地位而易于偏离非营利性、公益性的组织原则。这一原则也不利于形成多元化的公民社会(注:Gough Kristina,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China:An Overall Assessmento of Conditions and Possibilities Available to Civil Society and Its Organisations to Act in China,published by Sida,2004.)。总之,从民间组织自身的发展角度来说,垄断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注:康晓光:《创造希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漓江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57页。)。所谓限制分支原则指的是,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不许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定事实上限制了民间组织作用的整体发挥与扩大。
上述这些体制原则的存在(关键是双重管理体制的存在),也就是为何许多民间组织决定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原因,也就是为何许多民间组织“非法”运作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这些民间组织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它们就失去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权利,而且这些组织在接受捐款时,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因为它们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事实,导致了对它们定性上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民间组织“非法”运作,没有合法的登记注册身份,使它们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其运作模式及范围也变得相当有限。许多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者都有着令人灰心丧气的经历:放弃所有应该由这些民间组织享受的权利,因为它们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了,因为它们“非法”运作了(注:Liang S.,Walking the Tightrope: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China,2003.)。另外,控制型管理意图在于使民间组织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然而事与愿违,这种控制型管理却导致了3个不利结果:一是民间组织的“行政化”运作方式,重庆市一家由政府行业主管局撤局改建而成的单位,在1年3个月内,竟下达各类文件达500余份,党群组织也发文近150个,“上级指示”仍然是组织的主要运作方式,官僚化依然严重(注:《重庆日报》2002年2月6日。)。二是民间组织“官附性”的利益取向,由于民间组织的合法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业务主管单位的认可,因此,许多民间组织往往想尽一切办法讨好业务主管单位,甚至不惜利用行贿手段,在获得合法地位后,这些组织仍须时常讨好业务主管单位以便安全度过年检关。久而久之,这类民间组织形成了“官附性”的利益取向,一切唯业务主管单位利益是从,从而偏离了其公益及社会利益的服务初衷。三是民间组织内部的管理混乱,由于在登记注册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导致许多民间组织未曾登记注册而非法开展活动,从而,这些组织没有任何管理机制对其进行统一管理,久而久之,许多民间组织内部常常存在人员老化、经费短缺、财务混乱、管理不善、资金挪用等普遍现象。上述这3种结果最终导致政府及公民对民间组织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使政府相信有必要采取更为严格的登记管理制度、使公民逐渐丧失对民间组织支持的热情,而这些更为严格的登记管理制度及热情的丧失又将进一步加重这3种结果,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应当建立一套有效的登记管理制度。
三、资助型税收制度的缺失
登记注册之后,民间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募集和保持一定规模的资源以维持其活动。由于民间组织是非营利分配性的、自治性的组织,它不像一般企业以营利为主,也不像政府可通过获取大量的财政收入来维持其运转,相反,其大多依靠政府的税收优惠、补贴来汲取资源。因此,相关的税收制度就成为关系到民间组织存在与发展的举足轻重的问题(注:雷兴虎、陈虹:《社会团体的法律规制研究》,《法商研究》(法学版),2002年第2期,第47-56页。)。对于民间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人们的公益捐助意识相对淡薄的中国来说,这一制度显得尤为关健(注:葛云松:《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人民网《志愿服务与社会发展论坛》第1期,http://www.people.com.cn/GB/40531/40557/41317/41320/3025957.html 2004-12-01。)。然而,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对全国社团组织的抽样调查(有效样本1546个),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被民间组织列为主要问题(注:王绍光:《促进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选自王名主编《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83页。),有92.5%的民间组织表示在开展活动和组织发展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注:邓国胜:《中国NGO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http://www.usc.cuhk.edu.hk/wk-wzdetails.asp?id=1676 2005-3-19。)。
一般而言,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税收资助分为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两种。直接资助指的是政府拨出部分税收收入用于资助民间组织。在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普遍不足,民间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分化出来以获取民间资源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接受政府资助、受政府委托去实施某些项目的解决措施。因此,政府通过从税收中拨款给予民间组织的直接资助微乎其微(注:田凯:《机会与约束: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版。),从而更不用提有多少制度性安排了。
间接资助指的是,政府向给予民间组织捐款的个人和公司提供减免税的待遇,并给民间组织的收入以减免税待遇。对于民间组织的减免税收制度,将从捐赠人与受赠人两方面极大促进民间组织的不断壮大与发展。从捐赠人的角度,他们更有动力将原本应该上缴政府的税款资助民间组织;从受赠人的角度,民间组织可以从事一些经营性质的活动来扩大其运作资金。虽然,国家通过减免税收的制度对民间组织进行扶持是一项十分有力的机制,中国在价值观念上对此也认同,然而,在制度及操作层面上则还远未能兑现。由于中国长期存在民间组织不能营利的错误认识,中国的民间组织往往很少有营利性的收入,即使有也基本按照营利组织营利收入缴税规则进行缴税。因此,启动这个机制,对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将起着明显的推进作用。但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民间组织而制定的税收法。中国民政部门与税务部门在具体税收政策上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社区服务的民间机构是否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2)对于民间组织的收入特别是——些经营性项目的收入,是否需要纳税,各地有不同的政策(注:孙炳耀:《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http://www.social-policy.info/1032.htm 2005-03-19。)。例如,温州和上海先后出台了《行业协会管理办法》,河南出台了《关于加强民间组织税务登记及发票管理问题的通知》等等。事实上,往往在一些发展较好的城市,民间组织能够享受经营性收入的免税待遇,因此,这些城市的民间组织发展水平往往高于落后城市地区的民间组织发展水平。当然,经营性收入的免税前提应该是这些收入用于民间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公益事业,然而,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民间组织利用经营性收入的免税政策谋取私益。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关于公益性事业捐赠行为的全国性法规至少有3个:1999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2001年3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2001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扶贫、非营利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根据田凯的分析,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公司和其他企业、以及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的捐赠行为作出减免税收的规定,然而,对于如何具体实施各类减免、减免到何种程度等等,该法规都没有给予明确规定。这使得该法律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而几乎成为一纸空文;虽然《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也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民间组织的捐赠行为作出了减免税收的规定,然而,这一通知只是一个小范围的试点。一方面,试点地区的财政和税务部门并不一定要按照《通知》规定来执行;另一方面,这一《通知》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实行;虽然《扶贫、非营利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对境外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作出了减免税收的规定,然而,与中国国内民间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来说,这部分捐赠只是杯水车薪(注:田凯:《机会与约束: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其实,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激励公司及个人向民间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实际的捐赠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收入税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税收体制是建立在以流转税为主的基础上,而收入税不是一个主要税种。因此,目前的中国税收体制不可能对捐赠行为有太大影响。以企业的收入税来说,中国的税法规定,小于企业应征税收入3%的捐赠款项部分可以减免税收,而超过3%的部分不能税收减免。这么低的减免限额不可能给企业太多动力向民间组织捐赠。另外,企业不得不对其超过限额部分的捐赠款项进行缴税,这就进一步挫伤企业的捐赠积极性。在美国,这一限额是50%,澳大利亚则根本没有限额(注:L.E.Irish,China's Tax Rules for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A study prepared for the World Bank,2004,December.)。
四、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并不是说,民间组织由于是非营利的所以不需要监督。事实上,在某些因素干扰或某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民间组织同样也会出现价值目标的偏离。由于目前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对部分民间组织的投资捐赠往往占其资金运作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这些基金会对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方向有着很大的发言权,而民间组织为了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自然也就会牺牲部分的原则立场。这样一来就使民间组织陷入了一种循环:“花钱是为了申请到更多的钱,而得到的钱又为了以基金会满意的方式花出去。”(注:李景鹏:《关于NGO若干问题的探讨》,选自范丽珠主编《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56页。)按照李景鹏的进一步分析,通过不断地拿钱花钱,会使其组织内部人员也相应地获得各种利益,甚至有的民间组织“利用被援助、被救济者的痛苦做招牌来换取社会更多的赞助。为了不断地得到赞助而有意地不去彻底消除他们的痛苦。”这就与民间组织建立的初衷真正地背道而驰了,这也说明民间组织由于其非营利性的初衷更需要社会的监督,从而来消除那些打着民间组织的旗号实际谋着私利的组织、以及杜绝民间组织的价值原则的偏离。
另一方面,第三部门筹集经费的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从事一些经营活动。实际上,作为非营利的民间组织是可以营利的,但经营所得到的收入应该只能用于公益性分配。然而,由于目前中国对于民间组织的社会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许多民间组织将经营所得到的收入用于私益分配上。比如,作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医院,主要目标是为患者、为公众健康提供服务,但是,一些医院违背其宗旨、医生违背职业道德,通过向患者出售假药、高价向患者出售药品、收受红包等方式,为医院工作人员谋取私利,本来只要一百多元的外科手术材料,卖到患者手中竟高达1万多元(注:郭道久、朱光磊:《杜绝“新人”患“老病”——构建政府与第三部门间的健康关系》,《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http://www.usc.cuhk.edu.hk/wk-wzdetails.asp?id=3247 2005-3-19。)。再如,某地建立的抗旱供水服务组织,本来是为公众的集体福利服务的,可硬是制定经营指标,必须实现年社会效益100万元,利润10万元,人均利润1万元,在背离原来的服务宗旨转向营利后,竟然平均销售收入760万元,实现利税72万元,完全变成一个营利机构,而不再将社会服务与公众福利作为组织工作的出发点(注:苑鹏:《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引自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编《扩展中的公共空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所有这些例子都反过来招致许多人对民间组织从事营利活动的非议。于是,恶性循环使得民间组织不能营利,而不能营利势必造成民间组织正常开展活动的资金匮乏,制约了民间组织进一步发展,最终又在人们心中造成民间组织无用的观念。
实际上,对中国民间组织的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反映在中国民间组织的具体运作情况不为人所知。换句话说,公众或企业捐的钱花在了哪些方面、怎么花的、结果如何等等情况除民间组织自身以外没人知道。公民没有渠道向民间组织要求查看它们的财务状况或运作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的民间组织往往不公开编制出版组织年报,从而主动要求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说民间组织是作为一个公共机构为公共利益谋福利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对公众负责,对公众透明。而一套健全的社会监督机制是使其负责、透明的关键措施之一。
五、政策建议
针对阻碍目前中国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不利性制度因素,政府应该积极地建立起有利于中国民间组织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制度框架。
1.建立一套完备的民间组织立法体系
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调查显示,除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之外.仍存在大量非法独立开展活动的组织,它们没有在任何部门登记,也没有挂靠在任何单位或合法登记团体之下(注:邓国胜:《中国NGO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http://www.usc.cuhk.edu.hk/wk-wzdetails.asp?id=1676 2005-03-19。)。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类非法开展活动的组织数量会越来越多,类型与开展活动的形式也将越来越多样化,加上控制型的登记管理制度也将迫使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转入非法运作的队伍中。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大量非法运作的民间组织存在于法律的盲区。很难想象:生存于这一盲区的民间组织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必要的支柱。因此,国家应该尽快制定一部关于民间组织的统一规范的基本法。这一基本法应该“能够涵盖除政府、企业以外的所有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上述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在内的各种民间非营利组织。这个基本法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重申《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权利;明确登记注册是公民实现结社权的法律形式;通过登记注册赋予民间非营利组织以法人或其它合法地位;对合法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提供财政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对各种民间非营利组织加以法律上分类,并定义和区分不同分类的法规政策;认识与承认那些未经登记或按现行政策难以登记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起码生存空间,而从法律和政策上对其活动进行规范和制约,等等”(注:王绍光:《促进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选自王各主编《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9-83页。)。
在这一基本法的制度框架基础上,建立一系列针对民间组织的专项法律,如培育服务型登记管理制度;资助型税收制度;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非营利分配性评估制度等。
2.建立培育服务型登记管理制度
以上分析了目前中国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对民间组织合法性地位获得的诸多限制条件,这种限制可以被理解为“控制型管理”取向。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应该建立起一套“培育服务型”的登记管理制度。所谓“培育服务”,指政府基于培养、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角度去管理这一部门,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政府服务,目的在于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培养民间组织的主体意识及责任权利意识,提高民间组织的社会公信度,最终使该部门成为一个独立、有效运作的部门积极参与到解决各种社会事务问题中(注: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选自《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具体作法是:废除双重管理体制,同时建立一个单一部门(例如,目前民政部门下属的民间组织管理局),对民间组织进行统一的登记管理;取消最低启动资金的限制;根据需要就某些类型的民间组织作出必须登记的规定,而其它所有类型的民间组织本着自愿登记注册的原则,对于这些自愿登记的组织,政府给予制度化的直接资助、税收减免及其它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而随着民间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成熟,中国可以适时减少必须登记的民间组织的类型,最终使所有民间组织自愿地而不是被迫地接受政府的管理及服务,这种自愿登记注册的原则有利于培养民间组织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权利意识。
3.建立资助型税收制度
在转型时期市民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国,政府的资助对资金相对缺乏的民间组织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对民间组织直接资助的制度化应该是保证这类组织运作资金充足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将其税收中的固定一部分专门用于资助各类经过登记注册的合法民间组织,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确定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所享受资助的百分比。在民间组织收入减免税方面,应当明确规定申请减免税的条件、减免的范围,对民间组织经营项目的收入,应当按照税种区别对待;在资源税、流转税层次,视同企业经营,以保证平等竞争,但对用于补偿民间组织公益服务成本的经营收益,则应当免征所得税(注:孙炳耀:《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http://www.social-policy.info/1032.hom 2005-03-19。)。
与政府间接资助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的是从捐赠方的角度对社会捐赠行为减免税的规范立法。事实上,社会捐赠行为如果得到一个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参与,那么该社会的民间组织发展将有着更坚实的经济保证。然而,这种公民的广泛支持与参与需要一种税收制度加以激励与保障。虽然中国目前对于公益事业的捐赠立法有3个,然而,普遍存在缺少具体操作性的问题,另外,建立在流转税基础上的税收制度及较低的减免限额都极大地挫伤公民捐赠的积极性。因此,在这方面,民政部门应该积极与立法、财政、税务等部门沟通并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社会捐赠法制法规的具体建设,合法保护捐赠方的权利;在捐赠方的各类减免税问题上达成共识,出台具体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明确规定捐赠方申请减免税的条件、以及减免的范围及数量;应逐渐将税收制度建立在以收入税为主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减免限额等。当然,一部专门针对民间组织的资助型税收法的建立是根本。
4.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
通过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一方面使公民更好地了解这一部门、树立起一种主体责任意识参与监督管理;另一方面使民间组织更贴近社会、更好地服务于公民的利益要求。
根据其它国家第三部门的成功经验,一个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需要建立在“公开原则”的基础上。具体而言,民间组织有责任向社会提供详细资料来通告和解释自己是如何为其公益目标开展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的。这些资料事实上应该包括财务状况、决策过程、具体计划安排和如何确立目标的优先级等4个方面(注:C.Rochester,"Voluntary Agencies and Accountability",in J.D.Smith,C.Rochester.and R.Hedley,(eds.),An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ntary Sector,Routledge,1995.)。所谓财务状况,包括组织怎样筹措和募集资金、并且如何使用;决策过程侧重于机构是如何决策和行使其行政职责的;具体计划安排则包括计划安排是否使目标群体受益、是否改变和提升了目标群体的生活质量等;优先级则主要围绕组织的价值取向、首要目标与次要目标等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以就上述任何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向民间组织提出资料索取和质询。
5.确立一种非营利分配性评估制度
为了对民间组织的营利问题进行监管,可行之策就是推行民间组织的非营利分配性评估。主要做法是建立一系列评估指标,包括治理结构、资金使用与运作、经营收入的比例、财务与信息的披露、劝募的信息、筹资行为、组织所得是否用于成员分红等方面(注:郭道文、朱光磊:《杜绝“新人”患“老病”——构建政府与第三部门间的健康关系》,《战略管理》2004年第3期。)。“评估的组织者可以是政府指定的某部门,如审计组织,也可以是类似美国的NCIB(全国慈善信息局)和PAS(公益咨询服务部)这样的独立评估机构。前者是由政府机构执行评估,后者由独立的第三部门支持组织(其本身也是第三部门组织)执行评估。”(注:邓国胜:《营利组织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2-126页。)在中国民间组织还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由政府机构执行评估功能是可行也是必要的,再以接受来自公民个人的监督投诉为辅助。但是,最终的发展目标是由独立的民间组织自身来执行评估任务。
“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自治化推进传统社会向政治、经济、社会三元分立的现代社会转型。”(注:毕监武:《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领域成为最主要的改革对象,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都将无法进一步展开。于是,社会领域的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瓶颈”,而民间组织是否健康发展就是这一社会改革的反映(注:秦晖:《第三部门、文化传统和中国改革——关于中国第三部门历史、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若干问题》,http://www.usc.cuhk.edu.hk/wk-wzdetails.asp?id=313 2005-03-19。)。中国民间组织能否健康发展需要解决其动力机制问题,而制度本身是关键。通过本文分析,控制型登记管理制度的阻碍、资助型税收制度的缺失、以及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是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瓶颈”。因此,针对这些不利因素进行的制度建设与调整——建立一套完备的民间组织立法体系、建立一套培育服务型登记管理制度、建立一种资助型税收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确立一种非营利分配性评估制度等等——将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标签:组织发展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