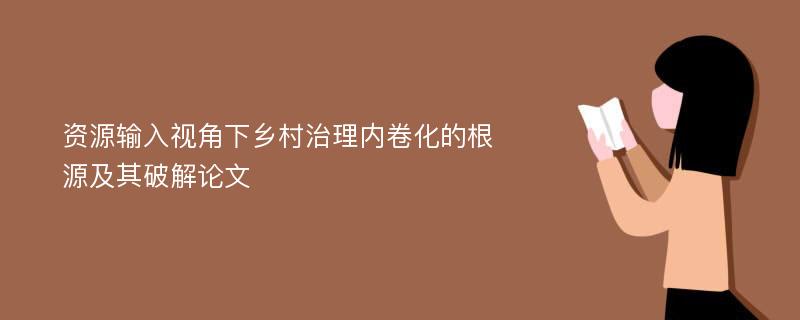
资源输入视角下乡村治理内卷化的根源及其破解
唐京华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要: 长期以来,乡村治理“内卷化”一直是困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从资源输入的视角来看,乡村治理内卷化的产生并非国家或乡村单方面的因素限制,这是一个双向度交互塑造的过程。其中,资源输入的“强主观性”和“弱公共性”、输入过程中的目标替代和地方势力截流,是乡村治理内卷化的重要外生变量;资源输入终端环境的复杂化以及目标对象理性化的行动逻辑,是乡村治理内卷化的重要内生变量。内外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形塑了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局。资源输入与乡村治理是互促关系,只有从资源输入的整体链条出发,正视并重视外部性资源输入与乡村社会各方面的衔接问题,才能真正破解乡村治理“最后一公里”困境,并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资源输入;乡村治理;内卷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农业税正式取消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二者之间由自上而下的资源提取正式转向国家公共资源反哺农村阶段,党和政府在乡村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和提升。自此之后,国家对农村资源输入的种类和规模一直保持不断扩大的趋势,然而受内外环境因素及主体要素的限制,长期以来乡村治理绩效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提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外部性资源对乡村的输入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基层治理的未来走向,并直接影响国家治理转型的整体进程。
内卷化一词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提出来的,他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一种文化模式。格尔茨将内卷化观念引入到农业经济研究中,他用农业内卷化来概括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长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1]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时,首次将内卷化一词引入到了国内。[2]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来指代国家机构通过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的现象。[3]之后“内卷化”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迅速成为研究和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词汇,在此过程中,内卷化的概念及内涵实际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4]在政治社会研究的相关领域中,内卷化的涵义概括起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以发展为基本背景,以停滞或倒退为基本后果,以复杂化为基本现实。[5]乡村治理内卷化是指乡村治理绩效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现象。进入21世纪以后,通过不断加大资源输入规模来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是近年来国家推动乡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现阶段,乡村治理的内卷化意味着国家对农村资源的输入存在问题。正因如此,围绕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现状,不少学者关注到了资源输入本身的问题。
从资源输入的视角出发,目前学界关于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研究主要是沿3 条路径展开:一是以项目下乡为基点,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追踪研究来剖析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并从中发现导致乡村治理内卷化的要素组合。李祖佩通过对国家级贫困县涉农项目运作的研究发现,乡镇政府的自利性表达是造成基层治理新困境的重要因素,[6]周常春、刘剑锋等在对云南扶贫进行调查后证实,取消农业税费并没有消除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困局,而且精英对扶贫资源的俘获会不断强化乡村治理的内卷化。[7]二是从资源耗损角度出发,研究资源输入过程中形成的分利机制与分利结构。陈锋认为在资源输送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等几个行动主体形成的分利秩序,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内卷化,[8]李祖佩的研究也指出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的利益同盟是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的重要原因。[9]三是从国家行政体制及财政制度设计角度,探讨资源输入在乡村治理低效的深层次原因。[10]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在资源输入有限的条件下,打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困境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资源输入背景下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的产生机理,但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性。一是缺乏整体性研究,现有成果多以个案分析为基础,具有明显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的特点,从资源输入角度进一步做宏观、整体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的剖析和认识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二是缺乏对资源输入本身的研究,对资源输入方式和属性的研究将有助于真正理解外部性资源输入对乡村来说意味着什么,进而深入挖掘导致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的内源性因素。鉴于此,本文将从宏观、整体性的视角出发,分别从资源输入的方式、资源输入的过程、资源输入的终端环境以及资源输入的目标对象等四个方面,来系统阐释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境,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思考。
3)重视工程招投标的资格审查。在工程招投标时,要十分重视对投标单位的资格审查以及中标候选企业的实地了解或项目考察,真正择优选出综合素质高,技术力量强,企业声誉好,项目经理经验丰富,有质量管理意识的施工管理团队,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先决条件。
将红茶脱腥处理前后的海螺肉,依照GB/T 5009.45—2003《水产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中的酸度计法进行样品绞碎,然后加入100 mL纯净水,并计算出pH值。反复测定3次,并求出平均值。
二、当前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境及表现形式
(一)乡村治理转型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造就了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而且加深了城乡二元分化矛盾。在日益开放与流动的环境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等都已发生了改变,迫切需要实现传统乡村管理向现代乡村治理的转型。因此,近年来党和国家一直致力于通过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的制度规范、健全乡村治理的组织架构、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扩大国家资源投入力度等来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但外力的介入并没有明显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村民的政治素养和对自治组织的认同感没有明显的提升。微观上,乡村治理转型滞后于农村社会环境的剧烈变迁,无法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宏观上,乡村治理转型滞后于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步伐。现阶段,要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包括乡村治理转型的路径、模式等都缺乏一个清晰的框架。
(二)公共利益增长缓慢
2000年以后,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缓和乡村关系、干群关系,我国开始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并确立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方式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的体制。农业税的取消彻底改变了基层政治生态,乡村关系、上下级政府关系都发生了大的转变,乡镇演化成为“养廉型”财政和“空壳化”政府,虽然承担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却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各项事务支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一方面弱化了乡村联系,降低了乡镇政府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乡村公共事业的边缘化,类似一事一议的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大多形同虚设,除去个别获得项目资源的村庄外,大部分乡村各项公共事务实际处于无人管理或者发展停滞的状态,有些村庄的灌溉设施、道路建设甚至出现倒退状况。
(三)乡村治理复杂化
患者行CT平扫及增强扫描,采用日本东芝公司320排CT Aquilion ONE进行容积扫描。增强扫描采用高压注射器经肘前静脉注入非离子型造影剂欧乃派克100ml,流速4ml/s。
(四)乡村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不足
近年来国家支农的政策导向是希望通过外部性资源输入和农村社会资源再生的方式,推动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进而推动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转型。从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也就是要通过外力的帮扶和内力的挖掘,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建立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然而,在外力帮扶力度不断加强的同时,由于内力挖掘不充分,广大村民的治理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激发,外力的帮扶始终悬浮在乡村治理体系的表面,导致治理效果短期化效应,不具有可持续性,当外力撤回时,治理改进的效果往往难以继续维持。
三、资源输入视角下乡村治理内卷化的产生机理
现阶段,国家对乡村的资源输入形式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常规性、规范化的运行经费,包括村干部收入补贴及日常办公费用等;二是具有规定用途的各种专项资金补贴;三是以项目方式下达到部分乡村的暂时性、有选择性的财政资金投入。此外,还包括国家在某个时期针对特殊地区所做的阶段性资源输入。前两种资源输入形式由于其本身的制度化、规范化特点,可操作性极小且无巨利可图,因此从资源输入视角出发,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更容易产生于后两种方式,尤其是项目下乡过程中。
(一)资源输入方式的强主观性与弱公共性
穿斗式是用高度不同的木柱搭成山字形,木柱之间再连接一些穿枋( fā ng),形成格子一样的木框架,格子里面可以填充木板、泥土、砖或石块形成墙体。类似的形式在欧洲叫“半露木”结构。
二是资源输入本身所具有的“弱公共性”。所谓“弱公共性”是指外部性资源输入相对于村庄居民来说所具有的低利益关联度。理论上说,国家资源输入虽来自于乡村社会之外,但因其被分配到乡村社会内部,用于支持与村民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特定乡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因而也具备明显的公共性。但实际上,由于这种资源的输入方式具有非普惠性特点,只有有能力、主动性强的村干部能够在竞争性资源获取中为乡村谋取到公共服务项目,这种资源争取模式降低了外部性资源输入在乡村的公共性,强化了其私人属性。村民普遍认为“有总比没有好”,能争来项目的干部就是有本事的干部,其主导输入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理所应当,由此导致以乡村体制内精英为核心,联合非体制精英和乡村混混对下乡资源的私人分割。
语文新课标指出“写作能力是语文核心素养的综合体现”。四年级的学生有了一定的写作基础,掌握了许多写作技巧,写作文似乎不再那么可怕了。但在四年级上册的习作中,我们又碰到了一只“拦路虎”——观察作文,在学生作文中,我发现了许多问题:
(二)资源输入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地方势力截流
2006年农业税取消以后,一方面“乡村”利益关联骤然断裂,乡退出村,村退出组,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普遍现象,[13]乡镇基层政府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同时也丧失了为乡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力。另一方面,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基层政府基于自我谋利的行动逻辑,将“维稳”和“争资跑项”视为乡镇工作的两大核心内容,在乡村治理中则遵循着自我利益导向的“不出事”逻辑,[14]担当被动执行、消极应对的一方治理主体。乡与村之间的这种悬浮、被动关系也嵌入到了资源下乡过程中,成为导致乡村治理内卷化的重要外生性因素。
首先,资源输入过程中的目标替代。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权开始逐渐远离乡村,乡镇的财权与事权被大量剥离,成为“养廉型”财政和“空壳化”政府。基层政权在乡村治理中普遍呈现缺乏活力与主动性的特征,现今比较普遍的乡村关系互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乡镇自上而下到村的行政任务摊派,要求村级组织予以配合和支持,并辅以必要的检查与督导;二是由村内组织、个人所触发的乡镇被动行动。“乡村”缺乏常规化的、制度化的密切交往,二者在利益关联性和行动规范性上越走越远。在治理资源短缺和乡村悬浮、被动的关系模式下,以项目制为主的外部资源输入成为乡镇完善乡村治理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受压力型体制的影响,乡镇政府往往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项目资源使用上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片面侧重于市政及交通设施建设,对民生服务供给则很少重视,[15]由此造成了下乡资源与乡村社会需求的错位。
二是机会主义谋利行为增生。机会主义谋利行为是指在外部性资源输入乡村的过程中,包括掠夺精英、灰黑势力和谋利小农等在内的少部分狡猾投机分子,充分利用信息优势、制度和政策漏洞或权钱交易等不恰当方式,占有本不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资源的行为。投机分子对输入资源的瓜分形式有两种,即精英俘获和谋利型小农行动。
其次,策略选择与地方势力截流。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不仅面临维稳和农村发展等常规性的目标考核任务,而且还有层层下达的非常规性任务,这使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得不向外寻求可以依靠的力量。资源下乡是一种公共资源的分配形式,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利益的争夺与冲突,乡镇由于缺乏利益制衡的手段和强制力,因此在面对诸如钉子户等棘手问题上,与一些地方势力结合成为地方政府理性的策略选择。近年来,虽然一些地方势力借助于资源开发、工程承包等逐渐脱掉了非法的外衣,但其内部运作所带有的灰黑性质却仍是普通农民群体深深畏惧的。二者相互结合,基层政府可以摆脱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更好的完成既定任务,地方势力则从中获得了大量的下乡资源。由于地方势力获取的资源不是从农民手中掠夺而来,而是从上往下截流,农民在此过程中虽受到了隐性的剥夺,但也获得了少量实在的好处,因此二者的联合很少能引起农民的愤怒和反抗。国家下乡资源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被大量的消耗和浪费,乡村治理效果提升缓慢,却滋养了一大批地方势力,广大村民实际分享的资源数量相当有限。随着地方势力的不断增强,其分利机制愈加灵活,分利能力日益增强,即使有再多的外部性资源投入,其效率也很难提高。
(三)资源输入终端环境的离散与复杂化
项目越往下,越要面对复杂的乡村社会,而更为复杂的是项目进人村庄本身也进一步增加了乡村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纠纷。[16]当以制度化、规范化运作为基本标志的外部性资源输入,与分散化、不规则的乡村社会相对接时,其结果是具有精细化设计模式的资源输入绩效不断被乡村社会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削弱。
一是共同体意识的式微与羸弱。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城乡封闭的边界,各种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比例和规模不断扩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转变,行动逻辑越来越趋于市场化,经济理性已大大超出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对其具体行动的支配,并由此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他们很少关心公共产品供给,对此始终保持观望态度,既不乐于出头表达利益诉求,也不会对个别利益投机者阻碍公共产品供给的行动予以谴责,这样的乡村社会环境既造成了原子化农民群体的无力感,无法为社会资源输入提供精确的目标定位,也助长了个别利己主义者的投机行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党、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农民从乡村社会“萝卜坑”式的全面管理中被释放出来,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乡村社会要素。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增长1.7%。乡村流动与开放的属性特征不断增强,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由流动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空心化、碎片化、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问题,城乡二元分化体制下集体产权、农村土地分配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等。为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然而,以发展为衡量标准,中国乡村治理体制实际并没有明显脱离“乡政村治”的最初形态,而是不断被复杂化,包括相关制度规范、组织架构等,其中不少内容形同虚设,乡村治理本身虽日益复杂化,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2月14日,在酒吧陪客户玩乐到转钟之后,郭启明意犹未尽地回了家。情人节的北京是个不夜城,在回家的路上,郭启明看着街边一对对搂抱偎依在一起的情侣,心里不禁有些惆怅。回家之后,他在QQ签名上写道:“天啊,赐予我老婆吧!”并发了一个咧嘴坏笑的表情,然后浏览网页。
第二,村级组织治权弱化。在乡村治理中,治权一词最早是由李昌平提出的,用来表示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申端锋进一步将乡村治权区分为物质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17]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村级组织治权弱化是指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党组织所掌握的物质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能力的下降。村级组织是实现下乡资源与乡村社会对接的重要组织依托。然而,自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国家对乡村组织治理资源的配置能力一直存在弱化倾向,农业税及“三提五统”费用取消后,村级组织丧失了治理的物质性资源,日常运转只能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此外,随着乡村原子化、碎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村级组织越来越无法承担起凝聚社区认同,汇聚和执行村民利益诉求的责任,精神上的权威性资源也基本失势。村级组织治权弱化使得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缺乏可靠的组织依赖,且存在一定程度的目标错位,导致资源输入与乡村社会的脱节,国家权力越来越直接面对分散化的农民群体。村级组织自身承接能力的不足是资源输入背景下,乡村治理内卷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资源输入中农民理性化的行动逻辑
第一,乡村社会的退化与离散。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基于血缘、地缘以及共同的生产劳动空间,人们形成了基本一致且共同遵守的乡土规则,对村民行动的规制和塑造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由此构成了村庄社会秩序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冲击并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乡政村治”体制确立以后,国家权力的退场也并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增强。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的流动性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不断加剧,传统社会规则的作用和村民的共同体意识明显淡化,而乡村却没能及时建立起能够有效应对社会无序化倾向的手段和途径。乡村社会的退化与离散,使得国家资源在输入过程中,既无法借力于乡土社会规则的作用,同时又无法有效对接松散的村民群体,进而产生资源的自耗。
一是资源输入方式的“强主观性”。按经济发展程度,可以将中国农村大体区分为发达村庄、普通村庄和贫困村庄。在以项目制为主的非常规性资源输入过程中,国家通过部门“发包”、地方政府“打包”和村庄“抓包”的机制,[11]完成国家资源与乡村社会的对接。在此过程中,为了实现下乡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项目制实际确立了自上而下筛选和自下而上能动性争取的“双轨”机制,但在具体运行中,项目制可导致资源分配不均,阻碍公共服务在基层公平及公正的提供。[12]那些较为富裕的村庄由于人脉、名声等资源优势很容易争取到项目资源,成为下乡资源的集聚地,贫困村即使在行动上颇为消极且缺乏有效承接项目资源的能力,也会因国家政策的照顾和倾斜而获得不少资源扶持。但是,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村庄却往往由于缺少明显优势和突出问题而成为边缘村,难以争取到国家项目资源的支持。其结果是发达村庄因自身发展能力较强,“锦上添花”的项目资源输入效果并不明显,贫困村庄由于自身组织资源承接能力、发展能力不足以及项目制本身的孤立性特点,外部性资源输入往往只能起到暂时性、阶段性的效果,难以长期维持,导致了国家资源输入的极大浪费。乡村治理改进的主体范围应是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村庄,而恰恰是这最具普遍性的中等村庄却常常被边缘化,成为资源输入选择性遗忘的角落。
道路建好更要管好。该村党员干部自觉当起道路监督员,并发动群众共同维护道路环境,完善和实施长效保洁机制,确保道路干净畅通美丽。如今,在该村,一条道路刚修好,大家就自发去培护路肩、打扫路面、管理绿化树木,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精英俘获中的精英在这里是一个中性词,指在某方面占有资源优势的群体,既包括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积极精英,也包括灰黑势力等在内的消极精英。其中,以村干部为核心的积极精英,往往既是外部性资源输入信息的优先掌控者,甚至是垄断者,同时也是输入资源分配或使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凭借信息和正式权力代表者身份,掌握资源的分配并实施精英俘获。此外,由于治理能力的缺陷,近年来乡村灰黑势力借助于开办企业、承包集体土地、水库等方式逐渐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成为资源下乡过程中基层政府的重要倚重力量,并不断盘剥和榨取处于弱势地位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力。
此外,在限幅机构与探测器一同飞行工作阶段以及钻取采样作业全工作过程中,限幅机构将受到随机的振动载荷以及钻具的横向负载:
谋利型小农行动是指在资源下乡过程中,部分村民所表现的个人理性取代公共理性的行为。小农思想具有保守、封闭、自私以及目光短浅的特性,其行为往往缺乏公共理性而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在资源下乡过程中,谋利型小农行动突出表现为机会主义上访户和钉子户,他们紧紧抓住基层政府“维稳”的软肋,通过无理上访、威胁上访和拒不配合的方式,逼迫基层政府对其行为做出妥协。在压力型体制下,面对“一票否决”的考核准则,基层政府往往利用好处收买的方式予以解决,造成了输入资源的巨大浪费。在资源输入背景下,面对原子化、碎片化的乡村社会空间,机会主义谋利行为的增生导致大部分缺乏强大组织依靠的老实农民处于集体失声境况,只能被动、消极的等待国家直补到账或者分享被瓜分剩余的普惠式资源。
三、破解乡村治理内卷化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输入资源的配置方式
在现有项目制体制下,村干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主观能动性在向外资源争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也赋予了村干部个人或其利益团体极大的自主权和能动性。[18]因此,资源输入背景下,单个乡村治理绩效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村干部的个人因素。为了削弱资源输入的这种“强主观性”,在项目资源到达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之后,须重视下乡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一要强化县、乡级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政权运作的民主化程度,以乡村实际需求为导向,淡化村干部个人因素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在充分考虑区域内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基础上,采用民主化的方式,实现下乡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二要完善资源分配结构,增加普惠式资源输入总量,避免资源输入的“两极分化”。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最大潜力是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中等村庄,“保两头,忘中间”的资源输入模式是低效且非理性的。在资源输入总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下,必须对资源输入本身做出结构性调整,增加基础性、普惠式资源供给量,弱化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特点。
(二)强化资源输入的内外监督机制
构建外部调控与内部制衡相结合的资源监督体系。由于项目制本身的竞争性特点,它在进入村庄之前属于强公共性资源,任何人不能将其非法据为己有。但当项目资源进入村庄后,却也会因其自身的竞争性特点而使之快速转化为高度私人化运作的公共资源,导致外部性资源输入的使用偏离预定轨道,因此构建完整高效的资源监督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从外部性资源输入的整体过程来看,内外融合的资源监督体系能够有效遏制公共资源的私人化运作。从资源输入的整体链条着手,一方面,应把增强乡镇基础性作用融入下乡资源监督体系的重要一环,明确乡镇政府在资源输入、使用及管理监督上的权责,充分发挥乡镇党组织对乡村党员干部的内部监督作用。另一方面,缺乏农民视角是国家资源下乡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实现资源输入与乡村社会良好契合的关键一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在资源输入过程中必须要注重加强普通村民与输入资源的利益相关度,并积极通过提高村民的组织化水平,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和资源分配的渠道来强化村民的监督作用,增强乡村内部普通村民对体制内外精英的制衡能力,以此来避免输入资源的非公共性利用。
(三)重视乡镇政府在资源输入中的作用
首先,着力增强乡镇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性力量。国家对乡镇基层政权建设经历了渗透、强化到削弱的整体过程,通过国家财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国家收缩了乡镇政权的财政资源、组织规模和行政权力,这在断绝基层政权做坏事可能性的同时,也使其丧失了做好事的能力。在外部性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克服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境必须要增强乡镇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性力量,在财政资源和权力行使上给乡镇留足治理能力提升的空间。不断推动政府财政体制改革,赋予乡镇基层政权积极承担政府责任的足够治理资源,增强乡镇常规化治理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使其真正成为能够承担起国家资源下乡任务和正确引导乡村治理责任的一级政府。
其次,增强乡镇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利益关联度。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的自利表达是地方势力截流得以实现并不断扩展的重要原因,而进入后税费时代以后,乡镇与乡村社会之间利益联结纽带的断裂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隐性因素。只有乡村治理绩效成为乡镇政府考核指标的核心任务之一时,乡镇政府在资源输入中才能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逐渐克服自利性表达和策略主义行动倾向,不遗余力地推动乡村治理改进;但同时也要注意,在有关乡村治理绩效考核指标的确立上,应避免“唯经济”“唯上访”或“唯明星村”的指标单一化倾向,重视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综合性。
(四)增强自治组织资源承接能力
首先,重视村级组织建设。村民自治组织处于国家权力与普通村民群体之间的中间地带,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是外部性资源输入能否扎根乡村社会,实现对乡村治理有效干预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实现下乡资源与乡村社会的有效对接,化解村级组织治权弱化的困境,必须做好组织自身建设。一是增强村党组织的核心领导能力,不断提高村民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重视民意的集结与表达,积极通过乡村治理形式的创新,引导更多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以组织化的村民来遏制和约束乡村社会不良势力对下乡资源的侵蚀。二是重建乡村共同体。村民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响应是提高下乡资源在乡村治理中的有效性的重要保证,要重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培养村民对村庄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积极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发挥道德、法律在约束村民机会主义谋利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激发乡土社会规则力量。现今外部性资源输入在乡村社会治理的中作用发挥强调的是一种技术性治理,这与乡村社会规则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协调,二者之间的张力大大降低了资源输入在乡土社会中的作用功效。现代化要素、市场要素的流入和发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规则的重新塑造,但基于一定范围内,特殊的血缘、地缘联系,乡土社会规则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存续,并成为乡村独有的运行逻辑。这要求国家资源下乡过程中,不能粗略忽视乡土社会规则,试图仅仅依靠程序化、理性化的技术治理方式来改造乡村社会,而应当在充分认识乡土社会规则功效的基础上,发现、培育并积极利用能够契合外部性资源输入的乡土社会规则,从而实现内外合力的有机融合,最大化满足村民真实的利益诉求,从而提高资源输入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
四、结论
乡村治理内卷化是国家资源输入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需求的外化形式,可能产生于资源输送链条的任何阶段。从资源输入的视角来看,乡村治理内卷化的产生并非国家或乡村单方面因素的限制,这是一个双向度交互塑造的过程。其中,资源输入的“强主观性”和“弱公共性”以及输入过程中的目标替代和地方势力截流,是乡村治理内卷化的重要外生变量;资源输入终端环境的复杂化以及目标对象理性化的行动逻辑,是乡村治理内卷化的重要内生变量。内外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形塑了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局。资源输入与乡村治理是互促关系,随着外部性资源输入的不断增加,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解决。我们在持续加大国家对乡村治理资源支持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资源利用的内卷化问题,只有正视并重视外部性资源输入与乡村社会各方面的有机衔接,才能真正破解乡村治理“最后一公里”困境,并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1]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5):96-110.
[2]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67.
[4] 马卫红.内卷化省思:重解基层治理的“改而不变”现象[J].中国行政管理,2016(5):26-31.
[5] 李祖佩.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J].中国农村观察,2017(6):116-129.
[6] 李祖佩.项目下乡、乡镇政府“自利”与基层治理困境——基于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涉农项目运作的实证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5):18-25.
[7] 周常春,刘剑锋,石振杰.贫困县农村治理“内卷化”与参与式扶贫关系研究——来自云南扶贫调查的实证[J].公共管理学报,2016,13(1):81-91.
[8] 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5(3):95-120.
[9] 李祖佩.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J].青年研究,2011(3):55-67.
[10] 欧阳静.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116-122.
[11] 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4):126-148.
[12] 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3(2):64-79.
[13]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 镇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1(2):86-101.
[14] 唐京华.村干部选举 “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 村换届选举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9(3):97-108.
[15] 高军龙,寇荷超,张海洋.协同治理:“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软着陆”的实现理路[J].理论导刊,2015(8):74-76.
[16] 付伟,焦长权.“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J].社会学研究,2015,30(2):98-123.
[17] 申端锋.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J].开放时代,2010(6):5-23.
[18] 田孟.项目体制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J].地方财政研究,2015(6):68-75.
The Roots of Rural Governance Involution and Its Solution from the Resource Input Perspective
TANG Jing-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169,China)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nvolution has been a major problem that has plagued China's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input,the emergence of rural governance involution is not caused by unilateral factors of the country or the rural.It is a two-way process.The exogenous variables can be listed as follows: “strong subjectivity” and “weak publicity” of resource input,the target substitution and the local forces closure.The endogenous variables includes the complexity of terminal environment and the rational action logic of the target objects.In general,it's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has jointly formed the rural governance involution.Resource input and rural governance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Only from the overall chain of resource input,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xternal resource input and rural society,can we really solve the "last mile" dilemma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resource input; rural governance; involution; pressure system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9)05- 0023-08
收稿日期: 2019-04-1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城市基层治理中社区协商民主的样态及引导策略研究”(N151402001)
作者简介: 唐京华(1992-),女,山东淄博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治理。E-mail: 1977939958@qq.com
(责任编辑 夏登武)
标签:资源输入论文; 乡村治理论文; 内卷化论文;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