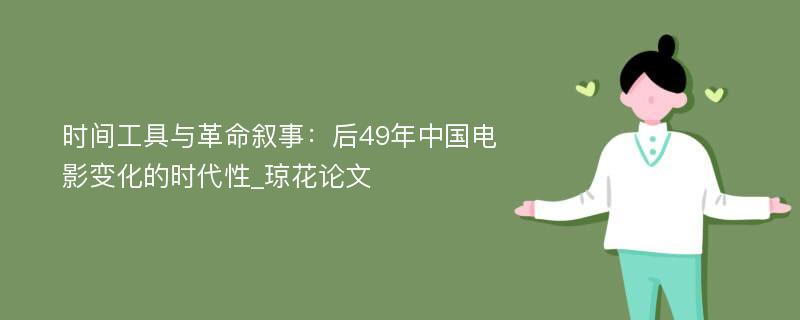
时间器物与革命叙事:“后49”中国电影变异的时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性论文,器物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11月11日,曾在左联风生水起的激进文人胡风,用一首情感四溢的长诗抒发了自己对月前天安门城楼那历史一刻的澎湃感怀。在这首赫然被命名为《时间开始了·欢乐颂》的诗篇中,物理时间幻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随着你抬起的手势,大自然底交响乐涌出了最高音,全人类底大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也幻化成了“洁白的心房充溢着新生的恩惠”的纯真婴儿,在此刻“神圣的时间”里,“现出欢喜的笑容,亮着温爱的目光,举起健康的手臂”,汇流到“响彻天地的大合奏”和“湿透发肤的大洗礼”中,向在“中国新生的时间大门上面”书写了超越但丁神曲的“中国人民的诗人毛泽东”欢呼致敬。①距此不到一年,华东画报社出版了一本由张乐平、张文元、韩尚义等上海名家参与创作、沈同衡作词的《解放前后大不同》漫画集,内容涉及中国经济、文化、社会、法律和市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在1949年“前”和“后”的比较。集子以描绘“前49”和“后49”景象的漫画结对串连结构,配以顺口溜似的解说词,目标读者群显然比胡风的长诗要宽广了许多。曾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漫画界、创作过《未来的上海风光的狂测》等经典的张文元,为集子贡献的是描绘城市经济生活“巨变”的两幅漫画:“前49”画的是股票交易所的疯狂,一个手拿数个电话听筒的股票投机商被四处飘洒的“发疯”“跳楼”“自残”“服毒”的纸签包围,满头大汗地跳到了交易所的桌子上;“后49”画的是城乡一体、秩序井然、顾客和商贩彼此微笑谦和的平静景象,对比之下凸显了所谓“过去生意靠投机,勾结官僚贪暴利,投机成功滥挥霍,投机失败害自己”和“现在生意讲实际,正当商业求本利,城乡互助物交流,有利人民也利己”的主题。②而另一位不甚知名的漫画家华农,则把比较的视点放在了日常生活和文化上:“前49”呈现的是穿着奇异、油头粉面的两男一女驻足在“今日开映好莱坞出品”的橱窗前,“后49”画的是一个剃了寸头、剥下了奇装异服的小伙,正虚心接受解放干部的马列教诲,准备走向“光明之路”;漫画配词曰:“过去多少小阿飞,美国电影是罪魁。全身像学洋流氓,横行胡闹生是非”;“现在阿飞都改造,指出光明路一条。小脚裤子自动脱,飞机长发也剪掉”。③
无论是胡风重启的时间,还是漫画集“49前后”的分割,凸显的都是时间在革命叙事和意义生产中的决定性。对不间断运动的物理时间而言,历史中的某一点不过是不可重复但却浸泡着过去和未来的一个普通瞬间,但对长诗和漫画所表述或呈现的主观时间而言,那一刻却标志着“时间的开始”和前时间的浑浊混乱以及时间“开始”后迥异的城市景观和国人精神。如果说诗歌和绘画的时间表现因为介质的限制还具有感觉的间接性和抽象性的话,那么电影和时间的关系则更紧密、更具体,也更直感,这不仅因为影像和时间、运动之间浑然一体的原初姻缘,更由于电影自诞生一刻起就创造了一整套关涉运动和时间的崭新逻辑。本文的研究路径起始于电影时间的讨论,兼及德勒兹“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观念以及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电影时间的浮现”论述的思考,重点在于依循这一理论脉络,以时间器物特别是钟表在几部“后49”影片中的使用为线索,分析“后49”中国电影悄然变异的时间性。④意识形态和电影生产体制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电影表意内容的革命性激变,这方面的例证俯拾皆是。不过,表意层面下变化的时间逻辑和关于时间的表述却并不比胡风长诗和通俗漫画所彰显的时间裂变更易把捉。本文旨在通过对“后49”影像时间逻辑的挖掘,论述中国红色叙事不仅意味着影像符号和言说话语的弃旧更新,也意味着电影现代性时间向电影革命性时间的裂变转型。如果说革命性也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性的话,那么,这一裂变转型从根本上说又是初生期电影与时间关系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也正因为如此,“后49”中国影像重建的时间逻辑却又充满了历史的悬疑与吊诡。
电影与时间:从《火车进站》到《劳工之爱情》
电影与时间的关系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电影I》和《电影II》思考的中心。德勒兹关于电影的论述,把电影看成是体现哲学思考和观念的一种体系,他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哲学家亨利·伯格森那里借来了关于世界乃是一个开放和充满时空流动激荡的完整体、亦即伯氏所说的“持续时间”(durée或duration)的观点,认为电影机制中的画面、镜头和蒙太奇等构成了“持续时间”完整体的截面。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完整体或“持续时间”的流动的话,那么,电影的画面和影像就是这一“持续时间”的某一有限切块,而切块之外的开放完整体(the open whole)仍在切块内间接显现。伯格森的时间和意识理论,将时间视为无法用数学和科学量度的持续流,一旦试图以数学或科学对某时刻进行度量,这一时刻则早已脱身而去。正因为如此,不可言喻的“持续时间”只能在意象中(images)间接显现,在想象的直觉中被捕捉到。⑤这或许是深受伯格森影响的德勒兹以哲学家身份完整介入电影这一机械文明时代所诞生的通俗文化样式研究的初衷,他在《电影I》和《电影II》中所提出的“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概念,不仅是对其所称的电影。“分类学”(taxonomy)的概括(受伯格森和皮尔士符号学的影响,德勒兹把影像分为六类,每一类皆由从属的三种符号构成,因此计有六类影像和十八种符号),而且更是理解完整世界的截面或切片,只有通过影像人们才得以窥见“持续时间”或开放的完整体的端倪。⑥
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思考枝蔓繁复,语义含混,新概念迭出,涉及的电影现象和电影人横贯东西,纵涉历史,需要专论方能窥知一二。不过,概括而言,他的“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大致与电影史发展的两个阶段即经典电影时期和现代电影时期相对应。在他看来,“运动影像”受日常世界常识性时空感所制约,最终需要服从常识世界的感觉定律。而以“时间影像”为标志的现代电影则不然,其中的常识性感觉定律被打破,代之以不受量度和精密计算同化的时间碎片。德勒兹以他详细分类的各种符号,如“视觉符号”(opsigns)和“音觉符号”(sonsigns)等,来阐释“时间影像”的浮现和发展,认为电影中碎裂时间性的出现最初可以溯源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尔后蔓延到各国电影,成为区分经典电影(classical cinema)和现代电影(modern cinema)的标志。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德勒兹关于何种符号之下出现了何种时间感的话,那么,我们或可总括地说,他的“时间影像”,涉及了各类碎裂含混的时间性,既有电影闪回中二分的时间,也有梦境片段和好莱坞歌舞剧中梦幻歌舞世界的漂浮时间,既有此刻实境和过往虚境的双重时间,也有折射、过滤和反映虚实交织的时间结晶(time crystal)。更为重要的是,在论及阿伦·雷奈、阿兰·罗布-格里耶、戈达尔和雪莉·克拉克(Shirley Clarke)、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的电影时,德勒兹提到了一种更具悖论意义的时间影像,其中“常识性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秩序让位给了过去的现在(presents-of-the-past)、现在的现在(presents-of-the-present)和将来的现在(presents-of-the-future)的悖论性时间”,其中“时间的演化生成(the becoming of time)显现在影像中”,此类影像“在‘此时’(now)中包含了一个‘前’,也包含了一个‘后’……显示了‘虚假的力量’,显示了时间演化生成的力量,这种力量侵蚀着固定不变的身份,使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区别难以判定”。⑦
在主要论述“时间影像”的《电影II》一书的尾声部分,德勒兹谈到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之间的“转型可能”及“混合”,认为“不能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或更漂亮、更深刻;只能说运动影像中产生不了时间影像”。⑧尽管如此,从他以伯格森时间哲学为基点切入电影研究以及他在《电影I》和《电影II》的具体论述和所举例证看,德勒兹显然对定义现代电影的“时间影像”偏爱有加。正如他所言:
运动影像依照时间的经验形式、依照时间的进程构成时间:一种与前、后有外在关系的连续的现在,故而过去是先前的现在,未来则是将来临的现在……运动影像从根本上说是间接的时间表述而非直接的表述,亦即不给我们提供时间影像……但与之相对,在现代电影中,时间影像不再是实证的,亦非形而上的;以康德的定义看,它是“超越的”(transcendental):时间在脱节中以其纯粹的状态显现自身。时间影像并不意味着运动的缺席(尽管常常包含逐渐递增的运动的乏匮),而意味着时间不再从属于运动;(相反),运动本身从属于时间……虽然与经典电影有密切关联,但现代电影所问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崭新的力量在驱动影像,究竟是什么崭新的符号侵入了银幕?⑨
如果说德勒兹的时间影像论述聚焦于“二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电影文化的话,那么,玛丽·安·多恩关于电影时间的思考则主要仰赖于19、20世纪之交萌生时期的电影现象。多恩的《电影时间的浮现》一书,把电影时间放在工业文明规制时间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就此建立了电影与现代性在时间观念上的紧密联系。人类对时间的考察和度量古已有之,远的有各式日晷,近的有各式水钟,西方有齿摆轮(Escapement),东方有苏颂钟;不过,机械钟表的普及和大规模使用却始于19世纪初期,这不仅与技术发展的缓慢相关,而且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使然。传统社会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发展模式,无论是在生产方式还是在行旅空间方面,都对精确测量的时间装置所需甚微,这也是为何当时领先全球的苏颂钟很快在中国被淡忘、各种西方机械钟表纷纷沦为大清帝国奇巧摆设的原因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推动了时间的理性化和标准化;火车旅行和电报传输的普及直接导致了所谓“火车时间”的出现。⑩1884年,在美国华盛顿国际时间标准会议上,以格林威治为子午线,世界首次被划分为24个时区。几乎在同一时期,致力于提高工业效率、被誉为“现代管理之父”的美国工程师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将时间的标准化和精确化应用到生产领域,发明了颇具争议的打卡机,旨在最严格地管理和掌控时间,消除任何时间的“浪费”。生产的泰勒化直接导致了精确计量的工业流水线的出现,不仅实现了时间的管控和理性化,而且也意味着身体的机器化和计量化。(11)
在现代社会时间理性化和标准化的大环境下,电影出现了。在多恩看来,初生的电影直接“参与到了更广泛的文化事项中,亦即参与到结构资本主义现代性时间和偶然性”之中。伴随工业文明迅猛发展而出现的表述新技术,如照相和电影等,对“现代性时间及其表述观念重整至关重要”,构成了19、20世纪之交人类时间认识剧变的重要一环。(12)多恩注意到,工业文明催生的现代性在时间观念上显示了深刻的悖论: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时间的规制和理性化,“时间变得单一、同一、不可逆转,也可以分解为能证实的单位”,最重要的是意味着“一种由技术引发的历史进步的不可避免性”,在电影中则表现为依赖视觉残留原理的余像现象和以镜头和片段构成、通过每秒特定格数投射到银幕上的持续时间和运动的假象;但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意味着与时间紧密相关的焦虑、异化、震惊感以及偶然性和不确定性。(13)这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既危险又具有无穷的诱惑力,危险是说对失去掌控时间和未来的恐惧,而诱惑则是偶然性提供了现代人解脱理性化工具化的机缘,因为未知至少允诺了追新求异的可能性和刺激性。电影的登场,不仅再次验证了时间的规制和理性化,而且更形重要的是,提供了现代人把握瞬间和偶然性的完整机制:
电影被视为时间的印记本身……这是一种未被理性化驯服的时间,一种非目的化的时间,其中每一刻都能生成意料之外的、无法预知的东西,生成使不确定具体化的时间性。电影……见证着时间侵蚀组织体系,成为偶然性的自由天地。(14)
在多恩看来,电影把握和表述瞬间性和偶然性的能力从一开始就完美地体现在卢米埃尔兄弟的“现况电影”(actuality film)中:“吃饭的幼儿,火车进站,工人离厂,摄影师到会,雪团大战,推倒院墙”等等,所有这一切,“捕捉的都是一个瞬间,记录并重复着‘发生的一刻’……旨在将瞬间定格化、重复化”。(15)或许最典型的例子是《火车进站》,因为影片从多个层面凸显了电影、时间和现代性繁复交织的关系。首先,火车本身不仅是现代性的标志图腾,更是前述标准化和理性化“火车时间”的体现;其次,关于早期观众因渐次逼近的火车影像而震惊四散的迷思,彰显了现代性所带来的速度、刺激、震惊乃至创伤性主体经验;第三,作为记录这一瞬间的电影机制,尽管自身受理性时间的规制,但却在画格与分秒的限制中捕捉并通过放映固化了现代性中那些本来不可重复的瞬间和偶然,由此为束缚在理性和工具化时间中的现代主体提供了嘉年华般宣泄的自由。
时间、电影和现代性的繁复关系也体现在中国影像传统中。当特定镜头仍处实验期的时候,中国现存最早的影片《劳工之爱情》(1922)就把一组颇值得玩味的特写镜头中的两个给了时间器物。(16)且说水果摊贩是夜回到家中,时而嗅闻绣花女抛赠的丝绢芳香,陶醉在你亲我爱的幻想中;时而却又想起横亘在幸福之间的江湖老郎中的作用,反反复复,不觉睡意朦胧。接着的特写镜头提醒主人公也告诉观众,此时已超过夜晚21点45分。镜头接到位处果贩楼上的全夜俱乐部,那里赌局正酣,嘈杂声中两个小混混因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镜头再切回果贩屋子,被惊醒的摊贩第一反应就是查看桌上的时钟。一个比前次更大的闹钟特写指向凌晨近三点。从叙事上说,两个时钟的特写凸显了故事线性发展的不可逆转性,但从意义层面看,特写也为片尾摊贩将楼梯改造为致人跌落的滑梯提供了某种道德的合法性。既然俱乐部客人们可以旁若无人地深夜喧闹,那么摊贩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社会阶梯的晋升也变得在道义上无可厚非了。一落一升之间,时间器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观众也在喧笑之余暂时从中国转型期的时间理性中脱身而出,陶醉在电影机制所允诺的“未被理性化驯服”的自由天地。
时间与革命叙事:从黄佐临到谢晋
“革命”一词,在中国话语中纷纷扰扰几千年,其沉浮徊转,几近模糊含混。学者陈建华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劳动保险孜孜不缀,心得甚丰。据他的考察,“革命”一词本源自中土,《易经》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恐怕是该词最古的出处。(17)因之,“革命”一词从原初开始就含有通过暴力改朝换代的意思,只不过经过各代儒士的阐释发挥,革命与天意民心挂上了钩,成为王朝循环更迭的合法说辞。不过,天意也好,民心也好,没有观察衡量的基础和制度,遂成为人人皆可用之的借口,也成就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和历史叙述中成者为王(坐拥天意民心)败者为寇(丧失天意民心)的逻辑。这也是为何后代君主和儒士们“在触及这个理论禁区时都小心翼翼”、孟子以民心和仁义为标准挑战君主权威的雄辩渐被后代儒士故意遗忘的重要原因。(18)
“革命”在半睡半醒中重新被激活并很快成为上至大儒、下至黎民使用的日常词汇,在陈氏看来,当在晚清政治社会动荡纷扰时期。不过,此时的“革命”,经过了西洋英法和东洋日本的旅行涤荡,早已与古意的“革命”渐行渐远。英语中的revolution与revolt词根相同,本来词义含混,用于政治领域则“叛乱”与“革命”之间“界限模糊”;更值得玩味的是,英法两国各自不同的变革给国人提供了两个版本的“革命”,一是17世纪引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非暴力“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二是18世纪晚期导致法兰西共和国在腥风血雨中诞生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再看“革命”在日本的遭遇,作为一个外来词从中国传入日本,かくめぃ(革命)的改朝换代思想从一开始就与“根植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观”(19)格格不入,经过日本儒者的阐释发挥,かくめぃ被本土化为绝对天皇观下的“尊王改革”或尊王变革思想,再加上英国历史的佐证,日本“革命”遂包含了“淘汰”或“变革”的意思,“所以明治维新和明治革命变成了同义词”。(20)不过,时事和文化最终还是让晚清激进党选择了法国意义的“革命”,并很快通过现代媒介的传播而普及到对时局日益感到无望的改良派和普通民众群体。此时的“革命”,虽然表面上承接中国古意,但在本质上却“脱离(了)过去‘周而复始’的含义,衍生出一种(现代性才有的)‘奇特的唯新是求的情结’。‘革命’被喻为‘洪流’‘巨浪’等,标示了不可抗拒的历史前进方向”,更是历史和历史必然的推动力量。(21)
无论是“光荣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也无论是明治革命还是近现代中国革命,“不可抗拒”和“历史必然”的话语逻辑与叙事脱不了干系。中国红色革命叙事虽然与“革命”一词相似,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浮沉跌宕,歧义丛生,但其起点却大致始自晚清特别是1840年,期间以1921年、1927年、1937年、1945年等为关键节点,到1949年达到本事的高潮,再以“历史必然”的总结结尾,在电影中则通常表现为浑厚的男声画外音。不过,正如本文引论部分的两个例证所显示的,该叙事原型在时间意识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吊诡。一方面,红色革命叙事必须以时间和历史为合法性基础,以鸦片战争以降的近现代史线性发展为铺垫,建立目的论为轴心的“自由”和“必然”。正如《解放前后大不同》漫画集所建构的逻辑那样,没有“前”也就没有“后”,“前”是“后”的叙事预热,“后”是“前”的叙事结果,二者互相依赖,“后”的合法性也在“前”的非法性中呼之欲出。但另一方面,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的断言,却在不自觉间与革命叙事的线性面向构成了紧张。“神圣”和“新生”时间在“一跃地站了起来”的那一刻,也是红色革命叙事与“前”时间断裂之时。从某方面说,这又是任何“崭新”话语逃脱不了的宿命:“后”的神圣化只能以涤荡“前”的记忆为代价。
时间接续与断裂的吊诡在“前49”制作、“后49”放映的《表》(1949,文华影业公司)中已隐约显现。与后来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作相比,黄佐临根据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同名小说改编的《表》显然有诸多“政治不正确”的“硬伤”:影片的主人公是街头流浪儿和知识分子味道颇浓的教导员,与工农兵自然关系不大;背景既非工厂乡村,更非炮火连天的战场,而是都市十字街头和正气最终压倒邪气的儿童教养院;更成问题的是,影片在描写流浪儿童和教导员联合起来与训导主任作斗争时,既未诉诸暴力革命的逻辑,亦未彰显共产党的力量。从很多方面看,《表》的互文性更应该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影作中找寻,其佐证乃是黄左临的改编版通过都市中产和流落城市街头“小瘪三”之间生活的对比,突出了原作中没有的、但左翼电影却偏爱至深的贫富差距和农村破产、城市畸形发展的主题。不过,影片对时间器物的处理却又在不自觉间埋葬了“前”时间,预示了在裂层中诞生的“崭新”时间的开始。
《表》的结构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小牛和他的两个小同伙混迹上海街头偷抢食物的故事,其中的转折点是小牛乘人不备偷了街角修表铺万老头铺子里的金表,而表的主人则是一个上海中上阶层的有钱“绅士”,被很自然地刻画为腔调蛮横的势利小人,万老头和女儿翠翠因金表不翼而飞面临牢狱之灾;二是小牛与小伙伴分赃不匀而扭打街头,结果自己被送往儿童教养院,期间受到教导员雷春华和以小胖为代表的小院友的感化,最终交出金表,加入了揭发教养院恶势力代表殷小臣的团体。串连两个部分的重要器物是那只随小牛一起被“送进”教养院的金表。影片中颇耐人寻味的一个场景是,经历了胆战心惊的洗澡风波后,小牛乘小院友熟睡之际,偷偷溜到教养院后门附近,乘着夜色把那只金表埋到了地里。金表的被埋,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是小牛与“前”或过去时间的诀别,并逐渐在教导员和小院友的耐心诱导下,拥抱满怀希望的“新”时间。影片前后对比的二分结构,尽管因恶势力代表殷小臣的存在而间有含混,但在时间和空间上却得到了双重强化。就空间而言,教养院外是贫富悬殊的都市罪恶以及“乡下人”初到城市的街头震惊和目眩神迷;教养院内则是教导员的慈父胸怀和小院友们的团结向上的群体精神。就时间而言,教养院外的时间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性时间的具象化:对都市富裕阶层来说,拥有了金表也就意味着拥有时间、拥有理性和权威,而在街头“小瘪三”和社会底层那里,以金表为象征的都市权力和现代性既意味着恐惧、焦虑和震惊,又似乎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影片中不断出现小牛紧盯商店橱窗内陈列的各式钟表的正反镜头);与之相对,一旦小牛被送到教养院内,另一种与之迥然不同的“崭新时间”逻辑开始浮现。小牛最初被警察送进教养院时,跟随患有脚气病的胖警和小牛的步子,镜头有意无意地在院门口悬挂的时钟上停留了片刻,仿佛预示了某种“新”时间的大门正在开启。随着剧情的发展,新时间的缕缕光芒愈益夺目:在教导员和伙伴的感召下,小牛交出了埋藏的“旧时间”(金表),带着灿烂的笑容加入到了建造新屋的群体之中。在“劳动创造新世界,自力更生,团结就是力量”的众声合唱中,全片以一个小牛面带笑容、举目憧憬未来的仰拍特写镜头结束。
如果说《表》只是开启了“新”时间的大门的话,那么,谢晋的《红色娘子军》(1960,天马电影制片厂)则带我们完全进入了变异的新时间之门。影片中有一幕在不自觉中与《表》的“深夜埋表”片段产生互文关系的“战场挖表”场景:洪常青凛然就义后,悲痛欲绝的吴琼花来到硝烟未息的战场,凭吊常青的革命英魂。跟随琼花若有所见的眼神,镜头转到了她踩在松软泥土上的双脚。很快,她发现了常青被捕前浅埋在战场的公文背包。琼花用手刨开了浅浅的泥土,打开皮色泛黄的公文包,特写镜头随之聚焦在包中三样寓意丰富的物品上:四枚银毫子,常青签字并盖有“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直属党组织委员会”印章的琼花入党申请书以及那只在影片中一直伴随常青革命生涯的美国造Keystone牌怀表。
银毫子和美制怀表是《红色娘子军》中反复出现的器物,前者至少出现四次,而且均为特写,后者则至少出现六次,一半是特写。关于四枚银毫子的寓意,学者多有论述,此处不赘。美制怀表的反复出现,则既关乎叙境中娘子军连几场战斗的关键节点,又凸显影片叙事的线性发展结构,更重要的功用则涉及革命时间的确立。通观全片,怀表不仅控制着革命行动的节奏,亦是权威、理性、知识的象征。娘子军连一共122人,但党代表洪常青是唯一佩戴怀表、掌控时间的人物;他循循善诱、特别是用中国版图开导琼花的情节,与脾气火爆、训诫战士不讲方式方法的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琼花禁闭室里的自言自语提问,“为什么常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既意在强调共产党与智慧之间毋庸置疑的天然联系,也旨在彰显掌控着时间器物的党代表的博学,这在后来琼花带着惊羡之情浏览洪常青的藏书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进一步而言,时间器物与权威、理性、知识和真理的联系并没有随常青的就义而中断。在挖出浅埋的公文包后,怀表很快转到了琼花的身上。此时的琼花,已不是那个满腔个人恩怨、只知道砍下南霸天脑袋的奴隶丫头,而已在常青和阶级姐妹的启蒙教育下,成长为一名“懂得多、看得远”的共产党员。特写中三样物品的同时出现,把琼花的红色成长故事推向了高潮:暗含个人情愫的四枚银毫子此时已转化为献身组织的会费,签字盖章的申请书为琼花领导娘子军连提供了合法性,而那只美制怀表则一方面象征着常青精神的永续,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生生不息的权威、理性、知识和真理的革命时间。影片结尾,党代表吴琼花身佩常青留下的怀表,向又一个娘子军连发出了动员令:放一把大火,把万恶的旧社会烧光,“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似乎为了更加强化这一点,影片以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琼花与红旗的叠印特写结束。
与《表》中时间接续与断裂的吊诡相异,《红色娘子军》无论是在叙事还是在寓意层面都呈现线性发展的逻辑。像流水线一样不间断前行的时间不仅保证了叙事的连贯性,而且寓意着寻找真理、认识真理、掌握真理的目的论时间旅程。革命时间就像那只老旧的怀表那样(颇具反讽的是,怀表产自革命的对立国)。准时,正确,代代相传,毋庸置疑,一往无前地指向“彻底解放”的那一刻。从表面看,变异的时间性似乎与多恩所论及的“单一、同一、不可逆转”的现代性时间吻合,(22)但在深层次上,革命时间却去除了现代性中因机器文明和生活速率畸变而导致的震惊、刺激乃至创伤体验面向;时间不再意味着焦虑和威胁,也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充满了未知的偶然性,而是一个由重构的国家电影机制理性管控和规制的单位,遵循着革命发展的线性逻辑和毋庸置疑的权威及真理性。不过,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像红色革命与美制怀表之间的紧张一样,革命时间或变异时间性的确立,在影像传统上仰赖的却是经典好莱坞“连续性”(continuity)和“真实时间”套路,即以“不易觉察的剪辑”(invisible editing)保证叙事的线性流,以清晰可辨的时间流来维持影像“真实时间”的错觉。换言之,如果以德勒兹的“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观念透析以《红色娘子军》为典型表征的“十七年”电影现象,“后49”中国电影尚未转型为德氏着墨甚多的“现代电影”(modern cinema),因为在“连续性”和“真实时间”的传统套路中,时间不是在碎裂含混、多重交织以及“脱节中以其纯粹的状态显现自身”,而是从属于运动和叙事,仅以间接的形态表述和显现自身。(23)就此而言,尽管“轰轰的雷声”和“神话里的巨人”宣告了时间的“开始”,(24)“后49”中国电影重建的时间性却吊诡地建立在其意欲竭力清除的以经典好莱坞为代表的传统电影逻辑上。
余话:再谈《不夜城》
笔者在《空间的审判:影像城市与国族建构》一文中,从空间再建构的角度谈到了《不夜城》(1957,江南电影制片厂,汤晓丹导演)所寓意的国家空间(state space)对城市空间(city space)的改写与管控。如果城市也和人类意识一样存在弗洛伊德所说的不同层面的话,那么,“后49”逐渐蚕食社会和个人空间的国族话语或可被看成是监控和驯化全球城市“本我”的“超我”力量。(25)在那篇文章中,笔者特别提到了影片中一处似乎游离在主要叙境之外的片段,其间“民族资本家”张伯韩(孙道临饰)默默地来到沙逊大厦的屋顶花园,远处是上海地标建筑海关大楼和楼顶的大钟以及高低错落的城市天际线和苍茫的黄浦江色。画面转为近景镜头后,我们看到张伯韩若有所思地来到花园的边际,目光朝下望去。镜头先切到从高楼上望去蝼蚁般渺小仓惶地行走在街头楼角的路人,紧接着再切回到张伯韩如梦初醒的近景神态。经过这一短暂的寂静后,无处不在的音乐和对话重新主导了影片的叙境。张伯韩如释重负般来到“民族资本家”的例宴上,公开宣布决定向党和政府坦白自己的“罪行”。
就空间重构而言,上引片段进一步彰显了张伯韩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因而“改造和教化张伯韩,也意味着规驯上海这座曾从中国版图‘切除’的不羁之城,将繁盛其中的‘暗黑’和‘混乱’的自由经济纳入意识形态上日趋一统的国家图谱之中”。(26)就时间的重构而言,这一片段或可解读为“革命时间”一统下罕见的“破裂”(cracked)和“断层”(fault),像“一条飞行线”(a line of flight)般给我们提供了进入“时间在脱节中以其纯粹的状态显现自身”的可能。(27)与《表》相似,《不夜城》的结构主要分为“前49”和“后49”两部分,始于1935年张伯韩留洋返沪继承父亲实业,终于张伯韩和家人朋友等在中苏友好大厦广场庆祝上海公私合营成功、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间以1951年工人积极投入红色印染布料生产的画面为转折,在时间上严格遵循线性发展的轨迹,为叙述张伯韩从西装到中山装、从漠视工人疾苦到被其献身精神所折服、从消极对待新政府到积极参与合作、从拒绝公私合营到快乐加入其中的革命传奇提供了明晰的时间脉络。不过,影片寻找真理、认识真理、掌握真理的目的论时间旅程却在张伯韩犹疑于沙逊大厦屋顶花园的那一刻显现了须臾的“断裂”(rupture)。这不仅因为该片段游离在影片叙境之外,更由于其暂时脱离了理性管控和规制的线性革命时间,在“断层”的隙口进入了现代性时间中焦虑、惶恐、异化、震惊以及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面向,也接近了德勒兹所称的“时间结晶”,哪怕仅只是一缕转瞬即逝的“飞行线”。
注释:
①胡风《时间开始了》,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0日。
②关于张文元《未来的上海风光的狂测》漫画的讨论,参见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③集体创作,沈同衡作词《解放前后大不同》,上海:华东画报社1950年版,第7—8、37—38页。
④Mary Ann Doane.Th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Modernity,Contingency,the Archive.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⑤Henri Bergson.The Creative Mind: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trans.by Mabelle L.Andison),p.11,p.165-168.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2010.
⑥德勒兹的影像“分类学”主要体现在《电影I》中,他所称的六类影像为:感觉影像(perception-image),动作影像(action-image),触感影像(affectionimage),冲击影像(impuLse-image),反思影像(reflection-image)和关系影像(relation-image)。参见Gilles Deleuze.Cinema 1:The Movement-Image,p.56-196(trans.by Hugh Tomlinson & Barbara Habberja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
⑦Ronald Bogue.Deleuze on Cinema,p.6-7.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2003.
⑧Gilles Deleuze.Cinema 2:The Time-Image,p.270(trans.by Hugh Tomlinson & Robert Galet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
⑨同⑧,第279—271页。
⑩1840年,英国大西方火车公司(Great Western Railway)首次采用格林戚治标准时间为公司火车时刻单位,以统一计算公司火车从伦敦到英国西南和戚尔士的时间,这一时间被称为“火车时间”。
(11)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是这一现象的最鲜活注解。
(12)Mary Ann Doane.Th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Modernity,Contingency,the Archive,p.4.
(13)关于现代性与速度、刺激,震惊效应以及创伤体验之间的关系,席美尔、弗洛伊德、克拉考尔、本雅明均有论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孙绍谊《重访早期电影:现代性理论与当代西方电影思潮》一文,载《当代电影》2012年第12期。引文见Mary Ann Doane.Th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Modernity,Contingency,the Archive,p.6-7.
(14)Mary Ann Doane.Th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Modernity,Contingency,the Archive,p.22-23.
(15)同(14),p.22.
(16)《劳工之爱情》中的其他几个特写是:木匠出身的水果摊贩和对街江湖郎中女儿之间的眉目传情和掷果抛绢引出了摊贩误戴近视镜的主观视点大特写;全夜俱乐部酒浓肉香之余麻将客赌运鸿福的牌局特写以及江湖郎中在水果摊贩的助力之下,生意大开后不断叠加的银元特写。
(17)《周易正义》卷五(脉望仙馆刊本,1887),第13页;转引自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8)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6页。
(19)沟口雄三《中国民权思想的物色》,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43页。
(20)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7页。
(21)同(20)。除《“革命”的现代性》一书外,陈建华关于“革命”的研究还体现在《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的部分章节中,参见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0页。
(22)Mary Ann Doane.Th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Modernity,Contingency,the Archive,p.6-7.
(23)Gilles Deleuze.Cinema 2:The Time-Image,p.270.
(24)同①。
(25)参见孙绍谊《电影经纬:影像空间与文化全球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5页。
(26)同(25),第23页。
(27)Gilles Deleuze.Cinema 2:The Time-Image,p.113,85,270(trans.by Hugh Tomlinson & Robert Gale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