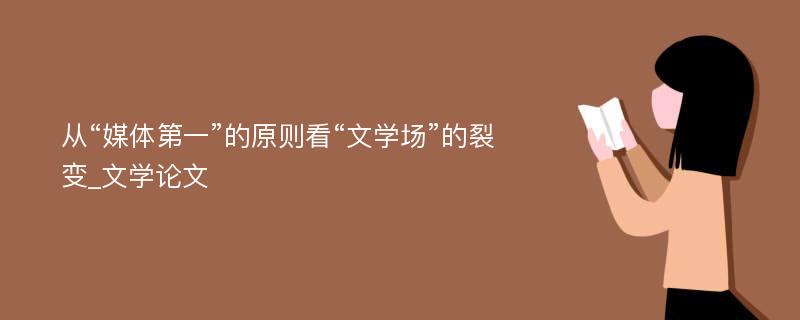
从“媒介为先”原则看“文学场”的裂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为先论文,原则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11)03-0018-09
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和进步都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关。艺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总是如影随形。几乎每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都以某种新技术的问世为基础。印刷的发明,使士大夫的诗文得以大量刊印和广泛流布与腾播,使拥有图书的人数大大增加。在西方社会,由印刷术的发明引起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复兴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知识冲破教会的束缚走向平民,文艺从王公贵族的深深庭院走向大众舞台。实际上,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印刷术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
印刷术具有连续性、同一性和可重复性等特点,可重复性这一特点使印刷书的价格相对于缮写的书籍价格要便宜得多,而且也让书籍的携带变得更加方便;同一性让职业文人应运而生;连续性使作家能够尽情地表情达意,能够对世界放声吟诵并直抒胸臆,表现手段狂放无羁。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印刷术造成诗与歌、散文与讲演本、大众言语与有教养的言语的分离,它直接改变了艺术生产的形式。”[1]印刷术的发明不仅造就了成功的出版商,也培养出了第一批职业小说家,并且对音乐和美术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静态地传播信息的印刷媒体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现代生活的需要。于是,新的媒体应运而生。近百年来,广播、电影和电视的相继出现,猛烈地冲击着曾数百年独步天下的印刷媒体的霸主地位。然而,对印刷媒介的致命一击也许来自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和应用。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提出过铅字行将消失的论断,认为以纸张为媒体的书籍已是日薄西山。在美国,托夫勒在他的《第四次浪潮》中也曾预言:“即使目前的词在以后仍然会被使用,但我们目前所谓的书却很可能消亡。”[2]与此同时,诸如罗伯特·库佛的《书籍的终结》、菲利普·迈耶的《报纸的消失》、阿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汉斯·贝尔廷的《艺术史的终结》、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杜书瀛的《文学会消亡吗》、陈晓明的《不死的纯文学》以及金惠敏的《媒介的后果》等著作与译著纷纷涌现。种种迹象表明,印刷文明的千年帝国也许真的到了改朝换代的前夕。
美国著名后现代小说家罗伯特·库弗说:“当今现实世界,我说的是这个由声像传播、移动电话、传真机、计算机网络组成的世界,尤其是‘先锋黑客’、‘赛伯蓬客’和‘超空匪客’,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纷扰嘈杂的数字化场域里。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印刷媒介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刻,命中注定要成为过时的技术,它只能作为明日黄花般的古董,并即将被永远尘封于无人问津的博物馆——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馆里。”[3]
今天,即将代替纸张出版物的电子出版物已经杀进书刊市场并开始争夺信息源和读者。与传统印刷出版物相比,电子出版物是立体的、充满趣味的,它的人机交互和自动检索功能极大地增加了读者接受信息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媒体电子出版物融文本、视频、声频、图形和图像于一体,绘声绘色,图文并茂,这既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提高了它的总体信息获取量。它体积小,容量大,操作简便,易于携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它都是出版业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同时也必然将会引发一场艺术生产的革命。
只要翻翻齐林斯基的《媒体考古学》就不难发现,当下流行的形形色色“终结论”绝不是空穴来风,纵观人类社会进化的历程,多少辉煌灿烂的文明早已灰飞烟灭!因为媒介链条的脆弱易断,历史上曾有多少经典著作早已悄然消逝。作为人类传递和保存信息的媒介,就是在这种与遗忘博弈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从结绳记事到刻木为文,从龟甲兽皮到布帛纸张,从专人缮写到活字排版,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智慧和经验,正在被越来越真实、具体、有效地以图文和其他形式保存下来。从铅字排版到激光照排,从“铅”与“火”的时代到“光”与“电”的时代,从用笔写稿到键盘敲入,再到网络传输,现代人资料与信息的传递已经准确和便捷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对于文学艺术而言,以网络为发展方向的现代传媒,无疑会带来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入性、广泛性和彻底性必定是前所未有的。以文艺接受为例,由于网络艺术的传播是数字化的、多媒体的和互动式的,网络艺术的接受者就像逛一个网络大超市一样,他们自由地选择艺术对象,同时还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还可以把网络艺术作品下载到个人电脑上,然后对其进行随心所欲的修改,接受者对艺术的鉴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二度创作”。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哪怕是即兴涂鸦的“作品”)送上网络。无论是艰深奇奥的作品还是通俗浅显的作品,网络一概来者不拒,诗人与大众之间已不再有鸿沟。
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说过,希腊神话和它对自然的观点以及对社会关系的观点,是无法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的。他认为,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是没有容身之地的[4]。我们过去一直把这些话理解为艺术生产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的“不平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论述分明也包含着一种惋惜,他认为就像阿基里斯不能同火药和弹丸并存一样,《伊利亚特》也不能同活字盘或者印刷机并存。他感慨地说,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4]?现代传媒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艺术的“必要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媒介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文论界关注的热门话题,现代传媒境遇下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介出现以后,文学与媒介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以及数字化语境中文学理论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等,都已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迫切需要探讨的重大学术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媒介不仅改变了文学艺术存在的本质,而且在改变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学艺术生存的基础。
事实上,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互动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媒介绝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作品及传播来说,媒介也不只是作品贮存的载体与流布的通道;对于读者来说,媒介也不仅仅是认识理解文学的门径与渠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介作为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它们既是文学生存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也是文学实现其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托,而且还是艺术理念与审美精神的寄身寓所。媒介在与文学长期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已逐渐由“是其所在”向“在其所是”生成转化,即媒介在对文学活动的“媒而介之”的过程中,已日渐深入地由文学的形式因素转化为它的内容与本质因素。
从文论史的视角看,文学媒介并不是一个新生概念。事实上,媒介及其相关研究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诗学命题。有关文学媒介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篇就以“首要原理”谈及媒介问题。他说:“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诗要写得好,情节应该如何安排,以及这门研究所有的其他问题,都要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得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5]亚里士多德这里所提出的艺术与媒介的重要关联,直接启发了莱辛对诗和画的差异的研究。莱辛的研究表明诗与画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分属于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范畴,但其最直接的差异却在于二者使用的媒介不同。艺术的品质固然取决于情趣、意象等心理因素,但其物化传媒也同样是直接决定艺术作品之成败精粗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媒介为先”的诗学传统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诗学》的问题时,开门见山地讨论“首要的原理”,而在讨论首要原理时,他首先涉及的就是摹仿的“媒介”问题。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所谓的“媒介”与我们所说的媒介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亚里士多德这一著名的文论与美学著作中,媒介即便不能说是“首要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至少也可以说是引导我们走向诗学原理的第一门径。
亚里士多德是从创作的视角发掘出媒介的重要意义,而当代学者王一川则是从文学接受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所谓“媒介优先”的原则。王一川认为,语言并不是直接向读者呈现的,而是借助特定的文学传播媒介来间接呈现的。不同时代的读者通过不同的媒介“接触”语言。《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当孔子收集、整理和阅读它们的时候,首先接触的可能是沉甸甸的“竹简”媒介,而不是这诗的四言句式;曹雪芹阅读它们的时候,接触的可能是手工印刷书;鲁迅阅读它们的时候,接触的是印制精美的机器印刷书;今天的读者阅读它们的时候,接触的则可能是通过鼠标在网上点击浏览的“电子书”。这种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必须首先接触媒介的状况,即“媒介优先”[6]。当然,人们对文学媒介的认识总会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即便都是优先考虑媒介因素,其内涵与结论也会颇不相同。毕竟,任何媒介都要依托于其传载物而存在。
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相当丰富的媒介论思想。例如,《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庄子区分了“书”与“语”的不同。世人所珍贵的“道”通过“书”这种媒介来传输,而“书”不过是承载语言的媒介,语言自有其可贵处。语言的可贵处不在它本身,而在它所呈现的意义。意义总有所指,意义的所指又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世人因为珍贵语言才传之于书。世人虽然以书为贵,我却以为书不足珍贵,因为所珍贵的并不是真正应珍贵的。庄子揭示了“书”这一文字媒介在他那个时代的文学传输中的基本作用:书是传输语言的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媒介在中国真正受到足够重视的历史却并不太长。近代以来,报纸与刊物对文学的影响快速凸现出来,媒介力量在文学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也迅速崛起,并越来越明显地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这才有了梁启超关于“报章兴”而“文体变”的论断。尽管当时也出现过黄伯耀《中外小说林》那样明确论及小说对报业依存关系的文字,甚至还出现过阿英把印刷与新闻之发达看作近代小说繁荣之原因的文章,但那些闪光的只言片语,毕竟与学术研究还有一定距离。就文学与媒体关系的研究而言,大约是到了近二十年,学术界才真正比较普遍地不再只是把媒介当作文学之载体看待,而是对媒介造成的文体观念、文体特征、创作意识和叙事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陈平原、王晓明和王富仁等人的相关研究颇有影响[7]。
新媒介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问题一向十分复杂。一方面,新媒介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仅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艺术消费经验而言,近六十年文学艺术之媒体的更新换代,足以令人生出沧海桑田的感慨。比如说,广播对于墙报可能是新媒体,而对于收音机它则可能是旧媒体;电影对于收音机可能是新媒体,对于电视则又可能被划归到“旧媒体”的范畴;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媒介出现以后,无论是报纸、书刊等传统媒介,还是以模拟信号系统为核心的“先锋媒介”,有时候都被一股脑地归入到传统媒介或“旧媒介”的行列中了。另一方面,媒介与非媒介之间也常常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看到,媒介相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其本质特征也具有极为复杂的多面性。譬如,文学艺术相对于语言来说是内容,而相对于审美意识来说却又成了媒介;语言相对于文字或声音来说是内容,但相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却又只能说是媒介;符号相对于纸墨等物质载体来说是内容,相对于可以传情达意的文字与声音来说却又是媒介。
二、“媒介即讯息”的文学意义
这种情形让人联想到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①。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解释:“所谓媒介即讯息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外面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8]传统文论认为,文学媒介属于形式的范畴,仅仅是主题、情节、观念、意象等所谓“内容”的载体,媒介本身是空洞消极且毫无意义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看法则不同,他看清了“内容”与媒介之间相互依存和潜在的可转换性特征,创造性地揭示了媒介自身的价值与功能。他认为媒介对“内容”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式媒介的性质决定着“内容”的形态特征和结构方式。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在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9]当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复杂多变且矛盾重重,与我们所理解的“媒介”、“新媒介”,尤其是“文学新媒介”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
当下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种广义的媒介观念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既有文献无不是历史与文化的媒介。例如中国儒家的“六经”就是今人得以了解先秦文化的重要媒介。自孔子问道于老子,得知夏、商、周三代的精神文化遗产,他历经五十余年,遍访多国诸侯,审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终于缔造出旷世的典范性文化媒介结构。有学者认为,孔子开创的“六经”体系,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与殷商的甲骨文献、西周的铜器铭文、埃及法老的泥版文书、巴比伦先知的旧约、印度释迦的贝陀罗经相比,编辑得更为严谨、系统和完整,因而成为更加成熟的“东方精神文化媒介”[10]。由此可见,无论是甲骨纸草还是金石简帛,不管是“四书”、“五经”,还是“旧约”、“新约”,任何能充当文化信息载体的东西,都可以看作是文化媒介。如此说来,有人将我们生活其中的网络社会称之为“泛媒介时代”,不仅言之有据,而且恰如其分。
尽管如此,为了避免概念的混乱,我们首先还是要把讨论的范围定位在当代文论的一般意义之“文学媒介”上。什么是文学媒介?王一川认为,文学媒介是文学的感兴修辞得以传播的外在物质形态及渠道,包括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大众媒介和网络媒介等类型[6]。这个定义对媒介“内在”的本质特征似乎缺乏应有的开掘,因此,定义者在“外在物质形态及渠道”的定义之后,补充了一句看似多余却意味深长的断语——“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意在弥补其定义忽视了媒介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的缺憾。
我们注意到,无论我们说的“媒体”、“媒介”或“传媒”,如翻译为英文都可使用同一个单词:“medium”(其复数为media)。其核心词无疑是这个“媒”字。“媒”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有10项释义:一、说合婚姻的人。二、说合婚姻。三、引荐的人。四、引荐;推荐。五、媒介;诱因。六、导致;招引。七、向导。八、谋取;营求。九、射猎时用作诱饵的鸟兽。十、酒母。何为“媒介”呢?《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一、说合婚姻的人。二、使二者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适合文学媒介的解释大概只能是第2项的意义。不过,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似乎将《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多数释义都囊括其中了。如“引荐”、“诱因”、“导致”、“招引”、“向导”、“谋取”和“营求”等,都可看作是使文学各要素(作者、作品、读者、社会等)之间“发生关系”的基本方式。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一系列著作中,他列举了大量的文学经典作品作为媒介发挥各种奇特功能的例证。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倾向于把“文学媒介”定义为使作者、作品、读者、社会等文学要素之间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譬如,行吟诗人荷马曾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说唱形式的“媒介”,电影《特洛伊》是《荷马史诗》的影视形式的媒介,《塞壬女仙》是史诗《奥德赛》和相关希腊神话的网络游戏版的媒介。如此定义媒介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它顺应了当代文学大众化、影视化、图像化和网络化等形态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使媒介概念顺理成章地突破了期刊、书籍等传统物质形态的束缚,而将广播、电视、电影、光盘、网络、MP3等多种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新方式和新方法,以及规范其存在和发展空间的物质形态悉数囊括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媒介的概念已不局限于创作与作品或作品与消费之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它理解为文学各要素之间互动的舞台,并直接将媒介理解为文学要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关于媒介与文学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相关新著陆续出版,如黄鸣奋的《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单小曦的《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等,都是文论界研究媒介问题的专精之作。特别是相关译著的大量涌现,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如由何道宽翻译的“麦克卢汉研究书系”,就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材料。
按照黄鸣奋的说法,对媒体新与旧的区分,是某种发展观的体现,或更准确地说是进化观的体现。在这里,媒体的演变被理解为历史过程。“新媒体”在时间上通常是较晚出现的;在功能或特性上,它与既有媒体是存在某种区别的。当然,上述演变并不一定以新媒体淘汰旧媒体的方式进行。新媒体出现之后,往往和“旧媒体”并存,只不过它们的职能各有不同,彼此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通常的情况是“新旧互补,相辅相成”。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媒体生态。黄鸣奋以电子媒体与印刷媒体、数码媒体与模拟媒体、线性媒体与非线性媒体的关系为例,详细地阐释了新媒体的三种定位。
人们所说的“新媒体”,无疑属于电子媒体范畴。在历史上,电子媒体之“新”,首先是相对于印刷媒体而言的。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传递的信息类型的差别可以用三对矛盾的概念来解释,即传播与表情、抽象与表象、数字与模拟。黄鸣奋说[11]:“印刷媒介仅包含传播,而大部分的电子媒介也传递了个人的表情。电子媒介将过去限于私下交往的信息全部公开了。电子媒介将过去人们直接而密切观察时所交换的信息也播放了出来;抽象/表象这对矛盾提供了另一种区分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方法。印刷媒介去除了讯息大部分的表象形式,它仅传递抽象的信息,但大多数的电子媒介传递的信息除了抽象符号外还有大量的表象信息。”
总之,“媒介即讯息”的论断,正日益得到网络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验证。从根本上说,文学和任何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最基本的功能无非是传播思想与情感的信息而已。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任何文学作品,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而言,它们都既是媒介,又是信息。
单就文学创作而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在激发灵感、搜集素材、辅佐构思、调动心智存贮、规范语言表述以及简化校阅修改程序等方面都已显示出有助于写作的惊人潜力。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介正在塑造着自己的现实,即所谓“超现实”(superreality),在这个所谓的“超现实”的世界里,无论是表意的“抽象符号”还是传情的“表象信息”,一切都将“数字化”为“讯息”,包括“媒介”本身也不例外。姑且撇开“文学即讯息”这一简单的事实,即便单从“工具”层面来考察媒介,新型网络的力量也绝不容小觑,它在改造人类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同时也使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悄然发生了变化,于是,关注内心世界的文学艺术也必然相应地发生本质变化。
三、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
现代传媒对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储存与传播方式、批评与鉴赏模式等等都带来了重大变化。其中,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化是新媒介造成的审美观念的转型。仅就网络化写作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文艺载体日趋多元化。从单一的文字读写和带着原始气息的口头传播形式到电子文化时代的多种“有声有色”的传播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传统文艺的疆域已经变得接近于无限宽广。其二,创作主体出现群体化倾向。“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使所有网民都有机会参与创作,各种新兴艺术式样也使艺术生产的分工与合作变得越来越明细化。其三,网络化写作极大地改变了艺术的创作方式。单个作家依靠“文房四宝”打天下的传统写作方式正渐渐被键盘操作所替代。文字的神韵逐渐消失而其符号功能则得到了加强。而且,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现代传媒还破坏了传统文学和艺术的本源的权威性,破坏了传统艺术模仿现实的权威性。这导致了美和艺术的生产方式、结构方式、作用方式、知觉方式、接受方式、传播方式和评价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并改写了关于美和艺术的审美观念。
过去艺术与生活两者之间的清晰界限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实际上,经过电子文化包装的现实早已像幻影一样迷离,而美和艺术因为高技术文化所提供的新手段(新闻报道、电影、电视、摄影)却反而成为现实,本源性、唯一性以及原作的观念悄然退出了艺术神坛。例如在一系列古典名著的游戏软件中,文献所载的“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实在在地被无数库存在“阅读”者和电脑的合作过程中的“可能发生的事”代替了。即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电子艺术也应该比纸质媒介艺术更有“诗的意味”和“哲学的意味”。
在互联网络这一媒体中,融入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电视等多种艺术样式,是各种媒介相互渗透、取长补短的产物。它将多种文化的优点集中起来,再加以创造性地发挥,这极大地提高了艺术生产的创造力并使艺术消费变得通俗直观和简单便捷。以光速传播的网络艺术是传统的印刷文化艺术难以匹敌的。
总之,在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传媒语境下,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历史性的大变革中,“文学不是‘终结’了或‘消亡’了,而是转型了。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生产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斗争又联合,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12]
有学者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传媒语境中“文学场”的裂变: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文学在广大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精英文学,又不同于大众文学的文学活动空间。网络文学的自由性、去中介化、在场性和互动性等传统文学活动所没有的特点,完全有理由要求重新划定文学存在的边界和文学存在的属性。当代社会中统一的“文学场”不再存在,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均形成了各自的“次文学生产场”,不仅每个“次场”内部充满了斗争,它们相互之间也竞争激烈,并未显示出“终结”迹象。
在《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一书中,单小曦提出并论证了文学活动第五要素论。他认为,在今天的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下,文学传媒是继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后文学活动的第五要素。如果考虑到传媒要素在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中的存在,对于重新确认文学存在方式意义重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文学的存在方式赖以构成的主要物质性因素由“四要素”、“三元素”扩展成为“五要素”、“四元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要素”、“元素”增加的问题,系统、场域中的新元素(特别是较活跃的新元素)的增加,会给系统、场域的整体存在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因此,在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类似的本体性构成要素已不单单是语言问题,而应扩展为包括语言在内的范围更广的文学信息传播媒介,即文学存在的传媒要素。这些传媒要素包括四种类型:一是符号媒介,如口语、书面文字符号等;二是载体媒介,包括石头、泥版、纸张、胶片、光盘等;三是制品媒介,如册页、扇面、手抄本、印刷书刊、电子出版物等;四是传播媒体,如期刊、电影、电视、网络公司等相关部门。这些传媒机构集生产职能与传播职能于一身,从传播学角度说,它们就是传播媒介。
批评家黄发有[13]曾将多种形式的媒体比作一张无形的大网,它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文学的跨媒体传播之网,更像城市地下盘根错节的各种管线,有煤气管道、通信光缆、自来水管,它们输送的资源点燃了城市的炊火,迅捷地给城市带来各种信息,滋养着城市中的生命。不能忽视的是,在城市的地层深处,最为庞大而复杂的管道网络是排污系统,它汇聚了城市最肮脏的液体,将它们排泄出城市的躯体。今日的媒体和文学同样如此,其中既包含着像水、火、通讯一样的不能或缺的精神资源,也不断地生产出大量的文化垃圾,如果不能正常地将它们排泄出去,文学和文化的生态都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且,这个年代的媒体和文学,产量最高的一定是日常化的精神消耗品,就像煤气、自来水和信息一样,它们带来了种种便利,但它们在被消耗之后,也会留下废气、废水和垃圾信息。
由此不难看出,技术在创造出许许多多的文化消费新花样的同时,也在把技术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强加给文化。如果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逻辑,即技术的逻辑和文化的逻辑的话,那么这两种原本并不兼容的逻辑如今出现了新的局面,技术的逻辑在文化中,特别是在大众文化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技术的逻辑正在逐渐消解文化固有的逻辑,并有取而代之的倾向。这样一来,在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一个尖锐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即周宪等学者所说的“工具理性对表现理性的凌越”。
当文化的媒介化趋势已经变得不可阻挡时,当技术的作用在文化中不断上升时,技术自身的工具理性逻辑便不可避免地增强起来,甚至有可能超越审美固有的表现理性,并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于是,技术的解放力量反而变成了解放的桎梏,对技术因素的迁就和依赖,在艺术生产领域也变成了一种潜在的足以造成创造力衰减的危机。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代媒介无休止的更新换代不断助长了技术力量向艺术生产的本体性渗透。由于当代艺术生产对科学和技术的依赖,在不知不觉间,传统手工艺性质的艺术生产活动和鉴赏型的艺术消费行为逐渐消失了,对艺术创造性的追求渐渐变成了对技术和工具的革新的追求。在科技意识形态不可抗拒的影响下,技术作为操纵艺术行为的幕后指挥,正在渐渐走向艺术舞台的中心。说到底,媒介对文学艺术最深层的影响是它已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悄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对于网络时代的文学艺术来说,新媒介绝不仅仅是工具和手段。
注释:
①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是当代文论家们引用得最多的名言之一.不过,这里的“讯息”(Message)被中国文论界的许多学者误写做“信息”(Information).这类误读显然与吴伯凡《孤独的狂欢》中提出的“媒介即按摩”(Message is massage)等妙解存在本质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