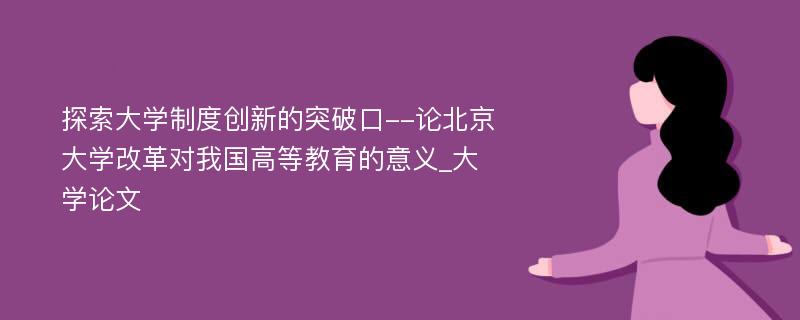
探寻大学制度创新的突破口——谈北大改革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破口论文,制度创新论文,北大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制度创新需要急迫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制度创新。北大改革的意义不只是在于北大本身的改革,它对于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具有象征性和导向性的意义;北大改革也不仅仅是要革新人事制度,短期的改革更需要着眼于长期的制度设计。
一、变“政府管制”为“大学竞争”
大学制度创新,要解决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大学过于由政府主导,大学之间没有实现充分的竞争。政府要面对所有的大学,就只能设立统一的规则、标准,用管三流大学的办法来管一流大学,或用一流大学的标准来衡量三流大学。结果是所有的大学都向同一个标准收敛。例如,教授本来是大学的职位,大学水平不同,选聘教授的标准也应该不同,不应该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博士学位也应是大学授予的学位,而不应是政府授予的学位。在现有的大学管理体制下,教授职位和博士学位是通用的,大学之间缺乏真正有效率的竞争,缺乏创造知识、追求卓越的竞争。几乎所有的竞争都变成了向政府争资源、争名额、拉关系等等这样一些不健康的竞争行为。政府的资源是通过行政系统分配的,大学的资源是大学行政部门争来的,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失衡,行政人员权力过大。
当然,政府对大学过度管制的问题并非中国特有,欧洲国家也存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严重。大学本身起源于欧洲,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为什么过去一百年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的大学把欧洲的大学远远甩在后面,成了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主要原因就在于,欧洲国家的政府对大学的严格的管制导致大学之间缺少竞争;而美国实行的是高度竞争的大学体制。大学之间的竞争使得每个大学都必须努力吸引优秀人才,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在一流的大学找到工作,水平越高的学者得到的待遇也越高,学术水平自然就会提高。而政府过度的管制必然导致大学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对大学提出的需求。
北大的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主要在于它对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有着很强的象征性和导向性意义。任何一个大学没有办法只靠自己成功,北大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鹤立鸡群,如果10年之后仍然鹤立鸡群,北大的改革是失败的,北大改革的成功,意味着在后面紧追北大的应该有十几二十几所大学和北大竞争,使北大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这样才能使北大保持必须永远往前走的动力。我们现在有1000多所大学,北大、清华在其中可以说是鹤立鸡群,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表现。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有1000多所大学,其不相上下的一流大学,至少应该有10至20所。几十所大学不相上下,或者至少在不同的专业务有优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充分的竞争。这种竞争对于推动学术进步,推动整个社会、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加快大学发展通常的办法是集中一些资金,加大投入。然而,如果不能形成大学充分的竞争格局,投入再多,可能都是在浪费资金。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讲,体制改革和大学制度创新比投入多少资金都要紧迫得多。我们现在应该向体制要效益。即使在现有的投入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把大学的体制真正理顺,不断创新大学制度,从而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学术市场,中国大学的潜力就不只是一倍两倍的问题。
二、变“内部市场”为“外部市场”
大学制度创新要解决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大学内部制度创新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学的内部治理,可以归结为一种学术上的“家族体制”。这是最彻底的“内部市场”体制:本校毕业生留校当教员,教员先从助教(或讲师)开始,然后一级一级提拔,直到正教授,然后工作到退休;新老教员之间通常是来自在现在体制的师生关系,同龄教员之间是师兄弟关系,整个院系像一个大家庭。在这种家族体制下,造成现行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教员队伍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走,没有淘汰;职务晋升以内部提升为主,缺乏外部竞争压力;职务晋升标准过分注重候选人论文数量和申请者之间的相对水平,过分注重内部平衡,过多地考虑了资历的因素,而对论文质量水准和候选人在全国学界的地位注意不够;部分院系新教员招聘近亲繁殖严重,博士生“自产自销”比例过大,等等,这些都不利于活跃学术气氛和鼓励学术创新。
事实上,自古以来学术界都是以外部市场为主,内部市场为辅。在西方,企业用人多是内部市场为主,外部市场为辅,但大学正好相反。在欧美国家,所有教职岗位的空缺都向外开放,如果不通过登广告的方式公开招聘,将被视为违法。即使某个院系或教授已经有了自己中意的后选人,也只能通过对申请人资格的特殊要求或面试来保证自己所希望的候选人入选,做到形式上不违法。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是由学术市场和大学的特点决定的。
首先,没有外部市场,就难以有知识创新。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授和创造知识。对研究型大学而言,创造知识是首要的任务。教员要创造知识,教员之间就必须能够平等地讨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教员是另一个教员的老师,甚至老师的老师,要让后者挑战前者的权威常常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家族式学院里,人们之间的客气多过争论,创新很容易被窒息。老师通常不期望学生与自己的观点相左,学生满足老师期望的最好办法是不反对自己的老师。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达到像老师一样的水平都很难。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学里很少有学生超过老师的,祖师爷的权威永远无人能挑战。一个人如果到四五十岁仍然不能在学术成就上超过老师,那不仅是学生的悲哀,也是老师的悲哀。西方的学者之所以能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因为他们不在老师的身边,享有更大的学术自由。而这只能在外部市场为主时达到。另外,科学创新常常源于不同思想火花的撞击,这在学术同事来自不同的门派时最有可能发生。同一老师教出的学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雷同,他们之间很难有思想火花的撞击。
其次,只有引入外部竞争,才有大学的优劣之分。学术市场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同一学科领域的学者使用的是同样的学术语言,衡量学术成就的高低有公认的统一的行业标准。一个优秀的学者不论到哪一所学校,都应该是优秀的。外部市场竞争不仅是检验一个人学术水平的关键,也是维护学术的行业标准的关键,更是导致大学有优劣之分的关键。哈佛大学是世界一流的,不仅因为哈佛培养了世界一流的学者,更因为哈佛只接纳世界一流的学者,也只有世界一流的学者才能进哈佛当教授。二流的大学之所以是二流的,是因为他们只能招聘到二流的学者,也只有二流的学者才愿意进入这样的学校。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如果一个大学不是以外部市场为主,而是以内部市场为主,一个人一旦进入就不出去,不论水平如何最终都能爬台阶当教授,而外部的人再优秀也进不来,这个大学实际上就变成了先来者的家族企业,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
最后,只有引入外部市场,才有可能实现职务晋升的公正。学术人才的信息是最透明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成果的所有者。当我们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学术论文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知道它的作者是谁。这就决定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学者可以有统一的市场价码,优秀的人才不会被埋没。外部市场也是显示个人价码的重要机制,竞争的学者市场可以给每个人最正确的评价。在竞争的市场上,要做到不公正是很难的。相反,如果教授市场是内部化的,个人没有市场价码,优秀的人才就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教师队伍的内部市场通常导致的是“同”,而不是“和”。“同则不济”,这是导致大学学术水平难以改进的重要原因;只有更大的对外开放,才能有“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局面。
三、改革需要着眼于长期的制度设计
北大改革方案公布于世之后,其他大学也会进行类似的改革。事实上有很多大学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改革,所以北大的改革不是超前的,但是北大的改革有一个着眼于长期的制度设计。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好“突破口”。有人说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准能动全身的这一“发”,先牵起来,而不能因为害怕动全身而不敢牵这一“发”。一定要把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过程分开,改革的过程只要有助于达到最后的目标就是可以的。
为什么选择教师体制作为突破口?第一,教师毕竟是大学里最重要的资源,是实现大学理念的源泉。如果教师的质量上不去,其他的如行政服务、后勤服务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教师体制晚改一年,就会有一些新的不合格的教师被提拔,以后改革就更为困难。所以早改比晚改好。第二,教师体制的改革将创造对其他方面改革的强烈需求,从而会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包括学校行政和后勤体制的改革,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博士生培养体制的改革,科研资金分配体制的改革,大学决策体制的改革,干部任命体制的改革,等等。至于政府对大学管制的改革,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但是坦率讲,学校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呼吁,但不具可操作性,只能等待政府出面来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北大的改革,对改革政府管理大学的方法本身提出了要求。
改革就像盖大楼一样,承重墙盖好是不能动的,动了,大楼就塌下来了。北大的改革里面也有承重墙。北大改革方案提出的新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1)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2)学科实行“末尾淘汰制”;(3)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4)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5)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6)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
其中,“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是指在讲师和副教授岗位的教员都有固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最多只能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副教授一旦晋升为正教授,将获得长期教职(类似国外的终身教职)。“学科实行‘末尾淘汰制’”是指学校对教学和科研业绩长期表现不佳的教学科研单位,将对其采取限期整改、重组或解散的措施;而在被解散单位工作的教员,无论有无长期教职,都得中断合约,但有些教员可能被重新聘任。这里,“业绩长期表现不佳”的标准是该单位在国内大学的相对地位,如某学科教研室长期排名在国内10名之后,将可能被解散。解散后,学校可能建立新的教研室,原来的一些教员有重新被聘任的机会,但不保证一定被聘任。如果学校不再建立新的教研室,有些教员也可能去应聘其他院系。至于具体的标准只能待后根据情况制定,不同学科淘汰的相对名次不同。无须讳言,这两个特征结合起来基本上就是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tenure-track”制度。这种制度也被称为“up-or-out”(不升即离)合同。在美国,这种制度是长期历史竞争的选择,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欧洲过去没有这样的制度,现在他们也开始学习美国的制度。在英国的其他大学,直接获得终身教职的也越来越少了。大部分讲师刚开始都是合同制。另外,有鉴于教师没有压力导致的英国大学的衰落,英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引入大学评估制度,政府的教育经费的分配是根据科研评估的分数分配的,大学不得不开始淘汰业绩表现不佳的教员和对学科实行“末尾淘汰”。中国大学的职务体系更类似美国,但教员工作的稳定性类似过去的英国,所以我们的问题更多。
首先,学术人才的选拔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不用说他人,即使一个人自己也难以在获得博士后一开始就确认自己是否是最适合做学问的人才。因此,在选人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大学必须给自己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一个人从事学术工作的最初几年是展现自己的才华的时间,是学校甄别优劣的时间。如果没有高的淘汰率,只进不出,必然导致有限的岗位被一些事后证明不合格的人占据。进一步,如果没有淘汰,也会诱惑一些明知自己没有学术创造力的人也来大学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如果有淘汰制,那些明知自己不适合做学问的人就会自己选择不申请。象哈佛大学,每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该校任教的年轻教员(assistant professors)的淘汰率在80%以上,也就是说,几年以后,这些年轻教员中只有不到20%的人能拿到终身教职(tenure),保证了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成为终身教授,那些被淘汰下来的人许多也可以在其他次一级的大学任教。
其次,学术人才的选拔只能由现在的同行做出,但人性的一个基本倾向是不希望别人超过自己,因此,如何防止“武大郎开店”是大学选人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学术竞争与企业竞争有所不同,企业不用优秀的人,市场竞争很快就会把它淘汰出局;但大学声誉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新建大学要在短期得到社会的认同是很难的,而一旦建立起好的声誉后,短期内也不可能垮台。这给老大学一个竞争优势。就生存而言,大学面临的竞争压力远远小于企业。比如说,即使我们北京大学从现在开始10年内只招收平庸之辈,10年内我们仍然十有八九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至少不会关门;而一个企业如果三年内不招收优秀的人才,到第四年十有八九就不存在了。因此,“武大郎开店”是大学用人制度面临的最大威胁。
第三,解决“武大郎开店”的问题,一是要使决定招聘决策的人没有后顾之忧,二是要使他们不得不招收优秀的人。在tenure-track制度下,现有的教授已经获得了终身职位,因此不再担心自己被新的、更优秀的人才所取代,至少他们对优秀人才的恐惧没有在自己无终身教职时大,这就为优秀人才的进入提供了可能。但即使他们不担心自己的工作受到威胁,也可能担心自己在本单位的学术权威受到挑战,他们仍然可能不愿吸纳优秀的人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学科上引入“末尾淘汰制”。如果现有的教员“武大郎开店”,末尾淘汰制将把整个“店”炸掉。这就保证了现有的教员有巨大的压力招聘更优秀的新教员,新教员水平越高,原来的教授的地位越稳,或者说新教员水平越低,现有的教授工作越没有安全感。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先天素质和良好的后天学术训练(特别是博士生阶段的训练),也依赖于个人在工作阶段的刻苦精神。人的潜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关键看有没有足够的压力,有没有足够的竞争,在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在tenure-track制度下,年轻的教员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有巨大的压力作出优良的学术成就,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而获得终身教职的诱惑使得他们更有积极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