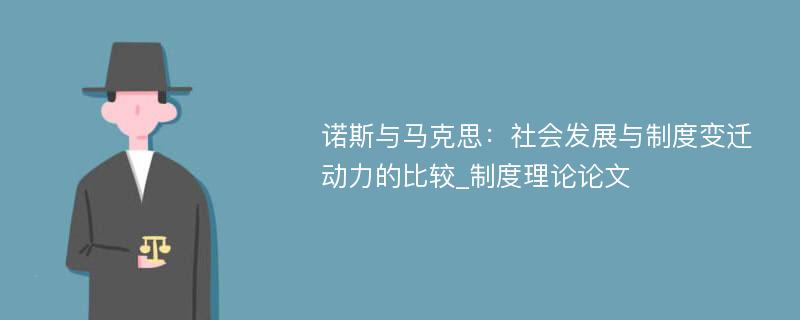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社会发展论文,诺斯论文,动力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6;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0)03—0025—09
马克思是第一个对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和变迁的一般规律做出系统阐述的思想家,后来的任何试图构建历史理论的人都无法回避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用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理论革新了经济史研究的道格拉斯·诺斯(D.C.North)教授,也躲不开马克思。 他在肯定马克思的贡献的同时,认为“马克思模型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一个理论解释技术变革率,还在于在忽视其他变革原因的情况下对技术的强调。例如,马克思轻视人口变动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单独的技术因素几乎不能解释许多长期性的变革,在这些变革中,技术似乎没有重大的变化,或技术变化似乎没有要求重大的组织变革来实现其潜力”(注: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2.)。可见,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歧之点,在于对社会发展或制度变迁的动力的不同解释。本文拟在比较马克思和诺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史实,对诺斯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的“局限性”的重要突破做些验证。显然,这种验证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次“证伪”。
一、马克思的生产力一元动力论与诺斯的批评
马克思对历史唯物史观做过如下纲要式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2—33.)
这段经典表述说明,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的这个看法基于这样一个因为太过普通而为以前的所有贤哲所忽略的事实:“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事实构成“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因而“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这也是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形成的前提。撇开这个前提,就谈不上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
用财产关系或生产关系来解释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起源和性质,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梯也尔等人对这一点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基佐在《英国革命史》等著作中就已经看到,要理解一定的国家制度,就需要研究社会中的不同阶级及其相互关系,而要理解这些社会阶级,又应该知道土地占有关系以至全部财产关系的性质(注:参看: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M].北京:三联书店,1961,第2章.)。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将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进一步归结为生产力的状况或发展水平,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使人们摆脱了18世纪以来启蒙学者关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二元论的困扰,将对于社会发展的解释唯物主义地置于一个统一的基础之上。因此,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称为“一元论历史观”。
根据“一元论历史观”,社会制度演进的机理可以概括如下: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导致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以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的变化;生产技术组织的变化又引致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变化(注:参看:林岗.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J].哲学研究,1987,(4).);而生产关系的变化最终引起政治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在理解这个社会制度演进机理时,要避免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当作是绝对的单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马克思本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多次强调过,生产关系,或者说财产制度、经济制度,也会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尽管最终起作用的因素还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仅表现为旧制度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而且表现为新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即新制度可以“诱致”更多、更快的技术创新,从而加快生产力发展。同样,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也反对作机械的理解,而强调在考察社会制度变革时,要充分注意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对于否定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朋友”将自己的理论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他是深恶痛绝的。他曾针对片面地将历史唯物论归结为“经济唯物主义”的庸俗说法愤慨地说:“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64.)可见,说马克思无视变革的其他原因而强调技术一个因素,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诺斯好像并没有读过马克思本人的有关论述以及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论点的阐发,因而误解了马克思。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解释制度变革的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没有作用,就谈不上反作用,尽管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首先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其次是既存的社会制度能够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所包含的对诺斯所谓“技术变革率的解释”。较之诺斯对私有产权制度诱致的技术进步的片面强调,根据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所做的这种解释,显然要更为全面和准确。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诺斯只是强调了制度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忽视了作为制度变革根本动力的、作为一个世代累积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生产力自身的发展。离开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在探索自然规律、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知识存量,为诺斯所片面强调的制度诱致性的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没有发生的基础。
至于诺斯以“单独的技术因素几乎不能解释许多长期性的变革,在这些变革中,技术似乎没有重大的变化,或技术变化似乎没有要求重大的组织变革来实现其潜力”为理由对马克思的批评,则似乎是出于误解。这种误解与他的制度变迁同马克思的制度变革的不同含义有关。马克思所着重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亦即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的变革。而诺斯的制度变迁,则不仅是指基本制度框架的根本变革,而且包括一定基本制度框架内任何“正式约束”(立法)和“非正式约束”(道德规范等等)的边际调整(注:诺斯.制度、 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确实, 这类边际调整不一定都是技术变化要求重大的组织变革的结果。它们可能与技术的变化有关,也可能由其他因素引起。但这种一定制度框架内的边际调整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理论的理由。因为马克思理论所要解释的并不是这种边际调整,而是基本制度框架的变革。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也找不到他试图将一定制度内的任何些微变化都归结为生产力变化的企图。相反,他在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的同时,注意到了“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的存在。例如,他在谈到古代奴隶制社会就存在过的雇佣劳动制度时指出,这只是“一种例外和救急的办法”,即所谓“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它并不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要求对奴隶制进行根本的变革。正是因为缺少生产力基础的支持,雇佣劳动制虽然古已有之,无论是在奴隶制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它都没有成为整个社会制度中稳定地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关系形式。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以手工工场的出现、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组织的形成这一系列的劳动技术组织的巨大变革,雇佣劳动制度才以资本主义的全新形式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4.)。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抓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个根本,才能摆脱历史上存在的大量次要和偶然因素的纠缠,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理出一条前后一贯的清晰线索。
二、诺斯的多元动力论与人口动力论
尽管诺斯对马克思的生产力一元动力论的批评似乎很难站住脚,但提出一套取代马克思理论的新理论仍然是他的权力。那么,他是如何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的呢?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注: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111.)。与制度变迁相对的是制度的稳定,这种稳定是一种均衡状态,“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注: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112—113.)。所以, 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再缔约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又是哪些因素使得再缔约给行为者带来收益,从而打破制度均衡,引致制度变迁呢?诺斯告诉我们,这些因素是“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其中,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等;偏好的变化则来自于观念、宗教教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以及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在诺斯看来,大多数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内生的,是各种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主体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另外一些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则是外生的,即来自于制度框架之外。既然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有许多来源,那么,很显然,诺斯的制度变迁动力是多元的。多元动力论无疑为诺斯提供了比马克思大得多的解释历史的“自由度”或者说随意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诺斯对制度变迁的解释中完全找不到一条连贯的线索。事实上,诺斯认为,在经济史上引致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都是外生的。所以,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外生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在这些外生因素中,最重要的又是人口增长。他将两次“经济革命”即专一公有产权的形成和18世纪产业革命的起因,都归结为人口变化,而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要批评马克思“轻视人口变动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的原因。不过,这样一来,诺斯又一次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的无知。其实,马克思是重视人口问题的。早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山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将“生命的生产”纳入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体的生产方式之中:“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0.)。后来,马克思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评中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人口理论:在历史上他(指马尔萨斯)会发现,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增加的,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但是,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历史规律,这些规律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的历史过程制约的。马克思认为,人口增长实质上是作为社会生产力基本因素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人口增长本身就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展开的。作为社会再生产有机组成部分的人口增长,因而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制约。从生产力方面来说,人口增长不能不受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物质条件的制约。因此,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人类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的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存在杀婴制度,在中世纪采取移民制度,等等。至于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社会人口状态,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与资本积累相伴而行的相对人口过剩。因此,马克思断言,人类社会的“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身的人口规律”。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口增长模式对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内生性,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人口状况的最终的决定力量。这也就是马克思不像诺斯那样将人口看作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并且不把它当作制度结构变革动力的原因。
其实,在人类思想史上,诺斯的人口动力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远的不说,18世纪的启蒙学者爱尔维修就从人的生理需要出发,将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口增殖,认为人口增长的压力是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的动力。在19世纪,这个观点为俄国民粹派引用时,已经被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学者驳得体无完肤(注:参看: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30 —499;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M].北京:三联书店,1961 ,12—20.)。我们无从知道诺斯的理论灵感是否来自爱尔维修。 如果不是,他不过是进行了一次对陈旧而错误的理论的再发现。
三、人口变化与“两次经济革命”
历史的事实是任何社会发展理论的真理性的最权威的鉴定人。现在,到了请它们出场的时候了。下面,就让我们将诺斯对“两次经济革命”的解释与有关史实做一对照。
(一)关于人口变化与专一公有权的形成
按照诺斯的说明,原始社会的专一公有权是这样形成的:在人口增长的一定范围内,狩猎部落的边际产量不变;但随着人口的增加,狩猎的边际产量递减,这时原始人群就会建立狩猎领域的专一公有权,以排斥其他人群,而这种排他性的公有权有利于技术创新;而当狩猎的边际产量低于农业的边际产量时,效用最大化的人就会选择农业;在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条件下,农业的边际产量也会递减,于是人们又发明了公社的专一所有权,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诺斯的解释要想成立,首先必须假设,自有人类以来,人口就是显著地不断增长的。但是,从卡洛·齐拉波的考古统计可知,在人类出现后的一二百万年间,人口增长率仅为0.0007%~0.0015%,人口规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在这一二百年间人口没有像诺斯假设的那样显著地不断增长呢?齐拉波指出,在低下的技术水平条件下,靠狩猎维生的原始人群的规模是由他们所能够捕获到的动物的数量所决定的,原始人会采取措施将人口控制在物质生产条件限定的范围内(注:卡洛· M·奇拉波.世界人口经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R.W.菲思对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迪科比亚人的考察也说明,原始人群的规模之所以长期处于稳定状态,是因为技术水平低下,生活资料匮乏。在这种情况下,部落为了维持生存,一方面实行杀婴制度,另一方面用独木舟将外来者送到海上淹死(注: R.W.Firth.Primitive
PolynesianEconomy [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39.)。J.古德尔则通过考证发现,主要以采集维生的早期前人群的规模十分稳定,一般不超过20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后期前人由于从森林向草原迁移,尤其是发明了捕杀动物的工具,组织起集体的狩猎活动,群体的规模增加到40人(注:参见:J.Goodall.Chimpanzees ofthe Gombe [M].Stream Reserve,1963,445—500.)。 这些史实表明,人口规模是技术进步或生产力发展的增函数。这与诺斯的描述正好相反:并不是人口压力通过专一所有权的确立而引致技术进步,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社会的人口行为改变,从而推动人口增长。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根据考古资料,对人口与技术的关系做过一个很好的总结:原始社会时期,技术创新一般先于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促进技术的推广,即先是发明拉力(
inventionpull)起作用,然后是人口推力(population push)起作用(注: 朱利安·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8章.)。奴隶制时期人们对待外族人的那种与前述迪科比亚原始社会相反的行为方式,也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证据:正是因为技术进步使得个人劳动不仅能够维持劳动者的生存,而且还能提供经济上的剩余,才发生了由杀死外族人到收养外族人以至发动对外战争以获取劳动力的人口制度的根本变化。如果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词汇,这可以说是技术进步导致了“劳动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诺斯告诉我们的却是一个与历史进程背道而驰的故事。
诺斯对“第一次经济革命”的解释所碰到的第二个麻烦是:专一所有权的形成是否就是技术进步的充分条件?在《非洲通史》上古卷中,考古学家提供的史实说明,大量发明了专一所有权的部落,从古至今却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创新。生物学家甚至在动物界也发现了诺斯所说的专一所有权,即大型食肉动物都有决不允许其他动物进入的活动范围,但狮子、老虎搞技术发明的故事似乎在童话中也找不见。就是被新制度主义者当做专一所有权引起技术创新的最有力证据的发明专利权,也早在14世纪就被威尼斯人发明出来了,但是白白等了二三百年,直到16世纪,才发挥出引致技术进步的明显功效。而且,据西方学者的考证,地中海国家发明专利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外国人泄漏本国的技术秘密,而并不是要保护知识产权(注:Paul,A.David.The Evolution of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ion[A].Abel Agbegran.Economicsin a Changing World[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这些事实显然是诺斯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而根据我们在前面叙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虽然专一所有权等制度发明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否发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取决于人类在发展生产力的长期实践中所获得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存量。
最后要指出的是,诺斯所谓狩猎的边际产量低于农业使得原始人群变成农民的说法,也是大可商榷的。有学者指出,在西方的史前时期,农业与狩猎在某些平原地区是互不相关的两个行业,农业直接由采集业发展而来,这说明在这些地区狩猎与农业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注: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我国的考古学家则指出,在我国的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当狩猎业为农业所替代时,前者的生产力正因为石器和弓箭的发明而提高(注: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并不存在断定前者边际产量低于后者的理由。事实上,世界不同地区的原始先民们以何种方式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是由他们所面对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而在诺斯的“第一次经济革命”模型中,却先验地为先民们提供了一份包括狩猎和农业在内的技术选择菜单,以便将他们实际经历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的历史过程”,硬塞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
(二)关于黑死病与产业革命发生的条件
诺斯是这样解释“第二次经济革命”即产业革命的:14世纪上半叶人口的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和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上升,从而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的黑死病(淋巴鼠疫),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涨,从而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力所有权得以确立;专一所有权、土地转让权加上自由劳动力所有权,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从而导致了产业革命。在诺斯的这个解释中,专一所有权、土地转让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这三个制度上的创新是产业革命发生的条件,而这三个条件形成的根本原因又是人口的增减。针对诺斯的看法,需要澄清两件关键的史实:一是14世纪上半叶人口增长、边疆拓殖、可转让的私人土地专有权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二是黑死病造成的人口减少是否导致了诺斯所说的经济后果。
先让我们澄清第一件史实。中世纪并非一个死气沉沉的黑暗时代。封建制度的形成,教会统治地位的确立,使动荡的社会稳定下来,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则为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失传的农业技术得到恢复,并获得巨大的发展。这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是,拓殖运动的起因却并不是人口的增加。蛮族国家与教会的政治斗争是拓殖运动的主要原因。在拓殖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教会寺院组织的对森林和沼泽及其他未耕地的垦殖,其目的在于拓宽教区以增强教会势力。其实,早在12世纪初甚至更早,就发生了拓殖运动,并持续到14世纪(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1—64.)。但由于生产力低下和技术手段落后, 初期的拓殖活动推进缓慢,有的甚至以失败告终。而14世纪上半叶拓殖的成功推进,主要是因为农业技术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记载,在当时的许多拓殖活动中,不少主教都是新技术的发明者和传播者。
14世纪前的拓殖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技术落后;而14世纪拓殖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现了用8 头牛或马拉拽的带轮铁制重犁代替传统扒犁的技术创新,而这个创新又是以冶铁技术在中世纪的进步为基础的。根据历史学家林恩·怀特的研究,这一耕作工具的创新大大提高了耕作的效率:“这种犁的第一个大优点是它能翻腾稠黏的土壤。这种土壤比通常用扒犁来翻耕的砂土能生产更多的作物。第二,人的劳动力节省了,这是由于重犁上的犁壁能翻出垄沟来,因此交错犁田就不必要了。第三,田间排水由于采用将田犁成长条的新模式而方便了:犁壁正常地把垄沟转向右方,这样渐渐地把松土堆向长条的中间,而在长条与长条之间留出了一条排水沟来。”这一技术创新引致了劳动方式的变化,即出现了共耕制。新犁要8头牛拉拽, 而单个农民一般没有这么多牛。解决的办法就是由几户农民联合起来共耕。同时,这个技术创新还引起了份地规划制度的改变,“敞田”即连成一片的条田,取代了由各家各户的篱笆分割开来的方块份地。这种技术创新在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的同时,有力地刺激了能够提供更为便捷和有力的大型牲畜即马的饲养。此外,三圃制的发明和推广,新的作物品种如小麦、大豆等的引种,种植和畜牧相结合及由此引起的动物肥料的广泛使用,也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怀特指出:“大约到公元1000年时,我们开始看到人口的稳定和迅速的增加,在西欧许多地区的城市主义和商业的兴起,如果没有粮食增长和农民生产力的提高则是难以理解的,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允许大部分人口脱离耕作从事其他事业。”(注:卡洛·M·齐拉波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09—135.)另一位历史学家P.布瓦松纳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种伟大的拓殖工作,不仅增加了财富,它也大大增加了人身资本。”(注: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41.)可见,技术进步是14世纪人口增长和拓殖成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诺斯却简单地将拓殖运动的动力归结为人口增加,武断地得出“人口的持续增长是推动中世纪盛世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因”(注: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49。)的结论,连人口为什么增加的问题都懒得提一提,似乎新增人口不需要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获得的新增的物质资料的供养,靠喝西北风就能长大,且操起古罗马帝国时代传下来的陈旧工具就能在环境恶劣的森林和沼泽地带开拓出新家园。
第二件史实,即黑死病使人口减少,引起劳动力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封建制度解体、自由劳动所有权确立,这似乎也是不牢靠的。詹姆斯·W·汤普逊是对此持保留态度的历史学家, 他说:“不论如何,把黑死病提高到惟一的‘持续不断的经济力量的尊严地位’是错误的。”(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38.)布罗代尔则是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他说:“农奴解放是否由于黑死病而加快,劳役折算是归因于黑死病还是别的影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 1992,556.)精于计量的诺斯应该提供确凿的数据来驳倒他们的保留和怀疑。但不幸的是,他自己承认:“要用数量来说明劳动价格相对于地租上升仍相当困难”(注: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96.)。事实上,他未能提供任何有关14 世纪下半叶西欧劳动力与土地相对价格的系统数据。不仅如此,将缴纳封建地租之后的农奴所得等同于自由劳动的价格,在理论上能否成立,也很有问题。因为,封建主同农奴的关系与劳动力买卖是历史上社会经济性质根本不同的关系,农奴所得与自由劳动力的价格也是社会经济性质不同的范畴,不能随意通约和折算。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假定诺斯成功地提供了自由劳动力价格相对于地租上升的历史数据。但是,问题又接踵而至:人口减少导致的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是否一定会导致诺斯所说的社会经济后果?法国史学家皮埃尔·维拉尔、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发现,12~18世纪欧洲各地的人口变化几乎是同步的,但在不同地方却导致不同的结果。14世纪整个欧洲出现人口锐减的趋势,并延续到15世纪。在这个过程中,西欧发生了地租降低和农民自由增加的现象,但加泰罗尼亚地区却出现了相反的运动,即地主对农民的控制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加强了。有趣的是,其原因正与西欧的反向运动相同: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上升。但是,东欧的地主们由此得出的结论与诺斯正好相反:劳动力相对价格越是上升,加强对农奴的人身控制所带给自己的收益就越大。布伦纳说:“西欧大多数地区,到16世纪农奴制已经消灭,另一方面,在东欧,特别是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和波兰,14世纪以来的人口锐减,却伴随着加强经济强制即农奴制运动的最后完成”(注:Robert Brenner. The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45.)。不知诺斯对此作何解释。
根据众多历史学家的论述,14世纪以来在西欧出现的封建束缚放松、代役租取代劳役、农奴自由增大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其原因也并不是黑死病引起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上升。汤普逊在《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但是黑死病并未导致这个运动;它只是加速了先前已有的运动。因为从13世纪以来(且不追溯以前),在欧洲进行的那个经济和社会革命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以货币关系取代了劳役关系。欧洲的自由佃农或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少量农奴的人的数量超过人们通常的估计。”(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37—538.)汤普逊在这里所说的“先前已有的运动”,是指在频仍的自然灾害冲击下,自12世纪初以来农奴不堪压迫而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反抗,即向教会管理的拓殖区以及城市的逃亡,或躲避到领主控制范围外的荒山野岭去开荒。在此前写作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他是这样来描绘这个运动的:“如果作进一步的研究,无疑地,我们将会更多地了解中世纪下列的经济社会情况——农奴制的增长和与此相反的农奴逃亡,人口的移动,村庄和田地的遗弃,有时全村的逃亡,新地区的殖民与居住,农业因必须宰杀耕牛而衰败的情况,像掠夺、游荡和飘泊这一类的道德堕落,狼从森林里出来吃死尸的祸害。”(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406.)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招徕劳动力,教会管理的垦区内取消了某些封建义务并改行代役租制度,这对贵族封建领地内的农奴很有吸引力。后来,这为某些领主所仿效,以与其他领主争夺劳动力。于是,租佃关系逐渐取代劳役关系,与劳役租时代相比,农民有了更大的自由。
但是,应当强调的是,这还远远谈不上农奴已经取得了诺斯所说的那种近代意义上的小自耕农的土地私人专有权和自由的劳动力的所有权。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在比较租佃农民与劳役制下的农奴的身份差别之后指出:“我们也不要把这样的对比做得太过分了……这些农民的身份仍然是受限制的……事实上,‘客籍民’不过是以租金为代价取得了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而且有关农民土地持有的问题仍服从于领主的裁判。实在可以说……小农耕作制度是与大领地并存的。大领地制是整个结构的法律基础,它虽然不再决定着人的关系,却仍然决定着土地关系。无疑地,最后,农民对于份地的占有很为牢固,已经有些像所有权了……虽则如此,直到1789年法国革命为止,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直不曾摆脱束缚的桎梏。”(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8—69.)可见,代役租的社会经济意义,是在保留封建制度基础的前提下,使人身依附转变为土地依附。这是在封建制度基本框架内发生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调整。这种调整虽然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私人所有权和自由劳动力所有权的确立,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事实上,近代意义上的农民小土地私有制以及土地转让权,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伦三岛,都是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过程中,亦即瓦解皮朗所说的封建结构法律基础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可转让的私人土地产权,是诺斯强加给生活在公元500~1500 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农奴的一种现代观念。事实上,前面提到的重犁技术和敞田制度的采用所导致的共耕的合作关系,不是强化而是弱化了农民的私有产权观念。新的犁地方式要求一个村庄的全部耕地分成两大块敞地,一块秋季种植,一块休耕一年以便恢复地力;每块敞地搭上篱笆或围上栅栏以防动物进入,但每一块敞地内私人所有的长条土地之间不再设阻隔的东西。正如怀特指出的:“这就意味着全部耕作均得在全村会议严格控制下进行”,“这样做必将破坏原有全部田间界标和私人产权”。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北欧的重犁耕作减少了个人主义,而在农民之中建立起对于他们自己事务的坚强的自治制度。”(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3—114.)
在这里,对自由劳动力所有权的形成,我们还要多说几句话。作为产业革命条件的自由劳动力所有权形成的真实过程,与诺斯的描述相去甚远。在英国这个产业革命的故乡,自由劳动力所有权的形成,主要是与被托马斯·莫尔称为“羊吃人”的过程即15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圈地运动中农民离开土地而沦为自由劳动者,完全是被迫的,是他们无力反抗封建贵族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结果,与由于劳动力相对价格上升导致的劳动者谈判力量上升风马牛不相及。劳动力自由所有权的获得,是以丧失中世纪形成的份地和村社公有土地世袭使用权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代价的。然而,圈地运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诺斯关于英国产业革命的论述中只是一带而过,而且与自由劳动者的形成无关(注: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87.)。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推动圈地运动从而造成自由劳动者的最终动力,还是那个诺斯认为被马克思过分强调的生产力的发展。圈地的直接动机是通过羊毛交易发财,而这种发财机会至少从两个方面来说,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的:一是航海技术的进步,二是意大利某些沿海城市中建立在手工工场基础上的纺织技术的发展。没有航海技术的进步,就没有海外贸易的扩张;而没有纺织技术的进步,就不会有对羊毛的巨大市场需求。按照W.W.罗斯托对工业革命发生条件的看法,“科学、发明和革新”,“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正是早期现代欧洲同以前的经济发展相区别、同18世纪的中国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的共同经历相区别的核心因素。……正因为很难理清这三者的关系,并把它们与经济进程联系起来,才使得经济学家那么看重商业革命,或者像诺斯和托马斯那样,那么看重私有产权的出现。要研究科学、发明和革新,追求最大利润的简单论点就不够用了”。罗斯托认为,“毫不夸张地说,重大的发明和革新在正规的理论中根本就没有地位”(注: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83.)。这是对包括诺斯的“新经济史”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肯批评。
在结束本文时,让我们引用意大利著名史学家齐拉波在为多卷本的巨著《欧洲经济史》所做导言中所说的一段话:“我认为把经济史分为‘新的’和‘旧的’以及‘质的’和‘量的’意义并不大。……基本的区分应当是好的经济史和坏的经济史,而这种区分并不依据用的是哪种符号,也不在于插入表格的多寡。而依据提出的问题是否中肯恰当,为解答问题搜集的材料如何,分析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是否准确,分析的方法必须适合提出的问题和获得的材料。”(注:卡洛·M·齐拉波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就制度变迁或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而言,究竟是“新经济史家”诺斯,还是他自称已被自己超越了的马克思,提供了对经济史的好或者坏的解释,恐怕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收稿日期]2000—03—22
标签:制度理论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