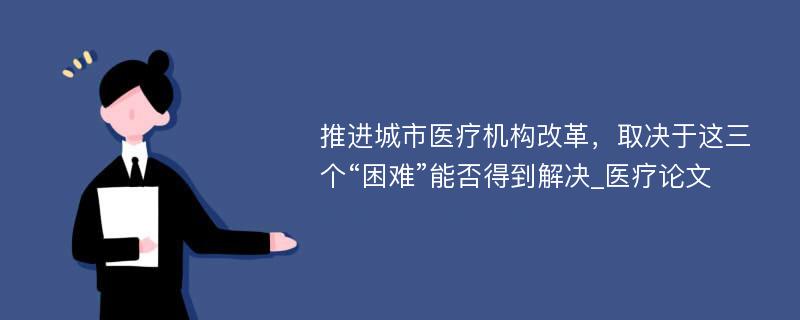
推进城镇医疗机构改革取决于:能否破解三“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论文,机构改革论文,医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务院关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出台,把城镇大大小小的医院一下子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据称,因失去药品收入补偿的大头,连以往对医院各种收费标准卡得最严、查得最紧的物价部门,都对医院的处境“同情”起来,缓和了过去的“强硬”。有一个省的物价部门的负责人就这样对该省的卫生厅长说:“卫生这回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你们提价吧,看要提多少。”
医疗界人士有紧迫感,却似乎并不悲观。“医院保险制度改革,的确给了医疗界很大的压力,很严峻的挑战,但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遇。医疗机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积存的很多问题,有了这个机遇,可以进行彻底的改革了。而且,改革是唯一出路,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辽宁省卫生厅厅长马晓伟的这段话,很具代表性地透露了医疗界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那种亦忧亦喜,从某种意义上“喜”多于“忧”的心情。
青岛市卫生局局长刘志远用了三句话概括他对新难题的态度:一是没法回避;二是必须面对;三是主动适应。
但是,“话”虽容易说,“路”却并不好走。
难点一:如何“以医养医”?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过程中,医院要同步进行补偿机制的改革。核心内容是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降低药品收入占医疗总收入比重,合理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也就是说,国家多年来对医院实行的“以药补医”政策“作废”了。
尽管多少年来,很多医务人员对以药补医十分不满,记者在多年对医疗部门的采访中,经常能听到这样激动的“质疑”:“我们究竟是医生还是卖药的?”可现在真不让他们“卖药”了,却又忽然发现,自己的利益受了“损失”。对大多数医院来说,药品收入一般占医疗总收入的比例至少在60%左右,这不是一个小数。
国家政策虽承诺要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也就是说,提高以往偏低的挂号费、诊疗费、检验费、护理费、手术费等收费标准,以期“医改”后的医院能真正做到“以医养医”。但是,第一,技术到底值多少钱呢?第二,值多少钱就能定多少价吗?第三,定多高的价算“合理”呢?
最重要的是,新的“医保”制度实行后,患者可以在若干定点医院中选择就诊医院,客观上各医院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可以预见的是,今后除了服务态度、医疗技术水平的竞争外,价格也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内容,从这一点上讲,与商家的竞争有相似之处。
正因为如此,在界外人看来对医疗机构大有好处的“合理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在医疗界内却无异于一个“烫山芋”——把药品收入“拿”走后,医疗技术服务不提价,医院无处“补偿”,活不下去;提价,尤其是提到与“价值”基本相符的水平,“病源”有可能会流失。这不仅仅是个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而且是个因长期实行“以药补医”政策而形成的观念问题。人们花钱“买”药,认为天经地义,如果花钱“买”的只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诊断”,甚至会感到“这病根本没看”。
医院身处“尴尬”,使一些院长在上级部门征询提价意见时,不得不忍痛请求“别提”,以留住患者。
“以医养医”本该是像“靠山吃山”一样地顺理成章,但过去做不到,现在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补偿”问题,将在一段时间内既成为医院各项改革的一个契机,又成为院长们最大的压力和最大的心病。
难点二:富余人员“流”向哪里?
从医院自身来说,提高质量效益首先必须减少浪费。在不少城镇医院,最大的浪费就在于布局不合理,人浮于事。因此,配合新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出台,医疗界普遍认为,城镇医院改革应该在调整医疗机构布局上下大力气。一种共同的意见是,今后卫生行政部门应该加强对城镇医疗机构床位、医生、大型医疗设备的宏观规划和调控;适度控制床位总量;控制城镇医生总量;控制大型医疗设备的数量。
相信今后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不会、也不可能再盲目了。可难办的是现在。怎样才能把像一团乱麻似的医疗机构设置重叠、条块交叉、床位、人员及设备膨胀的状况通过改革、调整,重建一个合理、高效的医疗布局?
有关政策已明确,对重复建设、服务任务不足的医疗机构可以实行“关、停、并、转、迁”。然而,真正做起来,难度不小。首先,目前国内尚没有大家公认的、科学可行的编制资源配置标准的方法。怎样配置才是科学、合理的呢?这需要做非常艰苦的“基础性”研究。第二,这不是卫生部门一家能做的事情,没有有关各方面的理解、支持、配合,根本不可能做到。第三,机构的关、停、并、转、迁直接涉及到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尤其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还通过行政手段来完成这项本该由市场机制来完成的事情,人为的阻力不小。第四,在这个调整中富余出来的人,向何处去呢?
“微观”到医院,降低成本,减少浪费必须做的最大的一篇“文章”就是“减员”。北京市去年对15家医院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试点,清退临时工千余人,内部转岗分流500多人,一年下来,仅工资一项就节约了700多万元。可见,“减员”是医院“增效”的主要途径。
最近一、两年中,各地的城镇医院都在加大清退临时工的力度,以改变卫生部长张文康所说的那种“正式工看,临时工干”的状况。但是,清退临时工不难,转岗分流医生、护士以及行政后勤人员,稍不注意,就会引起震动。就连已经完成全市1万多医务人员全员聘用制的青岛市,也很难在分流人员上有太大的“动作”。这个市的卫生局长刘志远说:“当然,不能一个下岗的也没有,那样,改革就太没有意义了,但决不能太多,人们还没有那样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现在这么做,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今后建立一种机制。”不仅如此,就像“医保”改革需要医院的配套改革一样,医院的改革也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套。如像青岛市那样,建立健全卫生人才市场,使医院减员分流有“出口”。
但不管怎样,今年内,医疗机构减员增效将动“真格的”。转岗分流“流”向哪里呢?
对此,一些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也顾虑重重。除了担心减员中的各种矛盾外,还提出,如果那些被分流出去的医务人员申请个体开业,卫生行政部门批还是不批?不批,你“裁”了人家,还不让大家自谋出路?批,势必增加新的社会医疗机构,使医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因为根据政策,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体及社会办医的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
难点三:社区卫生服务举步维艰
从理论上说,因为目前我国的卫生资源从总量上仍处于不足状态,那么,不论是“关、停、并、转、迁”的宏观调整,还是各个医疗机构的转岗分流,“减员”下来的医务人员完全不愁“上岗”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正是基于卫生资源配置、布局不合理,但资源总量不够这一点,提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把闲置、浪费在医院的医疗资源转移、充实到社区、到农村去。并具体描绘了未来最理想的医疗模式,即: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区。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既大大方便了群众,节约了医疗费用,也使医院的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有了依托。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要按设想使医疗资源从“上游”流向“下游”,并不会很顺利。首先,就像曾有一位省卫生厅长提问的那样:“我们的社区在哪儿呢?”这的确是个问题。以北京为例,人户分离(即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分离),上班与住家分离,住的是单位的房,人归单位“管”,与居住地“地方”上几乎没关系。甚至选人大代表时当“选民”,也是当单位所在地的“选民”,过去的公费医疗关系也跟着单位走,预防、保健以至计划生育等等,也都是单位负责,就连离退休人员,单位也有专门机构负责。因此,人们只有单位的概念而没有社区的概念。很多人甚至从来就不曾与居委会打过交道。
没在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社区卫生服务能够吸引多少医疗服务需求不能不令人疑虑。
其次,在一些经济发达城市,的确已经有一部分收入较高的家庭和个人有了请“家庭医生”的需求,但他们对“家庭医生”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上海市卫生局周局长说,“比如上海有的教授想请“家庭医生”,你这个家庭医生总要与他那个层次对得上号。”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供方”与“需方”至少要是差不多一个“层次”的人,否则在心理上不好接受。可现在能够“流”向社区去担当“家庭医生”角色的医务人员所具有的素质,与“需方”的要求可以说差得太远。因此,社区卫生服务前景如何,需要理顺的关系,需要做的工作还太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