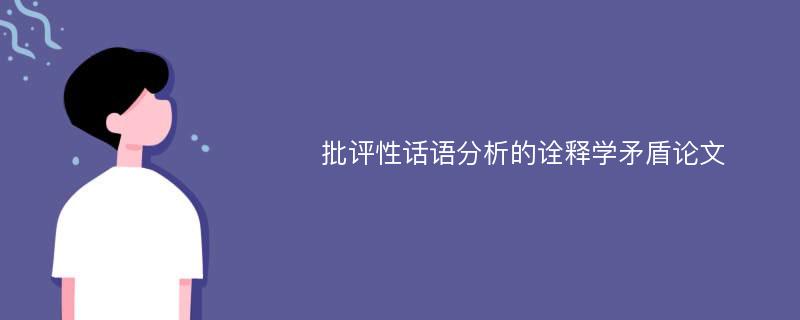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诠释学矛盾
熊 伟, 舒 艾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摘 要] 批评性话语分析在诞生及发展过程中广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其分析/阐释结果的客观有效性,语言学家威多森、斯塔布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代表费尔克劳夫等人曾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系列辩论。从西方诠释学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费尔克劳夫与威多森等人的争论是诠释学内部的分歧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的投影,对应着三重矛盾:科学实证方法与人文阐释方法的矛盾、客观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的矛盾、“批评性”阐释与过度阐释的矛盾。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思想,这些矛盾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互补性和张力的共同作用下,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得以持续发展。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诠释学;过度阐释;语料库方法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已被广泛用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学、传播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然而,自面世起,CDA 就面临了诸多批评与质疑。著名语言学家亨利·威多森(Henvy Widdowson)在多篇文章或专著中对CDA 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批评,还与CDA 的主要代表人费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gh)展开了系列辩论[1-3]。其中的一个核心论题是:CDA 的分析结果是否具有客观有效性?威多森指出,CDA 是在对语言现象与社会情境进行循环论证,其分析的本质是一种阐释,而CDA 的阐释带有一定主观性,使人对分析结果的客观有效性产生怀疑。费尔克劳夫对这一问题的答复较为含糊,既未说明实现不同分析结果的方法,又未确切证实CDA 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对于CDA 这样一项带有“工具语言学”性质的分析理论而言,最终结果的客观有效性几乎是其生存发展之根本。本文将剥茧抽丝、追本溯源,从诠释学① 对于“诠释学”这一概念,也有学者称作“阐释学”或“解释学”,但学界普遍采用“诠释学”指代这一学科,而“阐释”则指代具体的解释行为,参见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年版)第1 页对“阐释”和“诠释”的辨析说明,本文亦采纳这一观点。 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本质进行剖析和探讨,并结合当前CDA 的发展趋势提出一定建议。
一、问题的缘起
作为CDA 理论长期的批评者,威多森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CDA 的不足[2-10],其主要批评意见可基本归纳为以下四点:(1)CDA 对于分析(analysis)与阐释(interpretation)的概念含混不清;(2)分析者在分析/阐释时融入了个人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3)受上一点的影响,分析者的语言证据具有个人倾向性;(4)忽视了CDA 分析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理解的差异以及不同阐释结果的可能性。这四点质疑可谓相互关联、层层递进。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在于,CDA 的结果到底是一种客观分析还是一种主观阐释呢?
在小学教学中应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时,一定要科学合理地选择,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画面的美感,把课堂教学转变为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展示场所,在小学教学中应用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关键是优化整个教学过程,贯彻落实好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充分尊重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小学教师一定要科学合理地引导学生选择适用的教学资源,进而构建充分体现出自身特色的知识体系,并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中的重难点知识,从而极大地发挥出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实际价值,真正提升小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威多森提出,CDA 的名称采用的是“分析”一词,但“分析”与“阐释”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分析者往往揭示的是导致不同分析结果的原因,且每种原因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是合理的”[2]。分析伊始,分析者当然可以对结果做出一定设想,文本分析后,对于不同分析结果也可以有所偏好,但“阐释者则在一开始就优先考虑他们自己的理解倾向了”。因此,在威多森看来,CDA 更像是一种阐释行为而非分析行为。
而“阐释”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它不仅与作者书写文本时的意图有关,还与读者的阅读理解相关,读者个人的理解可能与作者的实际意图相去甚远。CDA 分析者们对作者意图的揣测“自然而然、无法避免”地建立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their conception of the world)、社会现实以及个人所处的现实(social and individual reality)、价值判断(value)、信仰及偏见(beliefs and prejudice)之上[2]。而在CDA 的支持者看来,语言并非是自然纯净的,话语是社会权力斗争的空间。这样一来,CDA 在进行文本分析时,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分析者已经预设待分析的话语具有意识形态”,一旦如此,“分析者便会不自觉地寻找可以论证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证据,而忽视其他语言现象”[2],最终的结论不免有片面、无效、不客观之嫌。
2.3 患者生存分析 患者生存146~908 d,平均中位生存时间(496±233)d。放化疗后1、2、3年生存率为73.1%、21.9%、13.1%。生存曲线见图1。Cox模型分析(表3)显示:T分期和淋巴转移数目是患者生存的影响因素(P值分别为0.048和0.019);跳跃性转移淋巴结数目越多,患者预后越差。
对于CDA 分析/阐释结果的有效性问题,不仅威多森提出质疑,另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迈克尔·斯塔布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意见。斯塔布的意见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11 个问题中[11],而前两个问题针对的就是CDA 分析/阐释的有效性:(1)采用何种标准评估CDA 文本分析的结果(By what criteria can CDA’s textual analyses be evaluated)?(2)CDA 阐释的权威性从何而来(What source of interpretative authority does CDA claim)?对于以上质疑,费尔克劳夫回应称:CDA 的阐释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阐释-1(interpretation-1)和阐释-2(interpretation-2)。前者与一般语言分析无异,即确定口头/书面文本的意义或特征;后者则结合社会情境对文本分析的结果进行解释,比如,揭示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是如何塑造阐释-1 中的话语现象的。而威多森将前后两部分的“阐释”内容混为一谈了[1]。根据这一答复,阐释-1 似乎被视为阐释-2的一部分,即语言分析是社会情境阐释的基础和依据。此外,费尔克劳夫虽然称多样性的阐释本就是CDA 的重要前提,但他并未提供实现多样性的操作模式,也没有给出CDA 结果的评估标准。对于CDA预设意识形态的问题,费尔克劳夫的回应是:任何自然或社会科学研究都有可能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即便是所谓最“纯净”的科学也无法避免,科学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绝对对立的[1]。综上,双方的讨论基本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即,CDA 所谓的文本分析/阐释之有效性或权威性究竟从何而来?费尔克劳夫并没有给出十分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二、CDA 阐释的三重矛盾
CDA 自身是一个杂糅了多门学科和多重思想的理论,因此,其内部的碰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根据费尔克劳夫的划分,CDA 的分析过程既有实证的文本分析,又有与社会情境相结合的阐释,而这两部分的源头指向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其次,从费尔克劳夫的答复来看,无论阐释-1 是独立于阐释-2 的一部分,还是作为铺垫为阐释-2 服务,他真正期望的是找到一种合理的阐释路径,通过文本分析和情境阐释来理解作者的意图,因此费尔克劳夫的努力更接近一种方法论。而威多森和斯塔布在质疑这种研究方法时,关注的是其阐释行为的合理性,他们思考的是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因此二者辩论的重心并不相同。最后,CDA 的“批评”指向隐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深挖式的分析阐释又如何与过度的阐释相区分呢?这重重的矛盾都指向了阐释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从阐释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阐释学的学科发展史、研究路径及相关论题,以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客观阐释学与哲学阐释学、批评性阐释与过度阐释等三对矛盾来梳理辩论双方的阐释学本质。
(一) 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方法的矛盾
西方哲学历经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一直发展到近当代哲学,逐渐分化为两派研究传统,一派是自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伊始的人文思辨型,另一派则为自科学时代弗朗西斯·培根以降的科学实证型。人文思辨的研究传统历史悠久,在科学时代降临以前具有牢不可破的权威地位。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经院哲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文艺复兴主题之一“对世界的发现”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开始兴起。培根吹响了科学实验研究的号角,在牛顿力学的凯旋声中,科学主义研究思想被推向了高潮。19世纪30 年代,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了著名的“精神发展三阶段”规律,认为人类精神发展经过“神学”及“形而上学”阶段,即将进入“实证”的科学研究阶段。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对形而上学产生怀疑,开始注重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探求变化的现象和事实的本原,如通过实验、观察、数据计算等方法,从大量的客观事实中找到一般性规律,使研究结果尽可能精确、量化和肯定。实证的方法排斥抽象空洞的思辨,认为一切可靠知识只能来源于事实经验,理论和假设的可靠性必须由事实来验证。
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兴起发展的过程,也是其与人文主义分裂对立的过程。“人文主义”认为人才是万物的尺度,重点关注人的价值、意义以及对生命的感受和理解,同时还强调客体的差异和多样性,这些是无法用数字来度量、用数据来表现的,只有通过描述性、阐释性的语言才能实现。因此,人文阐释的方法明确地站在了科学实证的对立面。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科学思潮携手并进,成为推翻宗教神学的主要力量,对于“人”和“世界”的发现代替了对上帝的盲目推崇和信仰。但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一些人文主义者仍对某些狂妄的科学主义感到不安。18 世纪中叶,卢梭抨击科学为罪恶的渊薮,将引发社会风尚败坏、道德沦丧,“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12]27。尼采则将科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我们无法生活在纯洁透明的空气中,也同样无法生活在远离日常生活的纯粹科学中,科学必须回到浑浊泥泞的地面,它必然在尘世游泳涉水,从而玷污自己的双脚”[13]。阿诺德在“文学与科学”的演讲中回击了赫胥黎对文学发展的悲观预言,他极力反对将自然科学置于教育的主导位置,认为人类在探索自然界的同时也要注重“人性的构造”。20 世纪50 年代,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指出,科学和人文割裂的现象愈演愈烈,这种两军对垒、各自为营的状态必然会妨碍社会及个人的发展进步[14]17。
在西方诠释学中存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两派对于阐释有效性之路径的争论一直延续到20 世纪。贝蒂(Emilio Betti)与赫施(Eric Donald Hirsch)作为认识论、方法论诠释学的重要继承人和捍卫者,均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提出了质疑。在贝蒂看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危及了阐释本身的客观性,使客观的阐释成为一种可疑的东西[18]47。作为一名法律史学家,贝蒂的旨趣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甚至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埃贝林(Gerhard Ebeling)等人都有所不同,他关注的是一种“客观的”、“可用于阐释人类行为和对象”的基础性原则。因此,在贝蒂看来,伽达默尔似乎在向无标准的主观性靠近,并且也没有提供区分正确与错误阐释的规范性方法。而赫施则在《阐释的有效性》一书里呼吁作者意图必须成为衡量任何阐释的有效性的标准[18]76。他提出文本含义(meaning)和文本意义(significance)的概念,认为文本含义归属实际文本,而文本意义指向文本含义与某个人、某种概念、某一情境或者某种可能性之间的联系。他坚定地主张文本含义保持不变,变化的只是作者或读者与文本含义的关系。他甚至还引进了“批评”(criticism)的概念,认为“批评”力图把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关联起来,揭示的是文本的含义。“批评”还对文本含义和其所在的历史语境的关系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如考察某一文本如何受到其所在的历史语境的影响,以及它又是如何影响当时的历史语境的[19]144。
很多护生在进入妇科实习之后,特别是男护生,在面对操作时能够见到妇科病人的隐私部位而出现紧张、恐惧、害羞,从而回避妇科护理操作,之后甚至更加会逃避一些护理教学。这类的护生并不能很快的进行自我角色转换,这种沉重的心理压力使其对于妇科实习失去兴趣,并且怀疑自我价值。
由此可见,原本相对立的科学实证方法与人文阐释方法在CDA 的阐释过程中实现了融合,CDA 的血液里就带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基因。从某种程度来说,阐释-1 的实证色彩为CDA的结论带入了客观有效性,在索绪尔言语-语言理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福柯话语-权力-知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观照下[15-17],阐释-1 又为阐释-2 指明了发展方向,阐释-2 并非研究者自由、任意、不受限制的自我发挥。然而,回顾CDA 的分析阐释过程,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若阐释-1 在收集分析文本语言证据时,就已经带有一定倾向呢?若分析者在起点就已经预知了目的地呢?他们只不过是规划出一条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路线罢了。那么阐释者的最终结论还是客观有效的吗?
CDA 的阐释方式似乎也经受了这样一种调和思想的洗礼。阐释-1 的重点为文本分析,通过对文本中的词汇、语法形式、图像符号和篇章结构等进行调查,总结出一般性的语言规律,而阐释-2 则将这些语言证据放置于社会情境中进行解释。由此看来,阐释-1 向实证主义倾斜,侧重于实证语料的收集、客观语言现象的整理与分析。并且,近年来,随着相关数据统计手段的发展进步,这一趋向愈发明显:语料库语言学与CDA 的结合日益紧密,各类调查统计工具的应用愈发频繁,丰富的语料被广泛用来证明研究的客观性。与之相反,阐释-2 则回归了人文社会思辨的传统,通过将宏观社会历史事实与微观语言证据相结合,以阐释的方法揭示不公正权力关系或意识形态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渗入人们日常交往与对话的。
CDA 当然可以声称揭示的是某种隐性的意识形态,但正如费尔克劳夫所说,CDA 的研究者要保持反思,其阐释结果也应受到一定标准的制约。对于那些违反了简洁、经济性的阐释、与可靠的事实或假说相违背的阐释结果,我们应当保持警惕。CDA 还应受到诠释学循环中整体连贯性的检验,而对于一些无法证实但也难以证伪、甚至有较强说服力的阐释,则可以保持乐观的态度。此外,由于CDA 似乎更适合被归类于读者意图,其研究者不应否认其他阐释结果的存在。对于某一文本,CDA 分析者与未接受过CDA训练的普通读者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经历、价值观、文化教养的普通读者之间亦可能产生不同结果。因此,认为CDA 揭示了某种不公正意识形态或政治权力存在的可能性似乎更为恰当。
(二)客观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的矛盾
西方诠释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对古代典籍的解释分析。在14—17 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们开始重读古代经典。历经岁月淘漉的文学和宗教文本,都已蒙上时间的灰尘,人们不得不诉诸系统的阐释方法对这些晦涩的文字予以解读,这时候诠释学主要朝着语文诠释学和圣经诠释学的方向发展。到了近代,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努力将诠释学建设成为一般科学,认识论成为诠释学发展的第一要务。受自然科学时代的影响,寻找一种客观有效的解释方法、如何真正“回到作者那里”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综上,CDA 中的“批评”一词表明,CDA 孜孜不倦探究的是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信话语中弥漫着隐性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文本可以将这种自然习惯化的隐性意识形态呈现出来,最终消除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然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CDA 瞄准的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意识形态,自然需要从意识形态丰富的文本中找寻答案,比如,在实际研究中,CDA 研究者们多关注新闻媒体、政治类文本,而非散文、诗歌等文学文本。既然如此,又何以断定分析的对象是隐性的、习焉不察的呢?反过来,若要对已经“日常习惯化”文本进行分析,以期揭示隐性的意识形态,又何以断定那不是一种过度解读呢?
看吧,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平心静气处理的结果,也许还会出人意料。所以,“日理万机”的老师们,与其臣服于消极情绪,被情绪奴役,不如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许会有意外收获。
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分歧就集中在阐释的认识性和存在性上。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阐释的目的是到达作者那里,揭示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而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已经间接表明,还原作者的意图、复原历史文本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在阐释者与作者或历史文本之间有难以逾越的时间鸿沟。因此,在伽达默尔那里,文本被“存在”起来了,阐释的结果指向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相融合的那一部分。在这两条路径中,一条的终点指向作者或文本的自在意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确立出认识方法;另一条经由现象学、路过和远离认识论的诠释学,走向“存在”的哲学,由此,阐释不再被看成对阐释客体的认识方法,而是对阐释活动、阐释者以及阐释对象作为“存在”现象的探讨。
科学实证的崛起对诠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西方诠释学最后又逐渐发展为西方整个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现代诠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虽致力于构建一种作为理解艺术的阐释的科学,但囿于其心理学的阐释、作者个体性、理解的神秘性等思想,施氏的诠释学演变为一种矛盾、辩证性的诠释学,最终未能实现一般化与科学化。施氏逝世后,发展一般诠释学的重任落到了狄尔泰肩上。19 世纪末,狄尔泰试图在诠释学中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找到科学基础,即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为阐释人类内在生命的学科构建科学基础,找到一种客观有效的阐释方法。受到大历史学派兰克(Leopolde von Ranke)、孔德等人的实证史料研究的影响,狄尔泰努力在科学实证主义和精神阐释方法之间实现一种调和,即将这种17 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生命冲动、生活经验阐释方式构建成一种客观有效的科学。英法经验实在论、实证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生命哲学在狄尔泰这里实现了融合,实证科学和人文阐释这两种伟大而又彼此冲突的研究方式产生了交汇。
西方诠释学派内部的两种派别的确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哲学基础上,且所关注的是诠释学的不同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两派的的确确存在一定分歧,诠释学的研究者们最终必须要在两种立场上做出选择。在CDA 阐释有效性的问题上,从诠释学内部的两派在客观有效性方面的不同立场来看,费尔克劳夫踏上的是狄尔泰认识论、方法论诠释学之路,以他为代表的CDA 研究者们始终致力于寻找一种可以有效揭示不公平、不公正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客观方法。无论是引鉴自然科学的语料实证研究,还是回归人文学科的思辨阐释传统,CDA 的阐释立足于一般客观化的诠释学研究方法。他们坚信,通过分析话语可以追溯思想意识(作者个体或特定群体、阶级的意图)。
而以威多森为代表的学者则从哲学诠释学的观点出发,拷问的则是CDA 研究者的“前理解”、“前判断”(prejudgment),疑虑分析者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偏见”,质疑CDA 阐释结论是否也只是一种“效果历史”。贝蒂与伽达默尔的对立基于他们不同的诠释学立场,而费尔克劳夫与威多森关于CDA 阐释有效性的辩论之本质则是两种不同立场的具体化。与贝蒂略有不同,赫施走在了中间地带,既肯定客观文本意图的存在,又承认了读者解释之主观化,还以“批评”(criticism)的概念鼓励阐释者充分挖掘文本、历史情境对当下情境的建构或关联。从这一点来看,赫施关于“批评”(criticism)的观点为CDA 的阐释提供了一定诠释学基础,但又与CDA 的批评(critical)有所不同。下文将进一步对这一点予以分析。总之,透过西方诠释学内部对立统一的“客观”、“哲学”两派的视角,可以发现费尔克劳夫与威多森的争论即源自于不同的出发点,前者寻求到达客观意义的路径,后者关注阐释分析的本质。二者立场不同,对于阐释客观性所秉持的观点不同,关注的焦点也不同,因此,很难判定孰对孰错。
确定了K2CO3作为碱试剂后,进一步考察了溶剂对该催化反应的影响.当反应条件为:1(1.0 mmol),2(1.2 mmol),Pd(OAc)2(摩尔分数5%),Cu(OAc)2(摩尔分数10%),K2CO3(2.0 mmol),溶剂(3 mL),110~150 ℃,反应6 h,结果见表3.
(三) 批评性(critical)阐释与过度阐释(over-interpretation)的矛盾
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批评”(critical)一词将CDA 与其他话语分析流派区分开来。在话语分析前冠以“批评”二字,表示CDA 的研究则至少带有以下意味:(1)CDA 将研究视野扩大至广阔的社会结构,结合社会现象和事实进行调查分析;(2)CDA 致力于揭示隐性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普遍存在并渗入了日常的交往与对话,往往被“自然化”、“习惯化”,但对维护社会结构起着重要作用;(3)CDA 的研究具有政治目标,特别关注“不公正/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4)在CDA 看来,话语具有建构、巩固、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CDA 期望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动态联系,以瓦解社会中不公正的权力关系,即CDA 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17]。
然而,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思想毕竟缺乏一定操作性,因为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回到已经逝去的时代或作者书写文本的那一刻。也许正是两位伟大思想家在实践操作性上的“不成功”,启发了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对诠释学本身进行研究,衍生出西方诠释学璀璨夺目的另一派——哲学诠释学。在对人的“有限性”和“历史性”进行现象学及诠释学的描述中,哲学诠释学一派摒弃了主客二分化的主张,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束缚予以反叛,并以从现象学“意向性”(intentionality)萌生的“前理解”(former understanding)取而代之。胡塞尔现象学的极端主观化在海德格尔这里发生了改变,但后者仍汲取了主客同一的精髓,提出无预设的阐释之不可能性[18]126。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完成了从“作者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的诠释学转向,对读者在理解过程中的主观性给予积极的肯定。然而,伽达默尔虽未直接否认文本中的作者原意,却以“效果历史”否定了到达作者原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现阶段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就是学校,对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了解还不够全面。因此,教师在语文的教学课堂中会注重对学生未来社会生活与发展所需技能的积累与培养。但学生对于社会的关注度过低,主人翁意识不强,课堂上的学习实际是要在社会上予以实践的。尤其是核心素质的体现,是要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是要参与社会实践才能有所拓展,学生的社会参与度亟待提高。
安柏托·艾柯(Umberto Eco)在《阐释与过度阐释》一书中为“作者意图”(intentio auctoris)和“读者意图”(intentio lectoris)找到了辩证性的“作品意图”(intentio operis),“作品意图”与“标准读者”(the Model Reader)相对应,“经验读者”(the Empirical Reader)可以对“标准读者”的类型进行推测[20]64。从作品意图的角度来看,“本文”已经成为了一个客体,这个客体被建立起来以论证阐释的合法性。20 世纪英美文学“新批评”的解读方式产生出了无所依傍、自由自在阐述文本意义的价值体系,这种对待文学及文本意义的态度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发生了激烈碰撞。在聚讼纷纭的国际大讨论中,艾柯所提出的作品意图似乎同样是一种折中的策略,既肯定了众说纷纭、争持难下的读者意图,又承认了作者阐释其作品的权利,并创造了作品意图这一概念试图固定住文本的实际意义。CDA 应当属于艾柯所定义的“经验读者”(Empirical Reader),他们“批判性”的阐释涉及但并不针对和强调“作品意图”,他们试图揭示“作者意图”,但“作者意图又往往无法企及”[20]25或难以得到肯定的裁决,最终似乎更适合被归类于一种“读者意图”。
但这难道就意味着CDA 的阐释只是读者意图发挥的结果吗?是否存在一定标准在合理的阐释与“过度阐释”之间划出界限呢?艾柯在《阐释与过度阐释》一书中给出了建议。他首先引用波普尔(Popper)的“证伪原则”对“不好的阐释”(bad interpretation)进行界定:那些违背了简洁、“经济”性标准的阐释、与“已知可靠”的假说相冲突的阐释属于这一范畴。继而指出,有时我们也许无法断定一个阐释是否正确,但至少难以判定它是错的。若一种阐释不能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或不能被其他的证据所排除,我们仍应该给予认可。艾柯还提出,若要对“作品意图”的推测进行证明,唯一的方法是将其放置于本文的连贯性整体予以验证。对一个文本某一部分的阐释若为同一文本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这一阐释就是可接受的;如不能,则应被舍弃。这一点实际为诠释学中的经典概念“诠释学循环”作了旁白,部分与整体相互依存的动态关系制约了阐释的限度,因此,某种天马行空、任意过度的阐释是无法逃脱文本整体所塑造的空间的。
考虑团队A和团队B共同参与维修,对于每个团队,在第i次维修中负责的运行单元数量分别为和对应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和
三、CDA 阐释矛盾的辩证分析
通过对科学实证分析与人文思辨阐释、认识论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批评”性阐释与过度阐释这三重矛盾的梳理,可以发掘费尔克劳夫与威多森关于CDA 阐释有效性之争的本质。CDA 从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多个学科中汲取营养,是一门杂糅性较强的理论。从其DNA 的构成上看,CDA 既有科学实证方法的研究倾向,又继承了人文学科的阐释传统。狄尔泰认为人文研究的关键词是“理解”(understanding),而“说明”(explaining)则适用于自然科学,“科学说明自然,人文研究理解生命之表现”[18]99。威多森在质疑CDA 名称中“分析”与“阐释”含混不清时,也许的确忽视了CDA 结构中“实证说明”与“人文理解”方法的兼容性。
在CDA“预见性、偏向性、排他性”的阐释问题上,威多森与费尔克劳夫两位学者的探讨是西方诠释学内部两派之间的分歧在CDA 研究领域的投影。认识论、方法论性质的客观诠释学派坚信文本客观性的存在,他们以探索有效的阐释路径为己任,相信通过某种客观有效的方法可以抵达那一终点。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派虽未否认客观性的存在,但由于其对主客二分以及客观有效路径的否认,抵达终点变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这两派萌芽于不同的哲学基础,关注的焦点和发展方向也各不相同,但它们最终都长成参天大树,成为支撑起整个诠释学大厦的最重要的两道横梁。对于诠释学的发展来说,这两派各有裨益;对于CDA 的发展来说,威多森与费尔克劳夫的观点同样不可或缺。费尔克劳夫从索绪尔、福柯、哈贝马斯、巴赫金、韩礼德等学者那里证实了以话语揭示意识形态之可能,而威多森则为主观性、任意性、偏向性的阐释分析敲响了警钟。他们正如火车的引擎与刹车,一个期望带领人们前往更自由、平等、解放的世界,另一个则负责把控车速,避免冲向任意主观的深渊。
哈贝马斯批判的诠释学在理解和诠释的基础上加入了批判的维度。然而,从批判学派汲取营养的CDA的“批评”(critical)往往是对“隐性”意识形态的解读和揭示,极易滑向一种“过度阐释”。实际上,这一矛盾同样与西方诠释学的一个经典论题遥相呼应:是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还是曲解文本。艾柯或赫施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通过作品意图还是文本含义、通过读者意图还是文本意义,他们都在寻找一种折中的方案,使各派的观点交汇融合。即便阐释立场并不鲜明,他们仍然为阐释结果的判定提供了一些参照标准,诠释学循环作为这些标准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可为CDA 研究者对最终结果的反思提供一定启示。CDA 不能否认其他阐释结果的合理性,应当说,CDA 的分析结果是众多可能性之一。
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知识或思想自我运动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即其自身的否定性。思想理论的这种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双重的否定:一方面,思想不断地自我充实与发展,从而变得越来越丰富具体、越来越有包容性;另一方面,思想理论又不断地对已有的部分进行自我否定和批判,在此基础上达到更高的逻辑层次、拥有更深刻的思想力度[21]。这两方面的否定具有双重功效,前者使思想和理论更加丰富完善,内容更加全面和充实,而后者则使逻辑更加清晰,思想更加深刻。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中这种内在的否定不是消极的否定,而是在自我否定和对抗中埋藏着积极、肯定的种子,由此继续前进产生积极的成果;这种成果绝不会是最终成果,否定性的环节会一直推动肯定的环节,而内部的矛盾与自我对立正是这股推动发展的力量。
上文关于CDA 理论的探讨正符合黑格尔辩证法所提出的发展规律。CDA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批判哲学的土壤中萌芽,不断吸纳不同学科的思想精华,从巴赫金那里汲取对话思想,从韩礼德等语言学家那里借鉴文本分析的方法,近年来又广泛结合语料库语言学、多模态符号学等理论,成为一种具有活力的分析工具。这正是理论不断自我充实和丰富的过程。而威多森等人的批判和争论正是这一理论内部的否定与自省,对分析结果有效性的质疑正是推动CDA 发展,使其逻辑更加清晰、分析更加客观、理论更加深刻的推手。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哲学诠释学、批评性阐释与过度阐释之间既相异又相融、既矛盾又互补,这种张力和交融正是黑格尔辩证法所说的推动力量。
如今,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文化因此而兴盛。作为老百姓,物质生活好了,对精神生活就会有更高的要求。在物质和文化这个节点上,如果文化的发展和服务跟不上,那将是很危险的。群众文化阵地,不被我们用健康的正能量的文化产品占领,那么就会被其他的不良习气占领。因此,文化工作者对群众文化的引领,十分重要。国家规划设计,给了我们文化发展的方向,我们文化工作者,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头羊,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和践行,现在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已经在城市社区、乡镇村屯,初见成效。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都积极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试图以大数据的量化分析弥补CDA 理论的不足。语料库可以为文本分析提供丰富的素材,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得到更为客观的结果,从而中和话语分析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偏见。长远来看,语料库方法的运用将成为CDA 研究的主要趋势。此外,在国内的CDA 研究中,施旭等学者针对西方话语分析理论的局限,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学术传统的话语分析方法[22]。他们认为,CDA 的思维方式、基本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问题导向,起源于西方传统,同时也局限于西方现实,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应不分时空地应用:在西方CDA 研究者看来,语言是人类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工具,人们通过话语的实践实现某种个人的或利益群体的目的,然而,在中国语言哲学传统中,语言的目的是“立德”,语言是为了帮助人们建立和保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因此,将西方的CDA理论套用于中国话语以发掘其中的意识形态似乎并不妥当;况且,CDA 研究者总是试图在语言和社会认知、文本证据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找到一种单一、机械的因果逻辑关系,忽视了事物的错综复杂性,这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中“变易”的思想以及综合“德”、“道”、“行”等多方面因素进行整体分析的观点不符[23]。因此,中国的CDA 研究者应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辩证观念,超越简单的切割、审判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避免简单武断地套用西方理论,应针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特点建立自己的话语分析系统。
四、结语
本文以著名语言学家威多森与CDA 主要代表人费尔克劳夫的辩论为线索,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了CDA 理论中的三重矛盾。通过梳理和辨析这些矛盾的本质,发现威多森与费尔克劳夫关于CDA 阐释有效性的分歧并非凭空产生,在诠释学的几大经典论题中都可以找到源头。CDA 的分析过程中既有科学实证的思想,又有人文阐释的研究传统,这与西方阐释学的发展历程是一脉相承的。费尔克劳夫等CDA 的创始人试图结合这两种研究传统并找到一种揭示文本真实意图的有效方法,而斯塔布、威多森等学者对这种方法的质疑是对阐释行为本身的哲学思考。当CDA 研究者们竖起“批评性”的旗帜向话语中隐性的意识形态进军时,过度阐释便成为了一种威胁和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语料库研究方法可被广泛运用,以中和分析者可能存在的偏见。然而,西方CDA 理论的普适性仍然值得推敲,不同文化的语言观并不相同,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也许并不完全适应中国话语研究的土壤。
总之,在黑格尔辩证思想的观照下,CDA 内部的诠释学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不仅呈现了CDA 结构的复杂性,更标志着CDA 理论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威多森与费尔克劳夫的辩论对CDA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而CDA 的研究者在循着其创始人开拓的路径前行时,应参考理论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结合分析对象的语言文化特点,挖掘实际的话语问题,并借助语料库等量化分析方法的优势,得到真正客观有效的研究结果。
[参 考 文 献]
[1] N.Fairclough.A Reply to Henry Widdowson’s Discourse Analysis:A Critical View[J].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96,(1).
[2] H.G.Widdowson.Discourse Analysis:A Critical View[J].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95,(3).
[3] H.G.Widdowson.Reply to Fairclough: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J].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96,(1).
[4] H.G.Widdowson.Review:Norman 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1992[J].Applied Linguistics,1995,(4).
[5] H.G.Widdowson.The Use of Grammar,the Grammar of Use[J].Functions of Language,1997,(2).
[6] H.G.Widdowson.Review Articl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Applied Linguistics,1998,(1).
[7] H.G.Widdowson.Critical practices:on represent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C]//Srikant Sarangi,Malcolm Coulthard.Discourse and social life.London:Routledge,2014.
[8] H.G.Widdowson.On the Limitations of Linguistics Applied[J].Applied Linguistics,2000,(1).
[9] H.G.Widdowson.Interpretations and Correlations:A Reply to Stubbs[J].Applied Linguistics,2001,(4).
[10] H.G.Widdowson.Scoring Points by Critical Analysis:A Reaction to Beaugrande[J].Applied Linguistics,2001,(2).
[11] M.Stubbs.Whorf’s Children: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J].British Studi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1997,(12).
[12] 卢梭.论科学和艺术[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3] 董立河.论尼采的反科学主义思想资源[J].天津社会科学,2002,(3).
[14] C.P.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5] N.Fairclough.Language and Power[M].London:Longman,1989.
[16] N.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
[17] N.Fairclough.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New York:Harlow Longman,1995.
[18] R.E.Palmer.Hermeneutics[M].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19] E.D.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20] Eco Umberto.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21] 孙正聿.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真实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2003,(6).
[22] 施旭.当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23] 施旭.话语研究方法须中国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08(15).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4-0084-07
[收稿日期] 2018-11-30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3g008
[作者简介] 熊伟(1969-),男,湖北大悟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翻译理论与跨文化研究;舒艾(1992-),女,湖北英山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2017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媛媛]
标签:批评性话语分析论文; 诠释学论文; 过度阐释论文; 语料库方法论文;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