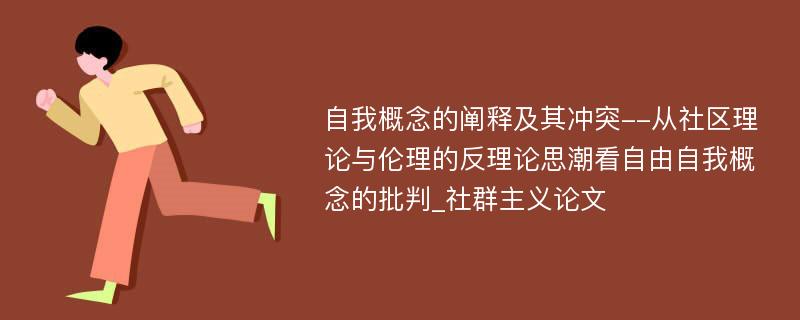
自我概念之诠释及其冲突——社群主义和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思潮对自由主义自我概念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自我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洛克提出自由主义思想以后,几百年来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思潮的一大主流,甚至成为人们生命与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弃的一部分。1971年罗尔斯发表其传世之作《正义论》,该书立足于卢梭的契约论和康德的义务论,以正义原则取代功利原则,强调正义、公平和个人权利的优先地位,并全面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可以说,《正义论》的出版对西方的哲学界、政治学界、经济学界甚至法理学界都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同时,这一现象也透露出,作为西方核心价值原则的自由主义并没有终结各种价值,它的可质疑性也将随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翻向新一页。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正义论》自出版以来便遭到来自左右不同方面的批评,到了八十年代,西方学界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开始在形上学方面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进行批判,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C.Taylor)、桑岱尔(M.Sandel)、麦金泰尔(A.Maclntyre)等。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本体论方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对自我的性质及其形成的理论是错误的,个体并非先于社会而独立存在;在价值辩护方面,他们批评自由主义无法给社群以内在的价值,社会只成为人们达成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与社群主义相呼应,在伦理学领域里,也出现了一种“反理论”(anti-theory)的思潮,他们对近现代西方的伦理学理论提出质疑,矢向所指则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康德的义务论以及罗尔斯的契约论等,他们认为脱离境遇和脉络的普遍的道德原则并不能给实际的道德抉择带来任何帮助。反观西方学界的上述理论,我们发现他们的批判涉及面甚广,然而,他们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式的自我概念的不满却是一个共同的中心,本文即试图对这一特点作出论述。
一
1980年,麦金泰尔在“道德哲学的危机:伦理基础的寻求为何困难重重?”一文中认为,当代人们的道德观念从总体上说是混乱的,不可能在价值层次的内容上取得共识,而寻求伦理之基础之所以这样困难,原因即在于仅凭理性并不能带来道德,至少不能带来具体的道德。麦金泰尔说:“当代道德论辩的主要特征便是,它们都是不确定的和冗长不堪的。当对立的结论展开相互攻击时,比如,‘所有的现代战争都是错误的’,‘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自由之战是正当的’,‘有时一种伟大的力量必须介入战争以保护和平所需要的力量平衡’,或‘所有的堕胎都是谋杀’,‘每个怀孕妇女都有权堕胎’,‘有些堕胎是正当的,有些则不’——他们源于理性辩护的那些前提原来相互之间是不可公度的。”(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p20.)麦金泰尔认为,当代的这种道德哲学危机原因并不难发现,各种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和捍格仅仅是它的表面现象,其深层原因则是各种道德观念都是在理性的旗帜下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而现代道德哲学的特征正充分说明了理性对于道德的无能。麦金泰尔说:“现代道德哲学有三个根本特点,首先它表现为各种直觉;其次是理性概念的运用;最后即是在各种对立的道德判断之间处理问题的优先性方面的无能。”(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第21页。)
这种理性对于道德的无能所导致的道德困境,当然有其悠久的哲学历史渊源。自从启蒙运动弘扬理性以来,哲学家一直试图为道德规则提供理性的合法性证明。洛克首先通过理性发现道德的基础就是神的律法,后来笛卡尔、休谟、边沁和康德相继提出理性的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则,并各自给予理性的辩明,但这些道德规则本身却很难统一,有的甚至互不相容。以边沁的利益最大化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以康德的道德律至上为代表的普遍主义,进行了几个世纪毫无结果的论战,最后向人们说明的是,理性对于道德建设实无多大的作用。每一种主张都被其它主张有效地批判,其总和即是全部陷入失败。麦金泰尔认为,试图给道德提供理性证明的方案已经决定性地失败了,从此我们先前文化的道德——因而也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就缺少了公共性,缺少了理性或判明的正当性。麦金泰尔认为,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先验说明充分证明了理性在其思想中所占有的根本地位。然而,麦金泰尔指出,罗尔斯“从未在他的结论中注意到,在他希望找到和谐与秩序的地方,他找到的是混乱。”(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第22页。)也正因为这个并不可靠的理性基础,使得以罗尔斯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遭到社群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不难看到,当代道德理论中流行的理性我与笛卡儿的“我思”之我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罗尔斯《正义论》一书所包含的道德理论之所以广受人们的瞩目,其中的焦点之一便是罗尔斯关于理性与道德关系的诠释。罗尔斯认为,我们讨论理性主义和理性观念应当避免把任何道德和价值因素考虑进去,换言之,依罗尔斯,理性乃是对道德价值保持完全中立的一种思想力量。道德规则若要普遍化、客观化其自身,它就应当把价值判断排除在自身之外。由是,道德实践的首要任务便是对这种普遍规则的遵行,一个人只要不违反这一规则便尽了道德的份。于是,现代道德哲学家的首要任务便一转而变为努力构造一套普遍适用的客观的道德规则,罗尔斯便把“基本德性”界定为“依据正当的基本原则去行为的强烈的和正常有效的欲望”,是完全依据理性的“干慧”所作出的行为。因此,在正义、公平的概念背后,罗尔斯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可以不依赖任何客观外在因素所制约而又能完全依据正义原则作出正确判断的理性自我。也正因为此,麦金泰尔认为,罗尔斯的“正义”概念包含着一种“道德帝国主义”(amoral imperialism)。(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第38页。)不过,在麦金泰尔看来,自由主义的这种理性自我观念却由于“缺乏任何合理的历史”而难于获得道德合法性之证明,因为根本上,“个人行为常常是一个社群行为(corporate deeds):我是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我的政党、我的社群,一如它呈现其自己给这个世界一样,它们的过去就是我的过去。”(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第33页。)“由于所有的道德总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性的当地情况特殊性相关联,当时的道德力图摆脱全部特殊性而成为一种普遍性道德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
然而,此处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为何麦金泰尔认为,以建立一套普遍的原则和规范为己任的现代德哲学(包括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包含了一种“道德帝国主义”?而这样一种“道德帝国主义”与他们所认定和设计的道德主体(自我)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当代西方道德学理论流派纷呈,林林总总,然而大体上可以这样认为,对形成几百年来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自我观(人观)进行世纪般的反省却是西方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之一,社群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流派。
二
一般来说,时至今日,愈来愈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建立一种“理想自我”的概念是获得整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想自我”包括合理性和自我诠释两个方面,合理性是指个人对道德行为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认识,并据此认识作出合理性论证;而自我诠释(selfinterpretation)则是对什么才是圆满的人生等价值关怀问题能藉着“自我”概念作出解答。伦恩(T.E.Wren)认为,“最严重的道德挣扎看来是关于自我诠释方面,而不是在抵御诱惑方面。”(注:T.E.Wren:Caring About Morality:PhilosophicalPerspectives in Moral Psychology,The MIT Press 1991,p165.)同时,托玛斯·奈格尔(Thomas Nagel)亦认为,利他主义得以可能的关键,在于某种自我概念的建立。(注:Thomas Nagel: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70.)那么,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其间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自我概念呢?
依罗纳德·德沃金,自由主义乃是以“中立立场”为其基本性格的,亦即在政治上表现为每个公民有受到平等的关注和尊重的权利,在价值上表现为对各种人生理想的选择不歧视也不偏袒。换言之,这一中立性格蕴涵着每一种人生理想都有其独立的价值,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任何标准来对各种人生理想判一个高下;同时一个公正原则的建立,不应当把价值观念夹带进去,有价值观念即有偏好。唯一可以说的是只要这种人生理想不与公正原则相背离,便是允许的。那么,自由主义的这个公正原则在伦理学上如何表现呢?要理解这一问题,即需要对自由主义的自我概念作出分析。
其实,毋需多大的思辩力我们即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的“中立立场”除了外在的社会政治的表现外,它实际上还包含了一个有关自我概念的独特看法,用桑岱尔的话说,自由主义的许多论旨,与自我概念密切相关。更早一点,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就曾经指出,自由主义心目中的自由是源于个人主义式的人的概念。(注:参阅《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07页。)但个人主义的中心观念即认为,个人优先于社会,对个人而言,社会只是一种为满足独立成员的目的和要求而特殊设计的协会(association)。如此一来,社会及社会组织本身就必须依靠各个人的特殊愿望和选择目标来作出决定,而这些独立的个人的愿望和目标却不能内在于社会来寻求,而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罗尔斯试图提出以道义论为底子的“公正”作为社会建构的基本原则来取代功利原则,不过,在涉及到公正的问题上,罗尔斯又纯粹追随休谟的《人性论》理路。(注:参阅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注1。)问题在于,这样一种个人主义式的公正原则在罗尔斯那里又蕴涵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假如允许简单的陈说,那么,在罗尔斯的心目中,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安排“对”(公正)与“价值”这两个基本概念,“对”与“价值”何者为先构成了公正原则与功利原则的根本分别。故而,罗尔斯提出了“对优先于价值”(the right isprior to the good)的著名命题。罗尔斯认为,公正或正义(“对”)乃是社会的首要美德,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公正原则是评价其对与错的首要标准。“对”即是合乎正义原则,任何价值若要与此相违背或相悖逆,便是不允许的,这便是“对”之道德的优先性问题。罗尔斯坚持,“对”并非要依从别的价值,毋宁说,“对”本身便具有价值的自足性,任何个体的行为选择若是依从“对”的原则,便已尽了道德的份。
然而,罗尔斯的这一命题又如何与自我概念相关?桑岱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限制》一书中指出,罗尔斯的这一命题其实假定了一个对自我的看法,在这种假定中,自我只是一种纯粹的选择能力。在桑岱尔看来,罗尔斯的这种对自我的看法其实延续了自笛卡儿以来近现代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即自我是一个可以独立于外在世界而存在的实体,是单纯而赤条条的自我,桑岱尔称这种实体主义式的自我为“无负累的自我”(unencumered self)。然则,“对优先于价值”为何需要这样一种自我?我们知道,罗尔斯是从“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推演出其作为分配公正的正义原则的,则“原初状态”是一种纯粹的前社会状态,完全自由的理性自我在这种状态中经过反复的推理和论证后,依据正义原则相互订立契约。人们在订立契约时又浑然无知于他们的自然天赋和社会地位,无知于他们的善恶观念,因而是“对”成了人们首选的标准,其余的一切价值皆是次要的,且在罗尔斯的心目中,价值既是人们的主观选择,它便可以随时改变,而自我却不能改变,若自我等同于这些目的和价值,便不啻于说自我也要随之改变,因而,构成自我的并不是这些目的与价值,而只是对这些目的和价值进行选择的能力,因而这种自我也便获得了超越社会的性格。
由此看来,在自由主义的逻辑格局中,自我与目的的分离,其结果就是使自我成为可以不必依赖外在世界而能独存的实体,这便是赤裸裸的无牵挂的自我。泰勒称这种近代“笛卡尔式”的自我为“自我定义的自我(self-defining self);(注:Charles Taylor:Hege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6.)桑岱尔则把这种自我的本质称之为“为选择而选择的自我”。(注:M.Sandel:Liberalism and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irdgeUniversity Press,1982,p170.)既然自我是可以独立界定的,那么,这种自我的概念一转即变成为凌驾社会或者说是先于社会的(presocial)。如是,即人们的一切选择行为仅仅只把社会当作是一个对自己有用的工具。对此,麦金泰尔批评道:“这种不具备任何必然社会内容和必然社会身份的民主化的自我能够是任何东西,能够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他本身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都没有。”(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三
可以说,社群主义从本体论上揭示自由主义虚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出他们将个人看作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观念。不论自由主义是以何种方式加以表述,在他们理论的内在格局中,个人的基本目标和价值是在前社会的状态下就已拥有了,只不过在前社会的状态中,由于充满了横蛮、恐怖,人们无法达成各自的目的,于是有理性和有欲望的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而订立契约,制订了共同遵守的规则而建立社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其功能对人们而言是工具性的,社会是各个“离境我”从正义原则出发选择的结果,是人们为了各自的目的进行合作的场所。然而,它也同样的包含了这样一个论旨:即个人是可以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本质上并不存在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社会更不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你、他只具有各自独立甚至相互矛盾的目的。这种脱离社会的自我由于没有任何文化背景而无法自我表达。麦金泰尔说:“实际上,如果把自我及其角色的历史与由自我所详细说明并借以表达其角色语言的历史分离开来,那就完全错了。”(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6页。)在社群主义者看来,社会是一个“共同的实体”(corporate entities),其总和要大于而并不等于无数个人的聚合。没有社会关系,个人是否拥有其人生或目的是深可怀疑的。
就对自由主义的自我概念作出批评而言,泰勒把这一问题称之为“本体论论题”。(注: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ed.by N.Rosenblu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60-163.)对此,社群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自我的选择标准和自我的认同上。既然自由主义的自我只是一种纯粹的选择能力,而选择的价值和目标又不是自我的一部分,那么,人的选择究竟有没有客观的标准?假设,自我是一种选择能力,外在世界又没有一种客观的选择标准(自由主义者反对这种客观标准。在密尔那里价值尚可以有比较,有高下,比如“宁愿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而不愿做一条快乐的猪”,但到后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那么,个人的选择也就变成了个人的随意性了。麦金泰尔称这种选择为“缺乏任何终极标准”的选择,(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3页。)是立场、态度、偏好的一种表达和超乎人们理解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自我与目标和价值之间的完全分离,人的选择目标可以随时改变而又不会影响到自我内部结构及其性质,如是,即任何一种自我选择的目标或价值,对于自我而言便顶多只有附属的意义,或者说彻底一点,只具有偶然的意义。这样终极关怀、生命理想、人生目的之类的属于安身立命的东西,便在这种自我的概念中作了无情而彻底的消解。在这种自我的概念结构中,视野所及都是一些相对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对于自我而言又永远都只具有偶然性。因为自我不期望这些事实对其自身有任何影响,而这些事实本身对于自我而言也仅仅只是过眼云烟,没有任何的恒常性。由此看来,自我的这种自由或自由的这种自我,的确象马一样,它把人从它的背上摔下来后,径自向前跑去,这种自由主义的自我概念最后即变成一种自我剥夺。泰勒在《自我之源泉:现代认同的构成》一书中认为,环境规定我们,个人作为一个自主的主体,实质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发展起来。因此,自我才不能优先于目的和价值,否则社会便会成为一个“工具性的社会”(instrumental society),而且也会“导致对公共自由的摧毁”。(注: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Ident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502.)
而在价值辩护方面,桑岱尔即进一步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等多只包含两种意义上的社群概念,(注:Charles Taylor:Hege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6.参阅第121-124页。)一种是工具式的社群概念,即每个人都抱有自利的目的,而社会只是为了这些个人的自利目的而建立的一种共同体。这一点可以说是契约论的原生形态。另一种即是情感式社群概念,那些参与社群的各成员间有些共同的目的,利益也不是完全冲突的。然而,除此之外,罗尔斯却未曾注意到尚有另一种“建构式的社群概念”(constitutive conception ofcommunity),这种社群概念除了目的和情感之外,最重要的特征便在于个人的自我认同(identity of self)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群来赋予的。因此,在建构式的社群概念中,自我是藉由社群来建立其角色和社会身份的。(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48-150页。)这种身份本身在麦金泰尔看来便包含了特定的责任和义务,我是丈夫,同时也是哥哥、舅舅和大伯,不是一个大学教授,这些身份标志不是个人的偶然属性,也不是人们藉此来发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而后又加以剥除的东西。这些身份标志本身就是组成一个实质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规定了我的特质,限制了对我的发问,也明确了我的责任和义务,这便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自我的圆满内容。没有这样一种独特的身份关系网络的连结和规定,我就什么也不是,或仅仅成了一位被这一社会共同体所放逐了的人。无疑的,个人的自我认同并不是一种观念的抽象,它体现为一系列特定的符号、习俗、礼仪、价值、目的,而这些内容来自个人处于其中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麦金泰尔认为,人们只有通过考察个人在某种场景或某个“叙述”中的行为方式才能理解他的生活,而社群规定了这些叙述的形式、环境与背景,反过来所有这些叙述构成社群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麦金泰尔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中从对传统、历史的反省角度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作出批评,并进一步提出了“由传统构成的和构成传统的”(tradition-constituted and tradition-constitutive)道德的合理的探究方式。在麦金泰尔看来,社会关系和历史传统规定了自我,而认识到自我是这样一种规定,目的是要发现自己是被置于朝向一定目标进发的旅途中的一个点,因而一个彻底完成了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成就。泰勒更明确地指出:“一个人只有处在其他的自我中才可能成为一个自我。没有环绕于他周围的那些关系,一个单独的自我永远不能加以描述。”(注:Charles Taylor:Hege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第35页。参阅第121-124页。)然而,自由主义的自我却在努力争取自身领域主权的同时,沦为“一种没有任何既定连续性的自我”,(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2页。)成为“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一个‘衣夹’”。(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以何种角色行动?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寻找一个确定的价值?”类似的追问在西方的历史上其实并不鲜见。若说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有引人之处,那么,依我看其最大特点便在于,他们对通行西方几百年的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弊端的揭露已由作用层进入到本体层。不过,从哲学的发展线索看,社群主义的这种揭露的批判似乎依然是迟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至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海德格尔便在其晦涩的纯思中证明,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并不首先存在,此在(自我)之存在,在其自身即已与他人、他物处于交道和牵挂之中,“此在本质上就自己而言,就是共同存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3页。)没有超时间、空空,也没有前社会的单纯自我。由是,海德格尔对自我的诠释学也便作出了其独特的规定:“此在的诠释学作为生存的分析工作则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向之归的地方了”。(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8页。)然而,更早地,马克思在1845年春就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寥寥数语,却将其间的义理意蕴和盘托出,全尽摄绝。
四
在最近的西方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趋向。他们以反省西方传统伦理观的面目出现,对功利主义(边沁、密尔)、义务论(康德)、契约论(罗尔斯)进行批评,恰与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省相映衬、相配合。综合地看,虽然社群主义和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思潮各有理路,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现代道德哲学未能注意道德实践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克拉克(S.G.Clarke)与辛普逊(E.Simpson)在他们所编的《伦理学中的反理论与道德保守主义》(注:S.G.Clarke& E.Simpsoned:Anti-Theory in Ethics and MoralConvervatis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一书中标明了这一思潮的“反理论”旗帜。
所谓“反理论”(anti-theory),简单地说,即是反对现行的道德理论对道德的理解,反对把道德原则普遍化、抽象化、程序化和技术化,注重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注重历史、文化和特殊境遇中的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的多样性。无疑的,这一思潮中的人物各有各的立场,然而,在他们的批判观点背后仍然有一套对人的特殊的看法。假如我们同意,任何道德理论都不是外在地挂搭在人之上的东西,那么,我们大体可以说“反理论”思潮所要检讨的是脱离境遇的自我与普遍道德规范原则何以可能的问题。反理论者普遍认为,以往的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即是努力建立一套普遍的道德规范原则,而且以此抽象的原则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具体的道德判断、道德实践仅仅是这一套原则演绎而来的结果。不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契约论者,他们都假定了人是自利而又有理性的,因此他们制订一套道德规范原则,目的正在于使所有有理性的人能明确地加以遵循,在他们看来,依照这一普遍的道德规范原则,便可以使人达到确定的道德判断。麦金泰尔说:“某些现代哲学家……正是在自我避免与任何特定偶然事态有任何必然认同的这种能力中,看到了道德能动作用的本质。根据这种观点,作为一个道德行为者……能够从某种与全部社会具体情况完全分离的纯粹普遍的和抽象的观点出发,对这种情景或特性进行评价。”(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然而,在反理论者看来,对于具体的道德实践而言,一套普适的伦理规范理论其实并无可行性和必要性,面对复杂多变而又多面向的道德生活,掌握一套普遍乃至完整的原理原则并不足以使道德生活趋于完善。无论道德原则如何完美,如果人们不具有各种具体的德行,它就不可能对个人的实际行为发生影响。克拉克和辛普逊认为,如果我们从实践和德性的方向而不是从计算和原则演绎的方向去思考道德,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期待圆融而可消解对立的原则事先预设在道德学说之中。(注:S.G.Clarke& E.Simpsoned:Anti-Theory in Ethics and MoralConvervatis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第8页。)换言之,具体的道德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冲突并不因普遍的理性原则的应用而归于消融。麦克道威尔(McDowell)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假如一个人知道他应当做什么,这与其说是普遍原则应用的结果,倒毋宁说是其作为某一种以特定的方式来理解处境的人的结果。”(注:S.G.Clarke& E.Simpsoned:Anti-Theory in Ethics and MoralConvervatis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第105页。)的确,人并不事先被普遍原则所占有,而是被具体的历史、文化所占有。人不是原则的,而原则却是人的。离开了具体的现实生活,人们便无法理解普遍抽象的道德原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伯纳德·威廉斯(B.Williams)认为:“哲学对于决定我们在伦理问题上应当如何思考,其所能做到的地方很少。(注:B.Williams:Ethics and theLimits of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74.)
不难看到,当代道德论中的这种普遍性倾向是以理性主义为底子的。麦金泰尔认为:“理性的本质就在于制订普遍的、无条件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原则,从而合乎理性的道德所规定的原则能够也应该被所有人遵循。”(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9页。)然而,麦氏认为,理性是用来计算的,它可以确定事实的真假和看到数学上的关系,在实践领域内,它仅可涉及手段,而在目的问题上,理性却必须保持沉默。反理论者普遍反对理性主义的强迫,认为对特殊境遇中的道德选择应当有特殊的理据,而不能藉由普遍的原则直接加以演绎。然而,以往的道德论——在罗丁(R.B.Louden)看来——却只限于对行为的指导,而且在他们的规则中已经“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答案”。(注:R.B.Louden:Morality and Moral Theory,OxfordUniversity,1992,p95.)这种普遍规则的霸权看来已难于获得其合法性证明,至少在人类学家看来,人总是具体的人,而道德的价值也常常表现为脉络的价值。譬如人类学家已经指出,在新几内亚的Gahuku-Gama族(处在农耕父系社会),“人”的价值仍是视情况而定的,而“道德”更是由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而定。依基督教义,杀人是错的、不道德的,个人生命有绝对价值,这与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无关。但在Gahuku-Gama社会,杀自己族人是错的,杀别族人即是允许的,所以战争时要避开母方族人。由此看来,道德原则如果离开了特殊文化的特殊德性,它就有可能什么也不是。
反理论者认为,当代道德哲学以建立普适的道德规范为己任,其实是将人化约为一种抽象的相同的单一元素的东西。由此出发,道德探究无非是为了建立一套单一的可公度性的标准,这样一种努力方向使得他们将多姿多彩的道德生活剪裁成一种单一式样,而道德选择和道德决断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甚至那些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做出决定的矛盾性,都被化约为一种程序。如是,掌握一种道德理论就犹如掌握一门实用科学的操作方法,道德理论被技术化、技巧化。这种道德哲学除了单元心态外,的确包括了某些幻想的成分在内,因为他们实际上假定了每一位道德行为主体(自我)在任何境遇中都会如机器人一般进行正确的道德程序的决策。
然而,在理论上,道德学说如何兼顾普遍性、规范性和特殊性、具体性?何种形态的道德学说才能真正切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并且能够从根本上回应反理论者(同时也是社群主义者)的责难,从而显示出理论上应有的创造性空间?这些问题的确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实际上,不论是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是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思潮,他们思想深处的根源皆来自韦伯所说的“世界解咒”以后理性化浪潮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珍视的事物被他们想要的东西所消蚀或摧毁,这两种力量相反而又同样难于割舍的精神向度构成了现代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紧张和挣扎。因此,如何克服在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情感、普遍与特殊等问题上滞于一极之诟病,看来只有从超越这种对立的思维方式上下手。无疑,作为一股社会和伦理批判的思潮,社群主义和反理论者都难免会有偏狭之弊,比如罗纳德·德沃金就认为,社群主义试图通过限制人们的自由来达到理想的社群概念是难于让人接受的,相反,自由主义倒给真正的社群概念提供了“最好的说明”(注:R.Dworkin "Liberal Commuity"',California Law Review 77(3),1989,p480.);而反理论者在提倡特殊性、具体性,主张脉络主义立场的同时,也难免会陷入粗鄙的相对主义。如此以水济水,终不出黄茅白苇,焦芽绝巷,又岂是究竟路头?庄生有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注:《庄子·天下》)因其落于一曲而未至根源,故不能配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或许,对我们来说,重回“生活世界”(lifeworld),建立“根源性伦理”(originalethics)仍不失为一条可供选择的努力方向,然而这个方向所昭示的是,不是从人的本质而是从人的实存中揭示意义,发现价值,寻求价值,寻求永恒。但这已超出本文所当叙述的范围了。
标签:社群主义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自我概念论文; 伦理学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读书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正义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