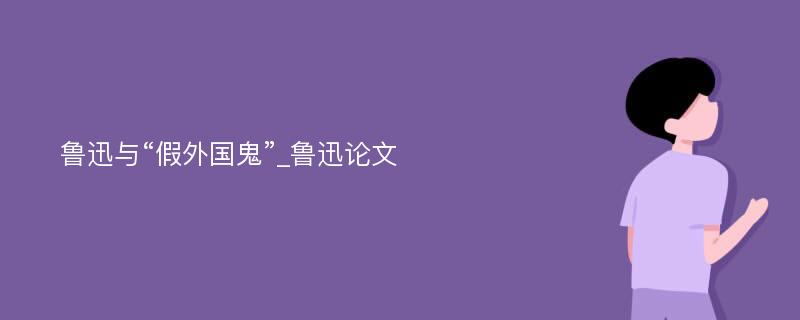
鲁迅与“假洋鬼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洋鬼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梦阳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红楼梦》第一回里,曹雪芹自叹道:‘满纸 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将此诗看做鲁迅对《阿Q正传》的自 叹,也不无道理。《阿Q正传》无疑是《红楼梦》之后,中国文学中蕴藉最为深厚的伟 大作品,问世七十多年来,经无数代研究家的无数次解读,似乎仍未‘解其中味’。” (注:张梦阳:《<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 10期。)其实,现在看来有些文章非但未解“其中味”,反倒离其本味愈来愈远了,其 中“对假洋鬼子”这一形象的读解即是一例。
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研究者们对阿Q这一形象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解说,提出了 多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方式。但在“假洋鬼子”的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 ,都认为“假洋鬼子”是一个毫无疑问应该加以批判的形象。造成这样一种看法的原因 很多,其中周作人和毛泽东对“假洋鬼子”的反感和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 Q正传》发表后,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
《正传》里所写的人物,除了静修庵的尼姑,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三两个没有什么表 现的之外,大都是鲁迅所谓呆而且坏的人,但其中又有个区别,大多数都是旧式的,新 式的人物只有一个,这即是假洋鬼子,却是特别的讨人厌。著者大概在这里要罄吐一下 对于这一种人的反感,虽然也未能详说,但主意总是表白出来了。照道理讲,这应该是 速成学生,头上顶着“富士山”的,不会得去混过几个月却把辫子剪了,以致做不成大 官,如他的母亲所说。不过若是“富士山”,那么回乡之后,便又可将辫子拖了下来, 不可能成为假洋鬼子,这一面可以免于阿Q等人的笑骂,但是一面也就没有了权威,后 来不容易有挂银桃子的机会了。著者说他当初剪了辫,后来留起了一尺多长的头发披在 背上,像是一个刘海仙,这是一种补充的说法,也仿佛可以看出他当初辫子并不是那么 爽快的剪掉。(注: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2年版,第139页。)
按理说作为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分析应该是较为可信也较有说服力的,他的一些关 于鲁迅的文章也的确成为后世鲁迅研究者的一些重要材料和证据。但在此处,我们却不 能不指出他对“假洋鬼子”的分析和定位显然偏离了作者的原意,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后世研究者对“假洋鬼子”这一形象的理解和把握。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 加以分析。
如果说周作人是以鲁迅的弟弟,并且以和鲁迅同时代而且思想有过深入交流的现代文 学大家的身份写这段文字,所以能够对后世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产生一种束缚的话,毛泽 东则是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思想权威的身份,影响了鲁迅研究的走向。毛说:“鲁迅在 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了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 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 。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从那以后,“假 洋鬼子”不准劳动者革命的罪名便铁板钉钉了。此后许多研究者便把不准平民革命作为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进行探究的结果之一。比如有的研究者就在自 己的著作中写道:“资产阶级根本不敢动员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也不打算去动 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要农民按照他们划定的‘秩序革命’、‘文明革命’的框 框行事,农民斗争一旦突破了这些框框,他们便借口‘行动越轨’,狂暴地压制农民的 革命要求。”(注:程致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思想者鲁迅论》,学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9页。)这样一种论调其实只是对毛泽东论断的重述和回应。应该说,在这一 点上,支克坚先生的文章是有着突破性贡献的。他在《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一文 中,非常精辟且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其实鲁迅也是不赞成阿Q革命的。这样就对“假洋 鬼子”压迫下层人民革命的罪名进行了有力的消解。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支 先生并没有进一步对“假洋鬼子”的被误读进行辨析。那么,“假洋鬼子”究竟是怎样 一个人物,我们应该站在一种什么立场上去认识和把握这一形象呢?
现在,当人们一提起“假洋鬼子”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已经预先包含了一种价值判 断在里面了。在潜意识层面,“假洋鬼子”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形象。一提起他, 读者立刻会联想到一个披头散发,提着文明棍,高谈阔论并且时不时蹦出几个英文词, 对下层劳动人民不屑一顾,而且常常会用手中那根“哭丧棒”虐待贫苦百姓如阿Q的一 个恶少形象。其实,这完全是对《阿Q正传》的一种误读。事实上,当我们不假思索地 随意运用“假洋鬼子”这个词去称呼那位钱大公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背离了鲁迅的原 意。在小说中,阿Q之所以对钱大公子深恶痛绝,鄙视地称他“假洋鬼子”,无非是因 为这位钱大公子上过洋学堂,而且去东洋留了半年学,回来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 了”,于是有了“里通外国”的嫌疑。当然阿Q更为痛恨的是他那一条假辫子,以为“ 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可见,去东洋留过学和剪掉了辫子是阿Q将 钱大公子斥为“假洋鬼子”的主要原因。因而,当我们随着阿Q一样称呼他“假洋鬼子 ”并且咬牙切齿充满厌恶的时候,我们也就不自觉地做了阿Q的同党。我想这是鲁迅的 一种悲哀。周作人曾经提到,鲁迅“在小说和散文中有不少自述的部分”。其实在这篇 小说中,“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 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 头发的故事》里的N先生一样,《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也有着鲁迅自己的影子 (注:周作人曾经指出:“《头发的故事》也是自叙体的,不过著者不是直接自叙,乃 是借了别一个人的嘴来说这篇故事罢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第41页。)。
纵观鲁迅的一生,剪辫之祸在他心底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他曾在多篇文章中 提及此事,愤懑之情溢于言表。1902年鲁迅去日本后不久就把辫子剪掉了,并且照相留 念,题诗明志。他把剪掉辫子当作自己迈向新的人生道路的第一步。然而没有料到这竟 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照片寄到国内,首先让家里人大吃一惊。据周建人回忆, 当时“我们一看,都一呆,原来他把辫子剪掉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乡还不曾见到 过哩!他去日本留学,冷言冷语已经不少,怎么竟把辫子剪掉了呢?”自己家的人虽然吃 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三台门里的亲属就不一样了,“子传奶奶看到了这照片,人都酥 去了,半晌,才说:‘阿樟怎么把辫子剪了?宜少奶奶,你怎么也不管管他?’”(注: 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177~178、180~181页。)
虽然他剪掉辫子的事在家乡族人中引起了很大的波澜,然而此时鲁迅尚在日本,并没 有亲身感受到。直到1903年8月,鲁迅回国探亲,才亲身感受到了短发给他带来的巨大 痛苦。周建人在他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虽然这段话很长,但是为了保持原 貌,还是把原文照抄在这里:
大哥到家的那天,我正好在家里,我只看见一个外国人,从黄门熟门熟路地进来,短 头发,一身旅行装束,脚穿高帮皮靴,裤脚扣紧,背着背包,拎着行李,精神饱满,生 机勃勃,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大哥呀!
他见过祖父、祖母、潘庶祖母、母亲,家里人倒也不说什么,没觉得这短头发有什么 不好,可是台门里一听见大哥回来了,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来围观他的头发,好像看 希奇的动物,那眼神真有形容不出的味道。等他们走后,大哥说,在上海,倒还不感觉 什么。人家分不清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可是他想到,在杭州、绍兴恐怕大家不习惯 ,所以就花了二元钱买了一条假辫子。
第二天,他便穿上衣衫,戴上假辫。这样该好了吧,但还是不行。台门里知道我大哥 回来的人更多了,无论台门里的族人或出去碰到的路人,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发现它 是假的,就一声冷笑;听说伯文叔还准备去告官呢!我大哥并不怕,戴了假辫子去看望 过寿老先生和别人。
假辫子既然要给人看出是假辫,那就不如显出真面目来得直截爽快。我大哥索性废了 假辫子,穿着西装,和我一起到大街去,他照例要上街买些纸和笔。
这可不得了了,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这冒失鬼”、“假洋鬼子”。我 听了也很气愤,然而寡不敌众,只好当作不听见。
于是,他不穿西装,改穿大衫,又和我一起到大街去。一路上,人们骂得更凶了:“ 这人一定犯了法!”
“说不定给人捉奸捉住,本夫剪了他的辫子呢!”
“这缺德鬼!”
我大哥试来试去,都找不出一个好办法,以后就索性在家里,不出去了。(注:周建人 :《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 78、180~181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剪掉辫子给鲁迅带来了多大的压力和屈辱!直到1909年,鲁迅结束 留学生涯回国以后,他还不得不承受着没有辫子而带来的屈辱,一回上海便买了一条假 辫子装上。装了一个多月,因为老是担心掉下来或是被人拉下来,于是“索性不装了” ,但是又遭到辱骂。所以鲁迅满怀悲愤地写道:“我想,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 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辫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注: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卷六,第191~19 3页。)其实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头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N先生”—— 其实也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由于屡屡被骂为“冒失鬼”、“假洋鬼子”,他也终于开 始反抗了:“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地打了几回,他 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地方还是骂……”(注:鲁迅:《头发的故事》 ,《鲁迅全集》卷一,第328、330页。)这里的“N先生”不正是《阿Q正传》里的“假 洋鬼子”吗?这手杖不就是阿Q所谓的“哭丧棒”吗?而被打的,不就是那些阿Q们吗?这 便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棒打阿Q一节的由来。
《头发的故事》写于1920年10月,发表在当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上。而《阿Q正传》则是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至次年的2月12 日全部载完。两篇小说的发表相距仅一年的时间,此时已经步入中年的鲁迅早已是一位 深刻的思想家了。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一年之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应该是有着内在的延 续性的。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对于那位N先生——“假洋鬼子”怀有充分的理解 和同情,因为他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难道一年之后到了《阿Q正传》中,鲁迅的思想 就来了个大转弯,转而尖刻地揶揄、嘲弄,以为他“特别的讨人厌”吗?
剪掉辫子给鲁迅带来的痛苦之所以刻骨铭心,原因之一就是被人追骂“假洋鬼子”给 他带来了巨大伤害。虽然鲁迅在决意剪辫子前对于可能遭遇的麻烦已经有所估计,并且 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但是回到绍兴后所遇到的种种侮辱嘲骂仍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他只好“呆在家里,不出去了”。当然,在这之前他也许曾经“横眉冷对千夫指”,甚 至手中添出一根手杖向嘲骂者们拼命还击了几回,但是最终,在周围万千阿Q们的嘲骂 声中,他还是选择了“呆在家里”,选择了退却。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丝毫无损于鲁迅的形象。他回国后的 第二年在绍兴中学做学监,对于学生剪辫的要求他还进行了劝阻。《病后杂谈之余》中 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这时“学生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有很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 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 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 ,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注:鲁迅:《病后 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卷六,第191~193页。)。鲁迅当然知 道没有辫子好,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辫子的“新党”。但是鉴于自己剪去辫子后所 承受的巨大压力,他还是恳切地劝告自己的学生暂时不要把辫子剪掉,尽管这一片舐犊 的苦心在当时并不为学生所理解甚至被误会为言行不一。根据胡愈之的回忆,那时每逢 圣诞日,鲁迅也会“戴上假辫发,率领学生向万岁牌跪拜”的(注:胡愈之:《我的中 学生时代》,见1931年6月《中学生杂志》第十六号。当时署名“愈之”,“我的中学 生时代”是栏目的名称,同期发表的还有章克标、尤墨君、夏丐尊三人的文章。),难 道我们据此就得出像学生一样的结论,以为鲁迅是言行不一致,并且进而推断出当初鲁 迅的辫子“仿佛也并不是那么爽快的剪掉”的吗?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很多的无奈, 有时迫于周围的压力,人难免要做出一些看似与自己的信念相违的事情,难道我们就因 此而否定他的一切,怀疑他当初的真诚吗?周作人1906年去日本之前在上海剪掉了辫子 ,但那时在上海人家是“分不清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所以大概也不曾遭到嘲骂 。直到1911年5月在鲁迅的亲自督促下他才回国,所以他大约从来没有体会过被人骂作 “假洋鬼子”的屈辱与辛酸。因为“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 来,算是革命了”,而在鲁迅看来,革命带来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却的是我从此 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也听不到什么嘲骂”(注: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卷六,第191~193页。)。作为当时剪辫留学生 中相对幸运的一个,周作人竟对他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视而不见,甚至做出那样不近情 理的推断,其中未免有点隔岸观火的意味。
《阿Q正传》中的钱大公子,留学回国后戴起了假辫子,甚至又重新留起了头发,也实 在有着不可言说的苦衷。因为剪掉了辫子,“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 回井”,家里闹得不可开交……鲁迅当初剪了辫子,虽然在外面遭到辱骂,但在自己家 里,家人还是理解他的,甚至他那位做过封建官僚的祖父也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好。但这 位钱大公子就不同了,他不仅要面对外面阿Q们的侮辱与嘲骂,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内部 母亲和妻子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戴假辫子,甚至又留起了头发,又有什么不 可原谅的呢?难道我们还要跟在阿Q身后鄙夷地骂他“假洋鬼子”吗?相信这绝对不是有 着相同经历的鲁迅所希望看到的。在小说中,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 厌恶的。不管怎么说,这位钱大公子在当时即使算不得时代的精英,至少也应该算是一 位受到过现代思想浸染的新人。真心也好,投机也罢,和阿Q们相比,他更能理解革命 的真谛,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鲁迅的心态是多面的、复杂的,他的敏感多疑已经是学界的 共识。有研究者就曾专门著文指出:“也许因为亲眼目睹的人间的凶险和欺诈太多,以 及身体状况的关系,鲁迅的疑心似乎比常人重得多。”(注:参见杨守森主编:《二十 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绪论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从这样一种性格 特征出发,敏感多疑的鲁迅他会乐意听到人们连续不断地对于“假洋鬼子”的反感和嘲 弄吗?被辱骂为“假洋鬼子”的经历是深深地印在鲁迅心灵深处的一块永远难以愈合的 伤疤。《阿Q正传》之后,面对人们对“假洋鬼子”的肆意讨伐与嘲弄,我想鲁迅除了 苦笑之外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感受了。至于鲁迅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说中用了“假洋鬼子 ”这一自己永远也不想听到的词语,我想这大概是出于一种自嘲和反讽。就像在与创造 社的论战中被斥为“封建余孽”,鲁迅索性就用“封之余”做笔名继续与成仿吾等人论 战一样。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也借N先生之口说道:“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 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 ……”(注: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卷一,第328、330页。)其中的兴奋 自不待言,而一种复仇的快感也流露无疑了。因此,一年之后鲁迅在《阿Q正传》中, 重又对那些当年曾经骂过自己“假洋鬼子”的阿Q们进行讽刺与调侃,也是顺理成章的 。鲁迅是深恶“十年媳妇熬成婆”的中国式的宿命的,这是他所着力批判的国民性的一 部分。1921年,当他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大街上走路,不用担心被骂作“假洋鬼子” 时,他会至此反戈一击,对着当年和自己有着相似境遇的钱大公子或者就是当年的自己 狠狠地戳上一刀吗?因此我以为,当我们揪着鲁迅说他“像一个刘海仙”这句话不放, 并且大张旗鼓地对“假洋鬼子”进行批判时,我们就背离了鲁迅的原意。也许正因如此 ,直到1936年7月鲁迅去世前的3个月,他还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 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注:见1936年7月19日鲁迅致沈西苓信。转引自《鲁迅年 谱》卷四(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鲁迅的这 句话同样适用于周作人对这篇小说所作出的解读。
事实上,这位钱大公子也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同狂人、孔乙己 、魏连殳、陈士诚、高尔础等人并列成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中的一员。同这些已 经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形象相比,“假洋鬼子”自有其独特的一面。他进过洋学堂,并 且赴日本留过学,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洗礼,后来回国后,他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巨大的 压力下,被迫重新留起了辫子。但当革命风暴到来时,他又立刻投身其中了。但是受当 时领导者革命理念的影响,还因为个人之间的矛盾恩怨,他对于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 的革命要求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假洋鬼子”的形象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有着某种普遍意义的。辛亥前后回国的留学生中,有着和“假 洋鬼子”类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在《病后杂谈之余》中鲁迅曾经提及上海有一个专门 装假辫子的专家,“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注:鲁迅:《病后杂谈之 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卷六,第191~193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当时社会上“假洋鬼子”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因此,我们可否这样理解:有着 若干自况意味的“假洋鬼子”形象,其实是鲁迅对自己笔下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群像的一 种丰富和补充。
标签:鲁迅论文; 周作人论文; 阿q正传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阿q精神论文; 头发的故事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