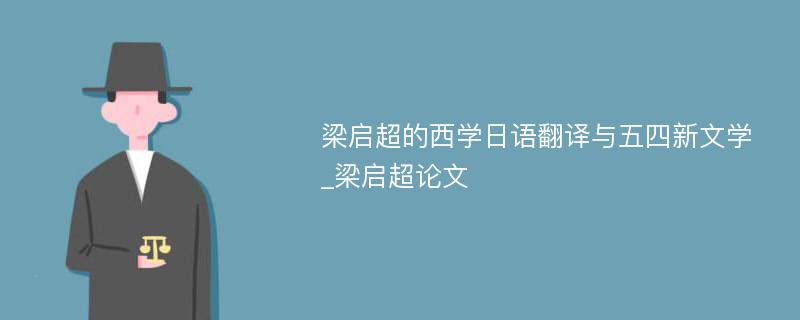
梁启超的日译西学与五四新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四新论文,文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5-0123-05
作为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大碰撞的亲历者和西方思想的传播者,梁启超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以及文学理论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建树。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从事翻译及创作,对于促进中国文学摆脱传统,吸收新鲜血液以至走向世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先导作用。但是,“当梁启超长途跋涉向家返回时……他曾经忍痛到达的反传统思想境地,现在被青年人从他那里作为自然的境地、自由的礼物和迈向未来的出发点接收了过去。”[1](P16)那么,缘何梁启超未能在文学领域内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反倒是受其精神指引的一代“新青年”实现了他毕生未能完成的超越呢?尽管钱基博在1935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将梁启超列入“新文学”一编中;但是,翻译方法的急功近利、文学观念的返归传统,以及中、日、西多种思想的交错杂糅等诸多因素,都严重制约着梁启超的思想观念,使其难以跨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重樊篱,进而实现他引导中国文学顺利转型这一主观愿望。
一、失意之英雄与新文体
在流亡日本的十四年间,为了摄取价值观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梁启超几乎涉足了当时日本各个流派,阅读了大量日文译著,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向国内广泛传播。蒋广学曾这样来形容梁启超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和传播:“如果从梁启超在1895年‘北京强学会’时开始系统接触西学算起,到亡命日本之后又通过大量学习日本人所翻译出来的西人著作,他用数年的功夫就走过了西方人数百年走过的路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中,并且在这儿著书立说。”[2](P402—403)但是,当时梁启超不仅不通西文,对日语语法也不甚了了,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穿越两种文化的坚固“墙体”,向国人传递了如此巨大的异质文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国新小说、历史学、新闻学、法学、政治学和财经等诸多全新的学科体系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并慎重思考的严肃课题。
就翻译和输入西方学说而言,在晚清的数十年时间,只有严复可与梁启超比肩。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较为系统化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启蒙家和翻译家,雄厚扎实的国学功底以及赴英多年的留学经历,不仅使他精通中英语言文字,更是对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有着深刻体悟与了解。钟叔河在《从东方到西方》中曾说:“在梁启超之前到西方去的人当中,容闳留学最久而未志于学,王韬助译汉籍而未译西书,仅仅有郭嵩焘曾经接触希腊先贤和培根、笛卡儿的学说,但只限于个人有所认识,没有进行传布;能够‘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的,的确非梁启超和梁氏一再提到的严复莫属。”[3](P614—615)梁启超也曾打算过学习英语,还有一位士绅愿意出资聘请专业英语老师教习梁启超,但由于学习英语需要充足的时间与精力,而梁启超事务缠身、活动频繁,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而中日文之间所具有的诸多相通处,使梁启超觉得学习日语比学习英语容易。在逃亡日本之前,梁启超撰写《论学习日本文之益》一文,大力倡导国人学习日语,并主张通过日文译著来吸收西学思想。后来,梁启超编写的日语速成教材《和文汉读法》,更使国人学习日语的高潮有增无减。梁启超则运用这种方法译介了大量日文著作和日译西籍。所谓“和文汉读法”,实际上是“汉文训读法”这一日语词汇的翻版,主要是用来阅读日本人汉译的西文著作或用汉文调写作的日文著作,而对难以“颠倒读之”的通俗文体则敬而远之。因为“和文汉读法”的奥妙在于:“通其例而头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4](P324)当时的日文大致分为四种文体:一是仿汉文体,二是和文体,三是欧文直译体,四是俗语俚言体。“和文汉读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平易畅达的仿汉文体,而对于古代日语和现代口语体日语,以及欧文体日语都无法理解。即使是在不太复杂的“汉文体”日语中,也存在很多被异化的汉语词汇,它构成了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的一个重大障碍。所以,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学习日语,只得选择汉学修养深、使用汉文调写作的作家的著作,如福泽谕吉、矢野文雄、德富苏峰、中村正直、柴四郎等人的书,均系受到浓厚汉文影响的日文著作。
福泽谕吉“通俗文体”和矢野文雄“欧文直译体”以及德富苏峰“欧文体汉文脉”的文章,都对梁启超独具一格的文体风格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尤数德富苏峰“以欧文脉入汉文调”的文体对梁启超新文体的创行影响最大。冯自由很早便指出:“任公之文字则大部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日之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一一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材于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5](P254)对德富苏峰文体风格的认同与崇拜,使得梁启超每每情不自禁地抄译德富苏峰之文,并仿效其文体和文风。德富苏峰为文雄奇畅达,如果不对勘日文原著,我们很难分辨出哪些是出自苏峰之手,哪些是出自梁启超原创。梁启超所特有的“新文体”是为了通过日本来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提炼出来的一种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文体形式,虽不如林纾的译笔那样顽艳古雅,也未及严复那样深刻系统,但是相对于桐城古文和同时代林纾、严复等人的文章而言,梁启超的“新文体”有着别样的魅力,与风行于日本的德富苏峰文风一样,他所译介的外国小说和西方近代社会学说,以通畅之文笔、喷薄之情感和雄壮之气势而见长,并以更强烈的吸引力与穿透力极大地影响着近代中国读者的阅读思维。当然,强烈的文化启蒙意识和急切的语言变革需求,以及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趋势,都是梁启超选择通俗易懂的“新文体”来从事写作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历来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那就是“和文汉读法”这一特定的翻译手段,也决定了梁启超必然选择这种平易畅达的表述方式。所以,梁氏的“新文体”与“和文汉读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变革过程中的最早实验品。
诚然,运用这样一种钩而读之的方法确实能使没有多少日语基础的中国人,读懂一些带有汉文调的日文著作,在表面上具有一种迅速掌握词汇意义的速效性,并能对在短时间内学习日语、传播新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学习方式作为一种认识异质文化的粗糙工具,远远不能满足国人迅速增长的西学要求,它从一开始就潜伏着一种巨大危机。从长远意义上来说,这种学习方法讲求的是“速”,但任何事物“欲速则不达”。如果说穿越两种语言文化的坚固墙体,会使译文与原著之间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或误读;那么,像梁启超试图仅凭着“和文汉读法”这样粗浅的阅读方法去穿越中、日、西多种语言的巨大障碍,而获得其思想文化的内在精髓,其间所产生的巨大误差与主观臆说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梁启超本人对于从日译著作中求西学的未来前途,也表现出一种茫然与困惑。他曾坦率地说:“虽然,所译之书,未必彼中之良也。良矣,译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即二者具备,而其书也。率西域十余年以前之旧书,他人所吐弃而不复道者,而吾犹以为瑰宝而珍之,其为西域笑也。”[4](P137)可见,“良”、“真”、“新”是梁启超译介西学所主观追求的最高境界,他主张运用“和文汉读法”去学习日语,意欲建造一座连通中西文化的巴贝尔塔,虽然也曾掀起过中国近代社会“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地憧憬西方文化的巨大浪潮,但由于语言文字的客观障碍和狂飙突进的译介手段,使得在这个不甚牢固的根基之上所建立起的诸多学科体系,也必将如巴贝尔塔一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全面坍塌的危险。从这一角度来看,梁启超只能算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失意英雄。以他的精神探寻为导向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否真如蔡元培和郑振铎所描述的那样,真正秉承着西方近代人文精神的思想精华?中国现代文学“狂飙突进”的三十年,又是否真的能抵得过西方文艺复兴三百年漫长历程?这一切还都是有待于学术界加以科学分析和认真考证的全新课题。
二、梁氏输入法与政治小说
梁启超运用速成的“和文汉读法”引入西方思想,自然免不了因主观误解而导致的客观误用,这不仅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明治日本近现代文化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使他对明治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受与理解受到很大限制,甚至还因为译介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变形”和报刊杂志上这种“急就章”的书写方式,最终发生了以传统去解读西方或用西方来遮蔽传统的荒谬性。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和文汉读法”“可笑之误谬甚多”,在具体的学习译介中难免会“务广而荒”。同时,由于其自身的性格特点,也使其学问有着“常有所得”却“入焉而不深”的致命缺陷。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曾毫不客气地指出,梁启超的译介工作“常常带有一种被称之为‘梁启超式的输入’的浅薄性”[6](P8)。当然,这种译介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形”现象,在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的译介行为中也比比皆是。日本近代文化认为西方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物质高度发达,而物质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就是“尚武”精神,这显然是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误读”与“曲解”,而这种见解又随着梁氏等人的大肆宣传和秋瑾等人的具体实践,直接导致了大批东洋留学生对于日本“尚武”文化的高度认同,并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社会革命的具体方式。对于梁启超而言,政治家的独特身份和思想家的启蒙意识,使得他对日本和西方著作的引用完全是务实性的,于己有用且可以阐明自己思想观点者则引之,于己无用且自己难以理解者则弃之。因之,考察梁氏的文章著述,几乎对于西方近代思想均有所涉猎,却都难成理论体系。这种断章取义式的译介工作,集中体现了近现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急功近利的思想特征。
在梁启超的西洋史传著作中,对传主具有高度自由的选择性,如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还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梁启超的选择视野,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梁氏所推崇备至的“造时势之英雄”。日本学者松尾洋二将这些西洋史传著作与日本原著进行对勘发现,这些史传的绝大部分内容都直接来自于日本明治学者对于西方伟人的主观撰述,梁氏仅出于国内时势需要作了部分的详略变化和些许修改。应该说,繁荣兴旺的日本史传文化,直接催化了梁启超一系列史传作品的最终诞生。同样是受这样一种实用理性与启蒙目的的功利驱使,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翻译和创作的巨大兴趣,也无意之中揭示了梁启超的政治诉求,期望借助西方政治小说的文本形式以实现启蒙民众的目的。历史也总是以某种偶然与巧合的奇妙方式,来反映时代的需求和民族的选择。19世纪70年代,丹羽纯一郎在回日本的船上,读了英国李顿的政治加爱情小说,不仅大受启发并很快将其译成日文,进而在日本掀起了一场翻译和创作政治小说的社会浪潮。明治时期,日本所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小说,有725部之多,到1887至1888这两年间进入全盛时期。二十年后,历史又一次把机遇和选择放到了一条由中国开往日本的轮船上,正是在这艘船上,梁启超第一次读到日本政治小说——柴四郎的《佳人奇遇》,他和丹羽纯一郎一样,深刻地感受到了政治小说所蕴藏着的政治理想和启蒙民众的巨大作用,并将其译文连载于《清议报》创刊号至第35期。在梁启超的带动下,许多政治小说被翻译过来,如《埃及近世史》、《经国美谈》、《政海波澜》、《波兰宪政史》等。早在1898年,梁启超就在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表现出期望借西方政治小说形式以启蒙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在1902年《新小说》第一号《论说》栏中,他笔挟雷霆万钧之势,以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的语句高举“小说界革命”的大旗,借此提出改良小说的口号,从域外文学中选择政治小说作为突破口,并创作了寄寓其政治理想的《新中国未来记》,由此而拉开了中国“小说界革命”的悲壮序幕。
川端康成在评论日本明治文学时曾说:“我总认为,明治以后,随着国家的开化和勃兴,虽然出现了一些大文学家,但许多人在西洋文学的学习和移植上花费了青春和力量,为启蒙事业消耗了半生,而在以东方和日本为基础、进行自我创造方面,却未达到成熟的境地。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7] 日本政治小说的兴起有其特定背景:明治时期,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实际需要,才掀起了翻译和创作政治小说的社会高潮。但是,日本文学在借助政治运动把小说地位提高之后,就与政治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超越政治又紧贴人情世态的所谓“纯文学”道路。至20世纪初,政治小说在日本已如昨日黄花,代之而起的是以二叶亭四迷、坪内逍遥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文学和以森鸥外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可以说,日本在成功吸收外来文学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文学体系。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梁启超从启迪民智和改良社会的政治需要出发,一味强调政治小说的功用价值,却极大地忽略了西方与日本现代小说的艺术审美特性。究其根源,是其思想意识仍无法摆脱“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文化观念。王国维曾批评说,梁启超将学问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做法不足以仿效;而梁氏也坦承,对他来说文学就是手段而非目的,“新民”才是他的终极追求。从改变中国社会落后面貌的政治需求出发,梁氏人为地将小说价值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高度。然而,其文艺思想建构粘滞于政治,这就不是西方的思想而是中国的文化了。他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将小说当作“改良群治”的工具,从长远意义来看,非但不能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反而使其沦为了现实政治的附庸,最终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陷入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只能在启蒙与救亡的夹缝中艰难前行。由于包括鲁迅、胡适、毛泽东等中国现代杰出人物都毫不讳言深受梁氏思想的影响,故自“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小说与现代文学贴近现实、关心政治,几乎成为一种非常时髦的社会风尚。仅仅就此而言,梁启超虽然在其改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具体实践中以失败告终,但其积极主张小说与文学政治化的主观愿望却大获成功。所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或现代文学史,梁启超关于新小说的倡导与实践,都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里程碑。
三、思想之牢笼与新青年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通过阅读日文书籍,广泛地了解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社会背景,从而形成了其思想启蒙的理论体系。但梁启超通过日本所接受的西学知识,往往与其深厚驳杂的国学知识,错综复杂地交缠在一起。从《新民丛报》卷首的图像选择,就集中体现出了这一点,我们既可以看到拿破仑、华盛顿、苏格拉底、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英姿,又还有禅宗六祖慧能、王安石、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邓世昌、谭嗣同等人的身影。由此而见,梁启超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始终呈现出一种亢奋与迷乱、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的思想困惑。曾有国外研究者断言,梁启超的这种情感矛盾“是一种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1](P2)。
循着梁启超徘徊在东西方文化两个世界的精神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梁启超走过了一个由全盘接受到选择吸收,然后逐渐疏离的漫长历程。但是,这一历程又并非总是历时性的有序交替,往往也是共时性的交织和纠缠。在以往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中,人们似乎并未充分注意到这三个异质文化板块的复杂图景。黄克武在《梁启超与康德》一文中指出,梁启超笔下的康德不但有康德、Alfred Fouillée、中江兆民等人的身影,也混杂了英国自由主义、德国国家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有机体论,以及佛家、儒家等思想因素,因而呈现出各种理念交杂、互释的“嵌合”景象。总之,《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对康德中国形象的建构展现出一个高度选择性的视角,他仅仅将他看得懂又感兴趣的部分译介出来罢了,在内容上可以说远不及中江兆民的译文来得完整与深入[8]。笔者在检索梁启超的著作时发现,梁氏所引述的外国人名以日本人名居多,虽然引述的西方人名多达五百余次,但多数都不是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提到的主要代表性人物。这一客观事实充分说明了一个关键性问题:由于巨大的语言障碍,梁启超并未透彻地领会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品性,他对于西方人文精神的大量阐述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言说,其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也就一目了然了。这就是梁启超一直在试图挣扎着超越传统,但又始终无法摆脱传统的阴影,进而成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悲剧所在。
罗素在谈论中国近代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艰难地与儒家的偏见抗争,虽然摆脱了束缚,但难免有孤独感。”[9](P57)梁启超那代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的浸润太深,要想在短时间里穿越几个世纪的时光而成为具有西方人文思想的现代人物,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虚幻梦想。他们不仅要承受来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双重负荷,而且还要承载母体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对抗时所产生的情感痛苦,这其实正是梁启超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从社会政治改良的角度考察,梁启超的“新民”意识虽然产生过强大的历史冲击波,但是他的“新民说”与“少年中国说”的思想基点仍是希望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而不是西方近现代人文精神的全面弘扬。从文学思潮演变的角度考察,梁启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文学改良运动,全面提倡新文体写作和新小说观念,将中国文学带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临界点”,但其所有的文学主张基本上都是对“经世致用”思想的重新阐释与现代包装。我们并不否认梁启超对于中国思想界与文学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实际上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潜在地延续着,而当深受其思想影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带着在海外所接受的西方人文知识现身于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舞台时,昔日的“新民子”只能成为一个被人们所遗忘的“落伍者”。而由他一手发动并领导的一系列文学改良运动,最终却难以进入“新文学”的历史序列。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连续,胡适等人的文化与文学观念虽然超越了梁氏时代的思想观念,同时也承袭着梁氏时代的思想局限。如果我们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则可以发现,从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文学思想中不难看出,梁启超那种以西方遮蔽东方、以现代遮蔽传统、以实用遮蔽审美的文学价值观,尽管被表现得更加隐秘和更加时尚,中国文学传统却被巧妙而合理地继承了下来。当然,我们今天研究梁启超的历史价值与存在意义,并非取决于他与五四新文学的亲和程度与谱系关系,他的价值在于他参与了中国文学转变这一历史事件,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我们认为更深层次的思想含义应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借鉴了梁启超人为地遮蔽传统的做法与技巧,以及梁氏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自励》一诗中,梁启超曾自比为狂泉的赐予者:“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言辞中为自己引介西学的成就颇为得意。但是,他为“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所开辟的道路到底是通向光明还是坠入迷途呢?这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在文学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必须认真反思的一个重要命题。
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晚年的梁启超在走过了漫长的求索之路后,具备了更为长远和开阔的世界性眼光,文化选择的方向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怀疑自己早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热情,完全沉入到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整理之中。十年饮冰室的沉静生活,换来的是累累硕果,完成了一大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成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他的生命愈是向尽头走去,其学术愈闪耀着生命的光彩。如果说他前期的著述可比作奔泻的激流,那么他后期的论著则有如深邃的巨泽。我们知道,在古代汉语中,“反”有“返回”和“反叛”两种解释,到了现代才裂变为“返”和“反”两个字,“反”字下面多加了一个“走”字底。梁启超从最初的反叛传统到最终的返归传统,中间经历了名利场上的起落沉浮,目睹了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体验了人情世故的冷暖沧桑。晚年的沉静并不能使他回到最初的起点,而是通过对明治日本和西方文化的洗刷来超越自我,“走”回到更深的一种传统中去,走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创造研究,所以才能在文学、史学和佛学等各个领域呈现出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此时的饮冰室主人,已不再是当年慷慨激昂的“新民子”,梁启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和再认识,只能在一部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中闪耀其智慧的光芒,并未能引起当时青年一代的思想共鸣,“那种对于他来说是一座冰山仅见尖顶的观念——在它下面埋藏着他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成了青年们的基石。”[1](P16)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中坚力量如鲁迅、胡适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最终也都返回到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其中有些学者还成为了新一代国学大师。而在新时期文学观念复苏期,曾全力倡导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新生代学者,如今也都开始回归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并一度掀起普及和研究国学的热潮。由此可见,梁启超的人生道路与思想历程,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间仍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其日译西学的译介行为以及在中、日、西多种思想中游弋的思想轨迹,对百年后的现代中国依然产生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五四新文学注重思想、讲求功利的美学原则,更与梁启超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便是我们坚定地认为,梁启超应该被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客观理由与科学依据。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日语学习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日语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