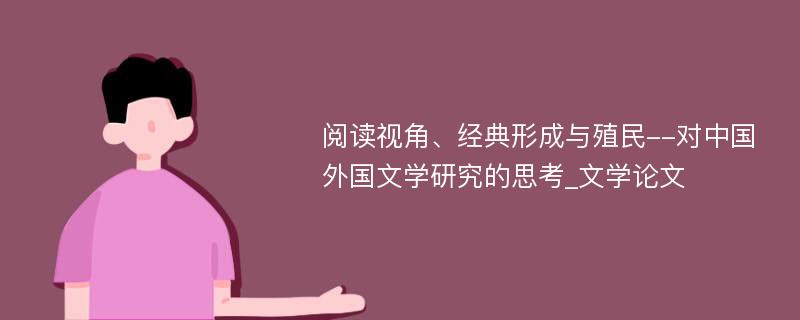
阅读视角、经典形成与非殖民化——关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点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视角论文,与非论文,我国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学理论中,“读者”作为一个核心范畴的异军突起,结束了长期以作者为中心来研究文学的历史。美国文学理论家Jonathan Culler认为, 现代文论界对于读者及其阅读活动的兴趣最早可从关注文本研究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中窥见一些端倪,因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传播了这样一个崭新的文学观念,即文学的意义生成取决于作品的结构模式和符号之间的差别关系,要了解文本结构和符号的意义生成过程, 文学研究必须对读者和阅读者作深入的研究(注: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32.)。 当代西方文论中尤其关注读者及阅读活动的批评流派要算读者反应理论了。这个批评流派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文学作品是作用于读者理解力的一系列语言行为,对一部作品的阐释便是对读者反应的描述,对一部作品意义的叙述便是对阅读过程的叙述。Umberto Eco认为, 在文学的全过程中,阅读在读者构建作品意义的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不仅参与构建意义,而且是文本意义的直接创造者(注:Umberto Eco,The Role of the Reader: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读者反应理论在把阅读活动抬高到创造作品意义高度的同时对读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批评家为了给读者具体定位而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标准读者,如 StanleyFish在他的著述中将“informed reader ”作为自己的读者原型(注:Stanley Fish,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Cambridge:Harv ardUniversity Press,1980,p.49.);Walter Slatoff 则提出要把“actual reader”作为研究对象(注:Walter Slatoff,With Respectto Readers:Dimensions of Literary Respons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p.54.)。
60年代盛极一时的读者反应理论无疑在形式主义批评之外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然而,到70年代,这一理论关于理想读者的假想定位引出许多质疑,关于读者的研究随之亦步入两难。较早将阅读活动从这一两难中解脱出来的是在解构主义理论召唤下出现的一系列反形式主义的批评潮流。女权主义与美国黑人诗学首先对所谓“informed reader ”的神话发起挑战,指出女性与美国黑人作为阅读主体所持有的独特视角。此后,以Edward Said 为代表的东方批评家从不平衡的东西文化关系角度对传统阅读活动进行解构;以Eve Sedgewick和Judith Butler为代表的“怪异”(Queer )理论家则从同性恋视角对读者反应理论中的所谓理想读者进行了新的否定。可以说,在读者反应批评之后,这些建立在不同阅读视角基础上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阅读和批评的理解。
从女权主义到“怪异”理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演进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作为文学意义的构建者和创造者的读者其阅读活动远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种非政治的纯审美活动,阅读活动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如果说女权主义和“怪异”理论揭示了阅读活动中的性别政治,那么,以美国黑人诗学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话语则揭示了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读者在阅读中的种族政治。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文学阅读的文化政治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直接影响下受到日益重视,于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于文学意义建构中的文化政治在近来的西方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以阅读政治为核心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人们把后殖民主义、少数民族话语和性别研究统称为“文化研究”。的确,前述三个批评流派在各自的文学阅读过程中往往不仅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对几个文学文本的解读,相反,它们常常超越文学,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进行更广泛的文化考察。虽然相比之下少数民族话语和性别研究对于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对同一文化内部的不同话语的解读,而后殖民主义理论更多地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话语研究,但它们在考察形形色色的文化话语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独特视角,同样关注各自的“文化身份”。
带着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全面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化话语,已成了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许多流派从传统的文化边缘出发努力开拓由自身独特的视角建构起的全新批评空间,给传统的文学评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化研究”强调,一个文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认同什么样的“文化身份”。例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对于同一个文本,一个前殖民地读者立足后殖民视角会建构出有悖于一个传统帝国读者立场的新意义,一个少数民族读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会读出一个社会主流读者读不出的意蕴。 著名文学评论家StephenGreenblatt指出,一个从文化上认同被压迫者的加勒比海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时,绝不会自动认同殖民者Prospero的立场,而会自觉地站在被殖民者Caliban 的位置上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行径进行谴责(注:Stephen Greenblatt,"Culture",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eds.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 Chicago&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231—232.);Edward Said也认为, 一个澳大利亚读者面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对自己国家的贬抑,不会自然而然地认同19世纪的英国政治和法律,相反,他会站在被流放者 Megwitch 的立场对英帝国表示鄙夷(注:Edward Said,"Introduction",Culture and Imperialism,London:Chatto & Windus Ltd,1993,pp.xv-xvii.);Terry Eagleton亦指出, 凡是渴望民权的美国黑人在阅读美国新批评家Allen Tate 和
John
CroweRansom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为南北战争后南方传统等级社会的崩溃唱出的挽歌时都不免感到愤慨(注: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inn 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46—49.)。
阅读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然而,每一次的阅读活动都是一个具体的过程,阅读者在每一次具体的阅读过程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是真实而时刻存在的,它存在于同一文化内部的阅读活动中,同时也存在于跨文化条件下的文学接受活动当中。关于同一文化内部阅读过程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人们在女权主义批评和性别研究中不难体会,关于跨文化关系中的阅读活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其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也有许多的论述,不过此二者都不是本文所要直接讨论的对象。本文更关心的是中国读者在阅读英语文学时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一个中国读者在阅读英语文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文化身份”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先后撰文对此进行了多方讨论。例如,高一虹在一篇题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依附矛盾》的文章中较早地指出,一个中国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会碰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注:高一虹:《我国英语教师的文化依附矛盾》,胡文仲主编:《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535—546页。)。王宁的《在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一文进一步证实,中国大学英文系文学教师在教授英语文学时会面对难以回避的“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注: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如果“文化身份”的认同在中国读者阅读西方文学的过程中是个实在的问题,那么,“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对于中国读者阅读西方文学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文学批评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课题——即文学经典的形成问题。
二
前文谈到阅读的视角和形式,一个与阅读视角和形式有着密切关系的话题是阅读的内容,文学研究不仅探讨如何阅读,更要考察阅读什么。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学理论告诉我们,作为阅读对象的文学经典,其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它的背后往往有着多种超文学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在早期的英国文学中,文艺复兴后出现的经典背后涌动着一个民族从被征服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时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7世纪中叶,由Samuel Johnson等人推出的英国文学经典的背后有着试图规范民族语言的实际考虑;18世纪以后英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学经典形成无时无地不受到来自文学外因素的影响。Terry Eagleton在其《文学理论导论》一书的首章中明确提出,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在每一个时代都打上了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烙印,他认为,在英国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中,文学曾先后被用来弥合社会裂痕、教化新兴的中产阶级、替代宗教而成为道德感化的工具,在帝国扩张中被用作同化殖民地民族的文化行李等等(注: Terry
Eagleton,"The Rise of English",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pp.17—53.)。
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选择和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文学作品随着岁月的流逝销声匿迹,而另一些作品则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代表民族文学最高成就的经典。那么,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创作中,什么样的作品通常能够成为文学经典呢?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批评界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入选经典是因为它有着无可辩驳伟大特征;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一个文学传统是由掌握着文学裁决权的某一社会群体通过密谋炒作而形成的。细想起来,前一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一部作品“伟大”与否需要有个标准,而任何标准都是站在某一特定的立场上的人所拟定的,文学中没有一种先验的绝对价值裁判庭。相比之下,第二种看法对于我们认识不同阅读群体间所作出文学价值判断的政治权利内涵有着相当深刻的意义,但是,它未能对同一群体内部出现的不同判断标准作出解释。美国评论家John Guillory 在他的《文化资本》一书中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经典形成理论。他认为,我们在讨论文学传统的形成时单纯讨论文学价值判断是无益的,虽然植根于社会和个人心理的价值判断行为是经典选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研究经典形成不应只局限于考察这些价值判断行为,因为事实上某些社会群体和特定的个人判断对于保存文学作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Guillory指出,经典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判断发生的社会大环境,因为文学的判断发生作用的前提是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通过大量印刷和复制,将判断结果向全社会广泛传播开来(注:John Guillory,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Chicago:Chicago UP .1993,p.vii.)。按照他的看法, 文学经典的形成常常与学校有着深刻的关系。人类自有文字以后,学校是传播知识的主要场所,学校最早为了满足特定的教育需要和达到特定的教育效果不断地筛选和使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作为传播知识技能的重要手段因而得以在学校教育中也得到传播。Guillory认为,文学在学校里找到了自己强有力的传播地,至于什么样的作品能在这里得以保存并成为广为人知的经典,学校的课程设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校的课程设置赋予它多少“文化资本值”(注:John Guillory,Cultural Capital: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Chicago:Chicago UP.1993,p.vii.)。
Roland Barthes 曾经戏谑地说:Literature is what getstaught in schools。Guillory 对于学校在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的认识与Barthes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应该说, 在当代西方理论界、尤其是英语世界,这样的认识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共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英美两国相继出现一批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权主义和黑人文学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在充分认识到学校在经典形成中的影响之后向传统文学经典提出了挑战,他们主张开放大学文学课程设置,吸纳那些素来为正统文学批评所不屑的文本以拓展传统经典的范围。到80年代末,英美大学在女权主义和少数民族话语的影响下进行的开放文学经典的运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90年代,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成了英美理论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此时,新旧势力围绕文学经典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锋和辩论。代表社会左翼势力拓展传统文学经典的努力在历经十余年之后受到了来自保守势力的非议,一批著名的英美批评家在各自的著述中对女权主义和少数民族话语推行的开放传统文学经典的运动提出了批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大概要算美国批评家Harold Bloom了。1994年,Bloom 出版了他的《西方经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在此书中, 他明确表示自己反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少数民族话语(Bloom称他们为“ school ofresentment”)关于开放经典的要求,在他看来,文学经典是一些不为政治、道德和社会因素所动的一组作品,他认为,经典本来就是讲究精英而且有所分别和歧视的,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注:AndrewBennett & Nicholas
Royle, "Monuments", Introduction
toLiterature,Criticism and Theory ( 2nd edition ) , London:Prentice Hall,1995,pp.50—53.)。《西方经典》一书为西方文学开列了一个由三千部名著组成的经典,并以莎士比亚作为这一系列经典的核心。
Bloom的经典理论与近半个世纪以前F.R.Leavis 在其《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一书中的经典立场是一致的,但他与John Guillory 等人对文学经典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二者一个主张经典的必然性,另一个强调经典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影响,互不相让。笔者认为,如果暂且不论这两种立场的最终是非,Guillory关于学校等社会机构影响经典形成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从Bloom 这样的批评界权威常常可以直接干预学校课程设置的情形看,文学批评界在学校形成和传播文学经典的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换句话说,代表某一社会群体利益和视角的个别批评家往往成了学校课程设置的“幕后黑手”。由于决定哪些文学批评家有机会直接插手学校课程设置不在批评家自己,而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诸因素的走向和潮流,所以,应该说,在每一个文学经典形成的背后,所有这些因素与批评家以及学校一起联手作业,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取舍和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
三
在文学研究中采用怎样的阅读视角以及确立什么样的经典是许多文学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跨文化文学接受中,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接受者接受文学的态度,同时也决定了接受的方式和结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个问题在跨文化情形下的表现形式,人们不妨就跨文化情形中的文学接受活动作两个简单的假想。我们先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即某甲文化中的一群读者从未接触过在势力上与自己完全对等的乙文化的文学创作,若是在这样一种绝对对等的“零接触”的状态下突然开始阅读乙文化的文学,甲文化中的读者常常可以从容面对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我们再设想,甲乙两种文化一弱一强,甲文化中的读者对于乙文化的接触若是迫于居强势地位的乙文化对自身赢弱文化的巨大压力,那么,作为弱势文化成员的读者关于读什么和怎样读的选择则常常不由自主地随着文化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在这两种假想中,关于甲乙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绝对“零接触”状态的假想并不存在,因为跨文化接触永远发生在具体的不同文化之间,一个文化的成员在接触另一文化的文学时总不可避免地带上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赋予他的特有眼光,一个文化的成员在面对另一种文化中的文学时必须透过这种眼光来决定自己读什么和怎样读。因此,第二种假想所描述的跨文化文学接受的情形更加真实可信。
在两个不对等的文化之间,弱势文化成员在开始接受强势文化的文学艺术时常常不可避免地会处于两难境地。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早期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列强文学的阅读和接受。20世纪初,中国文化人围绕如何看待西方文学和译介哪些文学作品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争。作为辩论一方的鲁迅站在一个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人立场,有意避开列强文学而将自己的译介视野投向了一些与中国有类似经历的被压迫民族文学,努力通过自己的翻译向国人介绍了不少东欧国家的作家作品。作为论争另一方的林语堂对此大为不满,他指责鲁迅“今日介绍波兰诗人,明日介绍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对此,鲁迅不以为然地写道:“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茄门’,而不知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的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到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注:鲁迅:《题未定草(三)》,白冰编:《鲁迅全集》,甘肃民族出版社,第215、216页。)
应该说,五四时期的鲁林之争除因两个文化人意见相左外,还表现了当时中国读者在面对西方文学时的矛盾心态。他们一个将历史和民族尊严融入文学跨文化的阅读活动之中,因而拒绝仅仅因为西方列强的强大而自动地拜服于其文学;另一个则因西方文明的“先进”而对西方列强文学表示自动的认同。这两种态度的共时存在反映了处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国读者在面对列强文学时普遍存在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种矛盾心态更清楚地得以显现。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干预,外国文学的接受和研究开始偏左,至“文化大革命”,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的译介工作几乎完全中断,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多局限于亚非拉文学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8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在短短十年多的时间里,西方文学与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一举占领外国文学研究的主阵地,一时间,我国读者对曾受普遍排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英、美、法、德的无数古典和现代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前几十年中国读者对列强文学所持的警觉和矜持全然消失。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力日益强盛,民族自信心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学者开始对前十年我国学界盲目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学的作法进行批判,许多人提出要在学术界建立自己的民族话语,以便在文化领域同西方列强展开新的对抗。
1994年,四川学者易丹发表《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一文,对外国文学研究现状表示担忧(注:易丹:《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他认为, 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自身文化立场不明确”的问题,在对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学的接受中,中国读者“缺乏独立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缺乏主动的批判精神”,对西方文学一味地认同和追随,以致把自己变成了西方殖民帝国文化的传播者和推销者。中国读者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曾经侵略过中国的西方列强的文学,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在半个世纪中一度经历了从全盘排斥到全部认同的摇摆。直到20世纪90年代,起源于殖民时代的这两种西方文学接受态度似乎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说新对抗论部分地继承了“排斥主义”的衣钵,那么,易丹所批判的“推销主义”无疑是“全面认同主义”的直接传承。当然,继我国改革开放结束了数十年的闭关自守之后,90年代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再有“文革”中那种非理性地排斥西方的现象,然而,那种“言必称西方”的自动认同者却大有人在。所以,对此现状表示忧虑是不无道理的。易丹的意见一方面与“五四”前后鲁迅先生的外国文学研究立场相呼应,另一方面与世界范围内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思潮相同步。这种担忧提醒人们,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界仍然面对着近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学界提出的那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即中国读者应以怎样的文化身份去阅读和接受西方文学?
怎样才能摆脱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困境呢?易丹的看法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注:参与商榷的文章有黄宝生:《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张弘:《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赵炎秋:《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吴元迈:《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分别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第4期,1995年第2期、第4期。),原因是他使用了“殖民”一词来形容我国外国文学界在面对西方文学时所表现出的无条件认同心态,以至将我国的部分外国文学工作者称作西方文学的“买办”或义务“推销”人。因而,他从殖民心态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反思并未受到同行的认可,而且他援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亦远没有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严格说来始于20世纪70年代,Edward Said 是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 近二十年来, 以 Said 、Gayatri Spivak、Homi Bhaba为代表的一批旅居西方的东方学者从他们特有的文化立场出发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后殖民主义从斯本格勒的“西方衰落”论中获得思想灵感,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找到了解构的阅读方法,从福柯的话语分析中获得了对于文本政治和话语权利的认识,从巴赫金的对话哲学中找到了理论支持,在所有这些激进理论的综合中,后殖民主义建构起的是一种强烈要求挑战中心、解构帝国主义话语和揭穿殖民神话的颠覆性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 这种反话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立足前被殖民国家和民族、对历经几个世纪的西方殖民过程进行考察,以生活在殖民帝国边缘者的全新阅读视角重读和解构几百年来从帝国立场出发编织的殖民话语,从中寻求启动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非殖民化进程。后殖民主义理论于90年代初传入中国,然而,从它一开始传入我国,我国学者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就表现得颇为谨慎(例如,王宁在他介绍后殖民主义的一系列论文中对Said等东方学者身处西方学界的文化立场表示怀疑(注: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 期。 ); 张隆溪对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提出质疑,他针对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有关西方文学中的“东方主义”现象,指出中国文学中同样存在着“西方主义”的内容(注: Zhang Longxi,"Western Theory and Chinese Reality",Criti cal Inquiry,Autumn,1992,pp.105—130.)。与此同时, 也有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把“东方”一语“蛮拧麻花”式地提炼出来,把它当作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东方文化和推动新一轮中国国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因此,即便有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提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摆脱殖民文化困境从而实现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非殖民化”的呼吁,但其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四
同易丹一样,中国旅居澳大利亚作家欧阳昱也认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大体上尚未走出一种历久形成的“殖民心态”,这种心态最集中地表现为在对待不同国别文学中仍存在严重的厚此薄彼的现象。为说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建构的外国文学经典作一个初步的考察。自1980年到1994年,我国先后出版的各类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作品导读的书籍不下数十种,在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大学外国文学教程。从总体上说,各类外国文学史每每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起始点统一叙述一个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文学、近现代欧美文学、俄苏文学和亚非拉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故事,在这些文学史中,庞杂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被清理简化成一个以西方列强文学为主线、以东欧和亚非拉文学为点缀的文学体系。在这高度压缩的体系框架内,有一个异常相似的外国文学经典书目,其中,古希腊罗马文学(埃斯库鲁斯)、英国文学(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斯、哈代)、美国文学(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法国文学(莫泊桑、巴尔扎克、左拉、普鲁斯特)和德国文学(歌德、托马斯·曼)构成了这一经典的欧美文学主线,亚洲文学中略提一提印度、日本和朝鲜,非洲文学说一说肯尼亚和尼日利亚,拉丁美洲介绍一下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等,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
二十年来,这一个外国文学经典体系通过大学课堂教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广大读者中,业已变成根深蒂固的认识。但是,必须指出,我们建构的这样一个外国文学经典从总体上看至少存在三方面的明显缺陷。第一、这一经典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第一和第三世界文学,在“简明”、“简编”的名目下明显冷落了第二世界(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文学。第二、即便是在反映第一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同时,又明确地将重点放在欧美文学上,围绕这些西方大国的文学,一方面希腊文学被永恒地定格在古希腊神话和亚里斯多德的悲剧时代(仿佛希腊不存在现代文学),另一方面,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学亦在轻描淡写中被一笔带过。第三、让这样一个以西方诸国文学为核心的文学经典体系在读者中广泛传播,使人先入为主地以为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天然地高于其他国家的文学。
从这样的外国文学经典建构中,不难看出,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尽管想在当年鲁迅和林语堂的分歧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但是,历史的沉重积淀总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偏向一边,不论我们多么想努力地保持平衡,但在一种难以摆脱的殖民心态的困扰下,却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到追随西方大国文学的路线上来。
正如易丹所说,我国早期接触和研究外国文学是出于对世界知识的主动渴求,带着那样的意图,我们本该用文学的而不是用政治、意识形态或其它文学以外的眼睛向世界文学伸出我们的触须去探察和发现世界文学的精华,然而,至今为止,我们为自己建构的外国文学经典所反映的一个突出倾向却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学的全面接受,尤其是对英美文学的积极认同。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英美文学有着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英美文学可谓独领风骚,在许多中国读者看来,英美文学代表着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英语文化的精华。英美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致有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的原因,二是与我国学校外国文学教学有关。在中国近代史上,闭关锁国的生存方式最先被英国人打破,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英国人长期割占着我们的领土,以世界头号强国的身份把自己的文学当作帝国的文化行李带到中国进行广为传播。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美国因其在中国的政治存在,给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此外,20世纪初以来,我国的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开始设立英文课程和英文专业,在大学的外语教学中,英文始终是我国外语教学中最主要的语种和专业,在这样的体制下,英美文学通过学校的课堂教学得以迅速和广泛的传播。换句话说,我国的英语教育为英美文学在我国现行外国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谋得如此突出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毋庸讳言,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确是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传统。自19世纪以来,它们为英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确立了很高的地位,也因此使不少人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力,不知不觉中,他们被一种殖民心态禁锢了起来,对这两国文学就只剩下完全的认同。
英美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历史迄今已逾百年,经历了这漫长的接触和研究,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出于对英美文学的景仰,在说起世界英语文学时每每将英美两国文学简单地等同于英语文学。出版一部英美诗选,选编者将书名定为《英语名诗欣赏》(国际图书出版公司,1999);一个收录古今英美文学名著的光碟被堂而皇之地冠以“英语文学经典”和“英文世界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我们知道,若从历史上说,英国文学是世界英语文学的源头,特别是在近两个世纪,英美两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英语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开拓者的作用。然而,在当今的英语世界,“言必称英美”式地把英语文学简单地等同于英美文学似乎不妥。这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英语文学飞速发展,内部结构出现了重要的变化。50年代以后随着英帝国的全球影响日趋衰微,英国一改昔日世界头号殖民帝国姿态而将自己重新定位为英联邦普通一员,先后独立的众多原英国殖民地在美国文学的感召下纷纷树起民族文学的旗帜,在短短半个世纪中,这些后殖民国家的英语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它们的出现,传统的英国中心主义被逐渐打破,世界英语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新局面。特别是60年代以后,崛起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加勒比海国家、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印度等地英语文学呈现出一派生机,一大批英国以外的英联邦国家的作家脱颖而出,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在后殖民土壤中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仅连续在英美两国夺得大奖,而且在世界文学大奖的角逐中屡获成功。如今的后殖民英语文学可谓与英美两国文学并驾齐驱,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今英语文学的崭新发展格局。然而,遗憾的是,对于20世纪世界英语文学的多元发展,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在意,仍然一味地沉湎于英美这两个大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对于一些后殖民小国的文学,极少理会,或者不愿问津,新时代世界英语文学的发展还远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五
我国当今学界的重要话题是英语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但是,由于绝大部分中国读者长期只接触到英美两国文化,所以对他们来说,学界所谓的英语文化常常仍等同于英美文化。面对这种情形,中国的英语文学研究界的重要使命就是努力拓展我国读者的英语文学视野,帮助他们全面了解世界英语文化。要做到这一点,研究界必须首先拓展我们在英语文学研究中的视野,打破传统英语文学研究的固有格局,以开放而不盲从的心态去面对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也许没有英美两国辉煌的帝国历史,但是它们却有着与我们一样受人欺压凌辱的经历,在接受英美两国文学的同时去阅读和研究它们的文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英语文学的最新发展方向和成就,而且可以使我们从这些后殖民国家的民族崛起中感受和学习他们摆脱殖民困境、努力重建民族自信的决心。
当然,摆脱殖民困境的任务不仅落在我国英语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身上。更广泛地说,它是我们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使命。在这个后殖民主义的时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克服在阅读外国文学过程中因文化身份而引发的矛盾,如何克服对某些西方国家文学的盲目崇拜,这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我以为,应该首先对我国外国文学阅读视角和我们到目前为止业已形成的外国文学经典进行全面的非殖民化的反思,与此同时,还必须在放眼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础上拓展甚至重建我们的外国文学经典。只有这样,作为世界文化精华的各国文学才会向中国读者展示出更加绚丽多姿的画卷。
标签:文学论文; 后殖民主义论文; 外国文学研究论文; 跨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读者论文; 易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