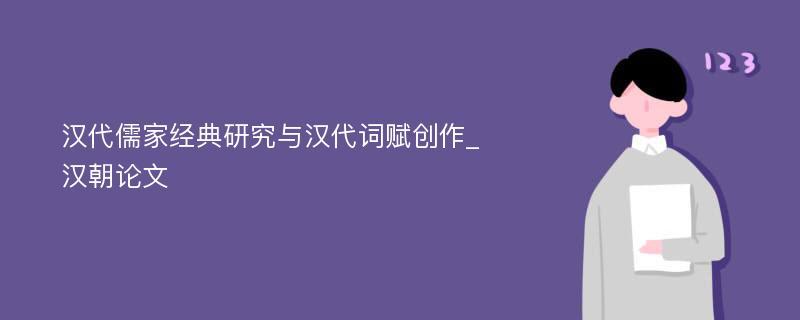
汉代经学与汉代辞赋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辞赋论文,经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9)04-0058-06
作为汉代文学代表性体裁的汉代辞赋创作,必然受到汉代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确定儒家思想为汉代正统的统治思想,以至于衍化出汉代三百多年的经学发展历史,就是此后汉代士人们(包括辞赋作家)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汉赋(指汉大赋)的兴盛,就与武、宣朝的“崇礼官,考文章”,“兴废继绝,润色鸿业”①有着直接的关系。准此作更深层的思考,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与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汉代辞赋家通过辞赋表达出怎样的政治理念,以及与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有无关系;汉代经学又怎样影响到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修养的思考,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将汉代经学分为西汉的“经学昌明时代”和东汉的“经学极盛时代”,这是纯粹历史层面上的分法。就汉代经学运动本身而言,分为三段更切合汉代经学发展的实际,这就是:从秦汉之际到武帝时,这是儒家经学登上历史舞台的预备期;从武帝到东汉章帝时期,这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建立并不断发展的时期;章帝以后直至汉末,这是古文经学渐盛、今文经学衰落、经学走向融合会通、乃至整个汉代经学衰微的时期。从汉代经学的运动过程来反观汉代辞赋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辞赋的创作与经学运动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武帝之前的汉代,作为先秦重要学派的儒家虽然被逐渐的认可和受到重视,但其他如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也同样在朝野广泛流传并产生影响,甚至如从道家衍化出的黄老之学还曾一度成为汉廷的统治思想。受此多元思想文化的影响,该时段的辞赋创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首先受楚辞的强势影响,许多辞赋采用了骚体的形式,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司马相如《长门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刘彻《李夫人赋》,以及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等,都可以说写得情文俱佳。再从辞赋作品的思想内涵看,《鵩鸟赋》无疑流露出道家思想,就是枚乘《七发》的“要言妙道”,应该说也有道家的影子。贾谊的《旱云赋》则表现出儒家仁政的主张。而东方朔的《答客难》则明显受到了纵横家的影响。另外,此段辞赋作品内容多为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其中士人的作品又较多为不受重用之感,表现出相当的真切性,这固然与楚辞的流风余韵有关,更重要的是,此阶段的士人既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即积极向王朝靠拢,又有与王朝相对疏离从而表现出相对独立自主意识的一面。而这一切所形成的原因,都与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的思想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的“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的“置五经博士”,建元六年(前135)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对策,元朔五年(前124)为博士置弟子员等等举措,使得重儒的风气笼罩朝野,儒家思想(当然是被改造后的)成为王朝的统治思想。尽管武帝施政是“内法外儒”,“王霸之道,杂而用之”,但儒家所固有的“缘饰”功用却受到了武帝的格外垂青和利用,于是催生了“劝百而讽一”的汉代游猎京都大赋,并作为汉代辞赋创作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东汉的中后期。著名的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班固《两都赋》以及张衡《二京赋》等。上述大赋创作的具体背景不同,所要表现的具体主旨也不尽相同,而“劝百讽一”的基本模式是相同的。之所以会出现延续时间如此之久、数量如此之多、分量如此之重的游猎京都大赋的创作,除了大赋本身因袭模仿的因素外,此期间浓重的经学氛围,应该是更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这种创作状况与前一阶段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再作一点具体的考察,还可以发现此阶段游猎京都大赋与经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班固《两都赋》末附有五首诗:《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赋后附诗,荀卿《赋篇》为其源头,班固是最早的承继者。班固为什么偏选这种方式且又专选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为吟咏对象呢?“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祭礼、庆赏、选士等活动都在明堂举行。《明堂诗》的内容为颂扬尊天敬祖,又特别歌颂光武帝配享列宗列祖。“辟雍”是古代天子的学校名。《辟雍诗》的内容与宣扬教育有关,而核心是“孝友光明”。据《尔雅》:“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灵台”,周代的台名。《灵台诗》写皇帝登灵台乞求天的福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从而实现“屡丰年”。班固选取明堂、辟雍、灵台作为吟咏对象,固然与崇尚古礼有关,而且更是为了配合现实政治的需要。请看,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刘歆治明堂、辟雍,著《三统历谱》。②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③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④联系上述史实,博览群书的班固特意选中明堂、辟雍、灵台为对象,通过赋末附诗的方式,以强化赋的义蕴的企图就很可以理解了。后面的“宝鼎”、“白雉”二诗,与现实联系就更紧密了。《东观汉纪》: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庐江太守献宝鼎。⑤《后汉书》: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⑥宝鼎也好,白雉也好,都属于祥瑞福应,正是班固生活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光武帝信谶,明帝、章帝更是推波助澜,《两都赋》的两首诗用谶纬来歌颂当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综合看五首诗的含义,所宣扬的是尊天、敬祖、孝悌、教化,再加之谶纬类的祥瑞福应,不正是经学所津津乐道的儒家的“正道”吗?汉代经学对汉代京都大赋创作影响之大、之深,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以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讲论五经异同作为标志,汉代经学逐渐进入古文经争立、今文渐衰、今古文融通的时期,那么,由此而至汉末,以两次“党锢”对士人的圈禁、太学的颓败、典籍的散佚、经生的云散为突出表现,曾经是如日中天的汉代经学也就伴随东汉王朝的倾覆而衰落了。就这一时段的经学历史而言,古文经学的成就是不应该被漠视的。尽管古文经的争立同样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但由于古文经学所固有的多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的客观解释和清理,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等特征在起作用,所以和今文经学炽烈的时期相比,汉武帝所看重的儒家经学的“缘饰”功用明显减弱了,古文经学的“尚实”风尚一定程度促成了传统儒家精神的回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此段辞赋的创作。回味这一阶段的汉代辞赋创作,与前段相比我们发现了不少变化。概括说:(一)自汉武帝起到东汉中前期,曾经一度辉煌的游猎京都大赋,只在顺帝时张衡创作了《二京赋》,此后便成为绝响,而且,细觅《二京赋》的宗旨,无论表现出的批判意识和对“礼制”的推崇和追慕,与班固的《两都赋》都有明显的不同(后详论);(二)总结个人出处,思考人生真谛,愤世嫉俗,甚或抒发个人愤懑不平之气的辞赋作品相继出现了(如张衡《思玄赋》、崔寔《答讥》、赵壹《刺世疾邪赋》、蔡邕《述行赋》等);(三)辞赋作家开始较多关心身边的物、景,出现了托物言志、写景抒情的作品,如此时期相当多的咏物赋的创作、张衡《归田赋》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四)写男女两性之情、其中特别是写女性题材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如蔡邕《青衣赋》、《协和婚赋》等;(五)游戏成分很重的流露闲情逸志的作品也出现了,如王延寿《王孙赋》、蔡邕《短人赋》等。
从贾谊写《吊屈原赋》起,沿着汉代辞赋创作的先后顺序一路阅读下来,我的感觉是,前期赋作所表现出的情、志,显得真切、自然、甚或还有一点楚辞遗韵的灵动之感;中期赋作则渐趋板正平实,虽大气有余而真切不足,特别是大赋的制作更是如此;后期又逐渐一定程度地回复了前期真切、自然的一面,但已经少有了前期的灵动的韵味了。当然,汉代辞赋的发展运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就某一个具体作家而言未必都与上述的感觉相切合,但就总体的大趋势而言,上述感觉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汉代辞赋创作所表现出的这种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有内在联系,辞赋创作的发展趋向与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向,基本上相一致。
政治与汉代辞赋创作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汉代的经学又何尝不是汉代政治的产物。但就汉代的士人而言,所追求的普遍道路是“读经”——“从仕”,因此,汉代士人与政治、汉代士人与经学,在这种双重关系的纠葛当中,他们政治理念的建立,以及由个人出处为契机而生发出的人格精神的思考,就与经学有了更深层的联系。这在他们的辞赋作品中有充分的表现。
汉代的经学,说到底是以政治需求为内动力,对先秦几部儒家经典(主要是“五经”)进行新的训解和阐释,及由此而生发出的文化现象。无论今文经学,也无论古文经学,都受到汉代被强化了的天人关系、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只不过今文经学表现得更为突出,其极致就是西汉末东汉初出现的经学的谶纬化。汉代经学的这种特点,一定程度影响及汉代辞赋的创作,如我们前所举班固《两都赋》对福瑞感应的歌颂,即属此类。还要说明的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有所不同,如拿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作比较,后者明显模仿前者。但《两都赋》强调的是尊“法度”,写汉光武帝是“案六经而校德”,“宪章稽古”,是“觐明堂,临辟雍”、“蹈德咏仁”;而《二京赋》所强调的是“礼制”,开宗明义就批评凭虚公子是“有胸而无心,不能节之以礼”,且对礼制内容的描写详备而突出。我们联系张衡疾“虚妄”、批谶纬的主张,再联系自西汉末刘歆争立古文经,强调礼制的重建以强化君权,以至于东汉前期古文经的再次争立,还是能看出今、古文经学的不同主张在辞赋创作中的潜在影响。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更主要的方面是无论今文经学,也无论古文经学,其对先秦传统儒家思想内核,如尊君一统、民本德政、礼乐教化、典章制度,乃至修身养性、孝悌节气等的承继和发挥却是一致的。今、古文经学所共同倡导的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汉代辞赋创作中则有更突出的表现,其中又以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东汉贾谊为代表。
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子虚赋》、《上林赋》),是汉代辞赋创作的转折点,是汉大赋的奠基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它固然是“润色鸿业”的产物,但又体现出作家的理性思考,从而表现出政治上的见解。《子虚赋》为抑诸侯而作,“奢言淫乐而显奢侈”(《子虚赋》语);而《上林赋》则突显出修王道,行仁政,倡礼乐,施教化的思想。所谓“游于六艺之圃,驰骛乎仁义之途”,所谓“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所谓“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所谓“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等,无一不都是儒家的政治主张。据考证,《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建元元年(前140)“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联系这样的背景,再看《上林赋》的这些政治主张,不仅看到了时代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看到了天才辞赋家司马相如捕捉时代气息的敏感。
扬雄是西汉后期大赋的写家,《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为其代表作。如果说《甘泉赋》的喻义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后三篇赋,其表现出的儒家政治主张就非常清楚了。《河东赋》写汉成帝过黄河祭祀后土后,又登西岳华山泛览三代遗迹。赋的落脚处是“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希望大汉超越“三代”,“以函夏之大汉兮,彼何曾足有比功”。怎样做才能超越“三代”,有一句关键的话说:“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这句话直译是敦促众神指示前进的道路,奋力用六经来抒发对王朝的歌颂。而颜师古注:“颂读曰‘容’。”“言发其(指六经)志而为歌颂也”。⑦认为暗含有汉代遵循六经治国,歌颂以六经治国后出现的繁盛景象。我认为颜氏的理解更切合作者的本意。在辞赋中提出以六经治国,更可以看出汉代经学对辞赋创作影响的深入了。《羽猎赋》讽谏意味很浓,“聊因《校猎赋》以讽”。虽同为田猎,但大汉的田猎是“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以为期”,开宗明义,就为该赋定下了基调。在极尽夸饰之后,表示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即以云梦、孟渚之田猎为奢侈,以章华之台为非是,而应该是“辍游观”,废土木之功而劝民农桑,是“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强调的是以农为业,以民为本,行礼乐教化。这仍然是儒家的治世方略和理想政治。《长杨赋》有感于请胡人田猎以观而伤农所作,其目的依然用于讽谏。田猎固然不可少,但应该“有节”,由此而描画出作者理想的蓝图:所谓“出恺悌,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事,存孤独,帅与民,同甘乐”,依然是儒家的政治主张;所谓“陈钟鼓之乐”,“掉八列之舞”,“酌允铄,肴乐胥”,“歌投《颂》,吹合《雅》”,依然是儒家理想的礼乐典章制度。与武帝时的司马相如相比,扬雄赋中的属于儒家的治国理念就更具体也更深入了。
从总的趋势看,东汉赋与西汉赋相比,批评朝政的意识逐渐强烈起来。西汉初贾谊的《旱云赋》,将大旱的原因归结为“政治失中而违节”,“窃托咎于在位”,即归咎于统治者政治上的失节违度,显示出以儒家思想批评时政的精神。扬雄《甘泉赋》有“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胪兮,宓妃曾不得施其娥眉”,这里是以颂为讽,暗讽汉成帝好内,宠信赵飞燕姊妹而荒废国政。到东汉辞赋的批评意识就更突出了,张衡《西京赋》写天子游冶,“于是众变尽,心酲醉。盘乐极,怅怀萃。阴戒期门,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怀玺藏绂”,然后“历掖庭,适欢馆,捐衰色,从燕婉”。这是写天子微服私行。酒已微醺,天子极乐后又怀惆怅,于是脱下帝服换上便装,偷偷从“期门”出宫冶游,甚至到青楼寻欢作乐。这里表面也是歌颂,但明显是对朝廷的讽刺和批评了。《东京赋》则出现了更不和谐之音,张衡借安处先生之口说:“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警告统治者一味奢侈浮华,如不加以制约,势必引起民怨。“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荀子最先提出的,我们看,这些辞赋家们的批评“武器”,都脱离不开儒家德政、民本的政治主张。至于东汉末赵壹写《刺世疾邪赋》发出“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的愤激之声,其批评意识之强烈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我们再来看咏物赋,汉初贾谊《鵩鸟赋》也可以说是托物言志的咏物之作。梁园文士们也写了不少咏物赋,如枚乘《梁王菟园赋》、《柳赋》,邹阳《几赋》,公孙乘《月赋》等,细读这些赋作,多为即景而作,有的当然免不了有对梁王的颂赞之辞,但更深的属于思想层面的内容几乎没有。但到汉宣帝以至于东汉,这类赋作虽仍然是咏物,但其中的许多作品承载了儒家的思想主张。王褒《洞箫赋》是那个信奉儒家、好辞赋的汉宣帝时代的作品,拿《洞箫赋》与《七发》中“龙门之桐”一段相比,就会看出明显的变化。枚作写桐树生长环境艰难,所以制成琴后,音声悲凄,“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所谓“天下之至悲”。如此而已。而《洞箫赋》写作的路数与之相同,也先写竹子生长环境艰难,后写工匠制作、装饰、调试,一路写下来,最后写音乐的效果。同样是写音乐效果,前者只强调“悲”,而后者则渗透进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所谓“若慈父之畜子”,“优柔德润”而“似君子”,是“仁声”,是“施惠”,甚至有让贪者廉洁、使凶者仁善的教化作用;所谓“咸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这明显具有儒家的乐教观念了。再看东汉蔡邕的《弹琴赋》,虽为残篇,但可以肯定,其集中描绘的是琴声中的雅音,“于是弦既抑,雅韵乃扬。仲尼思归,《鹿鸣》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同样是写音乐,由枚乘《七发》的“龙门之桐”到王褒《洞箫赋》,再到蔡邕的《弹琴赋》,其通过对音声的描写所传达出的不同思想是非常明显的。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辞赋创作内涵的变化,其深刻的背景就是伴随汉代经学的演进、发展,儒家思想对辞赋作家浸润的结果。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但由于只延续二世,短祚而亡,又因为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主张,所以士人特别是儒生如何处理与王朝的关系尚未来得及细细品味,更谈不上统一专制条件下完善个人品格以及人生意义的深层思考了。汉代四百多年的历史,给予士人以充分的实践和思考的机会,让他们仔细品味、总结个人出处态度以及如何完善人格的最高境界。汉代士人的这番思考是以经学所承载的儒家人格追求为底色,而又辅以道家超脱求真而完成的,并对后世封建制度下的士人起到某种定性化的作用。汉代士人伴随痛苦、愤激、甚或血泪的思考,在汉代辞赋特别是抒情言志赋中有集中的表现。
考察汉代辞赋所展现的士人人生思考和人格完善的历程,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或称之为特点值得注意。一是这种思考和完善,的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渐趋深入和深刻;二是儒家和道家的人生追求、处世态度互补作用对汉代士人的影响,贯彻于汉代始终,西汉后期和东汉中前期儒家思想影响较重,而东汉中后期以至汉末,道家的影响有渐趋深入强盛的趋势;三是如果说阴阳五行化的汉代儒家思想对士人在辞赋创作表达政治理念时还有一定的影响的话,那么,在人生、处世问题的思考上,就儒家思想层面而言,所接受的几乎全部是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我觉得,这与汉代政治发展形势相契合,也与汉代经学运动的历史相契合。
汉初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都是官场人生遭遇坎坷后的感情抒发,前者是借对屈原的评论来浇胸中不平之块垒;后者是借鵩鸟入舍,“为赋以自广”,虽然“自广”的结果是堕入道家一途,但也只是自我宽解、自我安慰而已,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思考。但无论如何,已经开始涉及到个人出处的问题了。武帝时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都为官场的“不遇”也即不被重用而作,仔细品味,虽都为抒发不平,前者显得平和,后者显得愤激。前者思考后的出路是返身素业,正心归善,谦退沉默,所谓“孰若返身于素业”,“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遵幽昧于默足”;后者思考后的结果是“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应该说董仲舒的思索基本是儒家的,而司马迁的思索在儒家的层面上又辅以道家的思想。这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思想。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在武帝时期,在士人思考人生出处问题时,儒家、道家思想的介入。我们再看西汉后期刘歆的《遂初赋》,该赋是作者放外以纪山川的形式抒发不平之情。“乱曰”宣布自己的处世态度:“处幽潜德,含圣神兮;抱奇内光,自得真兮。宠幸浮寄,奇无常兮;寄之去留,亦何伤兮。”这基本是以任意去留,幽居保真来安慰自己,应属于儒家的处事准则。而“大人之度,品物齐兮;舍位之过,忽若遗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则在自我安慰中渗透有道家的思考了。我们再看光武帝朝冯衍的《显志赋》。该赋不是一般的抒情之作,是冯衍一生志向的总结,所谓“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在出没于儒、道两家的认真思考后所做出的选择是,孔丘的“知命”他非常欣赏,老聃的“贵玄”他也非常欣赏,所谓“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但又提出了问题,为用的德,与为体的道,谁更值得亲近呢?他的答案是:“陂山谷而闲处兮,守寂寞而为神。”也即在闲处中保持住自己的真心,也即“既俶傥而高引兮,愿观其从容”。比较儒、道而抉择自己的处世态度,与前所述一般性的表达,要明显深入了一步。诚然,冯衍最后是“从容观变”,并没有完全放弃建业留名的情节,与他的思想有关,也与光武帝朝经学的繁盛有关。
我们还注意到,西汉后期至东汉中前期这一阶段士人思考人生出处问题时,在儒道互补总的格局下,对儒家人格的追求,占据相当重要的成分,前述刘歆是这样,冯衍是这样,此间的崔篆《慰志赋》、傅毅《七激》、崔骃《达旨》、班固《幽通》等,也都有这种倾向。支持崔篆临终“慰志”的是“惧《大雅》之所讥”,是“《氓》嗤之悟悔”,他“潜思以至颐”的是“六经之奥府”。傅毅所谓的“要言妙道”是“遵孔氏之宪则,投颜闵之高迹”,而且要仰仗此以为法度。崔骃说“进动以道,则不辞执珪而秉柱国;复静以理,则甘糟糠而安藜藿”。这明显是儒家“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主张。班固“致命遂志”所要“幽通”的是,自己要像圣贤那样“复心弘道”,“要保身遗名”,最终追求“皓尔太素,曷易色兮”。用《六臣注文选》李善的说法,就是“言人能笃信好学,死守善道,不渐染于流俗,是为白尔天质,何有渝变之色也?”⑧以儒家“守正”作为做人的最高追求。造成这种发展格局的原因,与此阶段古文经学的发展和繁盛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东汉政治的颓败和相对出现的经学的逐渐衰微,东汉中后期以至汉末,士人对人生出处的思考,道家的成分渐趋加重,思考的本身也显得更深刻了。张衡《思玄赋》作于后汉顺帝时,“衡时为侍中,诸常侍皆恶直丑正,危衡。故作是赋,以非时俗。思玄者,思玄远之德而已”。⑨他所思考的“玄远”之德是,“御六艺之珍驾,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以为罟兮,驱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逍遥。”儒家所谓的“六艺”,《雅》《颂》,仁义,墨家所谓的强本节用之道,都可以说是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墨无为以凝志”,守“仁义”而自足,也就是以恪守儒家仁义和道家的无为来实现自己心境的“逍遥”,以此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境界。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松、乔高峙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朅来从玄谋,获我所求复何思”。峙,立也;离,附也。《六臣注文选》刘良曰:“言仙人赤松子、王子乔高立物外,谁能往而附之?”携,离也。《六臣注文选》张铣曰:“言结束精神,远从仙游,徒使我心携离。”⑩此两句是说,即使赤松子、王子乔一类仙人,也不是自己真正追求的目标。真正追求的是“回其情志,以从玄圣之道而复行之”,做到子这一步,“复何思虑也”?(11)这也就是“回志朅来从玄谋,获我所思复何思”。张衡的人生境界是经过了认认真真思考过的,他既没有入仙也没有入道,他还是要生活在现实之中,坚守儒家的仁义和道家的无为。联系他写的《归田赋》所展现的理想是要在现实人生中实现“逍遥”,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总之,他是将儒家对人格守正的追求与道家所主张的自然无为相结合,追求一种自然本真的人格建构。伴随道家思想更多地介入到士人对人生层面的思考,这种思考与西汉时代的辞赋相比,就显得要深刻多了。崔寔是汉末桓、灵时代人,他的《答讥》过去评价不高。但若从思想影响辞赋创作而言,倒颇值得注意。该赋固然能折射出汉末官场政治的黑暗、压抑人材,但更重要的是,显现出辞赋创作中儒家影响的相对减弱和道家影响的增强。崔寔追求的是,“守恬履静,澹而无求,沉缗濬壑,栖息高丘”。这由道家的守静、无欲、无求,进而生发出栖息山林追求隐逸的生活方式了,暗示着汉末至魏晋,伴随士人人格理想追求的变化,因而出现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的变化。
我们检读汉代辞赋家的抒情言志赋,似乎没有发现儒家思想的阴阳五行化成分对他们思考人生方面的影响,换句话说,在这个层面影响辞赋家思考的基本上是传统儒家思想所主张的处事为人的准则。道家思想的影响也仅在思想的层面上,也没有入道教一流,这与汉代乐府诗和汉代文人诗有不少求仙、入道之作呈现出明显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辞赋创作主体的身份,与乐府、文人诗创作主体的身份不同相关。汉代乐府诗(特别是民间乐府)、文人诗的创作主体相对而言属于下层文人(或虽曾经为上层,但最终沦落为下层,如《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而汉代辞赋的创作主体相对而言则属于上层文人,也就是说,他们大都有为官为宦的经历,大都经历有经学的系统教育,因此在思考人生真谛的时候,仍然保持有相对“守正”的一面。总之,我觉得这仍然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班固:《两都赋序》,见《文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页。
②《汉书·楚元王传》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2页。
③《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69页。
④《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4页。
⑤《东观汉纪校注·显宗孝明皇帝》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6页。
⑥《后汉书·显宗明皇帝纪》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4页。
⑦《汉书·扬雄传》卷八十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40页。
⑧《六臣注又选·幽通赋》卷十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⑨《六臣注文选·思玄赋》卷十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⑩《六臣注文选·思玄赋》卷十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11)《六臣注文选·思玄赋》卷十五吕向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标签:汉朝论文; 儒家论文; 东汉皇帝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汉论文; 张衡论文; 读书论文; 两都赋论文; 二京赋论文; 吊屈原赋论文; 子虚赋论文; 上林赋论文; 甘泉赋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