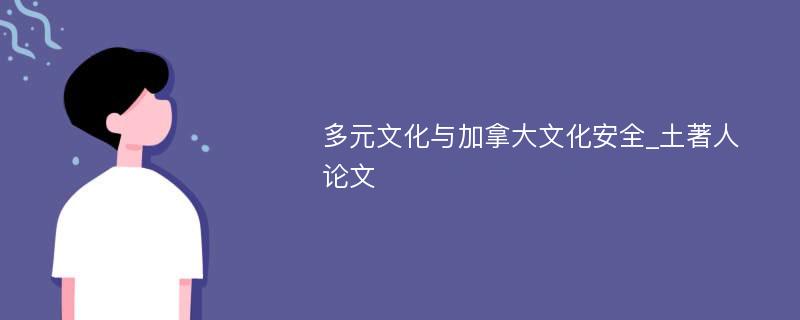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加拿大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创始人是意大利的巴蒂斯塔·维柯和德国的约翰·戈特弗雷德· 赫尔德,(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著,冯克利译:《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 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5页。)而加拿大则是第一个正式、明确地奉行多元文化主义 的国家。(注:Will Kymlica,“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in Canada”,James
Bickerton et al.(eds.),Canadian Politics(third edition),Toronto:Broadview
Press,Ltd.,1999,p.26.)我们正处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样性是其构成的特征。(注 :[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版,第89页。)全球化沿着辩证的逻辑向前发展,要创造一个既多元又统一的 世界。面对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冲击,各国政府以各自的方式进行回应。在它们为维护民 族身份与文化安全所作的种种努力中,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无疑是一种富有建设性与 启发性的尝试。它不仅为加拿大确立民族身份和维系文化安全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也为他国处理民族认同和文化危机问题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本文拟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 义的历史演变、文化效应以及它在文化安全中的普遍意义作初步的探析。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由来
加拿大于1971年确定了双语框架内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构想,1988年正式推出《多元 文化法》(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多元文化主义之所以在加拿大得以实施 ,既取决于历史上外在的原因,也得力于当代加拿大人自身的努力。
英法两国都于17世纪初便开始在北美建立殖民地。法国人在加拿大捷足先登,建立了 “新法兰西”,并且向殖民地移植自己的民族文化。然而,英国人后来者居上,在“七 年战争”(注:“七年战争”是英、法为争夺海外贸易霸权与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爆 发于1756年至1763年期间,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等地展开,前后延续七年,以英国人的 全面胜利而告终。英法双方于1763年在巴黎签订了《巴黎和约》,法国人让出了北美等 地殖民地,七年战争就此正式结束。)中击败了法国人。1763年的《巴黎和约》之后, 新法兰西落入英国人手中,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英国殖民者本希望通过不断输入英裔 移民,冲淡法裔居民的文化意识,进而把他们同化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中去,但 其企图遭到了法裔加拿大人的坚决抵制。迫于北美十三殖民地日渐高涨的反英浪潮,愿 意进入魁北克的英裔居民也很少,英国统治者遂暂时放弃了同化政策。
美国革命之后,大批忠于英国的托利党人涌入加拿大,安居在魁北克。随着魁北克省 城中说英语人口的激增,法裔与英裔之间的文化冲突不断加剧,形势一触即发。英国殖 民统治者为了把两个族裔分开,建立了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说英语的人被安置在上加 拿大,说法语的人被安置在下加拿大,但英国殖民者仍未放弃同化法裔加拿大人的企图 。上、下加拿大的划分并没有平息各方的不满,它不仅使本已具二元性的加拿大文化在 地理上得到了强化,而且又进一步加深了英裔与法裔的分裂。在改革派的声音不断高涨 之时,英国统治者非但没有倾听他们的呼吁,反而以高压政策对他们进行迫害,致使以 威廉·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等人为首的激进分子于1837年发动了起 义。
1837年的动乱平息后,英国把上、下加拿大合而为一,其潜在的用意是最终把法裔加 拿大人整合到英国殖民社会中去。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国殖民者施行了种种歧视性的法 案以保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配地位。(注: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fifth edition),Stamford:Wadsworth ,2000,p.462.)可以说,“英国殖民者自其对魁北克实行统治之日起便刺激、强化和激 怒了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法裔居民,使他们成为越来越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并没有 什么特别的恶意或邪念,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对大不列颠及其它的传统表达出一种共有 的敌对情绪”。(注:Hilda Neatby,“French-Canadian Na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J.M.Bumsted(ed.),Canadian History before Confederation :Essay and Interpretations(second edition),Ontario:Irwin-Dorsey Limited,1979 ,p.198.)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后,虽然英语和法语都受到宪法的保护,但双语制度仅在魁 北克实施,法裔加拿大人实际上还是受到压制,英裔与法裔的文化矛盾依然深刻。联邦 政府的成立非但没有使法裔加拿大人渐渐融入到联邦体系中来,反而使他们愈益坚定地 退守到以天主教为核心的法兰西文化传统之中,比以往更为封闭与孤立。
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平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注:“平静革命”是法裔加拿 大人于20世纪60年代发动的一场政治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法裔加拿大人抛弃了传 统的以天主教为核心的文化观念,启动了魁北克现代化的进程,与英裔加拿大人展开竞 争,其结果是法裔加拿大人的力量不断壮大,到70年代初开始全面主导魁北克。),以 及在此过程中崛起的魁北克党把法裔民族主义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英裔与法裔的文 化冲突随之进入了新的阶段。“平静革命”前,法裔魁北克人屈居英裔加拿大人之下, 但此后,他们一举夺回了魁北克的主宰权。魁北克政府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在民族主义 情绪的支撑下,它名义上是加拿大的省城,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次国家政府 ”,对加拿大联邦制度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内在的挑战。(注:Marc V.Levine,
“Canad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Quebec Independence Movement”,Winston
A.Van Horn(ed.),Global Convulsions:Race,Ethnicity,and Nationalism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p .317.)1976年魁北克党在大选中战胜自由党,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分离主义执政党 ,把加拿大民族推向了分裂的边缘。为了安抚法裔加拿大人,加拿大政府更换了国旗、 国歌,发行了新的邮票和货币,把自治领日改为加拿大日,并且通过了《官方语言法》 (Official Languages Act),同时赋予英语和法语以官方地位。
毫无疑问,魁北克的独立运动是促使加拿大在二战后改变其语言和族裔政策最为重要 的催化剂。(注:Carol L.Schmi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Conflict,Identity,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07.)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过程中,除了英裔与法裔群体外,被 称作“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的土著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土著人是加拿大最早 的居民,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们的文化在欧洲殖民者的摧残下衰微,又在加拿大政 府种族主义文化政策压制下进一步败落。但他们仍然顽强地保存着破损的传统,拒绝接 受强加给他们的西方文化。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土著人的 力量迅速上升。他们开始发起民族主义运动,直接向国家主权冲击。加拿大政府渐渐认 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鉴于过去粗暴地对待土著人,加拿大政府在1998年正式向他们表 示道歉。(注: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p.480.)土著人在为其共有的土著文化而斗争的同时,也成为多元文化主 义中的一支生力军。
“第三种力量”(The Third Force)同样是多元文化主义中不容忽视的群体。加拿大是 典型的移民之邦,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实行种族主义和排外的移民政策。(注:
J.L.Granatstein et al.(eds.),Nation:Canada since Confederation(third edition ),Toronto: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1990,p.337.)20世纪60年代起,加拿大政府 迫于国际压力和人力资源的匮乏,逐步废除了种族歧视性的移民政策,开始实行强调移 民教育背景和潜在能力的“打分制”。在此之后,进入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数都不是欧洲 人。(注: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p.487.)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优势迅速崛起,和非英裔、法裔及非土著群体 一起构成了加拿大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在这个国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 们对政府所实行的双语制和二元文化主义表示不满。“因为这些加拿大人担心,如果他 们所付出的劳动不能通过作为国家象征的文化得到珍视的话,他们将沦为社会中的二等 公民。”(注:Yasmeen Abu-Laban,“The Politics of Race,Ethnicity,and
Immigration:The Contested Arena of Multiculturalism”,James Bickerton et al.(eds.),Canadian Politics(third edition),p.467.)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特鲁多政府经权衡之后决定选择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只赋予英语和法语以官 方语言地位,并且于1988年正式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法》。该法案声明:加拿大政府 承认族裔与文化多样化之合法性,视多元文化为加拿大民族的基本特征与宝贵资源,保 障所有公民保存和分享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鼓励他们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 献。(注:参见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http://laws.justice.gc.ca/en/c-18 .7/29236.html)至此,多元文化主义历经斗争与曲折,终于降世。
纵观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殖民者在同化法裔居民上的失败 早就为日后英裔与法裔的文化冲突埋下了伏笔,不但使这两个群体注定要相互竞争与妥 协,也使加拿大民族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早期的竞争始终在英裔加拿大人主导的 语境中进行,法裔加拿大人一直面临着文化生存的危机。“平静革命”的到来扭转了这 一局面,双方开始进行较为平等的对话。法裔加拿大人的成功无疑唤醒了土著人的自我 意识,而“第三种力量”的加入则使加拿大冲破了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禁锢,进 入了多元文化主义时代。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安全效应
加拿大是世界上族裔成分最为复杂、相互之间差异最为深刻的民族国家之一,面临着 如何促进民族和睦,维护国家统一与文化安全的严峻挑战。多元文化主义无疑在这方面 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首先,它缓解了英裔与法裔的文化冲突,回应了土著人和“第 三种力量”的身份诉求,促进了民族认同。其次,它抵制了美国的文化渗透,维系了加 拿大的民族身份。然而,多元文化主义的优势也正是其缺憾所在。它并未完全实现多元 的统一之构想,加拿大民族共同体始终处于一种较为松散的状态,常常在魁北克族裔民 族主义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变得岌岌可危,民族的分裂和身份的危机成了它挥 之不去的梦魇。
英裔与法裔的文化冲突一直是加拿大国家统一与文化安全的最大威胁。如前所述,法 裔加拿大人在“英属北美时期”就开始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坚决的 斗争。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后,他们也从未放弃过身份诉求,始终把法裔文化的生存作为 加入加拿大联邦的先决条件。然而,英裔与法裔之间的文化分歧较大,各自对加拿大民 族性的理解也相差甚远。虽然两个族裔在政治与文化上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但英裔加拿 大人利用其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极力推行盎格鲁化(Anglo-conformity),试图把法裔群体 整合到他们的文化中去,因而造成了两个族裔的长期相互对立。
20世纪60年代前,法裔民族主义者虽要求自治和保护法裔文化,但大部分人并不赞同 分离主义。因此,加拿大政府在推行盎格鲁化时并没有危及到国家的统一。然而,“平 静革命”后形势急转而下,原有保守的民族主义渐渐让位于激进的分离主义。更为重要 的是,魁北克党在1976年的省级选举中一举击败自由党,分离主义势力首次主导了魁北 克。至此,加拿大民族共同体已经陷入了危机,形势甚为紧迫。(注:David V.J.Bell( ed.),The Roots of Disunity:A Study of Canadian Political Culture(revised
vers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12.)虽然分离主义在1980年的 全民公决中遭到拒绝,但倘若不妥善处理英裔与法裔的文化矛盾,加拿大有可能就此走 向分裂。加拿大政府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抛弃盎格鲁化,转而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多元 文化主义赋予法语以官方语言地位,并且为所有希望学习法语的加拿大公民提供免费教 育。同时,它还为愿意学习英语的法裔加拿大人或愿意学习法语的英裔加拿大人推出了 由政府主办的“法语沉浸”和“英语沉浸”培训项目(注:“沉浸式语言教育”是指课 堂上全部使用要学习的语言,放学回家后再使用自己的母语;通过要学习的语言,学生 们既学语言又学知识,沉浸学习的时间一般要占总学时的60%以上。),在全国加以推广 ,以促进加拿大的双语教育。这些措施无疑为法裔文化的生存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从而 缓解了英、法族裔的文化冲突,避免了民族国家分裂的悲剧。
土著民族主义也是加拿大维系国家统一与文化安全中的一大难题。土著人是北美最早 的主人,但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侵害,无力维系自己独特的文化。加拿大联邦成立后, 其政府并没有反省历史上殖民主义者的过错,而是以家长式的作风压制土著人。1970年 前,加拿大政府一直试图以公民身份为诱饵,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引起了土著人 的巨大怨恨。(注:Joseph H.Carens,Culture,Citizenship,and Community:A
Contextual Exploration of Justice as Evenhandedn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85-188.)随着全球反种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土著群体不断 觉醒,其力量也日见壮大。为了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土著人成立许多全国性组织,向 政府提出承认其文化之独特性和合法性、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自治政府的要求。(注: 参见E.Kaye Fulton,“Drumbeats of Race”,Gregory S.Mahler et al.,eds.,
Canadian Politics,Connecticut:The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Inc.,1993,pp.181- 183;Jack Aubry,“What I s Self Government?”,Gregory S.Mahler et al.,eds.,
Canadian Politics,pp.184-185;Andre Picard,“The Internal Exiles of Canada”,Gregory S.Mahler et al.,eds.,Canadian Politics,pp.186-189.)他们同魁北克人一 样,也对加拿大民族共同体构成了内在的挑战。詹姆斯·塔利指出,土著人与非土著人 应该在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的原则下进行文化间的对话,把彼此共同享有 的生活与命运看作加拿大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参见James Tully,“Aboriginal Peoples:Negotiating Reconciliation”,James Bickerton et al.(eds.),Canadian
Politics(third edition),pp.426-428.)毫无疑问,多元文化主义推动了这种平等而有 益的对话。为了贯彻多元文化主义,恢复和促进土著人文化的发展,加拿大政府采取了 较为全面的措施。它不仅为土著人提供财政上的支援,给予他们教育上的自主权,而且 还敦促加拿大各省加强宣传与推广土著文化,让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了解北美大陆最早居 民的历史和文化。这些措施较好地回应了土著人的文化诉求,促进了民族的和解与国家 的统一。此外,多元文化主义也在解决“第三种力量”的身份诉求、维持民族团结的努 力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加拿大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奉行种族主义移民政策, 导致非英裔、非法裔,特别是欧洲以外地区移民的强烈不满。二战之后,随着“打分制 ”的实施,大批非欧洲移民进入了加拿大。尽管面对同化的压力,他们依然执着于自己 的族裔传统,对政府的民族文化政策提出了重大质疑。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为他们维持 族裔文化提供了渠道。为了贯彻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政府大体上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 工作:(1)为少数族裔维护其传统文化提供资金援助;(2)消除少数群体全面参与加拿大 社会事务的障碍;(3)促进族裔间文化交流;(4)为进入加拿大的移民提供官方语言培训 。其中,给予少数族裔以财政资助是一项具有新意的举措。(注:Yasmeen Abu-laban,“The Politics of Race,Ethnicity,and Immigration:The Contested Area of
Multiculturalism”,pp.465-466.)这些举措在消除了种族歧视的同时,也促进了少数 族裔的民族认同。
多元文化主义的另一个效应是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维护。美、加两国历史上都曾是英 国的殖民地,文化皆根植于英国文化传统。相对而言,加拿大人较为保守,美国人更为 激进,但这种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建国以来,加拿大国内虽然存在大陆主义与加拿大主 义之争,但其政府一直致力于创建一个不同于美国的民族。遗憾的是它始终无力消解美 国文化的影响。二战期间,加拿大人意识到有必要在外来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冲击 下保持加拿大固有的文化特性,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注:姜芃主编:《 加拿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二战后,加拿大政府相继建 立了皇家民族文学、艺术与科学发展委员会和加拿大国立图书馆等机构,旨在发展民族 文化,阻止美国文化的渗透。
显然,受多元文化主义保护的法裔文化是加拿大抵御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天然屏障和 坚强堡垒。卡洛尔·斯米德指出:“两个持久性语言共同体的建立是把美国和加拿大区 分开来的重要因素:加拿大最大的弱点,即它的族裔构成,几乎是以某种有悖于常理的 方式成了它最大的力量所在。也许美加两国之间唯一真正的差别就是加拿大是一个二元 文化或多元文化的国家,而美国却都不是。如此看来,单单那种差异就可以让加拿大获 得自己独立的身份,甚至可以使它改善当下的景况,不致落到仅仅是美国另一个卫星国 或附属国的地步。”(注:Carol L.Schmi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Conflict,
Identity,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113.)
和加拿大的族裔构成一样,多元文化主义的效应也是双重的。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兼 顾了各方面的权益。然而,一旦深究下去我们便会发现,它既没有真正反映英裔文化的 主导地位,也没有完全满足法裔加拿大人的文化诉求,更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平等对待少 数族裔。多元文化主义的致命弱点是它内在的分裂倾向。它使加拿大难以在族裔多元的 基础上实现民族的高度统一,真正有效地维护其文化安全。
英裔文化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其地理与人口的分布上。从地理分布上看,除了魁北 克和土著人自治区以外,加拿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天下。从人 口分布上看,英裔文化同样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里我们仅需以文化最重要的象征—— 语言为例便可说明问题。根据加拿大官方所作的统计,1971年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 占总人口的60.2%,到了198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62.1%;相比之下,同时期以法语为母语 的加拿大人分别仅占总人口的26.9%与25.1%,其中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大部分都居住在魁 北克。1996年的数据显示,在魁北克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占其人口的81.9%,在安大略占2 .7%,在马尼托巴占2%,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占0.4%……在整个加拿大占22.3%。(注:以 上数据参见“Canada Statistics,1986”;“Census of Canada,1996”。转引自Luc
Albert,“Language in Canada”,Gregory S.Mahler et al.(eds.),Canadian
Politics,pp.117-118;Carol L.Schmi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Conflict,
Identity,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110.)由于英语文 化主宰了加拿大社会,移民进入加拿大后基本上选择融入英语而非法语文化,即使在魁 北克大多数移民仍出于实用的考虑倾向于学习英语。更让魁北克人感到不安的是,很多 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从魁北克移居他乡之后便改说英语。尽管有政府、公众的支持,以及 法语在教育中的使用,在魁北克之外,向英语同化的势头仍是迅即而广泛的。(注:
Joseph H.Carens,Culture,Citizenship,and Community:A Contextual Exploration
of Justice as Evenhandedness,p.114.)
多元文化主义在法律上赋予法语与英语同等的地位,但却不能掩盖现实中的不平等。 所谓的双语制并没有给英裔加拿大人带来多少压力,却给法裔加拿大人增添了较大的负 担。199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说双语的加拿大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其中半数以上的 人生活在魁北克。(注:“Canada Statistics,1997”.转引自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p.469.)斯岱芬·迪恩指 出:“完全实行双语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两种语言在一个地域内自由竞争时,占主 导地位的语言就会取代另一种语言。”(注:Stephane Dion,“The Reemergence of
Secessionism:Quebec”,Albert Breton et al.(eds.),Nationalism and Rationalit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37.)不仅如此,在魁北克人看来, 多元文化主义在民族层面上把法裔加拿大人从宪章群体身份(charter-group status)降 低到加拿大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族裔群体,无疑剥夺了他们创始民族的地位,是无法接受 的。(注: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p.493;Joseph H.Carens,Culture,Citizenship,and Community:A
Contextual Exploration of Justice as Evenhandedness,pp.109-110.)鉴于多元文化 主义并未彻底解决法裔加拿大人的文化生存问题,魁北克政府又于1995年举行了第二次 全民公决。联邦主义虽然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但魁北克党承诺要在未来适当的时候举行 第三次全民公决。魁北克分离主义有可能成为周而复始的顽症,反复困扰加拿大。
多元文化主义也没有真正帮助土著人和少数族裔摆脱文化困境。土著人在加拿大政府 同意赋予他们宪法框架内的自治权后,仍然面临着文化危机:他们希望维护自己的传统 ,但要更好地生存就必须学习英语或法语,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土著人坚持要求建立 有独立主权的自治政府,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继因纽特人与政府在1993年签 订了《努纳乌特协议》(Nunavut Agreement),建立了第一个与加拿大联邦享有平等管 理权的自治区后,其他的土著人也在与政府谈判,要求建立同样的自治区。(注:参见
Frances Abele,“The Importance of Consent:Indigenous Peoples' Politics in
Canada”,James Bickerton et al.eds.,Canadian Politics(third edition),p.451.) 如此发展下去,加拿大有进一步“巴尔干化”的危险。此外,多元文化主义所承诺的对 少数族裔文化的扶植不过是象征性的。1992—1993年度加拿大多元文化和公民部的预算 为1.18亿加元,占整个国家预算的1/1500;1996—1997年度联邦政府用于多元文化的财 政预算为1870万,1998—1999年度为1830万。(注:高鉴国:《加拿大文化与现代化》 ,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加拿大政府为英语与法语教育提供资金,而其他族 裔如想学习或维持自己的语言则要通过私人渠道来实现。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任 何群体离开国家的扶持都无法胜任文化教育这一庞大而艰巨的任务。难怪少数族裔群体 认为,一个不能保护或支持自己族裔语言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
在民族认同不强的情况下,加拿大人始终难以抵御美国文化的诱惑。1964年的某个夜 晚在哈里法克斯所进行的抽查显示,74%的观众在收看美国的电视片。(注:Robert
Bothwell,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Politics of Partnership,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House,1992,p.89.)1970年历史学家郑吉兹曾对加拿大中学生作 过一次调查,他发现大部分学生对美国总统的了解要多于对加拿大总理的了解;他们所 用的教材多数出自美国;许多学生根本就不选修加拿大历史课。80年代的跟踪调查的结 果同样令人沮丧。(注:参见David V.J.Bell(ed.),The Roots of Disunity:A Study
of Canadian Political Culture,p.6.)美国人不仅左右了加拿大人的文化倾向,而且 还控制了它的文化市场。到90年代为止,美国文化产品几乎垄断了加拿大的文化市场, 占据了它电影的95%、电视剧的93%、英语电视节目的75%以及出版业的80%。(注:[英] 约翰·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 页。)
为了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加拿大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产业,加拿大政府曾采取过 种种措施。例如,它要求出版物中有一定比例的加拿大内容(Canadian content),把文 化产业排除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外等等。然而,总的看来,这些保护主义举措的 收效不甚理想。对加拿大文化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它自身的脆弱。雷蒙德·巴 奏斯基指出,如何调适两个基于语言之上的身份所造成的政治困境,长久以来,既未彻 底脱离,又未明确得到界定的殖民关系,再加上与在军事、经济与文化领域都支配着它 的美国为邻,这些因素皆使加拿大建立一个坚实的民族身份之设想变得前途未卜。(注 :Raymond Bazowski,“Contrasting Ideologies in Canada:What's Left?What's
Right?”,James Bickerton et al.(eds.),Canadian Politics (third edition),p.95 .)
三、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安全的启示
多元文化主义是差异的政治与承认的政治,体现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追求平等与公 正的精神。多元文化主义不仅维护了加拿大的统一,还使它以鲜明的个性跻身于世界文 化之林。迄今为止,北美大陆曾出现过三种文化模式,即美国的大熔炉和加拿大早期施 行的盎格鲁化以及它后来选择的多元文化主义。其中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不但最具包容性 ,也最富启发意义。
盎格鲁化本质上是一种同化论。同化论认为,多族裔的民族要想确立身份必须让少数 族裔通过不断学习,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逐渐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理想中的民族应 该是一个没有族裔差异、同质化的群体。熔炉论者认为,多族裔的民族可以集各族裔传 统之长,塑造出一种全新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族裔差异的消 失。盎格鲁化漠视加拿大民族文化多样性之深刻,依据主导族裔的偏好来建构民族身份 ,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因而招致法裔和少数族裔的强烈反对,几乎把加拿大推向 了分裂。熔炉论虽然在理念上已经较为宽容,赋予少数族裔文化以生存空间,但在这一 模式中,弱势群体的传统往往会被强势群体的文化所淹没,最终形成的民族身份反映的 基本上仍是主流社会的价值,在本质上它仍是一种同化论,只不过比盎格鲁化稍微温和 一些而已。这种模式对于加拿大之类族裔构成复杂、相互之间差异极大的民族国家来讲 ,也会引发激烈的民族矛盾,危及到国家的稳定与文化安全。
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重要旨趣便是对少数族裔传统及所有公民文化权利的保护。它不 但承认族裔差异的合法性,还要进一步推进民族的多样化。在这个文化模式中,各族裔 文化,不分地区、种族,一律享有同等的地位,没有什么统摄所有族裔的民族文化,以 往的民族文化认同已经被民族公民认同所代替。公民认同是一种新型的、与族属意识、 族籍身份相互分离的政治认同。在这一认同模式中,民族认同从文化关系向政治地域关 系转变,多元文化的存在已经不再是民族建构的障碍,且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因而族裔 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随之得到了缓解。(注:[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 等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多元文化主义以民族政治认同统合族裔文化认同,跳出了传统上以民族文化界定其政治 边界的思维定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为多族裔民族国家如何缓解民族冲突,更有效 地维护文化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多元文化主义引起了人们对民族统一性的思考。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 国家都和加拿大一样,有着许多少数族裔群体,这些群体也都希望在全面参与社会、政 治、经济活动的同时,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勿庸置疑,对于多族裔国家 而言,相应的民族同化对统一价值观及其内聚力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族主义者 因此把建构共同文化看作自己的三大使命之一。(注:Natividad Gutierrez,“The
Study of National Identity”,Alain Dieckhoff & Natividad Gutierrez(eds.),
Modern Roots:Studies of National Identity,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1,p.3.)然而,民族共同的文化并不是完全同质的文化。文化的差异是无法 消除的,民族文化不可能像民族主义者宣称或希冀的那样,呈现出百分之百的均质,它 总是具有一定的混合性。(注:Anthony D.Smith,“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Alain Dieckhoff & Natividad Gutierrez eds.,Modern Roots:Studies
of National Identity,p.23.)“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尽管各国政府在教育体系、 整合的政策、大众媒体和其他政治性强制措施等方面的投入可观,迄今为止,世界上还 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形成语言和文化上的同质化。”(注:Natividad Gutierrez,“The
Study of National Identity”,p.12.)多元文化主义无疑反映了这一难以撼动的现实 。它揭示:世界是多元的,没有宽容便没有统一,民族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中不可以过 度强调文化上的同质性。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民族成员共享的历史、价值与理想。倘若民 族国家过度强调文化的同质性,对少数族裔强行实施同化,结果往往会把他们推向“他 者”,不断地异化。在极端的情形下,它还会催生离心力极强的族裔民族主义,使民族 国家陷入分裂的危机,影响到它的文化安全。其实,少数族裔群体不一定总是通过牺牲 共有的民族身份来强化他们的族裔性。恰恰相反,他们常常热衷于确认自己对民族的承 诺,以免因文化差异或其他原因招致别人的指责,说他们是不忠的公民。(注:David
Miller,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77.) 加拿大的经验表明,仅仅通过压制差异来建构民族认同不但会导致文化的冲突,还会威 胁到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印度和苏联因文化冲突而造成的分裂也可以使我们获得同样的 教训。爱拉特·阿克里夫指出,多族裔民主社会和平的文化条件是具备这样特征的政治 文化:它不仅具有多重身份、公民与族裔价值的平衡、相互宽容的多元主义规范,还有 着族裔间不断增进的理解。(注:Airat R.Aklaev,Democratization and Ethnic Peace :Patterns of Ethnopolitical Crisis Management in Post-Soviet Settings,
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Ltd.,1999,p.67.)马格热特·摩尔告诫人们,要创建一 个共同的政治事业,首先必须承认不同的身份。国家的政治文化必须尽可能地包容不同 群体的传统,确保在整个民族的历史中也有它们的历史。(注:Margaret Moor,
“Liberal Nation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p.190.)
其次,多元文化主义也引起了人们对民族认同至尊性的反思。现代社会的人对身份和 平等都有诉求。虽然民族国家是他们身份的主要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 民族身份都是至高无上的,而这种情形在全球化时代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当今,全球性 与地方性力量的成长对民族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发起了冲击,对民族认同的统治地位提 出了挑战。一方面,民族国家越来越受到超国家和次国家权威的制约,不得不认可其公 民所持的那些互相交叉、竞争的忠诚;(注:[英]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等译:《 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7页。)另一方 面,民族认同也不再像往日那样视民族为当然,具有高度的内聚性;民族认同的建构则 更具开放性和反思性。(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 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9页。) 多元文化主义显然较好地顺应了全球化中世界多样化的大势所趋。它告诉我们,民族国 家中那些重叠、矛盾的身份完全可以找到各自的表达方式,相互兼容、相互补充、相互 增进;各种身份之间不一定要有传统意义上严格的等级之分,民族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 时不应一味突出民族认同的优先性。民族认同固然还在民族共同体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其他形式的认同暂时也难以取代它的地位。但民族国家若想在全球化时代继续维持 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实现文化安全则必须既要倾听内部的声音,又要考虑到外部世界的 进程。加拿大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曾片面地强调民族共同体、民族利益和民族规划。这种 做法既不利于真实地反映该国的联邦体制,又有碍于表达它文化深层次的多样性,(注 :Alain-G.Gagon,“Rethinking Multinational Space:The Quebec Referendum and
Beyond”,Shlomo Ben-Ami et al.(eds.),Ethnic Challenges to the Modern Nation Stat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2000,p.213.)同时也有悖于全球化中世界 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容易酿成民族矛盾的激化与文化安全的困境。英国在处理苏格兰、 威尔士和爱尔兰族裔问题上的挫折、西班牙在解决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问题上的僵 局也都反映了类似的失误。
诚然,多元文化主义也有其自身的缺憾。它虽促进了民族的多样性,但却没有完全实 现其求同存异的设想,在超越了盎格鲁化的同时也暴露出较大的局限性和权宜性:它所 倡导的民族公民身份这个“弱式认同”(thin identity)(注:所谓“弱式认同”是指不 主张建构共同文化的民族公民认同,即民族政治认同;而“强式认同”则是指要求建构 共同文化的民族文化认同。参见Juan M.Delgado-Moreir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f the European Union,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0,p.95.)有时 并不能有效地聚合族裔,维持民族国家的统一与文化安全。鉴于其内在的分裂倾向,时 至今日,魁北克族裔民族主义的阴影、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幽灵依然徘徊在加拿大身旁 。即便如此,多元文化主义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但在加拿大确立了难以替代 的地位,也在美、英和澳大利亚等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其包容性的思想无疑对全球化 中民族认同与文化安全的维护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文化安全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 的平衡;其长远的维系在于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有机结合。如何调适多元文化主义中 族裔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进一步完善这一文化模式应该成为我们今后探讨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