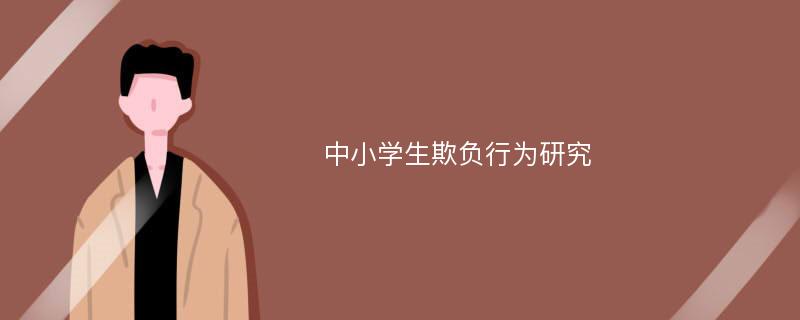
王倩[1]2010年在《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的编制》文中研究说明欺负行为是学校情境中常见的一种行为,在中小学生之间较为常见。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欺负行为在许多国家都具有较高的普遍性。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Olweus关于北欧国家的学校欺负行为的系统研究之后,国内外关于欺负的研究先后经过了描述性研究阶段和深入阶段。但是,迄今为止尚无研究从归因的角度研究欺负行为的认知基础。而认知这一因素对于个体的行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和决定作用。归因理论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渐成为主流的现代认知理论,它为欺负行为的研究指出了认知研究的新方向。欺负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行为,它对欺负者、被欺负者以及他们所在的学校环境均产生不良的恶性影响。那么,欺负者与被欺负者的归因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特点对于欺负这种行为的发生是否有所影响呢?而欲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自编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进而为进一步探讨认知因素对我国中小学生欺负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有效测量工具。本研究首先以归因理论为理论基础,借鉴目前归因测量工具的编制,确定了量表的维度结构;接着,对通过开放性问卷收集到的中小学生欺负者和被欺负者关于欺负行为的实际归因情况进行内容分析和频数统计,进而确定了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的条目。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有两个分量表,即中小学生欺负者归因量表和中小学生被欺负者归因量表。依据归因理论,每个分量表又由八个子量表组成,即ISC(内部\稳定\可控)、ISU(内部稳定\不可控)、IUC(内部不稳定可控)、IUU(内部不稳定\不可控)、ESC(外部\稳定可控)、ESU(外部稳定不可控)、EUC(外部不稳定可控)、EUU(外部不稳定\不可控)。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的两个分量表经多次施测和因素分析后,最终分别形成包含28个题目和26个题目的正式量表。每个子量表各有3-4个题目不等。最后,本研究分别用这两个分量表再次对另一独立样本施测,以进行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模型拟合指标均表明,本研究所建构的一阶模型拟合良好,可以接受。正式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符合测量学标准。另外,对正式量表的信效度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的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分别为0.926和0.890,各子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也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量表的编制具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而且经过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和教授多次深入的讨论,最大程度地保证了量表测量到所欲研究的内容,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本研究的研究结果:(1)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有中小学生欺负者归因量表和中小学生被欺负者归因量表两个分量表;(2)每个分量表都有八个子量表,即ISC、ISU、IUC、IUU、ESC、ESU、EUC和EUU;(3)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基本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邬洁妮[2]2007年在《华人中学生欺负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跨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欺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行为,是指力量较强的一方对力量相对较弱的另一方有意实施的有伤害性结果的负面行为。近20年来,学校欺负问题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国心理学家就欺负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然而研究主要还停留于描述性阶段,对欺负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多,跨文化研究更是少见。众多的研究已证实: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欺负行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马来西亚2所中学101名及中国1所中学85名华人中学生进行调查,得出以下结果:1.无论马来西亚还是中国,中学生皆存在严重的欺负问题,马来西亚中学生卷入欺负行为的有23.8%,无关者有76.2%。中国中学生卷入欺负行为的有21.2%,无关者有78.8%。2.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欺负情况在国籍和性别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3.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只有母亲教养方式的二个因子——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对中学生欺负行为的主效应显著,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均不显著。4.马来西亚欺负受欺负者的母亲比欺负者、受欺负者和无关者的母亲更多地采用惩罚严厉的态度对待孩子,中国受欺负者的母亲比无关者的母亲更多地采用拒绝否认的态度对待孩子。
张海燕[3]2005年在《小学生欺负行为调查及干预研究》文中指出欺负行为是中小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性行为,它无论对受欺负者还是对欺负者都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近年来,许多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学校教师和心理学家对欺负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且积极探索着系统有效的干预策略。本研究试图通过实验方法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欺负行为系统干预模式。 本研究抽取某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各两个自然班作为实验班和对照班,对实验班实施干预,干预分为三个层次:即班级干预、小团体干预、个体干预。班级水平上的干预主要是:召开反欺负家长会议、教师会议、班级会议、制定反欺负班规,使家长和教师对欺负行为加深了解,重视和正确处理儿童之间发生的欺负事件。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给儿童一个反欺负的外部环境,在给予受欺负者社会支持的同时削弱欺负者可能获得的“社会鼓励”。小团体水平干预是通过活动建立学生间的互动情境,引发学生之间的积极同伴互动,借此完善他们的人格特征,减少欺负的发生率。研究中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创设了一种互相尊重、彼此接纳的情境和氛围,使学生在认知、情感、行为各方面均受到影响,进而促进其人格特征的改善,从而使欺负干预达到较深层次。个体水平上的干预主要针对严重欺负者和严重受欺负者而进行,通过访谈了解他们经常卷入欺负事件的具体原因,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以期改变其严重欺负或严重受欺负地位。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小学生中欺负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 2.小学阶段男女受欺负状况基本相同,而欺负者男生显著多于女生。 3.三年级受欺负儿童比率及程度显著大于五年级,而欺负者比率及程度无显著差异。 4.通过干预,实验班受欺负和欺负他人的发生率均有下降,其中受欺负者比率显著下降;实验班受欺负程度得分和欺负程度得分均有下降,其中受欺负程度得分下降达到显著程度。
李淼[4]2010年在《大学生欺负行为与体育干预研究》文中指出欺负行为是指力量较强的一方(一个或多个)对力量相对较弱的另一方(一个或多个)经常有意识实施的有伤害性结果的负面行为。根据欺负行为的发生方式分为三种类型:直接身体欺负、言语欺负、关系欺负。欺负行为是社会群体常见的侵犯行为,普通高校中也普遍存在,大学生欺负行为对大学生学习、心理、社会发展和高校和谐校园环境的构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研究大学生欺负行为的内涵现状,解析大学生欺负行为与体育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拓展欺负行为研究的领域;对深化大学生欺负行为及其体育运动对其影响因素的认识,吸引更多的研究学者来关注和研究大学生群体当中的欺负行为现象,指导高校学生管理教育工作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比较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并以辽宁省普通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普通高校存在的大学生欺负行为进行探讨。其结果表明:大学生欺负行为以言语欺负和关系欺负两种欺负形式为主,各种欺负行为者在大学生群体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大学生欺负和被欺负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女生显著高于男生;理工院校理科专业与文科专业有显著差异,文科专业显著高于理科专业,体育院校体育专业与非体专业除关系被欺负形式外均有显著差异,非体专业显著高于体育专业;在年级和不同体育爱好行为特点上,大二和非常喜爱体育的学生检出人数最少,大四和不喜爱体育的学生检最出人数多;体育院校体育专业与理工院校理、文科专业大学生欺负行为有显著差异,理、文科专业显著高于体育专业。体育是在自然状态下对大学生欺负行为进行干预。体育对大学生欺负行为具有干预效果,对不同专业干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1)体育专业学生在参与体育运动的频数、时间、程度明显强于理工院校理、文专业学生。体育对体育专业大学生欺负行为干预效果明显高于理工院校理、文科专业;(2)体育专业学生在参与体育运动的频数、时间、程度明显强于非体专业学生。体育对体育专业大学生欺负行为干预效果明显高于非体专业;(3)非体专业学生在参与体育运动的频数、时间、程度明显强于理工院校理、文专业学生。体育对非体专业大学生欺负行为干预效果明显高于理工院校理、文科专业。通过本次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相关学生管理者应重视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欺负行为,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通过大学生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方式,对大学生群体中的欺负行为进行干预;在今后的大学生欺负行为研究中,针对大学生欺负行为干预做进一步的研究。
陈光辉[5]2010年在《中小学生欺负/受欺负的本土化内涵、基本特点及其与同伴背景的关系》文中指出Bullying研究始自上世纪70年代,自Olweus明确将bullying作为不同于aggression的一种不良行为展开系统研究之后(Olweus,1978),30余年的历程中先后有20余个国家和地区针对bullying的内涵、表现形式、基本特点、发生发展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干预等不同方面展开研究。我国的欺负研究始自上世纪末张文新对Olweus测量工具的引进(张文新,1999),国内十余年来的欺负研究大都采用Olweus问卷来考察欺负的基本特点和发生发展机制等,研究中都将欺负与bullying的内涵和外延完全对等。然而,欺负研究结果能否等同于bullying,二者是否可以进行跨文化比较,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二者的内涵和外延是对等的。本研究尝试从中国语言使用习惯和文化特点入手来考察欺负的内涵与外延,以证实欺负与bullying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异同。Bullying的核心特征是重复发生性,然而欺负一词的内涵中没有强调重复发生性,而是注重对力量不均衡性的表达。如果说重复发生性注重的是行为使动方所具有的特征,而力量不均衡性则是从行为双方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的特征。欺负行为不是先天具有的,因此其发生和发展机制更应该从行为双方的具体关系及其所处的关系网络来进行阐释。欺负发生于同伴群体中,是同伴互动过程的一种不良行为模式。不同同伴背景变量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能够使得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欺负的内涵特征,也便于考察欺负、受欺负发生发展的群体影响机制。本研究从一般性同伴地位、二元朋友关系特征、多元同伴网络特征三个层面考察了同伴背景特点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论文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系统考察了欺负的本土化内涵、表现形式、内在分类标准以及基本的发生特点,采用词源学考证、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数据信息,其中访谈和问卷调查的被试主要为中小学生。第二部分系统考察了一般性同伴地位(群体/个体同伴地位、异性/同性同伴地位)、二元朋友关系特征(朋友数量、友谊质量、友谊结构、朋友特征)、同伴网络特征(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网络中介性以及位置角色)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研究结果来自对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论文中总共涉及中小学被试2100余人。数据的整理分析使用的软件为SPSS13.0,Nvivo8.0,Ucinet6.2和PNET。研究所获得的主要结果或结论如下:1.欺负在中国是一种延续几千年的行为现象,内涵界定统一且稳定。能够同时描述这一现象的同义或近义字、词也几乎与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当。从古文典籍、成语、歇后语、惯用语、名言以及现代汉语词典中考察出的欺负内涵均为强者伤害弱者的行为。欺负内涵的界定性特征有二:力量不均衡性和伤害性。没有西方bullying的核心特征重复发生性。汉语使用中没有对欺负形式进行固定分类,并且欺负是攻击行为(aggression)的一个亚类,而不是攻击的亚类。2.中小学生的实际同伴交往中存在许多欺负现象,其界定性特征为力量不均衡性和因果性伤害关系,另外的一些特征可以有助于评判者获取这两个特征,如使动方的故意伤害性意图、受动方的受伤害性结果、难以反抗性、重复发生性和道德评判性。从表现形式来看,中小学生之间会采取身体、言语、关系和威胁等方式来实施欺负,但是其主观分类标准不是使动方实施欺负的方式,而是受动方遭受欺负的方面和程度。3.考察bullying测量题目的欺负确认率和自编欺负题目的欺负确认率发现,Olweus,Smith,Espelage所编制的三种bullying测查问卷的欺负确认率依次降低,自编欺负问卷的欺负确认率最高。欺负确认率的高低受到题目所暗示出的力量不均衡性特征和因果性伤害关系特征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动方的故意伤害性意图和受动方的受伤害严重程度对于欺负确认率的影响较大。从欺负确认率上来看,重复发生性信息也能够较好暗示出欺负的两个界定性特征。4.采用多维尺度分析和分层聚类分析发现,国内中小学生对欺负行为的分类依据为身体接触性-非身体接触性维度和敌意性-工具性维度,欺负行为倾向于被分为三类:造成生理伤害的欺负、造成心理伤害或关系损害的欺负、威胁。这与bullying的分类依据和分类结果不同。5.大样本的欺负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自编欺负问卷的因素结构并不理想。针对每个测量题目进行结果分析发现,男生比女生实施更多的欺负行为;年级差异因具体欺负行为而不同,中学生实施的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欺负行为显著高于小学生;男生认为不同的欺负行为主要发生在男生与男生之间,而女生则认为非关系欺负主要发生在男生与男生之间,关系欺负主要发生在女生与女生之间。欺负的两个内涵界定特征均是从使动方和受动方的关系上确定的,欺负、受欺负的发生发展也可能与个体与同伴的关系存在密切的关系。考察同伴背景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发现:6.个体角度获得的同伴地位(同伴接纳、同伴拒绝)与群体角度获得同伴地位(受欢迎、不受欢迎)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正向同伴地位上。受欢迎与欺负、受欺负均显著负相关,不受欢迎与欺负、受欺负均显著正相关;男生中的同伴接纳与欺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受欺负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女生中的同伴接纳与欺负、受欺负均显著负相关;男、女生的欺负、受欺负均与同伴拒绝显著正相关。男、女生的欺负、受欺负与同性同伴地位和异性同伴地位的关系模式存在差异,欺负的异性同伴地位高于受欺负的异性同伴地位。7.从二元朋友关系的角度考察同伴背景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发现,不良友谊质量、问题行为朋友特征、朋友数量均显著预测欺负水平,但是良好的友谊质量、朋友特征并不能够降低受欺负水平。处于不同数量化朋友结构和性别化朋友结构中的中小学生所表现出的欺负、受欺负水平存在差异,孤立者的欺负、受欺负水平显著高于大团体朋友结构成员和双性别朋友结构成员。8.小学生和中学生高、低欺负-受欺负班级中的朋友结构存在差异。中学和小学的两个班级中各有一个朋友结构相对开放和相对闭合。高欺负-受欺负班级内朋友结构倾向于更加闭合,并且部分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在能够形成自己的朋友结构或在主要朋友关系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低欺负-受欺负班级内朋友结构倾向于更加开放和不稳定,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均处于朋友关系结构的边缘化状态中。9.考察整体同伴网络结构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发现,网络密度大小能够负向预测受欺负,网络密度大的群体中的成员遭受欺负相对较少;个体在网络中的程度中心性,尤其是内向程度中心性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欺负和受欺负,即被班内同伴指认为好朋友的关系连接越多,其越不可能实施欺负和遭受欺负;个体在班级内所处的角色位置与欺负和受欺负没有稳定的联系,欺负者和受欺负者会随机分布在不同角色位置上,有时还会处于同一角色位置上。总之,整个论文立足于国际bullying研究前沿,围绕欺负、受欺负现象从两个切入点回答了欺负是什么和为什么发生欺负的问题。论文通过质性和量化研究明确了欺负和bullying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的异同,为正确解读本土欺负现象和跨文化比较结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二是从三个水平上系统考察了同伴背景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为更好地理解欺负现象的本质特征和欺负的同伴发生发展机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资料。另外,论文成功地将关系变量概念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了对发展心理学主题的研究。
马晓丽[6]2004年在《中小学生欺负行为的调查与相关研究》文中提出欺负是儿童之间以强凌弱的故意伤害行为,它是儿童之间滥用自身优势而对相对劣势者的故意伤害行为。本研究运用《儿童欺负问卷》、《艾森克人格测验问卷》和《家庭教养方式问卷》,采取匿名问卷法对中小学生中的被欺负与欺负行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欺负、受欺负儿童的人格倾向的差异、欺负与教养方式的关系等内容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1)中小学生的欺负行为严重存在。其中,28.0%的小学生频繁地被欺负,20.6%的小学生经常欺负别人;16.1%的中学生频繁被欺负,17.5%的中学生经常欺负别人。 (2)中小学生欺负和受欺负人数比例总体上随年级升高而下降,欺负和被欺负的男生人数明显多于女生。 (3)小学生以直接的身体攻击如踢打、推搡的欺负方式为主,其次是言语辱骂、破坏及其他方式,而初中生排首位的是言语辱骂,其次是身体攻击。 (4)欺负行为发生的地点排第一位的是教室,其次是操场和上学或回家路上。 (5)欺负行为与人格维度中的神经质和精神质有显著相关,被欺负行为与精神质有显著相关。 (6)欺负行为与家庭教养方式有一定关系,其中欺负与父母的专制、不一致的教养方式有显著相关,被欺负行为与父母溺爱及高期望性有显著相关。
肖娟[7]2009年在《对美国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应对策略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利用修订的学生欺负行为问卷调查(STUDENT SURVEY OF BULLYING BEHAVIOR-REVISED)对美国中小学生欺负行为的应对策略进行研究。主要对性别,年级,以及在欺负行为中四种不同的类型(欺负者,受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旁观者)与欺负行为的应对策略关系的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的应对策略包括:正面性策略(避免与寻
王倩, 韩仁生[8]2009年在《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的编制》文中指出本研究以归因理论为理论依据,借鉴国内外的归因测定工具,通过开放性问卷和访谈,确定了适合中国学生特点的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的结构和题目。该量表从内部-外部、稳定-不稳定性、可控-不可控性三个维度来探讨中小学生欺负行为的归因方式。它包括2×2×2共八个子量表,即ISC(内部稳定可控)、ISU(内部稳定不可控)、IUC(内
田峰溶[9]2013年在《小学生家庭功能、自我概念对欺负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欺负,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攻击行为,从上世纪70年代始,便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欺负行为不仅与个体自身心理特点有关,还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将影响欺负行为的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考虑能够更全面的解释欺负行为。因此本研究试图根据以往的研究,对小学生的家庭功能、自我概念对欺负行为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期能够进一步了解小学生的欺负行为。本研究从葫芦岛市和威海市的四所城镇小学中分层抽取三到六年级小学生,656名被试,以嵌入欺负和受欺负两个题目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Piers-Harris儿童自我概念量表》进行施测。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小学,欺负行为具有普遍性,男生欺负者显著多于女生欺负者,但被欺负者女生多于男生,却不存在性别显著;同时,欺负者和被欺负者的人数都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并且年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2.小学生家庭功能的现状表明,小学生家庭类型以平衡型为主,表现出较多的亲密-灵活类型和自由-有规律类型。在家庭亲密度上,高低年级存在显著差异,低年级小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得分显著高于高年级,即低年级的小学生与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强于高年级小学生,而在家庭适应性上,不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3.小学生自我概念的现状表明,当代小学生具有较高的自我概念水平;总体上,女生的自我概念普遍高于男生;随着年级的增长,小学生的自我概念发展呈现倒U型趋势。4.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小学生自我概念总分及各因子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家庭亲密度能够有效地预测自我概念各因子及总分,而家庭适应性则只能够预测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幸福与满足因子,家庭功能影响小学生自我概念;欺负行为的发生率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平衡型家庭类型较少的卷入欺负行为,中间型和极端型的家庭类型表现出欺负行为较多,家庭亲密度对被欺负的发生概率具有预测作用,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对欺负的发生概率有预测作用,卷入欺负行为的被试,其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没有显著差异;小学生自我概念和欺负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欺负行为的发生率。5.自我概念在家庭亲密度水平和欺负行为间起中介作用;自我概念在家庭亲密度和被欺负的发生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家庭适应性和被欺负的发生率间其完全中介作用。
王莉娟[10]2000年在《中小学生欺负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重点在于探讨小学3—6年级和初中1—3年级学生卷入欺负行为的情况,并进一步分析欺负行为与艾森克人格维度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中,使用量表法调查1122个中小学生小学67O人,初中452人对欺负问题的卷入状况,以探明中小学生欺负行为的现状。且进一步分析欺负行为与人格维度的关系,描述卷入欺负行为学生的人格特征。1.中小学生中有243人卷入欺负问题,比例为22.3%。其中共有184人报告为被欺负,比例为16.4%。其中共有59人报告为欺负行为,比例为5.2%。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着欺负和被欺负问题。 中小学生中受欺负的比例随年级升高而下降,被欺负行为存在显著年级差异。欺负的比例随年级升高而略有上升,但没有显著年级差异。 中小学生在欺负行为上,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受欺负方面,没有明显性别差异。2.欺负行为组在P维上得分高于其他组,被欺负组在E维上得分低与其他组。被欺负组在N维上得分高于未卷入组。欺负行为组和被欺负行为组,在L维上得分低于未卷入组。 男、女生受欺负得分与外倾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女生受欺负得分与神经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男生受欺负得分与掩饰性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男、女生欺负得分与掩饰性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男生欺负得分与精神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参考文献:
[1]. 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的编制[D]. 王倩. 曲阜师范大学. 2010
[2]. 华人中学生欺负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跨文化研究[D]. 邬洁妮.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3]. 小学生欺负行为调查及干预研究[D]. 张海燕. 山西大学. 2005
[4]. 大学生欺负行为与体育干预研究[D]. 李淼. 沈阳体育学院. 2010
[5]. 中小学生欺负/受欺负的本土化内涵、基本特点及其与同伴背景的关系[D]. 陈光辉.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6]. 中小学生欺负行为的调查与相关研究[D]. 马晓丽. 贵州师范大学. 2004
[7]. 对美国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应对策略的研究[C]. 肖娟. 第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 2009
[8]. 中小学生欺负行为归因量表的编制[C]. 王倩, 韩仁生. 第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 2009
[9]. 小学生家庭功能、自我概念对欺负行为的影响研究[D]. 田峰溶.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10]. 中小学生欺负行为研究[D]. 王莉娟. 河北大学.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