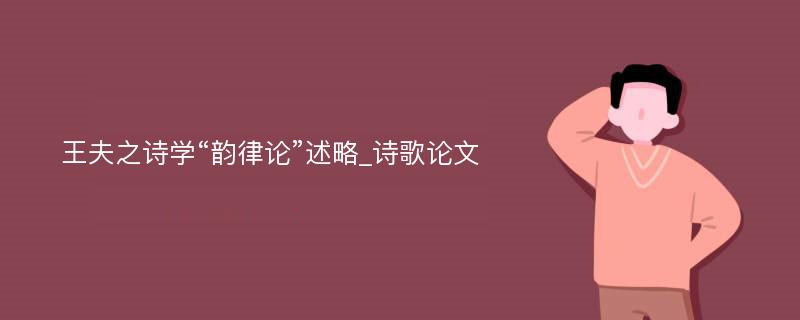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神韵论文,王夫之论文,述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典诗学史上,清代王士祯论诗好言“神韵”。其实,在王士祯之前,已有很多人谈到诗歌的神韵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船山在几部《诗评》著作中,大量使用“神韵”、“远韵”、“逸韵”、“清韵”、“风韵”、“缓韵”、“古韵”、“闲韵”、“幽韵”、“韵度”、“韵外得韵”等术语。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神韵”和“远韵”等术语。“神韵”属船山诗学理论体系中的艺术理想论范畴。由于学术界对船山诗学“神韵”论研究比较薄弱,故本文试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韵”等术语之辨析
“韻”字出现在东汉以后,并与音乐有关。自魏晋起,“韻”的含义发生演化:一方面保留了它的本义,即指音韻之“韻”,亦即音乐或声音的韻律,如魏曹植《白鹤赋》,“聆雅琴之清韻。”嵇康《琴赋》:“改韵易调,奇弄乃发”。另一方面“韻”进而向整个人生世界以及艺术领域拓展,被赋予更为广泛的美学含蕴。例如,受玄学影响,士人始用“韻”字品评人物的言行,指人的神情、神思、神貌、风神、风度、风资等,说明人的神情和风度的清雅、清远、闲淡、淡远、通达、放旷以及超拔尘俗等,故又往往是“风、韻”连用。如《晋书·庚凯传》云“雅有远韵”。
“韵”之前加以“神”做修饰性限定,则用以表示“韵之神”。“神”在中国古代美学和诗学中大致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指神思或作家之精神(心灵)以及创作中的艺术思维活动,多言创作时精神的专一或自由超越,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神与物游”、“神用象通”。二、指神明或神灵,多用以说明文艺创作中灵感勃发宛若有超自然的力量相助,如杜甫诗云“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皎然《诗式·序》云“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三、指与形相对立的“神”,即形神之神,如《世说新语·巧艺》载顾恺之论画:“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张怀瓘《画断》亦云:“象人之美,张(曾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见《历代名画记》)。四、指作品的内在精神本质,如明代焦竑《题词林人物考》云:“论人之著作如相家观人,待其神而后形色气骨可得而知也。”五、指艺术创作或艺术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极致有二: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注:以上参见成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神”这一条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总之,“神”在诗学和美学中既然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那么,以“神”修饰“韵”,更表示“韵”的神秘、神奇、神奥、神妙等。
关于“神”这一传统范畴,船山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船山对“神”概念多有论述。在此强调的是,“神”往往被船山称为“幽明之际”,而对“神”或“幽明之际”的把握则是人的认识的理想境界或最高境界:
今夫鬼神,事之所不可接,言之所不可酬,仿佛之遇、遇之以容,希微之通、通之以音,霏微蜿蜒,嗟吁唱叹,而与神通理,故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大哉圣人之道,治之于视听之中、而得之于形声之外,以此而已矣。(《诗广传》卷五,《论商颂二》)
呜呼!能知幽明之际,大乐盈而《诗》教显者,鲜矣,况其能效者乎?效之于幽明之际,入幽而不惭,出明而不叛,幽其明而明不倚器,明其幽而幽不栖鬼,此《诗》与乐之无尽藏者也,而孰能知之!(《诗广传》卷五,《论周颂六》)
总之,“神”乃“理”之神妙变化的体现、本质或依据。可见,“神”亦即“理”的妙用。在诗学研究中,船山既强调“体物而得神”,又主张“脉行肉里,神寄形中,巧参化工,非复有笔墨之气”,因而要“取神似于离合之间”(《古诗评选》卷四)。要之,“神”指诗人运用主体之“神”对事物的审美本质加以审美真觉,从而创造出象外有象、象外有意、韵外有致、味外得旨、意蕴无穷优秀诗篇的这样一种能力或境界。
船山在“韵”之前加一个“神”做修饰和限度,边缀成“神韵”一词,则用以说明“韵”之神妙不测。船山在几部诗歌评选中更是频频使用“神韵”一词来评论他喜爱的诗歌作品。且不说含有“神韵”之义的评语,单是明确地使用了“神韵”这一概念的地方就多达20余次。如,评王韦《与陈宗虞夜坐》“须如此种诗不入晚唐,亦不入宋,为复何故?只有神韵好。”(《古诗评选》卷五);评张宇初《晚霁》“宽平澹静,自有微至,真国初一好手;温于青田,密于来仪。抑昭代有数作者,在临川、季孟之间,神韵稍逊之,情理不相让也”(《古诗评选》卷四);评贝琼《秋怀》“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彦昺、廷琚,国初一双玉箸,更不令三百年来作第三座也”(《古诗评选》卷四)。以上几条评论所言“神韵”与“远韵”意义相同,可以互换,均是从诗的韵律、押韵、韵脚所产生的音乐美特征立论,认为这些诗作的声韵美不同于按四声八病说刻板填写出来的诗美,而具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音乐美,故谓之“神韵”。船山在几部诗评著作中还经常使用“远韵”、“韵外之韵”等。“远韵”者,说明“韵”之“清远”、“淡远”、“冲远”、“玄远”。而在“韵外之韵”这个术语中,第一个“韵”当为“声律”或“音韵”,第二个“韵”则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言以蔽之,船山所说的“神韵”、“远韵”、“韵外之韵”等涵义几乎相同。若单用“神”、“远”或“韵”的评论则多达几百则。总之,“神韵”论是船山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神韵”论在船山诗学理论体系中是一个标识诗学理想论的范畴。
二、“神韵”、“远韵”、“韵外之韵”之内涵
船山对“神韵”、“远韵”、“韵外之韵”等概念的论述没有较为系统的表述,而是散见于各类诗评文字之中。仔细考察和分析船山所论之“神韵”、“远韵”等,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强调“清神远韵”(《明诗评选》卷五,许继《自遣》评语),把“神韵”、“远韵”与诗人的生命之气、精神之气,与诗人主体清雅、清逸的神情联系起来评论,似乎兼综了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谢赫的“气韵生动”以及魏晋时期以“韵”来品评人物的美学传统等。船山认为,“神韵”或“远韵”来自诗人审美人格的神清气爽,来自诗人审美情感的清逸或雅正,来自审美主体的洒脱、幽深的风神和神情,是诗人清雅、清逸之风神与作品之委婉、和缓之音韵二者的异质同构。如:称“《关睢》之钟鼓琴瑟,《鹿鸣》之笙瑟簧琴,‘以友’、‘以乐’、‘以敖’,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容已。以此好德,非性其情者,孰能此哉?”(《诗广传》卷三,《论小雅一》)又如:称赞刘荣嗣《坐王氏园亭作》“清思中有远韵”(《明诗评选》卷六);又称李东阳《春兴》“高情远韵,不落古今,正尔赅成千载”(《明诗评选》卷六);称高启《采莲泾》“有韵有意”(《明诗评选》卷四);称赞梁有誉《咏怀》“神情远,音节舒”(《明诗评选》卷四),等等。下面评语所表述的亦为此意,如:
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桓其孰得哉?但此已空千古。陶、韦能清其所清,而不能清其所浊,未可许以嗣响。(《古诗评选》卷一,曹丕《善哉行》评语)
沈远之调。王昌龄学此,乃不能得其适、怨、清、和。(《古诗评选》卷六,谢脁《和王中丞闻琴》评语)
太史清姿自绝,未能为韩、苏所困,泛滥时不能自已。如此作者,道气雅情,骚肠古韵备矣。(《明诗评选》卷四,宋濂《清夜》评语)
其韵其神其理,无非《十九首》者。总以胸中原有此理此神此韵,因以吻合;但从《十九首》索韵索神索理,则必不得。江醴陵、苏韦州一为仿古诗则反卑一格,以此。(《明诗评选》卷四,刘基《旅兴》评语)
对于那些缺乏清雅、清丽之气,缺乏清远、清逸性情的诗人诗作则给予了某种批评,如对前七子的那种关东大板似的诗歌音乐美提出异议,指出:
空同以来,名艺苑者不鲜,五言近体亦斐然可观。七言之作殆乎绝响。计诸子之自雄,正倚七言为长城,得尽发其喷沙走石之气。乃彼所矜长,正其露短,神韵心理,俱不具论。(《明诗评选》卷五,顾璘《共泛东潭饯望之》评语)
其二,称赞诗的“用韵使字”等表达上的含蓄、蕴藉之美,认为诗歌“神韵”乃是一种言外有意或不以言胜而以韵胜的美,即所谓“大有警心,在风韵之外,非以言也”(《古诗评选》卷二,庾信《皇夏》评语)。如,船山指出:
用韵使字,俱趋新僻,早已开松陵、西昆一派。其寄托俯仰,具有深致,固有古度未衰。(《古诗评选》卷五,鲍照《园中秋散》评语)
亦似铭似赞,故近人亦知赏之,既似铭、赞,则更非诗矣。深达之至,别有神韵,固非赏此诗者所知。(《古诗评选》卷二,袁宏《从征行方山头》评语)
亦往往在人意中,顾他人诗入人意即薄劣,谢独不尔。世有“眼前景物”之说,谂此亦非不然。虽然,岂易言哉!……且如此诗,用“想见”二字,不换气直下,是何等蕴藉!抑知诗无定体,存乎神韵而已。(《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评语)
光响殊不似刘,刘俊,鲍本自俊,故鲍喜学之。然起二语思路远,遣向有神韵,固已敻绝。(《古诗评选》卷五,鲍照《学刘公干体》评语)
其三,认为“远韵”来自诗歌作品的整个艺术结构或韵度,这种结构或韵度具有一首优美乐章那样的从容、圆润、飞扬、清纯、雅正和悠远等。如称赞陆机《谷风赠郑曼季》“有言必善,无韵不幽,十句如一句,四十字如一字也”(《古诗评选》卷二);称赞江淹《效阮公诗》“一气不待回换,自不迫促。神韵则阮,风局则《十九首》矣”(《古诗评选》卷五);称赞庾信《对酒歌》“果尔清新!落尾四句俊而有余,足为乐府绝技”(《古诗评选》卷一);称赞白居易《杭州春望》“韵度自非老妪所省,世人莫浪云‘元轻白俗’”(《唐诗评选》卷四);称赞刘长卿《长沙早春雪后临湘呈同游诸子》“一结自然清韵”(《唐诗评选》卷四),等等。此外,船山还指出:
转速而气为之伤,而凄清之在神韵者,合初终为一律,遂忘其累。(《古诗评选》卷一,谢脁《铜雀台同谢谘议赋》评语)
子山小诗佳者挟英气;英气最损韵度,正赖其俯仰有余耳。(《古诗评选》卷三,庾信《和侃法师别诗》评语)
用神用气用韵度,但不用俗诗画地牢耳。子价真有渊源。五六入事,点染成致,非七才子辈寻事填腔活字印板套也。(《明诗评选》卷六,朱曰藩《鸡笼山房雨霁》评语)
忽然集,唐然纵,言之砉然止,飘然远涉,安然无有不宜。技至此哉!为功性情,正是赖耳。(《古诗评选》卷一)鲍照《代白苎曲》评语)
藏吐有风裁。永乐初,大绅、光大风韵自存。(《明诗评选》)卷一,解缙《怨歌行》评语)
通首求之,逐句求之,逐字求之;求之高,求之远,求之密,求之韵,求之变化。呜呼!尽之矣。(《明诗评选》卷四,蔡羽《九月十四日集东麓亭》评语)
其四,称赞诗的声韵、韵律或押韵合于诗人审美情感或诗人深远复杂的精神世界,因而“神韵”乃是诗歌作品的一种清远、幽深的意蕴美,诗有“神韵”意味着能给读者以一种意味无穷的美感。如,称赞徐孝嗣《答王俭》“神清远韵,晋宋风流,此焉允托”(《古诗评选》卷二);称赞简文帝《乌栖曲》“远思逸韵,为太白横江词所祖”(《古诗评选》卷一);称赞戴嵩《车马客》“裁成不迫促,正使曲终尽三叹之致”(《古诗评选》卷一),等等。船山在以下评语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如,他指出:
文章之道,自各有宜。典册檄命,故不得不以爽厉动人于俄顷,若夫絜音使圆,引声为永者,自藉和远幽微,动人欣戚之性。况在五言,尤以密节送数叠之思;矧于近体,益以简篇约无穷之致。而如建瓴泻水,迅雷破山,则一径无余,迫人于口耳,其余波回嶂,岂复有可观哉?(《唐诗评选》卷三,高适《自蓟北归》评语)
推含不测,就事逼真,慷慨流连,引古今人于无尽,逼真汉人乐府。(《古诗评选》卷一,梁武帝《河中之水歌》评语)
就地曲写,韵外得韵,……正不知有万里之源,天高日丽,银汉仙宫也。(《明诗评选》卷六,梁有誉《秋日谒陵眺望》评语)
陶、谢以下,不闻寄托之音久矣。……深思远情,正在素心者。……心理所诣,景自与逢,即目成吟,无非然者,正此以深人之致。(《古诗评选》卷五,江淹《无锡县历山集》评语)
就当境一直写出,而远近正旁情无不届。未尝不为清音高节,乃陶、谢风旨居然未远,五言之正宗赖以仅存。如此不愧与青莲同其光焰。笔欲放而仍留,思不奢而自富,方名诗品。(《唐诗评选》卷三,杜甫《初月》评语)
总之,“神韵”不是一种简单的悦耳动听,而是一种“大音希声”的美,即所谓“大音有希声焉,大烹有淡味焉,絺繍有隐色焉。人之所不可以视见听闻食知味者,莫此甚也”(《诗广传》卷四,《论大雅·三八》)。
船山对“神韵”、“远韵”的理解是符合现代心理美学原理的。从最本原的意义上说,“神韵”“远韵”来自诗句的声音及其组合(亦即船山所说的“韵外得韵”的第一个“韵”),但又超出声音的简单组合之上,它已具有一种新质(“韵外得韵”的第二个“韵”),类乎西方美学的“格式塔质”。我国古人也早认识到这个道理,如张戒《岁寒堂诗话》称“咏物者要当高其格致韵味,下得其形似”,将“格致韵味”置于“形似”之上。徐渭《题百花图长卷》亦云“不求形似求生韵”,视“生韵”高于“形似”。我国现代新儒学思想家、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释气韵生动》一章分析得更加透彻精辟,他认为:“音乐和文学上的韵,实际是由各种音响的谐和统一而成立的;也即是不离各种音响,但同时又是超越于各音响之上,以成为一种统一地音响,而这种统一地音响,是可以感受而又不能具体陈述的东西;因此,韵可以说是音响的神。也如人的不离形相,而又超越于形相之上的谐和而统一的‘神’或‘风神’,是相同的情景。”(注:见《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无独有偶,钱钟书先生也称:“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托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亦不离。”(注:见《钱钟书论学文选》第3册,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船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神韵”、“远韵”、“韵外之韵”等概念的,故称“信未闻之中有声,则其聪密;信未见之中有色,则其明浚……”(《诗广传》卷五,《论周颂十七》);又云“故言之善者,危音亢词,曲尽广引,而神不随之流也:其流者必不善者也”(《诗广传》卷五,《论周颂二十》)。此外,如前所述的各条评语都应作如是观。如评胡翰《郁郁狐生桐》“不谋而至,不介而亲,不裁而止。一引人远,一引人近。此所谓大音希声也”(《明诗评选》卷四);又如评徐陵《春情》“排律在大历以上,率繁重坚确;大历届以下稍为疏宕,又多郎当敷衍,密者如启如赞,疏者如论如说,风雅之道,坠失无遗。尽唐一代,能如此高朗冲秀有余韵者,千不得一二,何况宋人?唐之不逮陈、隋,犹宋之不逮唐也。”(《古诗评选》卷六)
当然,以上几层含义的划分并非绝对的,但通过上述丰富而又以片言只语形式存在的主要观点的梳理,可以大致认识船山诗学“神韵”观的基本内涵。
总之,“神韵”、“远韵”、“韵外之韵”等诗美源于诗歌的声情美,又超越于诗歌的声情美,它们所标举的是一种大音希声、余音缭绕、意味绵长、意境悠远的诗美,这种诗美显然为诗歌艺术的极致或至境,是船山对诗学艺术理想的表达。需要指出的是,船山“神韵”论的特色在于主要着眼于诗歌音乐美来理论。船山认为,诗的最高境界(无论是诗的性情、诗的意象、诗的意境,还是诗的声情、诗的韵律、诗的语言以及诗的结构等)都应该像音乐一样,都应达到音乐那种纯美的境界,而且是大音希声的境界。如,船山指出:“故《诗》者,与《书》异垒而不相入者也。故曰:‘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知然,则言固有所不足矣。言不足,则嗟叹永歌,手舞足蹈,以引人于轻微幽浚之中,终不于言而祈足也。”(注:《诗广传》卷五,《论鲁颂一》。)船山在这里不仅对诗与其他文体作了区分,更指出了诗的音乐美的极致状态,即把欣赏者“引入于轻微幽浚之中”,进入对某种终极的神妙的美的体验。这个意义上的诗之音乐美已不仅是一个诗的声情或情景的问题,而是对情景与声情的超越。是对某种超越的终极的诗美的追求。因此,“神韵”论属船山诗学理想论的范畴。
三、“神韵”与“取势”、“神理”的比较
虽然同为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但“神韵”与“取势”、“以神理相取”不同,“取势”和“以神理相取”着眼于诗歌审美意象基础上的意境美。“取势”乃在形神之间、主客之间、物我之间、情景之间以及意象与意象之间领悟出某种审美的诗意的联系。“取势”的结果是创造出一种动态多变、虚实结合、夭矫连蜷、回味无穷的艺术审美境界,所以说“取势”是如画论所称“咫尺有万里之势”,是“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以神理相取”亦是诗人于审美感兴中在形神之间、主客之间、物我之间、以及意象与意象之间发现并传达出某种诗意的(在远近之间)的联系(相因依,相含吐),这种发现是在审美感兴中实现的,这种传达是以宛转屈伸、含蓄蕴藉、富有暗示性和包孕性的艺术表达来完成的。诗人善于“取势”和“以神理相取”不等同于他的作品有“神韵”,故船山在评嵇康《曾秀才入军》时才说“二章往复养势,虽体似风雅,而神韵自别”(《古诗评选》卷二)。究其原因,乃在于,“神韵”主要是从诗的韵律、押韵、声韵、声情等音乐美特征立论,称赞诗歌艺术最高的声韵美决不同于按“四声”“八病”说机械填出来的声律,而具有一种妙不可言的具有终极价值的音乐美。要之,“神韵”源于音乐的声韵美而又超越于声韵美,“神韵”是诗歌音乐美的极致状态。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引郑朝宗说所云“神韵乃诗中最高之境界”(注:《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我们可将船山诗学的“神韵”论与“取势”论略加比较,比见出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如船山指出:
《纪事》称其不为新语,律体务实。所云“新语”者,十才字以降枯枝败梗耳。虚实在神韵,不以兴比有无为别。如此空中构景,佳句独得,讵不贤于硬架而无情者乎!以此求之,知此公之奏《雅》于《郑》、《卫》之滨,曲高和寡矣。(《唐诗评选》卷四,杨巨源《和大夫边春呈长安亲故》评语)
显然,这里的“神韵”即虚实相生,与“取势”一致。但是,以下评语则不然:
六代人作七言,于末二句,辄以五言足之,实唐律诗之祖,盖歌行之变体也。对仗起来固自精贴,声韵亦务谐和,乃神韵骏发,则固可歌可行,或可入乐府。如此首前四句。句里字外俱有引曳骞飞之势,不似盛唐后人促促作辕下驹也,故七言律诗亦当以此为祖,乃得不堕李欣、许浑一派恶诗中。呜呼,知古诗歌行近体之相为一贯者,大历以还七百年,其人邀绝,何怪“四始”、“六义”之不曰趋于陋也!(《唐诗评选》卷一王绩《北山》评语)
这里的“神韵”更着眼于音乐美的角度。正因为此,船山称赞汉高帝《大风歌》“神韵所不待论。三句三意,不须承转,一比一赋,脱然自致,绝不入文士映带。岂亦非天授也哉!”(《古诗评选》卷一)。案,刘邦《大风歌》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船山称此诗有“神韵”显然是从诗的音乐美角度来说,与后来的王士祯不完全一样。船山还有一段较长的文字论及“神韵”,更能见出“神韵”与诗的声韵美有关,他指出:
四言之制。实自《诗》始。广引充志以穆耳者,《雅》之徒也。微动含情以送意,《风》之徒也。《颂》为乐府之宗,即不主于四言,而与《诗》别类,其以歆鬼豫人,流欢寄思,将资于丝竹以成声,非全恃其言而已。是知匪《风》匪《雅》,托无托焉。自汉以降,凡诸作者,神韵易穷,以辞补之。故引之而五,伸之而七,藏者不足,显者有余,亦势之自然也。非有变也。……西晋文人四言,繁有束、傅、夏侯,殆《三百篇》之王莽。入隐拾秀,神腴而韵远者,清河(案:指陆云)而已。(《古诗评选》卷二,陆云《谷风赠郑曼季四首》评语)
显然,这里的“神韵”指那种“永在言外”的“晋魏以上”之诗的音乐美,魏晋以上的古诗有一唱三叹、意蕴悠长的诗美。
另外,在船山诗学评语中有一句“杜得古韵,李得古神”,曾受到有的学者的注意,但却未作出满意的解释。这句评语出处如下:
十全古诗,一无颣迹。“明月春欲堕”二句,从“高楼”、“玉台”生出,虽转势趋下,而相承不更作意。少陵从中生活,边有拖带。杜得古韵,李得古神。神、韵之分,亦李杜之品次也。(《唐诗评选》卷二,李白《拟古西北有高楼》评语)
本文提出一解,聊作引论。笔者认为,“杜得古韵”当指杜甫善写古体诗,尤其是指杜甫敢于对沈约的声律论说“不”,经常创作一些拗体诗,因而具有“沉郁顿挫”的风格。正因为此,船山在《古诗评选》中选杜甫的乐府歌行以及古诗多达三十余首。可见船山对杜甫古体诗之喜爱;同时,船山对那些拗体诗(包括杜甫的拗体诗)每每要特别地加以指明。所谓“李得古神”则应当指李白诗歌作品“风神清远”,飘逸超拔,远胜于杜甫诗情之俗;同时也指李白诗歌在“内极才情,外周物理”方面神妙莫测,为他人所难以企及。
严格地说,除了将“神韵”与诗的音乐美相联系有自己的特色之外,在对于“神韵美”的神清韵远、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内涵的开掘方面,船山超出前人之处并不多见,更多的体现为继承、吸收、综合前人的神韵论诗学观念并将其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并且,为前人的“神韵”论发展为稍后于船山的王士祯的“神韵”论,接上了诗学演进的脉络。船山“神韵”论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将“神韵”说与古代《毛诗序》、《尚书》、《礼记·乐记》中的传统儒家诗论、乐论联系起来,使传统儒家典籍中的相关思想资源获得了新的阐释,从而也使“神韵”说获得了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