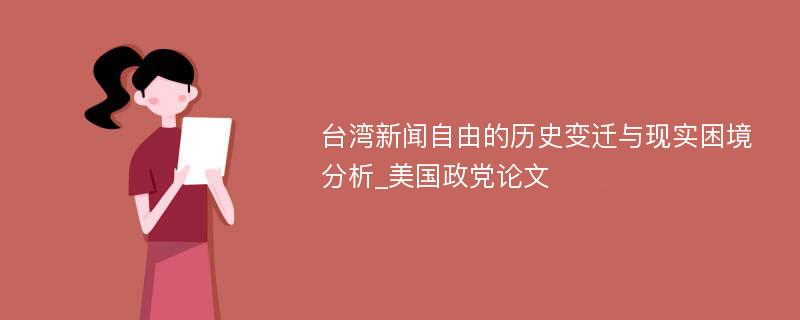
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台湾论文,困境论文,现实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称,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超越了美国和日本。①追溯台湾新闻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其自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本文从戒严统治时期、解严后及政党轮替后三个不同的时期,梳理了台湾新闻的历史变迁,并探讨其现实困境的成因,以期为理解台湾新闻开放的历史与审视其现状提供理性指导。
一、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新闻
极权统治时期,台湾新闻丧失了“第四权”的本义,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言论、新闻自由成了虚无的镜花水月。
(一)“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新闻自由无法伸张。台湾“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表明“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然而在解严前,台湾新闻自由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新闻自由无法得到伸张。戒严统治时期,为有效地控制当时社会和民众,国民党政府不仅施行“限张、限纸、限证、限价、限印”一报五禁的“报禁”,进行文化清洁运动对新闻进行严密管制,还实施了《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称〈九项禁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等一系列严苛的法令,“其中以1958年,‘立法院’密审议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对报刊警告,罚款,停止发行,撤销登记等处分之权利,对新闻自由带来很大伤害。”②出版法一直是钳制台湾新闻自由最主要的法律,直到1998年,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废除。在威权体制下,“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不平等,国民党威权政府从上而下的控制新闻媒体,让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倍极艰辛。”③虽有“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为基本权利,但在当时政府不仅以政策、法令规定媒体的目标、任务,介入媒介管理,而且还制定了媒体审查制度;军事单位还介入到媒体检查工作中,对新闻媒体实行严厉的事前请示、事后检查制度,更有党部组织对新闻机构进行严密的监控,新闻自由成了镜花水月,遥不可及。
(二)新闻媒体沦为极权统治“侍从”。对于新闻事业的所谓“反动言论”,国民党统治机器有许多制约的法宝,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查禁、停刊、撤销登记,甚至逮捕负责人与撰文者。④国民党政府一面操控、镇压大众媒体,另一方面又利用媒体向人们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民众建构特定的世界观,企图让人们接受权威统治,放弃抗争,并将权威控制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新闻媒体俯首称臣,成为极权政府的“侍从”,国民党政府对媒体“不同声音”进行打压迫害。当局根据尚未公布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条文,勒令言论最尖锐的《公论报》停刊三天,首开台湾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先例。此后,查封《天南日报》、《中国时报》、《民族报》、及《民众日报》停刊、三次叫停《自立晚报》、《经济日报》休刊,各报均遭不测;国民党还制造了刘自然事件、白克案、船长事件以及电台总经理刘晋钰案等传播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制造了传播、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极权政府对从事媒体事业人员进行辅助、奖励和优待,以收买人心,让新闻工作者在恩威并用的国家机器面前低头。政府对媒体的辅助、奖励与优待,散见于出版法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以及邮政法、邮政规则、新闻电报规则等与其他的相关法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⑤:配售食米、配售木材、申请外汇、办理新闻记者出国、新闻出版品传送优惠、交通优惠措施等六项。并通过暴力改组《公论报》、争夺《工人报》发行权、《联合报》退报运动等手段争取媒体,“国家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广电法、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限制媒体的发展,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论、规范媒体内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更甚者,结合(国民)党、政、军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⑥,以使媒体完全臣服为政府的传声筒。
(三)极权管制中的新闻:寻求正当化的传播途径。面对新闻自由备受管制、新闻媒体几乎丧失其社会功能的局面,新闻界只能在威权统治下积极寻求传播的正常渠道,为新闻自由的伸张而不懈的进行各种努力。
国民党政府威权时期制造文字狱和文字迫害事件,使得新闻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其间最早与党国机器相异的声音来自对《杂志不得设记者》禁令的反对。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发杂志业者与政府长期不休的争议,首开“异声”先河。“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屡次选派代表向“内政部”陈情,还在1969年2月4日以“国协字”第一五八号代电致“内政部”,请求“内政部”变更一六七九九号解释的《杂志不得设有记者》一令。1975年9月1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还提出《杂志社记者问题之研究》的报告,从法理、事实和性质等三方面提出杂志应设立记者,却遭到新闻处更严厉的惩处。此场争议历时10年之久,1988年新闻局长邵玉铭才宣示“政府对杂志设立记者的管制,应依出版法规定办理,并应将新闻记者法与违反出版法之相关法令排除。”⑦该宣示为杂志设立记者带来了一线曙光。1991年,新闻局举行出版业的新闻联谊酒会,邵玉铭当面告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理事长,“杂志社不得设记者之禁令已解除”⑧。此举是台湾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胜利之一。
“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媒介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媒介和政治反对运动相互支援的现象,”⑨从1974年到1984年这10年里,台湾一共出现了55种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志,声势和数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杂志不断冲击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当局禁忌,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尺度。
此后,新闻界也以各种方式寻求极权管制下的新闻自由途径,如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完成立法程序,于1976年1月8日公布广播电视法,成为台湾管理广播电视事业第一个立法的法令,明确权责分配,广电业务归新闻局广播电视处管辖,频道使用和规范归“交通部”总管,结束了台湾广电事业“无法无天”的日子,电子媒体这才“脱离以行政命令为最高法源管理电子媒体的模式。”⑩
二、解严之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新闻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报刊、电视等媒体数量激增,言论相对开放,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竞争的时代。
(一)“后报禁”时代第四权理论的出现。进入政治多元时期后,台湾的威权体制日渐被“黑金体制”、政治派系所取代,黑道、金钱势力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途径利益,伴随着金钱、派系控制的强化,媒体意识逐渐觉醒,受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影响,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传播教育、研究的学者,希望媒体可以扮演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权”,在社会当中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林子仪在《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理论基础》中首次肯定新闻自由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并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理论建构“新闻自由”理念,主张新闻媒体有别于一般人民言论自由那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的基本权利”(11)。此后,学者沿用第四权的概念,强调媒体“第四权”的权利,寄希望于媒体发挥监督舆论,引导受众的社会功能。第四权的声张彰显了媒体在公共利益领域的突出作用,“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目的在于使新闻传播媒体成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等制度性功能。林爱翎就曾提到“民主化与商业化在今日的台湾推动着人们与社会之间产生新进的关系,媒体为其中意义的传递媒介,在呈现社会真实的同时,也受到商业与政治两股势力的影响,并扮演民主社会中第四权的角色。”(12)
但新闻媒体事业的运作十分复杂,而且特别易受政府的操纵、压力等,伤害到新闻媒体独立自主性。台湾媒体在走过传统的威权政治全面掌控时期后,按理应该努力从政治“传声筒”逐渐转变为民众“良友”的角色。无奈的是,受禁锢的台湾“第四权”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就开始受到台湾政治力量与商业力量的双重冲击。原来备受媒体打压的对象试图取得媒体的经营权,政府、财团对于媒体的管控也日渐增加,新闻媒体在享受“无冕之王”美誉的同时,又如何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其在“监督政府”的提示,是否也该接受他方的监督?对此,吴文成提出了“第五权”的概念,“我听到的说法就包括:网路是第五权,电子媒体是第五权(相对地,平面媒体是第四权),学术界是第五权,媒体观察相关的基金会是第五权,目前比较顺耳的说法是,民众是第五权。但是不管如何,新闻媒体的确是需要自律或是被民众制约,而所谓的第五权绝对不应该是来源於政府或是被政府控制的机构。”(13)
(二)“第四权”的商业化、市场化。新闻媒体报禁解除之后,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但对政府施政能力的监督力度却并未相对提升,反而有“自愿被收买”的倾向。以有线电视为例,其发展就存在膻腥色、植入式行销、政治选边站以及新闻专业的红色警报等四方面的争议性问题。资深媒体工作者吴恕认为,“置入性行销完全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功能。而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以被赋予第四权,就是要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如果政府可以透过金钱操控媒体,影响民众的正确判断,事实上是阻碍了民主的正常运作,跨越了媒体与政府间的均衡界线。”(14)
2003年年12月5日,《中时晚报》与《联合晚报》卖掉整个头版,在一版同时出现了中国信托的全版广告。新闻被广告取而代之,这在台湾的媒体历史中还是第一次,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争议。作为媒体生存的主要来源,广告控制新闻已屡见不鲜,许多大商家看准媒体的投鼠忌器,在某些事件爆发之际即以广告预算对媒体进行新闻控管;媒体为了获得更大利润,新闻内容往往会优先选择有“兴趣点”的灾难、情杀、重大犯罪等意外事件来报导,徐佳士就认为“第四权”的本义已经被误解、误用,甚至歪曲,媒体的利益导向取代了“第四权”的神圣使命。
1999年春节前,裕隆汽车的劳资争议案发一个多月仍无媒体问津,“究其原因,因为裕隆汽车一向是国内汽车广告的大宗客户,造成媒体在新闻处理上可能有潜在性的压力。”(15)这实在不得不说是媒体的一大悲哀。公众期待新闻媒体准确而公平的进行报道,以“第四权”监督政府和社会,为社会的发展献策出力,推动民主化的进步。但解严后,台湾媒体的公信力不升反降:亲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育成的“脚尾饭”影带;TVBS记者自拍的《周政保呛声录影带》;还有2004年3月,电视台在“总统”大选开票之夜集体灌票造假,欺骗受众的丑闻等等。这些都让台湾媒体的“新闻自由”蒙上了一层灰色,新闻自由的滥用不但导致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也引来了学界和业界的持续批评。
(三)“新闻自由”公共服务意识觉醒。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的功能不断丧失,受商业力量驱使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新闻自由对公权利、私权利的侵犯,媒体为了争阅听率、发行量、收视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外交机密泄漏等公权利,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新闻广告化、出卖版面、植入式行销等等都备受批判。
解严之后,台湾媒体出现过一段百花齐放的竞争,但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挂帅,收视率、发行量凌驾一切,广告主掌握媒体生杀大权,“在整个转化过程中,公众利益有时候被抬得高高的,有时却被摆放在一边。”(16)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极权政治力的远去并未让媒体得到真正的自由,资本力的制裁和约束,让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了新的一种管制。学者们对此也开始进行了反思,“过去,我们向集权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现在,享有了新闻自由之后,我们才突然惊觉,原来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17)因此,学者提出,媒体应成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徐佳士曾对台湾媒体乱象进行批评:“在这种风气下,读者利益便被牺牲了。第一:缺乏纯净的,客观的,平衡的报道,读者既无法认识环境的真相。所谓‘知的权利’丧失殆尽。第二:对于一切新闻事件,是是非非已经被记者们下了定论,读者的判断权利也被剥夺了。”(18)
三、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总统直选”,陈水扁胜选,民进党执政,台湾首次完成政党轮替。政治阵营及国家认同的分化的大背景,加之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操控,使得台湾新闻自由在政党论题后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新闻自由“第四权”的沦丧。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进入低谷期,股票大跌、失业率亦创新高,媒体首当其冲,发行量、广告量直线下降。为转变经营困难的现状,各大报几乎全面“苹果化”,采用大图片,强化膻腥色新闻,将新闻广告化,甚至出卖版面接受政府及企业的置入式行销。媒体与政党关系的全盘颠覆,而快速转变的台湾政治、经济结构,还改变了媒体和政党的互动方式。这段时期的媒体“第四权”,已经完全驯服于政治力及商业利益。
媒体内部的压力来自于经营者的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老板为牟取经济、政治利益会选择迎合阅听人的最低级需求,让媒体阿世媚俗,生产受众喜欢的娱乐化、低俗化的内容。尽管部分较有历史责任感的媒体工作者也希望将使命感融入媒体,“传道授业解惑”以帮助世人认清局势,引导受众更好的使用媒体信息,但媒体的发行量、阅听率一旦未达媒体老板盈利的目标,又会招致媒体老板的责难,新闻工作者只能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下做出“正确”的选择。
除了媒体内部的控制外,商业、广告主也逐渐入驻媒体的运作。邱奕嵩就曾指出“除了媒体特定的立场钳制了新闻工作者外,日趋资本化及商品化的报业市场仍难逃商业巨兽的吞噬。广告主发行商业及通路业者,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左右新闻报道时有所闻,且有变本加厉之趋势。新闻工作者所谓的理想也只能在于现实压力之下,图谋有限的发挥空间。”(19)资本力的侵入宛如掐住了媒体的人中命脉,让媒体工作者的“理想”都胎死腹中,不得不为了媒体的利益要求而趟入“乱源之一”的浑水。广受争议的是政治力对媒体的控制,不同政党阵营以广告收买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等。
但是,总体上看“继自由化之后,台湾媒体对民主整合的两个重要指标——参与和竞争——开始发挥了积极的贡献。在这段期间,执政当局逐步检讨,改善相关法案,意在创造一个更自由的媒体环境,不过除非媒体的控制权能够突破垄断性的局面,政治议程的扭曲,依旧限制了政治的竞争和参与。”(20)无法摆脱政治力的制衡,仍是媒体发展的软肋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受媒体老板、政党人物政治力及商业主三方的制约,台湾媒体第四权还是对台湾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初,新媒体(尤其是有线电视与地下电台)开始通过电波频道提供异议资讯和观点,并且大量使用“call in”的节目形式,给市民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参与社会在政治过程的机会。自由化的媒介环境不仅带来了言论自由的较大发展,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讨论政论节目,更有专门恶搞政党以及政治人物的政论节目,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通过媒体“发声”,实现民主参与的第一步;其次民主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台湾媒体的发展;最后是“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对选举、制衡、政党政治等民主形式的促进,尽管部分媒体各自有独自的政治立场,在报道中也难免有所偏颇,但对于选举、制衡、政党政治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监督作用。
(二)新闻自由之媒体批判意识的觉醒。媒体在挣脱威权时期极权政治统治的直接干涉后,又受到了不同政党的操控。政客们都熟知媒体的特性,他们通过随时设定媒体感兴趣的议题掌握媒体的方向,还采用植入式行销的方式运用媒体进行自我报纸;而随着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媒体为了广告收入,为了发行量、阅听率,不得不做出牺牲,更是给政客们提供了可以对媒体予取予求的机会。
责任感是媒体的良心,然而,“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所以媒体可以为了政治立场不同而误导和扭曲真实,再根据错误的‘事实’大肆评论。”(21)而这些扭曲、错误的讯息由于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会逐渐变成“事实”,还可能误导受众以讹传讹,让人们不禁质疑:台湾媒体为新闻自由贡献了多少的真理。政治先行、媒体跟进的现状告诉我们,媒体已经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锋,而成为了党派人士发表政见的场所,新闻自由扩张的空间仅仅是媒体跟进政治的步伐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政党轮替时期的媒介之独特形态还在于政媒两栖的奇特现象:“立委”可能变身名嘴大肆爆料,既享受政治利益又能和媒体相抗争;而媒体人介入政治的现象也不再新鲜,这些人在媒体、政治中均左右逢源,导致媒体在结构、品质和专业性等方面都滋生出诸多弊病。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媒体都将权力争斗、立场对立放在新闻报道重心,蓝绿两党成了政治报道的主角。加上解严后很多新闻道德的基本伦理都尚未来得及建立,使得媒体伦理约束力十分薄弱,对媒体报道的伦理道德管制也相对无力。政媒两栖、政治报道单一化等问题不仅会影响媒体的威望,还将影响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并极大地伤害民主化的进程。
在媒体乱象日益突出的现状下,除了社会上普遍要求新闻界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外,各行各业、士农工商也开始承担起监督、批判媒体的社会责任。学界和业界对于“第四权”提出质疑,认为如今台湾媒体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社会公器“的性质,为了生存一味的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发展,不但不尊重新闻界的专业规范,而且缺乏自律自省的精神,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了积重难返的弊病。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新闻媒体第四权沦为政治特权,臣服于广告主及侵犯隐私权、“国家机密”等公私权利的种种指责,“大法官”提出了要给媒体新闻自由“减压”的要求。台湾在《“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56号解释》中,提出了“媒体自由权的‘减压制度’必要性”,在该解释书中,“大法官”首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概念,“究竟媒体的言论比一般人民所为的言论,不论是在重要性及其界限上,皆会有不同的‘宪法’意义。‘宪法’对新闻媒体的保障,除了一般人民的言论权外,尚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加持’,而为后者所涵括。因此,其保障也享有了关涉‘国家’民主宪政发展的高度法益,而邀得‘宪法’最高度的保障(释字第五七七号解释意旨参照)。”(22)但该解释书同时提出,由于媒体的特殊性质,社会应给予宽容,适当为媒体减压,“对于必须广泛提供各种信息给多元社会下品味不同、关心点不同、教育程度、专业不同……等读者需求的媒体,就必须考虑其必须‘快速且大量’提供信息的行业特色,否则就会被消费市场所淘汰。故对于媒体所肇致侵犯他人名誉的发生概率,一定比来自于个人言论自由的滥用来得频繁。因此,为保障新闻自由,使媒体能够履行其宪政秩序所赋予的任务,应当衡酌其‘行业特色’所可能带来的高度风险,而给予适度的‘减压’”(23)。
不论是威权统治下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还是解严后媒体百家争鸣打破垄断的言论空间、释放禁锢的民间活力的表现,抑或是政党轮替后媒体新闻自由的乱象,都源于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总之可以说,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①中国国情咨询网,《台湾新闻自由超美日》,2006年11月7日。[EB/OL]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7893。
②王天滨:《台湾报业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③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④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2002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第128页。
⑤徐泳平:《新闻法规与新闻道德》,台湾世界书局1993年版,第471页。
⑥王震寰:《广播电视媒体的控制权》,郑瑞城编著,《解构广电媒体》,台北澄社1998年版,第414-435页。
⑦王洪钧:《对杂志社设记者的芻见》,《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8年版,第691页。
⑧编辑小组,《新闻局会报已肯定杂志社可设立记者》,《“中华民国”杂志年鉴一九五○-一九九八》,台湾“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1998年12月,第128页。
⑨李旺台:《台湾反对势力——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高雄五千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⑩薛化元:《战后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考察(1945-1988)》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38页。
(11)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12)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2003年政治大学广电系硕士学位论文。
(13)吴文成:《传播媒体的子弹会转弯——浅谈近来新闻传播现象》,转引苏娴雅《台湾的媒体:第四权与公共利益》,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位论文。
(14)吴恕:《置入性行销杀了媒体监督功能》,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6日,A15版。
(15)张旻:《当媒体碰上衣食父母》,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1999年5月1日,第11期。
(16)苏娴雅:《煞不住的下冲列车:台湾媒体批判》,台湾米罗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页。
(17)姚人多:《建构一个界线清楚的媒体与社会》,台湾时报文化基金会主办,《再造公与义德社会和理性空间研讨会论文》,第233页。
(18)徐佳士:《记者?主笔?》,台湾《中华日报》1988年4月18日。
(19)邱奕嵩:《党政力量松手,报业向商业靠拢》,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2000年1月号,第17期。
(20)任格雷、蔡明烨:《危机与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与台湾电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5—106页.
(21)李旺台:《媒体乱象谁该负责》卓越新闻基金会“报禁解除二十年”研讨会论文,转引自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3页。
(22)(23)台湾第6865号《“总统府”公报》,2009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