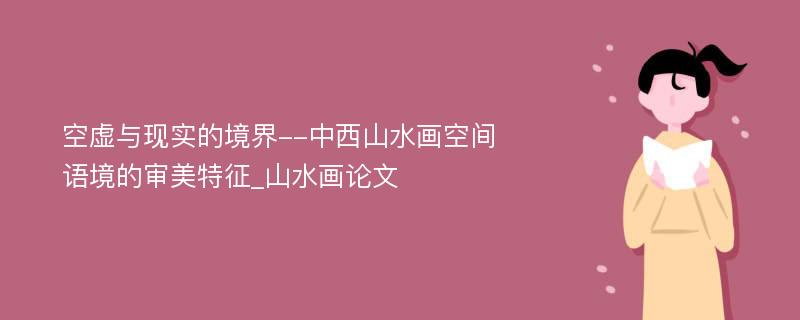
虚实之境——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空间语境的审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景画论文,山水画论文,语境论文,虚实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作为中、西方两大绘画体系中以描写自然山川景色为主体的艺术样式,虽具有类同性,但在空间语境上,却反映着各自的美学准则。中国山水画的空间感型是虚境;西方风景画的空间感型为实境。一个朝广延空间展开,一个朝纵深空间拓展。语境不同,正像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指出的:“各个美术有它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情绪为最深基础。”(注: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中国山水画始于六朝,至唐脱离人物题材朝独立画科发展。山水画追求虚境,思想根源是老、庄之“道”和魏晋玄学。这从南朝宗炳《画山水序》中提出的“道”(圣人含道暎物,圣人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和王微《叙画》中提出的“拟太虚之体”论,可见一斑。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认为自然界并不是完全孤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纯客体存在,自然与人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物我同一,心物相映。所以,古人对山水的解释,既不是纯客观的机械的摹仿论,也非纯主观的表现论和移情论,而是在“卧游”山水的境界里,“游目骋怀”,并以“无心”、“无为”之虚静心态和“步步看,面面观”、“俯仰终宇宙”的观察自然的方式,通过静穆观照,与万物同“放于自得之场”,共入自由之境。这种山水游赏的审美方式及老、庄“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的哲学命题,奠定了中国山水画虚静、空灵的美学基础,从而决定了中国山水画趋于“写山水之神”,得“意”中之“象”,“不著一字”,也“尽得风流”的艺术风貌。
西方风景画的出现,与中国山水画相比,显然是后来者。一般认为,西方风景画产生于15世纪,但真正脱离人物题材独立发展,应是17世纪。那时,在有绘画传统的尼德兰北部的荷兰,出现了大家熟知的表现乡村景色的写实风景,以其逼近现实的空间深度,望之“如镜中影、水中月”,(注: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所谓“逼真的假相令人更感为可怖的空幻。”(注: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西方文化中占主流的自然观认为,自然是纯粹的物质世界,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这种“天人相分”,“心物对视”的宇宙观,导致其美学追求趋于外在形式,因而,对自然的理解总是以科学的理性逻辑和认识为思想基础。这也就决定他们反映自然时,只能外在地感受它、认识它,把握它,而其内在精神却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彼岸世界。这样,西方风景画构成一种摹仿自然实在“如同自然本身一般”(注:《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逼真到“酷似造化才算高度完美”(注:《安格尔论艺术》,辽宁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的艺术标格,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因产生的时代相差千余年,又是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艺术形态自然相异。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两者的空间语境中看出。
空间语境,中西之别首先在于透视法的运用。概括地说,中国山水画使用的是“动点透视”,或曰“无点透视”,不受“定点”的约束;西方风景画使用的是“焦点透视”,或称“定点透视”,不能随景点移而视点动。这两种透视法的直接目的,是展示自然中的远近之感。在中国山水画里,远近空间是一种感性的、表象的,在处理方法上,一般为从下(近)到上(远)依次推进,没有固定的视平线,层层叠放,使之成为具有远近、大小的空间形象。这种远近、大小并非一种定式,而是一种灵动的空间,在特殊的情况下,远也可以大,近也可以小,随机而定。北宋郭熙《林泉高致·山川训》中提出的“三远”视学原理,即揭示出山水画特有的空间境界和丰富、灵活的表现力。“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注:郭熙,《林泉高致·山川训》。)“三远”法的视线是流动的、转折的,形成一种节奏,“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与西方透视法限定“一点”而不动的确大相径庭。中国山水画家排除“定点”的约束,可以纵身大自然,与之浑然一体。西方风景画的“焦点透视”,则始终遵循一种逻辑,即近大远小,近高远低,近宽远窄。此法则是按几何透视原理将由近及远的景物渐次缩小,以暗示景物间的远近关系,这种高度科学化的、理性的空间判断方式,必然要求绘画在处理空间结构时,如实再现自然,表现其本身的比例、秩序与和谐之美。因此,西方画家在掌握了“焦点透视”原理后,便充满信心地欢呼:“画家与自然竞赛,并胜过自然。”(注:《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关于透视法,中国早于西方千余年就已论及。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就说过:“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于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见其弥小。令张绡素以远暎,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注:宗炳,《画山水序》。)然而,中国画家并不以此为准绳,而强调“神明降之”,反对像绘制地图那样,“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注:王微,《叙画》。),刻板、机械地摹仿自然。山水画的创作目的不在于逼真地再现自然,而是为了“畅神”(宗炳《画山水序》),以至“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王薇《叙画》。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在透视法的运用上各取所好,西方为可“与自然竞赛”而欢呼,中国则不为自然所困而“畅神”。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不仅在远近空间处理上有别,在高低、广延空间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中国山水画一般都取平视法,无论高还是低,整体还是局部,一概视之。从高低空间上看,山水画中的树木,无论处在山顶或是山下,其根、干、冠同时展示,不予遮掩。山上的建筑物也如此,不仅能见其顶部,也可窥见屋内。而西方风景画中,高处的树木只能看到树冠的底部,顶部则因视线被遮而无法再现。同理,看低处树木时,树冠顶部则把底部包括树根和干全部遮挡,故只能见其顶部。建筑物亦如此。中国山水画在高低空间的创造上还有几种独特的方法,为西方风景画所未见。一种是拉大法。如五代荆浩的《匡庐图》、元曹知白的《群山雪霁图》、明兰瑛的《华岳高秋图》等,这些作品远处的高山并没有因远而缩小,反倒加强了远山的高度,呈现出“仰山巅”的“高远”之势。另一种是拉近法。如北宋范宽的《谿山行旅图》、南宋马远的《踏歌图》中的远山,并没因远降低它的高度,也未因远敷施淡彩,而是为了突出远山的高大,主观地将它拉近于观者面前,造成视觉上的逼人气势,这种视觉冲击力是推远所不及的。再一种是隔断法。山水画常有一种现象,即把山体的上段和下段通过烟云的空白处理,使其自然隔断,古人云:“山欲高,尽出之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注:郭熙,《林泉高致·山川训》。)在这里,“烟霞锁其腰”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符号,它暗示了景物在高低空间上无限延伸的可能性,让观者去联想山体耸入云端的那种视觉上的感受。西方风景画与中国山水画在这方面的处理总是对立的,你拉大他则缩小,你拉近他则推远,你隔断他则联结,你要摆脱客观的限制,他则如实反映客观。
再从广延空间上看,中西方的区别可说是:一为开放型的,一为封闭型的;一为进行式的,一为静止式的。中国山水画在创造广延空间上是一种灵魂变化的延展,它是按作者主观需要而巧妙设置画面,即使在一幅小画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无限宽广的悠远天地。相比之下,西方风景画则显得较为机械和保守,它在广延空间的创造上,只能依赖“立足一点”向左右极目远眺时所能看到的同一水平线上的景物延伸。所以,画中的形象在广延感上是单向的,一个时空的。中国画家从不习惯于对事物的瞬间写照,不像西方“画家只能画一瞬间的景象”(注:《狄德罗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5页。), 而是致力于表现人和万物共生共存、不断运动的心理时空。郭熙说:“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侧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注:郭熙,《林泉高致·山川训》。)这种观察方法的全方位性,如同“鸟瞰全整的律动的大自然”(注: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一般, 并以这种空间立场“在时间中徘徊移动,游目周览,集合数层于多方的视点谱成一幅超象虚灵的诗情画境。”(注: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历代所留下来的山水画长卷, 如《千里江山图卷》、《溪山清远科》、《鹊华秋色图卷》以及《富春山居图卷》等,可说都是由于时空立场的介入,在一个不确定的点上,“饱游饫看”使山川景物绵延千里而不绝。
相对中国山水画的“长卷”类,西方风景画虽然不能“面面看”,但他们采取全景式构图,也足以表现空间的宽广感。如17世纪荷兰果衍的《莱登风景》、尼尔的《风景》、英国吉尔特的《约克郡凯尔斯特尔教堂》,这些作品都是为突出宽广的空间而采取缩小景物的办法,令观者可以在一个定点上感受到大地的宽广和深远。但是,这种带有科学透视法的广延印象,虽富有逼真性,也有局限性,因为它缩小了可视可感的景物形象,与中国山水画的可把玩性和可联想性相去甚远。所以,较中国山水画边走边看多视角的“开放性”,西方风景画却更理智,更内敛,属于一种“封闭型”。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对空间的营构,还有一种语境,那就是双方都在致力的“虚实法”。然而,境界却是不同的。
中国山水画美学中的重要课题,即虚、实章法之理。古人有曰“虚实相生,乃得画理”(注:蒋和,《学画杂论》。)者,“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注:笪重光,《画筌》。)者,这“画理”、“妙境”,正是一种意境空间。在中国山水画中,山若实,水则虚,树若实,云则提空,深处敷之以淡,实处间之以虚,“实”和“虚”的对比使境界空旷,引向深远。如五代关仝的《山谿待渡图》,北宋郭熙的《早春图》、范宽的《谿山行旅图》,南宋马远的《踏歌图》、《寒江独钓图》,夏圭的《溪山清远图卷》,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卷》以及明代王履的《华山图册》、戴进的《春山积翠图》等,堪称古代山水画作中虚实映衬的典范。有为远近实写,中景虚拟者;有为云山掩映,通幅虚实交错者。布置虽不同,均得“画理”,各领“妙境”。一般来说,虚实关系是“实”为近,“虚”为远,虚实互映,产生出远近之感的视觉效果。这虽与西方风景画近实远虚的规定有相似之处,可在艺术表现上,却不是不可变通的定则,有时远也可以实,如范宽的《行旅图》,马远的《踏歌图》,远山清晰如同近景。再看马远的《独钓图》,这里的“实”是“独钓”,“虚”是“寒江”,从远近上看,“独钓”为中景,若按西方科学透视原理判断,它是处在远、近两极之间,有意思的是,马远并没有加强近景的交代,和远景一样,全部舍去,仍然远近分明。
西方风景画中的“虚实法”,基本是按“焦点透视”的原理发挥的。它遵循着“近大远小,近实远虚”的法则,按空气中阳光对尘埃的照射致使远、近景呈现浓淡不同的色彩、造成视觉清晰度的差别。这种视觉原理在中国画论中早就出现,如唐王维《山水论》中说:“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注:王维,《山水论》。)五代荆浩在其《山水节要》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但在山水画创作实践中并没有真正恪守这以法则。如“远人无目”说,现实中的人物远距离看不仅眉目难辨,而且形象轮廓模糊不清,山水画中的人物虽是“无目”的,但轮廓仍在,并且与近处人物同样清晰。在西方风景画中近处人物形象轮廓分明,眉目全在,而处于深景中的人物,由于光色的变化,形象则是朦胧的、模糊的,形成与环境色相协调的一个色点。风景画中的虚实处理,不仅在彩色浓淡上有变化、有层次,而且近景和远景,亮部与暗部具有冷暖色彩的虚实感。如近景色的饱和度强于远景色,亮部色的饱和度强于暗部色,近处趋暖,远处趋冷,亮部趋冷,暗部趋暖,这种冷暖色彩的调配,强弱之间的对比,令人在幻觉中饱览第二自然的逼真性。这在17世纪荷兰风景画和19世纪法国印象派作品中尤为突出。19世纪英国风景画家透纳更是运用色彩表现远近、虚实空间的大师。在这方面,中国册水画则不具备西方风景画的优势。
虚实法,中西虽都重视,但着眼点根本相悖。西方风景画多求“实”,虚为“实”服务,以增“实体”印象的强明,构成空间深度。在他们那里,虚只作为手段,不具有意境的可联想性。如在风景画中,山川、河流、树木等,所有虚处都在暗部或深远处。欣赏时,人的视线往往停留在阳面的实处,并饶有兴味地感知明暗程度、色相之别,去辨析朝暮、阴晴、四季不同,而虚境早已被人遗忘了。中国山水画则着意于“虚”甚至空白,这一点恐怕是西方人难以解读的东方艺术境界最微妙的地方。与西方风景画追求光影明暗、色彩冷暖和时辰感官的实境相比,中国山水画里朝暮如何、阴晴如何、春夏秋冬如何、山水形态如何、江南北国如何,并非审美指向,而是在“空白处”着力,赋于它更大的想象空间,画面多取一角半岩,留出大片空白,远山平野也在其中了,令人看来如是虚灵的、梦幻的世界。谁能不在这种“剩水残山”中荡漾出各种轻柔优美的愉悦感呢?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也是通过空白,唤出“寒江”这个可读、可联想、诗化的时空境界。山水画的中“虚(空白)的特殊性,就在于“空处妙在通幅皆灵”(注:王石谷,恽南田,《评〈画筌〉》。),或宁静、或悠远、或空旷、或萧疏。这正是中国山水画最擅长表现和具有无限魅力的一面。
对比起来,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在空间语境的创造上,各有所长。中国山水画是表象的、虚灵的,画家陶醉于情与景的梦幻中,与自然融合一体;西方风景画是客观的、写实的,画家陶醉于“与自然竞赛”中,并拿一种对立的、抗争的眼光去正视世界。如果说中国山水画以它的“虚”引领人们超越狭隘世界,去领悟宇宙和人生之道的精神体验的话,那末,西方风景画则多以它的“实”激发人们的实践精神,体现以人为主导的客观呈现方式。前者寻求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内,后者寻求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外。这一“虚”一“实”,一“内”一“外”,正是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空间语境的审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