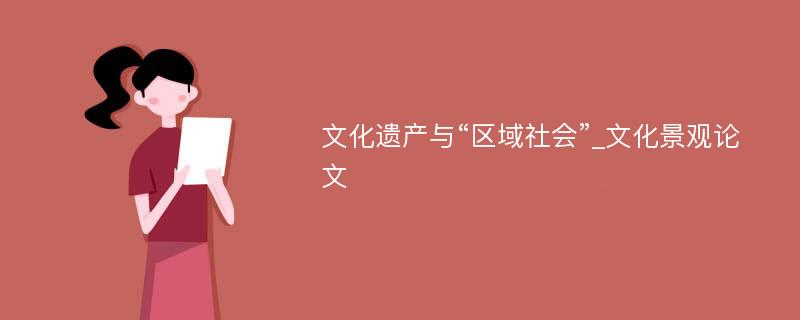
文化遗产与“地域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遗产论文,地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急剧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格局与文化生态。经由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世界遗产国际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国全面引入了国际社会通行的文化理念和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同时,国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多种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既善于学习国外经验,又坚持与实际国情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主体性。鉴于现阶段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本文拟对日本重视“地域社会”的有关经验作一些介绍,希望为中国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一、什么是“地域社会”
“地域社会”一词来自日语,可以考虑将其翻译成汉语的“地方社会”(或“乡土社会”)及英语的local community。考虑到汉语中的“地方”主要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故在介绍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时,本文仍使用“地域社会”这一表述。所谓“地域社会”,主要是指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集团、结构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和“地域共同体”的概念较为接近,只是后者更加突出集团这一侧面。日语又有“地域社区”一词,作为一个日英合成词,主要是指一个地域内居民生活的场所(或空间),居民们在其中生产、劳作、消费、娱乐,同时享有教育、医疗、健身和保安之类的社区服务,人们在其中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共同组织和参与本地特有的节祭和艺能展演活动等。换言之,“地域社区”的概念,有时可以和“社区”(community)、“地域社会”等相置换[1]。不过,从日语使用的文脉看,“地域社会”有时还被用来指称超越村落共同体或町(镇、街区)等基层熟人社会而更加广大一些的“地域”或“地方”。
日本“地域社会”的最为基本和单纯的形态就是村落,经营稻作的农村、种植杂谷的山村或从事捕捞的渔村等。村落往往会有一座神社,它构成该“地域社会”里居民精神世界的中心。同一个“地域社会”里的居民,被认为无条件地就应该是本地某神社(供奉着“氏神”)的信仰者(“氏子”)。这从当今的标准看来,有可能出现干涉个人信仰自由的情形。由于经常在同一座神社参加各种神事、祭礼和民俗活动,人们彼此就会产生一种“归属意识”。同一“地域社会”的成员,有时会相信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或他们各自的祖先彼此之间也曾经存在着很深的连带性。在多数情形下,同一“地域社会”里的人们往往从事着相同或类似的生计,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和人生经验。可见,旧时日本的“地域社会”往往就是一个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共同体,“外人”想要进入很困难。共同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人们的集团,其传统社会结构有利于抵御外部的安全威胁,也有利于共同和平均地利用周围有限的自然资源(土地、河流、山林、海面等),但它往往会形成对个人的压力,甚或会以牺牲个性和个人幸福为代价追求“地域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样的“地域社会”里固然存在某些竞争或个人的利益,但更加重要的规范则是成员之间彼此相互信赖、相互扶助、相互协作、相互救济。一些在当今看来可能不尽合理的“人情”、“义理”和社交规范往往具有强制性,这在带来社区连带感的同时,有时也会对个人隐私构成威胁。这样的“地域社会”大体上是自江户时代以来得以形成的,到明治时代则有了民族国家的强行介入。日本一般是在“市町村”这一国家行政的地方基层机构的体系之下设立“町内会”或“自治会”①,这类民间社团往往就成为“地域社会”的代言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及伴随而来的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促使日本各地的“地域社会”渐渐趋于瓦解。从某种意义说,“地域社会”的颓废乃至解体,是日本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之一。都市化进程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或其近郊,在实现了全社会中产阶级化的同时,日本还迅猛进入高度发达的汽车社会和IT社会,与此相应,农村、山村、渔村之类“地域社会”则出现了大面积的“过疏化”、“空洞化”、“邻居他人化”以及“高龄化”、“少子化”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由于迁徙自由和频繁的工作变动,持续参加“地域社会”各项传统节祭或其他民俗活动的居民日趋减少,很多长期传承于当地的传统产业、传统工艺、传统艺能(歌谣、舞蹈)等文化形态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承担者(传承人)后继不足的窘境。
多年来,日本各地出现了旨在复兴“地域社会”或使其“活性化”的种种尝试和努力,以应对超老龄化社会因人际关系高度疏离产生的弊端。为振兴“地域社会”,促使本地域内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当地基层政府与普通的居民、商工会、农协、渔协等本地社团之间密切合作,以扩大雇佣规模来遏制人口外流趋势。振兴“地域社会”,就必须强调当地的主体性。企业将其社会责任具体落实到为地方做贡献上,积极参与社区节庆活动;大学举办各种市民讲座;银行、邮政等为当地居民提供多种往往超出其业务范围的服务等。总之,产(企业)、学(大学及科研机构)、官(地方行政)、民(NGO、NPO、市民团体)相互结合,被视为振兴“地域社会”的基本模式。一般民众是地域振兴之可持续发展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他们组成了许多旨在解决本社区内特定社会问题(老年人福祉、环保、教育、医疗、防灾、社会保障等)的NPO组织和志愿者市民小组。与振兴“地域社会”有关的文化活动,主要有:发掘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传统产品(本地名吃、名产、社区标志、可促成“地域名牌化”的象征物和吉祥物等);扩大本地传统节庆祭典的知名度;对本地观光资源深度开发;建立美术馆、博物馆、历史民俗资料馆,保护本地历史性建筑物等。
使用“地域社会”这一概念时,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笔者想用它来特指超越村落共同体等乡土熟人之基层社区的较为大面积的“地方”,把它界定为介于国家的基层区划之“县域”和村落之间的“地方”。大体上,其范围可以经由“通婚圈”、“祭祀圈”和“集贸市场圈”这几个人类学的范畴来限定。所谓“通婚圈”,主要是指婚姻成立时相互择偶的地理空间,以某村落为例,其女子出嫁的大致范围以及该村男子所娶妻子来自的周边村落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乡土社会多实行宗族外婚及某种程度的村落外婚,由于交通条件限制和“娘家—婆家”关系的制约,通婚圈大致就局限在人们步行当日可以往返的范围之内。同样,“祭祀圈”大体上是指经常前来同一座庙宇(或庙宇群)上香朝拜,或轮值参加庙会宗教活动的人们所居住的大致范围。“集贸市场圈”则主要是指依赖于某个集贸市场(墟、集、场)或步行所及的周边若干个集贸市场的人们分布居住的大致范围。这三个“圈”虽然往往不能够完全重合,但可以反映出一个“地方”的封闭性及流动性,它们所大体框定的“地方”也就相当于一个“地域社会”。显而易见,正是在这样的“地域社会”里,生发、容纳和承载着绝大多数农耕生活时代的传统文化形态,因此,可以说“地域社会”是文化遗产的传承母体。
二、重视“地域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
日本以《文化遗产保护法》为核心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体系,从整体上说,具有重视“地域社会”、重视文化遗产的相关当事人(传承者、保持者、管理者)等特点,可以说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紧密协作、共同管理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行政体制[2]。例如,《文化遗产保护法》对所谓“地方公共团体”的地位和作用有详细规定,以确保其在本地域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用工作中承担具体而又重要的责任。通过由国家(中央政府)、地方公共团体、文化遗产当事人、社区组织及全体国民分别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全国范围内的系统体制[3]。
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出台于1950年,此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历经修订而逐渐趋于完善。例如,1954年的修法,明确界定了地方公共团体在保护、活用文化遗产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强调了地方公共团体的重要性。1975年对《文化遗产保护法》进行大幅度修订,将新设的“民俗文化遗产”(包括“有形民俗文化遗产”和“无形民俗文化遗产”)范畴纳入保护对象,并创设了“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制度,以保护那些承载和铭刻着各个“地域社会”之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村落和街区[4]。“传统建筑物群”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形成的历史性风貌,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历史、学术和文化价值。该制度要求各地对传统的建筑物群设定“保护地区”,亦即强调整体风貌的完整性保护。在日本,现代化的街区开发迅猛发展,导致传统的村落及街区景观迅速消失。有鉴于此,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各地相继出现了由当地的市民团体组织和发起的保护运动,其成果反映在法制建设方面,就促成了由国家选定“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这一制度。
“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的选定,首先需要由各地的市、町、村教育委员会进行“保存对策调查”,制定相关的“保存条例”,并据此展开必要的维修、修景、环境整备和防灾等保护工作;然后,由市、町、村向文部科学大臣提出“选定”申请,经法定的“咨问”与“答申”程序,才有可能被选定为“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一经选定,将由国家提供必要的经费补助,国税和地方税也都会有一些税制优惠[5]。这个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由基层地方及本地域居民来决定当地的“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保存地区内的现状变更、维修或改善其外观等保护事业,归根到底都以地方为主体进行。截至2010年6月,分布在日本各地的“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共计87处。这些保存地区的选定和保护不仅使其整体的历史环境或景观得到有效保护,而且通过鼓励地域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使这些地区成为富于历史个性魅力和生命活力的新社区。
日本在2004年对《文化遗产保护法》进行再次修订,又进一步创设了“文化景观保护制度”。“文化景观”主要是指不同地域因为人们的生活或生计及根植于该地“风土”形成的景观,例如,“梯田”(水田)、“里山”②、“水渠”(灌溉系统)、花园、人工植被等。地域社区的居民利用当地独特的气候和风土、环境条件创造出的“景观”,往往可直接成为观光产业的本地资源。新创建的制度以根植于地域生活和生业的景观为对象,促使其在当地得到保护并将其传承给后世。它不仅促进了一般民众对“文化景观”的理解,也有助于“地域社会”的振兴和发展,增强了景观所在地域社区的活力。
对“重要文化景观”的选定,基本和上述“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的选定程序相似。首先,得由各地方的基层政府,根据《景观法》确定其景观规划,制定与景观地区有关的都市规划,展开关于文化景观保护的调查等;其次,由地方上制定保护文化景观所必需的条例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计划(内容包括文化景观的位置、范围,保护的基本方针和保护体制,文化景观的整修和整理);再次,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提出申请,但需要征得有关所有权人的同意;最后,经过《文化遗产保护法》所规定的“咨问”、“答申”等法定程序,便可被“选定”。一经选定为“重要文化景观”,中央政府的文化厅便发布“公示”,并通知景观所有权人、占有者及地方政府。此后,地方上进行的有关“重要文化景观”的维护、修景、复旧、防灾等项目,均可依法获得国家财政的经费补助,同时在地方税的税制方面也有优惠措施。
上文以“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和“重要文化景观”的选定制度为例,介绍了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体系比较重视基层“地域社会”和地方公共团体的作用这一特点。保护好本地域的文化遗产,既是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地域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日本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比例高达97%)均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域的《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从而使本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地方法规作为可靠和具体的依据。同时,地方政府还设立和经营着许多旨在保护和“公开”本地文化遗产的公共设施,如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馆、历史民俗资料馆、文化传习馆及地域社区的文化中心等,并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普通市民参与,积极开展各种学习、爱护、传承和活用本地域文化遗产的活动,其中包括以普通市民为对象的涉及文化遗产的“启发”和“普及”活动。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全国各地均活跃着一大批致力于保护、传习、开发和活用本地域内各种文化遗产的民间社团,这些地方性和民间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在“地域社会”的文化传承中发挥着核心、骨干和凝聚的作用[6]。例如,和歌山县纪伊大岛的“须江狮子(舞)保存会”、岐阜县郡上市的“狮子舞保存会”、大阪市淀川区神津神社的“狮子舞保存会”、爱知县奥三河的“花祭保存会”等。日本政府为保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了“保持者”(所谓“人间国宝”)、“保持团体”的认定制度。各个地方政府的教育暨文化部门,均必须为使本地独特的传统工艺、手工艺或民艺的某些传承人能够获得国家认定而准备许多调查资料;很多地方往往还会成立“某某人申请‘人间国宝’后援会”之类的民间社团,而一旦有某人获得“人间国宝”的认定,他所属的“地域社会”整体都会引以为豪[7]。除少数分布在全国范围或局限于宫廷皇室的传统艺能以及某些超越了“地域社会”而存续的行业性艺能技艺之外,绝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包括艺能、技艺和民俗活动,基本上都是以“地域社会”或地域社区为依托和母体的。因此,对于它们的保存和活用,自然也就应该强调“地域社会”这一具有根本性的立足点。
三、几个代表性案例
这里,举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
(一)利用“地域社会”的传统习俗,维护世界文化遗产
岐阜县的“白川乡合掌造村落”,于1995年12月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该村落以巨大的正三角形“合掌”式屋顶构造的农家建筑为特点,被视为日本“豪雪地带”之山村民居的典型,其造型结构便于承重(积雪)和在屋顶阁楼内从事养蚕业等。这种民居的特点和优点很多,屋顶像人手“合掌”一般坡面陡峭,几近60度;屋顶内的阁楼山墙开窗采光,可确保通风,冬暖而夏凉。苫盖屋顶的材料是在当地就地取材的茅草和蒿草之类。在一片片绿色的稻田或旱地上耸立着一座座美丽的“合掌造”传统民居,构成了一幅独特的人文景观,被认为是日本传统山村的“原风景”。19世纪末,当地曾有过很多这样的民居建筑,但到20世纪中叶以后,数量急剧减少,除修建水库淹没了一些之外,也存在有人嫌它住起来不方便而出售或拆毁的情形。1971年,在一些外来学者的建议下,白川乡荻町成立了“村落自然环境守护会”,制定了“不出售、不出租、不破坏”的三条“村民宪章”,对村落进行整体性保护。1976年,当地的村落被指定为国家的“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当地村民通过各种文化遗产保护活动阻止了村落人口的进一步减少,甚至有一些外出的年轻人又回到村里,对“地域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建筑一座这样的民居,除了柱、梁、椽等骨架部分需要由专业的木工匠人承担外,其他如建材的筹备、部分搭建工序,尤其是屋顶苫盖茅草的作业,过去都是由全体村民通过一种叫做“结”的互助机制集体协作完成的③。采用本地建材、尽量不花或少花钱而由全体村民集体协作建成,这些都反映了山民的生活智慧。旧时白川乡盛行大家族制度,一栋房子里一般要住几十人,通常也不分家。人们必须通过集体互助才能够在严酷的深山环境里生存。每隔30~40年,其茅草屋顶就需替换更新一次。由于房屋的规模巨大且屋顶倾斜坡度很大,仅靠一家人难以完成作业;而且,由于房屋仍在使用中,故屋顶替换作业必须在较短时间完成。更换一次屋顶,据说要准备3年之久。首先要根据屋顶斜面面积对所需茅草数量和人力予以概算;一旦择定吉日,就向全村各家发出通知,请求大家在某一天来帮忙。事先割取必要数量的茅草,并确定参与人员的分工(男人们收集和搬运茅草、对茅草进行甄选、准备其他道具如绳子等;女人们为大家准备饭菜和作业间歇休息时的茶点,同时,也要准备作业完成时用于祝贺的礼品等)。作业一般不在两个坡面同时展开,而是先完成一面,再接着完成另一面。通常苫盖一面约需要2个工作日,每天需要200~300人参加,其中约有100人需要在屋顶斜面上作业,因此,其集体劳动的场面颇为壮观和激动人心。
2001年,长濑家的一次更换屋顶作业,就是在时隔30年之后举行的。不仅全体村民,甚至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环境保护团体和志愿者们,共有500多人参加了这次作业。长濑家的房屋比一般民居的房屋大一倍。仅屋顶斜面的单面就使用了12000捆茅草。当时,NHK电视台转播实况,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自从白川乡的“合掌造”村落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游客们蜂拥而至。村落人口仅有2000人,每年却要接待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游客多达150万人。大量游客来访引发了很多问题,诸如交通堵塞、停车场不足、游客排泄物的处理困难、游客超出旅游路线任意进入居民家中窥探等。与此同时,村民们以游客为对象大赚其钱,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村落内部不但产生分化,而且间接影响到人们的互助协作精神。由于人口老龄化、山村“过疏化”及第一产业(农业)的衰退,“结”这种互助机制慢慢地就变得难以为继。现在,通过电视影像的广泛传播,白川乡“合掌造”村落通过“结”这一互助和共同作业的机制来维系地域社区的运作和认同,这在全日本都得到了较好的评价,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二)福岛县只见町的民具保存与活用运动
日本福岛县只见町的教育委员会为编纂其《町史》的“民俗志”[8],遂在进行民俗资料调查、发掘和整理当地的民具资料(亦即有形民俗文化遗产)时,积极动员地域社区的乡民参与其中。经过对民具的详细整理、记录、保存与活用(如公开展示等),使民具的科学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这种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促进“地域社会”文化建设的成功实践,被誉为日本民具整理和研究的“只见方式”[9]。
从1990年起,在町教育委员会的主持下,当地一些群众性民俗社团(“朝日乡土研究会”、“明和民俗谈论会”、“民具谈话会”)、社区有识之士和民具爱好者们,组织町内几十位老年人从事民具的整理和分类工作。伴随着民具资料的整理和分类,又有不少民具被捐献出来。这些老年志愿者大都七八十岁了,几乎都曾亲自使用或制作过各种民具,对乡土民俗怀有深厚感情,希望能够把自己有关民具的知识传递给子孙后代。由于旧时农家生活中寻常可见的民具无不包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记忆,甚至是他们过往人生的见证,因此,老年志愿者们都觉得自己这一辈人有把它们记录下来和保护起来的义务。他们根据年轻时的经验和记忆,认真填写民具卡片,同时还把民具的制作方法、使用方法及相关的民俗知识均予以说明,有的人甚至还会讲述有关某件民具的故事。为把民具实际的制作和使用方法记录清楚并传承下去,老人们还亲自作为模特进行示范,再现旧时农田耕作或纺织的动作与技艺。对某些已经绝灭但尚存记忆的民具,老人们则进行民具的复原工作。民具的整理工作琐碎而又繁难,但老人们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他们整理出来的民具资料,从日本全国看也是非常珍贵、完整和规范的。由于达到了系统调查、认真整理、科学分类以及有固定的保存场所等标准,2003年2月,日本政府将“会津只见的生产用具和劳作服装收藏品”(其中生产用具1917件,劳作服装416件,合计2333件)正式指定为“国家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只见町接受捐赠和经多方收集的民具共计7500多件,其中多达2333件被指定为“国宝”,这在当地“地域社会”的编年史和文化建设方面无疑均是一件大事。
“地域社会”的民具铭刻着当地生活和生产的痕迹,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和民间智慧,在其逐渐退出现实生活之后,又将成为人们乡土记忆和寄托乡愁情感的载体。民具原本分属各个农户或乡民个人,但通过民具的保存与活用运动,其价值被重新认知:民具不仅是过去的遗物值得纪念,而且还内含着很多民俗知识,凝结着先民的智慧。现在,它们不仅成了“地域社会”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在被整理成民俗资料之后升格为日本国家的文化遗产。
(三)丰桥鬼祭保存会
爱知县丰桥市有一种民间祭祀活动(祭礼),亦即号称为“天下奇祭”的“鬼祭”,1954年被指定为爱知县无形文化遗产,1980年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家级的“重要无形民俗文化遗产”。“鬼祭”是丰桥市八町大街的安久美神户神明神社(又名“丰桥神明社”)的春祭行事,每年定期在2月10~11日举行[10]。它原本是在旧历正月初十、十四日举行的神事,故亦被认为是呼唤春天的祭礼,具有祈祷农作物丰收、占卜当年丰歉的性质。从1968年起,改为以建国纪念日(2月11日)为“本祭”,因前一天要做准备,亦为祭日,称为“前夜祭”。“鬼祭”的起源可上溯至平安时代。天庆二年(939),关东发生“承平天庆”之乱,朝廷遣使到东海的伊势神宫祈祷平定;第二年叛乱平息,被认为祈祷灵验;天庆三年(940),当时的朱雀天皇将三河国渥美郡北部的安久美庄(今丰桥市中心一带)寄赠给了伊势神宫。于是,这里便成为“安久美神户”(神的领地),并设立了神明社。神明社的规格较高,据说相当于“县社”,其主祭之神为“天照皇大神”,配祀诸神则有“仲哀天皇”、“神功皇后”、“应神天皇”、“火产灵神”、“武瓮槌神”等。
前夜祭主要是举行很多“神事”仪式,通常要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些“神事”仪式颇为古朴,被认为反映了日本古代神道的风格。本祭从早到晚要一整天,主要是在神社的拜殿前设置八角形舞台,表演“田乐跃”、“鼻天”之舞等传统艺能,其中有些是平安时代起流传下来、以滑稽著称的“田乐”之舞。“鬼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11日下午2点左右开始的“赤鬼”和“天狗”之间的相互逗趣和斗法。高天原(神界)的“天狗”(武神)试图惩戒性格暴烈的凶神“赤鬼”,双方斗法的结果是“赤鬼”被驱逐出“境”(神社)外。据说是有所悔悟的“赤鬼”(这时转换成益神),在神社周边的“地域社会”各町来回奔跑,直至深夜。“赤鬼”一路播撒白色的米粉以清洗自己的罪孽,并散发祛痰糖(一种供品)向人们表示歉意。据说此糖吃了可以避邪,而人们身上若沾有白色的米粉,则整个夏天都不会生病,因此,围观者争先恐后地抢拾祛痰糖,并希望沾染一些“赤鬼”撒下的米粉。簇拥在“赤鬼”周围的人,包括围观的看客、过路的行人,都会被米粉撒成白人。
神明社内的5栋建筑物(本殿、拜殿、神乐殿、神库、手水舍)是日本国家级的“登录有形文化遗产”。上述文物连同“鬼祭”这一无形文化遗产得以绵延传承千年仍得以维系的原因,就在于“地域社会”人们的团结和努力。丰桥“鬼祭”在国家登录为无形文化遗产时的“所有者及管理者”抑或“保护团体名”是“丰桥鬼祭保存会”。具体来说,正是这一“地域社会”的民间组织发挥着核心作用,主持和操办着一年一度的“鬼祭”活动。保存会的会长和骨干都是当地出身,他们都是神明社的“氏子”④。由氏子们组成的保存会对于把“鬼祭”传承下去有很强的责任心。繁杂和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从前一年9月份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第二年2月,“地域社会”内部要为此举行各种座谈会和全体大会,讨论种种事宜。各街区的人们彼此分工合作,或者练习神乐、舞步,或者将祛痰糖事先装袋,或者在神社内设营布置;“赤鬼”、“天狗”、“小鬼”、“青鬼”、“司天师”等在传统艺能表演中登场的角色,事先也均由神社周围的不同街区落实选出(有时通过抽签仪式选出)。此外,每年还从不同街区推选出多位“神役”、“头取”(祭礼负责人)和操持事务“诸役”。祭日来临,“地域社会”的各街区全部出动。操持“鬼祭”活动的头取、神役、诸役,每年都要轮换,这种每年轮值的方法可让“地域社会”里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增强“地域社会”的凝聚力。每年到“鬼祭”这两天,不少丰桥出身的外地人也会专程赶回来参加。
丰桥“鬼祭”的艺能活动中有一些由少年儿童承担的仪式情节(儿童舞蹈)。少年儿童因为纯粹、纯洁而被认为是更加接近神的存在,也更加适于担当和诸神沟通的角色。但近年由于“少子化”,要在范围不大的街区里选出合适(本命年)的孩子已非易事。因此,有人主张公开招募,但也有人反对,认为招募来的孩子没有氏子资格。保存会每年主办“鬼祭”都要花心思动员丰桥市内尤其是地域社区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们参加。孩子们参加传统祭礼活动和民俗艺能表演,可带来很多活力,也会渲染气氛。近年,丰丘高中“和鼓部”的学生们在神前“奉纳”鼓乐,就很受欢迎。每年举行“鬼祭”时,保存会还要主办“丰桥鬼祭绘画比赛”活动,市内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班以上的幼儿园小朋友每年都有近900件作品参赛。孩子们的作品均以在“鬼祭”上看到的活动为题材,往往很好地表现了“天狗”和“赤鬼”的动作神态及参加祭礼的看客表情。绘画比赛设置了很多奖项,奖项的命名均和支持“鬼祭”活动的各方有关,如“爱知县神社厅长奖”,“安久美神户神明社宫司奖”、“丰桥鬼祭保存会名誉会长奖”、“丰桥鬼祭保存会金奖”、“丰桥市长奖”、“丰桥市议会议长奖”、“丰桥商工会议所会头奖”(商工会议所相当于中国的地方工商联)、“丰桥市教育委员会奖”、“丰桥青年会议所理事长奖”、“中日新闻社奖”、“丰桥丸荣奖”等。每年都有数十位儿童和中学生的作品获奖。颁奖式之后,获奖作品还要在百货商店、地方金融机构(信用金库)等处公开展示一段时间。从奖项名称可知,参加和支持“鬼祭”活动的除了地方政府,还有本地企业、媒体等。通过绘画比赛,孩子们从小就知晓“鬼祭”活动的很多情节,在他们成人后,自然也会对“鬼祭”感到亲切,并产生把它传承下去的愿望。
旨在祈愿地方安泰、繁荣和民众健康的“鬼祭”,其内涵颇为古奥,在当地市民心目中有很高的认同度。“鬼祭”现已成为丰桥市的文化资源。纪念丰桥建市100周年(2006)时,以“赤鬼”为模特推出的吉祥物“丰桥鬼”(福神),其形象就取自“赤鬼”和繁体的“丰”字。每年快到“鬼祭”举行的时节,“丰桥鬼”就会在繁华的新干线丰桥站的大厅竖立着招呼过往客人。
四、结语
日本保护文化遗产的经验之一,便是重视“地域社会”。其政府文化政策中很多方面均涉及振兴“地域社会”,而文化遗产被认为是振兴地方不可或缺的“资源”。日本政府推动的诸多文化项目,诸如“家乡文化再兴事业”、“地域艺术文化活性化事业”、“推进青少年体验文化艺术活动”等,都不同程度地内含着活用地方文化遗产、振兴传统文化、促进地方发展的深意。2001年,日本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在国会得以通过,其“总则”也突出强调了文化对于人的意义以及“民众”的文化主体性原则。重视“地域社会”和文化遗产当事人各方的主体性参与,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表《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3年其报告的主题即为《民众与参与》,可知民众的参与已成为衡量发展的尺度之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例外,其目标是要实现世代传承或通过保护文化遗产以确保或增强所属社区的活力,因此,必须重视“地域社会”或文化遗产所属社区民众的广泛参与,包括让文化遗产各相关当事人(传承人、所有人、保护团体等)均参与到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中。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政府文化行政的强力主导下,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在普查、申报和建立名录体系初见成效的同时,今后更加重要的便是如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落实到具体的基层社区。文化遗产对于“地域社会”的意义无需置疑,在重视和依托“地域社会”保护文化遗产方面,日本先行一步的经验及案例[11],或许能够对中国的文化遗产社区保护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町内会”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居民委员会、社区或“街坊会”。“町内会”是指建立在村落或都市的街区(町、区),由当地居民组织的旨在维护社区亲睦和推动当地共同利益的“任意团体”(亦即不具备法人权利和能力的社团)。作为一种地缘组织,它在各地的称谓不尽相同(又有“町会”、“自治会”、“地域振兴会”、“常会”等称谓;在有些商业街,则称“商店会”)。虽然并非义务,但同属一个“地域社会”的人们往往有全员参加的倾向。
②“里山”主要指环绕村落周围、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山地和森林。相对而言,“远山”则是指人迹罕至的野山。
③结:日本基层村落共同体人们之间的互助组织机制或相关的习惯和规范,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地缘的近邻交往和劳动力的对等交换及共同作业的制度。一般在盖房子等重劳动或一时需要大量人手参与作业时,便全村集体出动或相邻之间互相帮忙。在白川乡,运营“结”这种互助机制的组织叫做“合力”。“结”所涉及的范围也并不局限于屋顶茅草的更换作业,它还涉及插秧、割稻、砍柴、割草及村民们的婚丧嫁娶等,可以说渗透到了山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④“氏子”:日本“地域社会”共同体所信仰的神社里奉祀的诸神,被称作“氏神”;而该“地域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该神社及其所祭之诸神的“氏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