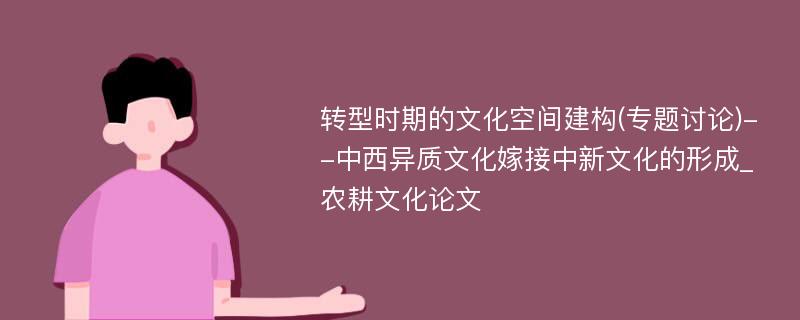
转型时代文化空间的建构(专题讨论)——中西异质文化嫁接中的新文化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新文化论文,中西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11-0005-12
中国从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走来,在经济变革的过程中,思想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面对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转型,中国特色文化的具体内涵与性质不同的西方工业文化有哪些共融面、契合点,则是需要弄清楚的基本问题。
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产生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性质规定着农耕文化的性质。而农耕生产方式的性质源自这种生产方式的资源——土地——的性质。
土地具有少变化的稳定性。“天下之物,有新则必有故。屋久而颓,衣久而敝,臧获牛马服役久而老且死……独有田之为物,虽百年千年而常新。”①土地的寿命与大地一样久长,得土地者便拥有传世恒产。不仅如此,与土地的这种稳定性相联系,其自身还具有另一特殊属性,即作为农业生产的资源,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再生性。只要耕地播种便有收成,季季如此,年年如此,永不枯竭。“或农力不勤,土敝产薄,一经粪溉则新矣。暨或荒芜草宅,一经垦辟则新矣。”②
土地的第二种特性是朴素、实在、守时。它总是朴讷无语,无所奢求;只要播种、浇水、施肥,总给予收获;并不因人因势而变,诚实无欺。这一品性培养出农民崇尚纯朴、厚道、诚信的性情,喜欢老实巴交的厚道人格,而讨厌浮夸、奸诈、机巧之徒。“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③
土地的稳定性引发出以土地为命的农民居住的固定性和生产的家族性,以及培育起了以家族利益中心的集体观念。那种居住的固定性与以家庭为耕种租赁单位,以若干有血缘亲情的家庭间协助合作的生产形式相结合,促进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家族集体意识。中国人的关注度由强到弱由近至远呈现出七层由小到大的时空圆,个人—家庭—家族—亲戚—乡邦—社会—国家。所以,中国的文化的命脉不是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而是生长于家庭的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亲情是第一位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④,道德是第二位的。道德与礼的功能在于维系亲情中上下主次尊卑秩序,并通过维系家庭秩序的稳定进而达到维系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农业生产具有强大的依赖性,农民因不能摆脱依赖而养成了顺从意识。农作物耕种收获的最大依赖是土地和掌握雨水风雪的苍天。如果没有土地,就不能耕作,就没有了粮食来源,无法生存,于是无地农民必须租赁地主的土地耕种,从而与土地主产生依赖关系。若有土地,而天气不好或遇上风、水、旱、虫、涝等自然灾害,庄稼颗粒无收,农民还是无法生存,从而对大自然具有依赖性。即使有土地、年景好,如果没有家庭成员的帮助、家族的帮助,个人同样无法生产、生存,因而又有着对家庭、家族的依赖关系。由于一个人对这种种依赖关系无法挣脱,必然采取顺从的态度,从而养成与依赖性相伴生的顺从意识。
农业生产对于自然的依赖、敬畏和顺从,生发出天地与人同心一体的天人合一思维,以自然为道的道法自然思想,以及天地大爱品德和万物生生不息的自强不息(包括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精神。人们每关注年景收成好坏、人事成败,先想到天地,从天地中找原因,“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⑤,“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⑥。于是,将天地拟人化,“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⑦;将人天地化,“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⑧,形成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阴阳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⑨。天地包容万象的宽大胸怀和普惠于万物的无私大爱,同样给予人无私品德的启迪,“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⑩,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佛学中的普度众生之惠等都与天地大爱对人德的启示有关;同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1),天地生生不息的精神也培育了人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建功立业的入世热情。
正是农耕文化的稳定性与再生性,衍化出耕种者朴实敦厚诚信的文化品格和重实际的务实精神;由家庭族群世代居住、耕种于一方水土的生产生活模式,培育出重亲情的家族集体意识、人情关爱和维系稳定秩序的德礼文化;农业生产对天地的依赖性、顺应性,启发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维、道法自然思想与和谐文化;天地泽惠、载育万物品格和自强不息精神,启发人以成就万物的大爱品性和建功立业的入世热情;天地阴阳的无穷变化,培育着中国人超强的感悟力和生存智慧。这些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内在的精华。
二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虽有其稳定性、承继性的一面,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更新作缓慢的演进。在跨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受到世界工业文化影响后,当下的中国文化已与传统意义上的农耕文化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工业文化(12)在本质上与农耕文化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其一,工业生产赖以支撑的资源不再仅仅是土地,而是无所不包的所有自然资源;于是,人类便向整个地球索要资源,从大自然中获取生产资料。这种向大自然进军、征服大自然的生产,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而不是顺应和谐。
其二,这种“人定胜天”的天人对立观念建立于人类对于自身力量的过分自信。其自信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自然界的主人,人具有永无满足的强烈欲望。二是人拥有不断实现强烈欲望的智慧与才能,不断地获得知识,进行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社会制度的改革,生产出可以满足人类欲望的现代化的先进工具和先进制度。这两种自信反映出工业文化的特质: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崇尚创新和竞争而不是压抑个性以求稳定。竞争和创新是工业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
其三,从工业生产的产品——商品——的属性中可以发现其有别于农业文化的价值观念。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生命,而只有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才能换回体现商品自身价值的货币,进而使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而商品价值的实现又是获得剩余价值的前提,当资本家把满足自己的需要——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当做自己的天职时,他必须首先想方设法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这一事实使一些思想家发现自利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关心、帮助、爱护他人则是出于爱自己的需要。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私欲——情欲是万恶之源的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四,生产商品的目的是换取商品的价值——货币,它不仅能体现出商品自身的价值,还成为衡定一切商品的价值的尺度,故而货币以及货币观念中映射出工业化生产的基本属性和工业文化的核心内涵。它们包括:拥有货币可以提高人实现欲求的程度和自由度,从而获得更大自由(尤其是物欲的自由);货币的等价交换原则唤醒并推动了人的平等意识;货币以税收形式成为体现公民和国家间关系的中介物,使每位公民以纳税方式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从而起到了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作用。这种以货币自身所具有的推进平等、自由、民主的功能与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工业生产的总目的所构成的以人为本的人本文化,与农耕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维护家天下统治的忠孝文化、民本文化,形成了鲜明的质的差异性。
其五,货币还体现出工业生产所具有的两种文化内涵:一是无限的联结功能,一是拜物主义。货币具有与一切商品交换的能力,具有将一切商品通过交换而发生普遍联系的功能,而随着商品生产的世界化,带来了交换市场、人与人关系的全球化。它不仅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市场将一国的公民联结为一个共同利益体,而且通过全球的市场将世界消费者联结为共同的利益体。特别是电脑与互联网的信息网络使这一联系更直接、便利和快捷,从而极大地增加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联系度。这一特征与农耕经济时代的小国寡民式的家庭自足形成了鲜明对照。货币一旦成为换取人们生活必需品的唯一交换中介,成为实现欲望的唯一的东西,货币便由人生的手段跃升为人生的目的。人的欲望的实现变成为货币占有欲的实现,于是便引发出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和拜物宗教。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里,物质的利益高于政治利益、道德、名声等一切之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不仅被视为人的本质,也视为国家的根本。这种物质至上、经济至上、金钱至上的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中“重义轻利”(13)、“贱货而贵德”(14)的价值观形成极大的反差。
三
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一个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个主张天人对立,强调矛盾斗争。一个强调顺应天意和时势,追求社会的和谐、安宁、稳定;一个强调适者生存,追求创新、冒险、竞争和社会的变革。一个重义轻利,将道义、声名的追求置于一切物(包括生命)的追求之上;一个则崇拜物质价值,将金钱、财产等物质利益的占有置于一切生命活动之上。一个以家庭、家族集体利益为根本,以家长制、道德和人情为维系社会整体的纽带;一个以个体利益为根本,以平等、自由、民主和法律为维系社会整体的纽带。
面对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是让人们自由地去选择?还是有意识地将农耕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先进文化嫁接为一个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崭新文化空间?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发展事实表明:文化放任自流之路是不可取的。它将会受到实用理性和功利主义目的性的支配,使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死魂复燃并与工业文化中的拜物主义、疯狂的占有欲沆瀣一气,导致中国农耕文化出现日趋后置和弱化的危机。
将两类性质不同的文化嫁接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化中华文化,需要找到共同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追求人生的幸福,即以实现人生的幸福为契合点将两种文化的精华嫁接再生为一种崭新的文化。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与自然界的生存变化和平相处。中国古代主张“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就哲学层面而言是智慧的。西方工业文化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类是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获得自身发展,故而应从自然手中夺取资源,造福人类。尽管前者意在追求食货需求满足的和谐幸福,后者意在追求货币化需求最大满足的幸福,但这两种观念的意图皆为实现人类幸福。由此看来,以人生幸福为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可以用智慧的传统文化观念吸纳西方的先进文化内核。具体来说,以科学创新精神为支撑点,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纠正天人对立的思想;以天地大爱品格接纳西方先进的人本主义;用古代重义轻利的乐道精神净化西方的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以中国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吸纳西方的创新冒险精神;以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进步政治理念,改革中国农耕社会遗留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陈旧思想和体制模式;以西方的科学主义接纳中国人的阴阳五行、刚柔相济的感悟智慧等;摈弃、剥离中国农耕文化中愚昧、专制等腐朽落后内涵和工业文化中使人类自戕和异化的黑色暗流。在操作层面上,应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沟通、扬弃和创新,在形而下的类式文化层面保护、传承,在中间政治文化层面进行大胆果敢、有序而稳健的革新。从而将两种性质迥异的文化通过理论创新和生活实践,建设成在生产和生活中切实有用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
注释:
①②张新:《恒产琐言》,见《笃素堂文集》卷三。
③《吕氏春秋·上农》。
④《礼记·中庸》。
⑤《吕氏春秋·贵因》。
⑥《管子》卷一。
⑦《庄子·达生》。
⑧《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⑨《礼记纂言》卷二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吕氏春秋·去私》。
(11)《周易·乾卦》。
(12)本文所言工业文化,是指建立于以三大产业(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为主体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广义的工业文化(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只是工业生产发展中某一阶段的某种方式,而并非已超出工业生产的范围)。
(13)《荀子·成相》。
(14)《礼记·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