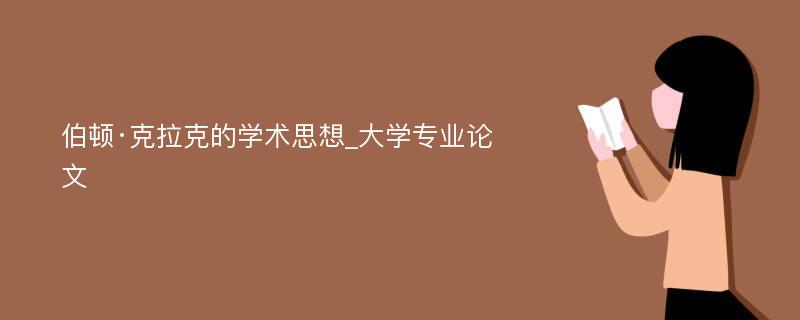
伯顿#183;克拉克之学术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拉克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伯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科演进的基础
学科在伯顿·克拉克教授看来,是一种结构化的分析方法,也是学术世界概念分析的起始。“学术专业化发展了一个独特种类的结构化的思考,被称为‘学科’,学科不仅仅是一种课程事务,而且是一种结构化的分析方法。”[1]“结构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管理复杂性的代名词,学科专业不仅对学术管理模式提出多元结构化的需求,而且学科本身固有的特性——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越来越复杂的结构赋予了学术组织管理之区别于其它社会机构管理的独特性,这种结构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教授的分配、资源的配置、工作任务的计划,以及实现对地位、身份、声望、尊重与奖励在组织成员间的分配。
关于学科产生的途径与过程,克拉克教授探讨了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尔特·梅茨格(Walter Metzge)所提出的——“实质增长”(Substantive Growth)的概念,以及驱动学术专业化发展的四个过程:学科的衍生(Subject Parturition);程序上的从属关系(Program Affiliation);学科的声望(Subject Dignification);学科扩散(Subject Dispersion)。例如,新自然科学学科从自然哲学和自然历史中衍生出来;化学早期的诞生及地位的巩固得益于医师的训练计划。再比如,当今的美国专业生活之雏形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就是“高等教育与专业教育又一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本科生教学计划之上增加了研究生教学计划等等。
通过对学科产生与扩展四个途径的演变进行案例分析,克拉克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学科高奏进行曲的行军图景。其一,学科或专业知识体系由简到繁、由一维到多维、由少而窄到多而宽的演进过程显现了一个三段式——以古典语言与文科为核心的传统学科,以现代语言、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为主导的近代学科,以高度分化的学术专业为核心的、以学科边界持续不断的延伸以及与之伴随的跨越边界活动为特征的现代学科。其二,揭示出学科演进的基础及规律:“美国系统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以来的增长和多样化,归于实质增长——学科及他们的寄主系统不断纳入新学科。正像像梅茨格所确认的——驱动令人惊奇不已的专业化发展形式的四个过程。”[2]克拉克认为,实质增长指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相对于学生数量、教育规模的增长之外的更为实在的增长,学术专业之“实质增长”过程就是学科演进的过程,也是学科演进的基础。实质增长的动力源,存在于社会劳动分工之中——新事物在抗争传统规章的过程中,努力寻求合法化的生存空间,成长为将人类文明不断推向进步的历史合力中的一部分。学科结构的分化实质成为高教系统发展的最活跃的动力学因素。“学术亚文化是一种有力量的现象。在美国,不同的院校类型和学科类型在每一个轴线上都呈现了难以计数的区别:学术身份的分化跟随着无法抗拒的劳动分工而前行。”[3]“学者身份”呈现出历史与当代的两条线路和图景,‘真理’采用了理性与经验的两种形式;‘知识’是最先进的支流。专业则被赋予一个超级构架,学术借此向社会阐明他们正在从事着有价值的事业。”[4]
二、学术组织模式的变迁
克拉克教授认为“学术(Academics)实质上甚至是由诸如‘我们是学者社团’等象征神圣的观念紧紧地联系起来的。”[5]概言之,从宏观上讲,学术组织相当于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即指将学术世界各个组织部分彼此联系起来的纽带、方式与方法。从微观上讲,学术组织模式即作为学术基层单位围绕学科组织起来,如讲座,系和研究所、各种跨学科的研究中心等。
中世纪大学行会演变形成近现代的讲座制。讲座制以“学术自治”为核心原则,接受捐赠,凭借“特许状”规定的某些特权抵制外部力量的渗透与干涉,等等。就此而言,讲座制仍属行会式学术组织,但相比中世纪大学行会,教师群体和学者议会的权力渐被削弱,而教授个人的权力日益突现,新的科研方式和专业联系开启了一个现代专业化时代。“从1820年以后,德国学术世界中的新学科即为建立和发展教学—科研实验室及教学—科研研讨会而艰苦地工作,这些努力极大地提高了他们自己的群体的科研生产力,也极大地加强了内部的科研训练。”[6]
研究生院与系的构建是为移植外国的先进制度与思想,并让它们在美国本土开花结果而作出的成功尝试。研究生院的设立,推进了现代科研体制制度化管理,提高了科研工作及高级人才培训的效率;另一方面,系的构建旨在防止学者社团过于滑向垄断与武断,通过建立“系务会议”及“一人一票”制(one-person-one-vote),有效保障高级教授与初级教师甚至学生参与系务决策的权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联邦德国的那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提供了显著例证,改革使大学里出现了许多新型学术单位,被称为"Sektiones"(相当于英美大学中的系)。
欧洲大学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之后,增加了新的带有不同功能的单位,改变了原有单位的结构。这些变革引发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教师工作负担量过重;(2)下级教师收入偏低;(3)在所有群体中,包括高级教授,感到被剥削的情绪在增加。[7]初级教师和学生群体经过艰苦不懈的斗争,使参与院校决策的权力得以合法化,改革的法令还有助于政府对高教领域的介入,所有这些变动的现实,都促使德国、法国、瑞典等欧陆国家的高教学术组织进行了朝向系或类似机构的改革。
三、教师群体的权力与分化
教师群体作为高教系统的中坚力量,其地位、权力、专门的知识与技术,及他们所信仰的价值观念体系等方面的特征,决定着高教系统特性明显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
其一,中世纪有“先生大学”(也有“学生大学”)。教师群体是学者行会的主体,也是拥有皇家“特许状”授予的多种特权的惟一群体。中世纪大学并不存在捐赠人和行政人员的群体,因此,掌握学术自治权的教师群体被世人称之为“社团”,而学术社团的精神由此演变为古典大学理想的核心。
其二,19世纪现代大学中的讲座制产生以前,教师权力在欧洲大学获得了稳固的发展。同时期,在大洋另一端的美国“殖民地学院”却呈现出另一番图景:捐赠人为主的董事会掌握着院校的决策权力,教师社团的影响虽然有所存留,但由于教师本身的雇员身份,社团的影响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另一方面,代表董事会行使院校统治权的科层行政群体产生,行政权力不断增长,教师权力逐渐缩小,校长与著名教授权力凸现。
其三,以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的讲座制为代表,近代社会赋予社团组织以规范的知识管理的特征。讲座制拥有社团的一些特性,如教授们组成各种形式的“学者议会”与各种委员会,拥有较大的决策权。随着大学学术管理复杂性的不断增长,教授个人尤其是学科带头人、学部领导及讲座教授等被赋予重要职权,讲座制也推动了以集约化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的运行机制。但由于讲座教授职权过大,也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存在剥削及严重压抑年轻低级职位教师升迁的现象。
其四,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的“大学时期”,它的研究生院与系的构建赋予了教师权力以新的意义。“在反科层中最有意义的是‘基层选拔’制(Election from Below)而不是由上级主管任命的广泛应用。如果选举权仍然保留在中央官员手中,那么对系教师成员的广泛的咨询对于加强可能的被任命者的接受性是必要的。”[8]系的建构不仅适合美国本科注重通识教育的传统,而且在多种利益群体渗透到高等教育决策领域中的要求不断增强的形势下,教师群体(主要指初级教师)在夹逢中为寻求参与决策的权力做出了艰苦的抗争,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就是一个例证。此后,增强教师群体及学生参与决策的权力通过合法化的轨道,在系及同类组织的民主化改革中得以巩固。
综上所述,教师群体权力的演变过程正是教师群体经历外部与内部分化的过程,这种分化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教师作为“学术社团”的主体拥有较独立的决策权与学术自治权;二是董事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不仅引起院校内部教师群体与行政人员的分化,而且也开始了外部各种利益集团向大学合法渗透与反渗透时代,同时,大学校长、讲座教授、著名专家、学院院长等少数学者领袖在教师群体中也产生了分化,前者成为教师群体中生产力最强,成果最多的少数上层群体,后者是以青年初级教师(包括讲师与助教)为主体的多数底层群体;三是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讲座制时期,教师群体的分化突出了教授个人权力,学术自治与社团的含义发生了历史演变与重心转移,讲座教授为代表的上层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垄断着学术社团,“强制性”推行其认可的文化与学术规则;四是系及同类组织的构建,赋予初级教师(也包括低职位行政人员和学生)群体参与院校决策一定的席位和系务管理投票权,初级教师群体在明星教授与影响院校决策的外部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中寻求生存的机会与空间。
同时,教师群体分化也按照机构分化与学科分化的路线,呈现了高度专业化时代的特征——分化导致多样化与竞争,“那些相反的力量倾向于将学术专业一分为二。声望等级的上层部分变得更加专业化了……而在底层部分,则变得较少专业化,更多的工作责任赋予学生的教学,比起学术带头人,他们更依赖于学生的反应和需求,并且严重为市场需求所驱动。上层群体试图证明他们在生产知识,底层则在扩大入学。”[9]
四、分化的学术系统
学术世界的分化与分工在克拉克教授的论著和论文中是一个关键命题。他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总括了分化的两个方向和两种职责,一是院校的分化,一是学科的分化。当我们循着院校和学科分化的路线对高教内在的结构特性进行探索时,便发现了许多吸引人的命题。例如,是什么力量将如此多样而分散的部分与人员联结起来?学术专业化与学科分化构成各国高教系统分化的核心和最基本的差异。所谓学术专业化即指以学科为中心的分化,专业化意味着随着专业自主程度的提高,赋予某种学术专业活动以一定声望、权威及地位,通过专业地位“合法化”的途径,获得相应的工作任务与资源配置的权力,因此,理解学术专业化将提供认识“学术权力”、“学术自治”等基本概念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学术专业系统被克拉克教授称为“小小的世界,不同的世界”,喻指分散性、竞争性、多样性与分权机制成为现代学术专业化运动的固有特征。
克拉克曾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作了详尽阐释,提出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由学科和院校交织而成的“矩阵结构”(Matrix Structure)。不难理解,“矩阵结构”正是学科与院校通过纵横交错的经纬线编织而成的学术世界网络,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各种参与者、资源及纷繁的工作任务都由此获得了合法存在的空间。当然,将分化的各部分联系起来的力量和各种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排拒主观和武断的。并非体现个体和某一群体意志的“矩阵结构”,内在地存在于高等教育系统长期演化与变革的过程之中。
应用社会分工理论对于分析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性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具有极其关键的意义,“学术结构的生命力暗示着一个宽广的政策,即从扩展的经验到现在合同的经验,是一种结构分化,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同义语。”[10]“教学与科研进退维谷的境地的根源,深置于竞争和等级的条件之中,这些条件隐藏在开放的和严重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统长期的运行机制中,如果不进行相当程度的分化,系统是不能够实现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的并存的。”[11]由此可见,分化的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了以院校规模迅速增长为特点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例如,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广泛分类的高教系统,其学科分类几倍于院校的分类: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生物科学领域知识爆炸式的增长,生物学出现亚专业化(Subspecialization)。在单一的大学里,生物学中大约有五个或更多的亚领域获得了独立的系或研究所的身份。如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设有生物学系、微生物学系、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生物数学和生物化学系、分子生物学系,还有一个大型的跨系的教学计划,也能够颁授博士学位。而生物学系本身也被列入30多个领域,它们提供研究生自由选择的可以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领域。[12]80年代末,设在宾州的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对科学学科的专业领域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当前仍然活跃的专业领域超过8000种。分化的高教系统结构越是成熟就越能推动各学科或专业领域寻求独立身份的尝试,因而就越能够推进专业自主程度的提高。当高教系统从应付规模扩展转变为迎接一个“契约式”的合作与控制的新时代的时候,由于“专业中的专业固有的离心性,尤其是每一个亚专业都是由科研的必要性所驱动的,这种科研不断地扩大其自身的知识基础。多元化(Polymorphism)于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趋势,分化(Differentiation)比共性(Commonality)更受鼓励。”[13]
由此可见,分化的多样化系统提供了维持大众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并存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克拉克指出:“那些想用各种行政管理规则取代专业规则的做法将使学术职业趋于衰退;明智的专家意识到只有专业的概念和实践才是根深蒂固的。然后他们一起形成专业灵感与自律的条件。在国家、市场和学术专业化之间的位置,无论其如何分化,都保持着高等教育运行与进步所必需的基础。”[14]
综上所述,克拉克以“矩阵结构”和学术分化理论为起点,从显到隐、由浅入深地构建了一个多样的、分化的、竞争的学术世界,学术系统因而承担着与其分化的机构一样复杂而多样的职责,学术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艰苦的思考,因此,学术活动与成果的评价都与学术系统的特性密切相关,“专业主义是一种整合工作意义的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信仰系统。”[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