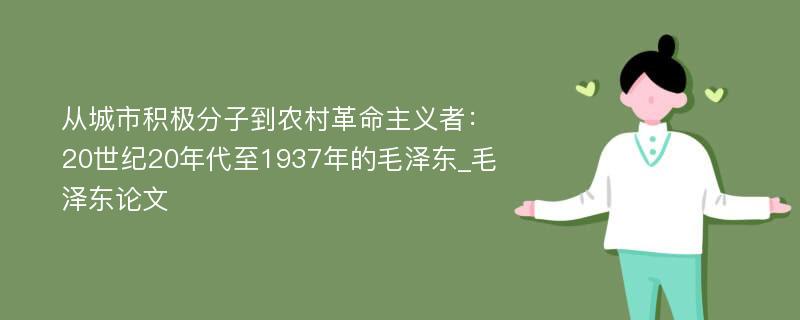
从城市激进分子到农村革命家: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的毛泽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家论文,激进论文,分子论文,年代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1)05-0046-10
本文从讲述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开始,涵盖了他漫长人生的前半生。在本文所涵盖的时期结束时,毛泽东成为了党的余部的领导人,这时党刚刚从第二次几近灭绝的大围剿中幸存下来,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和中国西北的人民群众,乃至应对来自日本的新威胁。因此,只有作为毛泽东后期生涯的序幕时,“早期毛泽东”看起来才有吸引力——这个时期,他正等待时机登上历史舞台。
然而,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革命的成功领导并非由偶然性或者深层的历史进程所决定。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是在1937年打下的。虽然1937年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农村阶级斗争,而是抗日战争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但是农村革命再次成为1945年至1949年与国民党之间的国内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本文的任务在于分析从最初接触和介入(通过以谋生存为驱动力而发动的农村革命)处于全面混乱状态的20世纪初的中国,到长征后重塑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的政治角色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尽管1937年局势危急,但当毛泽东在延安面对着全新的局面时,他充满着信心,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其早期经验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没有试图维护旧的秩序,而是尝试创建新秩序,而且他陶醉于隐含在革命事业中的风险、机遇和荣誉。
很自然地,他具有激进的政治观点,但是他既不是空想家,也不是孤独者。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更加重视实践。而且,即使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最终的政治力量是动员民众支持。务实性和民粹主义使他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入党,但在1927年,他所推动的农村动员使他处于被党边缘化的境地。然而,在1927-1930年党遭遇失败和被清洗之后,为了在农村生存下去,经过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党)终于产生了一个农村革命的方案。1934年,长征结束了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最初实验,并确立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的地位。1936-1937年,他不得不将自己对农村革命的经验教训,重新形成为领导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总路线。
虽然对于毛泽东来说,理论和实践从来没有分开,但是他的思想的发展却是本文所涉时期最重要的主线。我将追溯毛泽东所处的环境、他的思想以及他的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束于他在1937年所作的反思和概括,而不是将这个时期作为他后来的活动的根源。主要资料来自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主编的《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Mao's Road to Power)一书中前六卷收集的毛泽东的著作,因为这些不仅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反映了他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看法。不过,正如你将看到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一开始就一直是毛泽东成长历程中的主要特点。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毛泽东生于1893年。他在中国急需复兴的时期形成其思想意识。旧思想已逝去,新思想正待形成,青年承载着中国所有可能的未来。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这并不是一个借助发掘过去而重振当前的漫长过程。相反,这个时期所面对的是全面的危机,这种危机源于传统中国在西方优势力量的冲击下所发生的崩溃。那个时代的困惑和混乱,恰如那一代人的使命感和自由感一样,共同造就了毛泽东。
(时间上)被压缩了的思想的现代化造成了三个基本的思想冲突。第一,全盘否定中国的过去与坚持中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人格的全盘的自我否定相伴的是,对于改造自我和国家的强烈吁求。① 中国是软弱和落后的,因此,一切都必须从自我改造或者消亡中选择。第二,作为榜样的西方形象与作为威胁的西方之间的矛盾。“赛先生”和“德先生”使西方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耻辱成为可能。② 现代西方五百年来的历史和思想一下子呈现在毛泽东他们这一代人面前,从莎士比亚到卢梭再到斯宾塞,浓缩为一种充满着惊奇和钦佩的极为强烈的体验。然而,最切近的(体验)却是由于中国遭受侮辱而激起的愤怒。早在1905年,在毛泽东家乡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就有学生示威游行反对美国限制中国人移民和拥有财产权。③ 第三,中国新青年摆脱了特殊主义和习惯的羁绊,但个人的完全自由是与巨大的普遍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社区成员的意识依然保留了下来,尽管其传统的内容被消除了。得到赞赏的是个人而不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由于中国的形势处于全面的危机,可以说新青年获得了解放,但没有被赋予权力。
个人经历以及(时代的)背景塑造了毛泽东。在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对他的采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早期有重大影响的时刻,并不是产生于对抽象的或者是民族的关切的间接介入,而是源自他个人的切身经历。④ 可以肯定的是,其他的传记作者已指出,毛泽东美化他的革命出身,并忽视他的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在那个时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⑤ 毛泽东的自述,从10岁那年与父亲发生冲突开始讲起。由于他母亲怀孕,他从2岁到8岁被送到邻县四世同堂的外祖母家抚养。⑥ 很可能是这个早期的离家经历,以及母亲的同情心(的影响),使他在面对自己的父亲时形成一种自我的意识,也使得家庭内的反抗成为可能。也许,它还造就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的充满冒险精神的自信。
显然,出身于农村使毛泽东具有鲜明的南国风格,并显著地贯穿于他的一生。⑦ 毛泽东的乡土气并非后来的做作。从斯诺的描写中明显能看出毛泽东是非常质朴的:在1936年条件很艰苦的保安,当时他仍然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⑧ 但是对于西方观察家来说,很容易从毛泽东的粗野的农民形象跳到做出这样的假设,即他是,或者想要成为一个把眼光投向现代性的乡巴佬。正如萧延中所说,毛泽东的背景更准确地说应该被称为“农家”,而不是“农民”。⑨ 在西方,承载资产阶级文化的“城镇”一定是城市,相比之下,在传统的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文化界限并没有被如此精细地划定。毛泽东所受的教育与在城市里本来应该接受的一样,如果他有幸接受城市的教育的话。农村与城市的主要文化鸿沟出现在20世纪,随着城市成为新鲜事物和世界主义的中心而产生。像毛泽东这样聪明的、有冒险精神和叛逆的孩子是自然不愿意做一个这种令人兴奋的事物的旁观者,所以他在1910年搬到县城湘乡,1911年17岁时来到了长沙。虽然他在1925年曾告病返乡,但是直到1927年被蒋介石逼回农村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再搬回农村。
在长沙,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报纸,他变得更加注意中国和世界的时事。他还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做了广泛的阅读。他一方面在智识领域积极探索,另一方面更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鼓舞下,他参军六个月,亲眼目睹了湖南首任并非效忠于清帝国的正副都督在执政9天后被斩首,陈尸街头。他热心于体育锻炼。他与一位朋友一起在湖南晃荡了一个夏天。他投考政法学堂、警察学堂、制造肥皂的学校、商业学校。这是他对于城市新出现的大量机会表现出实践层面的冒险精神的明证。这也许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即如果毛泽东的英语好些,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长沙的一名商人。⑩
1914年3月,在毛泽东20岁的时候,他被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第三班,同年秋,被编入本科第八班。(11) 他于1918年6月毕业。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经历了思想的转变,《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第一卷中对此有记录。然而,在着手分析他早期著作之前,我们应当考虑毛泽东这些年的社会性发展(social development)。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实践活动的两条主线就是提升组织能力和政治化水平。去长沙之前,同窗好友就一直对他很重要;在1915年9月,毛泽东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主义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11月,被选为一师学友会文牍。1917年10月,当选为学友会总务,开始组织工人夜学。尽管在学友会内的组织很成功,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决定成立另外一个更为精英的组织。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12) 与学友会10月会议60人参加相比,只有12人出席学会的成立大会。学会也没有打算变成一个更大的组织。新会员需要有5名会友介绍。到1920年,学会有20名会友在长沙、18名在法国、9名在其他地方。(13)
无论在其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新民学会打开了一扇通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窗户。这是传统中国的组织和价值观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灵感的混合体。1920年末,毛泽东详尽地、非正式地对学会成立后的前三年进行了反思,他提出了学会成立的三个理由。(14) 首先,会友想要提高自己的个人素质,认为求友与互助是根本的原因。其次,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使其“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是必需的。最后,他指出,大部分会友都是杨昌济的学生,而杨先生强调不断地为自我完善而奋斗。(15)
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学会其他人的活动都不限于道德和思想上的自我完善。事实上,毛泽东的活动内容就像他在1912年参与各种培训课程时那么分散——体育教育、工人夜校、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广布全省的文化书社、平民通信社、驱张运动。毛泽东密切地关注他所推动的各种行动的可行性和重要性,总的来说,它们都相当成功。毛泽东无疑是一个“能干”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善于动员”的人。他对含有潜在参与者的重要听众采取这样的(动员)方式:并非“这就是我的想法。请跟我来。”而是“这是一个紧迫的、普遍的问题。要想有所作为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做。”
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的,毛泽东1920年之前的政治,是从支持杰出的传统统治者演变为认同激进的政治变革。(16) 然而,他的学校活动很清晰地表明,毛泽东早期的观点并非谨小慎微的征兆。在湖南一师第一学年的期末,他积极地参加了因反对加收十元杂费而驱逐校长的学生运动。(校长)威胁要开除毛泽东和其他十七名学生,但在老师们的干预下作罢。七月份,校长被迫辞职。(17) 很明显,毛泽东不是一个回避风险的人(risk-avoider),由于绝望而诉诸激进主义。相反,他是一个冒险家和活动家,出生在动乱的年代,养成了自己做决断的习惯,逐渐认识到唯一可行的行动是激进的变革。
总的说来,毛泽东现存的早期作品(1912-1917年)中的政治观点主要关注的是建立有效的秩序。这在他1912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18) 中有突出的体现。对于那些熟悉毛泽东后期生涯的人来说,这篇文章最突出的特点是贬低了中国人民,赞扬了古代法家的政治家商鞅。然而,这其中隐含着一致性。文章是建立在对中国积弱和几近解体的严重关切之上的。文章在将传统人物作为效仿对象这一点上是保守的,但它绝对不会捍卫现有政权而抵制改革的力量。(文章所传递的)信息是说中国正处在如此岌岌可危的境地,必须恢复对有效政府(effective government)的基本信心。只有善法是不够的,因为“非常之原,黎民惧焉。”(19)
毛泽东在1916-1917年对体育的重视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表达,也不仅仅是对湖南一师紧迫问题的反应,而且是一个解决中国软弱问题的相当直接的方法。《体育之研究》发表在中国最优秀的进步杂志上,开篇写道:“国力苶弱,武风不振”。(20) 但是文章主要强调的并不是只要每个人都锻炼,中国就将会取得的利益。相反,他不断强调每位读者都需要增强体质,每个人都必须从认识到行动。在社群的强大和个人的强大之间显然是存在着和谐的。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建立秩序的问题转移到更为基本的、个人的任务:强壮体魄和增强意志。文章的非政治化基调暗含着(作者)对于中国既不自大也不自卑。当然,中国还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以完成(历史)使命,但是通过锻炼,弱者能够变得强大。正如他一再强调的:“天地盖惟有动而已”。(21)
毛泽东对弗里德里希·泡尔生(Friderich Paulsen)著的《伦理学原理》(由蔡元培翻译)的批注,是最近30年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新文本。尽管格式(指批注的格式——译者)对上下文的理解有所限制,但是毛泽东的知识分子人格在1917-1918年湖南一师学习的最后一年的冬天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已转向关注个人,在批注中完成了这一转变。毛泽东在这一转变历程中给自己绘出了非常详尽的思想肖像。
当然,毛泽东对泡尔生的评注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自己思想的完全表达。泡尔生的文本确立了议事日程。如果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发表意见,那么他思想的列车将会有所不同。然而很显然,毛泽东的评注不只是对他阅读段落的冲动反应(一些包含了对后续文本的参考),更重要的是,他形成了一个与泡尔生的表述截然不同的、关于个人和道德的观点。泡尔生设置了主题,但是毛泽东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阅读泡尔生之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很不幸的是原文丢失了,他自己说这篇文章是他这段时期最主要的思想成果。(22)
吸引毛泽东和他的老师杨昌济的是泡尔生对个人道德状况的持续关注。按照西方的标准,泡尔生文章的主题思想既不激进也不新奇。相反,它是为主流道德的理性基础进行小心翼翼地和富于实践思想地重建,这种主流道德以自我为中心,但同时承认利他主义的高尚伦理境界。对于刚刚从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欧洲人,泡尔生试图(为他们)提供一种个人道德的指引,使其方向大致上与教会和国家所指向的方向相同。(23) 在内容、方式和目的上,泡尔生的作品属于新康德主义,对尼采持反对态度。
在中国的环境中,泡尔生的文章为道德问题提供了一个理性的、以个人为本位的基础,但却是非常新颖的。挑战也是相当大的,而传统道德的内容则不同。在西方,从笛卡尔(Descartes)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开始,一直延续着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重建现实性(的传统)。然而在中国,儒家世界的突然崩溃才产生了毛泽东那一代的个人。此外,泡尔生道德的基本方向与康德相同,是世俗化的新教,强调个人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中国伦理传统强调的“三纲”,即社群中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毛泽东对泡尔生的评论显示了他对个人主义道德重建的热情接纳,以及对泡尔生的个人与社会分离观点的批判。
毛泽东无疑对自己所发现的个人充满热情: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24)
但是毛泽东对个人主义的赞颂与泡尔生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同一段评论中,他继续写道:
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精明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毛泽东思路上的一些困难,但是对于理解他的思想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个人和社会的观念仍然是糅合在一起的。当毛泽东赞誉自私、批评利他主义的时候,他并不提倡尼采的反社会利己主义,甚至也不提倡像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或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样,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间接地为社会带来利益。相反,他不接受在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隐含在泡尔生对关注他人(other-regarding)的行为的赞扬之中。在毛泽东看来,宽宏大量的人不是为他人服务,而是从更宽意义上的自我去行动。他说:“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25) 在1920年对新民学会的反思中,他反复地使用了“个人与全人类”的表述,同样暗示着个人与全体的善是相同的。
如果毛泽东的个人主义不是(必然地)意味着个人优于集体,那么它所指的是什么呢?正如他后来遗失的文章《心之力》的题目所暗示的:变革的意志力的挖掘,而不是将社会分解为(彼此)自治的个体。中国全面危机的形势正在加剧,由于一个军阀的军队驻扎在学校,毛泽东的最后一学年即将提前结束。他的可行的活动范围缩小到为长沙市民筹集救济基金和组织新民学会的法国勤工俭学项目。这些活动的更大意义,尽管与中国的问题相比是如此微不足道,在于揭示意志力(个人或集体的)对于现实的改造能力。
毛泽东对于自己出生在混乱时代是很兴奋的: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26)
从最后一学年的那个富有意志力的非常自信的人可以看出,对英雄人物的这种赞美意味着(毛泽东)对非传统职业的选择。
1918-1919年毛泽东到北京和上海旅行,回来后更多地介入激进的民族思潮。他返回长沙时正好赶上领导湖南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有两层深刻但是相矛盾的影响。首先,民众示威所激起的热情直接影响了中国政治,在这种热情的刺激下毛泽东产生了立即发动变革的强烈梦想,这个梦想在他1919年春季编辑出版的《湘江评论》的一系列雄辩的文章中得以表达。然而,运动的结束与它的出现一样迅速,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然后,毛泽东放低了他的政治眼光,热情地参与到大胆的但却非革命的运动中:驱逐湖南省长并建立省自治政府。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第一段表达了毛泽东的乐观和热情: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得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27)
在这里,对泡尔生的批注中那个有着伟大灵魂的个人英雄变成了民众大联合的集体意识、意志和行动。他认为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是建立在人民联合的基础上的,因为被剥削者总是多于剥削者,所以只要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联合和力量(的重要性),他们将能获胜。意识是关键,因为即使是作为压迫者的士兵自己也是被压迫的,在人民的大声呼唤中,他们的子弹将会“化成软泥”。(28)
到八月份毛泽东主编最后一期《湘江评论》时,(毛泽东)对社会变革的高期望值已经有所降低。毛泽东从来没有批评“五四运动”,它已经成为他自己、他的同志们和整个中华民族政治化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它的失败为他的政治期望和内容(虽然不是总体价值观和方向)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现在的关注焦点是当前问题而不是关于变革的宏伟计划上。他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妇女现状的尖锐评论,但是他最重要的公共活动是反对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张下台之后提倡湖南自治。与此同时,毛泽东与新民学会忙于建设一个广布全省的书店——文化书社,毛泽东将它设计成一个允诺和强调公共服务和透明运作的典范。(29) 不久,他创立了同样注重开明的商业运作的湖南自修大学。
毛泽东所倡导的湖南自治与他后来的政治观点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第一,对于湖南独立运动,毛泽东得出了一些相当令人吃惊的论断。毛泽东的根在湖南,这一点直到他最后的日子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是他唯一一次建议中国的一个中心省份可以选择独立。(30)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全民动员的要旨是民主改革的确立——建立一个普选基础上的制宪会议。这在表现方式和内容上,都是非常激进的,正如《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当时报道的:
[宪法会议的建议]文件由三个人提出:《大公报》的龙先生,湖南一师的毛先生和书商彭先生……430位签名者中,约30人说要与本市的新闻界保持联系;大概200人是教师或者学者;约150名商人;还有,比方说,50名工人。有趣的是,工人不仅被邀请,而且工人阶级代表与城市最有文化的一些人肩并肩作为15名代表团成员向省长递交请愿书……无疑,此时此刻中国的目光都聚焦在湖南。(31)
这个目标与“民众的大联合”并不矛盾,但是目标是政治变动而非乌托邦式的变革。结果令人失望。当新任省长谭延闿,感觉受到湖南宪政民主的呼声威胁时,他就解散了示威者。
毛泽东与革命党,1921-1927年
毛泽东与居住在法国的新民学会成员的通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自己想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决心。(32) 他的两个好朋友,蔡和森和萧子升,与在法会友讨论学会未来道路时,意见出现了分歧,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讨论自己的观点。蔡主张共产主义,而萧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33) 毛泽东仔细地强调了他们意见的共同点,赞成萧意见的某些方面,但是他明确地主张积极的革命党。因为现在的教育体制是由精英控制,所以教育是一种不充分的革命方法,无论如何,是利益而不是知识决定了意见。毛泽东承认共产主义并没有像其他方式那样有吸引力:“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34) 因此,可行性是共产主义最主要的吸引力。在当前的非革命时代,它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行动指南。它确立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继续活跃地参与新民学会以及在他转向共产主义之前已经开始的(其他)各种计划,但是两个新的关切越来越吸引他的注意。第一,他开始参与劳动组织。尽管在建立学会之前他就已经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但是则是组织遍布湖南的各种联合,并参与了一系列罢工。虽然湖南不是先进的工业(或者城市)省份,然而在1923年之前是劳动组织的佼佼者——这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另一个主要活动是组织中国共产党。他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创立参加者(founding participants)之一,那次会议湖南代表占了五分之一。到次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湖南是三个最大的省级组织之一,仅次于上海和广东。(35)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领导者,任支部书记,也是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很显然,当毛泽东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并没有成为他人组织性武装的工具。诉诸共产主义是因为它为活动提供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总体框架,并提供了毛泽东已经并将继续为之努力的总体目标。作为一个成功的省级领袖,他带给中国共产党的比他从党接受的要多。
1923年2月2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大规模屠杀铁路工人,迅速地掀起了工人运动的大潮,但吊诡的是,它也增强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服从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服从。也因此结束了毛泽东作为激进湖南精英之领导者的生涯;他于四月份前往上海,开始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实际性(和分配的)工作任务。不久之后,他介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络工作。从而也终结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独立自主的权力基础的梦想,因而也结束了对共产国际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抵制。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受挫。因此,(国共)合作的时期到来了。
即便对于革命统一战线而言,毛泽东也不是一个快乐的官僚主义者。虽然有传记作者质疑如下的观点,即毛泽东在1925年长时间返回湖南除了疾病的原因外还有政治的原因,但是一个更合适的解释可能是:纯粹是源于政党政治的挫败,产生了(使毛泽东)身体衰弱的重压,也使得(毛泽东)需要数月的静养和恢复。(36) 迄今为止,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1925年初可能都是他的成年人生活中的最低点。就毛泽东回湖南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言,它不是一个政治上追名逐利之徒在通往成功的阶梯上少了一级台阶而做出的刻意的回避,而是蕴含着这样一种质疑:在当前非革命时期,所能做的是否就是真正值得做的。
在五卅运动大爆发之际,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农村之优势的观点,为回答“为什么坚持下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新答案。在上海和广州的暴动唤醒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同志们对于无产阶级的希望,这种希望不仅在长沙引起了共鸣,甚至在韶山毛泽东偏远的家乡也不例外。从农村的中心地区,毛泽东看到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潜力,这种革命是基于对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动员。这与认为革命建立在成功的政党政治的基础上、甚至是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来革命的观点有很大区别。从毛泽东的新观点来看,国民革命的合法性——以及革命党的合法性——依赖于对农民的动员。他的注意力从最进步的阶级转向了人数最多的阶级。
受到重新定位后的湖南经验的激励,毛泽东带着使命回归广州的政党政治。他对农民的强调与统一战线和个人(尤其是已经组织农民运动的彭湃)的公开立场并不矛盾,但是显然,他现在比国民党和之前的共产党更为重视动员农民。毛泽东强调的是动员农民的必要性,他的热情和专业知识很快使他在统一战线的农村工作中赢得了领导的地位。随着北伐战争准备的升温,以及力量的平衡在广东、随后是湖南和福建的逆转,农民协会快速地发展起来,它们明确支持国民革命事业。随着毛泽东更深地介入农民动员,他对于农民运动的中心地位的信念更加坚定。只要农民动员对于北伐早期的推动力有贡献,对于破坏敌对的军阀有贡献,它就能得到统一战线的赞许。但是,由于北伐的成功吸引了军阀联盟,而农民协会继续破坏当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农村,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开始认为农民运动失控。在这一点上,在1926年末和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感觉到组织纪律性和农民动员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而他选择了农民动员。
1927年1月,毛泽东对北伐刚经过的湖南五县进行了农民运动的现场调查。当他回到广州,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7) 如果把它作为1949年农村革命胜利的预言,那么它是一个高远的和成功的预言。如果把它看成是它所声称的那样,即对北伐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协会的分析,以及对他们的力量的预测,那么它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期望一样只是一个幻想。毛泽东向斯诺承认,即使中国共产党支持农民协会,并一直奉行积极的土地政策,反对反革命也不会胜利。(38) 这个非常诚实的承认是对“湖南报告”的热情和1927年后农村革命清醒现实之间差距的判断。
“湖南报告”与毛泽东早期著作的差异,源于农民协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局势变化。随着北伐军1926年下半年继续推进,农民问题从一个总体革命战略改变为农民协会应当被严加控制还是鼓励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尤其是首个“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其战略思考是从突出政治胜利的重要性,转向强调维持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再到防止激进农民对向北突进的破坏。农民协会分散和不可控的行为不能打败反对北伐的军阀,但是他们却能破坏统一战线。对于整个领导层来说,农村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是紧迫的,因而毛泽东以农民首席专家身份代表国共两党去了湖南。
“湖南报告”使用第一人称,并充分利用了毛泽东通过长期和大量调查获得的经验权威。迄今为止对农民革命潜力的成功预测无疑增加了毛泽东的自信,带着这份自信他写下了如下的著名评论: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39)
从本质上讲,毛泽东这里的评论和报告中的细节指的是,农民协会的自发组织无论在其实力上还是在其内部对于方向的把握上,都足以改造中国所有的村庄。因此,“革命的政党”对于革命本身来说是次要的,而且他们必须跑步赶上(革命的形势)。从诸如张国焘这样的党内官僚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已经入乡随俗了。(40)
“湖南报告”和1919年“民众的大联合”之间的一致是惊人的。二者都基于自发的群众运动而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即将发生的变革。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将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两篇文章都把群众的意志和能量归因于他们被少数剥削者压迫的体验;都降低了群众动员的组织作用。虽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返回到支持无政府主义,但是一个崭新的、使组织次要于动员的革命时刻显然到来了。
在过去的八年中,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也很明显。即便组织是次要的,但组织仍然被提出来。“湖南报告”是一篇报告,而不是宣言,它的目标听众不是群众,而是“革命党”。《湘江评论》隐含的偏重于城市/大都市的倾向已经被对农村/地方性的重视所取代。最重要的是,“齐声一呼”现在被一场旨在矫枉过正的阶级斗争所取代。群众不仅知道他们的攻击目标所犯下的罪行,从而实施公正的报复;而且,一般而言,为反对前统治阶级而实施的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胎记而不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污迹。速成的启蒙被通过革命行动的自我教育所取代。但是,教育者自己即将面临一个沉痛的教训。尽管如此,毛泽东于1925-1927年对农村的重新定位对于他后来适应革命根据地是很关键的。“湖南报告”对农村革命的展望是适时的,虽然它并不是毛泽东在1927年所经历和分析的。
生存与农村革命的产生,1927-1934年
在毛泽东充满热情的报告发表的六个月后,统一战线和农民协会瓦解,中国共产党已是江河日下。关于局势的逆转有两个基本的事实必须强调指出:第一,中国共产党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与蒋介石和各军阀的冲突中已经损员90%,在城市和广大的农村中只有分散的和转入地下状态的少量残余。党的抱负已被(现实)击碎,党的世界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希望。随着关注点从当前政治转向大学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上,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学术问题。(41) 生存似乎不太可能,成功更不可想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再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重现于中国政治中,那么它的灭亡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农村革命的新范式出现在为生存而进行的实际斗争中。局势的危急倒逼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生。毛泽东早期热情参与农民动员(的经验)为农村革命道路的开辟做了准备,但正是根据在敌对的环境中求生存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才最终产生了革命的新范式。
在1927年夏的一系列失败之后,毛泽东率领余下的支持者到湖南和江西省交界的井冈山,在那里与当地两个“左倾”土匪合作。接下来的15个月内,他与地方势力和中央委员会的各种指示和特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毛泽东扮演的是老鼠的角色。(42)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于1927年8月所得出的判断反映了毛泽东谋求生存的最初努力的重点。跑步、隐蔽和射击对他而言是新的技艺。由于短期的生存获得了成功,他(开始)琢磨更长期(的生存问题)。直到1928年10月份,毛泽东才弄明白,即使是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到当地地主的所有精英都想消灭共产党,但是敌人却缺乏组织,而且他们之间也有内耗。通过把根据地建立在边界地区,中国共产党能够利用对手,因为后者在攻击中不能相互合作。毛泽东不得不在遭遇战中非常警惕军事资产(military assets)所面临的风险,但是很积极地创造机会出其不意地(攻击)和骚扰(敌人)。正如毛泽东和他的总司令朱德在1928年5月所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43)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并不是主张农村革命,而是主张农村根据地的战略作用。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与毛泽东的观点)相冲突的命令几乎与敌人一样危险。他们担心毛泽东变得过于以军事为导向、过于以农民为基础,也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太过软弱。在最后一点上他们本不该担心。毛泽东组织了赤卫队反对地主,用“红色恐怖”扩大自己的山区根据地。其他的担心是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也有同样的担心。持枪的人很容易养成军阀主义和土匪习惯,而事实上,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招募无产阶级几乎是不可能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及批评“单纯军事的观点”指出了问题,但却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无论如何,毛泽东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存置于服从遥远上级的命令之上。
1930年的事件使毛泽东从在农村地区长期生存重新定位到持久的农村革命的新范式。一方面,红军在党中央影响下试图攻打和占领江西和湖南的省会南昌和长沙,这是灾难性的失败。另一方面,最初的井冈山根据地对于人数不断增加的军队来说太小了,因此毛泽东在年初把大部分军队转移到江西南部,并于年末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新根据地,不久被重新命名为“江西苏维埃”。在城市的失败和在农村的成功使毛泽东相信,对国民革命最终目标之追求,不应该潜伏在农村等待“革命时刻”的到来,而应扩大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总而言之,这是农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俄国经验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强调这些差别。
农村革命需要能够维持军队的经济基础、适于分散和贫困人口的政治结构,以及利用当地支持优势的军事战术。经济方面的挑战要求对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做认真的调查以及重新确定土地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本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例如鸡肉的价格、革命对不同家庭的具体影响。他告诉下属:“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农村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即从消灭旧的剥削者到如何动员“绝大多数人”以维持生产。与毛泽东最初提倡的相比,有效的动员要求更为有利于中农的政策和不那么敌对富农的态度。在政治上,新的重点是避免脱离群众,因为群众的支持是革命的基本源泉。它相应地需要一个扁平化组织以避免官僚主义并在活动中关注群众。
在军事方面,农村革命需要毛泽东为持久战而开展游击战。是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但是枪是从哪里取得的呢?和政治体制一样,农村的军队必须尽量缩短与人民的距离。一个金字塔必须被建立起来:由普通民众构成广阔的底座,他们协助完成像储存食物和侦察这样的任务;民兵则呆在家中并自己种植粮食;小型机动力量是军事先头部队。因为金字塔不能移动,因此如果能“诱敌深入”到根据地,那么军队才将是最有效率的。拥有关于当地的知识以及得到当地的支持,红军就能在弱时撤退,强时进攻。
诱敌深入的一个问题是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处于危险之中,这也造成了毛泽东和新根据地的地方党组织在江西的一场血腥的内部斗争。地方领导人反对毛泽东对富农的强硬政策以及他不保卫根据地边境的战略。由于一个秘密反党组织的存在使冲突变得复杂,导致了数千人被处决。(44)“福田事件”暴露了毛泽东革命中潜藏着的残酷。然而,从长期来看,“红色恐怖”削弱了群众动员的潜力,危及了革命的成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作为一名军事领导人和江西根据地的巩固者所取得的成功,导致了他在1932年末撤出军队的指挥部。他在江西的成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发动了一系列对江西苏维埃的“围剿”运动。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任务。第一次在1931年末,有10万部队参与,紧随其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有20万和30万人的部队参与。因为红军只有约3万人,而1941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有15.6万部队,所以毛泽东成功地抵御这些攻击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他拒绝中央委员会更为冒进的让他的部队向城市进攻的要求,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当中央领导层在1932年开始从上海转移到江西时,他们排挤作为军队和党的领导人的毛泽东,让他负责管理根据地——现在已被升格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区。
毛泽东刚刚在“福田事件”中与地方反对派达成和解,自己就变成了因缺乏恰当的“左倾”布尔什维克立场而受到鄙视的地方领导人。尽管不是一个叛徒,但毛泽东仍然是一个棘手的下属。他仍然大力提倡游击战,即便在被解除军队指挥职务后,红军还是利用了毛泽东的战术击退了1933年的第四次“围剿”,引起了现在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归国留苏学生(即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不满。毛泽东的农村政策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群众动员也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批判。现在毛泽东因对富农手软以及没有把阶级斗争坚持到最后而受到批判,这与他在前一年处决的人有着相同的罪名。
尽管(或者也许是)因为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事领导职务,他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所担负的职责引发了农村革命的创新,这种创新几乎和游击战一样重要。他现在负责管理300万人——按中国的标准来看不是很多,但足以提出建立多层级的官僚和比旧的根据地更为正式的统治方式的要求。此外,军事袭击、不断增强的封锁、红军的招募,更重要的是,革命本身造成的破坏,对于(根据地的)管理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对于维持根据地(管理)有效性的依赖并不逊于对军事上取得成功的依赖。
在这一点上,如果毛泽东向西方顾问请教,他们可能会建议(他追求)更高效的管理——更好的专业化程度保持着更好的记录,等等。事实上,他曾尝试过西式的解决方案:在一次地方选举运动中“吐故纳新”。一年多以后,毛泽东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县走完成了选举”,他判断“这次选举完全失败了”。(45) 作为韦伯式官僚机构和选举活动的替代物,毛泽东发明了群众运动,并把群众动员制度化。
毛泽东的改革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发起的。1933年2月,他负责“查田运动”,本来是清查隐藏的地主和富农,从而筹集更多资金。毛泽东担心运动会进一步扰乱农村生活并降低生产。因此,他设计了一个结合了土地改革、生产和军队招募在内的全面运动,并以八县为试点。(46) 范围更广的运动将在总结试点县的成功经验后发起。在动员的高潮过后,在巩固的最后阶段开始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1933年12月,毛泽东视察了两个试点县,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不是发现了很多敌对阶级,而是尽管有大量的志愿者参军,但是生产力却提高了。(47)
1933年的“查田运动”为后来延安时代的根据地管理以及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范例。然而,毛泽东对运动所做的巧妙的转换:从又一场自上而下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斯大林式运动转变为一场和谐的和最大化(群众)参与的群众运动,最终让“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忍无可忍。从1934年1月,毛泽东被免除了所有的领导职务;一场新的、强硬的“查田运动”开始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被认为是他的绝唱,因此他从江西经验中吸取的教训尤其有趣。这次讲话的基本观点如下: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8)
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对农村革命动力的理解已经走完了一个周期:从七年前“湖南报告”中对农村革命重要性的初步感知,到作为一股地区性的和弱小的力量在谋生存中所受到的发人深省的军事教训,再到认识到群众支持不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而是一个政治的进程,在其中,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融合是一个政策目标而不是一种假定。在毛泽东41岁的时候,受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打压,他无法想象到自己还有机会将这种深刻的见解付诸实践。但是第五次“围剿”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八个月之后,江西苏维埃被放弃。
党的领导和“毛主义”的形成
1934年的第五次“围剿”对于最好的将军来说,本来是一场挑战,但却成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灾难。有超过50万的国民党部队,并有空军参与其中,蒋介石采取了新的合围战略,缓慢前进并在周围建筑碉堡。具有一些军事背景的德国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建议中国共产党从游击战转变成阵地防御,从而遭受了重大损失。与此同时,在邻近的福建省,一个非共产党军队叛变蒋介石,提出与中国共产党结成联盟。谈判开始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是否支持叛军犹豫不决,在叛军被打败之前仍然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由于不再为福建的叛军而分心,国民党得以重新调集全部力量对根据地进行绞杀。
放弃根据地的秘密计划在五月做出,8.6万远征军在十月出发。撤退顺利地进行,但在十一月末,国民党追了上来,共产党在渡湘江时损失了一半兵力。长征有了一个不吉利的开始。随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名誉扫地,毛泽东首次成为军事负责人,随后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治领导人。但是,长征、抗日战争和中国西北新根据地的(复杂)形势要求毛泽东做出深远的战略再思考。
长征的第一件事是军队在行进的新环境中的生存问题。(49) 正是毛泽东的军事生存技能,而不是他对农村革命的洞察力,使他回归领导层。长征在官方上的说法是“北上抗日”,但是红军深知自己的弱点,正在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长征绕过中国的中心地带,经过少数民族占领的崎岖山地,寻找一个偏远的、靠近苏联的根据地。然而,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从获取到的(旧)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共产党根据地的消息,毛泽东遂将自己领导的红军部队开往陕北。长征在1935年10月22日结束,最终,根据地扩大到包括延安在内。
毛泽东不再长途奔波,但是他不足1万人的部队显得很弱小,而且呆在中国西北一个偏远的角落。接受外国记者(最著名的是埃德加·斯诺)的访问,是重塑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政治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50) 对于毛泽东来说幸运的是,被指令在新的根据地消灭他的国民党军队,是被日军赶出家乡的张学良的东北军。毛泽东所号召的抗日统一战线获得了肥沃的土壤。张对反共任务消极懈怠,当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赴西安训斥张时,张绑架了蒋并扣押他,直到他答应抗日为止。虽然蒋在被释放之后(先安内后攘外的立场)有所动摇,但是,日军在1937年7月发动的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才确证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正式开始。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面对的是自1927年撤退到农村之后的最彻底的重新定位。然而。毛泽东现在面对的不是具体的生存问题,而是一个更为理论性的问题。他在湖南和江西的农村革命经验与新形势下的抗日民族战争有哪些关联呢?
重新定位的第一个问题是军事战略。以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为基础的游击战,与抗击一个并非建立在本地阶级结构上并且有着现代军队的敌人的战争,二者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最全面的答案体现在毛泽东一系列主要的军事著作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是其中的第一篇。毫不意外,毛泽东指出,农村抵抗将会是打败日本的关键,因为日本占领中国战线拉得太长。但是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军事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敦促红军要警惕势态的变化。他写道:“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51) 因而,红军是要犯错误的,但是应迅速吸取经验。与此同时,(斗争的)目标转向了外敌则要求暂停农村的阶级斗争并转向爱国统一战线。
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引出了毛泽东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的创新。每一个创新都根源于他早期的思想,但迄今为止他还未明确地表述出来。首先是实践至上。面对新的形势,毛泽东要求红军关注现实,而不是书本。正确的领导是顺应情势的适当的领导,而不是教条式地援引本本的领导。第二个是对立统一。通过提出诸如“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这些对子式概念,毛泽东为指挥官们提供了一个智识框架,它也许对于理解某种形势有用,但却不指向去做什么。因为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所以一个指挥官不能通过(对既有的)范畴的探寻为其现有问题定位。最后一个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当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时,阶级斗争是适当的,而现在与日本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主要矛盾,那么统一战线就是适当的。
1937年夏,毛泽东提炼了这些观点,并结合意识形态的读物,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毛泽东总共授课110个小时,并在授课后留下来讨论——显然,他很认真对待这些哲学内容。(52) 这是毛泽东自20年前对泡尔生评论之后,最为持续地阐述他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并没有强调自己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或者当前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哲学的创新。相反,他强调马列主义的科学性。然而,这些哲学上的努力的要点并不是为了让中国适合于人所周知的范式,而是为了证明实践的首要地位和现实的复杂性。马列主义中存在着普遍真理,但却不能从中推断出具体情况下的适当的领导。
苏联在1938年9月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人的地位,而且他的讲话和著作,已经为中央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重新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根据新形势所做出个人调整成了官方的总路线。毛泽东的思想开始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新的正统。尽管毛泽东1937年的哲学著作中的观点,如实践的首要地位、调查和试验的必要性、矛盾的可变性等,得到了强调,但是,可以说他们是标志着具有积极变革性的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与具有较为固定和权威地位的“毛泽东思想”的分水岭。
结论
如果毛泽东在1937年去世,那么他很可能在今天被当做一位中国农村革命的民族英雄而被人们铭记,因为到那时,他已经为农村革命的组织和现实(变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思想的发展或他的思考将不会被记住。然而他前半生的学习过程为他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与他1949年后的领导有着更为遥远和不太确定的联系——在“大跃进”中实践的首要地位在哪里呢?曾经反对即使是共产主义经典的“本本主义”的人怎么能容忍20世纪60年代对“红宝书”的崇拜呢?没有早期毛泽东实用主义的平民主义,就没有晚期毛泽东教条主义的过激行为,但是他们之间似乎是两个世界。
注释:
① Wolfgang Bauer,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Munich:Hanser Verlag,1971),pp.453-507.
②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New York:Harper,1967; first edition:Cambride,MA:1951),pp.7-27.
③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④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Grove Press,1973; first edi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38),Part4.
⑤ Stuart Schram,Mao Tse-tung (Baltimore,MD:Penhuin,1966); Philip Short,Mao:A Life (New York:Henry Holt,1999); Lee Feigon,Mao:A Reinterpretation (Chicago,IL:Ivan R.Dee,2002),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New York:Collier,1957).
⑥ 萧延中:《巨人的诞生》,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4-25页。
⑦ 关于这些古怪的例子的汇集,参看Short,Mao:A life,p.22.
⑧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p.90-94.中文译文根据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61页。
⑨ 萧延中:《巨人的诞生》,第26-27页。
⑩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43.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12) 根据萧三日记,毛泽东说大会的日期是4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13) Stuart R.Schram,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Armonk,NY:M.E.Sharpe,1992-),Vol.2,pp.18-34.(即本文多次提到的斯图尔特·施拉姆著的《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译者)
(14) 同上书,第18-19页。
(15) 杨在这一年的年初去世,过世后成为毛泽东的岳父,但毋庸置疑的是,对他影响力的赞颂是真诚的。在毛泽东的学生时代,杨对他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
(16) Brantly Mao's Road to Power,Vol.1,p.xxxiii.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7-18页。1951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邀请校长(张干)。
(18) Mao's Road to Power,Vol.1,pp.5-6.
(19) 同上书,第6页
(20) 同上书,第113页。
(21) 同上书,第118页。
(22)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46.
(23) Brantly Womack,“Mao Before Maoism,”China Journal 46(July,2001),pp.95-118.
(24) Mao's Road to Power,Vol.1,p.208.
(25) 同上书,第202页。
(26) 同上书,第263-264页。
(27) Mao's Road to Power,Vol.1,p.318.
(28) 同上书,第380页。
(29) Brantly Womack,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2),pp.24-27.
(30) 相比之下,1924年的国民党宣言中包含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表示赞成。Katherine Palmer,“Mao Zedong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China's Minority Policy,”Southeast Review of Asian Studies 17(1995).
(31) “Provincial Home Rule in China:Every Province Its Own Master,”North China Herald,November 6,1920; cited in Short,Mao:A Life,p.108.
(32) Mao's Road to Power,Vol.2,pp.5-14.
(33) 被毛泽东引用,Mao's Road to Power,Vol.2,p.8.
(34) 同上书,第11页。
(35) Tony Saich,ed.,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NY:M.E.Sharpe,1996),pp.27-28.
(36) Schram,Mao Tse-tung,p.78.
(37) 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参看Mao's Road to Power,Vol.2,pp.429-464;或者参看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23-59页。
(38)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64.
(3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24页。
(40) 张国焘: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Vol.1(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71),pp.596-615.而对于毛泽东而言,他认为中央对于农民协会的态度“暗示着有些东西是反革命的”。
(41) 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42) Stephen Averill,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6).
(43) Mao's Road to Power,Vol.3,p.155.
(44) Stephen Averill,“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NY:M.E.Sharpe,1995),pp.79-115.
(45) Mao's Road to Power,Vol.4,p.335.
(46) Womack,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pp.161-172.
(47) Mao's Road to Power,Vol.4,pp.584-640.
(48) 同上书,第716页;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49) Harrison Salisbury,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New York:Harper & Row,1985).
(50)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或者参看Mao's Road to Power,Vol.5.
(51)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载Mao's Road to Power,Vol.6,p.394.
(52) 参看Nick Knight,ed.,Mao Zedong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Armonk,NY:M.E.Sharpe,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