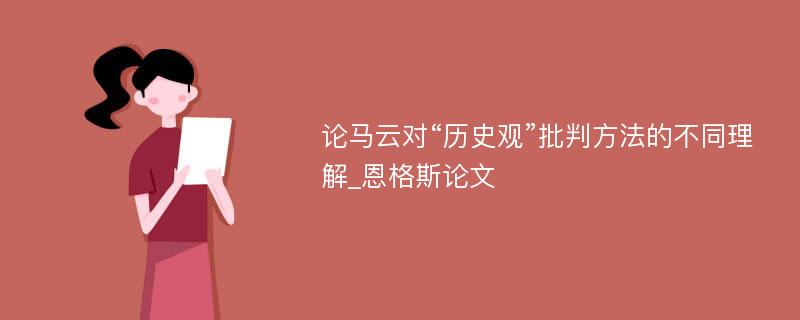
试论马、恩对“历史的观点”批评方法的不同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批评论文,观点论文,方法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2)05-0028-04
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文学作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艺批评方面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最早强调研究文学艺术要关注“历史”因素的是马克思,他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谈到,“五观感觉的形成是已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P126)。虽然这里的“历史”还仅仅局限在对美感产生原因的考察上,没有明确其是一种批评方法,但却为后来的“历史的观点”的提出,具备了方法论的意义。真正把“历史的观点”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明确提出的是恩格斯,他分别在评价德国作家歌德和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提到,“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2](P258)“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3](P587)由此可见,这个由恩格斯提出来的、由马、恩共同创立的“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经典批评方法,并在以后的批评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主要的文艺批评方法。
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主义观点。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文艺批评中的具体运用。“历史的观点”虽然是由马、恩共同创立的,但两位导师却存在着对这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理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本位与社会—历史本位
虽然马、恩都主张把文学作品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但在这一考察中,马克思更倾向于主体本位,而恩格斯则更倾向于社会—历史本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是作为一种先进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而出现的,它由从前的以“物”为中心,转到了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实践意义的伟大,因为正是人的实践才把主观和客观、社会和自然、精神和物质联系起来。反映在文艺批评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采用“历史的观点”,把作家或作品放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来加以分析,挖掘出作品或作品人物身上所包含的时代的、社会的、特别是阶级的内涵,从而对文学作品生发出精辟的见解。但是也应看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的发展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但马、恩对待“规律”的态度是不同的,一方面是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对这一“规律”的促成上,表现在文艺批评上就是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具体地讲也就是要看到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则还表现在对这个“规律”的遵循上。即在强调“规律”客观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对人的主体性有所忽视的一面。究竟是“人能弘道”还是“道能弘人”,在这一矛盾点上,马克思似乎更倾向于前者,即主体本位;而恩格斯似乎更倾向于后者,即社会—历史本位。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主体性特别加以肯定,“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P125-126)。“人的类特性恰恰是自由自在的自觉活动”[1](P96-97)。这是马克思的主体性哲学观。那么反映在文艺批评的实践上,马克思仍然强调文学的主体性。首先马克思认为创作主体即作家应具有充分的创作自由,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谈道:“你们赞赏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3](P7)其次,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对主体的尊重,表现在强调人的个性,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上,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强调文学创作要向莎士比亚学习,要塑造出个性丰富的人物形象。第三,强调文学发展的独特性和本体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关于艺术,大家都知道,它在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4](P112)。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针对伏尔泰创作史诗失败时说道:“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5](P296)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反对把文学等同于社会发展的庸俗观点的。
另一方面,恩格斯则倾向于社会—历史本位,这具体表现在,首先是过分强调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的社会身份甚至是阶级身份。“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一定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2](P259)。如恩格斯说歌德是“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2](P257-258)。“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11](P463)。这种过分强调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的做法,必然影响到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其次是过分强调作品思想内容中社会现实成分。也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谈道:“而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将来才能达到,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可见同样是要求拉萨尔学习莎士比亚,恩格斯更强调把莎士比亚当成一种艺术表现手段;第三是强调文学的发展观念。“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3](P582-587)。由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文学的发展观是持肯定态度的。
二、辩证中的统一与辩证中的对立
应该说“历史的观点”批评方法比其它批评方法较为科学的地方就在于它对辩证法的运用,因为这种批评方法在批评实践中,是把作家和作品放到具体的历史发展中去,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具体的辩证分析,既看到所批评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也看到其局限性一面。但是在具体运用上,马克思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中似乎更强调统一;而恩格斯似乎更强调对立,具体地说就是在批评实践中运用了“二分法”。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正如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的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P123)。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P120)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在辩证的关系中,更倾向于统一,这样的辩证观点一旦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上,就会生发出精彩的评论,如马克思在评价希腊神话之所以具有魅力的原因时谈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起来。困难的是,他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是就某些方面说来还是一种规范和不可及的范本”[4](P113)。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强调了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同时更看到了文学的独立性和难以超越性。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时,马克思认为剧本中的情节和人物要“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3](P574)。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非常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时作为具有诗人天赋的马克思更多地是钦佩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价值,因为在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个性塑造得最好。可见马克思更多关注的是作品的艺术性,现实性是通过艺术性而得到实现的。
恩格斯在辩证统一中更关注对立性,并进行了简单的“二分法”处理,就在同样是评价拉萨尔的剧本上,恩格斯则把文学的艺术性简单地看成是内容和形式及其相结合问题。虽然恩格斯也认为,“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3](P215)但这里的莎士比亚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代名词而已,因为席勒代表观念即非现实,在这里莎士比亚和席勒的对立已经变成了“现实”与“观念”的二元对立,那么“现实”是什么呢?那就是处在不同社会地位即阶级的人,其价值观念和其对自由与欲望之间的冲突,其实也就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二元冲突,如果说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二者处在统一中,那么在恩格斯的实践观中则是对立的。辩证法也就变成了按照人的阶级地位来确定其世界观价值的大小,进而确定其艺术价值的大小。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他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就已有了明确的表现,他早在评价歌德时就认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2](P257-258)。在评价巴尔扎克时也是如此,“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同情都在注定要消灭的那个阶级方面……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这些雄辩有力的分析初看上去是非常辩证的,但是,在这种看似辩证批评中我们也看到简单化的“二分法”的弊端,并且在这种对立中恩格斯也不是平等看待的,而是重视人的社会性而轻视人的自然性,而人的社会性又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性。因此,按照这种评价,就必然走上极端化和片面化。
黑格尔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6](P302-303)。从共时性的角度讲,黑格尔重视人物性格中对立的一面,但更重视人物性格中统一的一面,即多方面性格的完整地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恩格斯虽注重人物性格的两极对立,但从实际上来看,现实中的人和事物是极其复杂的。人物的性格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当我们只强调人物性格的两极化时,虽然比起古典主义的类型化人物性格复杂了一点,但还是不够的。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讲,黑格尔所谈到的人物性格是发展变化着的,把人物性格看成是一个不断对立统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人物丰富而复杂的个性特征。而恩格斯是从相对静止的观点来看待人物性格中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则带有永恒性,因为恩格斯用社会身份(出身)来确立人的性格特点,而人的身份(出身)则是一个相对稳定(确定)的东西,很难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人物性格也是相对不变的,并且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就是在这对人物两极性格的分析中,也不是公允的,而是仍然把人物出身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看作是人物最为基本的性格。之所以如此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实践内容,到了恩格斯这里更加狭隘化了,恩格斯把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实践内容仅仅看作是一种阶级斗争,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动力仅仅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认为的,“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P66)因此,这种把实践内容狭隘化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文学批评中的庸俗化,从而也必然使“历史的观点”中的“辩证”批评,将以“二分法”的形式,走向新的形而上学化。
三、认识价值、社会价值与革命功利性
虽然马、恩都看到并肯定了在文学作品中的“倾向性”问题,但马克思更倾向于认为文学的“倾向性”应等同于文学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恩格斯则更倾向于文学的“倾向性”应为革命功利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对此的理解是不同的。马克思所认为的“倾向性”是和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及其认识价值相关的,如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时说道:“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8](P686)马克思更关注的是文学的认识价值,是作为主体的人(作家)的实践能力,也即对繁茂芜杂的社会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对于人来说是另一种“自然”,是有机的“自然”,因此就和面对无机的自然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并且艺术比起科学来说,更能充分地体现人的主体性特征,因为艺术不但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对象化,而且还体现在人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作,文学艺术更能实现人的本质。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其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同时马克思反对把文学作品的“倾向性”等同于“功利性”,“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它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个人的生存”[9](P160)。
恩格斯对于“倾向性”是怎样理解的呢?他在《致敏·考茨基》一文中谈道,“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10](P385-386)。恩格斯的这段话对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给予了有条件的肯定,虽然强调了艺术性的重要性,但恩格斯更关心的是作品的思想性。因为在这同一封信中恩格斯还谈到,“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0](P385-386)。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关注文学的思想性已变为关注文学的政治功利性。本来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采用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评价文学作品,就会忽视文学的本体性和主体性,因而也就违背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恩格斯会极力贬低左拉而抬高巴尔扎克。还是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说道:“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11](P269)那么巴尔扎克就真的比左拉伟大吗?这应该说是很难说的事情,因为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创性,都有对文学审美形式的独特贡献,巴尔扎克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被金钱异化的社会,而左拉则描写了一个被自然欲望所充斥的社会,因此我们很难说某个作家比某个作家更伟大,而我们只能说的是他们风格不同。但是,恩格斯之所以要这样做,硬要分出伟大和次伟大来,这是因为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金钱罪恶的揭露,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更有利于从社会主义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由此可见,这里的“倾向性”已经变成了“功利性”,并且由文学创作的目的,变成了文学批评中的标准。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都肯定了文学的“倾向性”,但二人对此的理解存在着偏差,这种偏差对后来的继承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我们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观点”的文艺批评方法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并且一直到现在也还仍然是我们当代批评家们最为常用的批评方法之一。但我们还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对于“历史的观点”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不承认这种差别或回避这种差别,就不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这一经典性的文艺批评方法。
收稿日期:2002-06-06
标签:恩格斯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巴尔扎克论文; 文化论文; 莎士比亚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