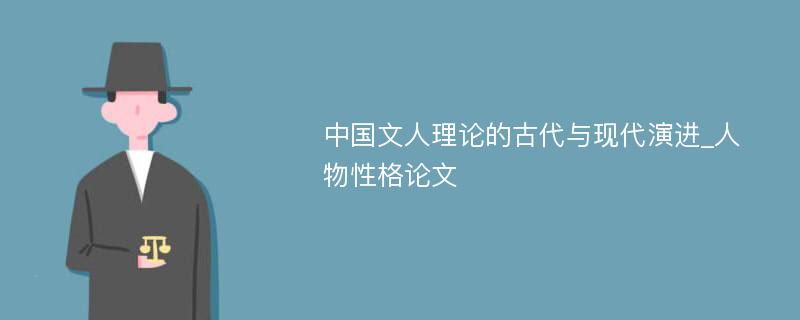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中国论文,写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叙事”理论被炒得火热的今天,实可与之比肩的中国“写人”理论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古往今来,人们围绕“写人”问题展开过种种集结着智慧的评论,并构建了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动态话语系统,形成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
一、形神论:依傍画论的初期“写人论”
在强调“表现”和“写意”的传统文论中,即使是叙事功能较强的史传理论,也不免突出“发愤著书”的抒情愿望,史学家们展现给我们的创作思想主要是强调写人中的精神寄托等问题,很少为我们提供切实可操作的写人理论。这样,来自绘画的“形神论”就相对滞后地成为中国文学写人论最初的核心话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在《淮南子·说山训》有关形神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传神写照”、“颊上三毛”、“点睛”以及“以形写神”等绘画法式;随之,谢赫《画品》提出了“气韵生动”等与“形神”论相配套的绘画原则,标志着绘画理论中的形神论基本走向成熟。唐宋以后,随着小说创作对“传神”等艺术境界的追求,形神论画理便被得心应手地借用到小说“写人论”中。据现有文献资料考察,唐代传奇《任氏传》谈到写人时向往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就已包含着形神意识。北宋赵令畤《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在评价小说《会真记》中的崔莺莺形象时进而指出:“夫崔之才华婉美,词彩艳丽,则于所载缄书诗章尽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态,则不可得而见。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1](P57)这里所谓的“不可得而见”的“都愉淫冶之态”,就是“气韵”、“神态”,而“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则是这种描写所达到的传神效果。南宋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时也主要从形和神两个角度展开。如他评“何晏七岁”一则说:“字形语势皆绘,奇事奇事。”对语言动作之“形”叹赏有加;评“谢车骑道谢公”、“谢公尝与谢万共出”等条则用了“意态略似”、“极得情态”等批语,分明有强调“以形写神”的用意。[1](P74-76)到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年间,随着中国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空前发展,形神论历史地成为当时“写人论”的核心。李贽是较早且有较大影响地直接征用“传神”等画论术语来批评小说戏曲者。他在《初潭集又叙》中评论《世说新语》和《焦氏类林》两部小说时说:“今观二书虽千载不同时,而碎金宛然,丰神若一。……譬则传神写照于阿堵之中,目睛既点,则其人凛凛自有生气;益三毛,更觉有神。”[2](P2-3)此将绘画形神论的重要术语一古脑儿借用过来,突出了两部小说的写人效果。袁无涯本《水浒传》“李贽”评基本贯彻了“形神兼备”的思想,如第三十八回眉批评关于李逵“黑凛凛”的描写说:“只三字,神形俱现。”[3](P1404)当然,这些评论还只是只言片语,没有充分展开阐释。在容与堂刊本《水浒传》的评点中,“如画”、“传神”、“入神”之类关于人物传神描写的眉批、夹批随处可见,如《水浒》第二十四回针对潘金莲因武松警告而恼羞成怒地骂武大一段文字,有眉批说:“将一个烈汉、一个呆子、一个淫妇人描写得十分肖象,真神手也。”同时,还有三十三个“画”字的夹批。[4](P742)这都足见题为李卓吾的评点者对小说传神笔墨的高度重视。此后,以“形神”为尺度的批评文字触处可见。如谢肇淛《金瓶梅跋》评《金瓶梅》之写人曰:“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1](P172)王世贞在评《琵琶记》时说:“各色的人各色的话头,拳脚眉眼,各肖其人,好丑浓淡,毫不出入。”[5](P288)汤显祖在《焚香记总评》中也说:“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手!”[6](P1659)至晚明,形神论已步入成熟,并在以后的文学评论中显现出极强的生命力。清代的小说戏曲批评家多用形神论来作为自己批评的主要话语。如《红楼梦》甲戌本第三回眉批评关于王熙凤的容貌描写曰:“试问诸公,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追像至此者?”[7](P75)一直到清末,吴趼人还颇为自赏地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二回的评点中说:“写苟才如画,有颊上添毫之妙,令读者如见其人。”[8](P87)实际上,时至今日,以形写神、形神俱备等仍然是评赏文学写人艺术效果的重要关键词。
中国文学“写人论”的第一主题之所以依傍绘画形神论展开,主要是因为文论家们善于综合运用触类旁通思维的结果,也是他们为抬高小说戏曲地位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二、性格论: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明末清初,金圣叹继承并发展“形神”论的基础上,标举出“性格”说,从而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一种新的理论并非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表现出对前有理论的嬗变式师承,这正是古今演变命题能够成立的基础。应当说,传神之“神”,本身就包含着个性的鲜明性,只不过并未加以突现而已。在金圣叹之前,如前引王世贞所言“各色的人各色的话头”,“好丑浓淡,毫不出入”云云,就涉及了有关不同性格的问题。特别是容与堂《水浒传》评本第三回总评提出的“同而不同”论,更是明显地强调了人物性格的不可重复性:“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4](P107)作者赞不绝口的就是在人物性格创造中表现在派头、光景、家数、身份等各层面的不可混淆性。正是在此类论说的基础上,金圣叹于《读第五才子书法》旗帜鲜明地推出了他的“性格”论:“别一部书,看过一篇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9](P9)这句话向来被视为金氏评点《水浒》的总纲领,强调写出人物生动的“性格”是一部小说创作成功的主要标志。相对于形神论而言,金圣叹的性格论更强调挖掘人物内在的气质、精神。如他指出:“《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9](P12-13)同时,他在评论武松这个形象时流露了更丰富的“性格”思想:“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小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9](P1395-1396)这不妨视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性格兼容论。其理论贡献在于评点者初步看到了人物性格塑造的多元复合性。
尔后,尽管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的批评也多处认真地讲到人物的“性格”,如第二十一回回首总评论刘备和关羽说:“两人同是豪杰,却各自一样性格。”[10](P221)但是,他们的评点更重在强调“性格”之“格”的一面,他们从明代沈际飞《牡丹亭题词》所谓“柳生騃绝,杜女妖绝,杜翁方绝,陈老迂绝,甄母愁绝,春香韵绝”的评语那里受到启发[11](P251),从道德、智慧的角度提出了主要人物的“三绝”说,即“智绝”孔明、“义绝”云长、“奸绝”曹操”[10](P16-17),将人物品格与才能的主导面加以放大,将现实性格的“超载”之“绝”上升到理论高度。这种“性格”学说似乎有违生活逻辑,因而一般被人们视为“性格”论的倒退。张竹坡对“性格”论的推动表现为他在胡祗遹、王骥德、叶昼、李渔等人关于“情理”说的基础上作了充分的发挥和应用。其《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说:“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12](P1503)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的“情理”就是创造人物形象必须遵循的性格逻辑与生活逻揖。脂砚斋关于《红楼梦》的评点从发掘人物的独创性入手,将“性格”论继续引向深入。庚辰本十九回夹批都有这么一段话:“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二人终是何等人物。”[13](P1413)这段话虽然主要还是从人物道德化侧面来大谈特谈人物性格,但其关于宝玉、黛玉性格的一系列“说不得”之论,已经触及人物性格描写的复杂性问题。所谓“说不得”云云,绝不是可以剥离的几重性格的叠加,而是难以辨明的多重性格的有机浑融。根据对性格的这样理解,他于四十三回夹批中反对把人写成“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13](P988),而于第二十回夹批中提出,“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13](P448)这就意味着,成功的人物性格塑造不在于所写对象是好是坏,也不在于其完美程度,而在于能够揭示出社会生活中人物性格特质的不同方面,显示其复杂性。20世纪初,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沿着脂砚斋的路数继续反对十全十美的性格论:“古来并无真正完全之人格,小说虽属理想,亦自有分际,若过求完善,便属拙笔。”[14](P266)鲁迅先生也深受《红楼梦》及脂评“写人论”的影响,从称赏《红楼梦》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这一传统创作格局出发[15](P306),极力推崇人物性格描写的多元化。后来,这种较为科学的“性格”理论不仅在“典型”论中摇荡着身影,而且还搭乘上新时期引进西方有关范畴的快车,直接开启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
可见,中国“写人论”所谓的“性格”有的侧重于以气质与情调为基本内涵的“性”,有的侧重于以品格与人格为基本内涵的“格”,有的则是“性”与“格”二者的交糅。
三、典型论: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细化及单极化
20世纪以后,中国“写人论”健步跨入了“典型”论的时代。从此,人们不仅经常拿着“典型”这把引进的标尺去衡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否符合典型化的水准以及估价其典型化的程度,而且还根据对“典型”各有侧重的阐发和理解来为现实创作和批评提供种种未必得当的定律,从而使“典型”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世纪性文论关键词。
从字源、词源上讲,“典”主要指“规则”,而“型”则主要指“模型”。由二者拼合而成的“典型”一词,也作“典刑”,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如《诗经·大雅·荡》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郑笺曰:“……虽无此臣,犹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16](P286)指旧法常规,后来引申为模范、典范。我国古代文论不大使用“典型”一词,即使偶尔使用,也多指成法或模型,而不是一个文论范畴,如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评《世说新语》《酉阳杂俎》说:“其叙事文采,足见一代典刑。”[17](P264)这里的“典刑”是成法、旧规之意。金圣叹在《水浒》第三十一回评武松送宋江时借用了上引《诗经》中的成句,第一次拿“典型”一词评论小说人物[9](P1752),后来,张竹坡在《金瓶梅》第八十六回行批评陈敬济时也说:“又一个要偷娶,西门典型尚在。”[12](P1277)这几处使用的“典型”的基本含义是“故法”,虽然同样不是作为一个文论范畴来使用的,但已经包含着共性与个性的因子。同时,在“典型”一词未被当作文论专门术语来运用前,典型意识已经存在。人们早就指出过,“同而不同”论就包含着一定的个性与共性因素,而金圣叹所谓的“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与别林斯基在《同时代人》所讲的“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识的陌生人”那句话,也已达到了认识上的惊人一致。因此,传统民族文化有机体本身的自觉力量成为这一理论赖以生成的基因。
尽管如此,“典型”一词毕竟是舶来品,其内质已大大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性格论。在“典型”定名之前,我国文艺理论界的先知先觉的评论家们已经开始吸取西化“典型”观念来探讨中国文学作品了,如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最后一部分论贾宝玉时就提出“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各人之名字之下”[14](P165),已经初步涉及典型的个性与共性问题;大约与此同时,收录于《小说丛话》的侠人关于小说创作的一段话说:“今明著一事焉以为之型,明立一事焉以为之式,则吾之思想可以瞬息而普及于最下等之人。”[14](P64)这里谈到的“型”和“式”的“著”和“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艺术典型的创造,“典型”一词呼之欲出。1914年,成之(吕思勉)的《小说丛话》在提到《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时也指出:“所谓十二金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十二金钗所受之苦痛,则此十二种人物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所受之苦痛也。”[14](P378)而他在该文中反复讲到的“代表意义”更不妨视为典型普遍意义的代名词。“典型”作为“成品”引进,始于鲁迅先生。对此,叶纪彬先生曾经指出:“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引进‘典型’这一作为美学范畴概念的,应首推鲁迅。鲁迅先生于1921年4月15日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直接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18](P294)“典型”论的风行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译介了恩格斯的有关论著之后。从此,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致敏·考茨基信》中的“每个人都是典型,而又有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这两封信中的两句话几乎被当作创作和批评的金科玉律,成为中国现代“写人论”的主要理论依据。
“典型”宛如古希腊的不和女神厄里斯,引发了中国文艺界数次大大小小的争论。先是1936年在周扬和胡风之间围绕人物性格的共性和个性的不同理解展开论战。虽然各有其片面性,但可贵的是,他们一开始就从恩格斯、别林斯基、高尔基等的典型论以及中外著名作家作品的创作实际出发,并特别注意总结鲁迅的典型创作经验和成就,这就为此后典型问题的研究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写人论”现代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式典型研究热潮的掀起,人们提出了典型的个性化问题,确立了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观。虽然这个阶段的探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也已经流露出崇尚完美英雄的端倪。1956年,何其芳有意回避了是否写英雄的敏感区,在《论阿Q》一文中通过批评一些论者“不知道文学上的典型人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只是他的性格的某一种特点在起着作用,并不是他的全部性格,而全部性格又并不全等于他的阶级性强调性格共性,却企图都从他的阶级身份去得到解释,因而把争论都纠缠在给人物划阶级上”的做法,提出了他有名的强调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共名说”这一派生话语,在求同的框架里强化了求异的成分,从而将典型从阶级性的基本话语中解放出来。[19](P12-14)不过,这种观点不久就引来非议,“典型”论的视域再度被禁闭。在60年代,蔡仪提出的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说被大多数人接受为描写典型的指针。期间,邵荃麟针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小说创作中的虚浮、肤浅的不景气现象,提出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中间人物论”。这种为数不多的超越主流话语的派生性话语认识到了人物阶层的复杂性,可惜并不能容于那个时代。特别是到70年代,在政治话语的强力干预下,“完美性格”说霸占了文坛,典型论彻底跌入神话人格的深渊,单极化“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模式得以确立。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典型论”政治化的危害及其所处的困境,便采取种种办法来拯救,除了李泽厚先生进行的对“必然与偶然联系”的新阐说外,典型的泛化也是其中的一招。于是,“典型性格”、“典型环境”等命题纷纷涌现。20世纪90年代后,尽管“典型”的危机已不可避免,但由于它长期居于“话语霸权”地位,故而其影响依然存在。
总之,“典型”论既是传统“写人论”的西化,又是传统“写人论”的细化和深化。尽管其政治化倾向一度给人们的身心带来很大伤害,但是由此生发的艺术典型、文学典型、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典型形象、典型性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典型化等一系列概念,使中国写人论得到不断的深化和细化。
四、多重论:中国“写人论”话语的新变及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在冲破种种社会化批评的遮蔽后,开始全方位借鉴西方各家文论来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于是,各种日趋人文化的“多重论”以及与之相仿佛的“面面观”、“组合论”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中国“写人论”的主题。
当时,随着人们逐渐对那个热衷于创造政治神话时代的远离,种种关于“英雄”的迷信的破灭,人们首先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文艺探索书系”的编写和发行来清算“典型”论的过失,传统的“性格”论被重新推到历史的前台。其中,系统论成为性格分析的主要助力。如林兴宅于《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的《论阿Q性格系统》,运用不同系统的专门理论剖析了阿Q性格的多维性,打开了人们评论人物性格的视野。与此同时,英国小说理论家佛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提出的性格理论进一步开启了人们关于“性格”研究的思路,在文论界再度产生了纠偏的效力。在种种新话语频出的背景下,1983年刘再复开始提出他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一方面从系统学说出发,指出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这些性格元素又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即形成各种不同比重、不同形式的二重组合结构”[20](P60);另一方面,积极接受《小说面面观》中的“圆形性格”和“扁形性格”等观念,并以此解答了困人很久的一系列性格论问题[20](P478-479)。虽然刘先生一时还没有彻底抛弃当时仍在走红的“典型”概念,但已不再固守这块阵地,而是有意识地通过传统性格论的重新发掘来营造自己的理论地盘。还未等“性格组合论”画上句号,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初见成效以及商品经济对人们真实生存条件的改组,文学共同体内的“大写的人”不仅面临着现实经济潮流所改变的文学内部变更的挑战,而且还遭受着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一方面,原有的关于“人”的想象关系解体,超越现实的理想化英雄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时空,于是,“典型”论万般无奈地遭遇到瓦解性的解构;另一方面,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以及文学创作模式也趁机蜂拥而入,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饱览了西方一个世纪左右的文学新思潮。传统社会性文学批评的空间被挤占,“典型”论所关注的人物的社会属性,即有关“写什么”的问题被淡化,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和情感性的“怎么写”问题受到特别关注。时至上世纪90年代,“性格”被当作解构“典型”的工具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也旋即被解构。人们在西方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开始了价值重估的探险历程,“大写的人”再度遭到冲撞,表现人的顽强欲望和本能冲动的“小写的人”得到了全面高扬,过去走红一时的典型化被心灵化所取代。
在全球化语境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将文学放在大的文化研究视野中会获得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文化研究随即兴起,进而为中国“写人论”的新变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以及西方原型批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强力渗透下,文化身份问题成为中国“写人论”的一个热门课题。当然,双重文化身份或多重文化身份的探讨既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又是民族传统文论中储存的人物角色认同的活力素使然。中国文论一向突出人物的角色性,如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九回总评通过比较分析指出:“施耐庵、罗贯中真神手也,摩写鲁智深处,便是个烈丈夫模样;摩写洪教头处,便是忌嫉小人底身份。”[4](P301)极力称赞《水浒传》写人逼近生活原型。又如,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则把“人”上升为戏剧“脚色化”的高度来认识:“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12](P1472)这些批评或者把人物摆在某一阶层认识,或者赋予他们以某种身份,或者将他们纳入某种道德归属或性情类别。这种未得到理论升华的角色意识一经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以及原型批评等理论的催化,顿时焕发出生机,“人”的角色性在“写人论”中得到了强调。当然,今天人们所关注的“人”不再仅仅是古代文论中社会化的“人”,而是现代话语背景下肩负着“多重文化角色”的“人”。
总之,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删汰,中国当代“写人论”已经形成了范式多样、话语丛集的多重论格局。也许我们将该时期的“写人论”定位为“多重论”似乎还显得为时过早,但这种命意足以使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所呈现出的繁花似锦的“无主题变奏”特征。
五、以形写神:中国“写人论”的气脉贯通
尽管中国“写人论”的主流话语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异,但却始终有一股气脉或暗或显地贯通其中,那就是“以形写神”。从“形神论”到“性格论”、“典型论”、“多重论”,一路下来,在人们已经逐渐远离画论“形神”的过程中,却在不断地用更新的术语来衍义着“形神论”这一精髓。
来自画论的“形神”之所以具有活力甚强的穿越性,首先自然与画论话语本身的相对稳定性有关。“以形写神”论自魏晋形成以来,得到后世画论家万变不离其宗的阐发,直到今天仍声音犹存。同时,有些“写人论”者本身也是画论家,如李贽在忙于戏曲小说评论时尚有《诗画》之类的评画之作明确指出:“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21](P216)这理所当然地增强了评画与论文在写人“形神”问题上的亲和感和融通性。当然,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评画还是论文,围绕“以形写神”的各种论调都是我国古代美学追求“写意”的特征在“写人论”上的反映,与西方的写实性美学所追求的重形式批评的传统正好形成鲜明对照。
在“形神论”、“性格论”那里,人们已经从“形”“神”相对论角度将“神”的本质定位为“形”背后的所以然,即所谓形而上的“神似”。在“神似”的倡导下,“如画”、“逼真”、“肖似”、“近人之笔”、“人情物理”等大致处于同一层面的话语在古代戏曲小说的评点中一再出现,“白描”、“犯中有避”、“比衬”等达成“神似”的种种艺术手段,亦即所谓的“活法”,也被顺手拈来捧场,而“千古若活”、“个个活跳”、“活起来”、“真如活现”之类的话语则成为有关戏曲小说人物成功创造的至评。容与堂本《水浒传》提出了关于人物描写的“千古若活”观。而关于“若活”的具体表现,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一回总评中说:“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如向希大说:‘何如?我说……’,又如‘伸着舌头道:爷……’。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12](P4)这样,“若活”以及可以视为其基本内涵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等话语便成为关于文学写人达到“形”“神”高度统一境界的具体描述。后来,这种话语得到人们不厌其烦的征用,如邹弢《青楼梦》第一回回评说:“写幼卿处纯是白描,追魂夺魄之笔,如见其人,如闻其声。”[22](P3)简直与张竹坡发出的是同一声音。解放后,在“写人论”中要求人物“活起来”、“立起来”的呼声越来越高。如,老舍在《人物不打折扣》中讲:“故事不怕短,人物可必须立得起来。”[23](P103)方柯《论性格系统》指出:“描写人物性格的整体特征的成功标志是人物性格具备了‘神韵’,人物性格活起来了。”[24](P32)诸如此类的论述不胜枚举。无论是原初的“神似”,还是演化而来的“若活”,都是建立在“形神”论基础上的关于写人问题的修辞性认知,用以指示文学写人所达到的逼真程度。另一方面,“形神”还是人们对文艺进行的生命化分解,在这个意义上的“神”即是附着于人物之“形”的形而下的“精神”、“神气”以及“个性”。在“神”的这层内涵被打开后,与之相关联的“神韵”、“风神”、“风致”、“生韵”、“气韵”、“生气”等等一系列术语常常被人们拈来形容文学写人所达到的鲜活状态。“形神”说自然会把人物的个性神情推为高于“形”的艺术指标来表现和追求,“性格”论也无法抵挡住这种诱惑。其中,上文提到的金圣叹就曾专门以“神理”来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应景性。而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更是认为作者善于“为众角色摹神”、“现各色人等”[12](P1507),这是“性格”论中的“传神”说。脂砚斋也不例外,如他一方面在《红楼梦》第十八回以双行批的方式认为:“《石头记》传神摸(摹)影全在此等地方,他书中不得有此见识。”[13](P382)另一方面又通过第十九回双行批针对具体人物的评点,以“情不情”说宝玉,以“情情”指黛玉”[13](P413)这就既着眼于“形神”说,又落脚于“性格”论。一句话,以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为代表的“性格论”评点家无不以“以形写神”为评论小说写人的尺度。在有关“典型”的探讨中,人们大多只是根据恩格斯的话将典型概括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分歧的存在也只在于这种统一是以共性为主还是以个性为主等方面。至于关于共性内涵的探讨也没有离开是阶级性还是性格类型性、是普遍人性还是人性和阶级性的统一等一系列纠缠不清的问题。统而言之,诸端诸层之探讨都没有离开一个“性”字。我们知道,中国“写人论”通常是将所谓的“神”、“性”、“情”等观念捆绑在一起来运行的。也就是说,中国“写人论”向来通过表现个性来支撑其传神理论体系。这样,“典型”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是一个“神”字。值得注意的是,典型论者们似乎更注重用“鲜明生动”、“点睛之笔”等现代化的话语来指代这个“神”,如蔡仪认为:“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的所以是典型人物,不仅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而且以鲜明的生动而突出的个别性,能够显著而充分地表现他有相当社会意义的普遍性。”[25](P281)所谓的“鲜明”、“生动”、“突出”等修饰语大致包含着强调形神兼备的意味。新时期的性格组合论、多重性格论也无不把“神”当作最高追求,充分显示了中国“写人论”在“形神”问题上的强大历史惯性。可见,从天赋的“性”,到伦常化的“格”,再到政治化的“型”,乃至多元化的“文化身份”,中国古今“写人论”紧紧抓住“形神”二字作文章,从而形成最能展现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
当然,我们在张扬“以形写神”的优长时,也不能不看到其疏短之处。就“以形写神”的提法本身而言,人们很容易造成重神轻形的误读和偏解,从而不时地导致文学写人误入歧途。“性格”论之所以一度被敷衍到“绝”境,“典型”论之所以曾经被带入单极政治化的迷途,就是人们在对“形神”进行局部的细化、深化过程中片面追求“神”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借助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策略来纠偏还原,使中国的“写人论”体系更加健康地运转。
总之,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它一方面保持着不断进化变革的活力,另一方面又延续着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气脉。
